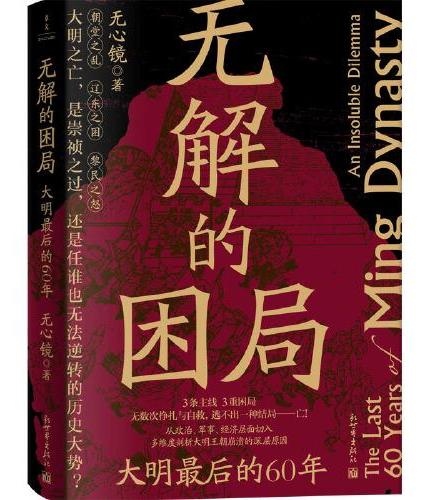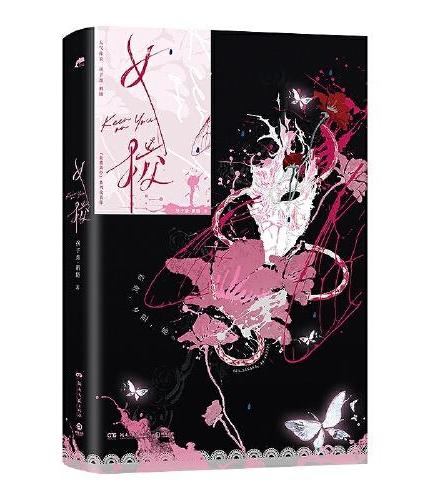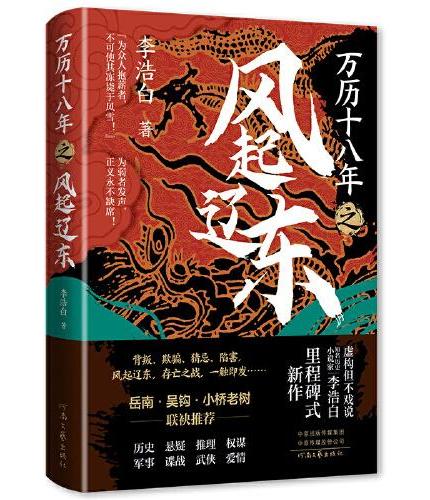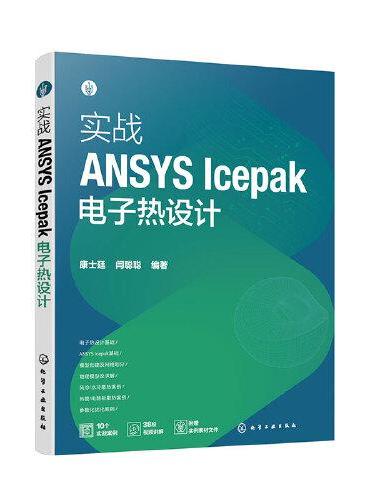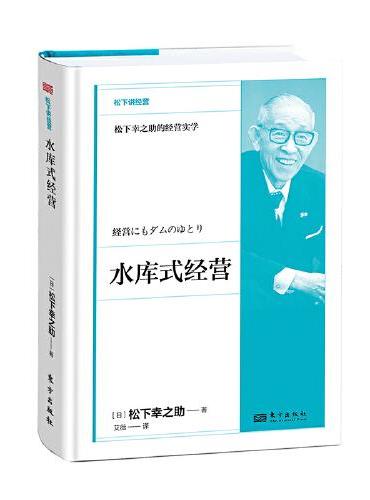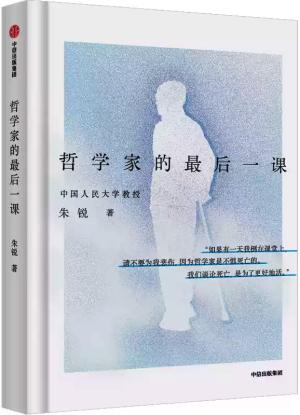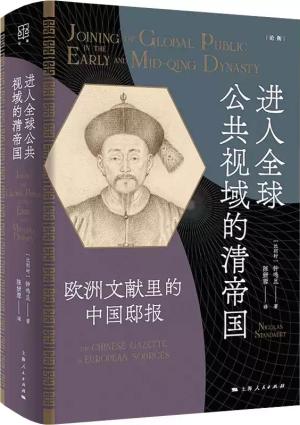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一群数学家分蛋糕:提升逻辑力的100道谜题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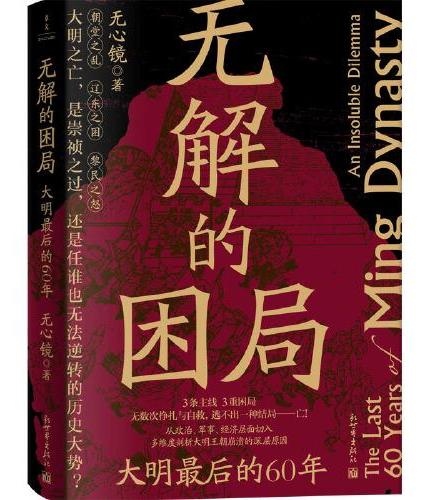
《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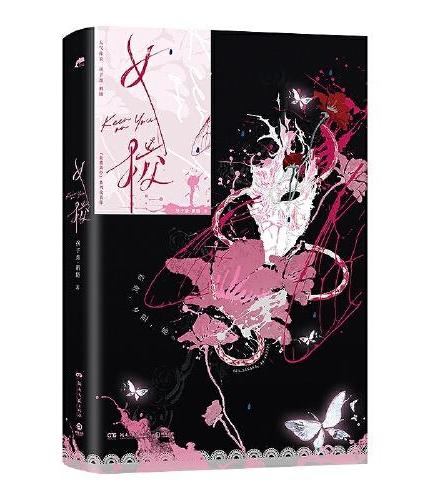
《
女校(人气作家孩子帮·鹅随“北番高中”系列代表作!)
》
售價:NT$
2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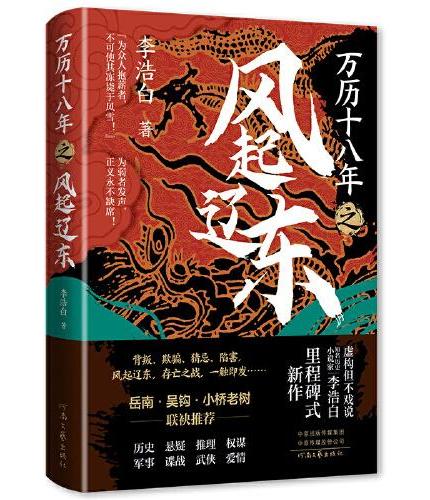
《
万历十八年之风起辽东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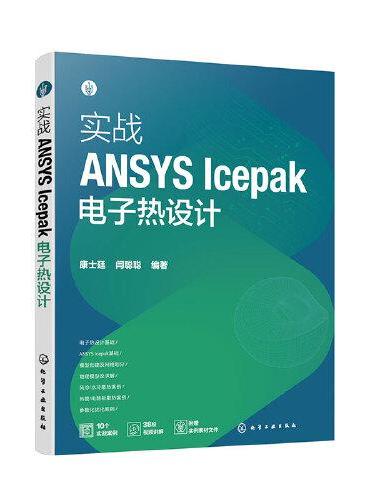
《
实战ANSYS Icepak电子热设计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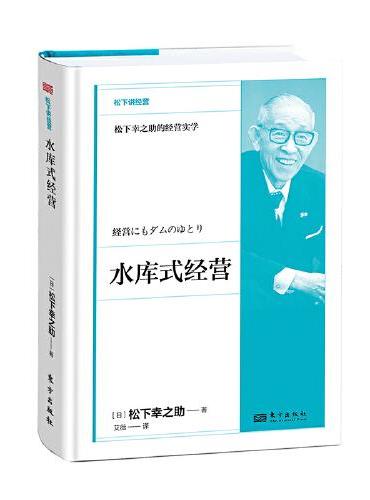
《
水库式经营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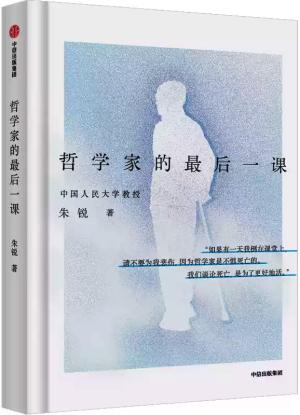
《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
售價:NT$
2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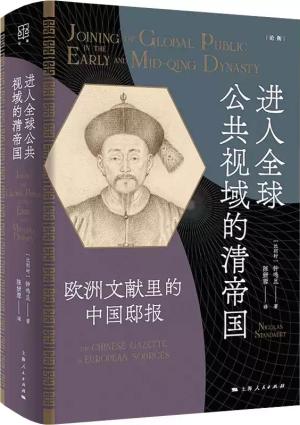
《
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欧洲文献里的中国邸报
》
售價:NT$
649.0
|
| 編輯推薦: |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清光绪13年(1887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
1898年入读武卫左军随营总堂,次年毕业参军。辛亥革命时驻守北京。
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期间参与倒袁运动。1916年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
其后随直军任国民军第三军旅长,后升至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
|
| 內容簡介: |
|
1927年率部改投山西军阀阎锡山并参于北伐。后先后出任绥远省、河北省政府主席。1931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负责指挥中日战争第一战区抗日作战任务,同年稍后回南京任军令部部长。在职时因贡献而于1943年获授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日军投降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参加盟军受降仪式。翌年任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并于次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59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2岁。著有《徐永昌日记》(1989年在台出版)
|
| 關於作者: |
|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字次宸,民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身处乱世而具备中国军人的一切美德;国民军第三军第二位掌门人,中原大战晋绥军的总指挥、抗战时期的军委会四巨头之一,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嗣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1959年病逝于台湾。
|
| 目錄:
|
第一卷 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1
第二卷 清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五年(1908-1916)15
第三卷 民国六年至十年(1917-1921)34
第四卷 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1922-1923)55
第五卷 民国十三年(1924)71
第六卷 民国十四年(1925)90
第七卷 民国十五年(1926)106
第八卷 民国十六年(1927)136
第九卷 民国十七年(1928)153
第十卷 民国十八年(1929)165
第十一卷 民国十九年(1930)188
第十二卷 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931-1932)217
第十三卷 杂记237
记我国军事学校沿革237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239
记毅军及武卫左军营制饷章243
记奉军244
记曹仲珊246
记胡佩庚248
再记员志青248
记别廷芳249
记彭家珍250
记郑毓秀250
记杨、濮、王、陈四友251
记贾宣之254
记刘喜奎254
论人才256
崞县徐氏族谱序跋258
王序258
吴序259
陈序260
阎序261
贾序262
自序263
贾跋264
自跋265
墓园碑记267
始祖天才公碑[谨按此为墓园原有古碑]267
崞县城北马家围徐氏先茔碑267
沿沟村徐氏先茔墓田碑268
沿沟村代州道徐氏先茔墓田碑269
故崞县徐先生暨配赵夫人继配张夫人墓碑270
崞县徐先生纪念碑271
兴国寺义阡记272
赵跋274
徐永昌将军百年诞辰纪念280
|
| 內容試閱:
|
第一卷
清光绪十三年至三十三年(1887—1907)
我家先世原为代州之振武卫人,至远祖天才公,始于明末天启、崇祯间迁崞县东关,我高祖满库公,再迁城西北舅家之沿沟村。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十一月一日我降生于此,兄弟姐妹共四人,我居季。幼随父母到大同,在我八九岁时二姐殁,其后兄亡。光绪二十五年大姐死(已经出嫁),二十六年六月一个热天,我母病故,同年十月,与我相依为命之慈父亦逝世。二姐之死我脑海中还不大懂得什么,父母之丧,真使我骇觉惊醒。母死时正闹拳匪之乱,八月初,西太后与光绪帝至大同,其年冬,毅军抵此。我于丧父月余之某日,到南关曹叔(大同人,于永昌为父执)之店去看曹叔,于其柜房遇武卫左军卢营(管带卢葵卿)的徐老先生(先生名椿龄,字芳年,营口人,时在武卫左军后路后营任书记),老先生见我身着重孝,问为谁氏子,曹叔为道身世,老先生大为怜悯,且因同姓,拟携我从军,我正感于前途茫然,遂即入营,后来卢营大部分到天镇设防,我随其小部分留驻阳高后方。
[沈注]永昌之父名庆,母赵氏。生永昌时庆年已四十四岁,乃往大同某粮店任管磨制面工作,未一载,赵氏病殁,永昌尚不满两岁。继母张氏原居孀,率其前夫所生一子二女来归,年均长于永昌,俱改姓徐。长兄吉昌早逝,长姊适胡,次姊待字,亦先后殁,继之张氏与庆去世,永昌遂孤苦零丁孑然一身矣。至“曹叔”为一车马店老板,永昌幼年常往打工,其名氏不详。请参阅汾阳王式通撰“故崞县徐先生暨配赵夫人继配张夫人墓碑”(见本书第二七页)及赵正楷著《徐永昌传》(台北山西文献社1988年版)。
[按:毅军与武卫左军一同护驾,因毅军总统宋庆,兼统武卫左军,又武卫左军成军时,其官佐均来自毅军,故无论军中或社会各方,仍皆以毅军称之,几不知有武卫左军。甲午中日战后,直隶总督荣禄,以北洋大臣主持训练五个新军,即聂士成之武卫前军(以淮军为基础)驻芦台、开平一带,董福祥之武卫后军(以甘军为基础)驻甘肃、袁世凯之武卫右军(以所练新军为基础)驻马厂、小站,宋庆兼武卫左军(以毅军为基础)驻山海关一带,荣禄自兼武卫中军(以八旗兵营为基础)驻京畿。]
[沈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戊戌政变作,慈禧三度临朝训政,囚载湉于瀛台,诛康广仁等六君子,命直隶总督荣禄即日来京,管理兵部,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复命宋庆所部毅军、董福祥所部甘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及北洋各军均归荣禄节制。十月荣复奏准改编成立武卫全军,分聂士成、董福祥、宋庆、袁世凯所部为武卫前、后、左、右四军,另募中军万人,自领之。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聂字功亭,安徽合肥人。董字星五,甘肃固原人。宋字祝三,山东莱州人。袁字慰廷,河南项城人。
我小时住大同南关牛家的宅院,此宅内外二院,各住三家。记得里院新搬来一家高姓,有女十七八岁,来时即病,不能举步,不久死去。迟了一半年,里院与我家很熟的吴姓十五六岁女孩,名美人子的死了,再过半年,我的二姐死了。我二姐与美人子均清秀,不很壮硕。又过半年,外院王家,是一种地人家,有女润子,十三四岁,很壮硕的亦死了。又过不久,外院刘家女孩名仙子的,十二三岁也死了。二、三年中连丧五女,年均不大(十二三至十七八),又不一定是传染病(我时年幼,不知他们所患是否一个病,若是传染病,我二姐应先传染我,且亦不能传染二年之久),而同院中尚有二三女孩则仍好好的,这是偶然抑非偶然?我母伤心于二姐之死,又因我父与人家做生意,在鼓楼西街,常有病,回来太远,即在鼓楼西街找一房住,不到一年房东太太死了,又迟半年,我兄亦死了,我母因住此伤心,又搬到泰宁观附近某巷樊家宅院(樊老先生曾做过某县守备武职,其第四子曾作阎伯川先生卫队团长,其第三子与我年相若)。我们住内院,外院住一开铜铺的人家,出来进去,见其太太脸黄黄的,不久死去。樊老先生有儿子、儿媳、四孙与二孙媳,其次孙媳,我呼为樊二嫂的,二十岁不到,迟半年也死了。她死后几个月,我母逝世,又过三个多月,我父逝世。短短一年多,先后又是四人。这些事故果真都是偶然么?何以偶然的如此巧而惨怛,若非偶然,那又是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我莫名其妙。我绝不信什么风水运气,可是此等遭遇,常使我念念不忘,无法解答,岂真有所谓数耶?我认为能说的通的,当然还是偶合。不过如属偶合,可以不论,如是数,则值得当成一个问题去研究,以求解决。
四书以外五经中,我只涉阅过三经,《诗经》我看的不过十之一二,《易经》则未尝略涉,故对易无所知,但我们乡党人士,多通习之。我所交游,如续西峰、弓海亭等读书虽有多少,闲尝均谈易理,贾煜如先生亦尝说其先人善演周易,我即联想到我父亦尝推演易卦,母病危时,有天已经不省人事,气息几于难测,大家都在张罗后事,父忽走开,自去演卦,旋即说不要紧不要紧,当时谁也不敢相信,病人已渐气绝,还说可以不死,既而母真苏醒,令人惊喜。若仅就当时情形看,不由人不信,但又过一二十天,我母终于不起,前卦所云,或亦偶然。心念此事,故并志之。
[沈注]续西峰,名桐溪,崞县人,山西大学毕业,曾任山西北路民团长、山西巡警道。弓海亭,名富魁,崞县人,曾任国民二军骑兵旅旅长。贾煜如,名景德,沁水人,曾任山西北路观察使,累官至考试院院长。
拳乱时,地方上许多儿童都去学义和神拳,他们自谓有神附体,人莫能侮。我曾对一与我同年之邻家樊氏第三子学神拳者,借故推之拉之,他竟随手歪倾,与平常一样,一点抵抗力未曾增加,我窃告父,所谓神附,都是假的,可是当时这些小孩们,竟能将大人骗过。
我小时有一不可解之谜,二姐在世时,当大同南关正月十五有三天最热闹的露天搭台戏,女人们白天都不愿去看,到晚上上灯以后,台下无灯,看不见人。我与二姐去看戏,女孩出门迟迟,是一阴天,我先出去,等她不来,我又回到大门以内,二门以外,门道很暗,忽见一火球,很快速地绕了一个小圈子,一转钻入水道不见了,我随即找寻,此时二姐适亦提着灯笼出来了,亦未寻见,究系何物,不能确悉。直到民四、五年我住陆军大学时,有晚看戏回来,在房后小解,又看见那样的一个火球,由水沟中进来,一打转又跑出去了,时当午夜,我正诧异,并在回想小时所见火球情景,忽听得墙外有叫卖食物声音,于是我立悟到是夜间行人手提灯笼一晃一晃的灯光,由水道射入,随其晃动而打转,有如火球,实即此也,天越黑火球越亮,可以说一直谜了我二十年,至此才得解答。
翌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初春,本路部队,经由阳高南行,过雁门关到忻州,驻约一二月,因我贪玩不大听话,徐老先生曾言着人仍送我回大同,后亦不知因何未送。春末,部队经太原开到清源乡(民国后改县),驻二十多天,于是部队走上党,我们营底(亦即辎重)经祁县、介休、灵石韩侯岭、霍州、闻喜等地,继续走大车路南行,在介休我第一次看到窑洞。过韩侯岭的前一两天,正连阴雨,早起出店,走不多远,即入深泥道路,一脚踩下,用力一拔,连鞋带袜均落泥中,念鞋袜本已破旧,索性将另脚所着,一并弃之,赤足走泥中,倒也自在。不想一二十里以后,全成光石路面,路上还有粒粒粗砂刺足,十分痛楚,我第一次赤足走这种路,一步一心酸,真不堪其苦。在霍州以北十数里处,有一很长的高坡甬道,我营大车,因下坡收剎不住,将驾驶头目的腿辗断。上年河东旱灾、大饥,似在闻喜,店主指过路七八小孩之一,说:可怜此子,尚不知其一家三代(翁媳孙),今天要服毒寻死。闻县衙门所与之救济,仅薄棺埋葬而已,可见我晋当时苦旱惨状之一斑。过闻喜后,似经解州境,即向东走茅津渡,过河到陕州。记得在距观音堂十几里路处,路半湿而光平,赤足急走,非常轻快,正跑得起劲时,不防左足突踏上一荆棘,刺入足心几分,疼得钻心,后来亦不记得如何走到观音堂。到观音堂后,同伴们才分给我一双鞋袜。由观音堂东行,在洛阳(当时称河南府)驻两天,又由孟津过河,经怀庆府,到清化镇,距清化镇一二十里路,两旁皆是竹林,北方人未见过生竹,有的人竟取一竿肩之,但久见不觉其贵,行数里后,亦即弃之。我们从大路跟大车走得慢,部队从小路走上党,经高平关下来,早到清化镇,等候会合。在清化时,我周腰及两大腿内侧,遍长红粒,奇痒难受,有人说在太阳地晒之可愈,实行半日毫无效果,后来离开此地,不记得何时治好。在清化镇驻约半月多,又走卫辉府,经彰德、磁州、邯郸、临洺关、顺德、柏乡而达赵州。宋宫保(名庆。清制不立太子,而沿明制设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官衔,太子少保称为宫保)时正驻此。赵州有桥,最出名,民间俗传为鲁班所修。在赵州驻约一个月,到乐城正定。正定有大佛寺,多谓佛像高三丈六,人人都去看,而我不知何由未去。由正定到祁州(安国)驻几天,到博野,博野驻一两月,到定州,再走保定。在距保定几十里路时,下起极大的雷雨,其日有人让马我骑,与另一骑同行,雨是越下越大,水则平地盈尺,赶到雨止天晴,我忽在马上打盹,时已走近保定,骤然前面尖呼叫一声,马即惊奔,将我摔下,竟至昏厥。后知为火车鸣汽笛声,其时火车刚通保定,为我初见,迨我醒来,只见胸前血染,同伴搀扶我说正到保定南关,又昏迷了,再过一天,我才醒来,是在保定之刘爷庙。驻两日后,便第一次乘火车到琉璃河,即暂驻此。时已秋天,我第一次看见螃蟹,琉璃河中插一铁杠,传为王彦章(后梁寿昌人,字子明,有王铁枪之称)撑船的篙。又所住商店,颇述去秋以来驻此的印度兵,如何奸及老妇(年轻者皆避之远处)以及种种骚扰情事,可见战败国人民无保障之惨痛矣。驻月余,天凉时又经涿州而到南苑,先驻五里店,中移八里庄,最后驻小红门。是年秋冬之交,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逝世,似离年关(我们在小红门过的年)不远。宋宫保殁于通州,卢营长哭之至痛,可见当时军中上下情感之笃。是冬,有伙伴高某,领我第一次去北京,记得曾到天乐园去看戏,在天桥大路上见印度兵来往不断,但未看到西洋兵和日本兵。
我第一回上北京是同高什长从八里庄去的,其时天坛门口与先农坛门口的北边,都是火车站(京保、京津),火车即始于此,那时前门楼(联军入京时焚毁)重建工程,只起立两柱,架一横梁,但彩画得很鲜亮,不知是当时建筑前门楼的一种礼法,抑是因西太后回京,不可无门楼,而象征为之。此为我入京所第一眼看到的。我们清晨起床即走,到京在正阳门大街鲜鱼口南路东之都一处吃饭,是一卖饺子的饭馆,只一二样小菜,如熏干肉煮咸菜之类,饺子在门外煮,门内甬道很深,有丈余宽,两边排桌坐吃,中间走路,只容一人,两人对走,须侧身而过,甬道最后端有一张很大的龙椅,雕刻得很讲究,传说康熙帝曾来此小吃过,以后此处即设一龙椅,不再动用。中间甬道上有高出半尺的鱼背形积泥,不知已若干年,凸凹不平,非常难走,但被认为风水攸关,不肯清除。当时前门大街,中间是光石板路,两旁为摊贩,再两边是走大车的土道,简直是两条深泥路,再向两边才是铺面,很热闹亦很嘈杂肮脏。高什长领我在鲜鱼口天乐园看一回戏,演的是金钱豹,行头当然比我们在外省所见的漂亮,可是戏中角色,由台口往后即随便说话,不如乡下戏班规矩。天桥以北,珠市口以南路西,隔几家即有一清唱馆,下午我们回时,经过其处,即进去看看。犹忆有一家,高入听,我不好意思进到里面,但因高在内,我亦不能独走,即站在门口看,觉其中有一女孩很好看,高见我尽的不坐,看了一场给钱而出,偕往南走,随问我好看否,我说好看,他问为何不坐下,我说不好意思,他问还想看么,我说想看,高于是又领我回去看,他又坐下,我仍站在门口;过一回唱罢,那个女孩收钱,走过面前,方觉其并不好看,我乃悟到无论看什么,远近往往不同。以上为我第一次到北京的印象。
我七八岁时在大同南关上过学,先生姓厉,时已七十多岁,长于篆书。记得他在我的
书本上题篆体二字,我问他这两头尖的字,是种什么字,他说是篆字。本来我因父亲养病家居,常教我念书写字,当时上学到半年左右,厉老先生对我所写的“仿”,总怀疑不是我写的,每隔几天即说一回,后来我父命将笔砚带校去写,其日我一早即去,写完以后老先生很高兴,在“仿”上批了很多字,等回家我父看后,说是夸奖的话,全家人都欣喜。第二天我仍到校去写,因去得略晚,同学们渐渐来多,围在身旁,扰嚷不休,写完以后,老先生又批了很多宇,我父一看,大不高兴,说我没有恒心,是一种顶要不得的事,大加申斥。这是我小时受到印象很深的刺激,觉得人要无恒,是最要不得的,我一生做事生怕无恒,此种心理,可说是受此刺激的影响。
当在琉璃河时,徐老先生常常写字,临九成宫帖。有次他写后未收拾文具,即行外出,我即就其书桌,照临半张,老先生回来见了,赓即说:“你写吧,不要动。”写后,他说我的字很可以练习,遂开始教我写字。自彼时起,一有时间,即临帖写字。若干日以后,老先生每持我字以示人,惜我于离开老先生后,未再着意于此。但后来却有人说,当时徐老先生有公文待缮,录事外出,老先生一气走开,由我代为缮就,置之案上,老先生回来问知其事,因教我读书习字云云,类似一段佳话,实即是以上一事传说之误。徐老先生从未教我读书。我由此一传说,联想到我素日的一种认识,即人之常情,近我者易恶,而远离者易美,俗亦有远香近臭之说,即离我近者很容易忽略其善,而每感其不善,离我远者又很容易受耳食之误,以不善成善。因为因素不同,观点即异,正如同鲁史记齐事每多贬,记晋事或多褒,因晋距鲁远而齐距鲁近。近者动静善恶,皆习知之,利害关系亦多冲突,因而显见其恶,湮灭其善;远者利害冲突较少,言谈动作,均难详悉,故多显传其善,掩其不善。
犹忆民八九年间,社会人士每多徐树铮(又铮,江苏萧县人)而薄吴子玉(佩孚,山东蓬莱人),以其时徐组边防军,收复库伦,吴则在腹地也。当时我曾与同学段伟霄论及此事,我举例说吾人脑海中,常想到岳武穆之“精忠报国”,与关壮缪之“夜读春秋”,假如我们与他住在一起,将见他们并非单纯如此,衣食起居好恶,甚多亦与吾人无殊,则不免又是一种看法矣。此后几年,社会上又讨厌冯焕章(玉祥,安徽巢县人)而赞扬吴子玉,亦正是冯在京畿时也。故社会常情,很多是于其人正进步时,说他不好,而于其已腐化时,又说他好,正如《史记》“相人失之贫,相马失之瘦”,迨其已富已肥,或且无所取矣,乃又以为可取。“远来和尚会念经”,都可说是对这一种错觉的写照。本来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是一件难事,故对孩提之童,或对正在努力之人,均不可轻下断语,而对朋友、对长官、对下属,亦勿为近恶远美的俗套所囿。以上均系就好一方面的人而言,至于太重感情,不分皂白,意气投,什么都好,意气不投,一切不合,此等人尚不足以语此。吾侪处人,对此两方面,均须切实注意。
是年冬,尚有二事可记,一是马宫保(名玉昆,字景山,颍州人,直隶提督,原任毅军翼长,今为武卫左军总统)来南苑看部队,一是西太后及光绪帝由陕经豫回京。一是乘马由北南来,一是乘轿由南北去的,均经过小红门,部队都要接送。次年(一九○二)春初,我随部队到通州,驻新城。是时通州正在与宋宫保办丧事(其时丧事要过七七,即殁后第七天为一七,第四十九天为七七,每七均有祭典)。宋宫保殁后,武卫左军由马宫保接统,毅军则由姜军门(名桂题,字翰卿,安徽亳县人,时本职为四川提督。军门是提督之尊称)接统,社会上始分别出毅军与武卫左军。本路(武卫左军后路)部队,是驻于通州新城之西仓(江南由运河运北京之米,大都储此东西两仓),我们于五月初六开固安县驻防(因地面不靖)。当走至离城几十里打尖时,我受暑难过,不能行走,徐老先生买益元散,取井水,调白糖饮之,休息半晌即愈,当晚到固安。驻到秋天,又经马驹桥回通州,仍驻西仓。到通州后,我每日更多余暇习字,部队则此一年中,做工时间最多,如在南关修演武厅,及在附近盖营房,与整理规模很大的东西仓,每一仓区驻五营人,操场附近驻四五营,南关驻四五营,炮兵驻操场,骑兵驻北关,同时并修复二十六年为外国军队炮击所破坏的城墙几处。
马玉昆自光绪二十年后,即做宋庆之翼长(即到作战时派其赴重要之一翼,任指挥官,等于后来之帮办或现代师中之旅长,惟彼时军队少,故一军万余人,其首领不称师长而称总统,其助手亦不称副师长或旅长,而称翼长,朝野亦重视之,实由兵少,地位崇高之故),二十六年联军入侵,由山海关调其到天津时,正当聂士成阵亡,武卫前军败溃,武卫左军在杨村一带作战时,马为翼长,本官为太原镇总兵。又一资深之某路王统领,本官为天津镇总兵,系马之儿女亲家,与另一统领就近受马指挥。某日在战争吃紧时。马召集二统领处分作战机宜,王统领对事有不甚服从情形,数语不合马即命其扈从杀王于室内,虽然表面是翼长杀统领,实亦可说是总兵杀总兵。毅军官佐,对宋宫保都是诚服而亲爱,对马则是服从而畏惧,马在北洋多少年极有威望,主因在于执法之严。
庚子年西太后与光绪帝出奔时,当时的武卫各军,残破之余,多无纪律可言。如荣禄之武卫中军,离京后即溃不成军,谈不到纪律;其次为武卫后军,本调来拱卫京师,旋令攻打东交民巷不下,联军到京,一触即溃,其后董福祥贬戍甘肃,后来之马福祥(字云亭,武卫后军马队统领马福禄之弟,曾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国府委员)、马麒、马麟(俱为武卫后军马队分统马彦海之子,曾先后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等,多为该军的分子。武卫前军在津沽防敌,曾认真作战,但因聂士成提督大沽战死,部队遂亦残破。纪律较好而部队亦较完整者,仅有曾在杨村一带作战之武卫左军与毅军(当时武卫右军已由袁世凯巡抚带往山东,未参与此役)败而不溃,嗣后退却,即一面对敌防御,一面护驾西行,故回銮后,西太后甚为倚重,留之近畿,而毅军更由于历史关系之深,常使驻南苑一带。姜桂题为人和平圆滑,善交接,其本人更常住北京,部队在南苑,由郭殿邦(宇先民,山西解县人)总兵帮统之。
我在光绪二十八年底或二十九年初,才补得正式兵(以前为伕)。在二十八、九年之交,俄兵占奉天,日俄构衅。记得是个初春,武卫左军奉调十几营人,由马宫保自率,开赴热河之平泉朝阳一带,预防日俄战争之扩及热境,我即随军由通州出发,经夏垫、段家岭、邦均、蓟州、石门、遵化、三屯营、喜峰口、当坝,走了十天,而达平泉,部队前方有到赤峰朝阳的,我营驻平泉,马宫保亦驻此。因我年岁小,初离徐老先生,在平泉待的不久,即告假回通州,徐老先生正在通州赋闲(我补兵后不久,卢营长被免职,调本营帮带升任营长,帮带即新军之督队官,今之营附或副营长),遂送我到南苑毅军李营当兵,在营中两三个月,我忽染伤寒症,当时部队中无医药设备,为防传染,他们着人送我回老先生家,一病三个月,老先生老太太亲为调护,自二十九年夏日起,直到秋天才算恢复。病愈后我又到京西大灰场毅军殷营当兵。在殷营我觉得很吃苦,有半年多派我打更,因为晚上打更,上午睡觉,下午打扫营长公馆院子,而出操反很少。某日听说南苑招考学兵,徐老先生亦正在南苑做程允和提督的幕府,我请假去见他,说要考学兵,他说:“已经考罢了,你何不早来?”我听说即急得大哭(我在老先生处哭是不止一次,心上一有委屈,即去老先生处哭一场),老先生接着说:“你只会写,要考学兵识的字还不够,我可送你回通州丁营当兵,同时帮司书贴写,藉此多识些字。”我于是到了丁营,每天下午不是抄录文书,便是在册报处缮写官兵名册,上午照常出操,但却不做工,如此者约一年半,正吴元恺之自强军驻通州时也。马宫保走热河后,清廷以京畿空虚,调湖北自强军吴元恺八营,来通州增防,该部队在技术方面的训练,比毅军或武卫左军好,但纪律不及,常常与人斗殴。吴江苏金坛人,每为人书“百练此身成铁汉,三缄其口学金人”之联。又日俄正式开战,是在光绪二十九年冬,三十一年秋议和。
我病伤寒时,正徐老先生在通州,赁居某通判家宅之一部,某通判有子,正在求学,此时已赴通判任所,我即在其小的书房养病。我病上午很好,午后渐渐发热,一直烧到深夜,天快亮时稍觉轻松。我于每天上午病较好时,即取阅其书,最使我爱看的是《左传句解》,因其有注解,容易看懂,故一看即感兴趣(因为我在卢营、丁营亦常看小说),其次是《聊斋志异》,因其书有蛇缠住一人的图画,引起我的好奇心,文字初看不甚明了,但反复看上几遍,亦能懂得若干。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春,贴写工作结束,但已不愿再去当兵,于是困居通州,为我生平最无办法的一个时期。通州有个万寿宫(在城内临河处)犹之北京的天桥,不过小了几倍,该地有说书的、卖艺的、占卜的。有天我在书场听说书,遇一曾在册报处认识的信阳徐某,现在赵倜(武卫左军右路统领)处当书记官,一望见我,即走过我这边来,他刚坐下,我即起身外走,如此者有二三次。我因赋闲(毅军中称之为闲员)觉得可耻,不好意思与人接近。我自幼即有此不好意思的习惯。到第三次,他不待我起身,即将我叫住,书场散后,他问我现做何事,我说赋闲,他说:“我有一表兄在此,我试与之设法看看。”后知他之关切,纯因看我老实与这几次躲他之故。其表亲亦信阳人,名何毓淮,是举人大挑知县,在马宫保后方办文案,听说我很老实,要我去见见面。见后他说:“我最近要上医院割痔疮,需要一个人照护与做饭,你能照应我吗?”我说可以。他又说:“你一方照护我,我一方与你想办法。”我即帮他半个多月,他病好了说:“此间新成一马卫队(即骑兵卫队)是要准备出关的,我无多积蓄,但想帮助你,我们表兄弟二人与你筹措些钱,借给你买马,你可到马卫队去。”(当时骑兵均为私马)我说我还有十八九两银子,他很觉奇异地说:“你在此流荡,何来积蓄?”我说:“几年当伕当兵积蓄得来,存在徐老先生处,因为赋闲,不好意思去取用。”他说:“如此便不必踌蹰了,借你几两银子即成。”我于是到了马卫队,此为光绪三十二年秋天的事。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我们马卫队随武卫左军帮办、吉林三姓副都统蒙旗人昆源去黑龙江省剿匪(昆父恩铭,曾任黑龙江省将军,故此时派昆赴黑省),因日俄战后,东三省到处闹匪,尤以奉吉黑交界处为甚。我们由通州出发,走十来天到平泉(原名八沟),由通州出发时过潞河,系走冰桥,冰已将开。在平泉驻一月,经朝阳到中后所,由平泉出发时过一小河,冰仍是将开未开。在中后所驻约十天,上火车东行,到新民府(方由新民屯改府,时张作霖正以小编制骑兵五营的巡防队统领驻此),我国火车刚修至此。驻亦旬日,再乘日本人所筑的窄轨火车,到奉天省之沈阳(其时奉天将军为赵尔巽,地方虽属中国,铁路上查票卖票均由日军管理),车过大凌河时,木桥响得骇人,再由沈阳坐日本火车到长春(方由宽城子改称长春府。此段铁路原为俄人修筑之广轨路,日俄战后,日人改为窄轨),车站距城约七八里路,由长春换乘俄国的广轨车(长春有日俄两车站,一在孟家屯,一在二道沟,但忘其何处为何站)到哈尔滨。计此行坐过三种火车,先坐准轨车、次坐窄轨车、后坐广轨车,车上设备不同,穷富不同,俄国车大,宽敞富丽,一切都好,日本车小而简陋,可是管理方面日车比俄车强。从沈阳到长春的一段火车,每一节车上有二日兵,分坐车门口,防范土匪上车劫掠。因其时地方不靖,日本火车各节车厢尚不能互通之故,日车车灯,是由车顶外面装下来,准轨车是由车内顶推转挂上,俄车则点蜡烛。机车燃料,中日用煤,惟俄车当时用木柴,故其烟筒上端,罩有大眼的铁丝网,随时有火星向后飞散,常常出事。我们的车有一辆即如此烧掉,颇受损失。俄国车站有宪兵,均穿大红裤子,我们到哈尔滨下车,即骑马开到呼兰府(原名呼兰河新改府,距哈尔滨四五十里),过松花江时,冰冻仍坚,车马行走其上,直如在土地上一样。在呼兰驻半月,昆帮办进黑龙江省(彼时其地名卜奎)见程雪楼将军,我们护送他到对青山车站,又过十数日,再去接他。此次过松花江时,虽仍走冰上,但已将开未开,岸边已消,乘马须跃上冰面,与内地气候,相差要两三个月,到阴历四月间,河始开冻。
我在通州所买之马,原只看他英俊,二十四五两银,廉价买到手后,才有人批评说:“此马满身有豆子大小的黑红点子,此名红砂罩,最妨人,所以价廉,你还是该换匹好的。”我未理会,骑过几次尚好,但当正月初一出发时,我一上马,他往前急窜,将我撂到马臀部,再一窜将我丢下来,再骑时我乘势往前骑,他又往后一缩,将我缩到马脖子上,又一摆将我摔下来,沿途捣乱,几无虚日。离中后所十几里路时,我未跨上,他即先跑,我手执缰绳,胸带短枪,被他拖了数十步(因恐手一松马即跑了),胸部为枪擦伤,殷然出血。一路上朋友们都对我说:“这种马天性不善,无法降伏它,不如卖了。”到呼兰后,即卖与一车户,另买一匹,该车户亦不信什么红砂黑砂,后来听说此马驾车不久,某次乱跑,将一腿插入下水道板盖内(呼兰下水道均用木板盖着)折断了,是未妨人而妨己矣。或者生此异样的皮毛,即有其异样的秉赋,亦所谓诚于中形于外者欤。
由中后所到新民屯,上车时,坐的不是客车,因时间关系,赶搭一列“小工车”(自修火车后,年年冬天开小工车,专为山东人上东北做工者准备的,票价甚低,由北京到新民屯,约一元二角钱,此种移民到东北后,为人垦种,日可得八角至一元之谱,当时黑龙江两个铜子买一斤面,故几年即可成家立业,我的同事即有多人留住当地不回来的),其车有边无顶,我们走的那夜正下雪,在车上无论坐立睡卧,满身是雪(从前上东北去的人虽有火车,仍如此之苦)。我们出发时,昆帮办带五营人,过平泉朝阳时,由马宫保增拨五营,共为十营,即七营步兵。陈希义(武卫左军左路统领,后做过大同镇总兵,曾在光绪二十六年杨村作战受重伤者)带五营、马子青(马宫保少君,绰号马二虎)带二营、杨良辉带炮兵一营、赵倜(字周人,河南汝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时任武卫左军后路统领)带骑兵两营。我们马卫队四十人,到呼兰后约一个月,即派我回通州送一公文,其时马宫保已回驻通州,我独自一人坐船(由呼兰至哈尔滨)、坐车,如此长途跋涉,此为第一次,抵通州后,交上公事,迟日取覆文时,我好好的面对面看到马宫保,此亦为第一次,他问我几句话,记得曾问:“你们驻的地方面多少钱一斤?”我说两个多铜子(其时刚使用铜子不久,一元钱可以换一百个铜子)。他说:“这样一个人一个月用不了九钱银子的粮,往常我们发米面每月九钱银子不够,现在九钱银子用不了,我信上没有写,你回去告诉帮办,还是照往常发面不要发钱,我不另办公文了。”我来回在北京、天津、新民、长春换车,均曾下车住宿,晚上无事,在天津、在长春两处都到戏院听过戏(在天津看过小兰英“问樵”、小连芬“采桑”,在长春看过王克琴“翠屏山”)。
光绪三十三年夏天,离呼兰约几十里之齐家甸(在呼兰、哈尔滨中间),发现一股六七十人的土匪,匪首绰号黄五省,北边派我们马卫队进击,南边由赵倜的骑兵堵剿,我们一打,他即南窜到赵倜那边去,除打死者外,一举成擒十数人,甚是顺利,是为我第一次作战。其年冬,又有以陶什托为首的一股土匪,大约有四五百人,由赵倜出剿,从哈尔滨以东之双城子,一直追剿几千里,直追到热河剿完乃止,为在东北剿匪最努力之一次。队伍回来时,脸上都是冻疮(陶什托后来当民国初年在库伦叛乱任哲布尊丹之陆军部长兼总司令)。
是年夏秋之季,倪嗣冲由哈尔滨来呼兰查事,回去时派我与刘某送他到哈尔滨,倪时为滨江道尹(东三省改行省后,徐世昌代赵尔巽接东三省总督,倪代程雪楼接黑龙江巡抚,张勋任东三省提督,驻哈尔滨,但似未到任)。其年深秋,昆帮办要买一冬天的吃的、烧的,派我们几人分头去办,有的去买菜蔬,我是去买劈柴。事过半月,有天我外出回来,听说买菜的那一位,被打四十棍开革了,他是马卫队中年纪最老的,我是最小的,我们的哨长(马卫队副队长)见我说:“小伙子,你真不错,查你查到河岸上卖‘半子’的,(当地劈柴是长约五六尺的圆木劈作两半,名曰半子)他们都说,不必查了,价钱错了,徐老总(时民间对军人的一般称谓无分官或兵)是不让的,他很老实,在我们这儿买的半子不少,随你在别处能用这价钱买到,我们即对不起他,所以说价钱很公道,你不必再查了。这是我们查到你的结果,但那老头子是被开革了。”
[沈注]光绪三十三年,诏改地方官制,以徐世昌为东三省首任总督,程德全(雪楼)署黑龙江巡抚(原为段芝贵,因案免)。宣统元年,徐内调,由锡良(清弼)继,程则于光绪三十四年调抚奉天,由周树模继。时倪嗣冲(丹忱)由佐杂洊至黑龙江民政司使,经锡良以其贪污劾罢。宣统二年,锡良去职,始由赵尔巽(次山)接任东督。次年,程亦由奉天改抚江苏。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行伍出身,曾充袁世凯山东抚标参将,庚子拳乱后调统北洋巡防军,授甘肃提督未赴任。徐世昌奏调充驻奉淮军翼长,驻昌图,经锡良劾其去职,宣统三年改任江南提督。又“滨江道尹”,属吉林省,民国二年始设置。
所谓关东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貂皮,人多知之,不必细述,乌拉草是野生的细草,约三尺上下高,类似内地之马兰而较细软,卖者割取其草,坐街头,用木棒在石上反复捶之,捶成细麻状,约二尺半长,扎成小把出售。当地人所穿之鞋,是用一块牛皮剪开折起缝合而成,名曰“乌鲁”,夏天穿空乌鲁,冬天即内絮此草,很暖和,冰天雪地,有此即不会冻足。此类鞋上加高腰,名“蹚土马”,内不絮乌拉草而衬一毡袜,毡袜经不起走长路,故步兵总是穿乌鲁,而骑兵则穿蹚土马。我在内地年年冻足,那年未冻。
其年冬,我觉得身体愈壮,每晚脱袜子,总是被汗湿透。年除夕与我们刘副队长猜拳,他嗓音极高,我无论如何要与他比高。到正月初四五,我无缘无故地忽然吐血了。后来我想是否年下猜拳喊破了喉咙,始终是一个谜,此是我第一次吐血。那时文武长官每逢初一、十五都要拜庙,冬天天不亮到庙参拜,拜毕出庙天始亮,我们则分布在沿途站岗,有一次站岗回来,我的脸冻得在两个钟头以后还疼得不止。住在当地的人,十之九冬天脸上都有冻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