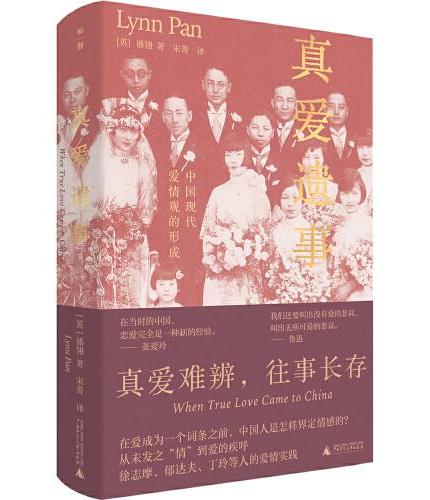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功名诀:左宗棠镜像
》
售價:NT$
908.0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NT$
439.0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NT$
500.0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NT$
959.0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NT$
407.0

《
有底气(冯唐半生成事精华,写给所有人的底气心法,一个人内核越强,越有底气!)
》
售價:NT$
347.0

《
广州贸易:近代中国沿海贸易与对外交流(1700-1845)(一部了解清代对外贸易的经典著作!国际知名史学家深度解读鸦片战争的起源!)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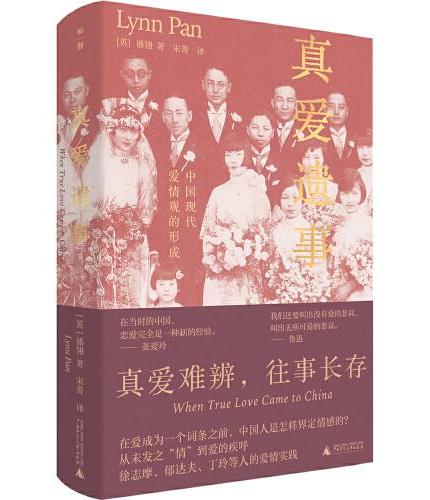
《
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
》
售價:NT$
551.0
|
| 編輯推薦: |
二十世纪主流文学大师
中产阶级的精神路标 《纽约客》短篇圣手
与卡佛共同引领文学的极简时代
创作巅峰期的短篇精华独家呈现
写给困于中年危机的都市男女
于孤寂无望的漂泊中逆流返航
|
| 內容簡介: |
|
《我会找到你的地方》是安·比蒂“《纽约客》故事集”的第二部。书中的人物大多步入中年,故事常蕴含某种危机:离婚的女人与前夫的男朋友发展了一段近似闺蜜的友谊;家庭聚会上,女主人竭力扮演着丈夫的朋友们的知心密友,最终还是无法挽留住丈夫;离婚的男人大清早出现在前妻家中的厨房,等待主人起床谈谈要回儿子的事……比蒂以平凡随意的细节映照出人们对传统世界隐忍不言的渴望,替他们发声,为他们代言。
|
| 關於作者: |
|
安·比蒂(Ann Beattie),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与雷蒙德?卡佛齐名的“极简主义”大师。《纽约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作品四次被收入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作品选集,并入选约翰?厄普代克编辑的《二十世纪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选》。比蒂善于描画美国一代城市人的情绪状态与生活方式,帮助中产阶级认识了自我,对于他们的成长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乃至被视为其精神路标。
|
| 目錄:
|
灰姑娘华尔兹
燃烧的屋子
等待
格林尼治时间
重力
奔跑的梦
漂浮
私房话
如同玻璃
流动的水
康尼岛
电视
高处
夏夜的天堂
时代
避暑的人
两面神
你会找到我的地方
|
| 內容試閱:
|
燃烧的屋子
弗雷迪·福克斯跟我待在厨房,他刚洗净擦干一个我不要了的鳄梨核,这会儿他正靠在墙上,卷着一根大麻烟。再过五分钟,我就没法指望他了。不过他今天开始得晚,再说他已经把壁炉的柴火搬进屋里,去路边超市买了火柴,还摆好了饭桌。“你是说就算不把盘子翻过去,你也能知道这是利摩日瓷器?”他在餐厅里冲我喊。他假装要把一个盘子扔进厨房,像掷飞盘那样。我家的狗塞姆信以为真,一跃而出,把毯子蹬到身后,向前滑去。随即他意识到自己错了。那情景就像BB鸟第一百万次诱使大笨狼冲过悬崖。塞姆失望地垂着下巴。
“我看到有满月。”弗雷迪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大自然。月亮和星辰,海潮和阳光—我们根本不会驻足停留为它们惊奇了。我们太沉迷于自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大麻,“我们站在这儿搅和锅里的酱,却不去窗前看月亮。”
“我想你说这些不针对个人吧?”
“我爱看你把奶油倒进煎锅的样子。我喜欢站在你身后看奶油冒泡。”
“别,谢谢你。”我说,“你今天开始得够晚。”
“我的活儿都干完了。你信不过我帮厨,我把柴火拿进来了,还跑了一趟腿,今早我带塞姆先生一路跑到普特南公园,累坏了。你确定你不要?”
“不要,谢了。”我说,“反正不是现在。”
“我就爱看你站在烟雾蒸腾的锅前,你额前的头发变成湿湿的小卷。”
我丈夫弗兰克?韦恩,是弗雷迪同母异父的兄弟。弗兰克是一个会计。弗雷迪跟我比跟弗兰克更亲近。不过既然弗兰克跟弗雷迪说的话比跟我说的多,弗雷迪又绝对忠诚,弗雷迪知道的总是比我多。我挺高兴他不会搅拌奶油;他会开口说话,思绪会四处游荡,下一次你再看奶油的时候,它要么结块,要么煮沸。
弗雷迪对弗兰克的批评只是隐而不发。“在周末款待他的朋友们,这是多么慷慨的举动啊。”他说。
“男性朋友。”我说。
“我不是说你是那种没有底线的女士。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弗雷迪说,“要是你现在在炉子旁边,吸一口这要命的东西,我还会吃上一惊呢。”
“好吧。”我说着从他手里接过大麻。我拿过来的时候一半已经没了。我吸了两口以后还给他,还剩下半英寸。
“要是你把烟灰抖进酱锅里我会更吃惊的。”
“他们吃完饭后你要告诉他们我干了这个,那我就尴尬了。你自己倒是可以这么干。如果你讲的故事是你自己的,我就不会尴尬。”
“你真了解我。”弗雷迪说,“月圆之夜的疯狂,不过我真的要在酱里撒上这么一点点。我忍不住。”
他撒了。
弗兰克和塔克在客厅里。就在几分钟前,弗兰克把塔克从火车站接回来。塔克爱来我们这儿,对他来说,菲尔菲德县就像阿拉斯加那么神秘。他从纽约带过来一坛芥末酱,一大瓶香槟,鸡尾酒纸巾,纸巾图案上一架飞机已飞过一座大楼,二十根白鹭羽毛(“再也买不到了—绝对非法。”塔克低声告诉我),还有,一个玩具青蛙,一上发条就会跳,就在他坠着镶莱茵石帽带的黑色牛仔帽下面。塔克在苏荷区有一家画廊,弗兰克给他记账。此刻他正躺在客厅里,与弗兰克聊着,弗雷迪跟我都在听。
“……所以我听说的一切都表明他过着一种纯粹是化身博士的生活。他二十岁,我看得出来他因为还住在家里,可能不想张扬同性恋的身份。他来画廊的时候,头发向后梳得油光水滑—只是用水,我离得够近能闻到—他母亲一直握着他的手。模样如此清纯。我听到的那些故事啊。我打电话过去时,他父亲开始找‘葡萄园’的电话号码,在那儿能联系上他—他父亲很不耐烦,因为我不认识詹姆斯,要是我就这么给詹姆斯打电话,我可能马上就能找到他。他边找电话边自言自语,我说:‘哦,他是去看朋友了还是—?’他父亲打断我说:‘他去了一个同性恋烧烤派对,周一就走了。’就是那样。”
弗雷迪帮我把饭菜端到饭桌上去。我们都在桌边坐下,我提到塔克谈论的那个年轻艺术家。“弗兰克说他的画真的很棒。”我对塔克说。
“他让埃斯蒂斯看起来倒像抽象表现主义了。”塔克说,“我要那个男孩。我真的想要那个男孩。”
“你会得到他的。”弗兰克说,“你追的人都能到手。”
塔克切下一小片肉。他切得很小,可以边嚼边说。“我是这样吗?”他问。
弗雷迪在桌旁抽着烟,眼光迷蒙地望着升到窗中的月亮。“吃完晚饭,”他说,看到我在看他,就把手背贴在额头上,“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灯塔。”
“要是你画画就好了。”塔克说,“我也会要你。”
“你没法拥有我。”弗雷迪突然生气了。他思量了一下。“这话有点假吧,是吧?谁想要我都能拥有我。这是周六晚上我唯一会在的地方,这儿没人烦我。”
“穿条松点的裤子。”弗兰克对弗雷迪说。
“这儿比那些混着香烟和皮革味儿的酒吧好太多了。我为什么这么做?”弗雷迪说,“说真的—你觉得我哪天会停下来吗?”
“咱们别这么严肃。”塔克说。
“我一直把这张桌子想象成一条大船,碗和杯子在船上摇晃。”弗雷迪说。
他拿起盘中的骨头,走到厨房去,酱汁滴在地板上。他走路的样子就好像是在风浪中颠簸的船甲板上。“塞姆先生!”他叫道,狗从客厅的地板上一跃而起,之前他正在那儿睡觉;他的脚指甲划在裸露的木地板上,发出轮胎在砾石路面上打转一般的声音。“你不用求我。”弗雷迪说,“耶稣啊,塞姆—我正要拿给你。”
“我希望有根骨头。”塔克说,向弗兰克转着眼珠子。他又切下一小片肉。“我希望你弟弟真的明白我为什么不能留他。他手头事做得不错,但他也可能什么话都跟顾客说。你得相信我,要不是我不止一次的尴尬透顶,我绝对不会让他走人。”
“他本该把大学读完。”弗兰克说,把酱汁抹在面包上,“他还得多晃荡一阵子,然后才会厌倦,真正安顿下来。”
“你以为我死在这儿了吗?”弗雷迪说,“你以为我听不见吗?”
“我没说什么当你面不能说的话。”弗兰克说。
“让我告诉你我不会当面跟你说的。”弗雷迪说,“你有个好老婆、孩子,还有狗,而你是个势利鬼,你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
弗兰克放下叉子,气疯了。他看着我。
“他有一次也是抽高了来上班。”塔克说,“你明白吗?”
“你喜欢我是因为你可怜我。”弗雷迪说。
他坐在门外的水泥长凳上,春天的时候那里是个花园。现在是四月初—还不算春天。外面雾很大。我们吃饭的时候下雨了,现在雨势渐缓。我靠在他对面的一棵树上,窃喜是天黑,又雾蒙蒙的,我低头也看不到靴子被泥巴毁得多厉害。
“他女朋友是谁?”弗雷迪问。
“如果我告诉你她的名字,你会跟他说是我说的。”
“说慢一点。是什么?”
“我不会告诉你的,因为你会告诉他我知道。”
“他知道你知道。”
“我不这么想。”
“你怎么发现的?”
“他说起她的。几个月来我一直听到她的名字,后来我们去加纳家聚会,她在那儿,之后我提到关于她的什么事时,他说:‘哪个纳塔莉?’这再明显不过,整个儿暴露了。”
他叹气。“我刚刚做了一件非常乐观的事。”他说,“我跟塞姆先生到了这儿,他掘出一块石头,我把鳄梨核埋在那个洞里,在上面盖上土。别说这些—我知道:外面成活不了,还会再下场雪,即使活了,来年的霜冻也会让它死掉。”
“他很尴尬。”我说,“他在家的时候躲着我,但是也躲着马克就不好了。他才六岁,他给他朋友尼尔打电话,暗示想去他家。只有我跟他在家的时候他就不这样。”
弗雷迪捡起一根棍子,在泥地上戳来戳去。“我打赌塔克对那个画家本人感兴趣,而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很火吧。他那种表情—一成不变。也许尼克松真的爱他母亲,但一脸那种表情谁会相信他?长一张没有表情的脸真是倒霉。”
“艾米!”塔克叫道,“电话。”
弗雷迪用那根泥棍子跟我挥手再见。“我不是个无赖。”弗雷迪说,“耶稣基督啊。”
塞姆跟我一起回屋,跑到一半,又转身回到弗雷迪身边。
是玛丽莲,尼尔的妈妈,她的电话。
“哎,”玛丽莲说,“他害怕在这儿过夜。”
“哦,不。”我说,“他说他不会。”
她压低声音。“我们可以试试看,不过我想他要哭了。”
“我过来接他。”
“我可以送他。你家正开晚宴呢,不是吗?”
我压低了声音。“什么晚宴啊。塔克到了,J.D.一直没出现。”
“嗯。”她说,“我肯定你菜做得很好。”
“外面雾太大了,玛丽莲,还是我来接马克。”
“他可以留下来。我来做殉道士吧。”她说着,我还没来得及反对她就挂了电话。
弗雷迪走进屋子,留下一路泥印。塞姆躺在厨房里,等着人给他清洁爪子。“过来。”弗雷迪说。他用手捶着大腿,不知道塞姆在干什么。塞姆站起来跑向他。他们一起去了楼下的小卫生间。塞姆喜欢看人小便,有时他还唱歌,来配合小便入水的声音。到处都是脚印和爪印。塔克在客厅里尖声大笑。“……他说,他跟别人说:‘亲爱的,你玩过转瓶子吗?’”弗兰克和塔克的笑声淹没了弗雷迪在卫生间小便的声音。我打开厨房水槽的水龙头,水声淹没了所有的噪音。我开始洗碗。我关上龙头的时候,塔克又讲起一个故事:“……以为那是奥纳西斯在铁砧酒吧,他执意这么说。他们跟他说奥纳西斯已经死了,他觉得他们是想让他觉得自己疯了。只能随他去了,没别的办法,可是上帝啊—他想挑衅这个可怜的老基佬,为斯塔维洛斯?尼阿科斯打一架。你知道的—奥纳西斯的对手。他以为那是奥纳西斯。在铁砧酒吧。”玻璃杯碎了的声音。弗兰克或是塔克放了一张约翰?柯川西雅图现场演唱的唱片,把音量调低。卫生间的门开了,塞姆奔进厨房,在碗里大口喝水。弗雷迪从衬衣口袋里拿出小银盒和卷烟纸。他把一片纸放在厨房的饭桌上,正准备往上面撒烟草,但及时意识到纸浸了水。他用拇指把纸捻成团,弹到地板上,在桌上干的地方又放下一张卷烟纸,撒下一撮烟草。“你抽这个。”他跟我说,“我来洗碗。”
“咱们都抽。我来洗吧,你擦盘子。”
“我忘了告诉他们我把烟灰撒到酱汁里了。”他说。
“我不会打断你的。”
“至少他付给弗兰克的钱是其他画廊会计挣到的十倍。”弗雷迪说。
塔克正边说边用手捶打着沙发扶手,还跺着脚。“……所以他想试探他,看看这个染了头发的老家伙是否知道玛丽亚?卡拉斯。耶稣啊!可是他太晕了,使劲在想歌剧演员该怎么说,他本想说歌剧女主角,却说成了家庭女教师。这时候,拉里?贝特维尔走到他旁边,想叫他安静点,他却放声大唱—唱起玛丽亚?卡拉斯的著名选段。拉里跟他说,再不把嘴合上,他的牙就没了,然后……”
“他不是同性恋,在同性恋酒吧里待的时间倒挺多。”弗雷迪说。
我尖叫着从水槽边跳开,打碎了正在水龙头下冲洗的玻璃杯,绿色的玻璃碎片到处都是。
“怎么了?”弗雷迪说,“耶稣基督啊,怎么回事?”
太晚了,我才意识自己刚看到的是什么:J.D.戴着一个山羊面具,那突出的粉红色塑料嘴唇贴在厨房水槽边的窗户上。
“对不起。”J.D.说着从门口进来,差点撞到弗兰克身上,弗兰克正要跑到厨房来,塔克紧跟着他。
“哦,”塔克说,假装失望的样子,“我以为弗雷迪亲了她。”
“对不起。”J.D.说,“我以为你知道是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