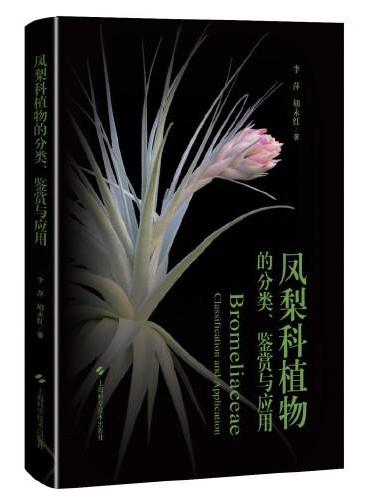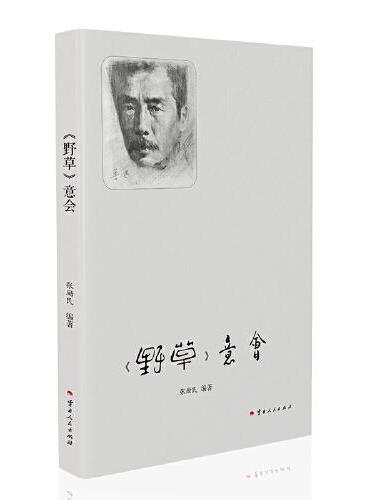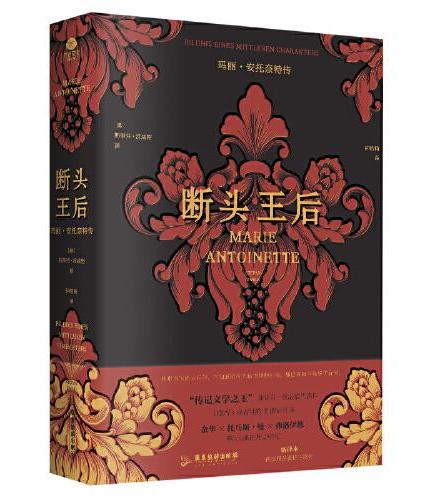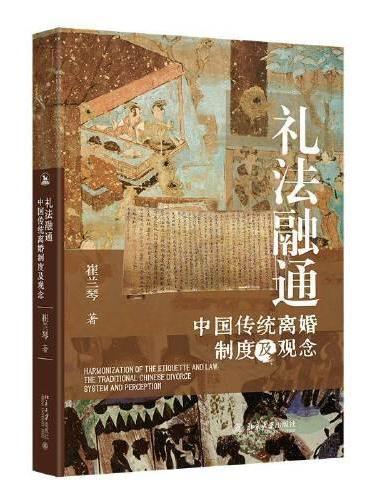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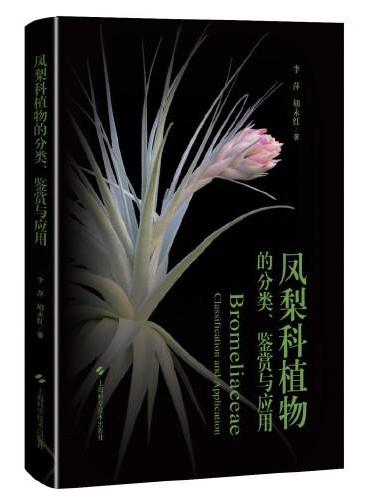
《
凤梨科植物的分类、鉴赏与应用
》
售價:NT$
22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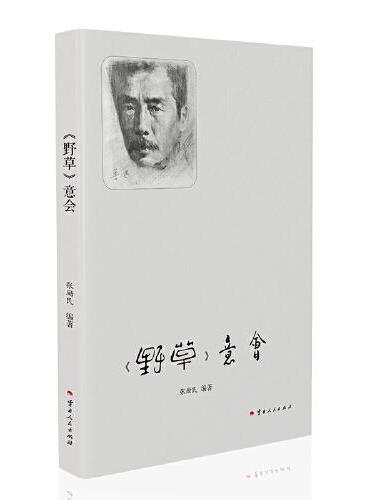
《
《野草》意会
》
售價:NT$
500.0

《
格外的活法
》
售價:NT$
403.0

《
大陆银行(全两册)(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续编(机构卷))
》
售價:NT$
28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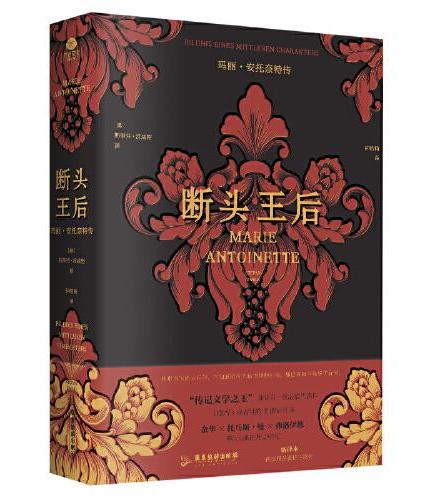
《
断头王后:玛丽·安托奈特传(裸脊锁线版,德语直译新译本,内文附多张传主彩插)
》
售價:NT$
286.0

《
东南亚华人宗祠建筑艺术研究
》
售價:NT$
454.0

《
甲骨文字综理表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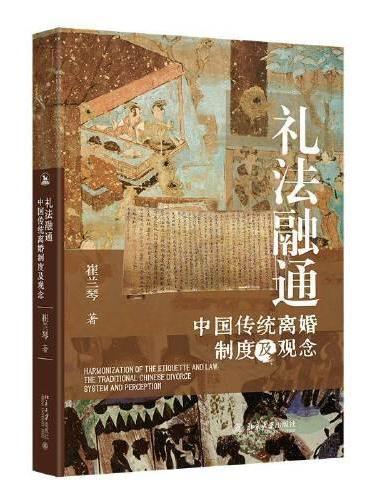
《
礼法融通:中国传统离婚制度及观念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暌违30年,一代学术经典荣耀回归,再现独特精神视野和探索勇气。
“新人文论”丛书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学术素养、独立品格及人文关怀,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与思想。
“新人文论”丛书映照着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对于文学创作及新文学研究,有着持续深远的影响,随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
| 內容簡介: |
|
《所罗门的瓶子》是一本既扎实又独到的集子。众口一词是文学研究的大忌,可不少评论文章读来都觉得似曾相识,令人不免憾然。作者在对鲁迅、茅盾、张天翼、高晓声、沈从文等作家的评论中,在拥挤的文学研究路途中叩开了一道深邃幽长的门户,他致力于作家心理机制的挖掘,把司空见惯的题目另辟蹊径,自成一家。
|
| 關於作者: |
|
王晓明,出生于 1955 年 6 月,祖籍浙江义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许杰、钱谷融教授。198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留系任教至今。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兼及文学理论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有《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无声的黄昏》等多部著作。
|
| 目錄:
|
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论鲁迅的内心世界
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
过于明晰的世界——论张天翼的小说创作
在俯瞰陈家村之前——论高晓声的小说创作
所罗门的瓶子——论张贤亮的小说创作
伟大人格的投影——读《朝花夕拾》
读《沈从文文集》随想
在尖锐的抨击后面——读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
艾芜和外国文学
另外一种散文——读周作人的《乌篷船》
批评的幻想
文学和悲观
批评家的苦恼
对一种缺陷的反省
宽容与自信
关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再思考——从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谈起
在语言的挑战面前
名词的蛊惑——从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谈起
关于批评观的困惑
后记
再版后记
|
| 內容試閱:
|
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
——论鲁迅的内心世界
在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前二十年,鲁迅就已经辞世而去。可说来奇怪,今天谁要是提起他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常常不是他那几十篇出色的小说,而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笔下的那颗“国人的魂灵”,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当评判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总会要遇到不朽这个词,可究竟怎样的人才能不朽呢?首先当然是那些贡献出伟大创造的人,屈原因《离骚》而不朽,黑格尔因辩证法而永存。但是,历史的筛盘上也有例外,它并不只留存伟大的创造物。当专制和腐败弥漫人间,旷世奇才生不逢时的时候,它又到哪里去淘取颗粒硕大的精神晶块?造物主毕竟是公平的,如果杰出人物的精神能量不能向自己的创造物从容转化,它就往往以人格的形式直接显示自己。社会可以阻挠它创造物的形式,却无法禁止它以人的形象来标示历史。不是有人说,谁懂得鲁迅,就懂得了现代中国吗?从覆盖他灵柩的白旗上的三个大字:“民族魂”,我似乎悟出了“不朽”的另一层含义。历史固然有理由轻视个人,在天才和他的创造物之间偏爱后者,但如果是评判一个严酷的时代,我们却不能不特别去注意前者。经过时间的淘洗,一切个人的言行都不免会黯然失色,我们从个人的躯体内照见那卓越精神的蛰伏形态,也很容易会感到深长的悲哀。但这却正是历史的安排,它不但把自己的代表权授予那些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品,而且有时候也授予那些众说纷纭的独特人格。鲁迅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显然把精神作用看得很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都用人的精神状态来解释社会的变动a,还一再强调最重要的是改革国民性。但他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决定论者,一旦涉及到具体的社会问题,他倒每每从物质的角度去衡量得失,并且告诫别人也这样做。他希望妇女能以天津“青皮”的韧性来争取经济权,在小说《伤逝》里更直截了当地宣告:“生存,爱才有所附丽。”孔夫子把“礼”说得比什么都重要,他的呆学生子路因此丧命,鲁迅却嘲笑说,倘若他披头散发地战起来,也许不至于被砍成肉泥吧?中国固然有注重“教化”的精神传统,鲁迅毕竟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深受科学思想熏陶,津津有味地捧读过《天演论》的现代人,他不可能不知道物质环境对一个民族生存状态的决定性影响,不会真以为靠几篇文章就能够起民众于蒙昧,他不是屡次说过,现在的民众还不识字,还无从读他的文章吗?现代中国的启蒙者中间不会再有过去的那种迂夫子了,至少鲁迅不是这样的迂夫子。但是,他为什么又把“国民性”之类的东西看得那样重要呢?
人类世界中似乎有这么一条法则,每一种活动虽然都有自己的原始动因,可一旦发展到高级的阶段,它自己的历史就会对它将来的趋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小至一场战争的胜败,大到一个民族的兴衰,都证明了这一点。这条法则尤其适用于人的精神活动,我们对一种新的刺激作出怎样的反应,正是取决于它和我们现有的全部认识形成怎样的关系。我们常常谈论人的主观能动性,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一种被动性,一种对过去思维经验的身不由己的依赖性。一个人越是成熟,就越不愿听凭外部条件去左右他的认识方向,他总要执拗地按照自己最习惯,往往也是最擅长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这当然是表现了主观对于客观的独立性,可就主观本身而言,却又同时暴露了现在对于过去的依赖性。从鲁迅对精神现象的重视背后,我正看到了这种依赖性。
还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鲁迅就陷进了家道陡落的窘境,祖父入狱,父亲早逝,在这一连串尚可估量的损失之外,他更遇上了人类交往中最模糊也最令人寒心的苛待:不是对你怒目圆睁,而是收起原先那见惯的笑容,另换一副冷酷的嘴脸,使你禁不住要对一切面孔都发生怀疑;不是由于你本人的情况,而是因为你身外某样东西的变化而改换对你的态度,使你发觉自己原来是一样附属品,禁不住感到惶惑和屈辱——鲁迅还是一个少年,就不得不独自咀嚼这份怀疑和屈辱a,这是怎样深刻的不幸?我不太相信中国古人对于苦难的种种辟解,事实上,鲁迅终生都没有摆脱这份不幸的影响。倘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凿开一扇窗户去观察世界,童年时代的不幸就像是构成了鲁迅这扇窗户的窗框。正因为深恶S 城人的势利和冷酷,刺心于本家叔祖们的欺凌孤寡,尤其是五十那一类亲戚的卑劣虚伪,a 他对百草园的热爱就没有能扩展成对大自然的敬慕,与水乡风景的亲近也没有培养出对田园意境的偏嗜,甚至他在南京和日本学到的科学知识亦未能牢固地吸引住他的注意力b——对病态人心的敏感挤开了这一切。请看他一九二四年冬天的回忆:“我幼小的时候……是在S 城,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个女人……据说她……亲见一罐盐渍的眼睛,小鲫鱼似的一层一层积叠着,快要和罐沿齐平了。”c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在我看来,这是鲁迅描画得最逼人的意象d 之一,那个腌臜的渍缸里,其实是装着多么可怕的愚昧!人的头脑中固然拥挤着形形色色的感觉和观念,但真正能扎下深根的却是那些潜踞在记忆深处的片断的意象。感觉本来就漂流不定,观念也常常会改换更新,惟有这种片断的意象始终如沉江的巨石,执拗地限定着人的精神底蕴。鲁迅的心灵是那样敏感而丰富,可至少在三十几年间,他萦怀于心的竟多半是“小鲫鱼”一类的阴暗记忆;看看他的回忆散文《朝花夕拾》吧,有心到童年去淘取愉悦的净水,却还是忍不住拽出了往日的余忿。请想一想,从这样的精神底蕴上,他会形成怎样的认识倾向?
当然,仅仅用鲁迅少年时代的经验还不足以解释他的整个认识倾向。一个成年人对世界的感受远比他儿时的记忆丰富得多,他势必要根据新的经验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态度。如果鲁迅日后遭遇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他甚至有可能逐渐淡忘那往日的阴暗记忆。不幸的是,情况恰恰相反,他成年之后的经历几乎时时都在印证他少年时代的心理感受,从在日本看的那场屠杀中国俘虏的电影,到一九二八年长沙市民踊跃看女尸的盛况,这些现实的见闻不断充实那些“小鲫鱼”式的意象的深刻涵义,以至当鲁迅把它们描绘出来的时候,它们早已不仅是往日的印象,而更凝聚着鲁迅现实的感受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循环,黑暗的现实不断强化他过去的阴郁印象,这种印象又使他对黑暗现象的感受特别深切,随着他那种洞察心灵病症的眼光日益发展,他甚至逐渐养成了一种从阴暗面去掌握世事的特殊习惯。在他儿时的记忆里,周围人们的精神病态常常构成了整个生活的最触目的特征。他以后越是目睹历史的停滞和倒退,越是失望于那些政治或暴力的革命形式,就越不由自主地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民族的各种精神缺陷,甚至到他们当中去寻找黑暗的根源。有位历史学家说,我们将带着旧神迁往每一处新居。就鲁迅的精神发展来讲,这旧神就是他童年时代的阴暗记忆,而黑暗的社会又在所有新居都为这旧神安放了合适的神龛,越到后来,新居的气氛还越合乎旧神的谕示,以至当鲁迅成年以后,对病态人心的注重几乎成为一种最基本的认识习惯了。他当然不会被动地依从这种习惯。他有自己尊奉的哲学观念可以依赖,更有近在眼前的切身利害必须考虑,凭借这两者的帮助,他完全能够超越自己的认识习惯。但是,他仅仅是能够超越而已,在他那些深层的心理活动中,在他对世态人情的具体感受中,在他观察社会的个人视角中——至少在这些方面,他仍然不能摆脱那种习惯。就在唯物主义观念逐渐支配他逻辑思路的同时,那尊旧神依然稳稳地坐在他心理感受的区域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他明明知道物质的决定性作用,却还会习惯性地把“国民性”看得很重。
我们从理性知识当中抽绎出一套对现实世界的完整理解,却又身不由己地要去体味另一些截然相反的生动印象。在许多时候,这种矛盾往往成为创造者的努力的出发点,可如果遇到分崩离析的黑暗时代,当历史和生活的必然性表现得异常复杂的时候,它却每每会成为先觉者的痛苦的总根源。人毕竟不能长期忍受认识上的分裂,他总要尽力把那些出乎意料的感受都解释清楚,这虽然不可能完全做到,但在一般情况下,他是能够把大部分感受至少在表面上协调起来的。可是,崩溃时代的知识分子却往往做不到这一点,他越是预感到山洪正在远处的群峰间迅速聚集,就越会对眼前这泥沼般的沉闷困惑不解。对现实的亲身体验非但不服从他对人生的理性展望,反而常常使他对这展望本身都发生了怀疑。古往今来,有多少有志之士就是陷入了这种矛盾的深谷,左冲右突,精疲力竭。我甚至觉得,黑暗时代对先觉者的最大的折磨,就是诱发和强化他内心的这种矛盾。不幸的是,鲁迅正遇上了这种折磨,那个时代以他童年的不幸为向导,以他成年后境遇对这份不幸的强化为推力,一步步也把他拖进了这样的一条深谷。
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对于人民的看法。当谈到大众的时候,似乎有两个鲁迅。一个是不无骄傲,认为“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a。并且引用报载北平居民支援游行学生的消息,有力地反问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b 对鲁迅来说,“人民”大概是最重要的认识对象了,他不会仅仅凭直接的印象就下判断,他势必要反复审视,要考虑到许多感性以外的因素。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决不会愿意否定大多数人的历史价值,他奋斗的目标正是为了唤醒人民,倘若否定他们,也就否定了自己。所以,只要能够抑制住悲愤的情绪,他就会以各种方式从整体上去肯定人民,那些为之辩护的话,正是他必然要说的。但还有另一个鲁迅,他满面怒容,竟认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c。即使到了晚年,无论是挖苦中国人“每看见不寻常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d, 还是拿街头玩把戏的情形来比喻民众的甘当看客e;也无论回忆绍兴“堕民”的“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f,还是由浙江农民的迎神惨剧而感慨他们“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g,都使人明显感觉到,那种对病态人心的心理直感仍然强烈震撼着他的灵魂,他好像仍然从“愚民的专制”的角度去理解世事,仍然把病态的精神现象看得很重。就人的认识动机而言,他对一样事物的理解最终应该趋向统一,可鲁迅对“人民”的认识却似乎相反,他越是仔细考虑,分歧反而越大。随着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自觉日益明确,他那种从整体上肯定人民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但他又无法摆脱种种关于“愚民的专制”的阴暗思路,这个令人战栗的提法并不是一种高度概括的逻辑结论,而是一种心理感受的牢固的凝聚,它的根基主要并不在鲁迅对感觉材料的逻辑整理,而在于社会很早就强加给他,以后又不断强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习惯。所以,它完全能够抵抗住理性愿望对它的压制力量,支撑那压力的仅仅是个人的理智,而在它背后,却站着全部黑暗的社会现象,以及它们过去和现在对鲁迅心理的全部影响。
正是这种心理感受和逻辑判断之间力量上的不平衡,决定了鲁迅晚年在理解“国民性”问题上的复杂变化。他早年似乎是把人民的不觉悟主要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麻木,还到历史中去寻找原因,用长期为奴造成的奴隶意识,用老百姓对于一等奴隶地位的羡慕来解释这种麻木。他那“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王道和霸道相交替的历史观,更在他头脑中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a。但是到一九三四年,他的说法完全不同了:“其实中国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所谓霸道,就是用暴力强迫人民当奴隶。鲁迅把中国的漫长历史全部归结为霸道,说明他不再相信精神奴役的成功,不再仅仅用麻木之类的奴隶意识去解释人民的命运;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把“国民性”扭曲成现在这样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是历代统治者的暴力高压。每个时代都对人们的认识倾向具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鲁迅的时代也不例外。从二十年代起,他经历了多次血腥的惨案;到上海以后,又时时闻知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的凶讯,他不可能不意识到暴力在黑暗专制中的巨大作用。他爱读各种“野史”,其中对历史上那些屠戮和酷刑的详细记载,又反过来印证了现实对他的刺激。那正是一个迫使人把注意力转向物质状况的时代,鲁迅对于王道的否定,就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这种制约,他在这一方面,并没有走在许多同时代人的前头。
我要说的倒是另一面,那就是尽管对物质因素的理性尊重日益渗进了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这却并没有把他引离开对精神病态的关注,甚至反而强化了这种关注。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尖锐地指出:“暴露幽暗者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b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在谈到忍受的时候又说,如果深入去挖掘中国人的忍从:“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c 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在受苦,而是明明知道,却不愿反抗;不但自甘于当奴隶,还憎恶提醒他的人。鲁迅这时候还用这样的眼光去打量群众,谁能说他改变了观察“国民性”的基本角度?恰恰相反,越到晚年,越意识到统治者的暴力压迫,他对奴隶意识的探究越加发展到令人战栗的深度。感受习惯的旧神对他影响太大了,他把对物质作用的重新认识都当作了校秤的砝码,他郑重地列出它们,不过是为了更准确地判明民族的精神畸形。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把精神作用看得很重的人。
这就是说,鲁迅始终没能突出那条矛盾的深谷,有时候还仿佛愈陷愈深。感受习惯和逻辑判断的分歧,对病态的精神现象和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的认识分歧,最终都造成了他整个理性意识的分裂。因为理性本身的复杂性质,一个心灵丰富的艺术家产生理性的分歧,本来并不奇怪。但是鲁迅理性意识的分裂竟有如此尖锐,却实在令人忧虑。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固然还只是刚刚沾上一点逻辑推理的边,那从社会信仰和功利意识出发的对人民的抽象肯定,却也远远不能消除他对精神病态的过分敏感。他极力说服自己去依靠大众,却偏偏多看见他们张着嘴的麻木相;他想用文章去唤醒他们,却越来越怀疑他们并非是真的昏睡。这就好比已经上了路,却发现很可能方向不对,到不了目的地,他怎么办?
还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鲁迅就写过这样的话:“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旦其首矣。然为基督宗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难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a 他已经向黑暗进攻了,要想不泄气,就得寻一样精神支柱。在启蒙时代的欧洲,先驱们是向人的理性,向建筑在这理性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寻求支持,他们的旗帜上写着“人”。这以后,启蒙者的身份逐渐由贵族变成平民,“人”也就逐渐演变为“人民”,由抽象发展成了复数。但鲁迅却没有先驱们的这份信心。他的感受习惯使他经常不相信复数的人。他从阿Q 们身上看到的往往不是理性,而是奴性。他本能地就要从相反的方面去寻找支持,不是复数,而是单数,不是人,而是魔。他十八岁的时候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家乡的:“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 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a 他还以离群索居的意思,取了一个“索士”的别号。既然亚当们不一定会如梦初醒地随他而起,他就得准备独自一人奋斗下去。如果他们甘愿被圈在伊甸园里当愚民,那他就只有背负撒旦的恶名了。他在这时候把个人和撒旦等同起来,说明他已经敏感到自己不但必然是先驱,而且多半也是牺牲。这是怎样深广的孤独感!
这极大地影响了鲁迅的处世之道。既然只能独战,他势必要把个人的独立性奉为根本。首先是看世的焦点。无论是叹息“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还是疾呼“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他注意的似乎都是顽强奋战的个人,而且是身处逆境的个人。这正符合他对历史的看法,历代统治者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制造愚民,那相反的力量当然只能存在于清醒的个人。其次是衡世的尺度。他无论判断什么事,都坚持以亲见的事实为准,他曾引用肖伯纳的话,说最好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倘碰上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他就采用一种以眼见的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推论的独特方法,他三十年代初的赞扬苏联,就是这样来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处世的态度。因为极端珍惜个人的独立性,他对参加团体活动似乎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一九二五年春末,在回答许广平关于参加国民党的询问时,他这样说:“如果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b 从一贯对别人借重和利用自己的异常敏感,到晚年的坚决不参加“文艺家协会”,都可以看出他给自己划定了一条基本界限,那就是为了维护独立地位和思想自由,他宁愿脱离任何团体。他甚至怕当名人:“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c 我能够理解鲁迅这种捍卫独立性的决绝态度,在一个常常并不信赖多数的人眼中,集团活动不可能占有太重的位置。在中国这样长期遭受专制统治的国度里,惟有大勇者才能不畏独战,鲁迅所以每每比别人看得深,一个主要原因,不正在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吗?
但是,他看来看去,竟只能找到这种散发着撒旦气味的“任个人”思想,却实在使人悲哀。社会是由复数组成的,也只有靠多数人的力量才能改变,一个有心献身启蒙事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何况他自奉是战士,诗人可以特立独行,战士却必须和左右保持一线,越是严酷的时代,社会战场上就越少有独战者自由驰骋的余地。鲁迅肯定没有想到,当他用“任个人”的思想来协调自己逻辑判断和心理感受的矛盾时,这思想却会把他引入另一种客观身份和主观心境的矛盾。他不得不努力去说服自己,不但在整体上尊人民的命,还要在具体的斗争中听团体的令。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他的确是竭诚尽心,在实际行动中尽量和别人取同一步骤。但这并不等于他内心就没有踌躇,一旦处境趋于恶化,这踌躇还日渐增强起来。
对北方许多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人来说,二十年代中后期是一段不堪忍受的岁月,谁能想到,紧接着新文化运动而来的竟会是那样肆无忌惮的复辟和反动呢?但鲁迅不同,他早已有过类似的经验,从辛亥革命开始,他看够了一幕幕称帝、复辟的丑剧。他必然要把这一次的反动和他过去身经的反动联系起来,甚至和他从古书上读到的那些历史上的反动联系起来,结果,他得到的就不仅是强烈的失望,更有深刻的怀疑。对个人来说,历史太广阔了,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站脚的地方去打量它,如果不幸置身于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那就非要超越自己才能保持对于历史的信赖。社会也太庞杂了,泛泛地相信历史进步论还比较容易,倘要把这种信念贯彻到对许多具体现象的理解中去,却非有通达的气魄和坚强的理性方能做到。可惜的是,鲁迅那把一切唯事实为重的心理尺度牵制了他,他无法用对进化论的抽象肯定去解释现实黑暗的卷土重来。他固然不相信历史会倒退,却禁不住对历史的停滞深感沮丧:“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a 至于“历史如同螺旋”一类的话,更在他笔下多次出现b。当他依着这样的思路去估量民族的精神发展时,那种对于联合作战的深藏的踌躇就剧烈地发展起来了。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先是在私人通信里,接着在公开的文章中,鲁迅接连发出了对一些年轻同伴的激烈指责。当去广州时,他甚至疑心一个学生是密探c。这和他以前对待青年人的那种隐恶扬善、一味鼓励的态度形成如此触目的对照,似乎他是对年轻一代极度失望了。可实际上,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进化论的虔诚信徒,就像对人民一样,他对青年也有两种不同的认识。在整体上,他相信青年必胜于老年;但对具体的个人,他并不一概而论。还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他就表示过对北京大学青年们的不满:“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指蔡元培)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d 心中早就有这样清醒的感受,就是再发现几个青年的机巧和狭隘,他也不至于会震惊到失去常态。所以,倘说高长虹们的确使他失望了,这失望却主要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自己,不是对身外原就各各不同的青年,而是对自己那以为可以同他们结伴前行的奢望。既然在中国,历史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然进步,那精神上的愚昧状态也就不会随着一代愚民的消失而消失;不但在上辈和同辈人中间,自己当然要背负撒旦的恶名,就是和较年轻的人们在一起,恐怕也还是免不了独战的命运——我很怀疑,鲁迅这时期对高长虹们的激烈反应,正是起源于类似这样的阴郁思路。因为,几乎和这些激烈的反应同时,他那撒旦式的情绪也日渐强烈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