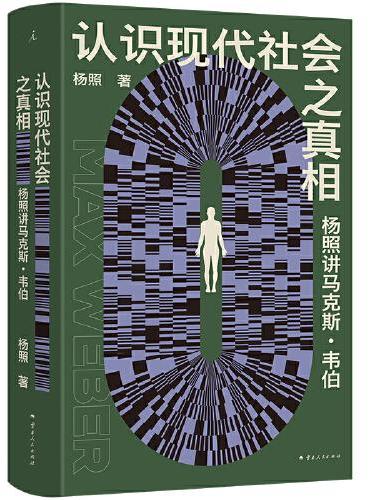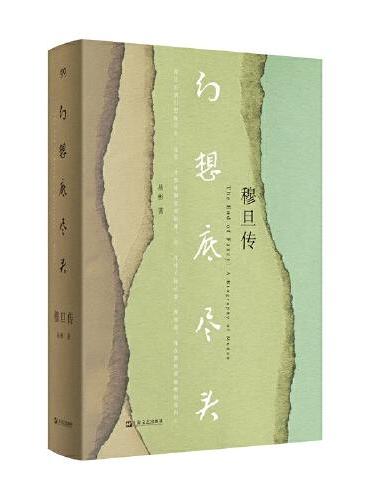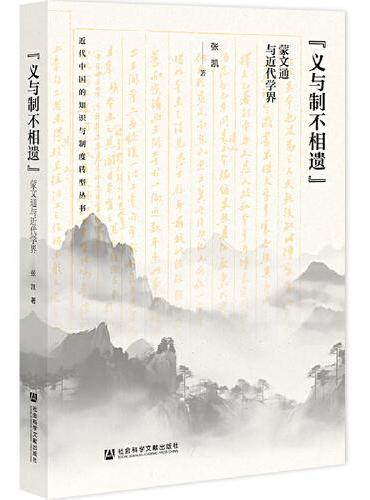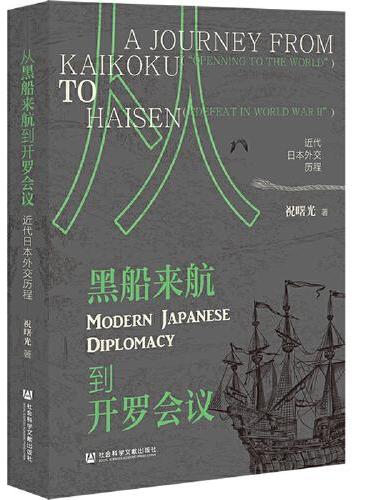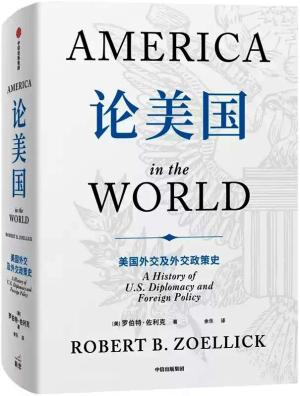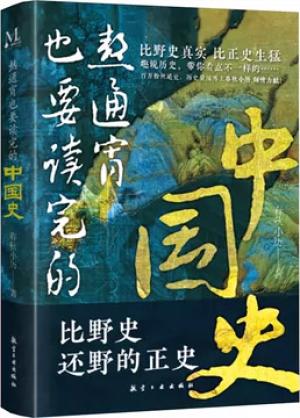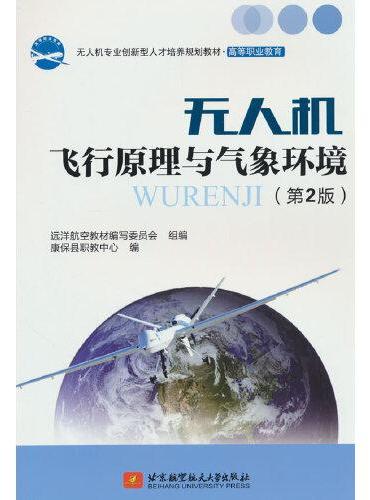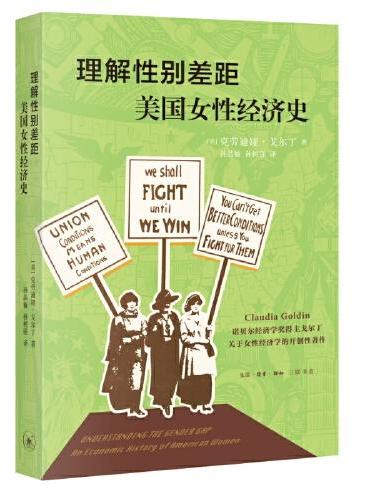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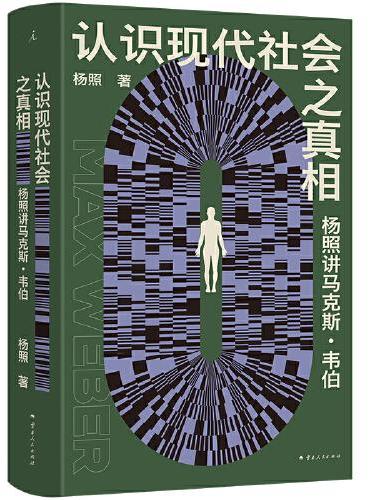
《
认识现代社会之真相:杨照讲马克斯·韦伯
》
售價:NT$
4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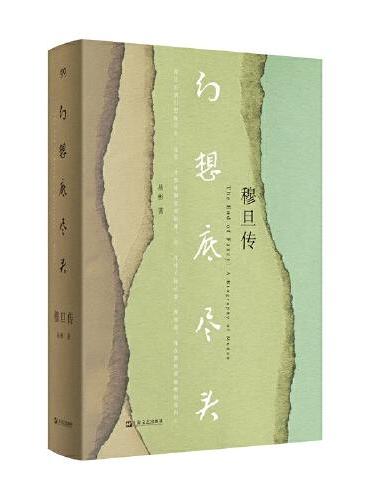
《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穆旦年谱》编撰者历时二十余年心血之作,基于《穆旦评传》精心修订,文献翔实可靠,完整讲述了一位中国诗人与翻译家并不平顺的一生。)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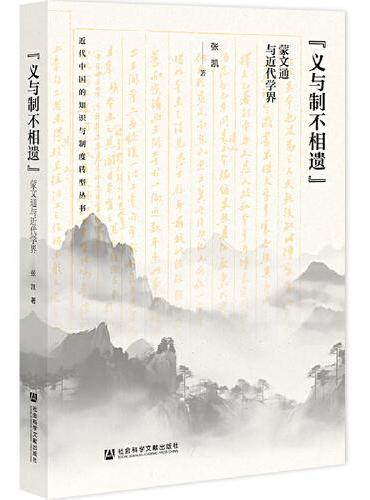
《
“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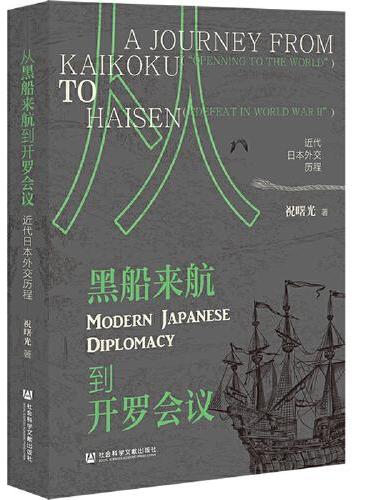
《
从黑船来航到开罗会议:近代日本外交历程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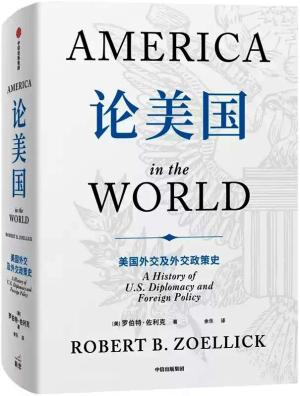
《
论美国(附赠解读手册)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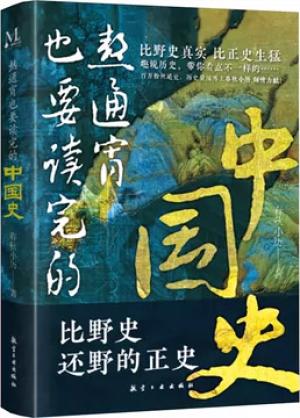
《
熬通宵也要读完的中国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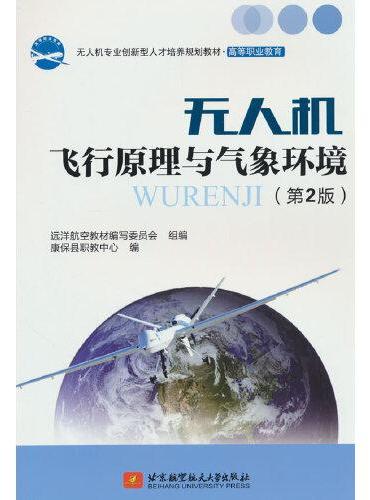
《
无人机飞行原理与气象环境(第2版)
》
售價:NT$
1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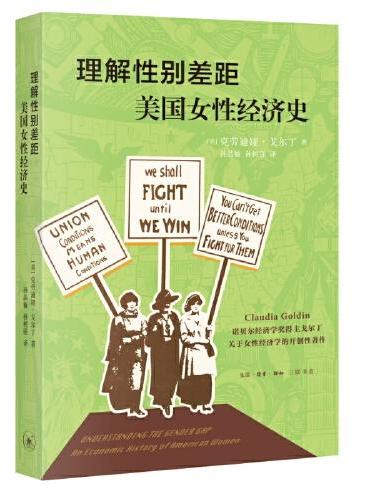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NT$
418.0
|
| 內容簡介: |
|
本书辑录了熊培云对生命、爱欲、媒介、美和正义等方面的思考。不曾毫无节制地抒情,也未沉迷于意象的构建,它们以诗或“诗评论”的形式呈现,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与光亮。当人们喊出“文学已死”的时候,作者却逃向了它。作者相信上帝的语言就是文学的语言,上帝不是真理,是意义,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生产和捍卫意义。
|
| 關於作者: |
熊培云
评论家,时代观察者。1973年生于江西农村,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曾任《南风窗》杂志主笔、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现任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 目錄:
|
自序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01
第一季 春
春日 39
星空 40
一代人 41
存在 42
你是你的沧海一粟 44
鹅卵石 45
除了美,我一无所知 46
春梦 48
孤星 49
梦醒时分 50
神回复 51
宿命的诱惑 52
镜中的上帝 53
这世上有两个你 54
谁没有两颗心 56
找我 57
第一次囚徒 58
虚度 61
放下 64
无常 66
几世同堂 68
其实我们并不拥有 70
美的箴言 71
去国行 72
一个人的人海 73
意义女神 74
第二季 夏
夏日 81
下雨天 83
风景 85
我常常思念南方 87
缅栀花 88
回家的少年 91
手机 93
破碎的人 94
后现代爱情 95
喇叭 96
谋杀 98
未见之证 99
上帝的语言 100
语义重复 103
十字架上的耶稣 104
钥匙 106
节日 107
赞美 109
生命在银行里 110
规范 112
第三季 秋
秋日 117
小王子 119
幸福大街 120
Neverland 122
夜奔 125
如果爱 127
此地今生 128
天长地久 130
过客 132
默誓 133
失眠的夜晚 134
那些哭着说爱我的人都烟消云散了 136
爱之三阶 138
Youtopia 139
安眠曲 140
身上人 142
这世界是女人的 143
坏梦想 145
秋天的遗嘱 146
葬礼 147
那时候我们还年轻 149
真爱公司 150
第四季 冬
冬日 155
寒潮来临 156
哀伤已是如此艰难 157
喜剧的反抗 158
人的命运 160
音乐之声 161
狙击手 163
理由 164
投诚 165
人形昆虫 167
成功家 168
屠婴 169
审判 170
连年有鱼 171
衣冠禽兽 172
偷生 173
寻牛 174
感恩 175
局外人 176
爱国便利店 177
恐怖分子 178
打群架 179
死神来了 180
牛的传人 181
捉刀 182
寻仇 183
爱与愤怒 184
英雄 185
忏悔 187
亡羊 189
万有引力 193
第五季 春
下雪天 197
重逢 198
万物哀伤 200
正直的两难 202
千声叹息 203
最后的世界 204
我的忧郁里有明亮的未来 205
所以然 206
我醒来算了 207
悲剧的诞生 209
Being Present 210
领悟 211
生活在湖边 212
赶花人 214
寂静 216
钢琴立于墙角 217
城市之光 218
这些年我游游荡荡 221
星月夜 223
我道歉 225
希望罪 227
致哀伤的人 228
暴风雪 230
这是我想要的美好人生 231
春日已近 232
我时时畏惧人群 233
无怨 237
天命昭昭 238
附录 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 240
后记 天命与人生 257
|
| 內容試閱:
|
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
拥挤的车站,混乱的码头,岁尾年关千里奔袭、穿越风雪的摩托车队,说到中国农民候鸟一般从乡村到城市,从异乡到故乡,你难免会想起这些奔忙于路上的种种场景。和“出埃及”一样,“在路上”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没有“在路上”,也就不会有希伯莱人的“出埃及记”以及我曾叙述的“出乡村记”。没有“在路上”,凯鲁亚克的著名公路小说也不会流传为经典,更别说在其后催生出与“在路上”相关的一系列文化。
1980年代(有人认为八十年代是从1976年到1989年),伴随着大批青年回城,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也开始试图进入他们梦寐以求的宽阔城市。
这是一个让人讴歌的年代。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万物开始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竞相绽放。
理性的花朵
毫无疑问,此前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告别“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与领袖崇拜便已经代表着某种政治理性的回归。至于社会理性在什么时候开始回归,似乎没有可量度的标准与标志性事件。不过,找到一些与之相关的社会现象并不难——当然,这同样得益于政治上的部分解禁。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政治禁书”、“被流放的知识”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视野之中。尽管禁忌仍在,但不再“知识越多越反动”。
对于那个书籍极度匮乏的反智年代里的悲伤故事,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略有记载: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它的样子越来越糟。我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余生也晚。和王小波比,虽然我也曾经在乡下生活了不少岁月,但我似乎要幸运得多。因为当我青春萌发,开始极度渴望知识与书籍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流行于八十年代的读书热与文化热。
1980年代的十年,文化热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尤其从1984年开始,有关哲学、政治与社会的讨论大量增加,文化活动四处开花。一些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陆续在郑州、上海、深圳、武汉等地举行,许多名牌大学也都建立了关于文化、文化传统、儒家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中心,各地纷纷组织面向公众的传统文化讲习班,无数关于文化的文章充斥各类刊物,各种文化类书籍摆满了书店。那个年代还没有哈里·波特,但正如陈彦先生在《中国之觉醒——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历程》一书中所描绘,1984年到1988年间的中国,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词的魔法,“文化这个词与主题成了当时中国真正的时髦”。而19841986这三年铸就的黄金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环境较为宽松,文化热可谓如日中天”。
和今天堆满大小书店的各类考试学、成功学书籍相比,八十年代人们的读书生活显得更有品质。此时,哲学、美学、小说、诗歌、科学等各类书籍纷纷涌现,欧美的各种经典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诸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弗洛依德的《梦的解析》等都成了无数才子佳人的枕边书。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来丛书”12种出版。第一批书仅用了4个小时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3万册,又在几个月内全部卖光。其后的“五角丛书”,几年间销售了1000多万册。
尽管仍然实行着严格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九十年代初我离乡上大学时甚至还必须从家里寄上一袋大米给学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差距远不如九十年代以后那么明显。那时候,即使一个像我这样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学生,也经常有机会被母亲带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课外书。母亲识字不多,每次都会请教书店里的读书人我挑的书是否真的有助于学习。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有时还会让隔天进城的村民将我要买而未买的书给捎回来。然而,这个中间环节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有一次我发现有本作文书前面少了几页,却又不好意思责备给我捎书的村民买了一本残书,只好将就了。直到几年后,我才在无意间知道这位村民因为半路内急,撕了前面几页擦了屁股。这个细节在我看伊朗儿童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时总会想起来——成人总是在不经意间毁坏儿童的世界。
拜赐于当年的读书热,我在中学的图书室里也没少找到流行于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让我备感吃惊的是,2008年我重回母校时,发现由于近年来农民拖儿带女大量外出,当地生源急剧减少,学校因此变得无比萧条。而当年那间让我垂涎欲滴的图书室如今空无一书,像遭了洗劫一样,只剩下满地的灰尘与几块断裂的架板。据留守的教师们说,许多老师都去沿海“打工”了。而当年那位曾经住在图书室边上的有志青年,早已弃教下海,远走他城,终于在2000年后做起了细节管理的生意,写了一本《细节决定成败》,几年间加印了几十次。
时光悄然流逝。我已经记不清在这所学校读过什么书——舒婷、北岛、三毛、席慕容、彭斯、歌德、泰戈尔、海顿斯坦、聂鲁达、普吕多姆、蓝波、雨果?值得庆幸的是,虽然身处乡下,借着当时席卷全国的文化热与读书热,我还是有机会读到过几本即将影响我一生的书籍,有机会亲历《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里文化相遇之奇境——只不过,那位最初影响我的外国才俊不是戴思杰笔下的巴尔扎克,而是英伦岛上的雪莱。在我的书房里,至今仍保留着我在14岁那年买到的杨熙龄选译的《雪莱抒情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正如傅雷的译者献辞为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锦上添花——“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杨熙龄写在雪莱诗选后面的《译者附言》同样让我一生受益。①
我相信,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每个人在其年少时都可能有着某种兼济天下的理想。回想起来,八十年代更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加论文”的年代——在此之前,写《未央歌》的鹿桥曾经用“诗歌加论文”来形容他在西南联大时“有理性,亦有心灵”的美好人生。因为诗歌,许多人在清贫而跳跃的生活中一厢情愿地做起了精神贵族。若非如此,你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本薄薄的《雪莱抒情诗选》能够畅销10年,足足卖出50万册。此前,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本诗选从1964年排出清样到1981年终于出版,足足等了17年。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意与想象的年代里,才有了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姐姐,今晚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样温暖人心的诗句;才有了《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这样共写心灵史诗的流行音乐;才有了雄心勃勃、壮志满怀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夜晚,当我偶尔听到电视里播放《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老歌,想到当年高唱凯歌的年轻一代如今纷纷下岗,心中竟涌起一种莫名却又难以抗拒的伤感。然而,即便如此前途茫茫,谁又能否认八十年代他们刚走出时代“黑屋子”时的意气风发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无比赤诚?
我在梳理八十年代的记忆时,找到了一些相关的影像志。它们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那个时候的人们虽然处在一种普遍的贫困中,但是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却是显而易见的:
1980年8月30号,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在外电报导中,这次会议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是壮观的政治仪式,而是一次做出重大决策,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民代表会议。
这次会议第一次邀请外国记者参加,并事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驻京外国记者感叹道,上一次召开人代会的时候,外国记者都被送到天津去旅行,人代会就像一次地下会议,甚至不许代表们告诉自己的家属,只是告诉代表们要带些钱和粮票。
在这种气氛之下,有人担心自己怕是要遇到什么麻烦了。这次会议也是充满直率的、生动的言论的会议,第一次出现了人民代表毫不客气地质询部长的场面。国外报道的结论是,中国正在谨慎的、逐步的成为较为开放的社会。(《电视往事》解说词)
我说八十年代是一个美好年代,是一个“恶补禁书”的年代,并非要武断地赞美那个时代完美无缺,或者断定它比现在这个时代好。
毕竟,那个年代同时也是一个流行“清除精神污染”的年代,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年代,一个可能因为跳舞像马燕秦一样被判处死刑的年代① ,一个流行“严打”的年代(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因为拦路抢劫被枪毙),一个由对抗走向激烈的年代。
我上面提到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同样以其坎坷见证了时代命运之波折。1979年2月,当谷建芬在家里为这首歌谱曲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受到批判。三十年后,谷建芬坦承这首歌给她带来了灾难。有人认为这是一首反党歌曲,他们甚至给谷建芬扣了一顶帽子,叫“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还有一顶帽子是“用资产阶级的音乐毒害青年”。而谷建芬的另一首歌曲《烛光里的妈妈》也被定性为建党以来最大的反党歌曲,因为里面用了这样一些句子形容“妈妈”——“您的黑发泛起了霜花”、“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您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不愿牵着您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等。有人说“妈妈”就象征党,你把党说得这么糟,这还了得。① 那时,在北京举办的创作研讨会上,电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也被批判为流氓歌曲。
我只想在此强调,那个心灵与理性的花朵并蒂绽放的年代,在其匆匆落幕、戛然而止之前,人们已经重拾生活的美好理想,紧随自己命运的召唤,开始追求心中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追求一个甘于平凡的理想的世界。
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刚刚从社会混乱与政治高压中走出来的他们,已经看到了隧道外的一丝丝光亮,初尝了长在新时代路边的一枚枚禁果,像是怀着一种初恋的心情,试着一步步走向开放与自由。而这一切,也正是被圈定在城市之外的农民得以“盲流”进城的大前提。
心灵的歌声
谈到八十年代的心灵,“诗歌热”无疑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种表现。不过,接下来我更愿意回顾那些回荡在八十年代的老歌。许多老气横秋、自诩高雅的人常常批评流行音乐“低俗”,是“靡靡之音”。然而,就是在那个年代,许多人不再做“红旗下的蛋”,而是做了“靡靡之音下的蛋”。
对于生长在乡村的孩子们来说,流行音乐首先代表的是公正,其次才是艺术。它首先是生活的音乐、平民的音乐,它像太阳的光辉一样,眷顾大地上的每个孩子,不仅照耀都市,也照耀乡村。与此同时,它又不像革命年代的歌曲一样强行灌输于人。毕竟,每个人因为无力抗拒而获得某种东西,那不是平等。
对于刚刚从极端年代里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或多或少都与“外面的世界”有关。即使是《乡间小路》与《垄上行》这样看似本土的乡村歌谣,也是从台湾吹来的新风。
“白天听邓小平,晚上听邓丽君”,有人将中国的八十年代简化为“双邓时代”。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邓丽君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齐名”,一个称“老邓”,一个叫“小邓”。前者主导政治,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后者引领生活,是中国人的生活与审美回归常态的标竿;前者让中国走向开放,后者让社会回归多元。告别《红灯记》里“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嗜血斗志,中国迎来了邓丽君式的温婉甜美。“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邓丽君借着她的“甜蜜蜜”征服了新一代中国人的心。当人性重新舒展,任何横加指责都已经无济于事,都已经阻挡不住一个开放而多情的时代卷土重来。
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一些当时流行的歌名与歌词。不需要太细心,你就能发现,那个年代的许多老歌都带着某种“在路上”的情调。同在蓝天与星空之下,从故乡到异乡,从乡村到城市,无论是欢欣还是愁苦,道路的另一端,总是延伸着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所特有的希望、自由与牵肠挂肚。
如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外面的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李娜的《人在旅途》:“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黄家驹的《海阔天空》:“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姜育恒的《驿动的心》:“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费玉清的《梦驼铃》:“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盼望踏上思念路,飞纵千里山,天边归雁披彩霞,乡关在何方??”;崔健的《花房姑娘》:“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它们一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最动人者当属文章的《三百六十五里路》:“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餐风露宿,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故乡到异乡。三百六十五里路哟,从少年到白头??”
与远行和相思有关的还有徐小凤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姜育恒的《再回首》,费翔的《故乡的云》、《海角天涯》以及那首让所有年轻人眼热心跳却又无比释然的《溜溜的她》??除此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潘安邦翻唱的苏芮那首见证时代波折的《跟着感觉走》。时至今日,我仍能想起上中学时边听这首歌边赶路的情景。——“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遗憾的是,正是这首曾经给年少的我带来无尽轻盈、快乐与青春活力的歌曲,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被认为有罪与不合时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同样,三毛写的这首《橄榄树》曾经让无数年轻人动容。远方是希望所在,只是由于经济与政治等原因影响,那时中国人能出国旅行者非常少,而来自台湾的三毛,以一种“万水千山走遍”的随性与坚毅,为那些喜欢听她讲述流浪故事的人打开了人生的视界。
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许多都是情歌。面对“外面的世界”时的忐忑不安,同样在这些歌曲中表露无遗。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邓丽君的那首《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待,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若干年后,当我辞去第一份工作赴法留学时,平时最常听的是一首法语歌——《Làbas》。这个词可译为“远方”、“彼岸”或“他处”。它是法国著名艺人JeanJacques Goldman在1987年翻唱的一首对唱歌曲,很有点《走西口》的味道。其大意是:一位乡下男子要外出打工,他的未婚妻拉着他的胳膊,劝他说你不要走啊,不要走,外面有太多风雨雷霆、艰难险阻,你不如留下来,我要为你生儿育女,而且,“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我们还有好多爱要做呢)。
尽管送行的场景颇为相似,不过这首歌比“汪汪的泪水肚里流”的《走西口》要深刻得多。而最让我感同身受的正是表现在Goldman苍茫男音背后的那种自由与自我:
远方一切都是新的,自由的大陆,尚待开发,没有栅栏。而这里,我们的梦偏狭无比,所以我要远行??这里一切已提前安排,我无力改变,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出身,而我生于贫寒??远走他乡需要雄心壮志,在我这个年纪,改变一切还有可能。但有信念和力量,梦想就不会遥远??在远方我可能会失去你,留在这里我将失去我自己。
这是一首赞美自由与开放的情歌,但我更愿视之为对同样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出乡村”的遥远回声。毫无疑问,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出乡村”在世界各国都是最普遍不过的事实。区别只在于,在一个功能正常的国家,一个男人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妻子或情人可能会阻拦他,因为“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但是政府不会像小情人一样拽着外出谋生的男人的胳膊说:“不许走,你要对我负责!”
事实上这种事情并没少发生。如前文所述,在极端的年代,在一个国家压倒社会、政权压倒人权的国家,既无市场经济,又无市场政治,人们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的权利均被剥夺,不得不做“工用螺丝钉”和“农用稻草人”,随便挪动自己的位置都算是对集体的“背叛”。而如果你要绝食抗议,那就属于破坏生产工具了。
我念书的中学坐落在千米高山脚下。那时候外出,还没有女生拉着我的胳膊浅吟低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更不会有“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那时我的生活里没有花,所有野花也都是别人的。记得是在一个夏日的清晨,我带着从学校食堂买的几个馒头和一本自己装订的诗集,孤身一人坐车到一百公里外的《九江日报》编辑部投稿。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大概正午时分,车子终于停靠在市中心的甘棠湖边。就在下车的时候,猛然听见湖对岸传来了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到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时常动情于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即使是这偶然的境遇也足以令我感恩。回想起来,这是一次多么完美的旅程!远处的歌声,时代的心跳,仿佛要将八十年代第一次远游的你置身于一场记录时代的大型MTV之中。这些年,我辗转于不同的异乡,虽然渐渐忘记了故乡的一些人和事,甚至连中学时有些同学与老师的名字也已淡忘。然而,十六岁那年第一次出远门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宛如昨时。生命的激情,梦想的催促,标刻时代的情歌,久违的怦然心动,都在那一刻交错、缠绕。而你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翩翩少年,于恍惚之间竟不知所以,愿意将自己的一生交付给文字,以为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恋爱真的开始了。
每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若干年后,我之所以中断写诗,同样是因为诗歌不足以表达我自己。如荷尔德林所说,人类充满劳绩,应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人类不能没有诗意,不过诗意未必要通过诗歌来表达。更何况,我常常想的是,这个世界包括我的人生并不缺少诗意的描述,而是缺少通向诗意的道路与方法。
没有人能够复原八十年代。在这个新时代,政治渐渐让位于生活,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如张雨生所唱的那样:“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的未来不是梦》)
时至今日,每当我听到这首老歌的时候,总免不了想起当年初听它时的情境与心境。恍惚之间,我甚至认为张雨生的这首歌就是唱给我和我们——那些在炎炎烈日下陪着父母忙“双抢”① 的乡村少年听的。他们虽是被“一国两策”流放或隔离的一群,但一样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理想与抱负,更受着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眷顾,让他们虽然无缘城中的蜜饯,却获得乡野的灵性。
后记 天命与人生
整理完文稿,再配上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拍的照片,一切接近尾声。从数以万计的照片中挑出这些照片,并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