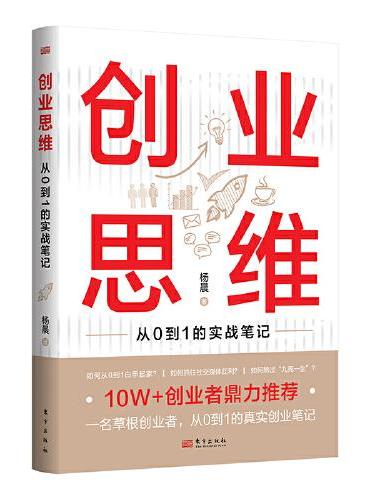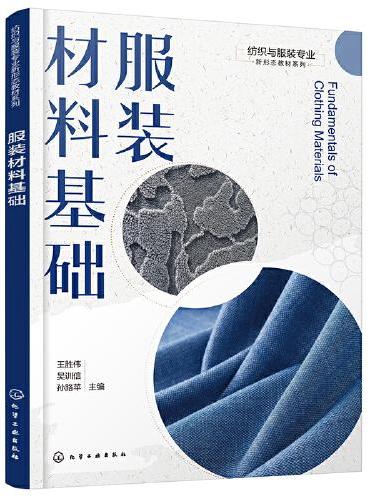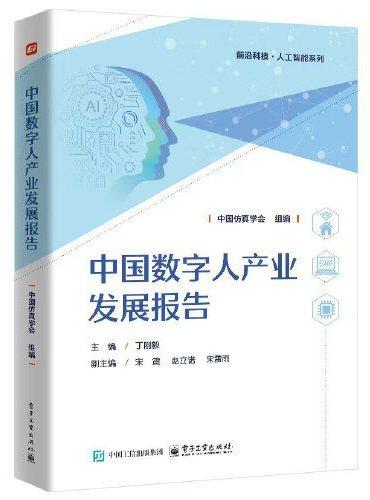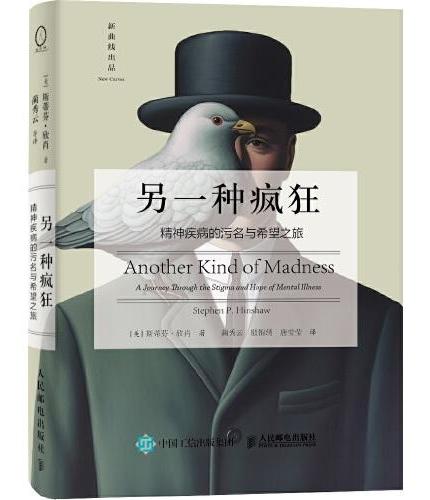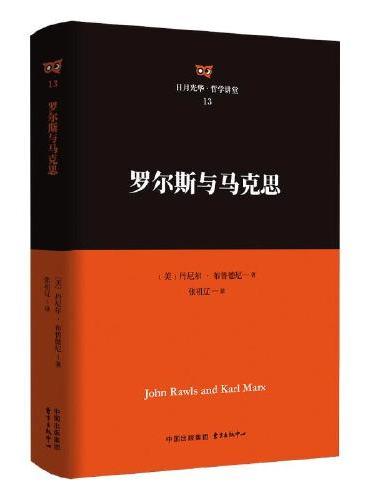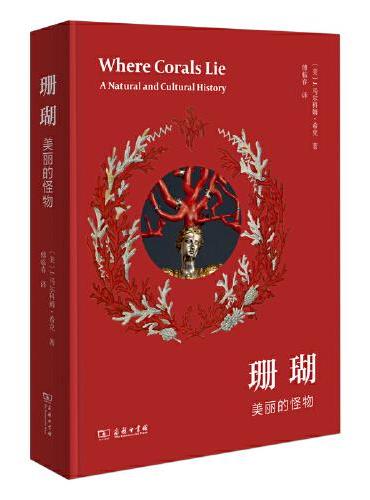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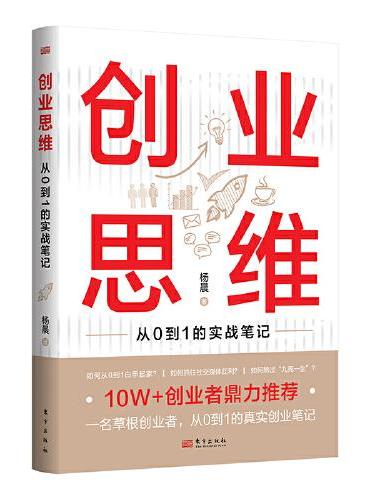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NT$
356.0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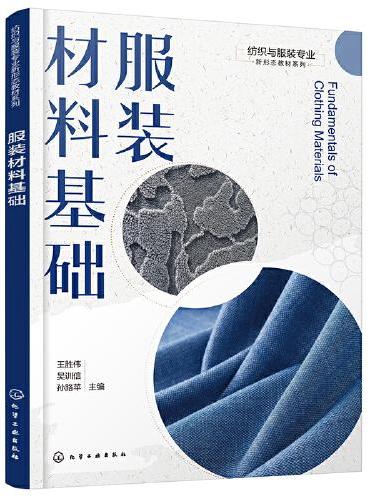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NT$
296.0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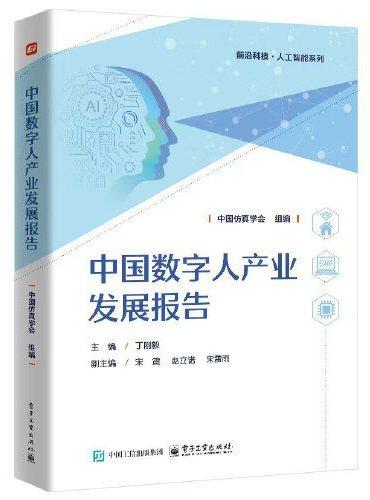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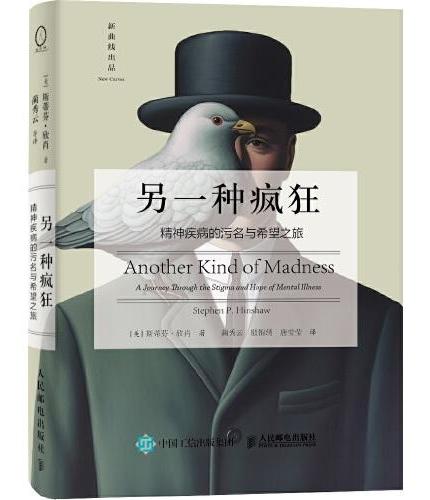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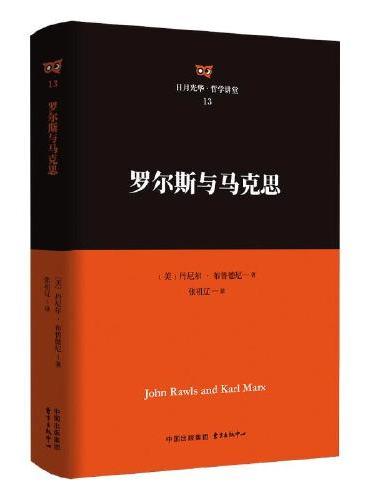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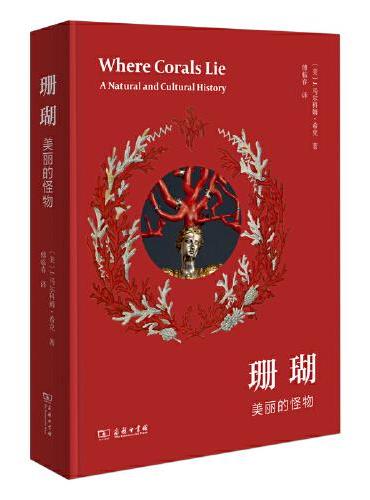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NT$
587.0
|
| 編輯推薦: |
《读者·校园版》改刊以来精华结集
最受中学生欢迎的三百篇佳作
青春激荡 文采飞扬
同类好书推荐
《读者·校园版 沸腾吧,少年!》点击进入
《读者·校园版 记忆的折痕》点击进入
《读者·校园版 思想的翅膀拍打屋顶》点击进入
《读者·校园版 未知的气味》点击进入
《读者·校园版 小心轻放的光阴》点击进入
《读者·校园版 经典珍藏书系(套装全五册) 》点击进入
|
| 內容簡介: |
|
本书精选了《读者·校园版》改刊以来,“成长故事”栏目的优秀篇章。“关注成长”是校园版的办刊宗旨,“成长故事”也是最受中学生欢迎的一个栏目,多种形态的真实的成长故事带给中学生成长启示。莫言、贾樟柯、张五常、黄健翔、九把刀、侯文咏……名家荟萃,美不胜收。
|
| 關於作者: |
|
《读者·校园版》是读者杂志社专门为中学生量身打造的一本优秀期刊。它以“关注成长,开阔视野”为办刊宗旨,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内容独特、鲜活、贴近中学生。全彩印刷、图文并茂,设计清新活泼。自2012年以全新的面貌上市以来,受到学生、家长和老师的一致好评,发行量连续攀升。2014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全国优秀少儿期刊”。
|
| 目錄:
|
黄健翔:我的十八岁,我的高考
吴念真:八岁,一个人去旅行
侯文咏:我的天才梦
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
毛尖:一个人的侠客行
大卫:十七岁的狂妄牛仔
梅莉?麦洛伊 阿丽西娅 译:阅读的回馈
田英文:未满十五岁,我被“托运”到美国
袁洁:只想成为鲁西西
莫言:童年读书
吴君宏:我的清华梦
李柏林:最伟大的预言师
斯蒂芬?弗雷 孙开元 译:读王尔德
押沙龙:谁的青春没有碰上小木块
白雪:偷来的《神秘岛》
张晓玲:我的武侠年代
张婷:青春总是突兀的
刘墉:叛逆少年的成长
张萍:高三,一场青春的“阴谋”
大卫?欧文 刘天放 译:我最好的老师
九把刀:一定要听到笑声
张玲 编译:童心永驻
付洋:等爱的狐狸
雷婧:美的教育
恩雅: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
贾樟柯:我比孙悟空头疼
张五常:你不必成为爱因斯坦
郭超群:记忆里的碎片
罗光太:一个人的青春战役
里则林:少年
安一朗:青春,始于谎言
侯焕晨:请尊重我的馒头
7号同学:请做一个勇敢、坚强的怪胎
詹志宏:待续的美好记忆
陆俊文:厕所里的书房
张战:天是怎样黑下来的
李若辰:攀比魔咒
林特特:我曾经是个差生
曾良君:永远十七岁的高中生活
大鹏:玩摇滚的好学生
卢十四:可我不想有出息
|
| 內容試閱:
|
我的天才梦
侯文咏
我仿佛知道杂志里面许诺了一个遥远、陌生却又令人期待的国度,总有一天,我会属于那里。
“被枪毙都有可能”
我很清楚地记得小学毕业典礼那天,大家唱《骊歌》的时候,班上有个女生在哭。我笑她“三八”,有什么好哭的,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没有感情的人。”
过了几十年以后,我忽然理解了这件事情。更准确地说,与其说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还不如说我有点无知。我并不知道,大部分的人,经过那一天之后,彼此就不再见面了。
毕业典礼上我拿了镇长颁发的“镇长奖”。下午级任老师还特地来我家里一趟,表示祝贺。爸爸妈妈摆开茶点,无限欢迎,大聊关于我的前途这类的议题。
“这个小孩子将来大好大坏,要么前途无量,要么被枪毙都有可能。”老师意味深长地表示。
我已经不记得我为什么会前途无量的理由了。我可能被枪毙的理由有好几个,其中我记得住的一个是:“他会写文章。”
我们是不是白白挨打了?
我从一个长着一头黑发的可爱小孩,被弄成一个剃三分头短发、有点像刚入伍新兵那样的青涩的小孩。
我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变得好丑。爸爸安慰我说:“你要上初中了,长大就是这样。”
虽然我勉强靠长大的理由说服自己,可是内心非常抗拒。
那时候,我开始阅读中文世界一些名家的作品。最先是洛夫、郑愁予、杨牧的新诗,随之而来的是徐志摩、朱自清、琦君、司马中原、子敏、张晓风等许多名家的散文。这些阅读的美好经验又带我进入了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七等生、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甚至是张爱玲这些当代作家的中文小说的世界。
老实说,可能是时代的关系,我看到的当代小说都带着苦涩甚至沉重的气氛,可也正好呼应了忽然加诸我们那个年纪的压力与苦闷。
我记得一进初中,班费里面就有一项是买藤条送给各主要科目的任教老师。藤条本来是农家用来打牛的器具,非常有弹性,打起来特别痛。通常只要打一下,屁股就会出现淤青,一旦打两下以上,鞭痕重叠的部分立刻皮开肉裂。历史书上说到明朝的廷杖打得人鲜血直流,我有些朋友认为文字夸张,怎么可能。我心想,这些在爱的教育之下成长的人真是不知民间疾苦。拜时代之赐,那种场面我在初中时代不但眼见,更是亲身领教过。
不像现在,这种教育方式在当时很少发生纠纷(毕业典礼之后,学生要蒙布袋打老师的不算)。我所就读的是升学率特别高的私立中学,很多望子成龙的父母都抢着把孩子塞进去。如果有父母亲不同意这样的教育哲学,学校很乐意让学生转学离开。有时候,学校的藤条打断了,甚至会有热心的父母亲捐赠新的藤条。
我的左右前后坐满了需要我照顾的同学。考试的时候,我除了要尽快把考卷写完外,还得空出时间,让左邻右舍抄答案。我在现实里过着这样所谓“好学生”的生活,可是我的周遭却充满着这么多荒谬的画面,我一点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变成了这样,而那些人却变成了那样。那时候,我读着小说里面更深沉的世界,写着人的穷、苦、贪、斗,我愈读愈觉得人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并不因为是儿童、青少年或成人就有什么不同。虽然我们的生活贫瘠而有限,还极力装出可爱的模样,可是成人或者是小说世界里的苦闷,我几乎都可以在生活里找到呼应。
后来学了统计学,我有一点想追究,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到底是真理,或只是不堪细究的某种信仰。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研究,所有这些挨了藤条的孩子,到底有几个人如父母所期望的成功了?如果他们成功了,有多少是来自藤条的帮助?藤条帮助一个孩子成功,它的有效率到底多高?是不是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意义?如果没有,是不是代表我们只是白白挨打了?
我想起班上有一个同学,后来变成了知名的声乐家。他应该算是班上同学的荣耀,这毋庸置疑。问题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声乐家和印象里中学时代的他联系在一起。我想不起中学时代曾经听过他唱歌,或者感受到任何他可能成为声乐家的特质。我搜遍记忆,勉强能找出来的,竟只有他挨藤条时,高亢的哀号声而已。
展开我的绝地大反攻
我在家里的顶楼清理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一有空闲,我就泡在那个天地里面写稿,或者是疯疯癫癫地阅读我弄回来的书。
我的母亲偶尔经过我那小小的空间,忍不住就要唠叨:
“你多花一点时间读正经书吧,不要老是看那些闲书。”
《家变》的作者王文兴曾写过《背海的人》这本小说。小说的第一页,就写了满满一整页脏话和“三字经”。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买回家看,正好被爸爸看见了。为了了解我在看什么书,爸爸以《背海的人》为样本,研究了半天。他皱着眉头问我:“你整天躲在这里,读着这样的书,你觉得好吗?”
父亲是个很温和的人。所以当他问“你觉得好吗”时,其实意思摆明这是“最后通牒”了。无可奈何,我搬回了楼下洁净明亮、只有教科书和参考书的书房,规规矩矩地做功课,过正常的生活。
过了一个月,我终于受不了了。我决定先从妈妈开始,展开我的“绝地大反攻”。
“你们对我最大的期望是照着你们的规定活着吗?”
“我们以前小时候,哪像你们这么幸福,有机会好好读书……(哇啦哇啦,叽里咕噜,中间省略)总之,我和你爸爸是为你好,希望你好好地读书,考好成绩,进好学校,将来进入社会做个有用的人……”
“所以,你们最希望就是看到我好好读书,考到好成绩啰?”
“当然。哪个父母亲不是这样希望的?”
“如果我每次都考前三名,达到你们的期望,你们可不可以也满足我的希望?”
“你有什么希望?”
“我希望你们不要干涉我的作息,让我自己决定。”
“好,”妈妈显然思考了一下,“如果你能考好成绩,表示你对自己负责。可是万一你说得到做不到……”
“我就依照你们开出来的作息表生活,绝无怨言。”
我花了一点心血研究,怎么样用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好的成绩,并且开始实行我研究后得到的心得。下一次段考,我很意外地拿到全校最高分。我的父母亲也吓了一跳。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约定。
于是我们让约定一直持续下去。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翻杂志
我变本加厉地爱啃书。站着啃书、坐着啃书、躺着啃书、歪斜着啃书。很快,小镇里那几个书店里的书被我啃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开始啃杂志。我不晓得从什么渠道拿到了订阅杂志的划拨单,突发奇想,以学英文为借口,号召同学集资,分别订阅了一些我觉得很炫的电影和摇滚杂志。
书寄来了,虽然里面的确写了不少英文字,可是更多的是怪异的图片,像是爱化装作怪的Queen 合唱团、戴个大眼镜的Elton John、粉墨登场的费里尼,还有斯坦利·库布里克的什么《奇爱博士》《发条橙》……
我生长的背景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南部的一个小镇。对于我那些还在学着“This is a book. Is this a book?”这种英文基本句型的同学,我订阅来的杂志不但不符需求,且内容前卫,里面的图片所夹带的颠覆或者是叛逆的意味,实在令人感到某种潜在的不安,更别说是同学们的父母亲了。
大家纷纷吵着要退资。无可奈何,我只好赔钱了事。我已经忘了是怎么弄到钱摆平那些债务的了,不过杂志无论如何是没办法退订了。接着的一年,那些已经订阅的杂志按时寄来家里,我变成了唯一的阅读者。
每个月我翻的那些新杂志,告示着美国、英国最新的排行榜,或者是影展、名导演的新作或新消息。老实说,我一个名字都不认识,更没有机会看过、听过杂志里面提到的任何一首歌,或者是任何一部电影。可是一期一期翻着,我可以猜想,那些不断被提起、重复或者是被崇拜着的名字,一定是很重要的人或作品。
我一个人翻着杂志,孤零零地翻着杂志。我看到演唱会挤着成千上万人,那么热闹,可是在这个小小的小镇,没有人在乎。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那样乐此不疲,或者是自信满满地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同。我仿佛知道杂志里面许诺了一个遥远、陌生却又令人期待的国度,总有一天,我会属于那里。
有一次,我经过小镇的唱片行,忽然看到了戴着大眼镜的Elton John 的海报。我赶紧回家要了零用钱,冲到唱片行买唱片。
好不容易,家里老旧的唱机播唱出了Elton John 的《再见黄砖路》的歌声以及旋律:
So goodbye,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听着听着,我的心中忽然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
我认得这首歌的样子一直只是杂志上的歌词。我随着自己的心情,为这些歌词编造不同的旋律,任意哼哼唱唱。我以为那就是故事的全部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竟然真真实实地在我的面前被播唱了出来。
而且,它和我曾编造过的千百种我以为应该是那样的旋律完全不同。
2012年第6期
叛逆少年的成长
刘 墉
“你知道我高中时为什么那么叛逆吗?”刘轩对我说,“因为我觉得我长大了,不该什么都听你们的。所以你叫我往左,我就偏往右。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该找到自己在哪里!”
“你找到了吗?”我问他。
“还在找。”他头一歪,很不服气地说,“因为你不让我自己去找!”
“你自己要怎么找呢?”
“去流浪。”他大声地说,“你知道吗?我有个同学,是英国的贵族,伊顿公学毕业的。在伊顿公学,平常大家都要穿燕尾服,算是管得够严了吧!可是他去年居然独自到澳洲去牧羊了。我还有两个同学,今年背着背包,自助到印度去旅行了。刚才接到他们的电话,说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他们一到印度,就遇上大雨,街上的积水淹过膝盖,到处漂着人的粪便和小动物的尸体,他们上吐下泻了两个礼拜,居然还跑到一个无人岛上住了几天,过瘾极了!”
“过瘾极了?差点儿送命!”
“当然过瘾,毕竟这是他们自己的旅行,不是跟在父母后面,住大饭店,坐轿车,吃大馆子。他们在寻找自己,他们找到了!”
我怔了一下,笑道:“好!今年暑假交给你自己,你去寻找自我吧!正巧,今年要为台南的德兰启智中心募款,你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去参加活动。你不必再跟我一起演讲,完全自己挑大梁!你也不用住在家里,自己去找地方住!”随后我又强调一句:“去不去也由你自己决定,跟我无关!”
6月20日清晨,刘轩搭飞机到达桃园中正机场。我没去接,他自己坐车到台北,中午又上飞机去高雄,在文藻语专演讲。然后赶到台南,跟主办募款活动的水长流公司开会,并搭最后一班飞机回到台北。
大概前一天太累了,他精神不大好,我问他一个人出去应付的感想。
他居然又是一副不太服气的表情说:“奇怪了!大家都叫我刘墉的儿子,为什么我总要活在你的阴影里?我还是没有找到自己!”
我又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说:“记住!你可能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别人的阴影,但最重要的是,千万别活在自己的阴影里。”
又隔了两天,他跟我吃中午饭。
“你找到自己了吗?”我问他。
“你一天到晚用BB机叫我,我怎么找自己?”他还是那个表情,“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打听我到哪里去了?我已经二十二岁了!”
我想了想,可不是吗!他马上就大学毕业了,我在他这个年龄,都结婚了。
从那天起,我再也不查他的行踪。后来知道,他在台湾的一个月,居然大部分时间在台南。除了到学校演讲,他还去瑞复益智中心见习,又到德兰启智中心做义工。更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和他应邀在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参加座谈会时,他居然带着十几位义工,表演了一场舞蹈。他不但从纽约回到台湾,而且完全融入这个社会,甚至本地话都学会了不少。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说他已经不再活在我的阴影里,他找到了自己!我将永远不会忘记,7月10日那天,在文化中心座谈时他的结语。
他提到在玉井乡的日子,提到那群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当他讲到离开德兰那一天,看着孩子们的交通车开走,孩子们向他挥手时,当着四千多名观众,他居然在台上泣不成声。
而那个跟我总是一毛、两毛斤斤计较零花钱的他,竟把在台湾赚到的七万块钱,都捐给了台南德兰和高雄的观音线。
回到纽约,全家人都觉得他一下子成熟了,变得更有礼貌、更关心家人。父亲节那天,他送我一个颈部按摩器,送给爷爷一副听音乐的耳机。当我们要带他去大冒险乐园玩时,他却要留在家里陪八十岁的奶奶。
更妙的是,他不再跟我“算小钱”。他的心胸变宽了,仿佛天地也宽了。
我突然领悟,要一个年轻人寻找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主动地参与社会、关怀别人、贡献自己。因为只有成熟的人才能懂得关怀,只有独立的人才能够做出贡献,人不是在“受”当中成熟,而是在“施”当中成熟,而且给予别人的愈多,愈会去关怀。我们做父母、做师长的,常忘记自己的孩子和学生已经长大,大到不再需要我们的呵护与监督。
他们不再喜欢被我们带着走,而是要自己走。
他们要寻找自己!
2013年第13期
童年读书
莫 言
我童年时的确迷恋读书。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类的忆苦戏。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我体能不佳,胆子又小,不愿跟村里的孩子去玩上树下井的游戏,偷空就看“闲书”。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后来,我的班主任家访时对我的父母说,其实可以让我适当地看一些“闲书”,形势才略有好转。但我看“闲书”的样子总是不如我背诵课文或是背着草筐、牵着牛羊的样子让我父母看着顺眼。人真是怪,越是不让他看的东西、不让他干的事情,他看起来、干起来越有瘾,所谓偷来的果子吃着香就是这道理吧。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一辈子也忘不掉啊。所以,前几年在电视上看了连续剧《封神演义》,替古人不平,如此名著竟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其实,这种作品是不能弄成影视剧的,非要弄,我想只能弄成动画片,像《大闹天宫》《唐老鸭和米老鼠》那样。
后来我又用各种方式,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几部经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全弄到手看了。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用飞一样的速度阅读一遍,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后来又把“文革”前那十几部著名小说读遍了。记得从一个老师手里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喂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许多疙瘩。从草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我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但母亲看看我那副样子,宽容地叹息一声,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让我赶快出去弄点草喂羊。我飞快地蹿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那时我真感到了幸福。
我的二哥也是个书迷,他比我大五岁,借书的路子比我要广得多,常能借到我借不到的书。但这家伙不允许我看他借来的书。他看书时,我就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悄悄地溜到他的身后,先是远远地看,脖子伸得长长的,像一只喝水的鹅,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靠近了。他知道我溜到了他的身后,就故意将书页翻得飞快,我一目十行地阅读才能勉强跟上趟。他很快就会烦,合上书,一掌把我推到一边去。但只要他打开书页,很快我就会凑上去。他怕我趁他不在时偷看,总是把书藏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就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地下党员李玉和藏密电码一样。但我比日本宪兵队长鸠山高明得多,我总是能把二哥费尽心机藏起来的书找到,找到后自然又是不顾一切地读,恨不得把书一口吞到肚子里去。有一次他借到一本《破晓记》,藏到猪圈的棚子里。我去找书时,头碰了马蜂窝,“嗡”的一声响,几十只马蜂蜇到脸上,奇痛难挨。但我顾不上痛,抓紧时间阅读,读着读着眼睛就睁不开了,头肿得像柳斗,眼睛肿成了一条缝。我二哥一回来,看到我的模样吓了一跳,但他还是先把书从我手里夺回去,拿到不知什么地方藏了,才回来管教我。他一巴掌差点把我扇到猪圈里,然后说:“活该!”我恼恨与疼痛交加,呜呜地哭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可能是怕母亲回来骂,便说:“只要你说是自己上厕所时不小心碰了马蜂窝,我就让你把《破晓记》读完。”我非常愉快地同意了。但到了第二天,我的脑袋消了肿,去跟他要书时,他马上就不认账了。我发誓今后借了书也不给他看,但只要我借回了他没读过的书,他就使用暴力抢去先看。有一次,我从同学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一本《三家巷》,回家后一头钻到堆满麦秸草的牛棚里,正看得入迷,他悄悄地摸进来,一把将书抢走,说:“这书有毒,我先看看,帮你批判批判!”他把我的《三家巷》揣进怀里跑了。我好恼怒!但追又追不上他,追上了也打不过他,只能在牛棚里跳着脚骂他。几天后,他将《三家巷》扔给我,说:“赶快还了去,这书流氓极了!”我当然不会听他的。
我怀着甜蜜的忧伤读《三家巷》,为书里那些小儿女的纯真爱情痴迷陶醉。当读到区桃在沙面游行被流弹打死时,我趴在麦秸草上低声抽泣起来。我心中那个难过,那种悲痛,难以用语言形容。
读罢《三家巷》不久,我从一个很赏识我的老师那里借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晚上,母亲在灶前忙着做饭,一盏小油灯挂在门框上,被腾腾的烟雾缭绕着。我个头矮,只能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保尔和冬妮娅,肮脏的烧锅炉小工与穿着水兵服的林务官的女儿的迷人初恋,实在是让我梦绕魂牵,跟得了相思病差不多。多少年过去了,那些当年活现在我脑海里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保尔在水边钓鱼,冬妮娅坐在水边树杈上读书……哎,哎,咬钩了,咬钩了……鱼并没咬钩。冬妮娅为什么要逗这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浑身煤灰的穷小子呢?冬妮娅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保尔发了怒,冬妮娅向保尔道歉。然后保尔继续钓鱼,冬妮娅继续读书。她读的什么书?是托尔斯泰的还是屠格涅夫的?她垂着光滑的小腿在树杈上读书,那条乌黑粗大的发辫,那双湛蓝清澈的眼睛……从冬妮娅向保尔真诚道歉的那一刻起,童年的小门关闭,青春的大门猛然敞开了,一个美丽的、令人遗憾的爱情故事开始了。我想,如果冬妮娅不向保尔道歉呢?如果冬妮娅摆出贵族小姐的架子痛骂穷小子呢?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没有了。一个高贵的人并不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高贵才是真正的高贵;一个高贵的人能因自己的过失向比自己低贱的人道歉是多么可贵。我与保尔一样,也是在冬妮娅道歉的那一刻爱上了她。说爱还早了点,但起码是心中充满了对她的好感,阶级的壁垒在悄然瓦解。接下来就是保尔和冬妮娅赛跑,因为恋爱忘了烧锅炉。劳动纪律总是与恋爱有矛盾,古今中外都一样。美丽的贵族小姐在前面跑,锅炉小工在后边追……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冬妮娅青春焕发的身体有意无意地靠在保尔的胸膛上……看到这里,幸福的热泪从高密东北乡的傻小子眼里流了下来。接下来,保尔剪头发,买衬衣,到冬妮娅家做客……我是三十多年前读的这本书,之后再没翻过,但一切都在眼前,连一个细节都没忘记。我当兵后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失望得很,电影中的冬妮娅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冬妮娅。保尔和冬妮娅最终还是分道扬镳,成了两条道上跑的车,各奔前程。当年读到这里时,我心里那种滋味难以说清。
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我童年读书的故事也就完结了。
2012年第23期
我比孙悟空头疼
贾樟柯
上初三的时候,我的一个结拜兄弟要去当兵。我送他,他坐在大轿车里一言不发。我想安慰他,便说:“这下好了,你自由了。”听我说完此话,他还是一脸苦相,我便有些烦他。在我的观念里,只要不上学,不做功课,不被老师烦,便是最大的幸福。而能离家远走,不受父母管教,那更是天大的喜事。我由衷地羡慕他,所以不太理解他为何总是沉默不语,并且低着头不拿眼睛看我们。车快开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再看他的那一脸苦相,便说:“你是不是怕我们看你远走高飞,心里不平衡,所以假装不高兴来安慰我们?”
我那兄弟抬起头来,缓缓地说:“自由?老子是去服兵役!”
我随口答道:“看你的苦相,倒像是去服劳役。”
我那兄弟不紧不慢地答道:“兵役,劳役,还不都是服役!”
我一下无话可说,他的话让我非常吃惊。我这兄弟平时连评书都不爱听,就关心自己养的那几只兔子,这要去当兵了,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也变了样。他的话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世界。那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刚刚过了变声期,从来不懂得思辨,对生活中的一切深信不疑。但我的那个兄弟突然具有了这样的能力,他的一句话,让我吃惊,更让我在瞬间超越了自己的年龄。我到今天都感谢他如感谢圣人,他在无意间启迪了我,让我终生受用,虽然直到今天他对此仍一无所知。
我想应该是巨大的生活变化,让一个从来不善于思考的养兔少年去思考自由的真相。他对当兵的看法超越了他形而下的处境,超越了社会层面的价值判定,超越了1984年文化的宽容程度,而直指问题的本质。他说出来的话,如此抽象又如此人道,如此让我触目惊心又如此让我心旷神怡。
我兄弟的思考引发了我的思考,送他离去,我在回家的路上想,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自由,逃出家庭还有学校,逃出学校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法则之外还有法则。我一下子明白了《西游记》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孙悟空一个跟头能行十万八千里,看起来纵横时空,自由自在,但到头来还是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这让孙悟空相当头疼,紧箍咒就是无法挣脱法则的物化表现。吴承恩在我眼里成了悲情的明朝人,《西游记》是一个暗示。整篇小说没有反抗,只有挣扎;没有自由,只有法则。我觉得《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里离我最近的一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自由问题是让人类长久悲观的原因之一,悲观是产生艺术的沃土。悲观让我们务实、善良;悲观让我们充满了创造性。而讲述不自由的感觉,一定是艺术得以存在的理由。因为不自由不是一时一事的感受,决不特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自由是人的原始感受,就像生、老、病、死一样。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们对自由问题的知觉。逃不出法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有限的自由,或者说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在我看来,悲观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务实的精神,是我们接近自由的方法。
199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不想再读书,想去上班挣钱。我想自己要是在经济上独立了,不依靠家庭便会有些自由。我父亲非常反对,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上成大学,便想让我去圆他的梦。这大概是家庭给我的不自由,我并不想出人头地,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看看电视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一个人的生命就比另一个人的高贵,我父亲说我心态不好,有消极情绪。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有消极情绪呢?我觉得杜尚和“竹林七贤”都很消极,杜尚能长年下棋,我为何不能打麻将?我又不妨碍别人。多少年后,我拍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小武》也被有关人员认为作品消极,这让我一下子想起我的父亲,两者一样是家长思维,不同的是我父亲真的爱我。
后来,我去了太原,在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考前班里学习。这是我和我爸相互妥协的结果。因为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避开了我的弱项,我则可以离家去太原享受我的自由。
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在太原上班,开始挣钱,经济上独立了。我很羡慕他。有一天我去找他,没想到他们整个科室的人下班后都没有走,陪着科长打扑克,科长不走谁也不敢走。我同学说天天陪科长打扑克都快烦死了。我突然觉得权力的可怕,我说他们打他们的,你就说有事离开不就完了吗?他说:“不能这样,要是老不陪科长玩,科长就会觉得我不是他的人了,那我怎么混?”我知道他已经陷在一种游戏里了,他有他的道理,但我从此对上班失去了兴趣。
在一种生活中,全然不知自由的失去,可谓不智;知道自由的失去而不挽留,可谓无勇。这个世界上的人应该不缺智慧,缺的是勇敢。因为是否能够选择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背叛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开始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结束一种生活,事关自由。自由要我们下决心,不患得患失,不怕疼痛。
小时候看完《西游记》,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对着蓝天念念有词,希望哪一句恰巧是飞天的咒语,让我腾空而起,也来一个能飞十万八千里的跟头。这些年跟头倒是摔了不少,人却没飞起来。我常常想:我比孙悟空还要头疼,他能飞,能去天上,能回人间,我却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带给我的一切。太阳之下无新事,对太阳来讲,有些事旧了,但对我来讲是新的,所以还是拍电影吧,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我悲观,但不孤独,在自由的问题上,连孙悟空都和我们一样。
2013年第23期
一定要听到笑声
九把刀
我念小学时就很喜欢乱讲话,惹人注意。上课时我常常不举手就冒出一句话,弄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举手再讲的话,会丧失笑点爆发的时机)。因此,每个礼拜老师都会联系我的家长好几次。
放学回家的途中,我经常会很懊悔,干吗要冒着回家被揍的危险讲笑话给全班同学听呢?为什么老师明明笑了,却还要这样罚我呢?
到了五年级,课程表上突然出现了两堂“说话课”。
说话课当然不是给大家闹哄哄聊天用的,老师会叫同学上台讲自己每周读书的感想,训练同学们对着很多人讲话的勇气。
如果说话课的老师跑去跟其他老师打桌球,就会由班长按照学号点同学上台演讲,此时大家就会讲得很快,例如:“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看了这本书,我决定从今以后要努力用功。”然后就面红耳赤地冲下台。
如果老师在教室后面改作业、压场监督的话,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地上台讲感想,但效果会很差,台下绝大多数的人睡倒一片,那几个醒着的,就是害怕被台上的同学“点”到的人——因为讲完自己读书心得的人,可以指定底下的任何人上台演讲。
有的人专门点好朋友(被点到的人:哎呀,你干吗呢),有的人专门点仇人(被点到的人绝对会一路瞪着点自己的人,愤怒地踏上讲台)。
有一天,我被点到了。
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昏昏欲睡的同学,我有一种不被重视的屈辱感——那是一种内心强烈的不甘。
虽然老师远远坐在教室后面,但我突然不想说读书的心得了。
反正,又没有人想听。
我不明白,确定是没有人听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摆个样子假惺惺地说出来?
于是我开始胡说八道。
我用班上同学的名字做角色,即兴说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搞笑故事。具体的内容忘了九成九,印象里是和同学一起在宇宙间旅行的故事。
台下的同学不只是笑,而且是狂笑;不只是狂笑,而且是不断地狂笑。
用大家的名字当故事角色,也让全班同学很有参与感,不可能有人睡觉,被我说到名字的同学不断地在下面拍桌大叫:“放屁!我怎么可能那样!”或为了反驳我干脆一直指着自己,说:“等一下换我上去说!换我!”
台下鼓噪不已,而老师似乎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大概也觉得热闹点不是坏事吧),便放任我继续把故事说下去。
我说完了,故意点了一个被我说成搞笑小丑的好朋友上台,他恼火地接着我刚刚讲的故事结尾讲,试图把自己的形象改成比较正常的样子。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搞笑的故事,大家照样笑得前仰后合。
从此之后,说话课就变成了搞笑的故事接龙,而我通常都是第一个上去起头的那个人,也尝到了什么叫作“被期待”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在台上把老师的名字也编进故事里之后(我很怕老师一直没有参与感,坐在教室后面觉得被大家冷落了),才被怒气冲天的老师轰了下来。这期间我一直在即兴地当众编故事,“畏惧人群”这四个字老实说我很不能理解,因为人群不就是用来亲近的吗?
后来上了中学,班会时间大家最喜欢选我当主席,因为我会把握每个机会搞笑,大家也觉得很好玩。不过高中时我就收敛了很多,唉,因为我受骗,迷上了努力用功读书这件事。
阴错阳差,高中毕业后我考进了好学生才能上的交通大学。
不管是上什么课,每次课堂报告,大家最期待的就是我登台。
我除了必要的“取得分数”外,肯定会添油加醋,鬼扯一堆故事,因为我完全无法忍受台下的同学各自在做自己的事,只有老师一个人在假装认真打分数。
记得有一次我上系里的选修课“商业概论”,准备要上台讲Acer电脑的行销模式前,班上就有点骚动,有人在桌子底下打手机,叫逃课的同学快点来教室,因为“今天九把刀要做报告”。
十几分钟后,教室里的空位全部被填满了。
老实说,按照惯例我除了讲一些与课程相关的内容,让教授觉得我读过资料,其余搞笑的部分一律不准备,因为准备了就太刻意了,我不喜欢。临场发挥才是幽默的王道。
我不负众望,让大家从头爆笑到尾。
教授很吃惊,因为他从来没看过有那么多人聚精会神地听讲。演讲结束时,全班鼓掌长达半分钟以上。
教授走向我,难以置信地说:“柯景腾,大家都很喜欢听你做报告。”
“唉,还好啦。”
“你可不可以以后每一堂课都上台讲五分钟,然后学期成绩我给你九十五?”
“不……不要。”
2013年第1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