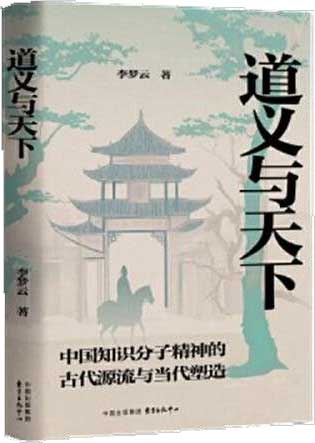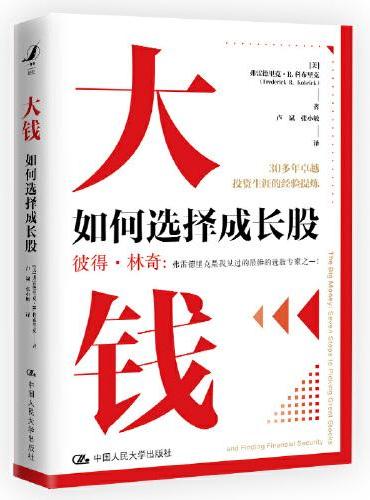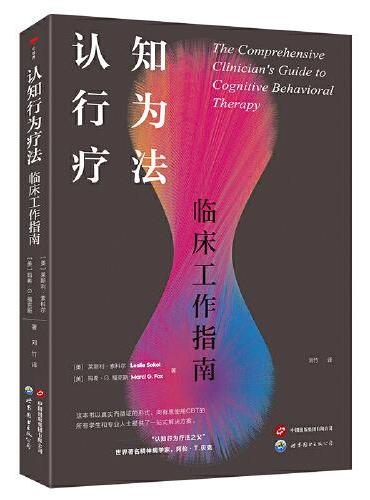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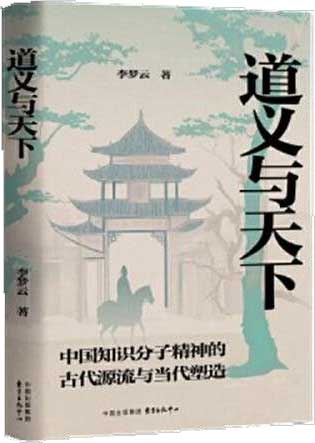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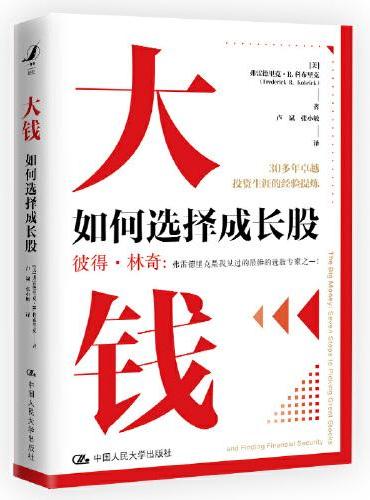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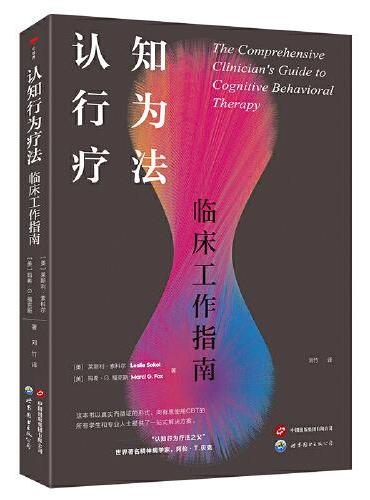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不单工于长篇小说,其短篇创作也一直为学界和读者所称道。《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以国外出版的最经典的福克纳短篇小说集为基础,由陶洁老师补充编选而成,撷取福克纳一生短篇小说创作之精华18篇。再借由李文俊、陶洁等人之传神妙笔,成就国内福克纳短篇小说最经典译本。
|
| 內容簡介: |
|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短篇小说集》集中了威廉福克纳短篇创作中的经典篇章,如《烧马棚》、《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干旱的九月》等18篇,代表了福克纳短篇小说创作的风格和主要成就。
|
| 關於作者: |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学院对他的评价是:“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
| 目錄:
|
烧马棚
两个士兵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干旱的九月
夕阳
殉葬
瞧!
调换位置
荣誉
曾有过这样一位女王
山上的胜利
阴间
清晨的追逐
花斑马
明天
沃许
路喀斯布香
莱巴嫩的玫瑰花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一
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座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桀骜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现在爱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那些名字庄严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们沉睡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那里尽是一排排在南北战争时期杰弗生战役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无名军人墓。
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镇长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的命令—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起,期限从她父亲去世之日开始,一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是全镇沿袭下来对她的一种义务。这也并非说爱米丽甘愿接受施舍,原来是沙多里斯上校编造了一大套无中生有的话,说是爱米丽的父亲曾经贷款给镇政府,因此,镇政府作为一种交易,宁愿以这种方式偿还。这一套话,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得出来,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
等到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这项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便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二月份到了,还是杳无音信。他们发去一封公函,要她方便时到司法长官办公处去一趟。一周之后,镇长亲自写信给爱米丽,表示愿意登门访问,或派车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却是一张便条,写在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细小,但墨水已不鲜艳,信的大意是说她已根本不外出。纳税通知单附还,没有表示意见。
参议员们开了个特别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对她进行了访问。他们敲敲门,自从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开授瓷器彩绘课以来,谁也没有从这大门出入过。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男仆把他们接进阴暗的门厅,从那里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又沉闷,这屋子长久没有人住了。黑人领他们到客厅里,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全都包着皮套子。黑人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这时,便可看出皮套子已经坼裂;等他们坐了下来,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壁炉前已经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
她一进屋,他们全都站了起来。一个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服,一条细细的金表链拖到腰部,落到腰带里去了,一根乌木拐杖支撑着她的身体,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她的身架矮小,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是丰满的东西,在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当客人说明来意时,她那双凹陷在一脸隆起的肥肉之中,活像揉在一团生面中的两个小煤球似的眼睛不住地移动着,时而瞧瞧这张面孔,时而打量那张面孔。
她没有请他们坐下来。她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直到发言的代表结结巴巴地说完,他们这时才听到那块隐在金链子那一端的挂表嘀嗒作响。
她的声调冷酷无情。“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沙多里斯上校早就向我交代过了。或许你们有谁可以去查一查镇政府档案,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我们已经查过档案,爱米丽小姐,我们就是政府当局。难道你没有收到过司法长官亲手签署的通知吗?”
“不错,我收到过一份通知,”爱米丽小姐说道,“也许他自封为司法长官……可是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
“可是纳税册上并没有如此说明,你明白吧。我们应根据……”
“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
“可是,爱米丽小姐—”
“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死了将近十年了。)“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托比!”黑人应声而来。“把这些先生请出去。”
二
她就这样把他们“连人带马”地打败了,正如三十年前为了那股气味的事战胜了他们的父辈一样。那是她父亲死后两年,也就是在她的心上人—我们都相信一定会和她结婚的那个人—抛弃她不久的时候。父亲死后,她很少外出;心上人离去之后,人们简直就看不到她了。有少数几位妇女竟冒冒失失地去访问过她,但都吃了闭门羹。她居处周围唯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那个黑人男子拎着一个篮子出出进进,当年他还是个青年。
“好像只要是一个男子,随便什么样的男子,都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似的。”妇女们都这样说。因此,那种气味越来越厉害时,她们也不感到惊异。那是芸芸众生的世界与高贵有势的格里尔生家之间的另一联系。
邻家一位妇女向年已八十的法官斯蒂芬斯镇长抱怨。
“可是太太,你叫我对这件事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说。
“哼,通知她把气味弄掉,”那位妇女说,“法律不是有明文规定吗?”
“我认为这倒不必要,”法官斯蒂芬斯说,“可能是她用的那个黑鬼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我去跟他说说这件事。”
第二天,他又接到两起申诉,一起来自一个男的,用温和的语气提出意见。“法官,我们对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过问了。我是最不愿意打扰爱米丽小姐的人,可是我们总得想个办法。”那天晚上全体参议员— 三位老人和一位年纪较轻的新一代成员在一起开了个会。
“这件事很简单,”年轻人说,“通知她把屋子打扫干净,限期搞好,不然的话……”
“先生,这怎么行?”法官斯蒂芬斯说,“你能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吗?”
于是,第二天午夜之后,有四个人穿过了爱米丽小姐家的草坪,像夜盗一样绕着屋子潜行,沿着墙角一带以及在地窖通风处拼命闻嗅,而其中一个人则用手从挎在肩上的袋子中掏出什么东西,不断做着播种的动作。他们打开了地窖门,在那里和所有的外屋里都撒上了石灰。等到他们回头又穿过草坪时,原来暗黑的一扇窗户亮起了灯:爱米丽小姐坐在那里,灯在她身后,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过草坪,进入街道两旁洋槐树树阴之中。一两个星期之后,气味就闻不到了。
而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感到难过。镇上的人想起爱米丽小姐的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终于变成了十足疯子的事,都相信格里尔生一家人自视过高,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爱米丽小姐和像她一类的女子对什么年轻男子都看不上眼。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叫作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因此当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我们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觉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即令她家有着疯癫的血液吧,如果真有一切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也不至于断然放过。
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人们倒也有点感到高兴。到头来,他们可以对爱米丽表示怜悯之情了。单身独处,贫苦无告,她变得懂人情了。如今她也体会到多一分钱就激动喜悦、少一分钱便痛苦失望的那种人皆有之的心情了。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习俗。爱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不论是教会牧师访问她也好,还是医生想劝她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也好。正当他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她发疯。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