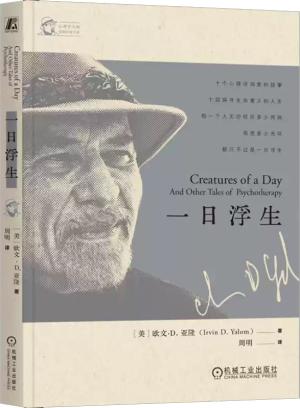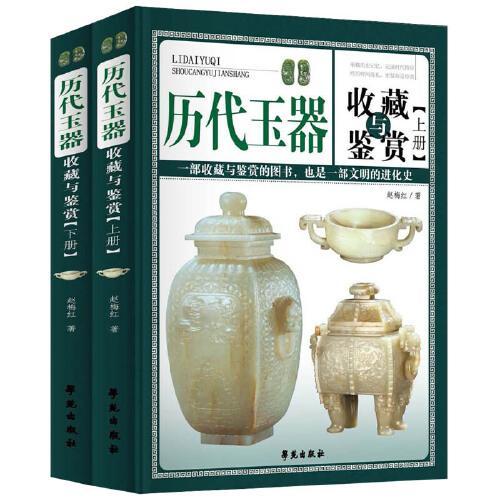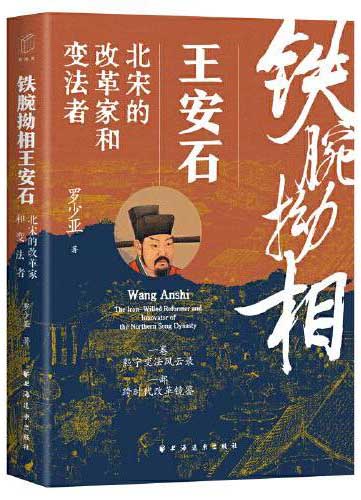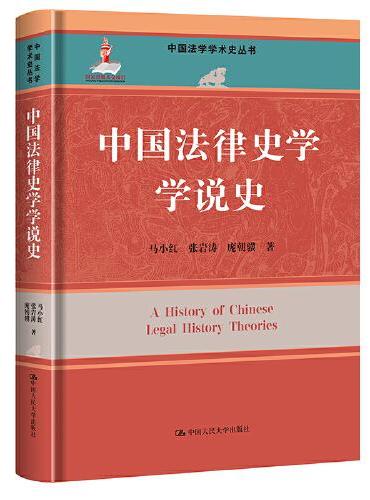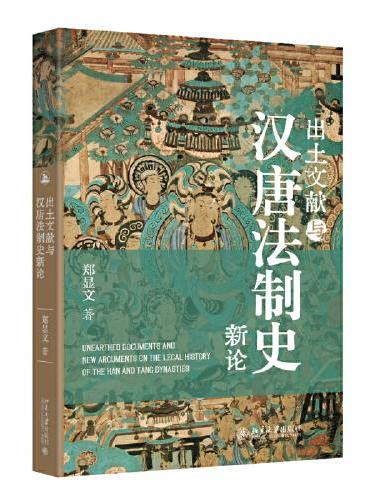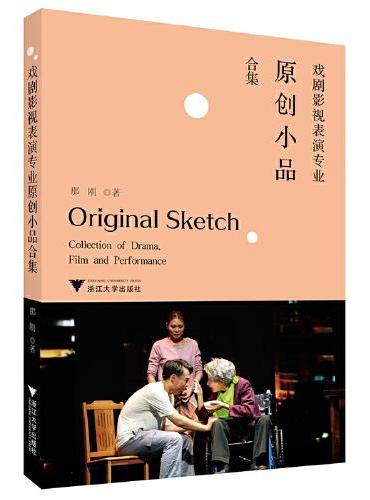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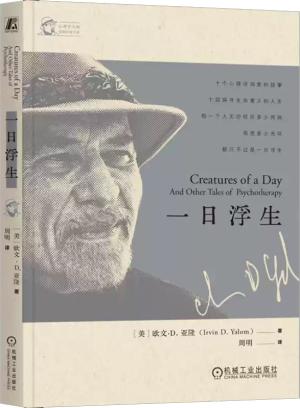
《
一日浮生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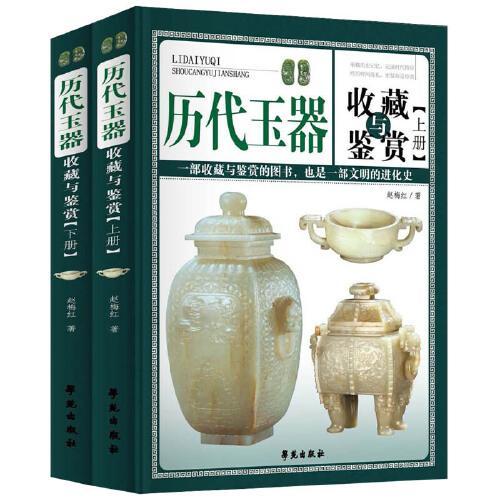
《
历代玉器收藏与鉴赏
》
售價:NT$
18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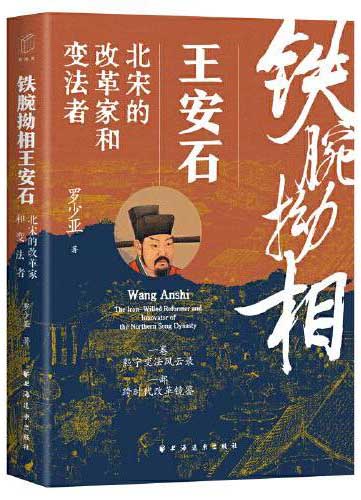
《
铁腕拗相王安石:北宋的改革家和变法者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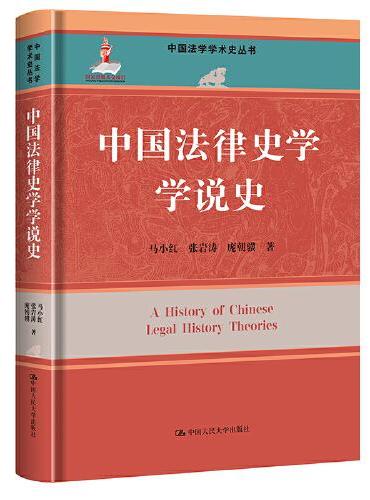
《
中国法律史学学说史(中国法学学术史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售價:NT$
857.0

《
方尖碑(全2册)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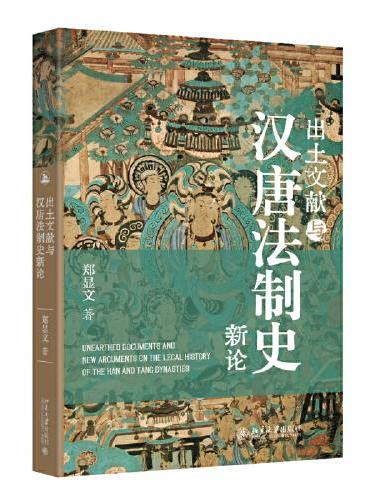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汉唐法制史新论
》
售價:NT$
398.0

《
最美最美的博物书(全5册)
》
售價:NT$
7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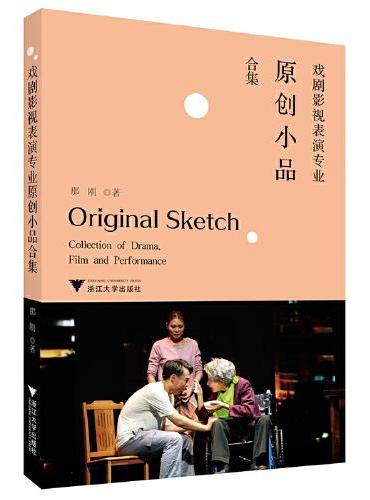
《
戏剧影视表演专业原创小品合集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女性圣经《第二性》就诞生于这个故事中。
★波伏瓦曾经承认,艾格林是她唯一的真爱,他赠予的一枚银戒指,最终被她带进了与让-保罗·萨特共同的坟墓里。
★即使爱情转眼已逝,某些场景、某些言语、某些空中的动作,却深深镌刻在情人的记忆中,随他们一起被埋葬。
|
| 內容簡介: |
《恋爱中的波伏瓦》内容简介:一位在人类的20世纪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世人都会在她的名字后面紧跟一本“女性圣经”《第二性》,但几乎没有人知道,《第二性》究竟诞生于何处。这里,这个故事,这不小说,这段秘密的传奇恋情,就是答案。
1947年,波伏瓦应邀造访美国,此时的她与她的“世纪情人”让萨特虽都承认双方的“偶然爱情”,但却因一个名叫多洛雷斯的女子介入而妒火中烧,与萨特关系胶着。就在刚刚抵达纽约的1月 26日凌晨,波伏瓦被梦中一个无声的声音惊醒:“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可到底是什么事呢?”
就在她做了这个梦的27天后,她遇到了一个最不可能相遇的男人,落魄芝加哥作家纳尔逊·艾格林。
两人用几个月时间相聚,相恋,相离,相思,最终,这段经历促成了《第二性》一书的诞生。在此后的14年里,波伏瓦与艾格林一直守望着一份绝密爱情,直至最终决裂,她却仍然称艾格林是她唯一的爱。他赠予的她一枚银戒指,最终被她带进了与萨特共同的坟墓。
|
| 關於作者: |
|
伊雷娜·弗兰(Irène Frain):1950年5月22日出生于法国莫尔比昂省洛里昂,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擅长历史题材小说,曾任法国重要杂志《巴黎竞赛周刊》记者,还是世界女性经济与社会论坛的创立者之一。
|
| 內容試閱:
|
这句话久久不肯散去,在黑暗的房间里回荡。身体挣扎着,竭力浮向意识清醒的水面。睡眠的胞衣被渐渐撕开,但昏沉感仍挥之不去。肯定是暖气的关系,它被开到了最大。
记忆逐渐苏醒。昨晚在拉瓜迪亚机场①,一走下来自巴黎的飞机,热浪已让人窒息。机场里,海关关员是唯一淡定的人,他们习惯了。有些人心不在焉,有些人吹毛求疵,冷漠地应付着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查护照、查疫苗证明、查行李、查牙齿、查护照签证页上的每一个接缝。“贝特朗·德·波伏瓦,西蒙娜·露西-埃内斯蒂娜-玛丽,1908年1月9日,生于巴黎。”等他们中的最后一位终于盖下“美国移民局,1947年1月25日”的章,她匆匆抓过唯一的行李,一只小皮折箱,朝出口飞快走去。
半小时后,大使馆来接她的车驶过布鲁克林大桥,她还在不停出汗。这回,是因为外交官刚刚带给她的坏消息让她十分恼火:三个月的时间里只安排三场演讲,至于媒体采访,几乎没有。他们草率对待她的巡回演讲。
汽车驶离大桥进入第一片高楼汇聚的峡谷,几分钟后她的呼吸顺畅了些。这座城市有一种怪异的美:灯光瀑布般倾泻到路上,小汽车、大巴士无声地从周六夜里的柏油路面上驶过,路边多彩的霓虹灯眨着眼睛。他们的车在宾馆大门前一停下,热气就扑面而来。她不禁自语道:“这地方的人真怪,喜欢把暖气开到最大。”
她浑身湿透,整个晚上汗就没停过。她在餐馆出汗,等到摆脱了大使馆的女人,在曼哈顿街上寻找斯特凡时,还在出汗。在哪她都感觉喘不过气,在朋友家门前也感觉窒息,当然她没有找到朋友。回到旅馆,在电梯里、在长长走廊里仍然如此。要不是巨大的疲倦和失望压垮了她,一整夜她都不会睡着,实在是太热了。
现在,这个声音又来了。它没发出一个字,但确确实实在说话。一个无声的声音,太荒谬了!
荒谬却如此真切:这个声音说着和刚才一样的话,完全辨得清:“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可到底是什么事呢?”
这句话来自一个梦境,这是肯定的,但是哪个梦呢?谁知道,肯定是每晚缠绕她的晦涩梦魇中的某一个。
快,醒过来吧。睁开眼睛,开灯,看到光亮,快!
屋子一下子从黑暗中呈现,这是她的房间,曼哈顿第八大道林肯大酒店。一切有了解释:终于来到纽约!这几个月太多煎熬,来美国前的等待太漫长。
继续睡觉,这是唯一可做的。可无法入睡,几点了?
再次开灯,看手表,凌晨五点。夜太短了,总是这样。
“我到底怎么了?”那个声音顽固地不肯散去。
她让屋子重新沉入黑暗:用不着绞尽脑汁,她现在碰到的事与十八个月前一样,和三个音节有关:多——洛——雷丝。
***
多洛雷丝是个噩梦,正如她的名字所示,多洛雷丝——痛苦①。
一说到“多洛雷丝”这个词,她神经立刻高度紧张,日夜窥视,一刻不放松,沉浸在仇恨与痛苦中;从暴跳如雷跌入垂头丧气,在房间里泪如雨下,还不能表露出来,尤其是什么都不能说。接着又把苦恼不断转换成疯狂的期待:“那该诅咒的女人很快会滚蛋,或者萨特会一脚踢开她。”
但他没有踢开她,她也没有滚蛋,甚至完全相反,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倒越来越如漆似胶。这段时间他们电话不断,信件、电报频繁飞越大西洋,而她就住在他附近,只隔了五六个建筑群。
那该诅咒的女人肯定不会做噩梦,肯定不知道就着酒精吞下安眠药时的苦涩,体会不到每天醒来时心如死灰心情。
萨特越来越沉默,即使开口也只谈论他和多洛雷丝是多么心心相印,他不明白怎么会发生如此奇迹,这是他以前从未碰到过的情况。他吐出的每一个字,刺得她肋间生疼,疼得难以名状,她需要给这种疼痛找到一个名称。然而灵感全无,也许因为嫉妒,嫉妒让人无能。对于这件事她想到的第一个词语就是“当胸一拳”。
还是用英国人的发音“梆①”比较好,在耳边很清脆,就像多洛雷丝等于疼痛:感觉一把大剪子落下,“梆!”心碎成两半。
最具杀伤力的一记“梆”要追溯到几周前,那天早晨萨特问道:“亲爱的海狸,你去美国巡回演讲的确切时间到底是什么?”1月25日至4月24日。“很好,我通知多洛雷丝。”什么,多洛雷丝?“是的,这段时间她会来法国……”
他处心积虑安排了这场乾坤大挪移。现在表示反对已经来不及了,两人机票都已买好,总之她这边,大使馆已经确认——她的巡回演讲箭在弦上。
所以多洛雷丝下周四就要离开曼哈顿,然后在迷人的(确切说是碍事的)海狸4月24日回法国之前回到美国。这三个月期间在巴黎会发生些什么?多洛雷丝正着手办离婚事宜,有传言说萨特打算娶她。
这就是那个声音的预言吗?
***
“亲爱的海狸……”萨特六个月来的老调。
他称呼那个该诅咒的女人多洛雷丝,却从不叫自己西蒙娜。他一直叫她海狸,那是当年他们一起考哲学教师资格时伙伴们给她起的外号。对他来说,即使在他们一起上床的那八年里,她也一直是“海狸”或“阳性海狸”①。不过他以阴性形容词与之相配,“海狸很迷人,海狸生气了”,听上去却与阳性形容词无甚差别,不过她并不在意。雌雄同体,很适合她。
总之在她无法入睡时,黑夜尤为漫长;而当她做梦时,夜更难熬。西蒙娜在噩梦的源起处,品尝到了苦涩。她向他发难、唉声叹气,祈求爱情中有她的份,做个萨特嘴里的“好女人”。
不能让那个女人为所欲为,如果听之任之,她会得寸进尺。唯一的办法,需要仰仗十八年前萨特与她签订的盟约:不管发生什么,她是他的恒星。
***
问题是萨特目前的生活中出现了一颗新星。他的话语、他的思想、他的梦幻,一切都飞向多洛雷丝。去年他的剧本《死无葬身之地》的题献,写的就是“献给多洛雷丝”。
“梆”。不久后,《现代》的创刊号,仍然是“献给多洛雷丝”。他事先并未告知她,她是在庆祝杂志诞生的晚宴上才发现,此时木已成舟。有人注意到她脸色惨白:“海狸要昏过去了……”
她听到了人们的窃窃私语,这严重伤害了她的自尊,但她及时控制住了自己,一直隐忍着,等回到整年租住的圣日耳曼德普雷旅馆房间时才忍不住泪流满面,噩梦连连。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但就是从这一天起生活变成一连串无休止的“梆”,所见所闻之事,无不如此。那些日子,你不愿去想的事却又出乎意料地砸到你头上,结果便是让你从早到晚有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痛,痛到忍无可忍,早上醒来真想用头撞墙:“索性就让这最后的‘梆’要了我的命吧,以后再不提这事!”
六个月前这样的情形差点就发生了。萨特和她一起吃午饭,他看上去非常阴郁。他的沉默如此逼迫,她的那个疑问自动就蹦了出来:“坦率地说,你到底更在乎谁?多洛雷丝还是我?”而他仿佛等这问题等了几个星期,脱口回答道:“我非常在乎多洛雷丝,但我现在是和你在一起。”
“梆”,这天的痛,不仅是因为他说的话(司空见惯的大男子主义回答,既要老婆又要情人),更因为他说话时的语气:金属般的冰冷,一如每次他打算离开那些年轻情人时说话的口吻。
她盯着自己的餐盘,头低得像个刚被人丢弃在角落的小姑娘。真相爆出,既清楚又可怕。多洛雷丝和他,并非逢场作戏,而是一种激情,他们俩在相爱。萨特那天向她承认说他从未经历过如此奇迹时,那可不是文学修辞。
单单“奇迹”这个词就够了:他那些出色的理性和思辨跑哪去了?解释人类共同面临的疑难问题时艺术而简洁的回答哪去了?他不仅晕头转向,并且缴械投降,拜倒在这位多洛雷丝的石榴裙下。这个女人在其他所有女人失败的地方获得了成功,他毫不设防地听凭摆布,上她的钩。
而她海狸,不久前还是法国最年轻的哲学女教师,生平第一次沦落到考试不及格者的行列。
***
餐馆的那一幕,到死她都不会忘记,记得每一个细节。那条美味的白鱼团在盘子里,她举起镀银刀叉,旋即又放回条纹桌布上,一口都咽不下。他倒是不紧不慢地嚼着,看她一直不吃饭,终于担心地问道:“怎么了?”
她勉强答道:“我卡了一根鱼刺。”
从她的声音里,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沙哑细小,少了平时的高亢。他站起来拉住她的胳膊,躲开众人目光,把她带回家里。一回家,他就用他的温情和语言天赋,让她如所有女人一样,忘了他是个小矮子。他还给她来了点哲学:“那只是个用词问题,我刚才表达得不好。你知道我们两人之间,只有事实说了算。你也看到了,我从来、从来没有抛弃过你。请相信一件事,我不会离开你。”
像往常一样,这招很管用。
过了一会儿他戴上护耳躺下,这意味着他拒绝继续讨论,他需要安宁。她走过去带上门避免别人打搅。
她突然感觉到了二十岁时的炽热。但即便如此,有一天晚上,怀疑猜忌的情绪还是缠上了她,她竭力排遣,自我安慰:“这是我臆想出来的,我不见得比萨特高尚。他和我之间的那份契约一直有效。我们之间的结合是坚不可摧的,没人能威胁到它,那个讨厌女人也不能。”
此刻,温暖的时光又回来了,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有过些什么呢?十八岁那年的明媚夏天,他不停对她重复,他们额头上有着他们自己才看得见的孪生胎一样的标记。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他还垂涎着其他女人。噩梦可能已经开始,间或她也有过一两次大爆发。就是在那时,他炮制出那份契约:“你和我,我们签一份两年期的协议,可延长……”
因为年少轻狂,也因为出乎意料,她甚至想都没想就说“行”,并未意识到人们一旦像外交官或军人那样谈及契约,那就意味着有战争的风险。
很快她就陷入担忧中。噩梦、争吵持续不断,尽管他们许下过永久的盟约:他们俩一个对另一个是“必要的爱情”,萨特这样声称,其他一些艳遇则是“偶然的爱情”。他们要发明一种全新爱情模式:可以在别处交付身体,但永远不能交付心灵。前提是,必须互不隐瞒。
所谓契约这回事,会不会是萨特的一个花招?一种文字游戏,用来替他卑劣的背叛找借口?因为萨特从一开始就在撒谎,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至少他从不说出全部实情。最后,偶然爱情在他的哲学和小说中走了样,变成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没有人比她更有资格来评判这件事:那部让萨特在战前一举成名的小说《恶心》,花费了她多少心血。她第一个阅读他的手稿,然后与他一起修改了不下十遍,直到他找到一位出版商。她在萨特那里的遭遇与他关于偶然性的哲学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突然意识到人在这个百无聊赖的世界上是多余的,不幸的人类在表象中徒然挣扎着。(总之,这是他在这部小说中要表达的。)这种感受完全就是她六个月前在餐馆对着那盘菜肴时的感受。“现在多洛雷丝成了必要爱情,我倒是偶然爱情……变成一个多余的女人……”
***
她一把扯掉被子,那动作中的愤怒就像那天萨特拉着她的胳膊离开餐馆,她把餐巾往桌上扔时一样。
没用。屋子依然那么热,天依然那么黑,黎明迟迟不来,必须独自一人摆脱记忆中的灰暗。
然而这些记忆像沥青般难以甩脱,似胶水封住一切出口,其中最痛苦的记忆也是最模糊的。战前的那些年——确切是哪一年?1936、1937、1938?她开始看清楚:萨特的肉体早已出轨多时,而她几乎没有。
或者说她选择女孩子作为出轨对象,通常是她的女学生们,那些年轻姑娘被她深深迷住,投送其怀,她也不拒来者,但最后总能设法把她们弄到他的床上,这样她就能知道他跟谁睡觉。由于他们之间什么事都说,她甚至还能知道他们怎么上床。
他们间的契约就这样变了味。虽然最本质的结合,精神上的投契,共同的野心及同舟共济的誓言得以延续,但肉体早已分道扬镳。其实那也算不得多大损失,他们从未在彼此的肉体中享受过多少乐趣,两人皆如此。或者说他们俩的肉体是通过她提供给他的“偶然情人”的肉体做媒介,而维系在一起。这也并非没有痛苦,有时候萨特会坠入情网,有时又毫不动心。必须保持这些关系的正常运作,管控好他与她们的分手。偶尔会有两个甚至三个姑娘同时竞争,这时事情就变得更复杂。这其中也有一些她在乎的女孩子,比如她以前的学生,现住洛杉矶的娜塔莉。蜘蛛网般错综复杂的关系需要全力对付,然而很久以前,那种可怕的“梆”已经开始撕扯她的胸膛,还有新近的噩梦也来撕裂她的夜晚。
有一天,为了摆脱其中的某场三角恋,她写了一部小说《女宾》,令占领时期的读者趋之若鹜。但战后,更大的荣誉落在萨特头上,一群群女人更像黄蜂般围着他嗡嗡作响。尽管如此,她仍然坚信:“这些愚蠢的女人,无非是过眼烟云。不管发生什么,我将仍然是他的必要爱情。”她继续掌控着全局。
已经面临地狱,可这个长夜又很像天堂,当那个该诅咒的多洛雷丝出现在萨特生活中时,所有的偶然爱情几乎顷刻消失,只给多洛雷丝留下了地方。在他首次去纽约旅行后,她就应该去找他,当时多洛雷丝还未被征服。他在打字机上不是在写作,而是想入非非,胡乱按键。他在写诗——萨特,写诗……后来事情越来越严重,在各种配给短缺的年代,他上天入地找借口找钱要横跨大西洋。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竟大功告成,再次出发去美国。而这次,他的猎物没能逃脱。
她知道就在离此地几步路的地方,他征服了多洛雷丝,他什么都告诉她。然而一说完,他立即用他那不可思议的手腕来达到新目的:和“迷人的海狸”保持距离。
她的黑色克星!是的。这段时间来他背着她所做的一切形成了一张蜘蛛网,而她却不在其中——要么这对她是个陷阱。现在不是萨特在指挥,而是另一位,是那个该诅咒的女人在操纵一切。证据:看看他的巡访日程,他委托多洛雷丝张罗。她出卖他,而他这混蛋,却什么也没觉察。
***
终于有一点微风了,从哪来的?像其他事一样,没法搞清。不过这让人感觉好受一点,有助入睡。
再次陷入迷迷糊糊的状态,意识拐入另一条支流。接着一切又命中注定般地沉入一片黑暗,那个顽固的无声的声音,再次响起。
那声音有时会换种形式。“有什么事正在发生。”这是一种预告,但总是同样的困惑,是什么事呢?
谁能回答?心理医生,也许会有神奇的发现……但这些只适用于其他人,当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灵魂医生,并且医生的名字叫萨特时,完全没必要去敲心理医生的门。再说心理医生从不会透露自己的点滴心境,而在萨特那里会得到回响,他也会细数他自己的苦恼,这还是很吸引人的。问题是自从那个多洛雷丝出现后,他越来越远离自己。
但怎能放弃与他的对话呢?那像酒精一样,多带劲呀,至少目前如此。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那些信,在书写这些信的时候,痛苦消失了,没有“梆”,唯有对词语的掌控。词语:那该诅咒的女人又懂得多少?她知道词语的秘密源泉吗?知道词语的陷阱吗?知道它们的操纵能力和魔法般的力量吗?
对,给萨特写信才是今天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在汗水湿透的床单下冥思苦想。她起身,在一张纸上记下噩梦中突如其来的那句话,然后去问问他的看法。如果其中藏了什么奥秘,他一定能看出来,并且肯定能给出让人心安的解读,给出有助生活的建议——对待这类事情他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对了,就在几星期前,那天自己心情低落到了极点,除了那该诅咒的女人,还有那本无人问津的小说,还有那篇只有少数专家才感兴趣的哲学论文,最沉重的打击当是那部刚刚经历了失败的话剧。这种情况下只需对他嘀咕几句诉诉苦,萨特就能指明未来的方向。
“我渴望书写我的生活,”她曾这样对他说过,“写我的忏悔、我的记忆,类似这样的作品……作为开始,我先要问自己,对我来说,身为女人意味着什么?”
萨特是如何回答的:“你会这么思考因为你是个女人……当然,你被抚养大的方式与男孩子是不同的。这件事需要更进一步考察。”
醍醐灌顶!女孩子的教育,是事先预设了方向的……突然一切都有了意义,每一次他们的思想都能高度融合,用以破译这个世界。
他们默默相互注视着,萨特不再说什么,她也不说话,思绪像脱缰的野马。
他顺其自然,只管一口口抽着烟斗,耐性等待下文。其实他早已料到,过不了多久他亲爱的海狸嘶哑的嗓音就会滔滔不绝填满这屋子。果然没猜错:“女人,当然是问题的核心,这是我的前提。答案:社会学、神话学研究表明,女人从出生到成长到死亡,一直都被男人主宰的教育蒙着双眼,好让他们更加确认自己的权威,让女人臣服于他们的帝国……”
她讲了近一个小时,一旦讲完,多洛雷丝早被她抛到九霄云外。更带劲的是,为那本告别萨特前被她称之为“我的关于女人的书”,第二天她就跑到国立图书馆查阅文献直到深夜。
不过这份热情只持续了一两周,奇怪的是另一个强烈念头取代了之前的狂热:去美国旅行。那时她一讲起此事就会激动得发抖,有人这么告诉她。现在她想起来了,那人就是她以泪洗面的日子里的好友,雕塑家贾科莫迪。他在圣日耳曼大道上遇见她,见她两颊绯红,两眼放光。他打量了她好一会儿,随后抓起她的胳膊说:“小心呀,海狸,到了那儿可别被哪个彪形大汉拐跑了!”
这可触痛了她:“谁,我吗?你可是了解我的,谁会要我呀?”贾科莫迪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抓着她的手臂。她挣扎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比萨特更吸引我呢?”
他不再盯着她看,继续赶路。
***
窗帘缝隙里露出鱼肚白,回忆也变得苍白。黎明来临,记忆的潮水退却,同时生出一股相反的力量,她渴望行动。
立刻起床!一旦有可能,倒要看看这个该诅咒的女人长什么样,肚子里有什么货。看看她的薄弱点,找准最佳进攻角度,因为这将是今天早晨,也可能是今晚或明天要打响的一场战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