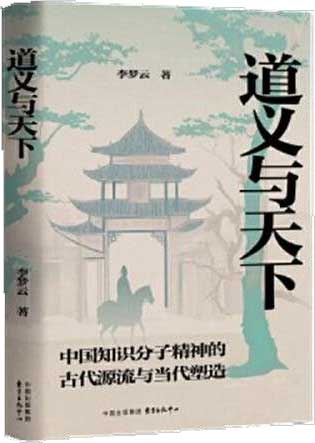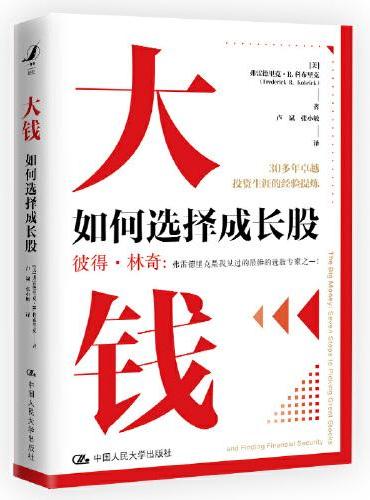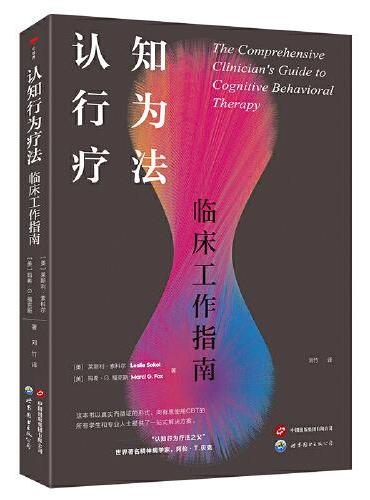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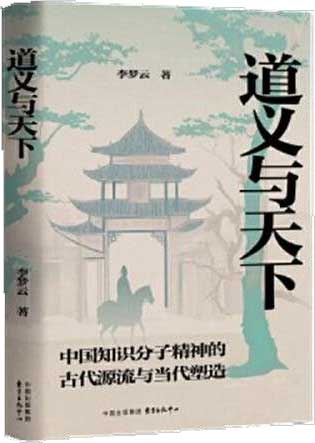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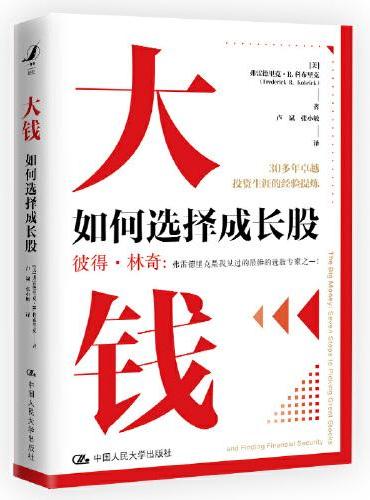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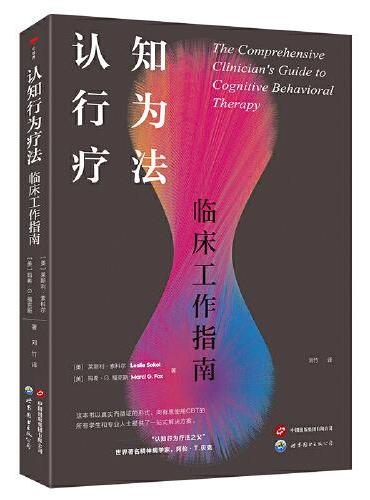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台湾自然书写领航者刘克襄,写给少年和大自然的家书
三十幅铅笔手绘地图、草木鸟兽图鉴
在十五岁,走遍岛屿的四季,记载自然变化
重现朴挚好奇的年少冒险时光
|
| 內容簡介: |
|
台湾自然书写领航者、“漫游达人”刘克襄,将自己年少时的探险经历,化作手绘地图和草木鸟兽图鉴,写成一封封家书,寄给十五岁的儿女,也寄向当年十五岁的自己。十五岁这“最后的童年时光”,如同每一年暑假的尾声,孩子们渴望冒险、迫不及待奔向未知世界,却也绕不开种种私我成长的烦恼。而广阔的山林和天空,无边无际的岛屿壮游,是启蒙和疗愈的最佳场所。书中配有作者精心绘制的插图,或鸟兽虫鱼图鉴,或山林小径速写,或古镇乡野地图。读者可从这场青春、少年和自然的隔空对话中,窥见时代变迁,体会生命流转不息的奥秘,为成长开拓全新的出口。
|
| 關於作者: |
|
刘克襄 1957年生,台湾自然书写领航者。从事自然观察、历史旅行与旧路探勘近三十年,透过摄影、地图、绘画和文字,不仅细腻地编织大自然的故事,更经营深度的人文生态思索,开拓富有创意的漫游路线。已出版诗集、散文、长篇小说、绘本和摄影作品三十余部,其作品洋溢着博物学家纵观博闻的特质,屡屡带动书写风潮,引起社会对相关题材的关注。代表作有小说《风鸟皮诺查》、《永远的信天翁》,散文《11元铁道旅行》、《十五颗小行星》,自然志《台湾旧路踏查记》等。曾获台湾自然保育奖、台北国际书展大奖。2011与2012连续两年获得《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奖。近年旅行的视野除了自然,更增添日常生活气息,如乡野小镇、菜市场等;并在每年的“台北文学季”担任文学地景走读活动领路人。
|
| 目錄:
|
序 十五岁,最后的童年
辑一 我的自然启蒙
大城守望
黑瓦小屋的家园
棒球小子
山城捕蝶
逃学到远方
孔雀鱼之恋
溯河旅行
老城老书店
浪荡台北
大湖泅泳
辑二 你们的山峦之歌
走过大霸尖山
一个消失的族群
阿里山的爱恋
离家出走
寻找一只大鸟
第一个女朋友
十五岁女生
三封未寄的绿皮书信
最后一堂课
我们的大河
|
| 內容試閱:
|
浪荡台北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电视播报蒋介石病逝了。还记得那天凌晨台中盆地雷雨交加,因而我一直怀疑,很可能他早就离开人世,只是选择这个“良辰吉日”公布而已。
此事暂且不表。我为何记得特别清楚,原来隔天早上,台中一中升旗典礼时,校长在操场涕泗纵横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未几,每个人的卡其服上,都多肩了一块小黑布。而我站得很不耐烦,跟旁边的同学聊天,被教官记了警告。
但这只是“国殇”的开始,此后每天报纸都以黑白版出现,电视也多半是单调的宣导纪录片和歌曲,什么流行歌曲和电视剧都取消了。比现在SARS 蔓延时,日子恐怖而无聊许多。
一个月以后,才出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从报纸获知,蒋介石奉厝慈湖之前,大概有一两个星期,棺木会停放在国父纪念馆,供民众和学生瞻仰。学校也通令,任何学生只要报备,可以自由选择一天,北上探望老人家遗容的最后一面。
能够不用上课,借此机会北上,我和几位同学自是兴奋莫名,下课时都在盘算着如何旅行。那时,大家刚好都看完一位大陆红卫兵的自传《天仇》。到台北看老蒋,遂被我们想象成一次革命运动,就像书本的主角搭乘火车到北京,进行大串联。随即,我们便决定牺牲星期六早上的课,星期五晚就搭乘火车北上。
那一晚,在家用完餐后,我赶到车站前的喷泉池,和大家会合。当场买车票,搭乘对号快车北上。上了车一看,这才发现列车内挤满了旅客,有不少跟我们一样,都是想去看蒋介石的学生。
原本以为,车上一定充满哀伤之情,岂料整个车厢热络异常,反而洋溢着某些奇怪的欢乐。好像许久未见的同学会。好几群年轻人围聚着,叽叽喳喳,仿佛高中三年来未讲完的话,都想趁这时好好聊个透彻。
我们没有座位,也不会想到需要座位。很多学生也是这样,有的就席地而坐,有的则卡进两张椅背间的隙缝,有的还想爬上行李架躺在那儿。初时,我们带了扑克牌,就站在走道上发起牌,认真地玩起拱猪。火车每停一站,都有不少旅客上下,车厢有些脏乱,以及溢出水渍。经过长长的山洞时,又涌进许多煤烟气,走道旁的厕所更不断传来异味。但我们毫不在乎,一路保持畅快的心情。
后来,还跑到车门,就坐在门阶那儿,胡乱地聊天,谈西洋流行音乐。什么都说完了时,开始唱歌。有些歌音调太高,我们就伸长脖子,涨红着脸,声嘶力竭地对着车外乱吼乱叫,也因而兴奋了半天。或许,这辈子坐火车,此时最快乐了。这也是十七岁以前,自己搭乘最远的火车旅行。
但火车过了竹南时,一个神情肃穆的军人大概是看不过去了,忽地站起,如丧考妣地怒目,对着整车的人大声斥责,说了什么面临这样危难的关头,大家居然不懂得夙夜匪懈,努力报答社会,竟然只知行乐。他非常伤心,不齿和大家为伍。
一时间,旅客们面面相觑,寂静了好一阵,只剩下火车震动的声音。只是没多久,大家又兴奋地闲聊,仿佛不曾发生过刚刚的事。那年轻的军人似乎也觉得自讨没趣,就闷在座位,一手支颐,遥望着车窗外黯幽的夜色,独自遥祭老人家了。
那晚的火车,虽然坐足了四个小时之久,却觉得时间怎么那么快,没一下子,就听到广播:“台北到了,要下车的旅客……”听到广播声后,我们都抢着站到车门旁,把头探出去,好奇地观看外头的世界。
这时火车缓慢地穿过中华路。中华路是当时最热闹的街道。街道上的商家,平交道栅栏后的车辆、行人,连平交道上不断作响的声音,对我而言都充满新鲜感。尤其是经过西门町时,我更是眼睛放亮。虽然那时因为管制,呈现一片黯幽的世界,但黑暗里远方大楼上的一点异样灯光,都让人兴奋莫名。
抵达台北火车站时,已经深夜十一点多。车站大厅空荡荡的,我站在那里发了一阵呆,又走到喷泉池前面,好奇地观看路过的行人。
我们走到天成饭店旁边的巷子里,吃了一碗牛肉面。老天!几根青菜和着肉汤的面条,一碗居然四十元。那时我在台中吃的才十五元呢!
吃完,问知国父纪念馆的方向后,就继续沿着铁道往东边走。这附近的火车似乎很忙碌,不断轰隆作响,经过我们身边。甚至,突然地发出震耳的鸣笛声。那时感觉,仿佛世界正在你旁边,就要发生一些大事,自己已经走在时代的尖端。
所幸,铁道旁边仍然有许多稻田,还听到青蛙和蟋蟀的叫声,很像台中市郊,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公寓大楼零星地散落着。走了许久,又经过几处平交道。那时还怀疑是否走错了,会不会走到基隆海边去?
结果,一直走到现今敦化南路附近时,两边还很荒凉。后来转到忠孝东路时,成排的大楼紧密地出现,才感觉到有些都市的气息。
那时已经凌晨两点,我们和成千上万学生挤在国父纪念馆外的街道,一个挨着一个。记得旁边就坐了一个北一女的学生。她很大方,问我从哪里来。我却涨红了脸,坐立不安,因为从未和女生坐在一块。结果,连个“从台中来的”都讲不清楚。其他同学也不帮忙,都躲在一旁窃笑。
那时国父纪念馆旁边还有广漠的稻田,我不时离开人群,跑到那儿透气。好不容易,别扭地熬到清晨六点。再排长龙进入馆内,匆匆地,看到他老人家躺在棺木里。只是那最后一面,一点也不像肖像上常看到的脸孔。那时也很怀疑,躺着的是否就是本尊。我只确定,自己搭了一趟遥远的火车,一夜未睡,去看他。
大湖泅泳
选择一个无所事事的日子,躺在开阔的湖边,晒着暖阳,并且聆听着自己喜爱的音乐,这种悠闲的生活,应该是何等快意的人生啊!
年轻时,我不仅如此萌生偷得半日闲之想法,而且,很快地,在寒假时就付诸实现了。
放寒假没多久,班上的伙伴们便率性地决定,前往日月潭露营。除了两天一夜的食物,特别带了一台偶尔会跳针的手提电唱机,以及六七张刮得伤痕累累的唱片。刮得最凄惨的一张,那是众人最迷恋的披头士。没了这电唱机,没了披头士,我们的露营就无法百分百。
露营的地点在潭东,青年活动中心的前面,一处平坦的开阔草坪。一抵达湖边,我们很快就搭好营帐,并且煮好肉酱面条的午餐。天公也相当作美,当我们饱餐时,适时地露出暖阳。我们仿佛游荡在风和日丽的海边,躺在草地上,闭起眼,恣意地挥霍下午的时光。大伙儿也不忘打开电唱机,披头士的歌曲一听再听,不断地摇头晃脑,歇斯底里地哼唱着。乡村的《Norwegian Wood》、童话的《Yellow Submarine》,或是抒情的《Yesterday》、《Let It
Be》,歌词内容都倒背如流了。
但不过短短一个小时光景,阳光持续照射下,大家开始觉得炙热,纷纷坐起,竖直背脊,有些烦躁了。也不知有何可以消遣,只好远眺大湖,注意大湖上零星的渔舟、船屋。
寂寞得有些发慌。怎么办?有人突然提议,何妨比赛游泳,看谁能游到湖中一艘无人的竹筏上,再游回来。
那竹筏少说有两百米之遥,游得到吗?何况没有人带泳裤,如何下水呢?我还在犹豫时,旁边的人已开始鼓噪。只听到旁边又一阵喧嚣的叫好声,只见一位同学早脱下长裤,着白色的四角内裤就冲下去了。其他人更加兴奋地叫好。可是,率先下水的同学,没游几米,就迅速地回头,慌张地冲上岸,一边紧抱身体,大喊“好冷,好冷”,随即头也不回地钻入营帐里。
他的滑稽动作,反而刺激了其他人的跃跃欲试。大伙儿一边向他喝倒采,一边在岸边热起身子。未几,又有两人冲下去。其中一位跟先前一样,不消几秒钟,就仓促上岸。但另一位,体育班的,勇健得很,不仅适应得轻松自如,居然还朝竹筏游去。
眼看他都勇往迈进,其他人也纷纷鼓足勇气,冲进湖水里。只剩下我和一位较矮小的同学。他们也被冰冷的水冻得哇哇大叫,但这回都坚忍着未上岸。我们两个未跟进的人,开始被嘲笑。这等情形,若不下水,似乎没有团队精神。我不得不脱下衣裤,冲入湖里。
一跑进去,不觉大吃一惊。老天!陆上天气炙热,但湖水仿佛才解冻般,还来不及哆嗦,整个人已经涌进一阵寒意。同学们在旁兴奋地呼叫,我却完全失去他们的声音,反而孤立在一个奇怪的冰冷世界。只听到,自己的心脏快速蹦跳,巨大的“咚、咚”声,在耳际,如雷般地轰响着。
吃力地回头,想要游回岸,但岸边的同学似乎也在讪笑。我只好硬撑在原地,不停地划动着。试着以脚探触,竟无法探触到湖底。
此时,耳边又传来一阵清楚的呼叫声,有一位同学游过来。我侧过头,他示意着往竹筏的方向,希望一起过去。紧接着,又看到那体育班的似乎已经游得很远了。
这时,我也不知仗着哪来的勇气和体力,竟答应那同学的邀请,一起朝竹筏游过去了。其他人则纷纷打退堂鼓,游回岸上。看到别人回头,难免有些后悔,但又怕此时回头,被人嘲笑懦弱。只好硬着头皮,努力地跟在后头,蛙泳前进。
突然,眼前一阵怪叫声。往竹筏望去。体育班的已经爬上竹筏,在筏上英雄式地挥手。同伴更加卖力,努力地往前划动。渐渐地,我被他摆脱,愈离愈远,而竹筏似乎不曾接近。
勉强游了一半吧,又有些三心二意。转头再看岸上,回头似乎更麻烦。知道已经不可能了,只好咬紧牙关,游向竹筏。
但愈游愈慢,似乎老是在原地浮沉,失去前进的感觉。等看到另一个同伴也登上竹筏时,竟有些丧失信心,除了头部,双手已无力摆出水面。
岸上的同学还在热烈地欢呼,根本未注意到我的疲惫窘态。倒是竹筏上的两个人,注意到我的体力似乎无法支撑了。他们在竹筏上大喊,这才引得岸上同学紧张起来。但我的视觉愈来愈模糊,若眼睛睁大一点,似乎都会浪费体力。只能模糊地感受一丝前方的光源,确定竹筏的位置。
我已经丧失游到竹筏的信心,只能支撑着,像一棵枯木般地漂浮,不让自己沉溺。霎时间,感觉到了死亡,似乎正在接近,而且牵着我,往湖底沉下去,而我毫无拒绝的能力。
接着,隐约听到竹筏上有人跳下水。又过了一阵,旁边有惊慌的声音,是那体育班的,他大喊着:“快到了,加油。”
他伸过手来,想要扶助,我却奋力地摇头。不知自己当时为何如此。但这一拒绝,竟激发了更大的意志。终于,察觉竹筏接近了。举起手,试图抓住竹筏的边缘。但举了很久,手一直急切地悬在高空挥舞,始终无法碰到任何东西。也因为这样心急,胡乱地拍打水时,竟囫囵吞了一口,呛得惊醒过来。就在这样惊吓中,突然间,碰着了一个实体。确定是竹筏时,才整个人安心地靠了过去,全然瘫痪在那儿。过了好一阵,他们两个再努力地把我拉上去休息。
趴上竹筏时,一想到要如何回到岸上,整个人更是四肢乏力。他们看我半晌不动,还以为我真垮了。
说也奇怪,躺了一阵后,再起身坐定时,体力似乎恢复了。好像也比较有把握游回岸上。我猜想,刚才可能是过于慌张,又未适量地暖身,才被冰冷的湖水吓掉了大半
体力。
游回去时,果然顺畅许多,几乎没什么困难就抵达。到了时,还受到最高的礼遇,晚上不用煮饭,可以任意地躺在营帐里听披头士。但我未休息太久,还是起身和大家一起工作。因为内裤湿了,躺着难受,还不如多活动,干得快。
吃完焦味浓厚的晚餐后,我们在草地上生起营火,继续烘烤身子和衣物。有几位还跑到杉林里,拖出了不少杉木和杉叶。这些最容易着火的林柴,让营火畅旺地烧了整晚,披头士也不断地唱着。我们仍跟过去一样,继续熬夜。营帐灯火通明,大家轮流玩拱猪、桥牌,直到后来都疲惫地横躺在一起。隔天,天露曙光,营火不知何时熄灭,只剩奄奄一息的余烟。
清晨时,我被炒菜的声音和香味吵醒,同学们都还在昏睡。我起身,探头。看到林子边出现了一座米黄色的帐篷,旁边有一辆机车。大概昨晚才抵达。
好奇地走过去,帐篷后有两个年轻人正在煮饭。他们正用一个铝盆炒高丽菜,菜里面加了虾米和香肠切片。或许是有些饿了,看来非常好吃的样子。另外,旁边还有一个锅子用来蒸饭。他们和我打招呼,邀请我一起吃早餐。我却故意说吃饱了。毕竟是陌生人,不好意思。
菜炒好后,他们各自拎了小钢杯盛饭,夹食铝盆里的高丽菜,一边远眺着大湖。他们是北部来的大学生,正在环岛旅行。他们共骑一部机车,后面有一个大背包,装载了营帐和炊具。一路旅行时,在各地杂货店买当天的食物。用完餐,他们马上收拾营帐和锅盆,研究旅行路线后,从容离去。这里是第一站。明天,他们要去阿里山,然后再南下垦丁,接着绕到东海岸。
这个陌生的邂逅看似平常,后来却深深地影响我。我长大退伍后的机车旅行,东西也十分简单,一样也是钢杯、锅盆等简单而方便的行头。连吃的食物,似乎都是高丽菜掺一两根香肠,或者依旧是面条、肉酱,如此就觉得人生很享受了。
那时,凡登山人使用的优质器材,我竟觉得是一种浪费的奢侈品,贵族化的享受,很不节俭。
不久,草地上又来了一群年纪和我们相仿的男女学生。他们带来了手提录音机,围成跳舞的阵容后,开始播放土风舞歌曲搭配。然后,在草地上快乐地手舞足蹈起来。同学们终于全被吵醒,呆愣愣地坐在那儿,看着欢乐的表演。
我远离他们,继续坐在湖边,想象着那对年轻人骑机车继续南下旅行的各种可能,一边远眺着昨天惊险泅泳的湖面,以及湖面上空荡的竹筏。年纪大时,才知道那竹筏是捕捉奇力鱼的,只是记不得是否有长草。
再过一阵,学校就要开学,高中生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好像苦日子还要撑一些时日,才会结束。望着大湖,竟莫名地感伤起来。
十五岁女生
十五岁的女生有两种,一种只会死读书,一种专门写信给男生。
这是女作家阿洛在十八岁时告诉我的。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她才从北一女毕业,和我一样吊车尾,考上阳明山上的偏远大学。她的另外一个高中死党,夏宇,更是无出其右,连个学校都没捞到。只是,后来随兴写诗,不小心变成台湾当代重要的诗人。我想她们的十五岁,应该都是后面的那一种。
我一直把这个深刻的印象留存着,直到现在,当你们跟我一起到野外旅行,我才知道,十五岁的女生,在她们还没十五岁以前,可能也有两种。一种像安静的蝴蝶,停在隐秘的森林里,很少挥舞翅膀;一种是不停地跳动的山雀,成群沿着树林,吱喳个没完。
最熟稔的一位,小学二年级时就认识了。每次旅行回来,都会书写观察的感受。不论是山路、古道的跋涉,或者是老街、古迹的巡礼,小女孩总能透过自己细腻的眼光,看到一个我疏忽的,或者难以关照的郊外环境。譬如以下两段的小小心得,就能窥知一二:
这里的树都是柳杉,没有别的树种,但它们长得非常高大,使人觉得空气清新,阳光在树林中闪耀,柳杉林中很潮湿,所以树干上长满了绿衣,我喜欢潮湿一点的树林,能使人闻到潮湿的森林气味,心情舒畅。不过在这里,我没有发现什么,只看到紫啸鸫在树枝上。
——11 岁时书写的鹿堀坪古道
合兴站很像从前日本的宿舍,很朴素的。我试着在铁轨上奔跑,冷风从耳边刮过,发出了飕飕的怪声,我想向无尽头的地平线奔去。真羡慕火车每天过着这么充满快感的日子。
——12 岁时书写的内湾支线
像这样保持着婉约,又洋溢着孩子气的笔调,无疑是大人和十五岁男生都写不出,也感受不到的情境。更教人疼惜的是,每次去一个小镇、一处山村,或一座山峦,她都会记录自己的旅行。这样一篇又一篇,直到初中以后,功课繁重了,才不得不暂时歇笔。虽然中辍,我想,她应该是很熟悉台湾地理和山川风物的孩子了。这样瞧着她长大,总觉得像是呵护一棵台湾杉的挺立,长高,一直往上。天空的色泽特别地蔚蓝。
我一直把她的旅行笔记,还有她和同学们做的卡片,放在多年搜集的老地图和自然志文献旁边。这是自然赐给我的最珍贵礼物之一。或许小女孩长大了,忘记了这些写过的文章,但我却小心地存藏着,隔一段时间,翻读那描述花草鸟兽和乡镇街景的纯净文字,都仿佛遇见喜爱的特殊鸟种或植物。
尽管那只不过是一篇篇寻常的旅行札记,但我仿佛知道一个小女孩的某一个秘密。在不久前的时光里,她悄悄地跟森林、跟草原说了一些心里的话。那种满足如在高山草原徜徉,山雾散去,惊喜地,乍见水鹿。
小女孩长大了,会不会像灵长类学者珍妮 古道尔一样,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自然科学的领域,我无法预测。也不想以这样的期待,去思考人生,或者投以寄望的眼光。我只是暗自高兴,她可以在自然里,仔细咀嚼,生命较深的那一部分心灵。
另一类女生,在野外课出现时,总教人莞尔却又担心。她们仿佛春天时才刚刚长大的小鹿,腿还未站稳,就跑出来了。每次的旅行都像是第一次的冒险。东闯西撞,分不清野外的安危。走在山路上时,可能比走在忠孝东路上更容易摔倒。过一座小桥,也会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滑跤。
或许,她们平常在学校就是如此了。不小心翻开她们的书包,耳环、指甲油、化妆品……里面可能还留着一两封写给男生的信,或者是骂教官的小纸条。她们的课本和以前的女生一样,继续画了许多美丽的公主,以及她们心仪的王子。她们被罚写的切结书(即承诺书、保证书,检讨。——编注),绝对远比作文还多。
但她们一走出教室,许多烦恼就抛诸脑后了。眼前都是华丽的世界,绚烂的人生。抵达海边时,我介绍海岸和大地的分界意义。她们像刚刚飞抵台湾的水鸟,好像发现新大陆,雀跃地喊叫。瞻仰老树时,我描述百年来村民的情感。她们团团围住它,舞动着身体,好像在跳土风舞。拜访老车站时,我建议她们,想象自己是一个即将远行的旅人。她们站到月台上,兴奋地唱歌,仿佛要去毕业旅行。
啊,那青春的脉动,迎风的激越,都让我的自然观察变得拘谨,不自然了。她们才是真正享受生命,而且挥霍得很潇洒的年轻人呢。
我相信,自己想要诉说的乡土风物,她们不会记得太多。长大以后,大概也很少会回到我走逛的自然世界。她们会像现在多数的六年级女生,在城市与城市间旅行,最多以自然佐茶,以花草寄情吧。
有次碰到两位就最为明显了。她们坐在车上时,一路兴奋地聊个不停。我在努力地谈着中法战争和刘铭传,她们在后面专注地聊NBA 和男朋友。还不时从背包里取出皮夹,争看着对方的男朋友们的照片,一边品头论足,一边窃笑着。
知道她们都有许多男朋友时,我着实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她们把认识很多男朋友,当作一种游戏。她们喜欢说“我的某某任男友”、“我和他如何交往”,等等。她们的男朋友,可能是学校的英文老师,也可能是某某偶像歌星。只要喜欢,都可以冠上这个称号。
但这都是单恋,单相思。百分之九十九,十五岁女孩子的情意结。那都是网上情人,虚拟实境。她们上网,把男朋友的像下载下来,跟自己在野外的一张照片合成。譬如,有一个认定了小牛队当家大前锋诺维茨基,凡有小牛队之比赛实况必定观赏,管他段考与否。而为了让两个人站一起时不那么悬殊,她只取上半身。于是,她和两米一的诺维茨基靠在一起时,就只差一个头而已。
啊!这些七年级末段班的。两个人相聚时,就变成菜市场。我如果了解她们,大概就知道麻雀集聚在一起,交头接耳时,都在说些什么了。
十五岁以前如是。在她们这段被压抑的阶段,如黑白电影般的生活篇章里,我只能期许着自己,就像其他老师,展示自己热爱生活的那一部分色泽。我也得努力,提供冒出绿芽和嫩叶的元素啊。
浪荡台北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电视播报蒋介石病逝了。还记得那天凌晨台中盆地雷雨交加,因而我一直怀疑,很可能他早就离开人世,只是选择这个“良辰吉日”公布而已。
此事暂且不表。我为何记得特别清楚,原来隔天早上,台中一中升旗典礼时,校长在操场涕泗纵横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未几,每个人的卡其服上,都多肩了一块小黑布。而我站得很不耐烦,跟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