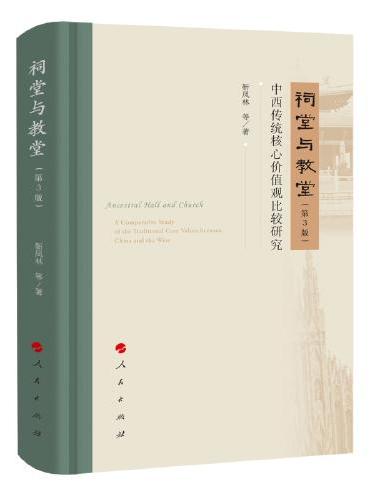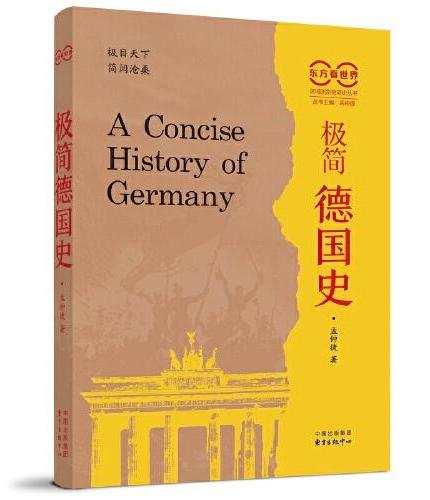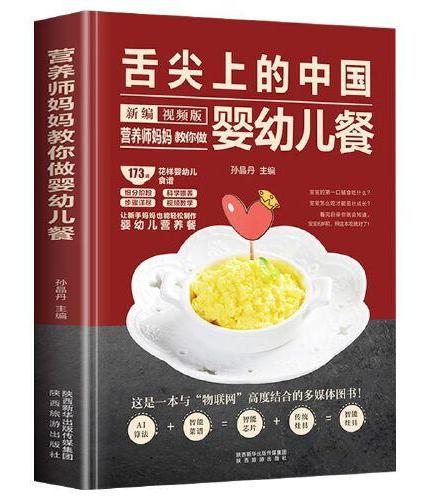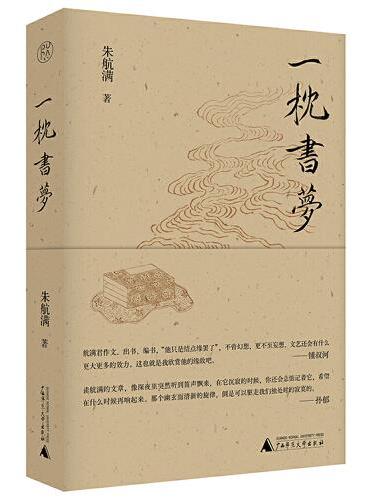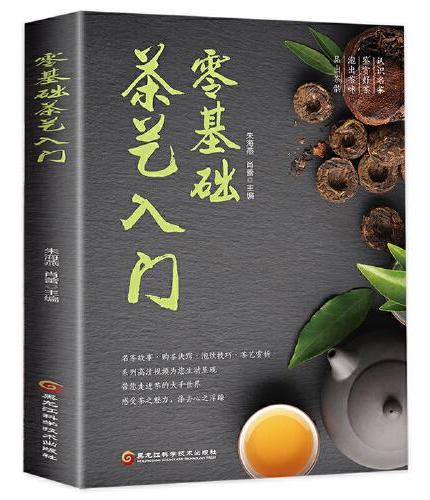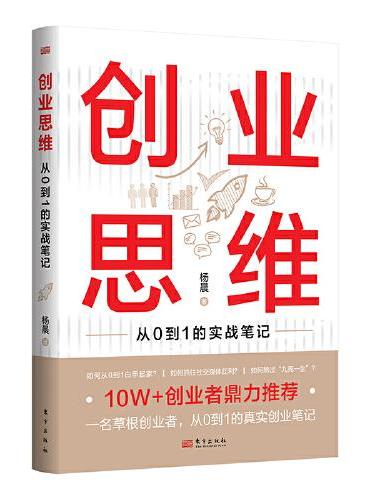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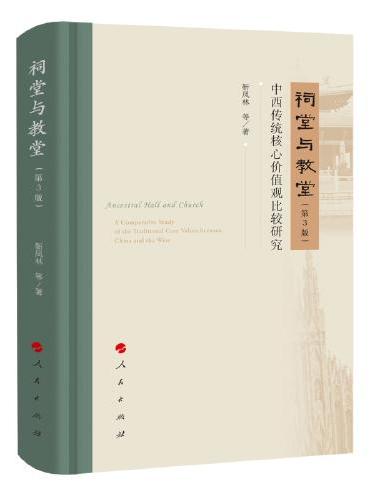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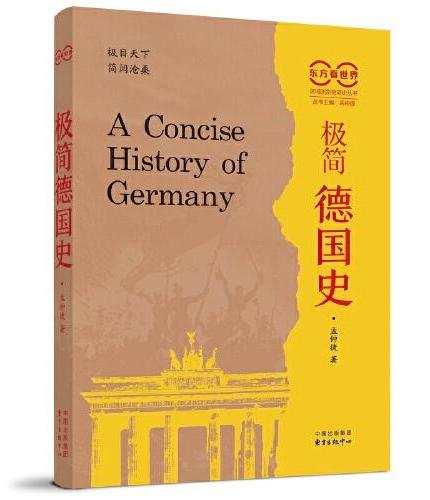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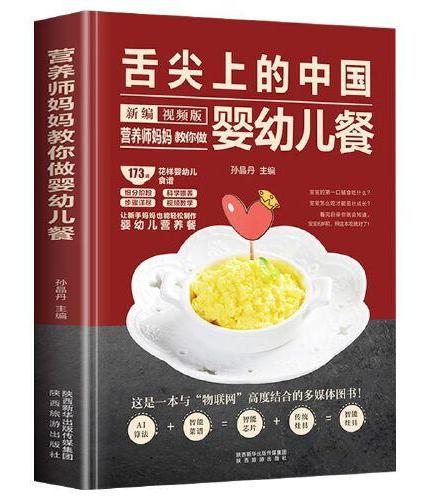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NT$
296.0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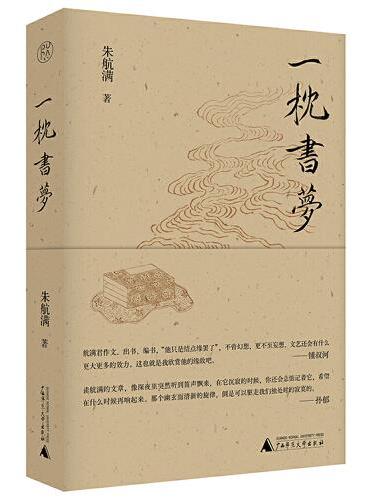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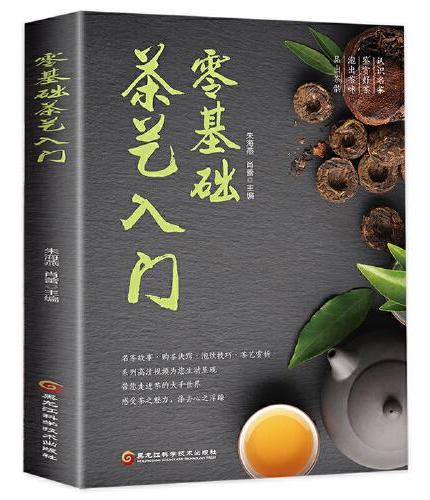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NT$
1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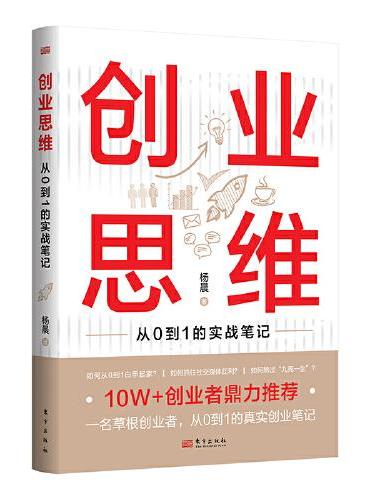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NT$
356.0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
本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真正做到了无障碍阅读。在每一本书前都写了前言,对书中许多字词典故也作了注释。
|
| 內容簡介: |
|
《欢喜冤家》每回写一个故事,内容多为男欢女爱之事,其中颇多传奇色彩。由于这些故事奇特,情节曲折,又是写下层人民生活的,在当时很受一般读者欢迎。内容包括:花二娘巧智认情郎;吴千里两世谐佳丽;李月仙割爱救亲夫;香菜根乔桩奸命妇;日宜园九月牡丹开等。
|
| 關於作者: |
|
西湖渔隐主人,其人不详,杭州人,可能生于晚明或明末清初,著有小说《欢喜冤家》《春染绣塌》。
|
| 目錄:
|
原序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第二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第三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第四回 香菜根乔妆奸命妇
第五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第六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耍
第七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第八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第九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第十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第十三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第十四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第十五回 马玉贞汲水遇情郎
第十六回 费人龙避难逢豪恶
第十七回 孔良宗负义薄东翁
第十八回 王有道疑心弃妻子
第十九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第二十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第二十一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第二十二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第二十三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第二十四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
| 內容試閱:
|
第一回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世事从来不自由,千般恩爱一时仇。
情人谁肯因情死,先结冤家后聚头。
这四句诗,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来。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他父亲名叫花遇春,年将半百,单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欢喜。长成六岁,上学攻书,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聪明,苦了先生,费尽许多力气。读了三年书史,一句不曾记得。不想到了十岁外,同了几个学生朝夕顽耍。父亲虽严,那里曾怕;先生虽教,那里肯听。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想到这般顽子,不能成器,到不如歇了学,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因此送了先生些束脩束脩:古时送给教师的酬金。脩,原意为干肉,又叫脯。,竟不读书了。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
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孩儿不肖不肖:不能继承祖先事业,没有出息,或不正派,品行不好。,年已长成。终日闲游,不能转头。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或者拘留得住。那时劝他务些生业,也未可知。”遇春道:“我心正欲如此,事不宜迟。”即时就去寻了媒婆。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却说几家女子曰:“某家某家可好么?”遇春听了道:“这几家到也都使得,但不知谁是姻缘,须当对神卜问,吉者便成。”别了媒婆,径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到是姻缘,余非吉兆。也罢,用了徐家。又见媒人,央他去说。
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并无亲族,到在姑娘姑娘:指姑姑。家里养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恰好媒人去说,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向来晓得花家事情:有田地房屋的人家,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自古媒人口,无量斗,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那徐氏信了,即时出了八字。因此花家选日成亲,少不得备成六礼,迎娶过门。请集诸亲,拜堂合卺合卺jǐn:新婚夫妇在新房内共饮合欢酒。。揭起方巾花扇,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但见:
秋水盈盈两眼,春山淡淡双蛾。金莲小巧袜凌波,嫩脸风弹得破。唇似樱桃红绽,乌丝巧挽云螺。皆疑月殿坠嫦娥,只少天香玉兔。
诸人一见,果然生得十分美貌,无不称好。一夜花烛酒筵,天明方散。未免三朝满月,整治酒席,这也不提。
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尚兀自兀自:仍旧,还是。疏云懒雨,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过了几时,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肖的单身光棍,姓李名二白,年纪有三十岁了,专一好赌钱滥饮,诱人家儿子哄他钱钞使用。这花林又着着:被,让。他哄骗了,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
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没了许多,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禀明了公婆;还存得几件衣物,送与婆婆藏了。公婆二人闻知,好生气恼,恨成一病,两口恹恹,俱上床了。好个媳妇,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央邻请医,服药调治,那里医得好。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又去要妻子的衣饰。见没得与他,几次发起酒疯,把妻子惊得半死。
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甚是冷淡。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姓任名龙,年纪未上二十。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三考:指科举制中的“乡试”、“会试”、“殿试”。出身,后来做了一任典史,趁得千金。不期父亡过,止存老母、童仆在家。妻子虽定,尚未成亲,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有一面之交。
一日,途中不期相遇,叙了寒温;恰好又遇着花林,各叙名姓。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径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请着任龙。席上猜三道五,甜言蜜语,十分着意。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三人契同道合,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终日思饮索食。
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竟不想着柴米夫妻。他父母一日重一日,那里医治得好,遇春一命呜呼,花林又不在家,央了邻家四处寻觅,方得回来,未免哭了几声。三朝头七,还到亏了任李二人相帮,入棺出殡,治丧料理。不料母亲病重,相继而亡,自然又忙了一番,方才清净。余剩得些衣衫首饰,妻子又难收管,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这番没了父母,竟在家中和哄了。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我们虽异姓骨肉,必要患难相扶;须结拜为弟兄,庶可庶可:才可。齐心协力。我年纪痴长,叨叨tāo:客套话,表示沾光。做长兄,花弟居二,任弟居三。你二位意下如何?”二人同声道:“正该如此。”三个吃了些香灰酒,从此穿房入户。
李二唤徐氏叫二娘,任三叫二娘做二嫂,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十分爱慕。每席间将眼角传情,花二娘并不理帐他。丈夫虽然不在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任三官青年俊雅,举止风流,二娘十分有意,常将笑脸迎他。任三官虽然晓得,极慕二娘标致;只因花二气性太刚,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所以欲而不敢。
一日,花二在家买了一些酒肴,着妻子厨下安排,自己同李、任在外厢吃酒。谈话中间,酒觉寒了,任三道:“酒冷了,我去暖了拿来。”即便收了冷酒,径至厨下取酒来暖。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那脸儿如雪映红梅,坐在灶下炊火煮鱼。三官要取火暖酒,见二娘坐在灶下,便叫:“二嫂,你可放开些,待我来取一火儿。”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听着这话佯疑起来,带着笑骂道:“小油花什么说话,来讨我便宜么?”任三官暗想道:“这话无心说的,到想邪了。”便把二娘看一看,见他微微笑眼,脸带微红,一时间欲火起了,大着胆,带着笑,将身捱到凳上同坐。
二娘把身子一让,被三官并坐了,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二娘微微而笑,便回身搂抱,吐过舌尖亲了一下。任三道:“自从一见,想你到今。不料你这般有趣的,怎生与你得一会,便死甘心。”二娘道:“何难,你既有心,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你同李二同去;我打发二哥睡了,你傍晚再来,遂你之心。可好么?”三官道:“多感美情。只要开门等我,万万不可失信!”二娘微笑点首。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并煮鱼拿到外厢,一齐又吃。三官有心,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天色将晚,李二道:“三官去罢。”三官故意相帮,收拾碗盏进内,与二娘又叮嘱一番,方出来与李二同去。
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出去掩上大门,恰好任三又到。二娘遂拴上门道:“可轻走些。”扯了任三的手,走到内轩道:“你坐在此,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任三道:“何必又去。”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两下云雨起来。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一来标致,二来知趣。二娘十分得趣。怎见得:
色胆如天,不顾隔墙有耳。欲心似火,那管隙户人窥。初似渴龙喷井,后如饿虎擒羊。啧啧有声,铁汉听时心也乱。吁吁微气,泥神看处也魂消。紧紧相偎难罢手,轻轻耳畔俏声高。
花二娘从做亲以来,不知道这般有趣。任三见他知趣,放出气力,两个时辰方才罢手。未免收拾整衣,二娘道:“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但愿常常聚首方好。只是可奈李二这厮每每把眼调情,我不理他;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那时花二得知了,你我俱活不成的。”三官道:“蒙亲嫂不弃,感恩无地,我怎肯卖俏行奸?天地亦难容我。”二娘道:“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任三道:“自古郎如有心,那怕山高水深。”二娘道:“今夜与你同眠方可,料亦不能。夜已将深,不如且别,再图后会罢。”任三道:“既如此,再与你好一会去。”正待再整鸾佩,不想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二人吃了一惊,忙回道:“我拿来了。”悄悄送着三官出去。拴好大门,送茶与花二吃了。花二道:“你怎么还不来睡?”二娘回道:“收拾方完,如今睡也。”
闲话休题。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同觅任三官。恰好任三官在家,便随口儿说:“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想转得来时,天色必晚了。闻知今日海边,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可惜不得工夫去看。”花二道:“李二哥,三官望亲,我与你去看戏如何?”李二道:“倘然没戏,空走这多路途,何苦!”花二道:“我有一个旧亲,住在海边。若无戏看,酒是有得吃的,去去何妨。”李二听见说个酒字,道:“既如此,早早别了罢。”三人一哄而散。
不说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且说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银子,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买办些酒食,拿到花家门首。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着他先去,不可说与奶奶知道。自己叩门而入。见了二娘笑道:“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一来一往有三十余里路程,到得家中,天已暗了。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且与你盘桓盘桓:逗留,留住。一日。”二娘道:“如此极好!”把门掩上。
三官炊火,二娘当厨,不时间都已完备。二娘道:“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也未可知。若被遇见,如何是好?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终日关闭,且是僻静清洁。我想起来,到那里饮酒欢会,料他即回,也不知道。你道好么?”任三听说,欢喜之极。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里边床帐桌椅,件件端正,打扫得且是洁净。壁上有诗一首道:
轩轩:这里指小屋。居容膝足盘桓,斗室其如地位宽。
壶里有天通碧汉,世间无地隔尘寰。
谁人得似陶元亮陶元亮:晋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辞官归隐。,我辈终惭管幼安管幼安:三国魏人管宁,字幼安。少时与华歆同席读书,因厌恶华歆的为人而传有割席而坐的佳话。。
心境坦然无窒碍窒碍:有阻碍。,座中只好着蒲团。
看罢,即将酒肴果品摆下,两人并肩而坐。你一杯,我一盏,欢容笑口,媚眼调情。自古道:“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调得火滚,搂坐一堆,就在床上取乐起来。这一番与昨晚不同,怎见得不同?只见:
雨拨云撩,重整蓝桥蓝桥:唐朝秀才裴航偶遇仙女云英的地方,在陕西蓝田蓝溪之上。之会。星期月约,幸逢巫楚巫楚:神女与楚王在巫山相会。之缘。一个年少书生,久遭无妇之鳏鳏ɡuān:死了妻子又没再结婚的人。,初遇佳人,好似投胶在漆。一个青春荡妇,向守有夫之寡,喜逢情种,浑如拌蜜于糖。也不尝欺香翠幌,也不管挣断罗裳。
正是:
雨将云兵起战场,花营锦阵布旗枪。
手忙脚乱高低敌,舌剑唇刀吞吐忙。
两人欢乐之极,满心足意而罢。整着残肴,欢饮一番。二娘道:“乐不可极。如今天已未牌未牌:下午一点到三点。了,你且回去,后会不难了。”三官道:“有理。只要你我同心,管取天长地久。”言罢作别,径自出门去了。不移时,花二已回。二娘暗暗道:“幸是有些主意,若迟一步,定然撞见了。”
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张着张着:瞅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若花二不时归家,他便躲入后房避了,故此两不撞见。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甚是没兴,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
一日,花二不在家,门不掩上的,他便撞入内轩,问道:“二哥可在家么?”二娘在内道:“不在。”李二听了这娇滴滴之声音,淫心萌动。常有此心,奈花二碍眼;今听得不在家中,便走进里面,道:“二娘见礼了。”二娘答礼道:“伯伯外边请坐。”李二笑道:“二娘,向时兄弟在家,我到常在里边坐着。幸得今日兄弟不在,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二娘,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二娘正色道:“伯伯差了。我男人不在,理当外坐,怎生到胡说起来!”李二动了心火,大胆跑过去要搂,早被二娘一闪,到往外边跑了出来,一张脸红涨了大怒。
恰好花二撞回,看见二娘面有怒色,忙问道:“你为何着恼?”二娘尚未回答,李二听见说话,闯将出来。花二一见,满肚皮疑心起来。二娘走了进去。花二问道:“李二哥,为着甚事二娘着恼?”李二道:“我因乏兴寻你走走。来问二娘,二娘说你不在。我疑二娘哄我,故意假说,因此到里面望一望;不想二娘嗔我,故此着恼。”花二是个耳软的直人,竟不疑着甚的,也不去问妻子,便对李二道:“二哥,妇人家心性,不要责他。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罢。”两人又去了。直到二更时分方回。二娘见他酒醉的了,欲待要说起,恐他性子发作连累自身,不是耍的,只得耐着不言。到次早,见花二不问起来,不敢开口。
李二从此不十分敢来寻花二了,花二也常常不在家,到便宜了任三官。日间不须说起,至于花二更深不回,常伴二娘;便是花二回来,亦都醉的。二娘伏侍去睡,也再不想寻起二娘作些勾当,故此二娘到得与三官十分畅快。三官或在花家房里过夜,或接连三日五日不出门,与花二、李二径自断绝了往来。李二心中好闷,想道:“花家妇人不像个贞静的,少不得终有奸谋破绽。待我慢慢看着,若还有些破绽,定不饶他。”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后探听。
恰好一日,远远望见任三走进花家而来。他连忙在对门裁缝店内看着,只见任三径自推门进去了,有一个时辰,尚不见出来。李二连忙走到花家门首一望,不见些儿动静。把门扯了一扯,又是拴的。他便想道:“多分多分:多半,大概。花二哥在家里,敢是留他吃酒,故此不出来了。”便把门敲上两下。只见二娘出来问道:“是那一个敲门?”李二道:“是我,来寻二哥讲话。”二娘答道:“不在家。”李二想道:“多分是妇人怪人,故意回的,不免说破他。”便道:“既二官不在家,三官怎么在里面这半日还不出来?”二娘道:“你见鬼了!任三官多时不到我家来了,谁见来的?”李二道:“我亲眼见他来的,你还说不在!”二娘怒道:“这等你进来寻!”便出来把门开了。李二想道:“古怪,难道我真见了鬼不成!岂有此理!”便大着步往里进,四周一看,并无踪影。他再也不想有后房的,便飞跑上楼去看,那有三官影儿,到没趣了,飞走下楼阁往外就跑,被二娘千忘八,万奴才,骂得一个不住。
不期花二归家,见二娘骂人,问道:“你在此骂谁?”二娘道:“你相交的好友!甚么拈香!这狗才十分无礼,前番你不在家,他径入内室调戏着我。我走了出来,恰好你回来。你亲眼见的。他今日又来戏我,我骂将起来,方才走去。这般恶兽,还要相交他怎的!”花二登时大怒起来,骂道:“这个人面兽心强盗!我前番却被他瞒了,你怎么不说!今日又这般可恶,杀这强盗,方消我恨。”径上楼取了床头利刀,下楼赶去。二娘一把扯住,忙道:“不可太莽,若是你妻子失身与他,方才可杀。自古捉奸见双,你竟把他杀了,官司怎肯甘休!以后与他绝了交便罢了,何苦如此。”花二的耳朵极绵软的,被妻子一说,甚觉有理。想一想,撇下刀说:“便宜了他。幸喜我浑家不是这般人。若是不贞洁的,岂不被他玷辱,被人耻笑。”二娘背地里笑了一声,向厨下取了些酒菜道:“不用忙了,快来吃一杯儿去睡了罢。这样小人,容忍他些。”花二闷闷地吃了几杯径自上楼睡了。
二娘又取些酒菜,往后房来与任三吃。将李二之事,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了一遍。道:“如何是好?”三官道:“我若如今出去,倘被他看见到不好了。我不如在此过夜,到明日早早梳洗,坐在外边,只说寻二哥说话,与他同出门去,方可无碍。”二娘道:“这话到甚是有理。只是此番去,你且慢些来。李二毕竟探听,倘有差池,怎生是好?”三官道:“我家有个小厮,名唤文助,认得你家的。我使他常来打听消息便了。”二娘道:“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请他吃几杯酒儿。着文助斟酒,待他识熟了面,然后着他送些小意思与我们。如此假意相厚,方好常常往来。”三官道:“此计必须如此方可。”两人同吃些酒儿,未免做些风月事情,方上楼去。
次早,三官起来,早已梳洗。二娘先把大门开了,三官假意坐在外厢,叫:“二哥在么?”二娘在内假应一声,上楼说与丈夫知道:“任三叔寻你。想他许久不来,莫非李二央他来释非?切不可又去与那强盗来相交了。”花二连忙梳洗下楼,与任三施礼道:“三官为何一向少会?”三官道:“小弟因宗师发牌县考,一向学业荒疏,故此到馆中搬火,久失亲近。今日家中有一小事而回,特来望兄。不知一向纳福么?”花二说:“托庇贤弟,你会见李二么?”任三道:“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花二道:“不必说起这畜生。”将前件云云之事,一一说了一遍。三官假意怒道:“自古说得好,朋友妻,不可嬉。怎生下得这样心肠!既如此,我也不去望他了。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妇,他未免也来轻薄。岂不闻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二哥,既然如此,也不必恼了,兄同小弟到家散闷如何?”
花二同了三官到家里,只见堂上有人说话。把眼一看,恰是一个说亲的媒人。与任三官配的亲,为女家催完亲事,等紧要过门。他母亲道:“又未择日,尚未催妆,须由我家料理停当,方可完姻。怎么女家反这般催促?”花二、任三听了,一齐笑着见礼。少不得整酒款待媒人,花二相陪。三人直饮到红日西斜,别了任三出门。
花二与媒人一路同行。花二便问道:“媒翁先生,为何女家十分上紧?是何主意?”媒人笑而不答。花二道:“莫非是人家穷,催他做亲,好受些财礼使用么?”媒人道:“他家姓张,乃是个三考出身,做了三任官,去年升了王府典膳回来的。家约有数万金,那得会穷!”花二想了想:“奇了,这等毕竟为何?”媒人问道:“兄与任家官人相厚的么?”花二道:“意气相投,情同骨肉。”媒人道:“这等,兄说的话,必定肯听的了。府上在何处?”花二道:“就在前面。”媒人道:“有事相议,必须到府上方可实言。”
两人到了花家,分了宾主。二娘点茶吃了。花二又问起原由,媒人道:“见兄老诚,自然是口谨的,才与兄议。万万不可与外人知之。”花二道:“老丈见教,断不敢言。”媒人道:“任官人定的女子,年纪二十岁,闺中不谨,腹中有了利钱。他父亲往京中去了,是他令堂悄地央人接亲,要我及早催他过门,以免露丑。许我十两银子相谢。我方才见说不来,心中烦闷,想此也必须得花兄暗地赞助。若得早娶,愿将所谢之银均分。”花二心下暗暗想了道:“领教,领教。”媒人道:“千万言语谨密些。”花二道:“不须分付。”媒人道;“尚有未尽之言,奈天色晚了,欲求同行几步,方可悉告。”花二同出门去了。
二娘在门后,初然听了此人说任官人三个字,他便半步不移,细细听了前后说话,暗暗叹息道:“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之不远,信不诬矣。”他又想道:“丈夫倘去相劝,毕婚之后,无甚说话方好。倘三郎识出差池,叫此女如何做人?必然寻死,岂不可惜?若不劝丈夫管他,倘此女父亲回来,看出光景,将女儿断送性命,也未可知。也罢,且待他回来,再作商议。”只因花二娘起了一点好心,他家香火六神后来救他一命。这是后话。
且说花二归家,二娘道:“方才之说,我已尽知。你的意下如何?”花二道:“娘子,这件事不难。我劝三官将计就计,省事些娶了过门。我又有酒吃,又有五两银子,有何难哉!”二娘晓得他耳朵绵软的,道:“丈夫差矣,你若去说得听也好,万一不听,你岂不坏了好朋友的面情!这五两银子,也有用了的日子,况未必有无。我想人生在世,当为人排难分忧。今任三妻子之忧,即任三忧愁一般。当拔刀相助,水火不避,才是丈夫所为。你若听,我到有一计较在此。”花二道:“贤妻有何妙计,何不为我说之?”二娘道:“方才媒人所言,肚儿高将起来,想不过是三四个月的光景。何不赎一服通经散,下了此胎,有何不可?”花二道:“此计虽好,怎生样一个计较赎与他吃?”二娘道:“不难,明日将我抬到他家,扬言我是任家内亲,央告我来说话。他家自然不疑,毕竟他母亲出来接我。我悄悄将此言与他母亲一说,自然妥当。”花二道:“好便好,只是先要破费药金。”二娘道:“痴子,若是妥当,那十两银子都是你的。”花二听了,拍掌大笑:“好计,好计!”
次日早起,打点了药金,径往生药铺中赎了一服下药。又去唤了一乘轿子与二娘坐了,径抬至张典膳家中。奶奶迎进,叙了寒温,吃罢了茶。奶奶问道:“尊姓?”二娘道:“奴是花林妻子,有事相告。敢借内房讲话。”奶奶引了进房坐定。二娘命众女使俱出外边,方附奶奶之耳,如此如此,说了一番。那奶奶面皮红了又红,千恩万谢,感激无地。一面整酒,一面连忙热了好酒,到女儿房里通知了此话,把药服了。
一时间,一阵肚疼,骨碌碌滚将下来,都是血块。后来落下一阵东西在马桶内了。奶奶道:“谢天谢地,多感祖宗有幸,逢着花二娘这个救星。”欢欢喜喜安顿女儿睡了。连忙去房中见了二娘,谢了又谢。将酒就摆在房内,三杯五盏,二娘起身告辞。奶奶再三苦留不住,开箱取了一封银子,一对金钗,一双尺头,一枝金簪,送与二娘道:“些须孝敬,休嫌菲薄。地久天长,报恩有日,幸勿见怪。”二娘千恩万谢,上轿而归。
天色已晚,花二见妻子归家,打发了轿夫,进内忙问事体如何。二娘把日间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将他送的物件,把与丈夫看了。喜得那花二满地滚跳道:“我明日与任三官说知,还要他的酒吃。”二娘道:“你这呆子,这是阴骘阴骘zhì:指阴德。事情,所以去救他。若与三官说知,可不又害了那女子!”花二道:“正是,几乎错了,还是贤妻有些见识。紧紧记在心中,再不说了。”二娘以后与任三官这般情厚,把此事再不漏泄。
话分两头,且说李二自从那日见了任三,又寻不着,又被花二娘骂了一场,心中不忿。一日,走到花家对邻一个周裁缝家门口坐下。那周裁缝道:“李官人,想是来寻花官人么?”李二道:“正是。”周裁缝道:“今早出去了。”李二道:“师父,你曾见任三官这一向到花家里来么?”那周裁缝极口快的,便道:“他是不出门的主顾,怎么到来问我!”李二道:“我前日分明见他进去,多时不见出来。进去寻了一番,又不见影,反受了一肚皮臭气,心内不甘。你若晓得这头路,我断不负你。”那周裁缝是个口尖舌快的人,他道:“我这几时不管人间事。若是十年前生性,早早教他做出来了。”李二道:“周师父,你若肯帮我做事,我当奉酬白金五两。”
周裁缝听见说许了五两银子,就欢喜起来,忙道:“若要如此,必须生个计较。此事一不做二不休,不是取笑的。先与他丈夫说知,一齐捉奸,方免无事。”李二道:“可恨淫妇,必在丈夫面前骂言说我,花二故此久不上门。今虽欲通言,奈无由得计。”裁缝笑道:“花二官是酒徒,扯到店上吃酒。中间三言两语,激起性子了,自然妥当。他若不听你,你却教他问我,我自搬他一场是非,自然信了。”李二道:“你这几日不出去做生活方好。”裁缝道:“只有一个张家,要去完他首尾,看早晚去完了,只坐在这里等着便了。”
李二计议已定。次日怀些酒资,恰好撞着花二,倒身一揖,花二假意还礼,眼看别处。李二道:“哥哥凡事三思。自古道,若听一面说,便见相离别。我有许多为你心腹话,不曾与你说罢了。”花二本待不理他,又听他说有心腹话,只得道:“有何话快说来。”李二见他答话,连忙扯了径上酒楼。将酒筛下一盏,送与花二。花二只得吃了,也回送李二一盏,道:“有话快说。”李二道:“且慢些,说将来,恐你酒也吃不下了。”花二一发疑心,只得又吃了几盏道:“大丈夫说话不明,犹如钝剑伤人。说明了,到吃得酒下。”李二故意欲言不言。花二道:“罢,你既不道,我也不吃了,去罢。”李二道:“说来恐你不信,反嗔怪我。”花二道:“我不怪你。”李二道:“也罢,说与你知,怪不怪凭你便是。那任三这几时你曾会他么?”花二道:“数日前,他馆中回来,我到他家中去吃酒了。”李二默然。又说道:“哥,前日二娘骂我这日,任三到你家来,二娘把他藏在家里,被我知道了,要进去搜捉,因此二娘急了,反骂将起来的。你是个大丈夫,不可被妇人骗了。”
花二想了又想,我妻子好端正的,怎歪说起这般说话。便道:“你既知道那日任三是在我家,就该直说了是。今据你此言,他两人一定有奸了。此事不是当耍的,可直直说来我听。”李二道:“说也没干。我亲眼见他进去多时不见出来,所以要搜。若是假说,天诛地灭。你若再不信,去问你邻居周裁缝便是。”花二说道:“是了,想此事有些因。多时不见他,想是那日躲在我家过夜被你知觉,恐你埋伏捉住,不好出门,反说来寻我,同我出门,方可掩人耳目。是了,是了,再不必言,必定事真矣。除非杀了二人,方消我恨。”李二道:“且噤声。事倘不成,反为不美。还须定计,方可除之。”花二忙问何计较,李二道:“计较到有,只是不可又被二娘识破,反受其害。”花二道:“不妨不妨,我自然谨密就是了。”李二道:“事不宜迟,你可今晚扬言,假说明早要往府城去有何事理,一面去约任三到家里说话。不可等他来,你可先出门去。他若来见你不在家,自然又留过夜。待我与你探听,如在时,报你知道,你却回家下手便了。”花二道:“是了。且别着,明日再会。”李二道:“万不可泄漏。”花二说:“不须分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