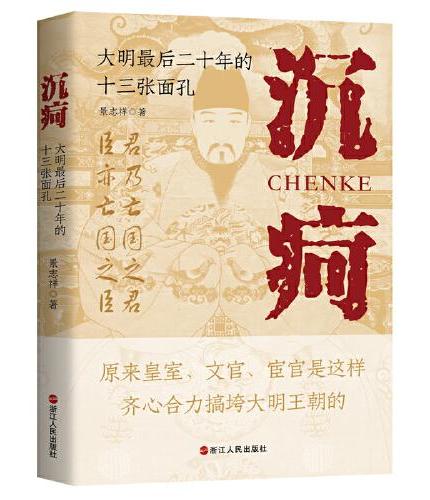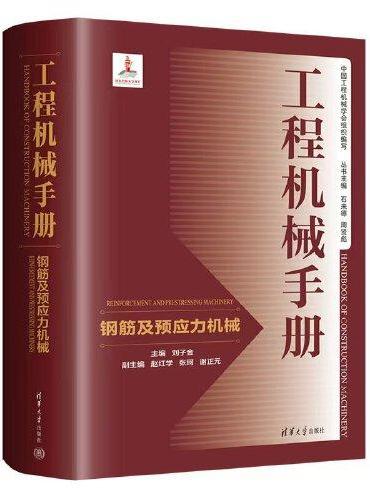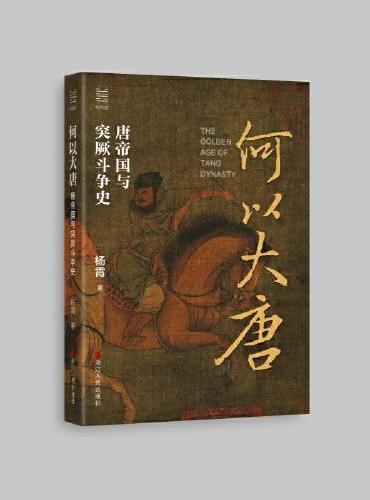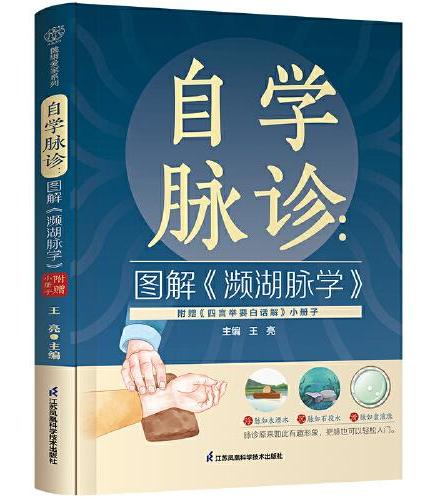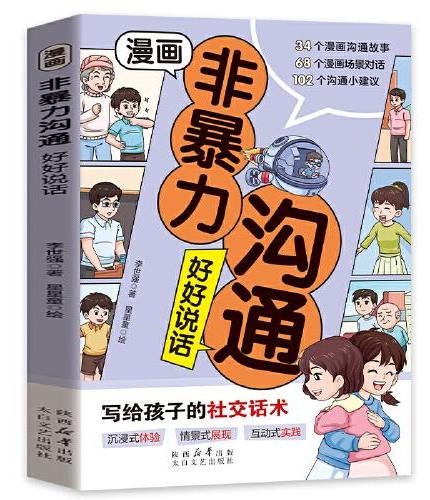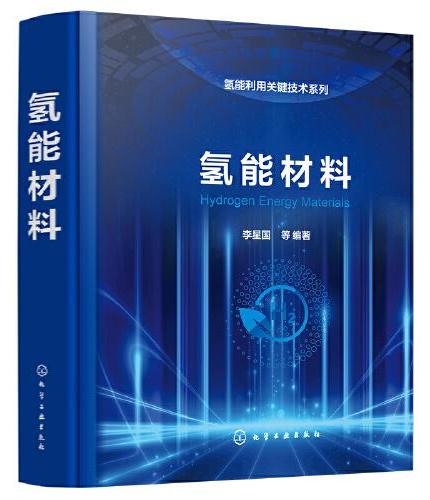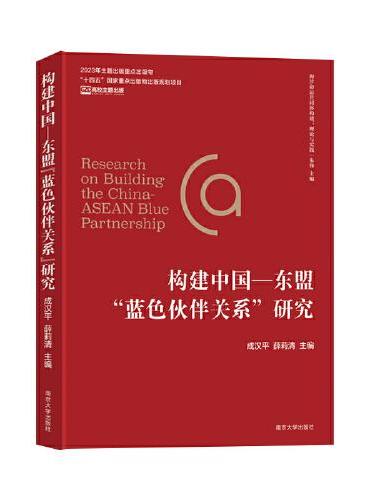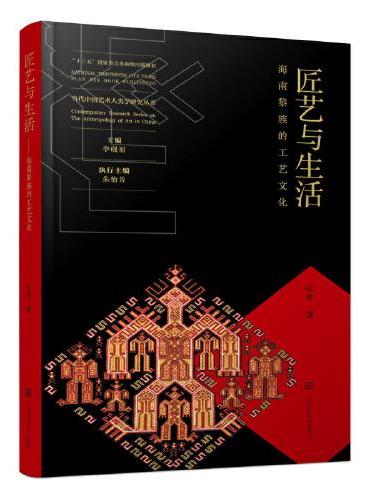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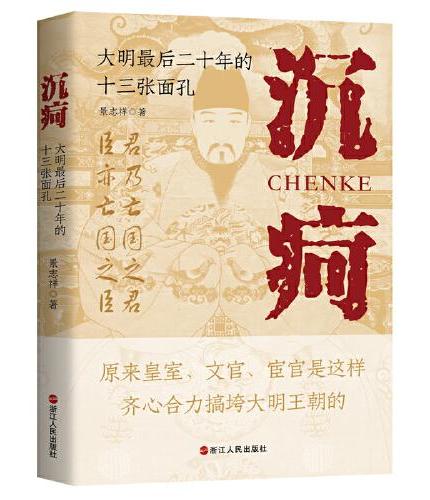
《
沉疴:大明最后二十年的十三张面孔
》
售價:NT$
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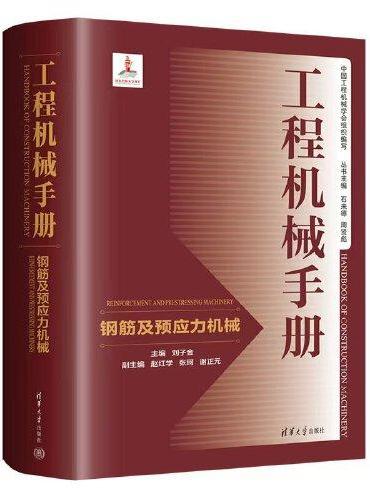
《
工程机械手册——钢筋及预应力机械
》
售價:NT$
16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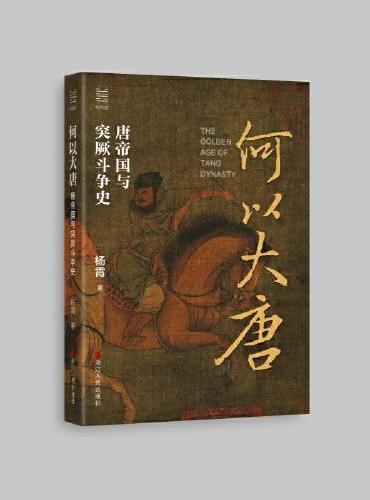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以大唐:唐帝国与突厥斗争史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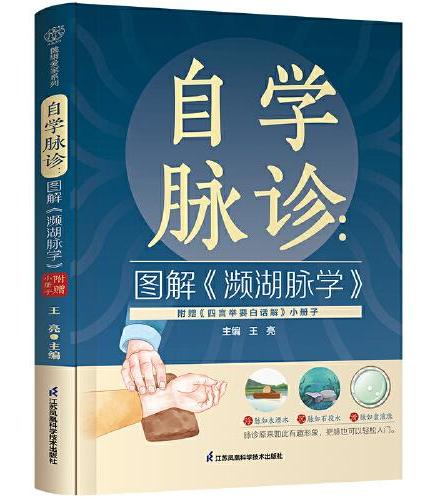
《
自学脉诊:图解《濒湖脉学》
》
售價:NT$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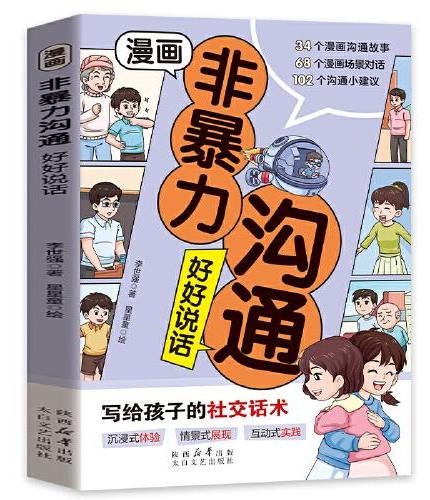
《
漫画非暴力沟通 好好说话写给孩子的社交话术让你的学习和生活会更加快乐正面管教的方式方法 教会父母如何正确教育叛逆期孩子 用引导性语言教育青少年男孩女孩 帮助孩子拥有健康心理的沟通方法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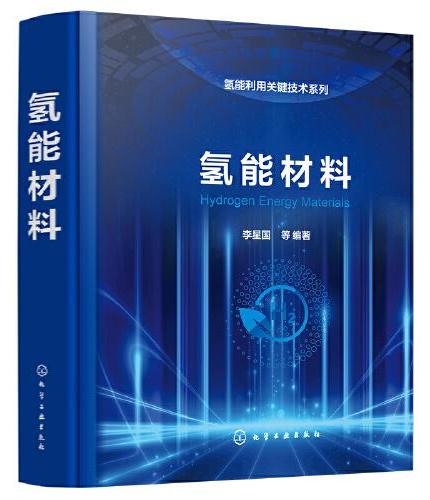
《
氢能利用关键技术系列--氢能材料
》
售價:NT$
18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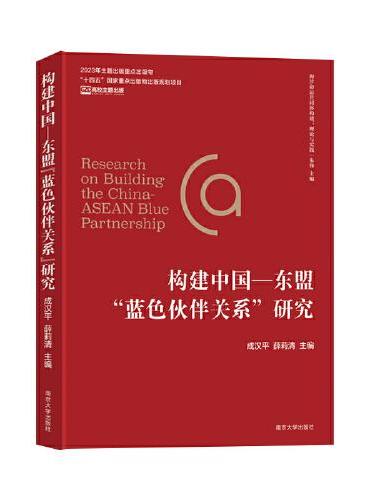
《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理论与实践)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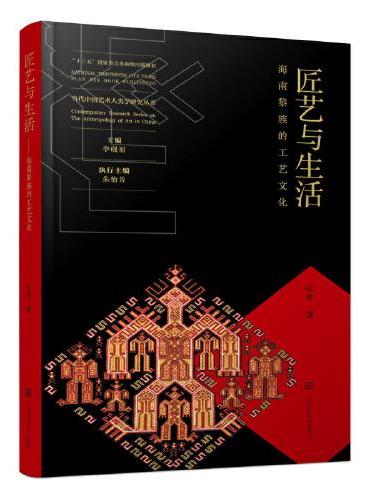
《
匠艺与生活:海南黎族的工艺文化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网络点击逾千万,积分过亿,晋江金榜重推作品
晋江大神 楚寒衣青 颠覆传统古言模式的诚意之作
智计百出 环环相扣 悬念丛生 高潮迭起
年度最受读者好评、公认最有新意的高智商宅斗权谋
她处心积虑,步步为营,能否让一切偏离原本的轨道,揭开重重迷雾,触摸命运最初、最动人的美好?
我费尽一生思量,只为守护所爱之人一世无忧,哪怕颠覆天下
多少年,为守护所爱之人,她几乎用尽生命里全部的温柔,谋一场无关风月的局
因为有想要保护的人,我才变得强大,这执念左右着我、塑造着我,深至骨髓
最睿智的女主袖手乾坤,最可爱的男主暖人心扉,你我合卺结发,同生共死
你见过最坏的我,你能接受最坏的我,我这一生惊才绝艳,只为你盛开
◆年度最受读者好评、公认最有新意的高智商宅斗权谋
◆晋江大神 楚寒衣青 颠覆传统古言模式的诚意之作,古言架空史上首部以“守护”为主题的重生复仇文
◆原名《见善》,网络点击逾千万,积分过亿,晋江金榜重推作品
智计百出×环环相扣×悬念丛生×高潮迭起
一个胜利者前世笑傲到最后,却遗憾重重。
一朝重生,她处心积虑,步步为营,只想让一切偏离原本的轨道,揭开重重迷雾,触摸命运
|
| 內容簡介: |
人这一生,很难知道自己明天要去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正如人生之幸福与人生之输赢,并不存在绝对的联系。
少时为金尊玉贵的国公府嫡女,长大了是深受敬重的名门长媳,徐善然以为自己的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到老,然而一朝风云,娘家获罪,曾柔情似水的丈夫竟想将她药死于病榻!
摧心肝折断肠,她终是赢了。
但快乐好像早从她身旁悄然溜走。
她想家。
想父亲,想母亲,想那些真正爱她、疼她而已魂入幽冥不能再见的亲人。
若有一日,有幸再见,即便那是注定的劫,她也心甘情愿承受。
一个胜利者,前世笑傲到最后,却遗憾重重。
一朝重生,她处心积虑,步步为营,只想让一切偏离原本的轨道,揭开重重迷雾,触摸命运最初、最动人的美好。
为此,多少年,她几乎用尽生命里全部的温柔,谋一场无关风月的局。
她说:“人类这种生命,是会因为有想要保护的人而变得强大的啊!”
|
| 關於作者: |
楚寒衣青
晋江超级作者,多部作品收益位列网站金榜。文笔细腻,故事构架大气磅礴,情节极尽波澜,擅长以各种计谋延伸剧情,环环相扣,深受读者喜爱。
笔名至今已延伸出许多版本,足以逗人一笑。平生无一值得聊叙,唯独心态尚可,烦恼总不过一个晚上,就像夜晚过后太阳总要活力十足地跑出来。
即将上市:《纯白皇冠》
微博:@楚寒衣青青
|
| 目錄:
|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前生梦
第二章 山野间
第三章 公府内
第四章 内务忙
第五章 少小猜
第六章 忠奸分
第七章 春日浓
第八章 宁王至
第九章 信步走
第十章 乐生悲
第十一章 费思量
第十二章 忆故人
第十三章 诞辰会
第十四章 恶鬼道
中册:
第十五章 心尖意
第十六章 祸水引
第十七章 举国宴
第十八章 困丝茧
第十九章 破声鸣
第二十章 百戏闹
第二十一章 骤雨疾
第二十二章 肘腋变
第二十三章 心腹火
第二十四章 魔念生
第二十五章 白幡动
第二十六章 见家长
第二十七章 父子仇
第二十八章 狸猫换
下册:
第二十九章 好事成
第三十章 嫁衣烈
第三十一章 新婚忙
第三十二章 庸人扰
第三十三章 余波荡
第三十四章 信一字
第三十五章 西北望
第三十六章 立根基
第三十七章 云飞扬
第三十八章 宫闱深
第三十九章 携手共
番外一 一生一代一双人
番外二 盛世江山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前生梦
人要什么时候死,只有自己最清楚。
徐善然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一根手指都动弹不了,意识一时模糊,一时清醒。眼前的景象一会儿是小时候的闺阁,蜻蜓腿卷草纹香几上的白玉双耳三足香炉中冒着丹桂的清甜,穿青枝缠花纹袄的妈妈站在床头斥骂小小的还一团孩子气的丫头;一会儿又是自己寝室中雍容华贵又暮气沉沉的摆设,苦涩的须弥香直冲天灵,玉琵、玉琶两个丫头的面容隐在模糊的帘栊之后,眼底唇角全是愁苦。
时间如同水波一般带着她晃悠悠地漂荡着。
她躺着,安静地等着,不断轰鸣的耳朵里渐渐能听见声音了,像遮得严严实实的布帛忽然抽了线,终于有空隙让声音能够挤进来。那是她乳母的声音,柔美的女声因为蓦地拔高而显得有些尖厉,高高低低、远远近近地传进徐善然的耳朵里。
“我不过离了一瞬,你们竟这般不经心,显见是打量着四太太性子好不计较,却不想想耽搁了姑娘岂是你们吃罪得起的!”
“一屋子的人还有没有个喘气的?有没有不干吃饭会说话的?姑娘到底怎么了?”
蒙了层五色纱的窗格在阳光下转着细微的光芒,院中有人影晃过。
徐善然慢慢看清楚了屋内的陈设,像是收拢在记忆里的东西一一跳了出来——紫檀木座的山水画屏,斜插着冬梅的龙泉大瓶,挂着老叟访南山图并一张琴的雪似墙壁,依次摆放着案头清玩的大书桌……
徐善然又费力地将自己的目光转到了屋内的人身上。一个梳圆髻的妈妈站在床边冲她笑着说些什么,唇角虽然高高扬起,脸上却又有挥之不去的惊慌;四个丫头都待在角落,低垂着脑袋不敢出声,整个身子都像僵住了一样没有动弹。
李妈妈,竹实,棠心,绿鹦,红鹉。
她们在她出阁之前陆陆续续都走了,有做错了事被撵的,也有年纪大了、老了被家人接走婚嫁供养的。现在想想,她们没有跟她到林府,真是一件值得多多烧香的好事情。
她怎么会梦到小时候呢,是病糊涂了吧?徐善然这样想。然后又想:是菩萨的慈悲吗?让她在下地府之前再看看生自己养自己的地方?
可是再熟悉的景致,没有了熟悉的人,也不过徒添伤怀,不如不见。
她轻轻地闭一下眼,再张开的时候,那鲜妍明媚的闺阁就如同薄纱一样被轻轻抽走,再映入眼底的,依旧是再熟悉不过的双螭团寿字罗汉床和窗户外那株连叶片都被她数了个遍的梧桐树。
鲜亮厚重的锦被像一层沉重的铠甲压在她身上,被下的肢体没有一处不泛着酸和疼,鼻端嗅着的须弥香忽然浓重起来,嗅着嗅着,思绪便仿佛被牵引着,将她出嫁后的人生回味了个遍。惊慌的、苦涩的、冰冷的……也曾经有过一些婉约甜蜜的日子,但最终都和着那些痛苦,加倍地变成滚烫的怒火和憎恨,搁在胸腔之内,片刻不熄,烧心烧肺地燥热。
这一日的天气尚算不错,榻边的窗格被推开,晨风刚好将几朵梧桐花吹进窗户,落到被面之上。
徐善然盯着窗外的梧桐树看,高高大大的树木几乎遮蔽了她眼前的天空,偶有的几隙阳光,也如同被施舍般地落到地面。
她记得自己刚来的时候,极为看不惯这棵高大的乔木。习惯了北地开阔的她在刚刚嫁到江南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不习惯江南的天气,不习惯江南的饮食,不习惯江南的服饰,也不习惯从姑娘到媳妇的转变。
京师一等国公府的嫡女,便是宫里头的那些娘娘也未必有的出身,嫁到谁的家里都不算高攀,何况虽为世家,但家中大人却只领了一个三品职衔的延平林?所有人都说她低嫁了,唯独她自己觉得还好。
纵然门第稍低一些,难得的是传承日久、规矩俨然,族中不仅有四十无子方可纳妾的古训,更兼夫婿十分能干,她嫁过去那一年,也正好是夫君金殿传胪的那一年。
本身有家世、有嫁妆,夫婿能干,夫家也规矩守礼,更没有妾室、庶子闹心,怎么看她都应该如同在国公府一般,继续着自己金尊玉贵的生活。
大抵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日子吧?
她和林世宣的感情并不糟糕,最浓情蜜意的时候,她也在床笫间咬着对方的耳朵撒娇卖痴地说,等自己成了这个家的老封君,便要将所有挡着光线的树木都给砍掉,当先的自然是那棵种在主院、将小半个院子都密密遮盖的、据说已有三百来年的梧桐树。
不过一棵树而已。林世宣揉着她,唇角眼底永远是那种耐心又细致的微笑。他很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又是被翻红浪,一觉到天明。
盯着窗外久了,眼前又是一片花白。徐善然倦怠地合起眼睛,静静躺在榻上。没过片刻,就感觉有人到了左近,细碎的窸窣声随之在耳边响起,是玉琵和玉琶细声的对话:
“老夫人呢?”
“还在睡着。”
两句话落,房间又恢复了安静。
徐善然感觉到有人为她掖了掖被角,又有各种细碎的声音,间或还含着某些古怪的响声,像是气死风灯上破了个口子,又恰好有风吹过……
她睁了睁眼,眼皮却仿佛有千斤的重量,只裂开了一条缝隙,刚够她看见窗前的那片深绿,就再次合上,带她重新陷入黑暗。
耳中的人声倒还算清楚。
玉琵稳重的声音里多了一丝急切:“我说你这个小蹄子,你好端端地抹什么眼睛?是谁给你气受了,你好在老夫人面前做这副模样!”
跟着是玉琶还带着哽咽的嗓音:“多少年姐妹了你这样说我?我只为老夫人……”
“为了老夫人,便更不该这副模样!”
“我只是忍不住……”
话到了这里一转,又有第三个声音插了进来:“老爷过来给老夫人请安了。”
房间内静了片刻,跟着玉琵的声音响起来:“老夫人还在休息,请老爷回吧。”
闭着眼睛的徐善然费力地牵动了一下唇角,嘴角似扭出了一个弧度,又平复了下去。
年轻的时候,说自己成了老封君就要将院子里挡阳光的大树全部砍去,但等她真当了老封君,她看着院中的这棵大树,却越看越觉得可爱。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如同眼前的这棵大树一样,将自己的根须深深扎在了林府之中,掌控着遮蔽着林府的一切人事。
院中的丫头到底没有挡住一心尽孝的儿子。徐善然听见对方进来,跪在床头抹泪自责,句句不离愿意折寿换她安康的表白,唬得一屋子的下人劝着架着,吵吵嚷嚷好一阵后,徐善然的耳边才恢复清净。
这时候又是玉琶呸了一声,快言快语地说:“我看老爷要是真有一分孝心,就不该每次来都要哭天抢地指天立誓一番。外头不知道的人看了,还以为我们家的老夫人已经过身了呢!”
玉琵怒道:“还不闭嘴!合着事情你做就行,别人做就不行?”
“那哪一样……”玉琶回了一声,声音到底歇下去,房间内便再没有了交谈声。
是不一样的。徐善然心想。
她身边的这几个丫头,被她收着身契,打小调教着,一日日放在眼前看着,从垂髫稚童看到如花似玉,哪一个不比那个对她又畏又恨的庶子贴心贴肺?她们流的眼泪,她相信至少有一半是为了她;而那个庶子呢?她也相信是真情实意,真情实意地喜极而泣。
多高兴啊,压在上头的嫡母要死了,磋磨亲娘、药死亲娘的嫡母要死了,掌控着他成长乃至婚姻的嫡母要死了,一手推他上官位又抓住他没法放下手中权柄的心理而日日受着尊崇供奉的嫡母终于要死了!
熬着,熬着,总算熬到了这老妖婆先走一步,世上哪还有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事情呢?
“姑娘?姑娘?姑娘回答妈妈一声好不好?”
“姑娘是不是在跟妈妈做游戏?姑娘该起身了,姑娘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且说一声可好?”
“姑娘,太太马上就……”
过去的声音在回忆的间隙里又遥遥地传来。徐善然努力想要辨认清楚,却有另一种摸不清的力量将她禁锢在回忆里。
大概真没有多少时间了,回忆绕着回忆,搅得她都有些不安生。
在她的记忆里,她和林世宣甚少争吵,便有几句拌嘴,也没有将气过了夜的。
翩翩贵公子,皎皎世无双。那些说她低嫁了的女人后来听闻林世宣的风仪后,不知有多羡慕她,又将手中的帕子揉碎了多少。
林世宣只有她一个妻子,至于那些通房歌妓,不是没名没分就是不在眼前杵着,她也犯不着生那个闲气,她真算是一颗心都扑在了对方的身上。
所以最后……
最后,在知道林世宣一碗一碗的药想要药死她的时候,她才真正觉得天塌地陷了一般。
外祖绝嗣,满门凋零。
娘家获罪新帝,男丁也多是流放千里。
但国公府的女眷还留在京中,嫁出去的姑娘也并不跟着获罪。
那一段时间里,徐善然将出生二十多年里都没有尝过的苦头尝了个遍——忧虑亲人,忧虑自己,仅仅几天,就瘦得尖了下颌。
是林世宣执着她的手说世有三不去,她永远是他的原配嫡妻。
其实那个时候,不管林世宣是要将她送进家庙还是送她一纸休书,她哪怕苦恨对方无情无义,也只能无言以对。婚姻结二姓之好,出嫁女因娘家而煊耀,难免也因娘家而飘零。她能够理解林世宣,毕竟他刚刚从京师外放,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又要扶起延平林,不可能得罪新帝。
家庙或者休书,她都接受。
但林世宣在她面前低诉情语,一转眼却将害命的药并食物递到她手中。
当时她已经喝了有月余,渐渐地便在床上不大起得来。林世宣每每来看她的时候总要温言软语抚慰一番,她也拼命想要提起精神,她还有亲人,还有孩子,还有丈夫……
直到她当时的贴身大丫头跪在脚踏前,单薄的身子委顿在地,战栗哭泣到连话都说不出来。
她说了很多,徐善然一个字都不相信——林世宣为什么要杀了她?她没有了娘家撑腰,不管是进家庙还是被休,她都没有办法反抗。而他们夫妻数载,朝夕相处、情投意合,膝下还有一个刚满五岁的佳儿,便是一只猫、一条狗,养了那么多年,丢了伤了也要心疼一阵,何况是日日同床共枕的妻子?
林世宣胸膛里的心是黑的、冷的,还是空空如也的,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徐善然又陷入那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飘摇之中了。
周围的景致都模糊成了深深浅浅的色块,她被笼罩在其中,渐渐地没有了身体上的知觉。她多多少少能感觉到什么人来到了自己身旁,一声一声地在说着些什么,可是不管她怎么认真去听,都不能辨别清楚,只得继续想林世宣的事情。
这么久的时间,那么多的事情——结缡、育儿、中毒、丧子、同床异梦,再到反目成仇。她送走了公公、熬死了婆婆,再装着、骗着、伙同着外人斗倒了那个男人。
至亲至疏是夫妻。
看着那个男人从踌躇满志到愕然倒下,看着那个男人从仪容绝世到瘦骨伶仃,她最后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畅快。
也许是装得太久,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骗到耗尽了感情。
也许是学得太多,学他冷心冷情、智计百出,学到熬干了心血。
到最后,爱也淡了,恨也淡了,林世宣乃至阴郁沉闷的林府对她而言,都只如一根鱼骨卡在喉咙,不吐不快。
林世宣倒下的那一天,对她而言应该是畅快的。可是畅快之后又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
当身边再没有可以分享的人的时候,再多的富贵、才华、权势都只如清水浮萍,池上柳絮,无根无源。
徐善然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一天。
那一天贴身的丫头跪在床前,瑟瑟发抖地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告诉她,一声一声说林世宣如何在药里、粥里加相克之物,要让她毫无痕迹地死去。
她不想信,不能信,不敢信!
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心腹,如果她还有娘家,大可大刀阔斧地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但她已经没有娘家可以依靠了。仅剩的、仅余的丈夫,到底是爱着她,还是想要杀了她?
徐善然最后在林世宣来看自己的时候提了一个要求——她希望将自己的娘亲接到别都来。娘家获罪,正子嫡孙的男丁都判了流放,唯有她这一房的庶兄,因有恩于新帝,得以被特赦留京,照顾家眷。在她的印象中,这只是一个老实的、和她没有多少接触的庶兄。可是嫡母、生母俱在,又是庶子当家,哪怕这个庶子在过去的那些年里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恭敬,她也能够想到自己娘亲的日子,只怕庶兄过去有多恭敬地敬着嫡母,未来就有多不恭敬地待着嫡母。
把母亲接来的念头在她接到消息的时候就有了,可是直到此刻,她才宣之于口。
然后,林世宣回答了。他面不改色、毫不迟疑,就抱着她,回答她一个朗朗的“好”字,太像最初时候他在床笫间答应她砍了那棵梧桐树的时候了。她一抬眼睛,依旧能看到对方眼里依稀闪烁着的温柔,那么真挚。徐善然几乎沉溺在这样的温柔之中。
然后在无边的和暖中,她慢慢地醒过神来,从心底感觉到一点寒凉,进而这点寒凉便顺着血液流淌周身,叫她手足冰冷。她前几日才从娘家的义子哥哥处得到消息,流配边关的徐家人在解押的路上遭遇了强人,连同押解的官差在内,没留一个活口。她的娘亲在得到这个消息后就投了缳。新帝震怒,下旨严查,又将徐家仅剩的庶子连连拔擢,以示加恩。在她的那个哥哥找过来的时间里,这件大案子已经成了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林世宣不可能不知道。林世宣在骗她。他怎么能这样理所当然、毫不造作地骗她?
这个时候,距离徐家人事发已经过了十来日,距离她母亲投缳也过了旬日。
她的义子哥哥在徐家出事之后擅离职守,一路从边关潜逃进来,再找到她的时候,都能将事情打听得清清楚楚,而丈夫是詹事府少詹事、身为正四品命妇的她连自己父母死绝了都不知道。
没有人能明白那一刻她心中的恐怖。
她看见的、听见的,有什么是真的?她是不是庙里那尊泥塑的菩萨,一年到头,只要任人供上三炷清香、四季蔬果,就能闭起眼睛,遮住耳朵,露出端庄微笑?林世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的丈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徐善然后来想了很久,看了很久,终于慢慢地明白过来:他的心确实是黑的、冷的、空空如也的,哪怕还有一点儿的温暖,也从来不曾停留在她的身上。对林世宣而言,女人真正如衣服,一件旧了总有新的,一件坏了更有好的。在他的心目中,排行第一的始终是他的滔天权势、满腔抱负,排行第二的也还有延平林氏,而余者便皆如尘埃草芥,不值一提。
林世宣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徐善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否认这一点。作为只差一步便要进内阁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宰辅的人,他有资格得到这个称赞,可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走到这一步,有谁是傻瓜?只要有一道缝隙,他们哪一个都能抓住机会将其撬成天窗般的裂罅。
徐善然心里有畅快,也有得意,虽然不长久,但到底是有的。
她看着愕然倒下去一下就中了风的男人,一瞬间想了很多。
在他因为她娘家败落时既要清誉又要圣眷而想要药死她,又因为被公主看上赶忙收手治好她的时候,在他在书房里因明知她在外头看着而对心腹潸然泪下说出她父母的事情,说“性命垂垂,不敢说且不敢不说”的时候,在他们一起看着稚儿小小的身躯失去最后一点温度,她连着吐了好几口血,他照旧揉着她、沉着声音安慰她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自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
徐善然何尝想得到?从头到尾,她在外人眼中都是一如既往地金尊玉贵——娘家没有出事的时候,有着帝国数得上的家世;等娘家出事了,夫家又权势赫赫如日中天。
恁地好命。外头的所有人都这样说她。
可她丧父、丧母、丧子,到最后,也只有一个婢妾生的庶子,在她的床头明着哭、暗着笑,日夜盼她早点死。
徐善然并不如何恚怒。这个庶子的路她早就安排好了,他是哭是笑、是唱是念都无甚关系。人这一辈子,眼睛瞎上一次就够了。
至于她自己,她还有什么没有经历过、没有享受过?也差不多了,该下去了。下去看看,看看父母,看看稚儿,他们会嫌她来得太慢吗?会认不得早已失了原来面目的她吗?
模糊成一团的眼前忽地一亮,像是有一只凭空出现的手拨开了迷雾,徐善然看见一个妇人站在自己的床前。
那妇人微胖,圆脸庞,头插白玉观音满池娇分心并二三草虫簪子,双耳垂着一对赤金镶宝玉兰坠子,外罩一件绲银边藕荷色暗花纱绣百鸟百花披风,底下则穿一件茄花色对襟袄。
她眉头蹙着,白皙圆润的脸庞写满了担忧,双手轻轻拍着徐善然的肩膀、胳膊,点了胭脂的嘴唇一张一合,徐善然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但是她能够辨认出对方的口型——她在叫善姐儿,她在叫着自己的名字。
娘亲,娘亲,娘亲……像一壶煮沸了的水滚起来,徐善然在看见人的那一刻,脑海里来来回回翻腾的都是这个称呼,眼底心间都被面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占据。平静了很久的心湖突然被搅乱,酸涩从心尖处一路蔓延到眼眶,但干涩的眼眶早已落不下一滴泪来。
她想抬抬手,就抬抬手,擦去母亲眉间的愁绪和惶恐;她还想张张嘴,就张张嘴,说上一句迟了很久的话,告诉母亲别怕——别怕,爹爹死了还有我。我就来了,娘亲等等我,别走,别丢下我一个人。
可她的身体被看不见的锁链捆得严严实实的,又被牵着继续飘荡。走着走着,面前母亲担忧的面孔忽然被林世宣微笑的脸庞所取代——瘦到突出了颧骨的脸颊上已经隐约爬出皱纹,再没有了往昔光华灼灼、风采奕奕,只剩一对眼睛依旧锐利。
那双锐利的眼睛看着她,好像能洞穿她的衣服和血肉,一直看进她的心底。
但她坐在床边的海棠绣墩上,微笑着和林世宣对视着,她早就不怕这个男人了。
那是在林世宣弥留之际。
“我快要死了。”躺在床上的男人感慨地说,声音溢出口腔,像生了锈的铜器互相碰撞,沙哑喑沉。
这是又一个晴朗的日子。整座府邸都因为主人病情的恶化而忧心忡忡,少了花匠的打理,庭院中的那株梧桐树都将枝丫伸进了卍字雕花窗格。
林世宣盯着枝丫上零星的绿色,忽然问徐善然:“你不是说想要将院子里的梧桐树都砍掉吗?怎么这么久了,它还长着?”
“父亲母亲都喜欢它们,我将它们留下来,也是对父亲母亲的孝道。”徐善然坐在绣墩上,长长的裙子掩着她的绣鞋,她坐直肩背,侧着头,平和地对林世宣说着话。
林世宣笑起来,笑到一半又咳嗽,好一会儿才缓和过来,又是好笑,又是叹息:“徐善然,我一直有一件事不明白。”
“你比我预料的要有智慧得多。说真的,我没有想到最后打败我的居然是你,而不是魏水秀,也不是冯庆元。”他缓缓地说。
“但正因为这样,你更应该明白,你根本没有必要斗倒我。你明明知道的……我做成了阁老,难道还能休妻?难道还要杀妻?我做不成阁老,他们难道还会念着你的好,时时刻刻帮助你?这些年我躺在床上一直在想,徐善然,你既然聪明地猜到了我当日的手笔,又将那些东西整理出来传了出去,怎么会看不透这一点?而如果你没有看透这一点,你又怎么能将那些东西整理出来递给那两个奸逆?
“孀居之妇与阁老之妻,何其远也!
“徐善然,你大可等我当上了阁老,你大可等你的庶子长大成人能支撑门庭,你大可先当一言说众人应、一言笑众人和的阁老夫人,再充分享我死后的哀荣……可是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倒了,你除了出上一口气之外,又能得到什么?你究竟在想什么东西?”
徐善然的目光轻轻在林世宣脸上一触,便移开了,并不因为回避,只是毫无意义。
她究竟在想什么?
她究竟得到了什么?
为了将这个男人拉下来,她学着对方的一切,学了很多很多。学对方的所思所想,行事手段,她一点一点地朝对方靠去,变得和他一模一样,变得和他贴心贴肺……可她不是林世宣,她再可怜,亦可怜不到林世宣的模样。
她慢慢地说:“你还记得你曾经在中秋宴上对我说过的话吗?那一年是启光七年,对,就是你倒下的前一年。当日户部侍郎宋廷来找你,我知道的,这个人平日为官贪鄙、苛刻下属,又不敬上司,哪怕有个好家世,也是做不长久官的。
“他平常和你并无多少交情,但在他被言官风闻弹劾,找尽了旁人再来找你的时候,你答应了。为什么呢?我问你,你跟我说:‘随手之事,为何不为?’又笑道:‘将军今日为卒背吸脓疮,卒明日便为将军沙场百战去,马革裹尸还’……
“这些事情,我也是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那么些年的温存爱意,那么些年的体贴柔情,唯有那一天晚上,你真正对我说了实话。你对我的那些,亦不过是随手之事、随手为之。我为你主持中馈、打理家事、抚育孩子,这还远远不够。等有需要了,你还要我用命来还你这份随手为之。
“若你真的爱我、重我、敬我,忧我之忧,苦我之苦,我便舍了这条命给你又怎么样?
“可并不是那样。林世宣,你从不爱我,更遑论重我敬我、忧我忧、苦我苦。
“林世宣,孤狼丧妻尚要哀嚎长夜、徘徊不肯去;羊羔乌鸦且有跪乳之恩、反哺之义。你呢?对于你而言,伦理、道德、良心、血缘、仇恨、义理,有什么比得上你的雄心壮志、宏图霸业?或者说,有什么比得上你沟壑难填的欲望?”
“哈哈,哈哈!”林世宣纵声长笑,他笑完恨声说:“就这些?徐善然,我说你聪明,可你愚不可及!你指责我无情无义、重利重权,可你最后对我所做与我前日对你所做又有何区别?你既和我一般,又来指责于我,是何道理?就算成王败寇,你打倒了我出尽胸口恶气恨念,我也只当你妇人之见……可你并非如此!并非!我输了,我败了,我躺在病榻不能起来,你也并不志得意满、喜上眉梢,既然这样,你又为何要断你我青云之路?你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有的,有的。
在家园被毁、在父死母丧的最后关头,她一直依赖的、一直倾心相爱的丈夫颠倒了她的整个天地与信仰。多痛苦啊!就好像血肉灵魂都被扭曲了似的疼痛,疼得恨不得下一刻就能够死去。
可她没有死。她将自己的骨头一根一根敲碎再拼好,将自己的血和肉撕下又再粘回去,将自己身体里、灵魂里对一个名叫“林世宣”的男人的所有依恋全剜去。
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荣华富贵、滔天权势能引她动容?
她并未喜上眉梢,因为对于林世宣的所有刻骨的恨连同刻骨的爱,早早就离她远去了。
她依旧痛苦,因为这个世上总有一些她无法忘怀、无法割舍,她的那些亲人,只是那些亲人,她已经逝去的亲人,她怎么也忘不了他们,可是她已经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很多年的时间,她越来越了解林世宣,可林世宣却不再了解她;她越来越像林世宣,可又从来不是林世宣。她越了解这个男人,就越学尽对方的冷漠残酷;她越了解这个男人,就越厌恶对方的冷漠残酷。所以最后,红袍喜嫁、夫妻燕好,琴瑟和谐、稚童绕膝,兜兜转转走到尽头,她对于林世宣,只得冷漠与厌恶二词。
最后的最后,她没有回答,只看着床上怒目圆瞪的林世宣。
回光返照的男人用尽全身力气,嘶声喊道:“我幼承庭训,秉烛夜读,及至学富五车,金榜高中,我步步为营,算尽机关,我只差一步,就可当首辅,掌天下权柄!我不甘!我不甘!!我不甘……”
屋外盛放的光芒漏了一小块进窗户,在地上勾勒出一片明晃晃的光焰后又跃上枝头,在叶梢点出一点金芒。
凉风徐徐吹动她的裙摆和帐幔。
喊了许久的男人忽然面露浑噩,半直的身躯跌回床榻,声音一下子变得含混。
徐善然听了很久,才听清楚对方嘟囔着的是圣人的言语:“……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恶也……”
她伸手微拂,拂去裙面尘埃。
徐善然又回到了自己的闺阁之中。
这一次,仿佛因为回忆已经告一段落,她在自己的闺阁里待了很久。看着妈妈、丫头进进出出,看着父亲、母亲、婶婶、伯伯进进出出,连祖母和祖父都见了一面。
她有心想要说些什么,动弹一下,可是她和他们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她只能看着听着,却没法做出任何事情来。
一连许多天的时间,都是如此。
最初激动的情绪已经平复下去,她有些灰心,还有说不出的茫然。临到头了,能够回来看一眼,固然了结心中的愿望,可是所谓梦境,不就是实现人心中所思所想?让她再见到父母亲人,却又不叫她碰触他们,叙述别情,这又是什么意思?再说这梦境也实在有些长了。
徐善然有时醒有时睡,但周围的时间竟似过得缓慢无比,并不像往常的那些梦境似的一会儿一个样。往往她睡下去的时候,李妈妈并几个丫头在做针线,等她再睁开眼睛,那绣布上的花朵也不过填了半色。她还常常看见自己的娘亲,娘亲经常陪在她的身旁,柔声细语地说着话,又有妈妈引着一个一个大夫和提着药箱的童子走进来。
那都是一些面善的人。
几个太医院的御医,几个京师中有名的大夫,他们一个个来到她的床前,开了许多方子,又留下了些诸如“多引着病人说话”、“多带着病人活动”、“不要刺激病人”等等言语,然后一碗碗的药汤就如流水一般递到她的眼前。
徐善然知道自己得了病,她甚至还知道自己病的症状是怎么样的,差不离也就是呆呆的木木的,口不能言,手足不动,连吃饭如厕都不懂……是癔症吧?徐善然想。她知道自己小时候得过一次癔症,但并没有关于生病的任何记忆,只在后来的日子里,从娘亲身旁的桂妈妈口中听过寥寥笑言,说是娘亲当时为了她什么都顾不上,她看了自家的太太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见太太会拍桌子大声骂人;又说娘亲在那段时间真个是求神拜佛,这边刚请了一尊救苦救难菩萨,那边赶紧再迎一位玉清元始天尊……
那时候她还小小的,也就七八岁的模样。她听见桂妈妈说话的时候,看见娘亲微笑着看她,也就跟着笑起来,她那时候是有多傻啊!
孩子之于母亲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在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才终于明白。
那时候她的娘家还屹立不倒,她和林世宣也一直琴瑟和谐,尽可说世上事全无不足了,可在她怀了孩子并费尽力气将其生出来之后,那种血肉相连、心神相继的感觉,就好似整个世界都和之前有些不相似了。
所以在她孩子走的那一天,她整颗心都要被掏空了。
所以当看见她不能说话、不会动弹地躺在床上,喝一口药汁都要人慢慢撬开牙关喂下去,娘亲心中到底得有多难受呢?
可是母亲在她生病的第三天后就不假他人之手,将她抱到上房细细照料了——母亲总觉得那些妈妈、丫头不能好好照顾她。
仿佛也被母亲料到了,就在第三天的夜里,本该守着夜的棠心睡得死沉,直到第二天母亲来到的时候才睡眼惺忪地从桌上抬起脑袋。后来桂妈妈说的也就是这一次。
那时候母亲一下子没来得及管棠心,而是先匆匆摸了一下她身下的被褥,登时勃然大怒,指着棠心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好不容易顺下一口气,母亲第一句话就是:“叫人牙子来,把这眼里头半点没有主子的贱婢赶紧卖走!”
棠心当时又羞又怕,跪在地上瑟瑟求饶,半点没有往日的泼辣。最后棠心虽没有被卖走,却也让母亲给调得远远的,说是洒扫庭院去了。
她房里的妈妈和其他丫头后来也跟着说了一些求饶的话,但母亲再也不信她们了,直接就将她抱到自己的房里见天地照顾着,连父亲来了也不能多引母亲一个目光、多勾母亲说一句话。
“善姐儿今天喜欢吃什么?厨下做了嫩嫩的滑蛋,还烫着,娘亲喂善姐儿吃两口好吗?善姐儿小心烫,来,张张嘴巴,啊——
“外头的天气很好,廊下的那些鸟儿声音都停不了了,善姐儿以前不是最喜欢弄鸟儿吗?娘亲让小丫头给善姐儿找一只最漂亮的红嘴翠羽鸟儿,好不好?
“善姐儿睡了好久,想不想和娘亲说说话?娘亲耳边好久没有善姐儿的声音,娘亲很想听善姐儿再说说话……
“来,善姐儿,喝口药,不要怕苦,吃完了娘亲给你拿蜜果……”
徐善然眼看着药碗里的涟漪,那是一颗一颗眼泪砸下去溅出的痕迹。她渐渐地明白了日后母亲的眼睛为何总是不好,每每被风吹了或在油灯下久了总要干涩难受一阵——母亲哭得久了,哭得狠了,眼睛便伤了。但以前,桂妈妈没有对她说起这件事,娘亲也没有对她说起这件事。
真正爱你的人,哪怕为你哭干了泪、哭伤了眼,也全当是寻常。她心里说不出地怅然。
如果可以说话,她真想告诉娘亲别说话了,她现在又回复不了;也想告诉娘亲别伤心了,将她交给丫头、婆子带就好。
看不见样子,就没有那么多冲击;不去想了,心情也就慢慢平复下去了,就如她最后对待那一个接一个的噩耗与背叛,她最后总会好的。
可是母亲始终没有放弃。时间越久,母亲的精神就越紧张,对她的照顾也就越发细致。
徐善然已经不记得自己这样活死人似的有多久了,也许有十数日了,也许有一个月了。
大夫来了又走,药方换过一张又一张。每次再请的时候,那些大夫看着她虽然没有明说什么,但徐善然并不难从那些大夫的眼神中看出他们的想法,他们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站在这里,不过是尽尽人事。
许多天的时间,来来去去的人和最直接的感情让徐善然再也不能将这当成一场梦境。徐善然想,自己也许是在死之前回到了小时候。她有些迷惑,她当时竟病得这样重吗?那最后又是怎么好起来的?是不是得等现在的她走了,过去的她才能好起来?那她什么时候会走?她又想,走了就再也看不见她的亲人们了。“总不能让母亲这样哭下去啊!”一个声音在她心底低低地说。像心头最柔软的部位被撞了一下,又酸涩又快活的感觉涌上来。
是啊,总不能看着母亲这样哭下去啊!
真好,在走之前,还能再看看母亲为她伤心,为她快乐。
母亲苦苦的支撑并没有维持太久,在某位御医直言要家里准备后事的时候,母亲的神经几乎立刻就崩断了。桌上的茶壶和梅瓶被母亲拂袖扫下。母亲涨红了脸,指着御医高声叱骂,又大声叫着桂妈妈和她从娘家带来的心腹下人的名字,让她们将口出狂言的御医立刻打出去。
母亲的娘家,她的外祖家,也和国公府一样是凭军功起家的。国公府传承已久,除了家丁依旧按照祖训要学枪棒之外,仆妇、丫头都不沾这些了。但母亲的娘家不一样,母亲的父亲、她的外祖父年轻的时候一直镇守边关,家也是在那里安的。别说母亲的那些哥哥,连同院子里的丫头、仆妇,就没有不会骑马不会枪棍的。也只有母亲,是在外祖父回京之后才有的,因为是唯一的女儿,从小被如珠如宝地捧着,一点不让沾这些苦活累事,倒是身旁的丫头被多方教导,一个个都有不凡的身手。
那个直言不讳的御医真的被撵了出去,后来有没有国公府的大管事或者父亲跟着出去赔礼,徐善然并不知道,她只知道母亲抱着她大哭了一场,哭得一点都不漂亮,声音凄厉得就像夜里的枭声,只听着,就叫人肝肠寸断。可是哭完之后,母亲一刻也没有耽搁,她让桂妈妈使管事准备了车子,又让丫头收拾了好些包裹,全是她平常需要使用的。母亲自己只带了两包衣服,跟着她们去京师郊野的大慈寺。
这座寺庙得过先帝的钦赐,还健在的住持据说有大法力。母亲之前已经使人下帖子请过几次了,父亲的名帖乃至祖父的名帖,可都没有将人请来。母亲这一回直接带着她上山去。
母亲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表示虔诚,就软轿仆妇一概不用,直接将她系在身上,一步一叩首地往山上前行。烈日晒花了她的妆容,青石磕破了她的额头,汗水将衣衫浸湿,从没有干过活的身躯摇摇欲坠。
徐善然永远不能够知道,一向娇弱的母亲是怎么就这样坚持带着她走完了一千多级的台阶;一向顺从丈夫、孝敬公婆的母亲又是怎么在明知道丈夫和公公都不信僧道,直言“僧道尼婆,祸家之始”的时候,还毫不迟疑地带了她出来。
她看着母亲带着她攀上最后一个台阶,在住持面前低到尘埃里般苦苦地哀求,又在住持终于松口、点出方法的时候,仿若眼睛都迸出光来般狂喜。
她看着母亲依着住持所言,沐浴净身,禁食一日,然后在菩萨面前磕长头,虔诚地一遍遍念诵着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说着日日戒斋,说着每年布施,说着一切一切,只有一个愿望——“求菩萨让濠州徐氏十三代五女徐善然安康无恙。信女何素雪愿日日侍奉佛祖……”
一颗泪珠从眼角滑落衣襟,捆住她身体的力量似清风般消弭远去。徐善然张开嘴巴,费力地从喉咙中挤出两个字:“菩萨……”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菩萨垂目,慈颜常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