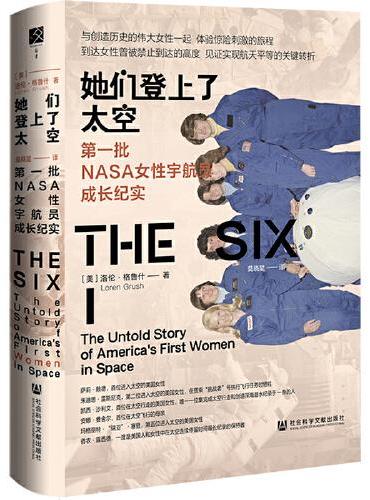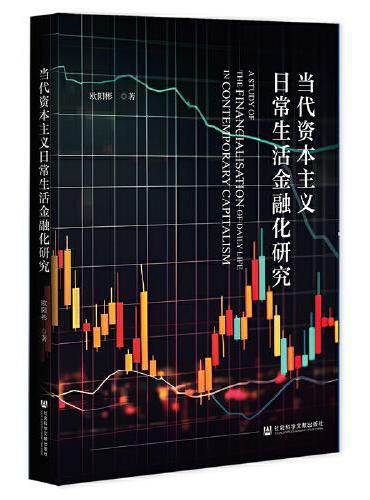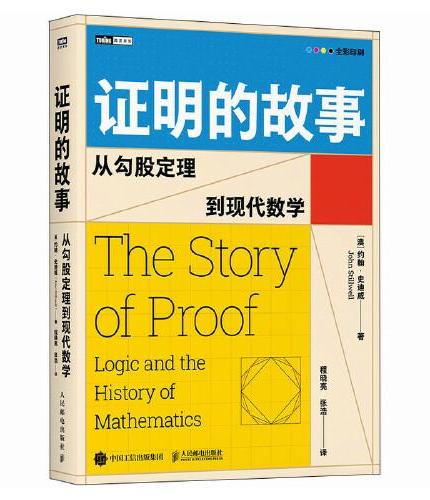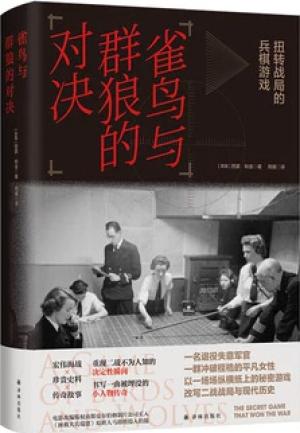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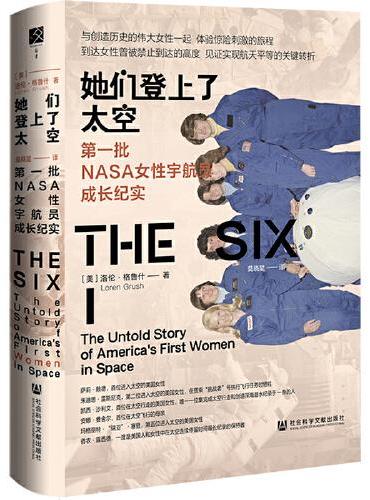
《
她们登上了太空:第一批NASA女性宇航员成长纪实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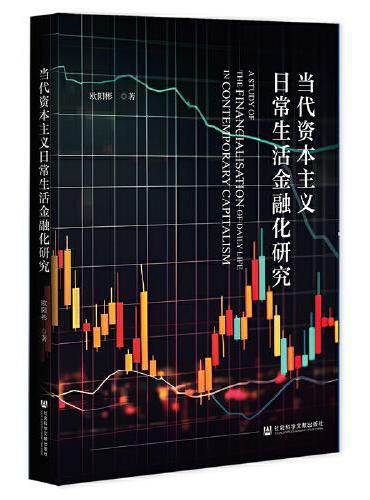
《
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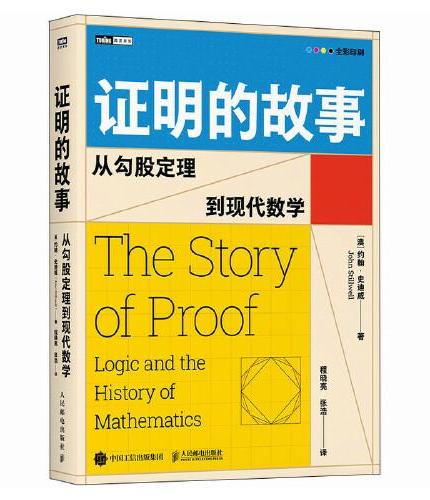
《
证明的故事:从勾股定理到现代数学
》
售價:NT$
6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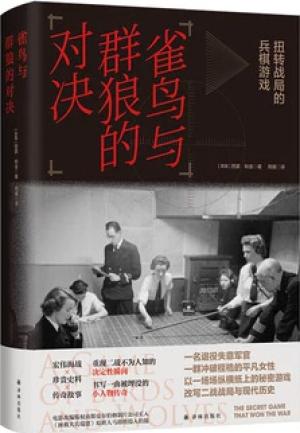
《
雀鸟与群狼的对决:扭转战局的兵棋游戏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对于社会,我不是知道的太多了,而是知道的太少了。”
郑小驴首部散文随笔集
深入社会肌理观照不同层面
韩少功、阿乙、葛亮推荐阅读
郑小驴有丰沛的想象力,灵敏的感觉力,文字的鲜活和精准已非同寻常。如能获得思想和经验感受的持续补位配置,定能根深叶茂,一飞冲天。
——韩少功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一个年轻人有思想,且将之表达得恰到好处,必是历练的成果。郑小驴的文字,是值得期待的。
——葛亮
一个被低估的作家。
——阿乙
|
| 內容簡介: |
《你知道的太多了》囊括了郑小驴近几年来的专栏随笔和散文写作,共五辑。系统收录了作者在《南方周末》《方圆》《深圳特区报》《都市时报》等报刊发表的专栏文章。
《你知道的太多了》涉及社会问题的篇章,立论严肃,见解深刻。将关注重心放在了社会转型期,对一些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和习惯思维做出了掷地有声的、有立场的批判;而作者的旅行记闻,则是写出了轻松、优美的情致,带给人美的享受;散文则别有韵致,自成风格,展现了一位小说家全方位创作的才华。
《你知道的太多了》是郑小驴首部散文随笔集。作家出版社将陆续推出他的小说作品《蚁王》《南棉》,向读者全方位介绍这位80后作家中的翘楚。
|
| 關於作者: |
|
郑小驴,作家,著有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少儿不宜》《痒》,长篇《西洲曲》等。曾获湖南青年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等多种奖项。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
|
| 目錄:
|
第一辑你知道的太多了
围观能改变什么
语言暴力的美学
头发是个大问题
镜头中的谎言
廉价的爱国主义
如何当一名中国作家
再见,周克华
关于记忆力的问题
致我们暮气沉沉的青春
路在何方
冷漠的症结
温柔的暴力
道歉有多难
公民的戾气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临时工
消费主义时代下的青年们
异化的时代
坏人都老了吗
饥饿艺术家
谁带回了杜伦迪娜
在路上的毁灭
犬儒时代
黄昏分居
谢幕的第一代进城务工者
一来记者就死兔子
第二辑云南好色记
昆明记
人间烟火:西双版纳
美哉,傣菜
雪山短歌
雨天的寺庙
创库
也说丽江
作为尤瑟纳尔的海男
穿越北回归线
一个朋友
米线在云南
大理,大理
把灵魂留住
众神之河
藏餐
哀滇池
抽大烟
红嘴鸥,红嘴鸥
一个人的好天气
独克宗古城
质数的孤独
春风沉醉的晚上
虎!虎!虎!
将云朵统统摘掉
历史的另一面
迷人的亚热带
当他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生吃
说说李广田
回忆多年前的一场友谊
香巴拉的诱惑
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云南看云去
一段下落不明的生活
将人统统泼晕
青年旅舍
想想她,马雁
第三辑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灵魂的城堡
我们杀人吧
预言家之死
在世界的边缘
写作的三个关键词
短篇里的刺客
时代的精神病人
百愁之门
第四辑芭茅溪札记
被遗忘与被抛弃的
芭茅溪日记
第五辑散文
1986:春天的咒语
父子
吾祖
秋天的葬礼
|
| 內容試閱:
|
围观能改变什么
“这个世界上总有些糊涂的家伙认为一个人就能改变什么,你只有杀死他才能让他相信自己是错误的,这就是民主斗争。”这是电影《生死狙击》中那个大坏蛋美国参议员信奉的厚黑学。这种哲学当然很恐怖,所以马克·沃尔伯格饰演的BobLeeSwagger一气之下端了他们老窝。这当然是英雄主义的冒险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人是根本行不通的。
或许应该选择一种更温和理智的方式,大家围聚在一起,面无表情,用集体的沉默形成围观的力量,迫使施压者改变立场,选择退让。这当然是好事,如果真的有用的话。好比当年印度圣雄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这种民间不服从运动,选择罢工、卧轨、绝食,面对暴力绝不逃走也不还手,的确让大英帝国的殖民警察们伤透脑筋。这招屡试不爽,以至于1938年,他在答复路易斯·费歇尔的《甘地与斯大林》提问中,“德国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样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纳粹暴行的注意”。这是种悲天悯人的献身精神,在甘地看来,死亡的唯一区别在于是有尊严地自杀或者蓬头垢面地死在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前者比后者更能唤起人类的同情心。我想甘地过高地估量了人类的同情心,至少后一种死亡,在二十余年后的纳粹头子艾希曼眼中,屠杀六百万犹太人这种滔天大罪的责任无需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来。他自认为扮演的不过是体制这台机器身上的某个零件而已,他选择无条件地接受指令,从而认为个体无需去承担法律和道德上的惩罚。甘地的这种同情心和殉情精神,在艾希曼他们面前是可笑的。
不管怎么说,在围观和暴力二者之间,我依然会选择前者。至少围观并不意味着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很多场合,我们会习惯性扮演围观者的角色。面无表情,或者内心带着些许的期待,对即将发生的诸多可能性充满了幻想的热情。我曾长时间关注过某个城市的城管方面的新闻,这个城市很多负面新闻都是由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摩擦引发的。在众多的新闻图片中,毫无例外都会看到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他们围着一两个制服工作者或者执法面包车,中间会有一两个小贩盘腿坐在地上,满是委屈和愤懑的神情。我惊讶于这接二连三的事端背后,结局的惊人相似性:群情愤慨、新闻报道之后,马上风轻云淡,了无痕迹,人们剩下的热情很快就会被另外的新鲜的事端所吸引,将视野匆匆忙忙收回,重新扮演新的围观客;而很少有人持续着这种宝贵的热情,持续追踪和关注这件事,总结经验教训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事情的再生。以至于这个城市的城管面对一次次的被围观,表现出疲倦、厌恶、麻木和不再当回事的样子。所以即便这种事再出现一百次一千次,城管依然在野蛮执法,小贩依然在乱摆乱设,看客依然兴致勃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会出现任何的改变。这种围观,或许更多的是满足了围观者本身的猎奇心理,而不会让“围观”的本质发生化学变化。当围观并不能改变什么时,围观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怀疑。甘地至死也不相信有人会刺杀他,他相信悲天悯人的同情心能唤醒全世界,化解仇恨和矛盾,他忽视了接受他这种思想本身就意味着极端。
一年前,一位台湾左派作家朋友对我说,台湾的今天是靠人民一步一步努力争取过来的。他将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很有底气。然后他问我,“你们又做了什么?”很惭愧,我内心沉默着回复他,“我们在围观”。像这些看客们,面对每天发生的各种令人吃惊和愤慨的事情,表露出一时半刻的情绪,然后又重新回到搓麻将、看《天天向上》、逛街购物、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中去了。身处多元化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快乐的时候,可以去洗脚,K歌,看新闻联播;不快乐的时候,则在网上跟帖灌水,将简单粗暴的器官语言发泄完毕之后,又喜滋滋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
如果围观只不过是让自己在这围观的队伍中增加一个看客,就像甘地提倡的自杀论并不能改变希特勒极权的本性一样,那围观又能改变我们什么?
2014/12/05
语言暴力的美学
修炼成老油条后,人总爱将粗话、脏话常挂嘴边,充当着防身武器。比方说我们常遇到一些让自己不痛快的人或事,在转身离去的刹那,最能释放内心憋屈的莫过于一句顺口而来的脏话。或者再勇敢决断点儿,当场撕破脸的,抖着手指头(恨不得戳人眼里),粗鄙的脏话像密集的子弹迅速精准猛烈地射向对方,试图借用粗暴的语言将其置之死地而后生。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更是泛滥成灾。每则热点新闻背后的评论,通常是语言暴力的集散地。高高盖起的回帖,大多数以粗话开头,以脏话结尾。粗话好比舞台上的高音区,气势恢宏而激昂,在气场上足已压倒对方,横扫千军。所以粗话、脏话往往最简明直接,不耍花招,一枪爆头,都是往死里去的,算得上语言的最高境界,集大成者。暴力语言有时也充当敢死队的角色,开头最脏的几句话,类似于程咬金的三板斧,从身体问候到人祖宗,过后对方若还岿然不动,语言的暴力锐减,顿时黯然失色,自损八百了。这有点像曹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意思。很少见有人将脏话一而再再而三向对方重复喷射的。所以说脏话得有个度,越少越有力量。
人爱说脏话和粗话的一个重要原因,莫过于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类似于关键词的功效。费半天工夫,有的时候一大堆文明的辩解反而比不过一句简单粗暴的脏话,这叫一箩筐好话比不上一马棒。很多时候,很难保证不出口成脏,比方上下班高峰期的地铁、公园里轻浮的拥抱、无处不在的庸俗的广告、虚假做作的新闻播音员、长篇累牍的空洞大论、日渐增大的生存压力……为了不费口舌,省时省力,一句脏话横空出世,用它高度的概括性和总结性将我们愤怒席卷而空,好不痛快!
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在“所指”的时代里,“同志”“玻璃”“菊花”早已超出“能指”范畴,而昔日的“太阳”“舵手”也早已恢复了正常的健康的词义。这些词语曾经爆发出的暴力足以将人击倒。在“文革”时期,这些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红卫兵们随便给人头上扣一顶“毒草”“牛鬼蛇神”的帽子,昔日风光无限的人在这场革命+暴力的语言狂欢中,无不俯首认罪。语言暴力施加给人的压力与痛苦,早已超过暴力本身。特定情况下,“所指”带来的痛苦远甚于暴力本身带来的痛苦。罗兰·巴特“文革”时期访问中国时,他对这场集体的谵妄表现出不安的困惑。“乏味、预知、千篇一律、没有细节”,这是罗兰·巴特当时的内心感受。所有的一切,都是既定的,语言谨慎、严格地限制于“所指”的范围内。这当然无趣。不是对那套暴力语言特别沉迷的人,谁也不会怀念和向往那个年代。
有的时候,说大话、套话、空话也是一种语言的暴力行为。它削减了细节和个性,毫无真实性可言,空洞而乏味,一点也不可爱,好比一张脱焦的照片,面目模糊。
卡夫卡在《谈话录》中特意提到:“语言是行动的开路先锋,是引起大火的火星。”有的时候,脏话意味着危险性。脏话的级别越高,这种危险性就越大。市井中,我们常看到这种升级情况下,俩人从破口大骂到大打出手的过程。特殊年代,说你是黑五类,大不了关牛棚,说你是“现行反革命”,就足够让人吃枪子了。
我见过最高级的语言暴力,两个北京人,用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对骂,全程不带一个脏字,情绪稳定,粗听温文尔雅,细听句句致命。这种高级的骂法我是死了也学不来的。或许这种骂法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至少它不会导致情绪的升级。只是这种让人产生情绪的脏话,少说也罢。我是这么想的。
2012/4/2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