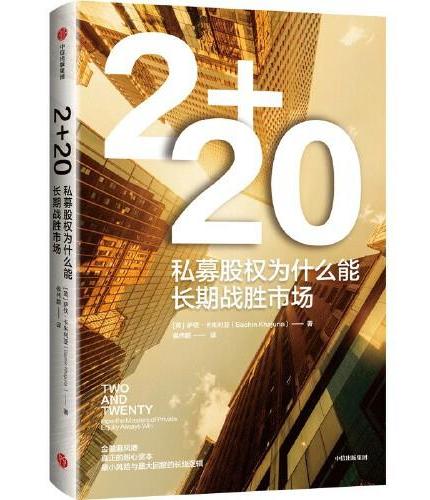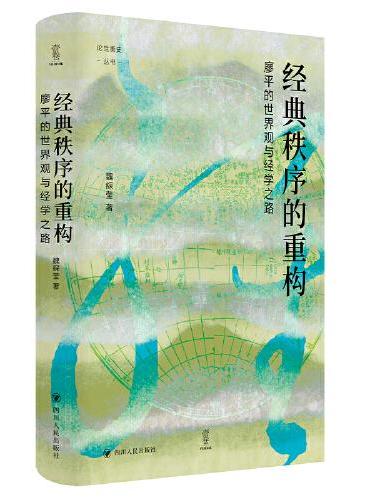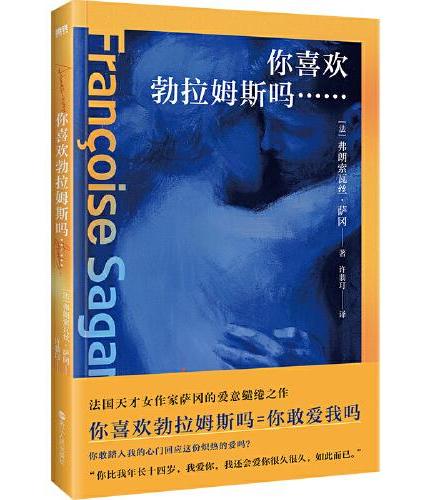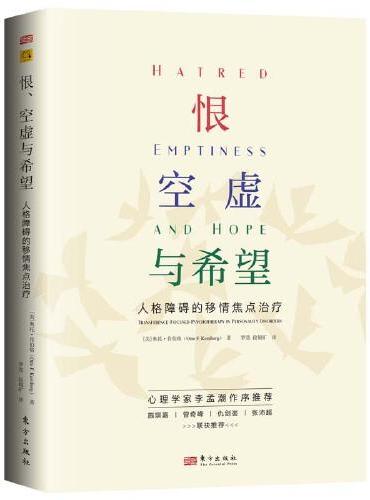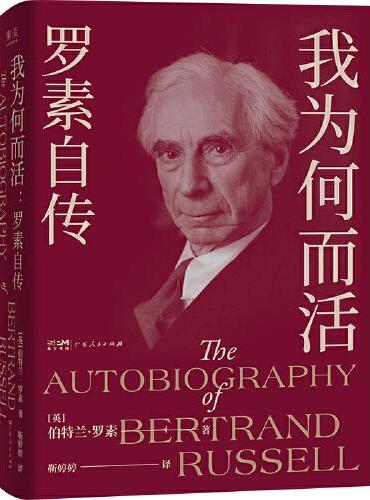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NT$
403.0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NT$
1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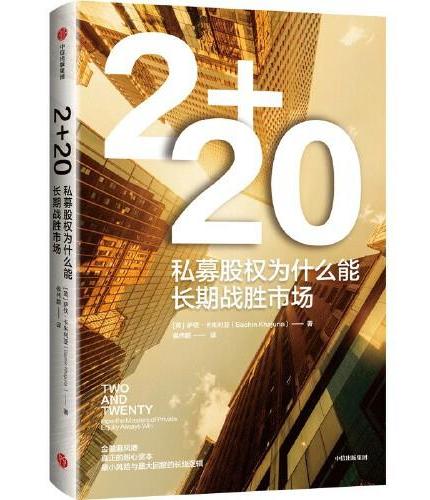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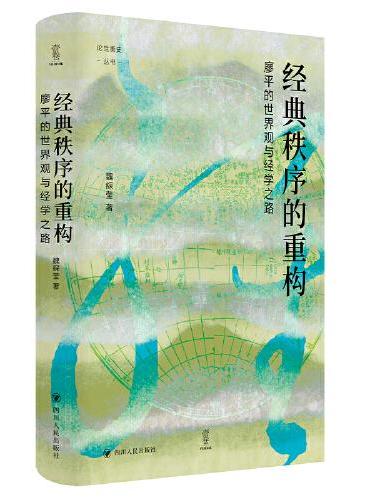
《
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探究廖平经学思想,以新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转型)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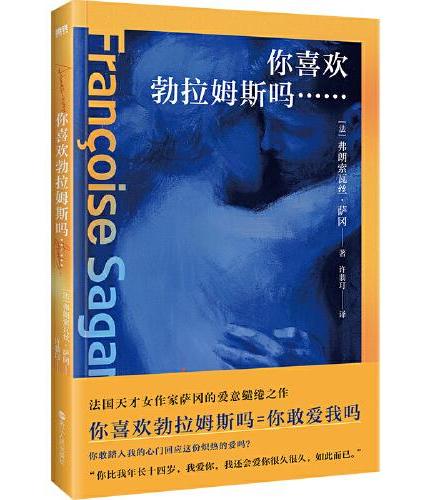
《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
售價:NT$
245.0

《
背影渐远犹低徊:清北民国大先生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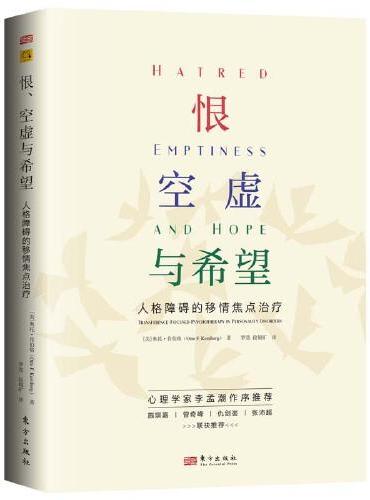
《
恨、空虚与希望:人格障碍的移情焦点治疗
》
售價:NT$
4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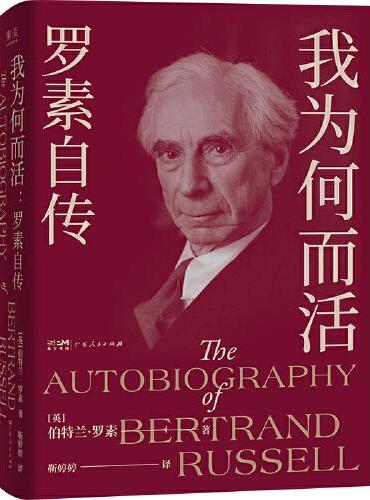
《
我为何而活:罗素自传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透过这位铁血忠魂的英烈,让人感受到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男儿的不屈的气概,一种舍身而取义之德品。
张自忠将军同时得到国共双方**领导人称赞,毛泽东赞他“尽忠保国”,蒋介石哀挽“英烈千秋”,周恩来口中的“中国军人之魂”
由于他个人的影响,在中国的五个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济南都有以“张自忠路”命名的街道。
|
| 內容簡介: |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张自忠是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中国最高将领,及时推出相关作品,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
小说从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重点描写张自忠喜峰口抗战、台儿庄抗战等抵御外侮时的忠勇英烈。即使在担任天津、北京市长期间,因为特殊的岁月,主要的作为仍然是和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全书不仅较完整塑造了张自忠的形象,更以流畅凝练的语言,把一些次要人物和小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达到了史实性、艺术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撼人心魄的民族沉重感。
|
| 關於作者: |
|
张秋铧出生于湖北仙桃市,现居天津,先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进修、南开大学作家班读书。1968年开始发表文章;1979年春,在著名作家魏巍的引导下从事文学创作,发表了各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园中情》、《抗日名将张自忠》、《太阳半张脸》,中篇小说集《烟雨南运河》,长篇传记文学《走向和平》,心理文化随笔《贯通一生的心理手册》等;长篇史诗《啊,钓鱼岛》即将付梓。荆楚文化的滋养和燕赵文化的熏陶,使他的作品朴实清新,可读性强,大气磅礴而又不失婉约,形成了鲜明的个性风格。
|
| 目錄:
|
第一章沧海显英雄002
第二章喜峰口救孤020
第三章巍巍大境门039
第四章情满海河水060
第五章娘娘宫巧遇075
第六章敲山震群虎092
第七章金钢桥斗智109
第八章扶桑花不香127
第九章卢沟起狼烟148
第十章一身系千军169
第十一章激将赠迎春191
第十二章板垣羞杀娇208
第十三章烽火中遇旧225
第十四章武当山说玄241
第十五章又续兄弟情259
第十六章鄂西有奇缘274
第十七章结交在相知293
第十八章星陨大洪山312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沧海显英雄
大河横贯中华大地。万里黄河九道弯。
在蒋、冯、阎大战打得难分难解的节骨眼上,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竟浇熄了民国以来最大的这场内战。人们谈起雨,谁都说这是天意。天老爷帮谁谁就胜。
倾盆大雨日日夜夜下个不停,把个黄河惹恼得咆哮起来了。中原大地千山万壑的雨水,似乎都汇集到了这里。混浊的河水带着滚滚泥沙,宛如一条巨大的黄龙,桀骜不驯地翻卷着,奔腾着,打着漩,怒吼着,排山倒海般地向东倾泻,席卷着房屋、树木、庄稼和人畜。
天不遂人意。中原大战初期,西北军攻势凌厉,中央军节节败退。但自从进入盛夏,遇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罕见暴雨,前线战事急转直下。西北军没有后勤接济,官兵们在雨水中吃不上,喝不上,子弹不够,伤兵等着死。于是,在中央军白花花银圆的诱惑下,有的部队在战场哗变。终于,这支部队土崩瓦解了!
冯玉祥望着败下阵来的士兵们,跪在泥水中,仰天大哭:“老天爷,您老人家成心败我啊……”
终于,翻卷了半年多的内战风云,于1930年10月初消散,留在中原大地的是满目疮痍,累累弹痕,处处是饿殍,村村有哭声。
这几天,大雨虽然停歇,但黄河已经爆发的脾气还没有歇息,仍然打着漩儿在怒吼着。
黄河北岸的一个渡口。几个军人守候在那儿,专等南边的渡船驶来。堤岸那边的柳荫下,还等候着许多中下层军官。他们在寻找失散的部队,还有失散的妻儿老小。
从南岸驶来的这条渡船不大,船上坐满了人。艄公立在舵位上,张着帆,巧妙地利用风向,把船驶向对岸。船到河心,水急浪高,木船穿浪而过,就势驶向北岸的渡口。船头上的撑篙人,把一盘缆绳抛向岸边;岸上人赶紧揽在怀里。几个兵拉着缆绳,把船固定在木桩上。船刚停稳,士兵们抻出一块跳板,搭在船头。
船上的人都是伤兵和家属。人们小心地踩着跳板,走到岸上。脚踏到岸上的人都很激动,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大战中没有死去,没有被俘,女人没有被凌辱,就是天大的幸运;如今又回到了部队,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岸上的士兵搀扶着伤兵走下跳板,指引他们往北走;有的家属见了接应他们的士兵,流着泪,掏出钱来塞到士兵手里。
这时,一个年轻女人抱个包袱,挪动着小脚,战战兢兢地在跳板上走着。越害怕,小脚越不听使唤。走到跳板中间,跳板不由得忽闪起来。她撑不住,刚要挪步,身子一晃,随着一声惊叫,扑通掉进河里。
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见一个军人疾跑几步,跳到水里。
水没过腰,但还够不着落水的女人;他再往前行,眼看黄水漫过了胸脯。近岸的水流虽不那么汹涌,却也异常湍急。黄水打着漩儿,把那女人翻了个个儿,眼看就要被拖进水底。这位军人赶紧往前凫水,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女人的后衣领,顺势往回一拽。
当他往回游的时候,一个浪头打过来,使他呛了一口水。他忍住胃肠的翻动,用后腿狠蹬几下。脚可以够得着地了,他才把女人抱起,踉踉跄跄地爬上岸来。
士兵们帮他接过女人,放到河岸上吐水。
他连咳带吐,仿佛眼睛、鼻子和嘴里都往外冒酸水。一阵难受过后,他抹下头上的帽子,擦把脸,瘫软地倒在沙地上……
过了一会儿,那女人醒过来了,口里喃喃地喊着一个人的名字:“冉德明——冉德明——”
“冉德明!有冉德明这个人吗?”一个老兵十分机灵,他理解女人叫唤的可能是什么人,便冲河岸上歇息的军官们喊了几嗓子。
“有,有!”柳荫下有人答应。
“你来看看这个人,兴许你认识。”
叫冉德明的下级军官,听说那个落水的女人认识自己,心里疑惑,但好奇心催他飞快地跑去。就见那女人浑身精湿,头发上有黄泥,但那清秀的脸庞令他大吃一惊,忙叫着:“秀秀!”
这轻轻地一声叫唤,倒使那女人清醒过来了。她见到眼前的亲人,抱头痛哭:“你,德明!”
原来,这女人是冉德明连长的妻子。今年春天结婚不久,丈夫就归队了,好久没有音信。夏天,公婆催她到郑州去看望丈夫。到了郑州才知道,部队在打仗,丈夫生死不明。不久,部队战败,她随家属们北渡黄河……
冉德明拥着妻子又悲又喜,突然,他想起了什么,问那几个士兵。“刚才救她的是谁?”
“是一个长官。”那个老兵说。
部队败北,官和兵都得通过黄河铁桥和这几个渡口,除了本部队的人,相互认识的人不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刚才那个跳进黄河救人的人,是一个军官,没错!
“那位长官呢?”冉德明问。
“喏!”老兵用手一指。
那军官在救人的瞬间,啥也没有想,可跳进河里后才感到,水深流急,时刻都有危险。加上连呛几口水,上岸后一时精疲力尽。
冉德明见那军官在地上仰天歇息,跑步上前,打个敬礼,说:“谢谢长官救了我媳妇!”
那军官坐起来,随口道:“没事没事,快带她去换身衣服吧,小心……”话没说完,就见冉德明再次打个敬礼,惊呼:“张长官,老校长!”
原来,这个军官就是张自忠。
张自忠今年40岁整,硬硬的板刷头,胡子拉碴,那身灰布军装上沾满泥水,腿上、鞋上有黄泥。平日英俊的脸庞显得十分消瘦、憔悴,只有那对精明的眼睛还是那样炯炯有神,右下颏上那两根长须还是那样很有风度地支棱着。此刻,张自忠也认出了年轻人,说:
“冉德明,原来是你!”
冉德明心情激动,双膝一软,跪下,抚着张自忠哭起来。年轻人这个时候的哭,不仅仅是为了感激,还为部队战败,群龙无首,日后归属……
张自忠也不由得一阵心酸,揉揉鼻子,拍着年轻人的肩说:“不要哭,出膛的子弹不回头!关键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要把劲攒着打外国佬,可不能再搞窝里斗了。”又说,“你还活着,媳妇也来了,你该高兴,去吧,照顾她去吧。”
张自忠像大哥,像长者,那样体贴、亲切。冉德明止住哭,又问了张自忠许多情况。
“你带着收容的弟兄们和家属,往焦作方向走吧,那里有我的部队。”张自忠说。
“那长官您呢?”
“我还要继续收容部队。”张自忠说,“西北军散的散,降的降,我的25师没有什么大损失,我有责任把这支部队带走,日后也好向冯先生交代。”
大战初期,张自忠奉命率部由陇南天水奔赴河南,先后和徐源泉、张治中、王金钰的部队打了几仗,胜多败少,部队伤亡不大。当大战已见定数,冯玉祥宣布下野时,张自忠赶紧把部队带过黄河,在焦作一带集结;自己则坐镇黄河渡口,收容残部和家属。他要决心保存这支部队,给中国军队留下西北军种子……
冉德明是张自忠的学兵,后来到其他部队当班长、排长、连长。在战乱中见到妻子,又遇到了老长官,心中悲喜交加,对张自忠的忠勇精神又多了几分了解和敬佩。他说:
“我执行命令,望长官保重!”他吆喝一声,“弟兄们和家属都跟我走!”
伤兵们互相搀扶着,家属规规矩矩地走在队伍后面,秀秀也走在家属中间;只有一些散兵吊儿郎当。总之,人们形成一个集体,往北走去。
张自忠见冉德明媳妇衣服单薄,又刚刚受了惊吓,便脱下自己的军衣,递给冉德明说:
“快给你媳妇穿上吧,小心着凉。”
刚刚逝去硝烟和战火的中原大地;没有金灿灿的原野和蓝湛湛的天空。只有弹坑、工事和纵横交错的堑壕,只有被砍伐的树桩和烧毁的房屋残垣;颗粒无收的大田里,趴着打毁的大炮、枪械和汽车;死伤的骡马,被饥饿的人们割去吃掉了;残肢断臂的伤兵们,在痛苦地呻吟着,因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和得不到救治,而活活地死去;神情麻木的人们,谁也顾不上掩埋人畜的尸体,遍地是焦煳味和尸臭味……
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自然是中央军总司令蒋介石。他用装备精良的军队和美元、袁大头,把一个个对手击败了。大战期间,他一直在柳河车站的专列上督战指挥。此时,他命令专列开往郑州,一显占领者的威风。
一度冷清的郑州火车站,今儿个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中央军的将领和地方各界名流,在这里恭候蒋总司令。一时找不到军乐队,地方人士便找来几套锣鼓,“隆咚呛,隆咚呛”,敲打得甚是热闹。
不多一会儿,专列徐徐开进车站。不等停稳,荷枪实弹的卫队士兵迅速跳下车,张着机头,在列车周围警戒着。顿时,气氛紧张起来,有几个地方官员的腿肚子不停地转筋。
列车停稳之后,全副武装的蒋介石从车上走了下来。他穿一身黄呢军服,佩着武装带,腰上别支小巧的美式手枪,后面披着黑色斗篷。他40挂零,中等个儿,瘦削的身材,深陷的眼眶,嘴上有两撇胡子,显得神采飞扬。
迎接的将领和官员不觉上前几步,争着向他敬礼、握手。但蒋介石只是向他们点点头,摆摆手,“好,好,”打了几声招呼。锣鼓敲得山响,震耳欲聋。刚刚被枪炮声困扰了几个月的他,实在不愿再听这么聒耳的声音,他一挥手,说:
“不要敲了!”
锣鼓声戛然而止。人们的脸上凝聚着惶恐。蒋介石不去理会他们,掀掉斗篷,从容地在月台上走了一个来回,站定,摘去手上的白手套,悠然地环顾四周。他仿佛听到了两年前到郑州和冯玉祥结拜金兰时那悦耳的军乐声;仿佛看到了西北军和晋军与他的中央军在怎样的拼搏鏖战,血肉横飞;仿佛感觉到了失败后的冯玉祥、阎锡山此刻的沮丧、懊恼和颓然……一阵不可名状的喜悦和激奋,刹那间洋溢全身。他捏着的白手套在另一只手上拍打几下,不觉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将领和官员面面相觑,毛发悚然,不知蒋总司令为何这般狂笑。有几个土乡绅站不住了,浑身像筛糠似的瑟瑟发抖。
大笑过后,蒋介石用他那浓重的奉化口音朗朗吟唱道:“天下英雄谁敌手?只有蒋某!”
这时人们才释然,他原来是为胜利而欢笑。几个贴近的亲信忙凑过来,恭维道:“天下谁也不是您的敌手,蒋总司令才是当今英雄!”
“哈哈哈……”又一阵大笑过后,蒋介石正色道:“俘虏的那些人中,有谁不愿意投降的?”
“有,有个姓王的师长。”邵力子想了想,说。这次到前线督战指挥,蒋介石没有带参谋长,除了他的卫队和几个参谋,只带了邵力子和周佛海两名文官协助他处理公文。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生是西北军的人,死是西北军的鬼,宁死不投降。”邵力子说。
这次大战,阎锡山最狡猾。一看张学良派兵入关,而自己又没有打败蒋军的希望,便赶紧令部队后撤,龟缩进他的山西老巢。虽然损兵折将,但毕竟没有赔掉老本。而冯玉祥就不同了,他的性格决定他强硬到底,死不后退,敢于战到最后一个人。在被围被俘的西北军各部纷纷投降的时候,只有那个叫王丕襄的师长宁死不降。不说一句软话。
“他娘的个屁!”蒋介石气得骂起来,“老子缺美元,不缺光杆师长!”他气鼓鼓地在月台上走几步,眼里冒着火。突然,把手里的白手套往远处的铁轨处一扔,吼着:“把他给我毙了!”
一个参谋赶紧给前线打电话,传达这一指令。
邵力子忙站出来说:“总司令,地方官员已经给您把行辕准备好了,请您到那儿去休息。”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蒋介石的气还没有消,那深陷的眼里仍然燃着火光。
“总司令,那儿条件方便些,您还是去吧,大伙都在这里迎候您啦!”周佛海也来劝说。
蒋介石这时好像才发现,车站上还有这么一帮子人。他挥挥手,对他们说:“你们去吧,都去干自己的事去。我就在车上。”
蒋介石说的是真话。郑州是冯玉祥的地盘,战争刚结束,散兵游勇还在活动,哪儿也不如列车上安全。一旦有情况,开车就跑;住行辕好像住鸟笼子,谁要来捣乱,如同瓮中捉鳖。
可是邵力子他们摸不透他的心思,还在一个劲儿地劝说。蒋介石不耐烦,也不答话,自个儿走上列车,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侍卫长王世和算是最了解总司令的,他认为是在生那个不投降的王师长的气。他给沏碗龙井茶,放到蒋介石手里,说:“我们打了胜仗,这是最值得高兴的事。总司令这些日子辛苦,您好好休息,犯不着为那些俘虏们伤脑筋。”
“你不懂。”蒋介石端起茶碗又放下,又把目光对着邵力子、周佛海说,“你们不懂。”
手下人怎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他招降了那么多西北军将领,要是人人都长有一块反骨,日后谁听他的指挥?在这么些对手中,他最佩服冯玉祥,最羡慕西北军。条件那么苦,常常没饭吃没衣穿,可打起仗来却骁勇无比。中央军武器精良,可士气不那么高昂。要是能把骁勇的士气和精良的武器加到一起就好啦!
他端起茶碗,用碗盖划动浮茶叶,品一口,问邵力子和周佛海:“查一查,看西北军中,还有没有实力完整的部队。”
周佛海半天没有说话,这会儿抢着说:“西北军以卵击石,全军覆没,哪还有什么完整部队!”
“怎么没有?”王世和毕竟是军人,又不大喜欢周佛海那番阴阳怪气,反驳着。
“谁?”蒋介石放下茶碗,睁大眼睛问。
“西北军第11军副军长兼整编25师师长张自忠。”王世和像背报告词似的一口气说完。
“张……?”蒋介石瞪着眼,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江浙口音把“自”与“治”说不分明,以致他把这个名字听成了他的部将“张治中”。
“就是,就是……”邵力子也说不清,但迅捷地从一摞军官花名册里,抽出了一张登记表,放到蒋介石面前,说:“就是他。”
这张登记表的上首,有张英俊的军官正面免冠相片,其表中这样记录着——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8月出生,山东省临清县人。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加入同盟会;1914年欧战爆发,日军趁机侵占青岛,兵临济南,他投笔从戎,到奉天车震部当兵;1916年,车震将其推荐给冯玉祥。历任差遣、排长、连长、副官、营长、学兵团长、旅长、军官学校校长、师长、副军长……
“张自忠,知道,知道!”不等看完,蒋介石手击书案,连声说,“他现在哪儿?”
“过了黄河,可能在焦作一带。”王世和答道。
“快,给他发去委任令,”一切都使他记起来了。蒋介石异常兴奋,踱了几步,说:“委任为28路军总指挥,赏金10万块光洋。”
因为他了解张自忠的才干,更知道他的作用。那年他派刘峙到西北军中参观,冯玉祥给他看的就是张自忠的25师;前年,冯玉祥又派张自忠率第二集团军旅以上军官参观中央军,之后,让他到南京向蒋、冯做了汇报。张自忠长期任学兵团长和军官学校校长,西北军相当一批中下级军官是他的学生。如果能得此人,不仅增添了一支劲旅,而且所降各部也会稳定。
蒋介石本来打算在郑州只待3天,可给张自忠发去委任令后,第二天没有回音,第三天没有消息,等到第四天,还是没有一点儿动静。他纳闷:给了张自忠那么高的名分,那么多钱,而且我蒋某人日后绝不会亏待他,他怎么不为之所动呢?蒋介石这个时候的心情,就像曹操看到关云长舍弃高官厚禄,不远千里去寻找刘备时一样。既恼羞自己自作多情,又忌恨冯玉祥有这样忠义的将领,又佩服张自忠的为人和气节……十分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最后无可奈何地叹息道:
“这个张自忠啊,唉……”
连着两天两宿,张自忠始终在渡口收容失散的部队和逃难的家属。
战争后期,中央军没有追杀打散的西北军。张自忠趁机把部队拉过黄河,又让工兵营找来船只,便开始在渡口收容残部。凡是西北军部队,不管哪个系统,不管长官是谁,只要愿意过河,他都负责收容;愿意回家的,把刀枪留下。
士兵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一个个叫花子似的。重伤兵人们带不了,扔下了;轻伤兵被人们搀扶着,一步一挪地艰难行进着。有的倒背着枪,有的拄着枪,像拄着根打狗棍;插在背上的大刀片,血渍、泥土和雨水,把刀刃给锈蚀了。许多士兵的脚在泥水中泡烂了,化了脓;长期洗不了澡,身上长了虱子和疥疮,有的阴部瘙痒,长有湿疹……
看到士兵们的惨状,张自忠的心就一阵紧缩。又一只渡船划过来了,他从河岸走下码头,准备迎接归队的士兵。这时,传令兵从堤岸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报告长官,师部电话,让您亲自去接。”
张自忠对那位老兵交代了几句,走向堤岸去接电话。电话是参谋长张克侠打来的,他说:中央军总司令蒋介石来了委任令,让他出任28路军总指挥,赏银圆10万块。
张自忠拿着听筒,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心里一阵躁动,满脸涨得通红;之后,脸色平静;之后,脸色死灰,满头大汗淋漓。好半天,才说:“我一会儿就到!”
他撂下电话,二话没说,向卫兵一招手,跨上战马,紧磕马肚,向焦作方向奔去。坐骑撒开四蹄,马蹄有节奏地敲击着黄土地,紧张而清脆的蹄声,在荒凉的原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张自忠下马,把缰绳扔给卫兵。
他俩见面只用眼睛打个招呼,张克侠扔掉烟屁股,和张自忠进了师部。他们来到密室,屏退左右。克侠把蒋介石发来的委任令放到张自忠面前,说:“刚收到,我就给你打了电话。”
张自忠瞟了一眼,把目光转向克侠。
张克侠把脸埋下,闷着头抽烟。良久,他问张自忠:“你打算怎么办?”
“我先听听你的想法。”
他把脸抬起来,看着张自忠说:“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有吃有喝,不操心受累,但必须仰人鼻息,听人驱使,任人宰割;一条是忍饥挨饿受穷,操很大的心,但腰杆子笔挺,心里踏实。不知你老兄想走哪一条路?”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张自忠问。
“我就是这么想的,让你来定夺。”
张自忠没有说话,眼睛死死地瞅着墙角,头不动,身不晃,眼不眨,似一尊静止的蜡像;许久许久,他抬起左手,捻着右下颏上的两根长须,捻着,捻着,捻着……又不知过了多久,他霍地站起来,在窄狭的民房里踱步,步子由快到慢,由慢到快,像一头烦躁的雄狮。
张克侠懂得他此刻的心情。这不是个人的升降荣辱问题,而是关系到西北军数万人的命运,关系到冯先生一辈子的心血呀!降与不降,全在张自忠一句话。事关重大,决心难下。克侠不去打搅他,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偶尔瞟他一眼。当他抽到第5支烟的时候,张自忠突然站定,平静地对张克侠说:
“好吧,你去把各部队的旅以上干部都找来。”
张克侠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知道张自忠已经决心下定,而且知道他走的是哪一条路。他扔掉烟屁股,走出屋,让参谋和传令兵分头去找各部队的长官。
这个时候,张自忠才觉得口渴得很。他倒了一碗水,咕咚咕咚喝了;又点燃一支烟,“吱,吱——”地抽了几口。抽了大半截,他扔掉烟,整理一下衣帽,紧了紧武装带,走出屋子。
工夫不大,村外响起一阵阵“嘚嘚”的马蹄声——师长、旅长们都到齐了。没有口令,他们一字儿排开,站在张自忠面前。他们中间,有的是他的老同事,有的是他的学兵,有的是他的老部下,也有的和他不熟悉。但今天,失败的命运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张自忠原本名声响亮;眼下又主动收容残部,都称他功德无量,十分敬佩。
张自忠站在台阶上,冷峻地在各位师、旅长脸上扫视一眼,说:“各位弟兄辛苦。”他把那张委任令在手里晃一晃,“请各位看看这个。”
那张委任令从排头传向排尾,又递给张自忠。人们一阵骚动,在议论,在嘀咕。
“弟兄们都看过了。”张自忠说,“这里有官有钱,谁愿意去,谁尽管走;不怕吃苦受罪的,那就跟我走!丑话说到前头,跟我走的人,可能没有官做,可能饿肚皮。”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走,我们不愿意当那个鸟官!”“愿意跟张长官走!”
张自忠摆摆手:“先不要说,考虑好了再定。”
大家一阵缄默,然后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愿意跟张长官走,吃苦受罪我们认了!”
张克侠站出来说:“兵败之后的这么个烂摊子,要是投到人家怀抱里去,将来就要受人家宰割,到那个时候,想走也走不成了!”
“对,张参谋长说得对。”一个旅长站出来说,“我们信得过张长官,你带我们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好赖大家都是西北军的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话都能说得拢。”
这个旅长叫黄纲,三十出头,身材魁梧,过去没有和张自忠共过事,但为人正派,又很能打仗。此刻听他这番言语,张自忠对他产生了几分好感。
旅长何丰说:“西北军的脾气就是不听人摆布。张长官,你就带我们走吧!”
瘦瘦高高的赵登禹也是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可他在宋哲元手下当旅长也有年头了。在这次恶战中,他的旅损失不小,这时他也站出来说:“张长官,我看啥话都不要说了,弟兄们信得过你,你就带着大家伙走吧。蒋介石的委任令刚发出,还等着你的回音哩,要不,中央军追来就糟了,这么些人跑都跑不掉。”
汾河两岸,有一块肥沃的土地,这就是晋南大地。晋南地理位置特殊:东面是太行山,西和南是黄河。山与河形成掎角之势,宛如几道天然屏障。晋南人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耕耘繁衍。这里有史以来受战乱影响小,所以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民风淳朴。张自忠选择这块风水宝地屯兵养兵,实在是高瞻远瞩之举。
张自忠率领大军到达晋南不久,西北各省部队也陆续到来。近5万人马,分布在运城、闻喜、曲沃、侯马一线。眼看天气渐冷,人吃马喂,疗伤治病,休养生息,无不需要足够的军需保障。西北军原本就穷,战败之后元气大伤,更是一无所有。许多士兵还穿着单衣,很多人没有被子盖。有的部队一天保证不了两顿饱饭;伤兵和病号得不到应有的治疗。
原西北军某些资格较老的将领,大战中打散了,跑了,如今听说残部到了晋南,便纷纷到这儿来察看,有意统领这支部队。但一看这副惨相,那股雄心就冷却了。
有个头目既想统率这支部队,又不想为这个破烂摊子伤脑筋。于是和张自忠商量:我为正职,你为副职;我主对外事务,你管军内事务。张自忠说:“现在不需要名分,就需要对5万来弟兄负责。眼下最要紧的是保障军需供给;不然,官要穷跑,兵要饿散,或者糜烂百姓。”
他们一个个摇摇头,都走了。这副担子,只有落在张自忠肩上。他不断地调解矛盾,不断地劝说官兵,不断地筹集粮草、衣物、药品……
几阵呼呼的北风,带来了飘飘扬扬的雪花。士兵们意志消沉,情绪低落,蜷缩在炕头上,抽烟,赌博,骂街,谈女人。
这支部队向何处去?
张自忠在思考:自己不愿成为冯玉祥之后的第二个西北军王,就中国当前形势看,也不可能再滋生手握重兵的大军阀。作为军人,只想报效国家,抵御外侮,造福百姓。眼下要统御这支残部,最重要的是没钱没物没粮草,完全指望晋南这块土地养活这么多人马,是不可能的。生存都困难,更别谈发展了。眼下要紧的是,必须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接收这支部队。
那么,找谁最为合适?中央军是不能找的。而离得最近的是阎锡山,但张自忠对他信不过。此人私心很重,不讲义气,待人小气,而且出尔反尔;印象好的是桂系将领李宗仁,他曾经和冯玉祥南北联手反蒋,关系颇厚,去找他,肯定会接收。但问题也不少:南北两方的军队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而且把部队从晋南开往两广方向,中间不知会遇到什么情况。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风险极大……
他辗转反侧,前思后想,认为唯一信得过而且条件方便的,眼下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原奉军少帅、中原大战时入关的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现住北平,只派有两个军在关内驻守热、察、平、津、冀等广大地区,兵力不敷,实力单薄,正需要扩大实力。而自己所收容的这批人马,虽说是残部,但军官多,老兵多,素质好,只要得到应有的物资装备,战斗力是很强的。将此情况向少帅陈述,他不会不接收。
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克侠。张克侠没有答话,闷头抽了几口烟,半晌才说:
“以你的学识和才干,完全有能力带这支部队。但我觉得,就是有人接收,你也最好不要当正职。你长期在第一线当师长,与其他部队联系少;虽然许多中下层军官是你的学兵,但难就难在还有几位师长以上军官和一些老资格的旅长,就怕他们不服你,从中给你为难。”
张自忠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克侠说的是实情。军队山头林立,派系繁多。上级用下级除了才干,重要的看你是不是曾经跟过我,是不是忠诚于我;下级对上级,看你是不是我的老长官,是不是我所信得过的人,不然我就不跟你走。张自忠是1916年投奔冯玉祥的,而西北军中,还有许多当年和冯玉祥在清兵帐下的一些人,这些人现在大都是旅以上军官,冯先生平日对他们都礼让三分。在这混乱之际,自己临时把这支部队带出危险境地是可以的,但要真正统领、驾驭它,老资格的将领肯定不听命。
他们正商量着,突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点名让张自忠到北平去面谈。究竟谈什么,电文中没有说。张自忠与克侠都认为,肯定是与接收改编这支部队有关。
于是,张自忠向克侠、文天等人交代一番,让他俩好好掌握部队。自己则换身行头,一副小商人打扮;又带两个护兵当作小伙计,带上盘缠和干粮,一行三人上路了。
他们从侯马雇条小船,沿汾河溯水而上,昼夜兼程,四天之后到清徐上岸;然后顶风冒雪,步行数十里到榆次。在这儿没有片刻耽搁,直奔车站,搭乘去石家庄的火车。在石家庄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登上了去北平的列车。临近北平,张自忠的心里似乎有些紧张和激动,他从来没见过张学良,该向少帅说些什么呢?
到了北平,他们先找个旅馆住下,吃过饭,洗个澡,就到首善医院去见他的特务团长刘山。
二人相见,喜不自禁,互相询问了一些情况;张自忠说明来意,让他协助做些工作。他们一同来到旅馆,张自忠凭着记忆,让刘山列出图表,标出某部驻何处,有多少人和枪。他们一直工作到凌晨。
张自忠小睡一觉,起床吃过早点,身揣张学良的电报和那份部队实力图表,英姿勃发地去少帅府……
少帅府设在中南海。
自从辛亥革命首义成功,中国结束了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以后军阀混战,群雄争霸,一片乌烟瘴气。但凡进驻北京城的军阀,一个个都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中南海。何也?这是公地公房,随便抢占,而且风景极美,历朝历代都是统治者的基地。于是,这里的主人你上台来我登场,频繁上演一幕幕丑剧、闹剧、悲喜剧。
张自忠来到西华门,就见门口站着几个哨兵,荷枪实弹,威风凛凛。他向带班长打个稽首,递过自己的名帖,说:
“我是奉少帅之命来的,请班长报告一下。”
带班长看看名帖,又把来人打量一番,见他虽是个小商人打扮,但英气勃勃,显露军人气质,便客气地说:“你这哈来得太早,怕是少帅还没起床哩。”话虽这么说,还是报告去了。
不多一会儿,出来一位副官,盘问张自忠几句,就把他带了进去。张自忠从未到过中南海,就觉得拐了几道弯,经过几重园,来到一个较大的园子,副官领他到客厅坐下。
张自忠的一支烟没有抽完,就见厅外几个人影一闪,张学良将军走了进来。他一身戎装,只是没戴帽子和手套。他先伸出手,十分平易地说:“久仰,张军长一路辛苦。”
张自忠的副军长只是挂名,而实际是师长职务,西北军中人们从不称他为“军长”或“副军长”。少帅此番称谓,显然是了高抬张自忠的身份。
他们寒暄一番,说了些路上的情况。
张学良今年31岁,要是一般人,只是个乳臭未脱的毛头小子。孔夫子说三十而立,而许多人到这个年岁却立不起来。可眼前的这位少帅,一靠大帅的荫庇,二靠自己的才干,早在4年前就被北洋政府授予上将军衔,不久前南京政府又委任其为全军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其名分仅在蒋介石之下。
少帅见比自己年长9岁的张自忠有些拘束,便没有问及军队情况,而是让他陪自己吃早点。他素来晚睡晚起,侧重于夜生活;要不是张自忠求见,他还要多躺一会儿。其时10点已过,张自忠是吃过早点的,可又不便让对方扫兴,就硬着头皮陪着。不过,少帅没有少年得志的凌人盛气,没有架子,说话也很随和,张自忠的心里便踏实了许多。一边吃早点,一边谈部队情况。待早点吃完,情况也说得差不多了。
勤务兵把早点盘子收走。张自忠从身上掏出那张部队实力分布图表,呈给张学良。
张学良让副官拿来一张地图,展开,对着图表一一查看,满意地点点头,问张自忠:
“张军长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自忠此行,就是来请教少帅的。”
“冯先生亲手创立的西北军,在全国名声响亮。这次中原战败,情有可原。”张学良说,“眼下部队已经收拢,张军长功不可没,等于第二次创建了西北军,应该请冯先生出来为好。”
“我们多次派人和冯先生联络,先生无意复出。”张自忠还告诉,冯先生暂且隐居太原,还给他往晋南捎了两本书,也捎来话,让他去找张少帅。他说,“我和将领们多次商议,都愿意在少帅麾下,接受少帅指挥。”
张学良再次看了看那张部队实力分布图表,说:“只要冯先生没意见,将领们也愿意,我倒是乐意接收这支部队。应该说,这是支素质很好的部队。将士们相信我不会亏待,我也相信这支部队今后能成为东北军中的得力骨干部队。”
他俩商量了部队整编的许多细节:这支部队对外称东北军第三军,暂编两个师,每个师6个团,师以下不设旅;由于军官多,可编两个军官教导团,一个为团以上,一个为营以下。老弱病残官兵愿意回家的送盘缠和生活费;部队的军需、装备,先按两个师配备。张学良说:
“张先生,那我就委任你为第三军军长吧。”
张自忠没有应承,想了想说:“少帅应该理解西北军,这支部队不仅兵老,将也老,比我资深的人很多,我怕是承担不了这个重任。”
“张先生不必过谦。先生文武全才,堪称西北军之佼佼者,完全可以统领这支部队。”
“少帅过奖,在西北军中,我的资望浅,德不足以服人,才不足以驭众。”张自忠想了想说,“如果少帅信任我,我可以推荐一个人。”
“谁?”张学良问。
“宋哲元先生。”这是张自忠近日不断思索、反复敲定的一个人选。他说,“宋先生是我们的老长官,多次出任总指挥,资深望重,待人忠厚。”
张学良知道宋哲元。他和刘骥、鹿钟麟等人是冯玉祥的左膀右臂,多次出任总指挥,向蒋介石发出过讨伐通令;而蒋介石也在讨伐令中点过宋哲元的名。张学良问:
“宋先生现在哪儿?”
“在天津。”张自忠告诉他,在战局急转直下时,许多人纷纷降蒋。唯有宋哲元避居天津,听候中央处理,要杀要剐由他去,反正就是不投降。“宋先生呵,就有个山东人的倔脾气。”
张学良笑了,说:“张先生也是山东人,也有那么个倔脾气嘛!”
张自忠淡然一笑。他明白,这是少帅对自己的赞扬,不过此刻,对谁也不便褒贬,便说:“如果少帅允许,我明日就去天津请宋哲元先生,相信他会复出的,然后我引他来见少帅。”
张学良见张自忠诚心诚意要去请宋哲元,心里对他很是钦佩。有的人为了升官,不惜施展手段,卑鄙地巴结上司,自吹自擂。而张自忠以大局为重,不仅不伸手,而且主动退让,这不仅表现他忠诚仁义,而且他非常有自知之明,确有儒将风度。张学良站起来,再一次握着张自忠的手,恳切地说:
“荩忱兄,我十分敬佩你的人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