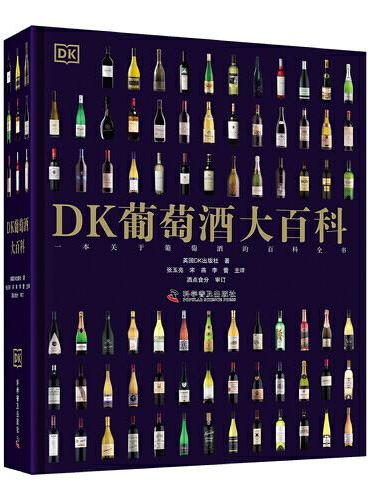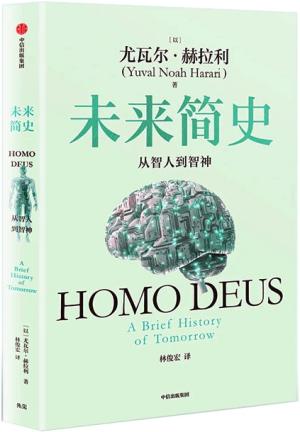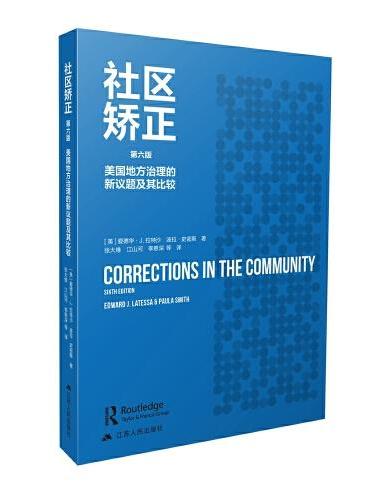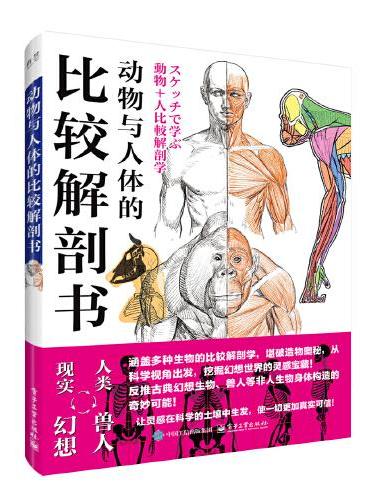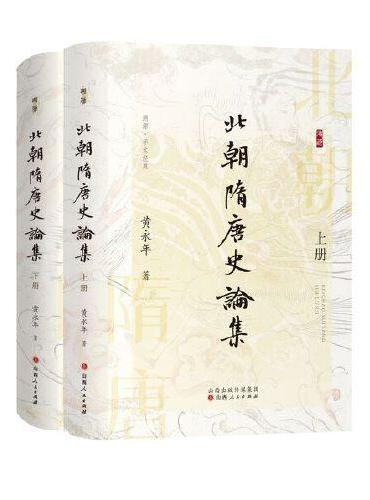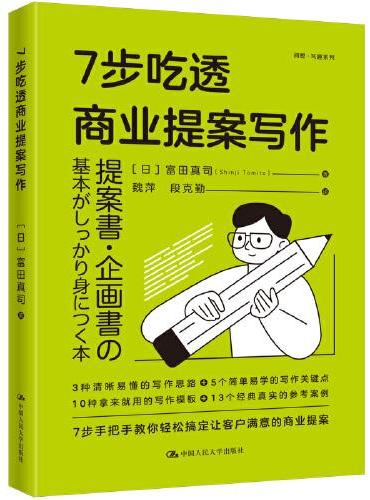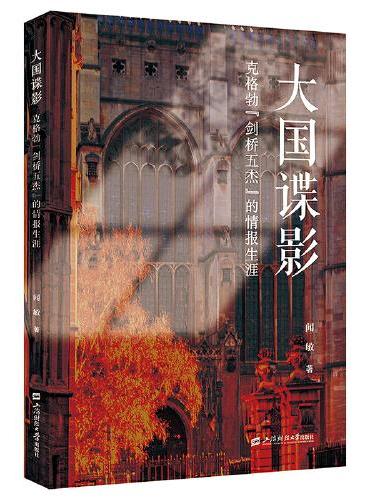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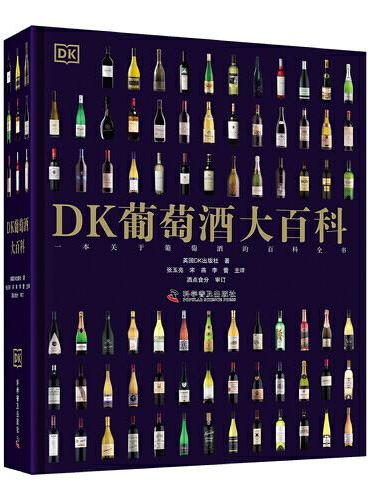
《
DK葡萄酒大百科:一本关于葡萄酒的百科全书
》
售價:NT$
2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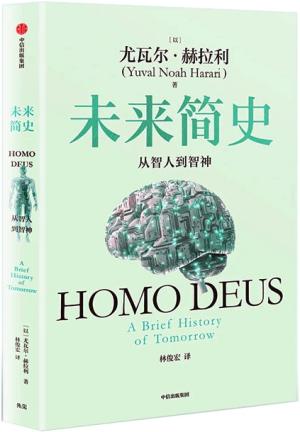
《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2025白金纪念版)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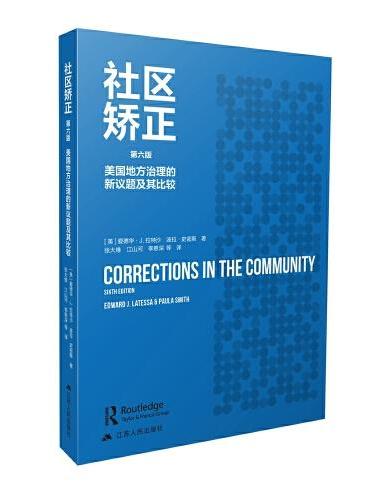
《
社区矫正(第六版):美国地方治理的新议题及其比较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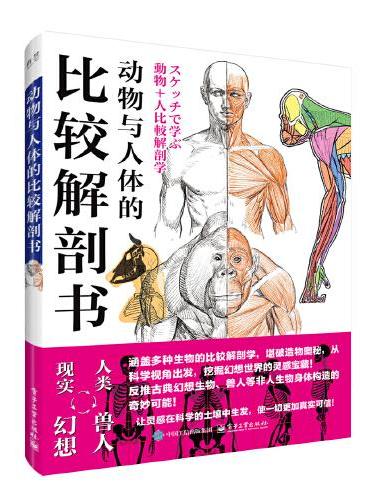
《
动物与人体的比较解剖书
》
售價:NT$
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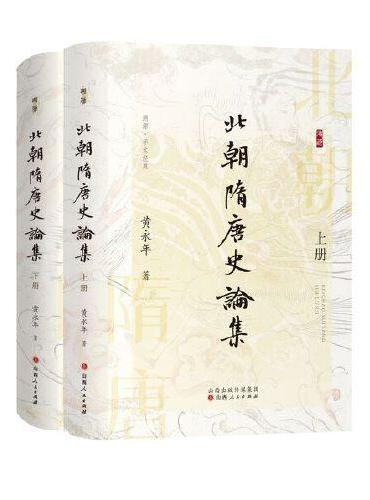
《
北朝隋唐史论集
》
售價:NT$
1270.0

《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全5册)
》
售價:NT$
12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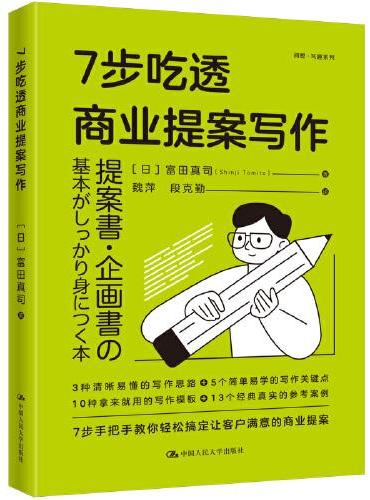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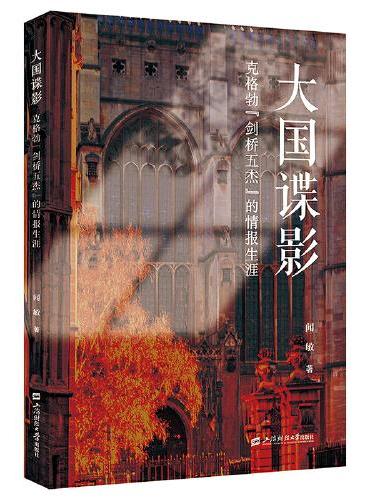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编辑推荐:
一时冲动,世世不祥
他用十世孤寂,换她重生一世,却连去她身边都不敢……
《桃之夭夭》6期连载 精心烹制幻想言情大戏
铁血真男人夜祺推荐:这是**一个让我频频落泪的故事
这年头,没钱也任性!
*傲娇的男老板——
他流落人间,不老不死
经营一间轿行,价格贵得吓人,却不是每单生意都接
*磨人的小妖精——
她悔了婚,逃了家,不管他去哪座城市,都拧着行李偷偷地跟着他
|
| 內容簡介: |
杜望的轿子能让人变换性别,起死回生,预知未来,回到过去!
谢小卷握了握拳,默默发誓:紧跟杜望有肉吃!
这边杜望表示: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那边谢小卷却早已从“凤鸾双喜轿”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
那个人竟是杜望……
|
| 關於作者: |
远在:脑子里有很多稀奇古怪想法的水瓶座,想要去很远的地方亲眼见证奇奇怪怪的事情,脑子一热就会把想到的事情付诸行动。写文也依然倾向于各种奇奇怪怪的设定,和走到绝路的故事,经常想为了攒人品做个亲妈,但想到的梗多半都虐到自己睡不着觉。
2015算是自己的幸运年,希望以后依然一如自己的笔名,远行远思,自由自在。
|
| 目錄:
|
第一章 紫绸祥云轿
第二章 凤鸾双喜轿
第三章 回梦肩舆
第四章 沉木冥棺轿
第五章 坤巽离兑轿
第六章 倾雪流玉轿
第七章 丹心澄明轿
第八章 百川归寂轿(上)
第九章 百川归寂轿(下)
第十章 三更入魇轿
第十一章 神行千里轿
第十二章 离魂溯追
第十三章 浮光匿影轿
第十四章 巫山不负巫山云
第十五章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第十六章 尾声
|
| 內容試閱:
|
紫绸祥云轿
一
又一年的新辞旧岁,爆竹声炸的整个清平热闹地像是换了个人间。东街32号悄然挑出一张青色的帆招,上面绣着前后两个胖滚滚的扛着轿子的圆娃娃,虎头虎脑甚是可爱,另有一张原木小匾,上面四四方方地写着“广记轿行”四个字。
轿行老板叫做杜望,出乎意料的是个颇为新派的年轻人,头发剪得干净利落,穿着一身烟灰锦的茧绸长袍,温文尔雅,只一笑露出一侧一枚虎牙,另一侧一枚干净的酒窝。带着单枚的银链玳瑁眼镜,另外一只桃花眼微微一抬便惹得走过路过的女学生们小脸发红,莲步不稳,你推我我推你嬉笑着跑开了。
年三十天气特别好,暖阳晴雪。杜望拎着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抱着本香谱看的津津有味。有街坊的孩子们结成团儿,挨个儿进临街店铺讨些瓜子糖果,说些吉祥话。到了广记轿行门口,大概是没有见过这样年轻俊俏的老板,都有些害羞。杜望很好说话,去柜台里给每人满满抓了一兜新炒的花生,又一人给了一个小铜板,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走了。杜望坐在椅子上看书,觉得自己的衣襟被人扯了扯,一脸宠溺地低头看向自己身侧的虚空处:“你们也想跟那些孩子一起玩?可人家看不见你们,怎么跟你们一起玩?”
“伙计,我要用个轿子。明天上午叫到河西胡同张家。”说话的是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像是识文断字的人家。
杜望抬起头,迎着阳光微微眯了眼睛:“我这儿的轿子,只请不租。请出去的轿子就是您自个儿家的,因此费用也比别家的轿行贵些,您如果想要租轿子,往西边走那头也有个轿行,是十来年的老店了。”杜望一笑:“还有,我是这儿的老板,不是伙计。”
中年人有些不忿:“你这是轿子还是神仙。城西的轿行我知道,年头太久,轿子都破烂流丢的。明儿是我们家老爷子七十大寿,要体体面面地去庙上柱香。你只管开价。”
杜望回柜台里拿了一个梨花木的托盘出来,上面整整齐齐扣了二三十个三分来大的小木盘,上面雕着古色古香的纂体,绘着各式各样的轿子。杜望似笑非笑:“既然这样,您就挑一个。”
中年人瞅得新鲜,翻出来一个紫绸轿子的牌子,杜望微笑:“紫气东来,明天早上河西胡同张家,我记下了。”
中年人离开,杜望捏着银元笑着对身边虚空处说:“看见了吧,有生意上门,你们两个别整天惦记着偷懒。”
二
次日,河西胡同张家。
张家老爷子张秉梅今年七十整寿,人活七十古来稀,老爷子却精神矍铄,头发虽然全白,一双眼睛却粲然有神。听闻张秉梅是当年的举子,虽然因为性子耿直在官场上没有作为,但一笔梅花画得极好,在当年的官市上都是卖得上价儿的。
杜望靠着已经停在门口的紫绸轿子看着张秉梅被儿子送出门,一边嚼着花生一边自言自语:“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可比他儿子要俊俏多了。”
杜望正要扯出个笑脸上去迎一迎,张秉梅的儿子张怀仁脸上突然动了怒,“你怎么还有脸来?”
杜望一粒花生米险些噎在喉咙里,连忙咽下去用手无辜地指了指自己,随后发现张怀仁看的不是自己,转身一望,只看见一个女人站在自己的身后。
那是个柔美如诗的女人,仿佛从江南最好的烟雨水墨中走出来。她的年纪其实不算小,大概三十上下,穿一身月白旗袍,越发衬得两弯月眉绰约生姿。旗袍上绣着的是折枝梅花,杜望看着那梅花,把花生递进嘴巴里嘎嘣一声咬开,又脆又响。
女人的脸微微白了一下,“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应该来看看老师。”她的眼光从张怀仁身上跳过去,望向张秉梅:“老师,我给你带了新做的打糕。”
张怀仁上前两步,劈手抢过打糕就要扔掉,被张秉梅摆了摆手拦住。张秉梅看着那女人,目光是慈爱的:“年前你信上说你到女中里谋了一份教职,干得怎么样?可还辛苦?”
女人眼眶含泪:“还是当年老师教我的底子,我再原封不动地教给那些姑娘。现在的小丫头们手指可灵泛多了,不像我当年笨得厉害。老师有空真应该来女中看看,看看那些孩子那些画儿……”
张秉梅点点头:“那就好,教书辛苦。你从小一到天冷就有咳疾,记得用一例川贝枇杷泡着放在讲台上,时不时喝上一口。”
张怀仁急了,扯住张秉梅的胳膊把他从回忆里晃出来,叫了声“爹——”
空气中有片刻的沉寂,张秉梅终于再开口:“东西我收下了,谢谢你。月生啊,我很好,你不用再来探望我这个老头子了。”
那个叫做月生的女人随着最后这句话眼泪一下子落下来打在脸颊上,她强自忍住,躬身轻轻称了一声“是”,转身离开。
父子俩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张怀仁还是忍不住呸了一口,低骂了一句:“不要脸。”
张秉梅嘴唇有些哆嗦:“是我不好,她也算是你个半个妹妹。”
张怀仁果断说道:“我哪里有这么不要脸的妹妹,爹你也真是……”话要出口张怀仁抬头看见杜望连忙把话咽了下去,回头对张秉梅说:“爹,您看轿子都来了。您一个人行么?”
张秉梅笑着挥挥手:“就是去庙里上个香,你赶快忙你的去吧。”
张怀仁答应了一声,冲杜望点了点头,匆匆忙忙地离去了。张秉梅撑着一根修竹拐杖稳步走向杜望:“小兄弟,怎么就你一个人,轿夫呢?”
杜望笑眯眯地:“轿夫去旁边粉店里填肚子了,一会儿就过来,外头风大,老爷子要不先去轿子里等着。”说着杜望从袖子里掏出一把花生递给张秉梅:“老爷子吃点么?”
三
那把轿子着实漂亮,通体暗光流转的紫色绸帘,绣满了姿态俊逸的祥云,绸帘旁边还滚着深灰色的风毛,相当的富贵大气。张秉梅卷起轿窗的缎帘跟杜望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杜望一边聊一边听张秉梅在轿子里面磕着花生,不由得笑起来:“老爷子牙口真好。”
张秉梅也笑:“我原来不爱吃的,当年被月生缠着要剥给她吃这些吃食,慢慢也就爱上了。”
杜望故意问:“月生是谁?”
张秉梅沉默了片刻:“是我的徒弟,她五岁学画,是我给她启得蒙,已经有二十几年啦。”
杜望却偏过话题:“老爷子坐稳了,咱们要起轿了。”
张秉梅坐在轿子里,只觉得轿子被轻飘飘地抬起,走的又快又稳。他好奇地想往外面看,却发现刚才打开的轿帘已经落下,怎么也打不开了。杜望带着的笑的声音在旁边响起:“轿帘我帮您捂着呢,当心走了风您着凉。”
张秉梅有些奇怪:“你怎么还跟着?”
杜望漫不经心地说:“这是我们轿行的规矩,出轿掌柜的要跟着,提防轿夫偷懒。”
随着杜望的话音落下,张秉梅听见了几声孩子的笑声,以为是路上的孩子也没有留意。轿子走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就落下,杜望的声音很松快:“老爷子,已经到了,下轿吧。”
张秉梅迈腿走出来,却一奇:“轿夫呢?”
杜望随手一指:“喏,不是在这儿么?”
张秉梅这个时候才发现在杜望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个胖乎乎的小娃娃,约莫五六岁模样,可爱得像是从年画里走出来的一样。张秉梅愣了愣,突然笑出声来:“年轻人就是喜欢开玩笑,轿夫该不会刚才没吃饱,刚停了轿子就跑哪儿去喝羊汤就大饼了吧。”
杜望笑而不答,反问道:“你去庙里求什么?”
张秉梅有些奇怪杜望为什么突然不用敬称,但他虽然文人出身却没有酸腐之气,豁达得很:“求家宅安宁,小儿怀仁事业顺利,一生平安……”他望着杜望真诚的眼睛,突然心底隐秘的愿望也脱口而出:“月生能够觅得良伴,此生幸福安乐。”这话一出,张秉梅突然觉得眼眶发酸,几乎要流出眼泪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连忙用衣袖遮住眼睛,嘱咐杜望:“你们在这里等我烧完香出来。”说完就匆匆转身离去了。
四
难怪人们都说新年新气象,张秉梅觉得今天自己格外地神清气爽。虽然说自己往常身体也不错,却从来没有这样松快过,连那十几级台阶也轻飘飘地就上来了,手里的修竹拐杖都显得累赘起来。
张秉梅从大师手里取了几柱香,到手有些奇怪。平时他来寺里上香,和尚们看他年纪大心也诚,给他的香也是格外加持过的。但这回拿到手里的香却是寻常的佛香,他还呆愣着,面前的大师已经冲他微笑了一下,示意他可以到佛前参拜了。
张秉梅将手杖靠在一边的柱子上,静心持着香三拜后将香端端正正地插在香池里,回身在蒲团上跪下,诚心念诵祈福,待到所有能想到祈福的都祈福到,连家里养着的一猫一狗一只正在下蛋的芦花鸡都祈福过后,月生的名字终于不可抑制地涌上嘴边。
张秉梅今年已经七十岁了,前二十年一直醉心诗书,二十八中举,仕途不顺,妻子早逝,感情也是薄淡,只留下一个儿子怀仁,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却也算让人省心。他这辈子没爱过什么人,除了月生。
月生是他朋友的女儿,受朋友的委托,他来为月生开蒙并传授画艺。那个时候月生不过五岁,小小的人儿坐在案边听不进去书,头便耷拉在几案上睡过去。他自己讲书讲得入迷,猛地抬头发现月生已经跟周公杀得正酣,一条晶亮的哈涎从粉嘟嘟的嘴角直直垂在书本上,湿成圆圆一个点。张秉梅又好气又好笑,觉得这样贪纵太对不起友人的重托,书卷便不轻不重地敲在月生的丫髻上。月生猛地惊醒,痛倒不怎么痛,只是十足地委屈,哇地一声就大哭起来。张秉梅从来没有带过孩子,更没有带过女孩,只能忙不迭地哄:“是先生错了,是先生错了。”那一年,张秉梅四十岁。
月生虽然不喜欢读书,但在画画上很有天分。张秉梅自己也是十分喜欢画画的人,于是倾囊传授。十七八岁的时候,月生的一笔傲骨梅花便画的很得张秉梅的韵味。张秉梅为了奖赏自己的爱徒,便在一边剥花生瓜子给她吃。月生一边飞快拈在嘴里,一边催促:“老师快点,老师剥地快点。”张秉梅那个时候已经辞官不做,整日在家画画斗鸟,闲来教月生几笔丹青。他那年五十岁出头,但因为身体很好,人又清瘦,望过去不过是四十岁的年纪,正是男人将一生所阅所看都敛在身上熠熠生辉的时候。月生也是花一样的年纪,不久便被父亲安排婚事。月生很不高兴,大闹着不要成亲要去读女大。月生劝服不了父亲,只能去求张秉梅。她心志坚定,甚至还将自己长长的麻花辫剪成了新式女性的短发,被人指指点点。张秉梅其实也心疼那一头长发,但在月生面前只说好看,还拗不过月生去劝友人放月生去读书。友人对张秉梅却是冷冰冰的:“女孩子大了就要收心,不赶快嫁人,难免做出败坏门风的事情,张兄说是不是?”
张秉梅被友人的目光刺得周身一凛,大家都是聪明人,话里话外的意思点出三分就足够。不需要友人多说,他就自己提出再不见月生。
月生再去见张秉梅的时候便被张秉梅谎称生病闭门不见,她提着张秉梅爱吃的打糕站在窗前,声音裹着委屈软软糯糯的:“老师,你见我一面啊。”
张秉梅心突然揪成一团,只能将整个人都裹进被子里。他忽然发现,友人的警醒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张秉梅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居然不知不觉喜欢了自己的学生。
五
月生见不到张秉梅,也不愿意被父亲抓回去成亲,于是连夜要逃出清平报考女大。她父亲驱马追赶,却在荒郊野外失足跌落马背,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断了气。月生母亲早逝,世上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她闻听消息回家奔丧,在父亲灵前痛哭着将女大的录取书撕得粉碎,一个头深深地叩下去,发誓此生绝对不离开清平。
月生父亲死后,族人站出来指责月生害死父亲,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将月生的家产瓜分殆尽。张秉梅怜惜月生孤苦,把她接到了家中居住。张秉梅一直想要为月生找一门好亲事,但月生有了那样的名声,一般的好人家都不愿意来提亲。即便有喜欢月生美貌和才华愿意不计前嫌的,月生也反对的很激烈。
月生很快到了二十岁,女人一过桃李年华,再不谈婚论嫁几乎就是要做一辈子老姑娘了。张秉梅终于忍不住对月生发了脾气,月生倔强地抬起下巴,眼泪一个劲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落下来,迫不过终于说出了口,自己不想嫁人,只想照顾老师一辈子。
那一年张秉梅五十五岁,其实这样岁数的乡绅纳一个二十岁的小妾,在邻里并不算是奇闻。但是张秉梅不愿意,他已经老了,很快就是一柸黄土掩过去,但是月生还年轻,他不能拖累她。张秉梅终于抖着嗓子装作糊涂地开口:“你想要照顾我也好,怀仁已经到了娶妻的时候,虽然没有大的作为,但是人品很好,更何况有我在不会亏待你的,不如你做我儿媳妇吧。”
怀仁那个时候走到门口,本来想要敲门给父亲请安,突然僵住了手,心砰砰跳了起来。他虽然称不上有多喜欢月生,但是冷不丁父亲要把一个漂亮姑娘说给自己做媳妇,还是有几分开心的。
月生的眼泪却终于落下来,声音藏着无尽的凄婉:“老师,你不会不知道。我是爱着您的啊。”
张秉梅手里捧着的茶杯突然落在地上,发出清脆刺耳的破碎声,怀仁僵着的手慢慢捏成拳,挥袖而去。
次日清晨,张怀仁命人把月生的所有东西打包好扔出了屋子。月生穿着一袭简单的竹布旗袍,剪短的头发已经留长了,松松地挽在脑后,只一双雾蒙蒙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张秉梅。
张秉梅站在张怀仁身旁面无表情,只淡淡开口:”我在朋友家里已经为你谋了一份西席的位置,你去教他们家女儿读书吧。”
赶月生走不是他的主意,但他了解儿子的脾气,也明白这其实对月生而言是最好的出路,他只能不动声色地为月生解决了衣食住行的大问题。但任谁看来,都会觉得他生气并且不屑。
六
张秉梅六十五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几乎真的要把他送去西天,怀仁甚至已经含着悲痛为他备好了寿材。月生闻讯赶来,扑在张秉梅床头痛哭,任怀仁如何辱骂都不离开。而当时昏迷了三天三夜的张秉梅居然在月生的哭喊中睁开了眼,只哑着嗓子哆嗦着说了一句:“月生来了?”
月生闻言攥着张秉梅枯瘦的手,只一叠声地哭着说道:“是我来了,老师,是月生来了。”
那一幕让张怀仁哑口无言,他床头侍奉多日,都抵不过一个小小女子的柔肠和眼泪。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对月生绝非简单的师徒之情。
月生尽心尽力照顾张秉梅了三个月,直到张秉梅康复后才销声匿迹地离开。只在逢年过节,托人送上一篮子打糕,自己并不出面。自从那夜戳破了不该戳破的窗户纸,她觉得自己无颜出现在张秉梅面前。张秉梅知道,月生是因为今年是自己的古稀之年,才亲自送上了打糕,却也没想到能撞见自己出门,还说上了话。
“请菩萨保佑月生,早日得觅良配,生儿育女,不要一生这样孤苦。”张秉梅从回忆中拔出来,念完祈福,深深叩了三个头。刚要起身,觉得脚面上一软,下意识就弯腰捡起了鞋子上一方秋香色帕子。
自己的帕子,似乎不是这个颜色?
有面色绯红的娇俏女孩儿凑上来,声音软软的:“多谢公子。”说着伸出自己柔软白嫩的手掌。
“啊?”张秉梅有些摸不着头脑,女孩更加害羞,指着那方帕子:“公子,那是我的帕子。”
张秉梅下意识将帕子递给女孩,女孩红着脸看了他一眼,还想要说话就被身旁的闺中好友拉走了。张秉梅隐隐听见那闺中好友对女孩低声说:“你胆儿真大。枉你看上了,可惜是个呆头鹅,白长得那么俊俏。”
公子,呆头鹅?
张秉梅愣了一会想起去拿靠在一边柱子上的手杖,但猛地抬头正好看见光滑的鎏金柱子上映出自己的倒影。
眉宇轩昂,身姿挺拔,分明是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
七
张秉梅仓仓皇皇地跑下石阶,连手杖都顾不得拾。两条腿松快有利,眼前的景致水洗过一样的清凉,鸟鸣花香,都较之以往梗清晰地被感知。张秉梅站在庙宇脚下,抬起的手腕上的皮肤是光洁的,露出充满生命力的青色血管。轩昂气宇让来往姑娘都投来爱慕的眼光。
杜望站在他面前,笑吟吟地,两个胖娃娃一边一个抱着他的裤管也是笑吟吟的。
张秉梅哆嗦着嘴唇,想要说些什么,问些什么。
杜望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唇边轻轻地嘘了一声,桃花眼眯成一条缝,轻轻说道:“广记轿行,欢迎惠顾。”
杜望、轿子、胖娃娃在人山人海的庙宇前瞬间都消失了,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惊奇,似乎从头到尾能看见他们的只有他自己。张秉梅呆站在原地,忽然觉得心脏砰砰砰地跳动起来。
他要去找一个人!
女中的放课铃刚响,欢快的女学生们就熙熙攘攘地挤出了教室。月生默默地将教具收拾好,离开的时候却不小心带翻桌子上的颜料盘,好好的月白袍子上顿时染上了五花八门的色彩。月生有些狼狈,正低头擦拭的时候,教室的门被嘭地一声推开撞在了墙上。
月生被吓到,抬头看见面前的青年男子。他粗重地喘息着,额头上大汗淋漓,手还扶在门把手上。看上去倒不像坏人,反而像是识文断字的。
月生便小心翼翼地问:“请问您是?”
没有回应,月生恍然大悟:“你是来找这里的学生么,她们刚刚放学,你去追还追的上。”
依旧不说话,男人只是盯着她,嘴唇哆嗦着。月生有些尴尬,顾不上身上沾着的颜料,抱着教具匆匆忙忙地擦过男人身边要离开。却在擦肩而过的瞬间听见男人颤抖的声音:“我找你,就找你。”
手腕也被捏住了。
教具撒了一地,月生挣扎着想要惊呼,却正对上男人的眼睛,一滴泪轻轻滑落,声音是温柔的慈爱的:“梅花莫要点得太重,当心伤了灵气。说过你那么多遍,为什么不听话?”
寂静的教室里,只听见两个人粗重的呼吸声,月生觉得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一定是有哪里不对。
但是这个人的眼睛,这个人的举止,这个人身上穿着的长袍,还有昔年学画的时候只有这个人会对她叮嘱的话。她用空出来的手紧紧抓住自己的领口,听张秉梅终于说出口的话:“我也是爱你,月生。”
月生哆嗦着嘴唇哭出声来:“老师……”
八
世间总有种种奇妙难以解谕,比如广记轿行,广记轿行的轿子,和广记轿行的杜望。
过了年,很快就到了元宵节,杜望躺在躺椅上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看着荣和二宝翘着朝天辫争着玩一个灯笼。那个灯笼是张秉梅亲自画的,跟月生登门送来算是谢媒礼。张秉梅喜欢孩子,跟荣和二宝玩得很是融洽。荣和二宝却更喜欢漂漂亮亮的月生,可惜月生看不见他们,只能根据张秉梅指点的方向冲两个奶娃娃温婉而笑。
杜望裹了裹毯子,“可惜啦,只有坐过咱们轿子的人才能看得见你们,不然也多个人陪你们玩。”
阿荣阿和齐刷刷地抬起头睁着大眼睛盯着杜望:“那请月生姐姐来坐。”
杜望噗嗤一声笑出来,顺手将荣和二宝拎到一边:“不是所有人坐咱们轿子都是好事儿,看你们今天抬轿辛苦,许你们再玩半个时辰。”
两个孩子刚要撅嘴表示不满,门就被嘭一声踹开了。
寒风裹挟着酒气钻进来,荣和二宝吓得连忙瑟缩在角落里。杜望倒是连屁股都没挪一挪,抬眼看着醉醺醺的张怀仁:“这不是张大爷么?小店打烊,若是请轿子,还请明天请早。”
张怀仁拎着酒罐子坐下,脸色潮红:“我只问你一句,怎样让我爹变回来?”
杜望眼睛眯成一线,“张大爷,你自命孝顺,张秉梅一生中可曾有一时半刻有这三天来得快活?而你斥责月生罔顾理法,又可曾自问自己心里是不是生了妒忌的心魔。”
张怀仁红着眼睛,大声吼道:“你若不说,我今天烧了你这邪性的铺子!”
杜望冷笑一声:“我杜某人的铺子,也是你这种人说烧就烧的。”
死一般的寂静,张怀仁知道杜望必然有奇异之处,反而不敢轻举妄动,但酒气上涌居然痛哭起来。杜望站起身,声音淡淡地:“凡事自有因果,当初是你自己走进我的铺子,亲手为你爹请得轿,如今又能怪谁呢。还请回吧。”
张怀仁走了,阿和吮着指头,糯声糯气开口:“阿和瞧着,那个大叔也挺可怜的。”
杜望噗嗤一声笑起来:“天下可怜人多了,咱们开轿行的可怜得过来么?”
话音刚落,一股子焦糊味道入鼻,杜望大惊失色,连忙拿过放在柜台上的轿盘,只见梨花木的托盘上原本放紫绸祥云轿的地方焦糊了一片。杜望忍不住咬牙:“好一个张怀仁,居然敢烧从我广记轿行请出来的轿牌!”
九
不到凌晨的时候,门被轻轻敲响了。
杜望是和衣睡在店里的,像是早有预料一样,他推开门,门外是白发苍苍的张秉梅。
他变回了年老的模样,甚至显得更老,映着身后大街上的积雪,满眼都是苍颓。
“月生还在睡着。”他轻轻说:“我没敢吵醒她,自己悄悄来的。过往的那几天我很快活,也不敢奢求今后天天都是那样的日子。杜老板,我只想求个说法。”他抬起眼睛,老泪纵横:“是苍天看不过眼了么,是觉得我张某人终究配不上月生吗?”
杜望手扣在门沿上,表情宁静:“张怀仁烧了紫绸祥云轿,这轿子原先是他为你请的,轿牌也一直留在他那里。是我疏忽了,忘记嘱咐你把轿牌要过来。”他顿了顿:“坐进紫绸祥云轿的人,会返老还童。因为轿子被烧,所以加诸在你身上的法力也消失了。”
张秉梅瞪大了眼睛,手也忍不住拽住了杜望的袖子:“这么说,杜老板只要再做一顶紫绸祥云轿,我就可以再次回到年轻的时候了?”
杜望有些不忍心,沉吟了一下却还是开口:“广记轿行,所有的轿子都不重样,请走就是请走,烧毁就是烧毁。张秉梅,我这里再没有让你返老还童的办法。”
张秉梅的手滑落,跌跌撞撞后退了两步。杜望想要上前搀扶,却被他躲开。杜望叹口气:“其实月生不会在意的,最开始你就是如今的模样。”
张秉梅苍老的手掩住眼睛,浑身都在发着抖:“但是我在意。”
张秉梅转身走了,在苍茫雪地里留下一串脚印和旁边孤单单的拐杖印。荣和二宝挤在杜望身边看着张秉梅的背影,阿荣更是扁了扁嘴巴就要哭。杜望有些头疼地捏了捏太阳穴:“你们说,月生什么时候会来?”
该来的总会来,月生来找过一趟张秉梅,发现不在便急匆匆地走了。三天后又再次来到广记轿行,容颜清减不少,一双雾蒙蒙的眼睛看见杜望就要往下掉眼泪。
杜望吓得一激灵,跳起来说:“别哭,千万别哭。我看不得女人掉眼泪。”
月生咬了咬嘴唇:“他不见了,三天来我翻遍了清平。最后才知道他平安回了家,但是对我闭门不见。我在他门口站了很久,他才让张怀仁递了张纸。”
折得整整齐齐的徽宣,简简单单的两句诗:“一夜冬风梅花落,明月何必自多情。”
杜望有些唏嘘,月生却噗通一声跪下来磕了一个头:“他不肯见我,也不愿意同我说话。我知道杜先生不是凡人,还请开释小女。”
杜望有些为难地抓了抓头皮,最终还是横下心蹲下来一五一十地将原委给月生说了。
十
广记轿行后院,一模一样的紫绸祥云轿。只轿帘上绣着的流云纹是反着的。
杜望看着月生:“你可想好了?”
月生的手抚摸着轿帘上的花纹:“我想好了。”
荣和二宝站在轿子的前后两侧,齐刷刷地放声大哭。阿荣便抽着鼻子说:“阿荣不哭,阿荣不哭,漂亮姐姐坐上轿子,就能看见阿荣,陪阿荣完了。”
阿和却一边抽噎一边说:“可是,漂亮姐姐坐上轿子,就不是漂亮姐姐了。”
两个人哭得心酸,累得杜望也抽了抽鼻子,连忙不好意思地说:“是荣和二宝舍不得你。”
月生一笑:“两个小家伙快别哭了,待会还要帮我抬轿子呢。等我出来就能看见你们了。”说着掀开轿帘毅然决然地坐了进去。杜望将手上转来转去的轿牌递给月生:“这是这个轿子的轿牌,你收好来了。只有一点,这个轿子原本不是柜上用来请的轿子,即便烧了轿牌,法力也不会消失。你真的想好了?”
声音从轿子里斩钉截铁地响起来:“想好了,还请杜老板起轿。”
依旧是一炷香的时间,轿子稳稳停在张府院内。
杜望声音有点滞涩:“到了,姑娘下轿吧。”
月生掀开轿帘,慢慢走下来,先是冲杜望一笑,又弯腰看着荣和二宝:“终于看见你们了,真可爱,跟老师说的一样。”
荣和二宝扁了扁嘴巴要哭,被杜望一边一个摁在怀里,只对月生说:“快些去吧,他等你很久了。”
月生点点头,慢慢拾级而上,在张秉梅的房门上轻轻敲了敲,无人应答,又敲了敲。
杜望远远地看着执着敲门的月生,似乎永远不打算开口一样。
张怀仁端着饭盘从穿廊走过来,好奇地停留在月生身旁,上下打量后谨慎开口:“请问,您是家父的旧识么?是哪家的老夫人?”
敲门的手突然停滞了,她没有转头,也没有搭理张怀仁,而是慢慢地又敲了敲门,终于开口。那声音是微微哑着的,颤颤巍巍的,属于一个花甲老妇的声音:“老师,是月生来了——”
绣着相反流云纹的紫绸祥云轿,不是返老还童,而是加速衰老。
张怀仁手里的饭盘当啷地砸在地上,他不可置信地后退两步:“你是月生?你是月生!!”
门吱呀一声开了。
垂垂老矣的张秉梅,望着门外同样垂垂老矣的任月生,顿时泪如雨下。
月生轻轻微笑,带动脸上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花,她轻轻说道:“梅有枯荣,月有圆缺,我总是会陪着老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