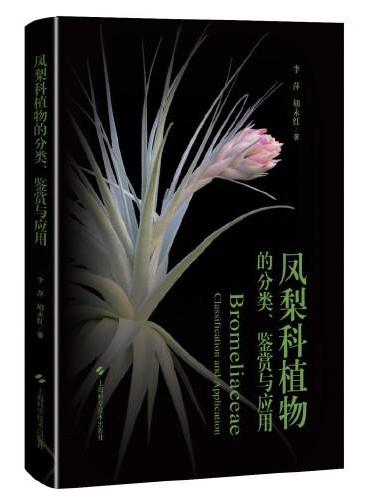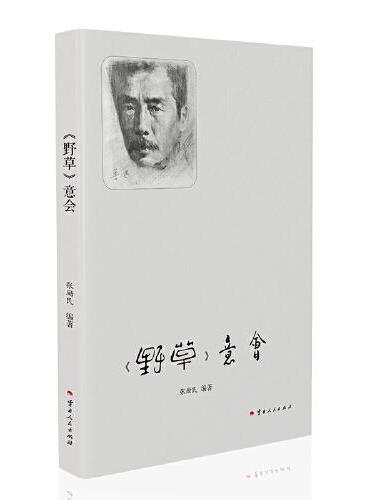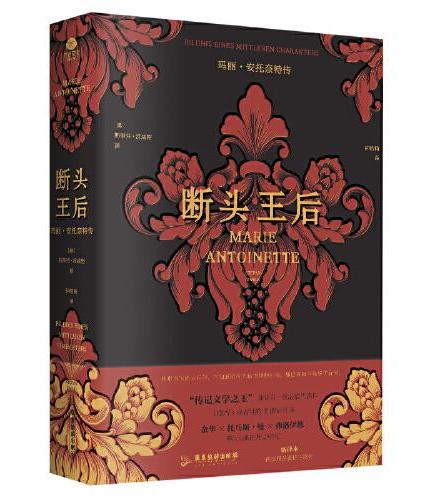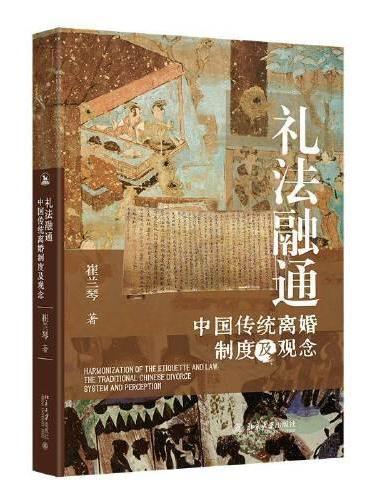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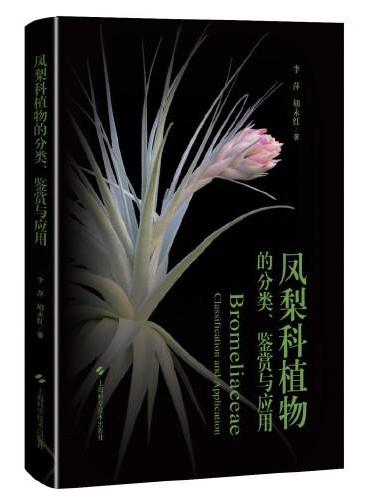
《
凤梨科植物的分类、鉴赏与应用
》
售價:NT$
22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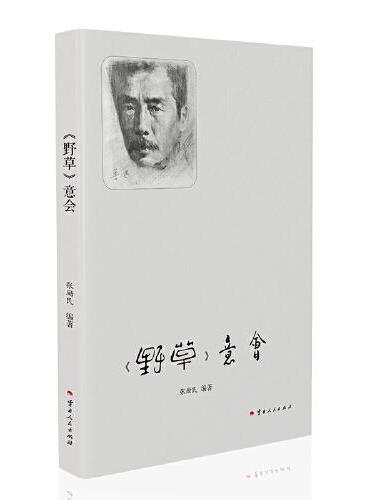
《
《野草》意会
》
售價:NT$
500.0

《
格外的活法
》
售價:NT$
403.0

《
大陆银行(全两册)(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续编(机构卷))
》
售價:NT$
28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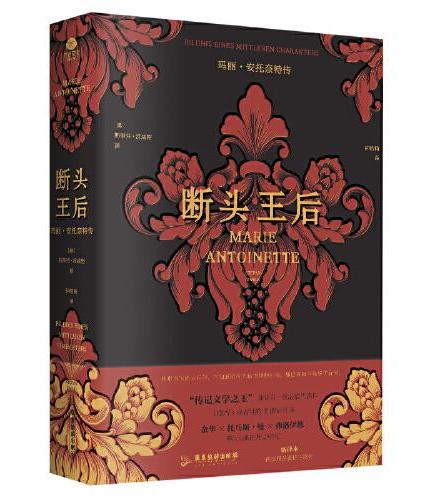
《
断头王后:玛丽·安托奈特传(裸脊锁线版,德语直译新译本,内文附多张传主彩插)
》
售價:NT$
286.0

《
东南亚华人宗祠建筑艺术研究
》
售價:NT$
454.0

《
甲骨文字综理表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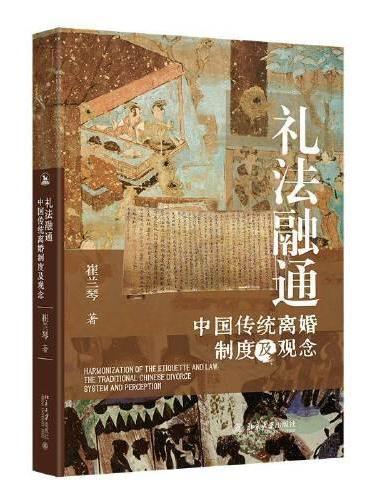
《
礼法融通:中国传统离婚制度及观念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语录摘录:
★一个伟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而我认为,牢记过去就意味着变态。背叛也许是弃暗投明,而变态却只能让他人和自己都受到伤害。
★所有的语言均出于一人之口。它证明:1. 语言先于世界;2. 世界被语言说出,凡说出的都存在;3. 语言永远无法说出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而诗歌永远在言说这个世界“没有的东西”。
★废话主义者认为,世界没有刚需。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任何一首伟大的诗歌,都可有可无。但诗人对世界却必不可少,因为他们永远在帮世界说话。
★诗就是废话,废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自由的愿望。
《天上的白云真白啊:乌青诗选》
|
| 內容簡介: |
|
这是一本关于思想和诗歌的著作,作者为当代知名诗人、“废话教主”杨黎。在书中,作者以谈话的方式,追随起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孟子、庄子等古贤的言说风格,从独特角度展示了杨黎对语言、写作、人生的“世界观”。何为废话?何为语言?何为诗歌?且听杨黎娓娓道来。对了,本书文采厚实,堪称废话经典
|
| 關於作者: |
杨黎,男,1962年8月3日生于成都。1980年开始写作,当代诗人、作家,废话理论的提出人和阐释者。
曾与万夏、于坚、韩东、李亚伟等一起发起第三代诗歌运动,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发言人。也与周伦佑、蓝马等一起创办过《非非》,是非非诗歌的领军人。本世纪后,进入网络,与何小竹、韩东、乌青等创办橡皮先锋文学网,提倡废话写作。现居北京和南京两地,是《橡皮:中国先锋文学》杂志主编,废话四中校长。
主要著作有《小杨与马丽》《灿烂》《打炮》《向毛主席保证》《一起吃饭的人》等。
|
| 目錄:
|
(代序)我写,故我不在:答李九如问
答朵渔十二问
杨黎在北京:答马策问
言之无物:答木朵问
关于《五个红苹果》:答马策问
关于《向毛主席保证》:答刘波问
谁明白我究竟在说什么:答吕露问
打开天窗说亮话:答张后问
废话里的杨黎:答于一爽问
我在写一本叫《废话》的书:答云南《生活新报》记者王雪玲问
活在中国,我已经做好准备:答美国诗人柏艾格先生问
我听到了语言的声音:答康宁问
|
| 內容試閱:
|
一、关于“废话”的诗学追问
李:黎叔,问你个“形而上”的问题,你热爱生命吗?你是否觉得生命是最高价值,是最大的“善”,因而也是诗歌的最高追求?
杨:我在16岁那年“为赋新词”、荷尔蒙爆炸,对生命的理解就是极度的欠缺和欠缺带来的痛苦。后来到了18岁,我恋爱了,品尝了男欢女爱,自然认为生命真的奇妙无穷。当然,在一次一次的高潮过后,我20岁了,30岁了,开始冷静地思考作为世界的意志和表象的语言――那个时候,我仅仅认识到语言即世界,而没有认识到是语言说出这个世界――我把“形而上”的生命置于绝对的逻辑关系中,而不是放在冲动的上下文里去解读,我要的是它的基本含义和绝对价值。但是,说实话,我没有得到答案。
即使在今天,我如果轻易地认定我热爱生命,视生命为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大的善,那么,我所表现出的见识与一般大众的见识也就几乎相似。相反,我如果理直气壮地认定我不热爱生命,那我的见识是不是就非常与众不同?只不过,这几乎相似的一般见识和与众不同的非常见识,在面对生命本身的基本意识上,完全没有正解和误解。这是我多年迷茫和伤感的主要原因,也是我诗歌写作的最终动力。
所以,热爱生命几乎是人类的基本觉悟,但绝对不是诗歌的最高追求,甚至,也许是恰好相反。作为废话理论,认识到生命的语言形态与生命的诗歌形态的相对差异,是我们理解废话的开始。我明白,这些并不是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本身我不敢回答,这些只是自我迷离和自问自语。
李:《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怪客》《冷风景》等诗歌呈现的就是“绝对的逻辑关系”吧?曾经作为一名中文系学生,我所学习的当代诗歌史完全无法触及你所描述的个人对生命理解的那种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显然是极其重要的。能否再详细谈一下当年你自己的这种变化――现在回头看来,那简直是一种“突变”。
杨:具体而言,《怪客》(1983)和《冷风景》(1984)之间刚好有一个“逻辑”差异,而写于这两首之后的《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1986)却填补了这一差异。
我曾经很骄傲,以为诗歌和诗人的自我迷离从《怪客》之后就结束了。“对于你来说我便是怪客”“对于怪客来说怪客便是怪客”的著名诗句,把1980年中期的青春思考,以及突然降临的“从重从快从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在这之后,我自动放弃了我的初恋(4年),还自动放弃了我的工作(银行),带着一个“专业”诗人的内心和几块散碎银子,开始为期半年的自我流浪。所以,当回到成都,回想起越走越寒的旅程,冷静面对文字(这很难),我写下了《街景》《小镇》《风向》等诗篇。
所有的经历都是语言的经历,没有超出语言之外的经历,所以,所有的冒险、体验甚至突变,也都只能是语言的冒险、体验和突变。到了1986年,我和小安结婚,我写了一系列短诗,《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是其中一首。我喜欢这些短诗,它们假装说了很多,其实又什么也没有说。
这段日子短暂、混乱,具体细节我都在后来的《灿烂》中均有描述。而还有一些,在我的小说《废话》里有许多。我其实喜欢谈自己的经历,但我不喜欢把它们和诗歌一起谈。我一直认为,两者彼此是分得开的。
李:古希腊人是赞美身体的,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人再次发现了身体之美与善。但是自从笛卡尔和卢梭发现了内心的价值以来,现代人似乎越来越推崇作为极端个人化心灵体验的身体,这与古希腊关注身体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你是否觉得独特的个人体验,是现代诗歌的基础?
杨:纯粹的身体其实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我即使在赞美它们的时候,我也是站在荷尔蒙的角度在赞美。如果没有性的诱惑,我对身体以及身体的整体和局部,说到底,我都没有兴趣。古希腊也好,文艺复兴也好,我无法在性之外感受到它们的任何冲动和震撼。
我也许会赞美上帝。对于女性从头到脚的每一个地方,啊,她的乳房、小腹、屁股、大腿和小腿,她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被安排得那样整洁、光华和充满弹力。但是,我也知道,百年之后,这些光华、整洁和充满弹力的地方,都会变为一块一块的白骨。赞美还飘荡在天空中,被赞美的身体已经灰飞烟灭。所以,佛教从来不赞美身体,认为身体就是一堆臭皮囊。不过,我喜欢这些皮囊没有臭的时候。
我不仅喜欢这些没有臭的皮囊,我自然也喜欢思想。皮囊的高潮与思想的高潮,我认为后者要更深入和更广泛。因为说到底,高潮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语言现象。只是高潮其实不需要深入,也不需要广泛。百科全书式的光芒,以及著名的我思故我在,让身体经过思想之后,成为一具仿佛不朽的“作品”。它让我想起木乃伊、舍利子和标签,个人体验代替了个人行为而失去原始快感。
这也许是现代诗歌的基础,只是这不是废话和废话诗歌的基础。对于一个废话主义者而言,所有的体验都是语言的发现。我们整个生命的展开,无论是以行为的形式还是思考的形式,都是语言事件对现实事件的还原。我们的思,是语言的逻辑演绎。而我们的在,是这一演绎的具体呈现。
在这个问题上,既然已经说到这里,我想我愿意补充两句。我的写作,不是在语言内部建立,而是在语言的系统上建立。我写,故我不在:这也是我在上面面对生命的选项时那么迷茫、那么伤感的原因。天苍苍,谁能出语言而不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