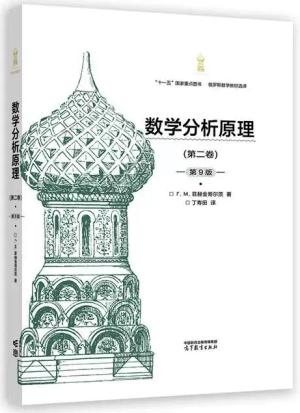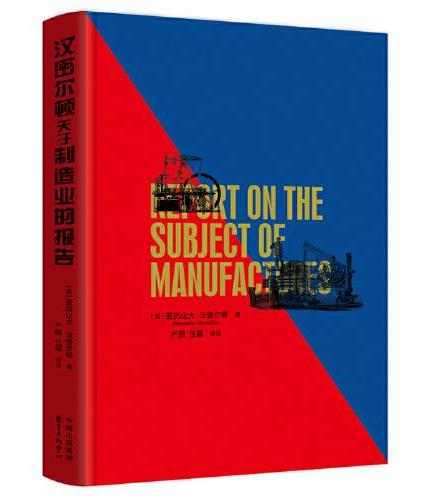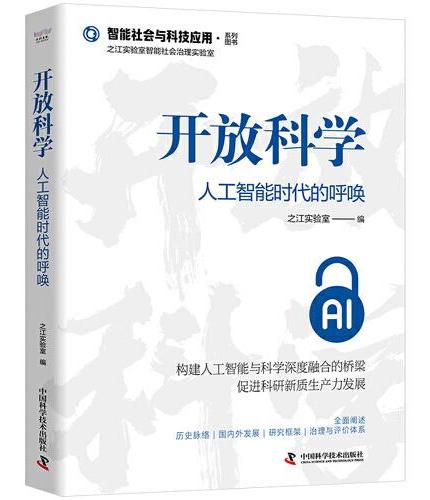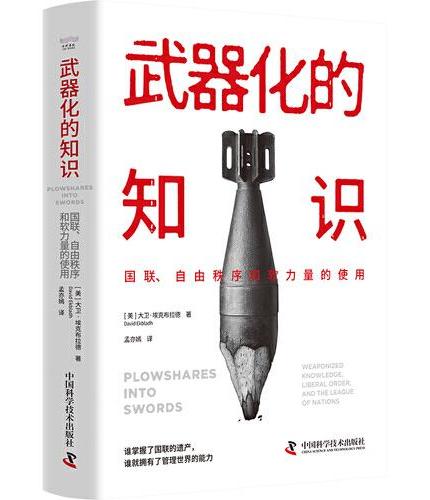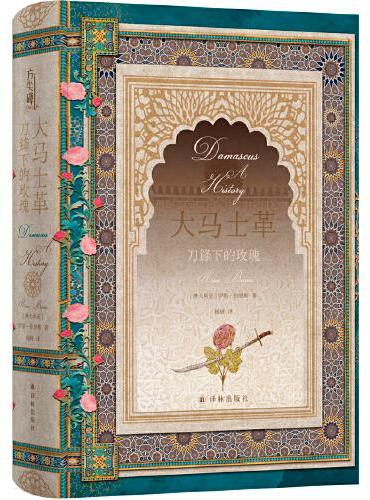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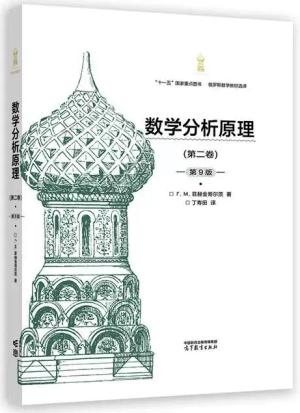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NT$
403.0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NT$
14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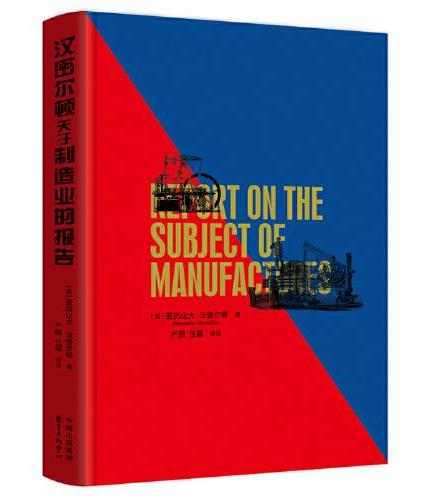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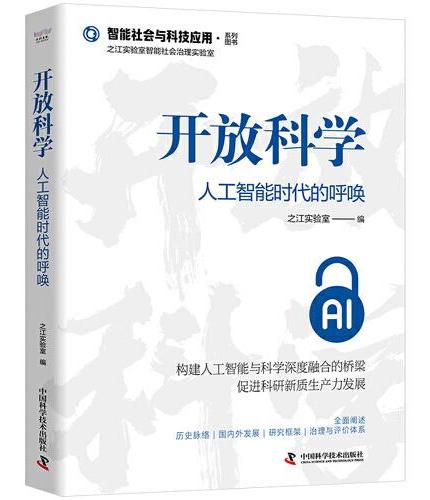
《
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
》
售價:NT$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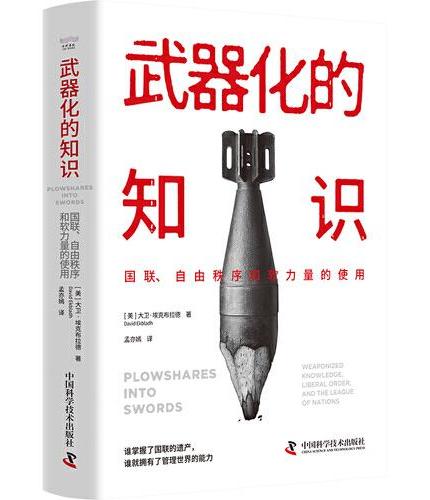
《
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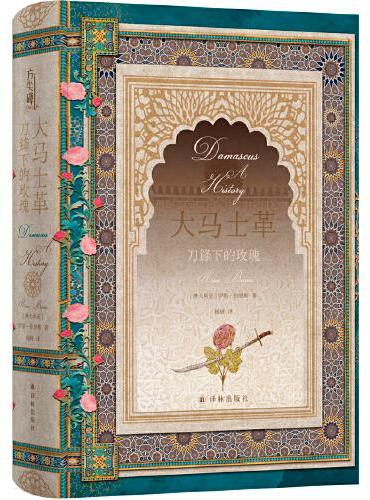
《
大马士革:刀锋下的玫瑰(方尖碑)
》
售價:NT$
607.0

《
造脸:整形外科的兴起(医学人文丛书)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1、本书称得上是一篇古代悬疑大作。以高妙的刑名之术以及复杂的断案过程作为本书的核心,类似于《大宋提刑官》,又融入了晚清历史风云、国仇家恨,以及朝野中外各种势力的权谋博弈、利益争斗;还有神奇玄妙的奇门异术以及地宫、迷宫的探险。既类似于《鬼吹灯》和《盗墓笔记》,又有徐克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狄仁杰之神都龙王》和电影《四大名捕》的影子。
2、作品跨度晚清和民国,各种清廷人物和军阀(如东北王张作霖)都在本书中以新的面目出现。作者脑洞大开,许多对历史的假设和猜测很有说服力。
3、作品越到后面越能体现出家国情怀,与日本势力的争斗是一大亮点,令年轻读者热血澎湃,有正能量。
|
| 內容簡介: |
一位大清刑名圣手,在破获各种鬼案、妖案之后,终于找到了所有魑魅魍魉的后台,也找到了自己的惊天身世。
一部旷世奇书《轩辕诀》,跨越时空出现在晚清至民国这个动荡的时代,激起了清廷高手、地方军阀、江湖英雄、日本势力的激烈争斗。
帝都的妖氛,骇世的龙图,轩辕的传人中日奇门异术的顶级高手决战于地宫之内、高山之巅。
历史,也许就在这一刻改写。
|
| 關於作者: |
|
茶弦,原名闫龙飞,男,80后,本科学历,现居杭州,美院专业画师。后向影视编剧道路发展,单独编剧或与他人合作编剧多部。闲来创作小说,尤其善于悬疑推理类。《轩辕诀》系列为本人最新创作的百万字悬疑小说鸿篇巨制。
|
| 目錄:
|
第一部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诡胎暗结 006
第二章 巧言令色 014
第三章 噬脑山魈 022
第四章 隔墙有耳 030
第五章 诡猴怪彘 039
第六章 明察暗访 050
第七章 封皮造畜 059
第八章 盲叟托孤 070
第九章 夤夜缉凶 080
第十章 影林荡寇 093
第十一章 锄暴诛恶 104
第十二章 罪有攸归 114
第十三章 立枷斩首 124
第十四章 破墓空棺 135
第十五章 驭咒驱尸 146
第十六章 异变陡生 157
第十七章 暗通款曲 168
第十八章 元凶逆渠 179
第十九章 左道旁门 190
第二十章 胄佩夹绢 200
第二十一章 固山隐卫 212
第二十二章 旌鼓如荼 226
第二十三章 抵牾扞格 239
第二十四章 岁聿其莫 255
第二部目录
第一章 红粉骷髅 001
第二章 厉鬼索命 013
第三章 钎针透颅 024
第四章 悬丝傀儡 036
第五章 法外施仁 049
第六章 天下熙攘 062
第七章 崇文海眼 073
第八章 水影墨池 084
第九章 李代桃僵 096
第十章 不速之客 109
第十一章 分庭抗礼 121
第十二章 铩羽而归 133
第十三章 内忧外患 145
第十四章 空村绝户 158
第十五章 泥犁炼狱 173
第十六章 地藏浮屠 187
第十七章 横夭虎疫 200
第十八章 泾渭殊途 218
第十九章 代马依风 236
第二十章 诸业空相 252
第三部目录
第一章 烛影冥妃 001
第二章 陈仇宿怨 017
第三章 泣血妖画 031
第四章 尔虞我诈 048
第五章 云谲波诡 064
第六章 神锋握胜 079
第七章 太阿倒持 094
第八章 力挽狂澜 109
第九章 生离死别 123
第十章 泪洒城关 139
第十一章 万象森罗 153
第十二章 薪火相传 168
第十三章 攫攘争逐 181
第十四章 鸠占鹊巢 191
第十五章 霸海双蛟 202
第十六章 木牛流马 212
第十七章 鬼手奇工 223
第十八章 峥嵘铁舰 234
第十九章 天书再现 245
第二十章 龙光遽奄 256
第四部目录
第一章 凶宅妖兽 001
第二章 喉啭拟音 016
第三章 虎麟臣相 029
第四章 红颜祸水 043
第五章 冤家路窄 057
第六章 百密一疏 070
第七章 阴差阳错 085
第八章 扬刀立威 098
第九章 凿壁龙门 112
第十章 地窟谜骸 125
第十一章 山海合盟 138
第十二章 居心叵测 151
第十三章 命途多舛 162
第十四章 引蛇出洞 174
第十五章 聚啸成兵 187
第十六章 阴阳至尊 199
第十七章 伯仲难分 211
第十八章 两败俱伤 224
第十九章 香消玉殒 236
第二十章 折戟沉沙 250
|
| 內容試閱:
|
浩浩愁,茫茫劫。妖氛起,金瓯缺。山河表里,人鬼莫辨。人亦有时殇,鬼亦有时灭。一缕忠魂无断绝。成耶败耶,尽在轩辕。
楔 子
福祸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正邪之分,仅存一念。业从心起,心为业用。曲直是非,司命有辨。报应无差,毫厘不爽。
夫积善者,天赐绵寿,寿终正寝。寝延余荫,泽被子孙;然累恶者,天夺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殃及后世。
康熙六十年 京郊门头沟
夜阑深宵,万籁俱寂。空荡荡的戒台寺中,却是灯火通明。佛堂大殿上,盘坐着一名清癯的老僧,僧袍褪至腰际,袒露出嶙峋的上身。
老僧背后,跪着个小沙弥。小沙弥手里攥一把利刀,浑身战栗,涕泪潸然。
老僧面色铁青,低声喝道:还等什么?动手吧!
师父小沙弥声泪俱下,泣道,寺里都空了你你跟我一同下山吧!师父!求你了下山逃命吧!
阿弥陀佛。老僧宣声佛号,慢慢合上双眼,既入空门,便应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师少时,累犯杀孽,心魔已定,又能逃往何处?苦海无涯,恶业无穷,是非因果,终需偿还就于今夜,了结这桩宿怨吧!
可是我小沙弥悲痛欲绝,我下不去手啊!
慧存!那老僧神情一凛,厉色道,本门所传的《轩辕诀》,论透物理,参尽天机;为师背后所文的密图天书,更是至关玄秘,此二物,实为一体,绝不能落入暴徒手中。一旦二物被夺,这世间定然再掀大乱。事不宜迟,速速动手!
慧存伤绝无措,嘴中嗫嚅:师父逃吧
我意已决,断不可改。老僧一弓腰,后背豁然亮出。割皮之后,你便从密道下山,从此隐姓埋名,将《轩辕诀》好生保管!
谨遵师父教谕徒儿纵豁出性命,也不让歹人得逞!慧存擦一把眼泪,将手中尖刀哆嗦着抵在老僧脊梁。
一抹殷红,沿刃渗出。老僧身子剧烈一颤,口中牙齿咯咯作响。
师父!
不碍接着割!
慧存泪如泉涌,继续战战游切。
豆大的汗珠,不断从老僧额上淌下。而那件半褪的僧袍,已是血污尽染
当剥下那块粘连的皮肉,老僧早已疼瘫在地,不省人事。
慧存大哭着,替老僧止住血,而后撬开老僧牙关,塞入一颗药丸。
一炷香工夫,老僧缓缓苏醒,面色惨白,无半点血色。慧存已替他包扎好创处,重披上一件洁净僧衣。
师父慧存紧握老僧的枯臂,经书已取下一并放入褡裢中了
好老僧点点头,气若游丝,不知大还丹的药力能否撑到那刻咳咳扶我起来吧
慧存闻言,赶忙相搀。老僧借着力道艰难地爬起,重新盘坐在蒲团上。
待喘匀了气,老僧将手一抬:你去吧
慧存扑通跪地,泣不成声。半晌,才重重磕下三个响头,挥泪出了大殿。
与此同时,一乘藏青软轿,正在寺外崎岖的山道上蜿蜒前行。几名身着黑衣、怀揣利刃的精壮汉子,紧紧护在轿边。
轿中人面白无须,年约不惑。他眉头紧锁,不苟言笑,一双冷峻的寒眸中,透出几丝焦灼。
陡然间,一个轿夫踩上块碎石,脚底一个趔趄,就朝旁边摔去。
眼瞅着软轿便要侧翻,一名壮硕的黑衣人飞扑而至,稳稳托住轿杆,将轿子轻轻落于地上。
那轿夫吓傻了,怔在原地不敢动弹。
废物!黑衣人右臂一甩,寒光划过。轿夫喉头喷出一道血花,身形晃了两晃,便一头栽倒路边。
黑衣人踢开死尸,赶紧朝轿而跪。奴才该死!让主子受惊了!
罢了,轿中人挑起轿帘,冲黑衣人道,图伦,将尸首面目刮花,别留下痕迹!
嗻!图伦答应一声,便去处理死尸。
须臾,尸首草掩停当。图伦又跟上软轿,继续护行。
眨眼光景,轿子抵至山门外。轿帘一掀,轿中人走将出来。随行的黑衣人,皆拔剑执刀,冲着寺内虎视眈眈。
主子,图伦一指大雄殿,人在里面!
进去看看!轿中人一挥手,众人便鱼贯而入。
金革击撞,殿中顿时杀气腾腾。而那老僧,却依旧闭目端坐,仿佛未曾听见周围动静。
单九龄!见老僧从容入定,图伦却按捺不住,主子在此,还不速速跪拜?
阿弥陀佛。老僧双手合十,二目微睁,贫僧方外之人,眼中只认得佛祖,不识什么主子。
你图伦脸色一变,当即扬刀。整个大殿内,剑拔弩张,杀机四起。
不可妄动!轿中人斥住图伦,踱至老僧面前,单九龄,你我一别,应有十余载吧?可惜啊当年尚虞备用处的统领,却沦落成一个颓朽老僧!
善哉善哉,老僧淡淡回道,贫僧虽老,雍亲王却是暴戾如常
这轿中人,竟是康熙四子雍亲王胤禛。
放肆!图伦挺然上前,举刀便砍。
雍亲王眉宇一冷,暗蕴风雷:退下!
图伦一惊,赶紧收住刀,讪讪地退避一旁。
单九龄,雍亲王扬起脸,言语间满是孤傲,本王此番的来意,你应该清楚吧?
老僧道:王爷想必是听说了那得轩辕者得天下的传闻。
不错!雍亲王道,世间风传:秘诀轩辕,得之可问鼎天下。哼哼,本王虽不知那《轩辕诀》究竟为何物,不过却已打听到,它现在就存于你单九龄的身上!
老僧颔首道:事到如今,也无须隐瞒。贫僧守护那《轩辕诀》,已有数十年了。
果然在你身上!雍亲王眼睛一亮,这样吧单九龄,只要你把《轩辕诀》乖乖交出,辅佐本王登掌大宝,那过往之事,本王便一概不究了。你日后的富贵荣华,也自会不少!
王爷差矣,老僧摇了摇头,叹道,想我出家之人,青灯古佛,素斋寒衣,岂会希图那般浮名虚利?贫僧生平所疚,便是曾为粘杆处鹰犬唉那《轩辕诀》业已毁去,劝王爷尽早收手,莫做下那等杀父弑君、谋朝篡位的不臣丑事
笑话!雍亲王嘴角一抽,面上有些挂不住,本王天庇神佑,外有年羹尧,内有隆科多,何患社稷不掌?要取那《轩辕诀》,也不过是想瞧瞧,它是否有传闻中的那般神妙。况且,《轩辕诀》就文于你背上,焉有毁坏之理?!
不愧是雍亲王,刺风探秘,举世无匹。老僧微然一笑,不置可否,然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能否容贫僧多说几句?
雍亲王怫然斜睨,齿间迸出一字:讲!
老僧咳嗽一阵,缓缓说道:王爷此时,初具九五之相。可此相极浊,不似真龙之气。若是强求,必罹大祸,虽得虚华一时,却不得长久一世。恐将耗损大清基业,殆尽千秋祚运到那时,外夷频欺,群豪蜂起,牝鸡司晨,江山转易
满口疯话!一派胡言!雍亲王勃然大怒,快!将这逆贼拿了!剥皮取诀!锉骨鞭尸!
图伦等黑衣人得令,呼啦一声全围上前来。图伦熟谙老僧根底,知他是粘杆处首任头领,极难对付。所以一出手,便绝不留情,抡起长刀,照着老僧顶门,就要劈头砍下。
金风飒飒,刀气纵横,那老僧却波澜未惊,只是垂头盘在原处,不闪不避。
图伦大惑,生生收招,将刀锋一偏,架在老僧颈上:耍什么花招?有本事使出来!
没想到连喝三声,那老僧依旧未动。图伦用刀背一格,那老僧身体,竟轰然倒地。
众人皆惊,忙近前察看。发觉那老僧,早已气绝身亡。
割皮!雍亲王暴跳如雷,把《轩辕诀》全剥下来!
众黑衣丝毫无滞,一拥而上,将尸身翻起,几下扯碎了僧衣。
当看到那血肉模糊的后背时,图伦目瞪口呆:主子《轩辕诀》被割走了!
什么?!雍亲王一怔,继而咆哮道,找!把这寺里寺外,翻个底朝天!找不着,就放火烧寺!绝不能让《轩辕诀》外泄!还有!火速召集所有粘杆拜唐!将这方圆百里的光头,不分和尚秃子,统统抓来鞫审
熊熊烈火,映红了半个山头。望着山顶冲天的火光,慧存肝肠寸断。他紧紧身上的褡裢,血泪盈襟,含恨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次年十一月,康熙帝骤崩于畅春园。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随即颁布遗诏。雍亲王夤夜登基,克承大统,改年雍正。
雍正四年,廉亲王胤禩、固山贝子胤禟,因结党妄行数罪状,被削王夺爵,除宗圈禁,更名阿其那塞斯黑。
同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获罪九十二条,被赐自尽。
雍正五年,隆科多获罪四十一条,打入诏狱。次年,死于禁所。
十三年,雍正帝暴毙圆明园。垂危之时,雍正帝留下秘嘱,着后人继续寻访《轩辕诀》的下落。然此后历代皇帝千寻百访,却终无一获。
公元一八五一年,落魄秀才洪秀全率教众起义,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清廷之创颇巨。
公元一八六一年,西太后叶赫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女主临朝。
公元一九〇〇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联合远征军犯侵中土,由京津攻陆,一路破竹。紫禁城沦陷,帝后仓皇西逃。此后,清廷一蹶不振,积弱衰疲。列强割据,刀兵四起。哀鸿遍野,狼烟风滚
第一章 诡胎暗结
光绪三十一年冬 京城 前门外大栅栏
漫天的雪,足足下了两日。直到掌灯时分,这才稀稀拉拉的停将下来。悦来客栈前,掌柜老王耷拉着脑壳,蜷蹲在门口石阶上,一袋接着一袋,咂着铜嘴旱烟锅。微翕的三角眼中,满是通红的血丝。
雪封了官道,阻了过往的商贾。偌大条街上,连个狗影都寻不到。愁云中一弯瘦月,洒下些许惨光,斑斑驳驳,落映在皑皑覆雪上。
栈内油灯如豆,瑟瑟颤抖,不时爆出几个灯花,将掌柜的身影拖得老长。
啊
一声妇人哭啼,从内堂骤然传出。那动静听着无比诡异,挠肝钩心、凄凌揪腑,如同野猫闹春,又似濒死呻吟。
咳咳咳!一口浓烟呛在嗓里,王老掌柜顿时气短。额上青筋爆起,两只枯眼翻睁,皱纹堆垒的面皮,都憋成了酱猪肝。
费力半天,王老掌柜吐出一口黄痰。浓痰出喉,他便身子一软,瘫倒在台阶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缓了好阵子,王老掌柜这才撑爬起来。浓汁般的浊泪,顺着脸上沟壑吧嗒吧嗒地滴落。在脚底浮雪上,溶出密密麻麻的小坑洼。
突然,王老掌柜狠抹脸颊,冲着空荡的街头破口大骂:进财,你个杂毛崽子还不回来啊内当家的就要死了!找个接引顺产的婆子,你却从早找到黑!你个崽子是不是让狼叼了啊
老天爷你不长眼啊!王老掌柜猛地站起,狂张二臂,呼天抢地,这辈子我修过桥,补过路,并没做伤天害理的恶事啊!你已夺了我送终的儿,难道还要抢我传宗的孙吗?!老王家三代单传,就余下这点骨血了求求你!求求你开开眼、发发慈悲!别让我们王家断了根、绝了香火啊
一番歇斯底里,激恼了本以为死绝了的狗。大的、小的、胖的、瘦的,皆是没命地狂吠。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撕破了重重夜幕。
街头牌坊外,影影绰绰透出一团黑影。离得近了,才发觉是一驴二人。那驴腿拐唇豁,背上还驮个婆子。老驴慢吞吞地挪着蹄子,发出沉闷的嗒嗒声。前头牵驴的,正是步履蹒跚的进财。
狗崽子!可回来了!王老掌柜抽疯一般,朝前奔窜迎上。
扑到近前,王老掌柜泪涕也顾不得擦,一把抢下婆子,就要往内堂里拉。
别别扯那婆子面无血色,嘴里含混不清,歇口气先歇口气
老姐姐,先救人吧!儿媳妇就快撑不住了!王老掌柜不由分说,死拽硬拖地,将婆子拉进内堂。
进财累脱了相,刚哆哆嗦嗦地拽住驴嚼子,没承想一个踉跄,一头撞上了驴腹。连人带驴,双双砸进了雪窝子里,半天动弹不得。
躺在雪上,进财大口喘着粗气。溻透的热汗融着雪水,连同呼出的热气,化成一袭白雾,笼罩得一片模糊。
内堂里,王老掌柜端过一个海碗。老姐姐,喝口姜汤活活血脉,这就救命吧!
婆子没二话,接过碗大灌一口。姜汤下肚,婆子脸上的霜色退淡些许。她打个嗝儿,又使劲搓搓手:走去看看吧
王老掌柜一听,赶紧引着婆子去里间,婆子颠着小脚跟在后边。
来到里间,王老掌柜将门帘子一挑,却迅速扭头,将脸别在一边。
那婆子见状,只当他避着儿媳临盆。可当她朝屋内一瞥,竟倒抽一口寒气!
里间内,炭火烧得滚旺,烘的人面皮生疼。可那婆子手脚冰凉,宛若在三九天跌进了冰窟窿里。只一会儿,那婆子便觉两膝发软,一个立不住,一屁股蹲坐在地上。
炕上铺条褥子,一个浑身精赤的妇人,正仰在上面。只见她肚腹高高隆起,两条白花花的腿大分着,双臂耷拉在炕沿儿,无力地垂着。妇人脸上,神情十分古怪。她双眼半眯,唇角微微挑起,露出一抹诡笑。黏稠的涎水从嘴边淌出,腥膻无比。鼻孔里、耳朵里、牝户里都汩汩冒着黑血,将褥单染得一片狼藉。
突然,那妇人上身一挺,腰肢开始如水蛇般曲扭,随着剧烈的抽搐,妇人手脚频频乱摆,好似与人交媾。
啊!
一声尖叫从那妇人喉里钻出。这尖声撕心裂肺,却又混着些浪吟,化成一根硬利的芒刺,朝耳朵眼里直直扎来。
那婆子打个急战,胃里一阵翻腾,干呕几下,扶墙爬起,颤巍巍地便想夺门而逃。
老姐姐,你要去哪儿?王老掌柜眼疾手快,将婆子死死扯住。
那婆子捂着胸口,骇得语调都变了:接接不了!你家这活我接不了!
使不得啊!王老掌柜扑通跪倒,老泪纵横,这情形是和别家生产不同可这可这大小两条命,都攥在老姐姐手上了啊!老姐姐!你行行好吧!我老王家就剩这点盼头,若再有个闪失这一家子就全毁了啊
那婆子两眼紧闭,嘴唇死咬,任凭王老掌柜如何苦求,只是拼命地摇头摆手。
实在没辙了,王老掌柜将脸猛地一抹,瞪着血红的眼珠,一字一顿道:这样吧!老姐姐若肯帮忙,这客栈的产业物什,就划一半归你!我再去庙里求个长生牌位,天天用香火供着,祈求老姐姐多福多寿!老姐姐我求求你了!要是再不出手那两条命可就眼睁睁断气了!
说罢,王老掌柜俯腰磕头,脑袋把砖地撞得咚咚直响。
那婆子一瞧,犯了踌躇。眼下这情形,倒还真不好走。甩手出了这门,那母子必死无疑。传将出去,街坊四邻怕要戳自己脊梁骨。名声臭了,以后谁还敢找她接生?再者说了,王老掌柜又许下了重诺。悦来客栈买卖不小,一半的资财,足够自己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了!
想到这层,婆子暗自琢磨:想我做稳婆数十年,接生过的婴孩,少说也有百八十个。什么死胎、畸胎、怪胎,啥样的没见识过?难道还单怕了这光腚妇人?!更何况,只要接好这桩活,养老的财帛便有了着落!得!自古富贵险中求,接就接!
婆子利欲熏心,胆气竟稍稍壮起来。她瞥一眼王老掌柜,硬起头皮,一步一挪地靠近炕前。
权衡再三,婆子终于卷起袄袖,吩咐王老掌柜取些热水,再抱些洁净被褥来。
见婆子松了口,王老掌柜哪敢怠慢?冲将出去,转眼备齐所需。因这事棘手,婆子顾不上男女忌讳,留下王老掌柜,候在一旁帮衬。
婆子草草净手后,这才回到炕前摆弄。她定定心神,从炕头上拿只枕头,塞垫在妇人腰下。紧接着,又使了把劲,将妇人双股分撑。
见妇人肚皮下蠕动得厉害,婆子微皱眉头,冲那妇人道:自个能使上劲儿吗?
可连问数次,那妇人始终没应,一双半睁的红眼中,散出两道幽怨的寒光。仿佛那剧烈的胎动,并未给她带来半丝痛楚。
婆子打个激灵,额头冷汗直冒:她她怎么没动静了?
王老掌柜急道:许是疼迷糊了老姐姐,你紧着点儿啊!
别催,婆子抹一把汗道,我再想想办法
那妇人使不出力,婆子只好去捋她肚子。可一捋之下,那胎儿竟在腹内蹿动起来。婆子慌了,后背全被冷汗打湿。一个没生下的胎儿,怎会有这般大力?无奈老掌柜催促得急,婆子只好强忍慌惧,继续揉捋。
渐渐地,像有了些成效。那胎儿在腹内动了几动,慢慢朝宫口移去。婆子大喜,忙又加劲按压。不一会儿,妇人牝户里面,便探出一截小指。
坏了!婆子心下一惊。若非婴头先出,必定要难产。拖得久了,那婴儿恐怕会憋死。
情急之下,婆子顾不了许多,握起那截小指,便往外拉。可一握之下,那婆子便觉掌心一疼,低头看去,手掌竟被划了条血口子!
婆子脑中嗡鸣,登时就蒙住了。那截小指上,居然生着锋利的长爪!
眨眼工夫,一个毛乎乎、血淋淋的怪胎便破腹而出。那怪胎一抖搂,把身上污血糜肉,甩溅了婆子一脸。怪胎虽小,却活动自如。沤湿的皮毛上不断滴着黏液,散出冲天的恶臭。
突然,那怪胎睁开眼,露出幽绿的双睛,紧接着怪嘴龇咧,发出阵阵阴笑,口中盘错的獠牙,十分的狰狞。那骇人模样,简直就是阿鼻炼狱里爬出的恶鬼!
嘎嘎嘎嘎嘎那鬼胎怪叫几声,后腿一蹬,便纵上婆子肩膀。
婆子两眼爆血,吓了个魂飞胆丧,喉咙咕噜两下,便直挺挺地砸倒在地。
猛然间,那鬼胎狂躁起来。身子一展,浑身骨骼咯咯乱响。鬼胎一低头,看到婆子那灰白的死眼。它凑上去嗅嗅,前爪在胸前狠挠,嘴里 呜呜低吼着,流下长长的馋涎,好似觅到了珍馐美味。
鬼胎一张口,一条青舌头吐了出来。只一舔,便将婆子眼珠卷在了嘴中。无珠的眼眶边,也连皮带毛的舔去一条,露出了白生生的骨茬儿。
几口嚼下肚,那鬼胎浑不知饱。它抬起左爪,抠住婆子脖颈。右爪比着颅腔划割一匝,又插入眼窝。只一掀,便揭开了天灵盖!
棕的皮、红的肉、白的骨,还有那淋漓的鲜血,将沟回纵横的脑髓托衬得无比粉嫩。鬼胎咽了口唾沫,开始慢慢舔食。它微眯着眼,纵情吮咂。利齿间不时地淌落下髓液,洇得身上白斑点点。
王老掌柜骇破了胆,白眼一翻,顺墙瘫倒在地,晕死过去。
半袋烟光景,鬼胎似乎吃饱了,嗅了嗅昏迷的王老掌柜,狂叫两声,便逃得无影无踪
约寅牌时分,进财被泡宿尿憋醒。进茅厕放完后,他才记起:昨晚被其他伙计搀进屋,自己倒头便呼呼大睡。记得昨个内当家初产,也不知 生了个丫头还是小子。按说这会儿应该有喜信了。
越想,进财心里头越是惦记,索性转去柜上,打算瞅瞅动静。
到了柜上,却没人守着。往常这会儿,王老掌柜早在那里拨拉着算盘清理账目了。
还在内堂候着?进财一面嘀咕,一面朝内堂走去。
这进财是个弃儿,被王老掌柜从外头捡来。喂食给饭,拉扯成丁,算是王家的义子螟蛉。所以进财不拿自己当外人,抬脚便入了里屋。
门帘一挑,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便扑头盖脸地袭来。进财赶紧掩了鼻子,朝里面看去。
只一眼,纵他是个七尺汉子,也僵在了当场!
那接生的婆子,头残颅破,血乎乎的剩着个空腔子。内当家的不知死活,赤条条的瘫在炕头。王老掌柜歪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狼藉触目,腥臭逼人。进财的胃里活似翻浆,一股股酸水拨滚搅涌,差点把隔夜饭倒出来。他干呕几下,摇摇欲倒,赶忙扶住门框,勉强撑住身子。
那婆子不必说,内当家的身上僵凉,显然也是不活了。进财哆嗦着,朝老掌柜胸前一摸,试着多少还有口热乎气,连忙爬滚出屋,大唤着帮搭救命。
伙计们闻声赶来,都骇得瞠目结舌,半晌才回过神来,一条毯子盖了内当家,又七手八脚地把老掌柜抬出来。
消息传开,客栈里炸了锅,闹哄哄的,乱成一锅粥。王老掌柜被送入里厢后,进财领着人忙活起来。有掐人中的,有熬参汤的。一个杂役脚长腿快,便跑去报官。那血淋淋的产室,断没人敢靠前,只是找了俩胆儿大的远远守着。
折腾了半天,王老掌柜终于醒来。进财抹把泪脸,急忙询问情由。可王老掌柜似乎吓傻了,只是咧着嘴,抖抖索索,说不出一句利整话。进财贴耳过去,这才隐约听见鬼胎二字。
天一放亮,客栈门前便围来一群妇人。一个个叽叽喳喳,冲着客栈里指指点点。
吴婶,听说了吗?昨天夜里,这客栈里头死人了!
可不是嘛!说是闹了妖精,把王家上下,一股脑儿地全啃净了!就连那条护院的黑狗,都被掏空了肝肺肠子!
吴婶你又唬人!悦来客栈里压根儿就没养狗
啧!你还别不信!那狗就养在后院里,之前我可瞧得真真的嗐!说什么狗呀?说妖精!那妖精眼珠子跟铜铃似的,嘴一咧,有这么大个!血盆大口一张能咬掉一个人头!
快别说了!我听得直发毛瞅我这些个鸡皮疙瘩这事到底真的假的?
那能有假?都是客栈里传出来的信儿说是老王儿媳妇临盆,结果就招来了淫妖你们是不知道那淫妖把孩子嚼了还不算完,又当着老王的面,把他儿媳妇压在炕上,活奸了两个时辰哪!啧啧下面都弄烂啦!
妇人们正嚼着舌根儿,身后却爆出一声大喝:死老娘们儿,净他娘的胡咧咧!
妇人们回头一看,原来是报案的长腿杂役,正引着顺天府的几名差人赶来。
都散了吧!别堵着门口!延误了官差办案,你们谁也担不起!
长腿杂役一面叫骂,一面推攘,在人堆里硬挤出条道。几名差人见状,忙入到客栈里。
来验案的官差有三:一名仵作,两个衙役。
衙役一个红脸,一个高瘦,皆大咧咧的,一脸骄横。那仵作倒是和颜悦色,双目之中透着精明。进屋后也没闲着,东一眼、西一眼的不住打量。
红脸衙役来到柜台,抓起账簿翻几翻,随手扔下。他一抬头,瞥见柜上存着坛老酒,二话不说,剥掉封泥。
真他娘的香!坛中酒气扑鼻,红脸衙役美得直耸鼻子。他也不取碗,端起来咕嘟咕嘟灌了几口。
喝过了瘾,红脸衙役一抹嘴,打个酒嗝儿。呃这里有主事的没?去喊过来!
您老稍等,这便去叫。长腿杂役应了声,转身入了后堂。进财一听,有些犯愁。眼下老掌柜这副样子,哪还能去回话?没奈何,只得自己赶去应付。
来至前厅,进财忙冲官差拱手:几位官爷受累!我家掌柜受了惊,现在还下不来炕,官爷有什么话,只管问小的吧。
聒噪什么?高瘦衙役一瞪眼,喝道,先把事说明白了!
是是是,进财慌道,是这样:昨个儿我们内当家的要生产。掌柜的一早便让小的去找稳婆。谁承想,这两日风雪紧,附近的稳婆死活不肯出门。没办法,小的又到医馆打听。可连跑了十来家,也都因雪大不出诊。纵是磨破了嘴皮,也没人愿意跟来。最后,一个研药的伙计看不过,偷偷告诉小的,说张家堡子有个稳婆,手艺不错。只要酬钱给得足,三河也能去得。小的一听,赶紧奔了张家堡子。等找见那婆子,许了三两银子,那婆子便痛快答应。小的不敢耽误,接上婆子便回赶。路上风雪太大,迷得都张不开眼。等赶到客栈,天已黑透了。老掌柜迎着那婆子,就请进了内屋。小的累脱了力,便去睡了。哪知这一觉醒来,就出了这桩惨事没别的,求官爷们多多费心,好替我们东家报仇雪恨!小的在这厢,给官爷们磕头了!
说着,进财便流泪跪倒,冲着差人叩头不止。
那仵作点点头,开口道:难得你这份忠心,头前带路吧!
进财抹泪起身,引着官差来至内堂。
刚到门口,便闻到一股血腥,仵作皱了皱眉头,抬脚进去。这仵作验尸查骨,见惯了寻常凶案。可乍眼瞧见屋内场面,竟骇得寒毛倒竖。那双摸过无数臭尸的手,不自禁地抖将起来,额头豆大的冷汗,也不住地往外溢。他忙打开随身挂匣,取出一瓶丸药,急急服下。这瓶丸药,唤作定神丸,由高人秘方调配。这定神丸清神醒脑,专镇尸秽污毒,故仵作常备身边,不离左右。
服下定神丸,仵作不似之前那般慌乱。他俯下身子,开始拾骨验尸。
地上血肉横飞、脑浆四溅。婆子的残尸,缺了颗眼珠子,另一颗也是半瘪,挂着睛脉拖在脸上。头盖骨被切开,断口十分齐整,也不知被何种利器所伤。左边锁骨窝,戳下几个深深的血洞。右臂肩头,也显出紫黑的瘀痕。半干的浆血,凝在外露的骨茬儿上,格外刺目。
仵作又来到炕边,揭开蒙在妇人身上的毯子。那妇人手足僵硬,已然气绝。观其死状,十分可怖。尸首下身撕裂,腹间塌瘪,一节脐带也被拖出了体外。股间的伤口,像被犁过一样,两侧的皮肉都朝外翻着
这二人死因甚异,仵作也不敢贸然开尸。只好收起验具,另行打算。
官差商议了一番,决定暂将尸首收厝,运回府衙再做定夺。念王老掌柜惊惧不起,便容他缓上一日,明早再过堂问话。
当尸身被抬出时,围观的妇人都吓得尖叫连连。不多会儿,悦来客栈闹鬼的事,便不胫而走,转眼传遍了大街小巷。一时间,满城风雨,惶惶不安
他人如何心惊肉跳,暂且按下不表。只说经了一昼夜,王老掌柜虽然两眼水肿,神志倒还恢复不少。
翌日清晨,顺天府便过来提人。进财赶忙迎上,从门口牵来套好的骡车,将王老掌柜搀将上去。待王老掌柜坐稳,进财一甩鞭子,同着差人,来至顺天府衙门。
下车后,进财搀住王老掌柜,由官差带着,领入了正堂。
正堂上,分列两排衙役,手持堂棍,威风凛凛。当中危坐的,正是顺天府尹。只见他面透忠英,颔蓄长髯,一身正气,不怒自威。身后漆屏上,绘着海水江崖、红日初升。头顶匾额,高悬肃清畿甸四个烫金大字。府尹道声升堂,两边衙役便齐喝威武。
王老掌柜眼眶发烫,不由得双膝跪倒。求青天大老爷做主啊草民的儿媳死得冤啊
老汉休得哭嚷,府尹拍一声惊堂木,将事情始末,与本府一一道来!
进财跪在一旁,也悄声劝道:掌柜的,先别哭了,把事说明白了,大人好替咱们做主
王老掌柜点点头,拭去眼角老泪:大人,这事说来一言难尽啊昨晚儿媳妇临盆,跑遍了四九城,才请来一个接引婆子。没承想儿媳妇竟生下只妖怪,害死了生母,啃吃了稳婆许是嫌我人老肉酸,才没对草民下嘴
府尹眉额一拧,喝道:公堂之上,岂能信口雌黄?!这朗朗乾坤,何来妖孽?莫不是你老眼昏花,将凶手误看成鬼怪?
不不不!见府尹着恼,王老掌柜急忙说道,大人,真不是胡言乱语,确实是有妖怪呀!那可怕的情景草民这辈子都忘不掉唉现在想来,草民的儿媳妇,还真像是怀了鬼种啊
府尹暗暗忖度:这老汉看着木讷老实,不像在乱言欺人。可他口口声声说是有鬼,莫非里面另有隐情?
想到这儿,府尹清清嗓子,开口道:本府掌印数载,克己奉公,断案无计。既然判得了官司,就能断得了鬼神!若真有妖异作祟,本府拼尽全力,也会替你做主!你不必心慌,详述端倪,到时自有公道!
先谢过大人了!王老掌柜叩个头,面露难色,草民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大人见谅则个
讲!
由于此事关系着家风声名,草民斗胆,请大人屏退左右,才好启齿
府尹稍加迟疑,便道:也罢,且随你。听完再做理论!
说完,府尹一挥手,让众衙役退下,只留刀笔书吏,记文录案。
见王老掌柜年岁不小,府尹吩咐取张杌子,让他坐着回话。
王老掌柜叩谢一番,由进财搀着,在杌子上坐定。才待开口,堂下突然闯进一人。进财眼尖,一下便认出,正是昨天那名仵作。
那仵作径直奔向府尹,低声耳语起来。府尹沉吟半晌,这才将头一点。仵作见状,朝着府尹一揖,又急匆匆地退了。
等仵作走后,府尹冲着堂下说道:王家老汉,你且在此宽坐。待会儿开堂另审,你再和盘托出!
还没等王老掌柜开口,府尹与那书吏已转至后堂不见,偌大的公堂上只剩下进财与他大眼瞪着小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