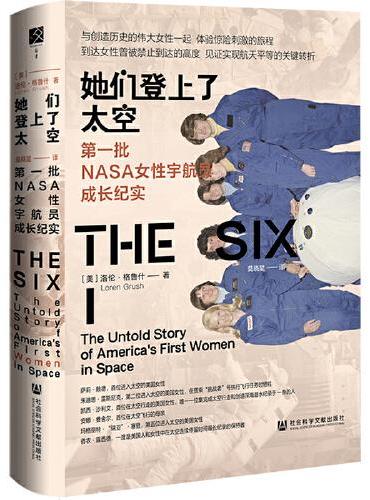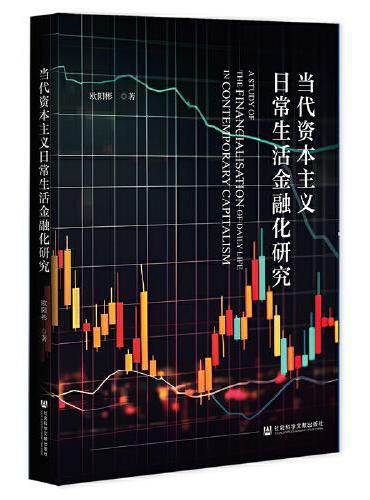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NT$
35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NT$
485.0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NT$
551.0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NT$
1010.0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NT$
40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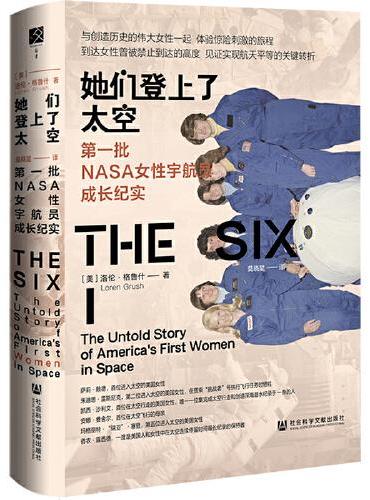
《
她们登上了太空:第一批NASA女性宇航员成长纪实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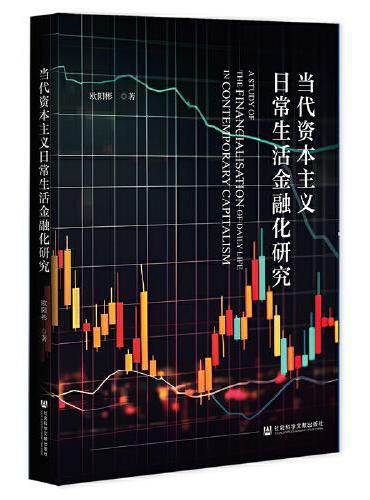
《
当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金融化研究
》
售價:NT$
653.0
|
| 編輯推薦: |
★《本托的素描簿》共收录约翰伯格创作的近70张全彩素描水彩画,是伯格本人作为画家的一面在中国内地的首次集中展现。首次向中国读者全面展现伯格了不同于艺术评论家、摄影理论家,以及散文小说家的画家身份。绘画,是伯格创作生涯的起始,如果不了解伯格的绘画,不了解他对绘画的沉思,将难以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伯格的思想。
★ 约翰伯格在《本托的素描簿》一书中,以亲身示范的方式,精彩地呈现了他对自己以往有关观看、艺术、反抗等观念的整合与凝聚。我们不仅能从字里行间和每一幅素描中读出艺术与当下生活的纠缠与共生,读出伯格始终如一的对社会、文化、政治的介入意识,也能读出伯格潇洒却并不放浪的文学想象力。
★ 全书穿插了约翰伯格从斯宾诺莎的两本著作《知性改进论》和《伦理学》中摘录出来的文字,它们与伯格的素描、文字相映成趣,共同演绎了大师与大师的精彩唱和。与此前的大部分艺术写作不同,伯格富于创造地将哲学著作中相对晦涩和冷峻的论说,与自己创作的、更加轻盈的素描与文字并置呈现,而不是以评论的口吻援引它们。这样的处理手法不仅没有引发某些令人尴尬的失调症,反而促使两种风格迥异的表达之间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彼此辉映、妙趣横生
|
| 內容簡介: |
命运常常具有几何图形版的规则,但却没有可以用来表示它们的名词。素描可以代替一个名词吗?约翰伯格
在《本托的素描簿》这本书中,对素描这项活动能把我们带往何处、指向何物有着深刻体悟的约翰伯格,将互为参照的文字与素描缝制在了一起,并以这样的方式与17世纪荷兰哲学家贝内迪克特斯宾诺莎对话。
小名叫本托的斯宾诺莎平素很是喜欢画画,据说他会随身携带一本素描簿,用来画下眼见之物。但在他去世后,这本素描簿却没有出现在他的遗物清单中,遂成为一个失落的传奇。对于关注绘画的伯格来说,他常常会想象斯宾诺莎这个人文主义思想的同路人是如何用他的哲学之眼观察事物的,想象他会在这本簿子上画下什么样的素描。如此的想象也激发了伯格自己的创作灵感。于是,在一本被伯格认定是本托的素描簿的簿子上,他同时以素描和写作两种方式,与生活在几个世纪前的斯宾诺莎展开了隔空的交谈。
在伯格看来,素描是一种探测方式。人类*初产生素描的冲动,乃是出于他们的实际需要:搜寻某物,测定位置,安放某物,安置自身。毫无疑问,这种对素描富于启发性的理解,是伯格的创作之所以发生,也是他与斯宾诺莎的对话之所以可能的主要前提和关键提示。此次《本托的素描簿》全新中文简体版共收录伯格65幅全彩素描水彩,以及由素描引发的内省文字。正是在文字与素描的相遇中,在伯格的思想与斯宾诺莎的思想的相遇中,他们变成了彼此的替身。
|
| 關於作者: |
约翰伯格(John Berger,1926-2017)
英国艺术评论家、小说家、画家和诗人,192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44至1946年在英国军队服役。退役后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学习。1940年代后期,伯格以画家身份开始其创作生涯,于伦敦多个画廊举办展览。1948年至1955年,他以教授绘画为业,并为伦敦著名杂志《新政治家》撰稿,迅速成为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之一。
1972年,他的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在BBC播出,同时出版配套的图文书,遂成艺术批评的经典之作。小说《G》为他赢得了布克奖及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2008年,伯格凭借小说《A致X:给狱中情人的温柔书简》再次获得布克奖提名。2017年1月2日,约翰伯格在法国安东尼去世。
|
| 內容試閱:
|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大约十年前,内拉(Nella)在莫斯科,和一些俄国的老朋友们待在一起。有一天她路过一家旧货商店。也许,它的自我定位是古董商店。那时,莫斯科的居民正在变卖家里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因为工资和退休金制度已经崩溃。你可以在街角买到这些家当。对于内拉来说,世上任何一个城市的二手商店都像词典一样无法抗拒。她走进去打开页面。这次她找到了一幅画。布面油画。一件小幅静物,画的是一些红色菊花。
她买下了。画的落款是:克勒贝尔(Kleber),1922。价格比一首歌还要便宜。便宜得多。
回到巴黎,她不知道应该把画挂在哪儿。似乎什么地方都不合适。画上处处都有剥落的盐粒大小的颜料碎片,可以见到底下的白色画布。内拉有个习惯,摇摆不定的时候,她就等待困惑自行消失。通常确实有效。于是,她用一个黑塑料袋把画包好,搬到车库,放在那些被人遗忘的包裹中间,这些包裹装着衣物、书籍和其他无法归类的东西。收拾之前,她曾把画指给我看,当时我想:19世纪室内花卉,没有一丝变化,一定是俄国的。菊花倒在狭窄的隔板上。后面立着一个空的玻璃花瓶。待会就要插进花瓶?还是刚刚取出,准备丢掉(就是太早了点)?不管怎样,还是留在车库里吧。
光阴荏苒。某年车库被淹。内拉把画从袋子取出,摆在客厅的不同角落。颜料剥落得更厉害了,露出了更多白色画布。现在,画的破损已经变得比画面本身更加引人注目。
我没法把它扔掉,上周内拉对我说。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会试着修复这画。可它根本没法复原,破损太多,我又不会修画。我只能把白点涂上颜色。
于是我着手进行。我在白色浅盘上调色。但是,我有好多年没用过油画颜料了。画素描时,我用墨水或丙烯。油画颜料的调色方式非常特殊。你在浅盘上一笔一笔地寻找某种音色,但是,只有等你涂到画布上,才会发现颜色是否符合你在寻找的声音。
等待修补的剥落白点数以百计。阴影中的花卉呈现黑绯红色。吉他棕色是壁架下面木头抽屉的颜色。贝壳灰色是架子所在角落的墙壁。光线下的花瓣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品红。所有这些都暗示着这是一个狭小的房间,但很可能,在1922年,有许多人住在里面。
我一心修补这些白点,一个接着一个,完全忘了时间。时间感的丧失,带来个体意识的松弛。一笔接着一笔,一色接着一色,我正趋近一个系统的景象,而这景象却是属于一双此时仍非为我所有的眼睛。这双眼睛在其他地方。
我在观察1922年9月下旬的一天,一间沐浴在午后光线中的小屋,扔在角落搁板上的鲜花。内战已经结束。可是饥荒仍然四处蔓延。现在,几乎所有白点都补好了。
夜间,我好几次起身去看这幅油画。或者,不如说是去看画中的小屋角落。我不能就这样把它们丢在那儿。不管是架上的鲜花还是油画本身。你仍然能够看到原来曾是白点的那些地方。麻子疤痕。我必须把它们恢复到更好的状态,回到那个9月下旬的午后,可怕的寒冬来临之前。
我应该更加无拘无束地画。可是我在画的时候,又不能把它当做我自己的作品;它是克勒贝尔的。这一事实是如此严峻,是我先前料想不到的。可是如果我不能自由作画,我就无法恢复那些光线。
次日清晨,我继续画。我坐在那儿,油画搁在我的膝盖上,旁边桌上放着调色盘。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以哀悼为主题的诗,其中有几行描写了一朵掉在人行道上被鞋踩碎的菊花。这几行诗写于二十年之后。静物中的绯红菊花此时仍然毫不知情。
我想知道画上都有什么,这一渴望鼓动着我,使我可以大胆尝试。我发现,光线洒在小屋角落两堵墙壁和半打丢下的花朵上,就像来自某个不可思议的遥远未来的某种承诺。
大功告成。它就在那,克勒贝尔作于1922年的一幅油画。
某个时刻暂时得以保存。这一时刻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所以,承诺有可能是面向过去的吗?
一个人无论为任何事物的意象所激动,即使那物并不存在,他也会认为它即在眼前,并且只有当那物的形象与过去或将来的时间的意象联结在一起时,他才会想象那物是在过去或将来。所以单就一物的意象的本身而论,不论和过去、将来或现在的时间相联系,它总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不论这意象是属于过去、将来或现在的事物,它所引起的情绪或身体的情况是一样的。故不论这意象是属于过去、将来或现在的事物,它所引起的快乐或痛苦的情绪是一样的。
《伦理学》,贺麟译,第三部分,命题十八,证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