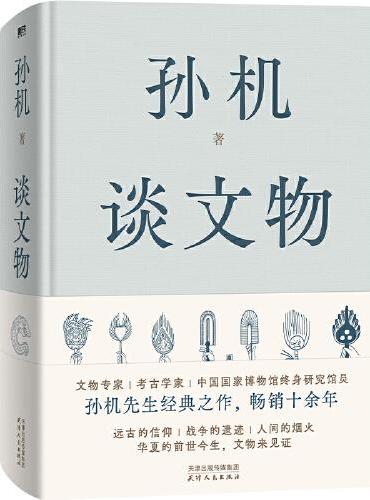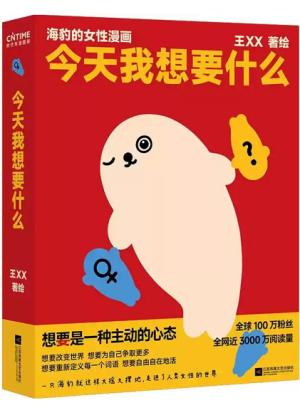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孙机谈文物
》 售價:NT$
551.0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NT$
254.0
《
讲给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 售價:NT$
245.0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NT$
500.0
《
埃勒里·奎因悲剧四部曲
》 售價:NT$
1426.0
《
今天我想要什么:海豹的女性漫画
》 售價:NT$
347.0
《
日常的金字塔:写诗入门十一阶
》 售價:NT$
347.0
《
税的荒唐与智慧:历史上的税收故事
》 售價:NT$
500.0
內容簡介:
由王超的小说《去了西藏》改编剧本的《寻找罗麦》影片即将于2018年 4月全国公映,同名图书同时出版。故事讲述了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小说讲述了中法两个男人之间一场不为人知的感情。在一段象征涅槃与救赎的莲花之旅中,已经走向人生终点的罗麦与一直在路上的赵捷,对于他们来说,怎样的结局才是完满。抑或,只是留下长久的叹息,以及对将来的美好向往。
關於作者:
由王超的小说《去了西藏》改编剧本的《寻找罗麦》影片即将于2018年 4月全国公映,同名图书同时出版。故事讲述了一个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小说讲述了中法两个男人之间一场不为人知的感情。在一段象征涅槃与救赎的莲花之旅中,已经走向人生终点的罗麦与一直在路上的赵捷,对于他们来说,怎样的结局才是完满。抑或,只是留下长久的叹息,以及对将来的美好向往。
目錄
Part 1 自序
內容試閱
一个韩国影评人曾要我写下我最喜爱的十部电影,我答应了,想了好几天。那是拍完《安阳婴儿》一年以后,正要写《日日夜夜》的剧本。这个提议让我有机会搜寻脑海里的世界电影,也自然让我回忆起过去的观影时光。最早还是青少年,喜欢搜集电影连环画。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在中国的电影院开始能看到日本、欧洲及南北美各国的电影,且是《远山的呼唤》《最后一班地铁》《德克萨斯州的巴黎》《W 的悲剧》《苔丝》《沙器》之类的文艺片,不像现在那时,影片公映后,还会很快出版该片的连环画,卖得也好,我爱搜集,像一本编辑好的电影剧照。80 年代,南京的电影院真让人怀念。欧式古典建筑,却莫名的有东方气质流露,磨旧的大理石台阶前,成排的法国梧桐遮挡着骄阳,或雷阵雨。最近,从《读书》里得知,20 年代,南京中山陵及民国首都规划总设计者吕彦直早年留法,深受 19 世纪后期和20 世纪前期欧美建筑界流行的以巴黎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艺术思想的熏染。后又回归中土,将西方古典翻译成中国现代建筑。而其实,巴黎的电影院规模都不大,也不繁复,二十年后,我才有体验,南京的大华、胜利两家电影院临摹的实在是法式歌剧院 。那时,我常在大华电影院华丽而陈旧的立柱半穹隆屋顶宽阔的前厅排队买票,或有时散场后,等外面的雨停。记得法斯宾德的 《莉莉玛莲》我连看了三场,引起售票员的注意。匈牙利名导萨博的奥斯卡外语奖影片《靡菲斯特》,最近我才淘得碟片,二十年前,在南京的电影院里,我连看两场,印象深远。我还看到过斯皮尔伯克的第一部长片《决斗》,讲两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的疯狂追逐,绝少对话,好看的哲学,我也是连看了三场。若干年后,得知此片曾风靡欧洲。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在家待业,后来又成了一名工人,而作为一个文学青年,80 年代没读大学,肯定是郁闷的,所以,南京的电影院就成了我的私塾。我是 1979 年,上高中时在新街口邮局里发现有本叫《电影艺术译丛》的杂志,是今天《世界电影》的前身,80 年就改为现在的名字了,我每期都买。1981 年夏天开始,我让我母亲在工厂里订。这样,我就算是接触到世界电影史了,那时,该杂志很注重史论的译介。但我也就是爱看,没有钻研。我好像是带着一种玩赏的心态,或为一种嗜好,或如今天的哈韩族追逐时尚般追逐那上面的剧本,理论及国际电影的新旧动态。它既强烈地吸引我,又仿佛与我隔了一层,犹如隔岸观火。因为,那时与自己的生存更密切的还是写诗。作为一个与工厂环境格格不入的文学青年,电影就像是自己的梦工厂,而诗则是氧气罐。80 年代又是观念大爆炸的时代,但哪怕自己是一名工人,我也跌跌撞撞地跟在这个潮流的后面,生啃那些新出版的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及西方马克思。这样,我就在每月阅读《世界电影》的时候,自然地爱上伯格曼,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戈达尔,及阿仑雷乃、罗伯 - 格里耶、杜拉斯等,当时被称为现代派的一些导演,因为他们的电影剧本恰恰是那些我还一知半解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形象阐释,我如入迷宫般兴奋的晕眩,直到若干年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看到这些导演的电影胶片或录像时,才如被熟人领出了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