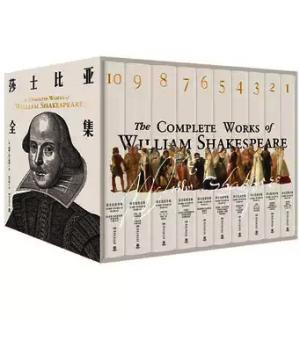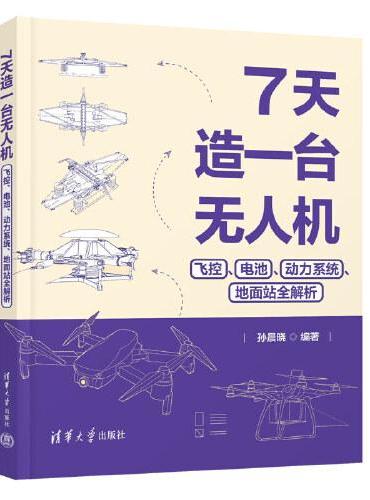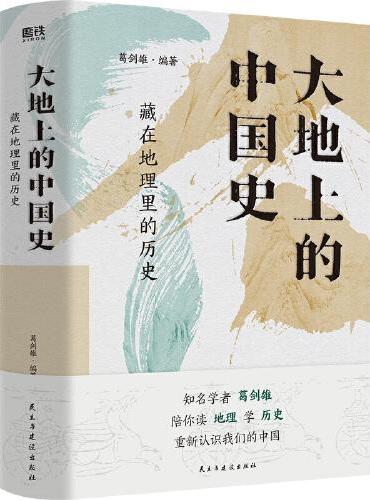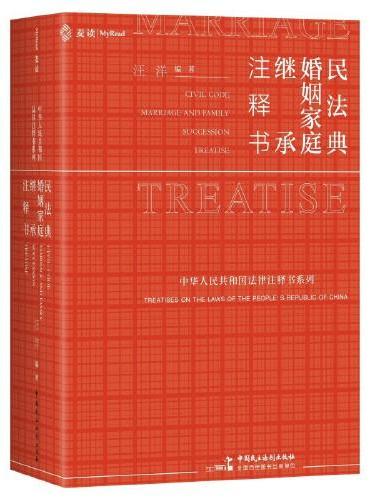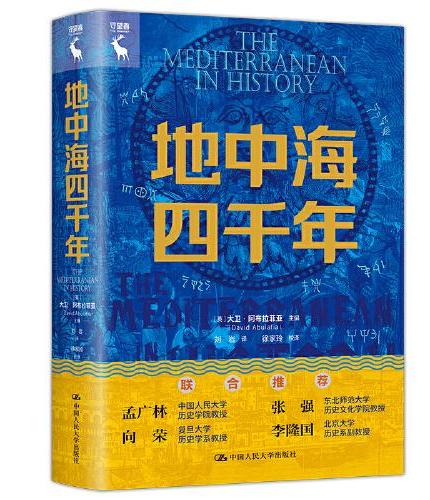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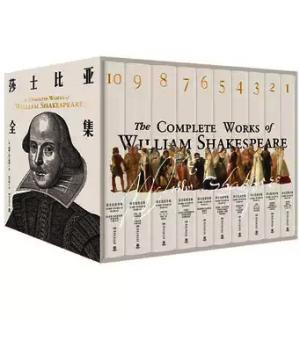
《
莎士比亚全集十卷
》
售價:NT$
274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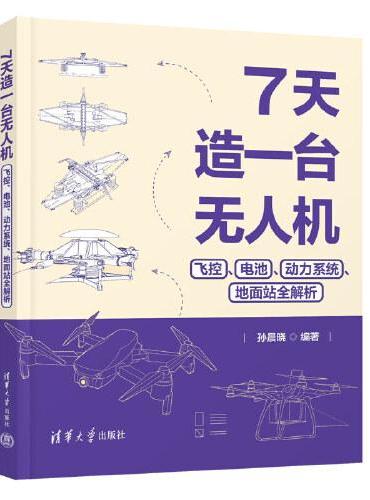
《
7天造一台无人机:飞控、电池、动力系统、地面站全解析
》
售價:NT$
3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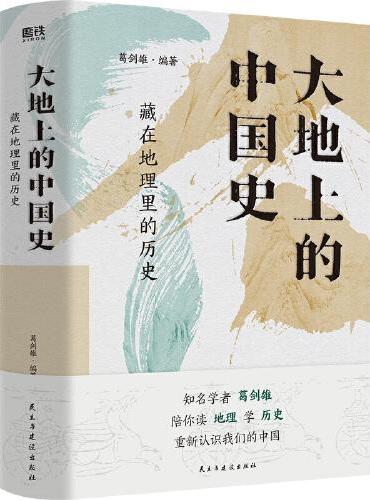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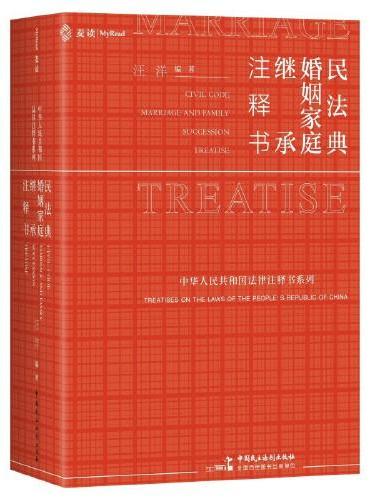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NT$
6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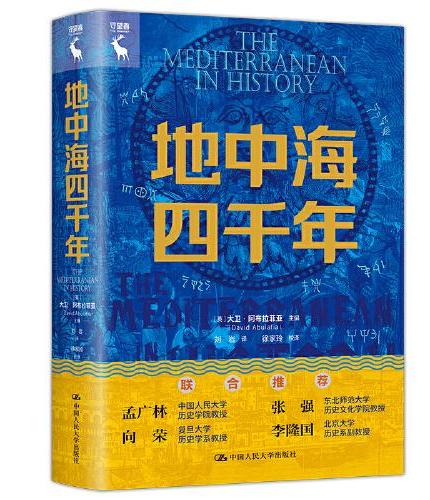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NT$
857.0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NT$
316.0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NT$
194.0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1. 云集海内外两岸三地23位名家大师的43篇经典文章,以散文为经,涵盖了食衣住行等更对中国文人口味的消闲之事。名家名作荟萃,尽显人文之美。
2.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为万千读者度身甄选;既囊括常见的关于读书的名作,也选采了许多不见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专业眼光,菁华品质。
3. 选文内容广泛,重描述不重概括;文章挥洒自如,妙趣横生;篇幅适中,随读随止。用更少的时间阅读更经典的文字,过更从容的生活。
4. 特别邀请专业主播为全部文章录制朗诵音频,扫描二维码,即可收听。上下班途中、散步休息随时随地,视听结合,拉近你与经典的距离。
5. 书中作者大都浸淫汉语写作数十年乃至一生,他们通晓汉语音韵节律,精通遣词造句。阅读这些文字,对提升美学鉴赏、提高写作都大有益处。
6. 书中尚在版权期内的文章,除个别作家作品外,所选文章均获得作者或版权继承人的合法授权,从而保证了选文完整性、quanwei性。
7. 不仅适合成人、本专科院校学生提高文学、文化素养阅读,更可作为初高中学生课外阅读之用,更可作为馈赠礼品。
8. 全书风格明快,富于变化;内外双封设计,采用烫
|
| 內容簡介: |
|
《闲情乐事》这一集子里收入的基本上都是闲文,由陈平原选编,搜集了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梁实秋、贾平凹等23位作家的所谓士大夫趣味作品,所收的43篇文章涵盖了食衣住行等更对中国文人口味的消闲之事,*后殿以一组忙闲之辩的文章。每一篇都是作家个体性情的自然流露,都是生活的艺术的散文小品。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人生的精义就在于如何把握忙与闲之间这个颇为微妙的度。
|
| 關於作者: |
陈平原
1954-
广东潮州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
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领域有着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
代表作品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
|
| 目錄:
|
目 录
|再 记|
| 序 |
|附 记|
|导 读|
北京的茶食 ◎ 周作人 | 001
喝茶 ◎ 周作人 | 003
谈吃 ◎ 夏丏尊 | 007
我的戒烟 ◎ 林语堂 | 011
吃茶文学论 ◎ 阿英 | 016
吃瓜子 ◎ 丰子恺| 020
吃酒 ◎ 丰子恺| 027
辣椒 ◎ 王力| 032
奇特的食物 ◎ 王力| 036
烟 ◎ 吴组缃| 040
茶馆 ◎ 黄裳| 047
止酒篇 ◎ 宋云彬| 051
吃粥有感 ◎ 孙犁| 056
十载茶龄 ◎ 邵燕祥| 059
陕西小吃小识录 ◎ 贾平凹| 062
壶边天下 ◎ 高晓声| 071
途中 ◎ 梁遇春| 082
论西装 ◎ 林语堂| 090
住所的话 ◎ 郁达夫| 095
蹓跶 ◎ 王力| 099
衣裳 ◎ 梁实秋| 102
雅舍 ◎ 梁实秋| 106
旅行 ◎ 梁实秋| 110
骨董小记 ◎ 周作人| 114
假山 ◎ 叶圣陶| 119
天冬草 ◎ 吴伯箫| 124
小动物们 ◎ 老舍| 128
小动物们(鸽)续 ◎ 老舍| 134
囚绿记 ◎ 陆 蠡| 141
鹤 ◎ 陆 蠡| 145
手杖 ◎ 王力| 152
下棋 ◎ 梁实秋| 154
鸟 ◎ 梁实秋| 157
南京的骨董迷 ◎ 方令孺| 161
生活之艺术 ◎ 周作人| 165
谈流浪汉 ◎ 梁遇春| 169
春朝一刻值千金 ◎ 梁遇春| 185
言志篇 ◎ 林语堂| 191
秋天的况味 ◎ 林语堂| 196
人生快事 ◎ 柯灵| 199
撩天儿 ◎ 朱自清| 202
闲 ◎ 王力| 210
暂时脱离尘世 ◎ 丰子恺| 214
|编辑附记| ◎ 216
|
| 內容試閱:
|
|导 读|
陈平原
收集在这里的基本上都是闲文。除了所写系人生琐事无关家国大业外,更在于文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闲情逸致。把善于消闲概括为士大夫趣味未必恰当,只不过文人确实于消闲外,更喜欢舞文弄墨谈消闲。谈消闲者未必真能消闲,可连消闲都不准谈的年代,感情的干枯粗疏与生活的单调乏味则可想而知。有那么三十年,此类闲文几乎绝迹,勉强找到的几篇,也都不尽如人意。说起来闲文也还真不好写,首先心境要宽松,意态要潇洒,文章才能有灵气。大文章有时还能造点假,散文小品则全是作家性情的自然流露,高低雅俗一目了然。当然,比起别的正经题目来,衣食住行、草木鸟兽乃至琴棋书画,无疑还是更对中国文人的口味。即使是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也不难找到一批相当可读的谈论此类生活的艺术的散文小品。
一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分毫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这话是夏丏尊在1930年说的,半个世纪后读来仍觉颇为新鲜。唯一需要补充的是,不单普通中国人爱吃善吃,而且中国文人似乎也格外喜欢谈论吃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小品中,谈论衣、住、行的佳作寥寥无几,而谈论吃的好文章却比比皆是。
对于烹调专家来说,这里讲究的吃简直不能算吃。显然,作家关心的不是吃的内容,而是吃的形式。更准确地说,是渗透在吃这一行为中的人情物理。说他民族的鬼只要香花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仍依旧非吃不可,故祭祀时要献猪头乃至全羊全牛(夏丏尊《谈吃》);说中国人天上地下什么都敢吃,不过为了心理需要,人们对于那些奇特的食品往往喜欢锡以嘉名(王了一《奇特的食物》);说理想的饮食方法是故意往清茶淡饭中寻其固有之味,而这大概在西洋不会被领解(周作人《喝茶》)这实际上探究的是体现在食上的民族文化心理。
正因为这样,谈论中国人吃的艺术的文章,基于其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类:重在褒扬中国文化者,着力于表现中国人吃的情趣;重在批判国民性者,主要讽刺中国人吃的恶相。两者所使用的价值尺度不同,不过在承认中国人能吃而且借吃消闲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林语堂为洋派的抽烟卷辩护,不过说些心旷神怡或者暗香浮动奇思涌发之类着眼于实际效果的话(《我的戒烟》),哪及得上吴组缃所描述的那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的抽水烟:有胡子老伯伯吸烟时表现了一种神韵,淳厚,圆润,老拙,有点像刘石庵的书法;年轻美貌的婶子吸烟时这风姿韵味自有一种秾纤柔媚之致,使你仿佛读到一章南唐词;至于风流儒雅的先生吸烟时的神态,这飘逸淡远的境界,岂不是有些近乎倪云林的山水?你可以不欣赏乃至厌恶这种充满装饰意味的生活的艺术,可你不能不承认它自有其特点:它的真正效用并不在于过烟瘾,而是一种闲逸生活的消遣与享受(吴组缃《烟》)。实际上中国有特点的食物,多有这种非功利的纯为体味闲中之趣的意味,欣赏者、批判者都明白这一点。
夏丏尊怀疑中国民族是否都从饿鬼道投胎而来,因此才如此善吃(《谈吃》);丰子恺讥笑中国人甚具吃瓜子天才,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吃瓜子》),自然都颇为恶谑。可跟同时代关于国民性讨论的文章比较,不难理解作者的苦衷。至于吴组缃厌恶跟古老农业民族生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闲散的艺术化生活(《烟》),阿英慨叹不断的国内外炮火,竟没有把周作人的茶庵,茶壶,和茶碗打碎(《吃茶文学论》),更是跟待定时代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消闲那是山人隐士的雅事,与为救亡图存而奋斗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无缘,唯一的作用只能是销蚀斗志。这种反消闲的倾向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格外紧的年代里得到畸形的发展,烟茶之嗜好甚至成了治罪的根据。这就难怪邵燕祥要为一切饮茶者祝福:但愿今后人们无论老少,都不必在像喝茶之类的问题上瞻前顾后,做最坏条件的思想准备。(《十载茶龄》)
其实,夏丏尊、丰子恺等人本性上又何尝真的不喜欢消闲,只不过为感时忧国故作决绝语。听丰子恺谈论吃酒的本旨乃为兴味为享乐而不求功利不求速醉,你才明白作家的真性情。而这种说法其实跟周作人关于茶食的诸多妙论没多少差别。在周氏看来,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因而,喝不求解渴的酒与吃不求充饥的点心便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装点(《北京的茶食》)。没这些当然也能活下去,可生活之干燥粗鄙与精美雅致的区别,正在这无用的装点上。所谓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不在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实不限于日本的茶道(周作人《喝茶》),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中也不乏此种情致。这里讲究的是饮食时的心境,而不是制作工艺的复杂或者原料之珍贵。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普普通通的家乡小吃,而不是满汉全席或者其他什么宫廷名馔。除了贾平凹所说的,于家乡小吃中地方风味,人情世俗更体察入微外(《陕西小吃小录》),更有认同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味。靠挥金如土来维持饮食的档次,那是暴发户加饕餮,而不是真正的美食家。美食家当然不能为无米之炊,可追求的不是豪华奢侈,而是努力探寻家常饮馔中的真滋味全滋味。这一点,财大气粗的饕餮自然无法理解,即使当年批判消闲的斗士们也未必都能领会。周作人的喝清茶,丰子恺的品黄酒,贾平凹的觅食小吃,实在都说不上糜费,可享受者所获得的乐趣与情致,确又非常人所能领悟。
不过,话说回来,近百年风云变幻,这种以消闲为基调的饮食方式实在久违了,绝大部分人的口味和感觉都变得粗糙和迟钝起来,难得欣赏周作人那瓦屋纸窗清泉绿茶与素雅的陶瓷茶具。这点连提倡者也无可奈何。于是文中不免或多或少带点感伤与怀旧的味道,以及对苦涩的偏爱。周作人把爱喝苦茶解释为成年人的可怜之处,可我想下个世纪的中国人未必真能领悟这句话的份量但愿如此。
二
比起食来,衣、住、行似乎都微不足道。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对食的兴趣明显高于其他三者。难道作家们也信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吃到肚里是真的?抑或中国过分发达的食文化对其兄弟造成了不必要的抑制?可纵观历史,则又未必。或许这里用得上时下一句名言:越是乱世,越是能吃。战乱年代对服饰、居室的讲究明显降到最低限度,而流浪四方与旅游观光也不是一回事,可就是吃走到哪儿都忘不了,而且都能发挥水平。有那么三十年虽说不打仗,但讲究穿着成了资产阶级的标志,更不用说花钱走路这一有闲阶级的陋习,唯有关起门来吃谁也管不着,只要条件允许。这就难怪谈衣、住、行的好文章少得可怜。
林语堂称西装令美者更美丑者更丑,而中国服装是比较一视同仁,自由平等,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于太露形迹了,所以中服很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论西装》),这自是一家之言,好在文章写得俏皮有趣。梁实秋谈男子服装千篇一律,而女子的衣裳则颇多个人的差异,仍保留大量的装饰的动机,其间大有自由创造的余地(《衣裳》),文章旁征博引且雍容自如。可林、梁二君喜谈服装却对服装不甚在行,强调衣裳是文化中很灿烂的一部分,可也没谈出个子丑寅卯。真正对服装有兴趣而且在行的是张爱玲,一篇《更衣记》,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了。语言风趣学识渊博还在其次,更精彩的是作者力图描述时装与时代风气的关系,以及时装变化深层的文化心理。讲到清代女子服饰的特点时,张爱玲说: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消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民国初年,时装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喇叭管袖子的妙处是露出一大截玉腕;军阀来来去去,时装日新月异,并非表现精神活泼思想新颖,而是没能力改变生存境况的人们力图创造衣服这一贴身环境;三十年代圆筒式的高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丰柔的肉身,象征了那理智化的淫逸风气;四十年代旗袍的最重要变化是衣袖的废除,突出人体轮廓而不是衣服。至于四十年代何以会在时装领域中流行减法删去所有有用无用的点缀品,张爱玲没有述说。其实,几十年时装的变化是篇大文章的题目,非散文家三言两语所能解答。张氏不过凭其机智以及对时装的一往情深,勾勒了其大致轮廓。
住所之影响于人的性格乃至一时的心境,无疑相当突出。因而,对住所的要求往往是主人人格的潜在表现。在郁达夫、梁实秋谈论住所的文章中,洋溢着鲜明的士大夫情趣,讲求的是雅致而不是舒适。当然,舒适需要更多的金钱,雅致则可以穷开心。穷是时代使然,可穷也要穷得有味这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心态。郁达夫要求的住所是能登高望远,房子周围要有树木草地(《住所的话》);梁实秋欣赏不能蔽风雨的雅舍,则因其地势偏高得月较先,虽说陈设简朴但有个性,有个性就可爱(《雅舍》)。
梁实秋说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旅行》),这话起码不准确,翻翻古人留下的一大批情文并茂的游记,不难明白这一点。只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国人才变得最怕旅行。旅行本来是逃避平庸、逃避丑恶以及培养浪漫情调的最好办法,它使得灰色单调的人生显得比较可以忍耐。可倘若旅行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也自然只好猫在家里了。完全圈在四合院里,不必仰屋,就想兴叹。于是有了变通的办法,若王了一所描述的忙里偷闲的蹓跶(《蹓跶》),以及梁遇春所说的比有意的旅行更亲近自然的通常的走路(《途中》)。何处楼台无月明,自己发现的美景不是远胜于千百万人说烂了的名胜?关键是培养一个易感的心境以及一双善于审美的眼睛,而不是恓恓惶惶筹集资金去赶万里路。于是,凡人百姓为谋生而必不可少的通常的走路,也可能具有审美的意义,当然,前提是心境的悠闲。
三
与谈衣食住行不同,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对草木鸟兽以及琴棋书画的关注少得可怜。虽说陆蠡说养鹤、老舍说养鸽,还有周作人说玩古董与梁实秋说下棋,都是难得的好文章。可总的来说,这一辑文章明显薄弱,比起明清文人同类作品来,并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新意。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写作此类文章需要闲情逸致,这一百年虽也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生活的艺术,可真正允许消闲的时候并不多。
这也是本书最后殿以一辑专作忙闲之辩文章的原因。一方面是传统中国文人趣味倾向于消闲,一方面是动荡的时代以及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要求远离消闲,作家们很可能有时候津津乐道,有时候又板起脸孔批判,而且两者都是出于真心,并无投机的意味。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之间价值评判标准的矛盾。在我看来,忙闲之辩双方各有其价值,只是要求入选的文章写得有情致,火气太盛的大批判文章难免不入时人眼。自以为手握真理可以置论敌于死地者,往往不屑于平心静气展开论辩,或只是挖苦,或一味嘲讽,主要是表达一种情感意向而不是说理,因而时过境迁,文章多不大可读。
还有一点,提倡消闲者,往往是从个人安身立命考虑,且多身体力行;反对消闲者,则更多着眼于社会发展,主要要求世人遵循。为自己立论,文章容易潇洒轻松;为他人说教,则文章难得雍容优雅。当然,不排除编选者对前者的偏爱,并因而造成某种理论的盲点,遗漏了一批好文章。好在批判消闲的宏文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肯定,各种选本也多有收录,读者不难找到。因而,即使单从补阙的角度,多收录几篇为消闲辩护的文章,似乎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
正如王了一所说的,好闲未必真的一定游手,如果闲得其道,非特无损,而且有益(《闲》)。整天没完没了地工作,那是机器,而不是人真正意义的人。丰子恺讲求暂时脱离尘世,放弃欲念,不谈工作,白日做梦,那对于健全的人生很有必要,就因为它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暂时脱离尘世》)。其实,这一点中国古代文人早有领悟,从陶渊明、苏东坡,到张潮、李笠翁,都是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的快乐天才。这里忙、闲的对立,主要是所忙、所闲内容的对立,与周作人从日本引进的努力的工作,尽情的欢乐不尽相同。只是在强调消闲对于忙碌的世俗人生的重要性这方面,两者才有共同语言。
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梁遇春,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反对无谓的忙乱,提倡迟起的艺术,迟起本身好似是很懒惰的,但是它能够给我们最大的活气,使我们的生活跳动生姿(《春朝一刻值千金》);讥笑毫无生气的谦让平和,赞赏任性顺情、万事随缘、充满幻想与乐观精神,无时不在尽量享受生命的流浪汉(《谈流浪汉》)。有趣的是,梁遇春谈流浪汉,选中的中国古代文人是苏东坡;而这跟提倡闲适名扬海内外的林语堂正相吻合。可见两者确有相通之处。
承认消闲对于活人生的意义,并非提倡山人隐士式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更不欣赏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忙忙碌碌终其一生不大可取,以闲适自傲也未必高明。如何把握忙与闲之间的比例,这里有个适当的度,过犹不及。人生的精义就在于这个颇为微妙的度。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于畅春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