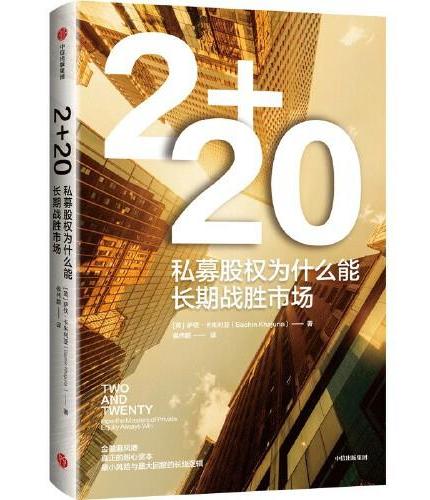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NT$
316.0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NT$
194.0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NT$
347.0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NT$
254.0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NT$
296.0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NT$
403.0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NT$
1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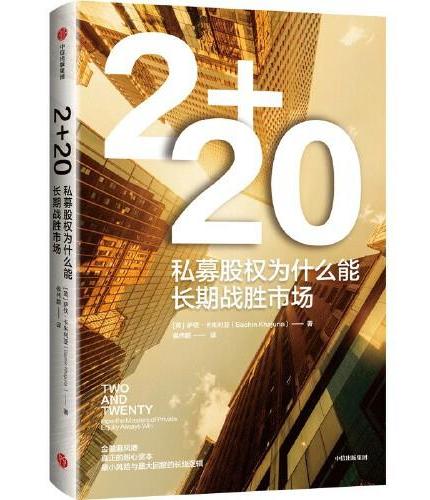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NT$
403.0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沿袭了扎加耶夫斯基一贯的碎片化的风格,其中鲜明的创作特色,或可称为个人历史化的抒情贯穿始终。他带领读者穿行于历史和当代的欧洲文化,使他们因此而改变、丰富,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悬而不明的处境。与他的诗歌一样,这部自传体随笔明亮,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更有一种持久的令人惊叹的力量。他把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必然是不完整的,但也是完整得令人吃惊的。
|
| 關於作者: |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波兰著名诗人、随笔散文家和小说家,一九四五年出生于利沃夫(今属乌克兰),波兰新浪潮诗歌代表诗人及主要理论阐释者。主要代表作有诗集《无止境》(Without End)、《震惊》(Tremor)等,随笔集《两个城市》(Two Cities)、《另一种美》(Another Beauty)、《捍卫热情》(A Defense of Ardor)等。
杨靖,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文明研究所所长。迄今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五十余篇,译著十余部。
|
| 內容試閱:
|
译序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是波兰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出生于波兰的利沃夫(今属乌克兰)。一九四五年雅尔塔会议后,利沃夫成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刚满四个月的扎加耶夫斯基随全家迁居西里西亚的格利维采,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中学毕业后,扎加耶夫斯基进入波兰旧都克拉科夫首屈一指的雅盖沃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先是在一个冶金学院任教,后到一家文学刊物做编辑,直到因参与政治抗议活动被除名一九八二年,因团结工会争取民众权利引发的工潮,波兰当局发布戒严令,作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扎加耶夫斯基虽未受到监禁,但仍因个人原因,被迫离开营房般阴沉的波兰,移居巴黎。在法国,他迅速加入到波兰移民知识分子小团体,参与文化刊物的编辑工作。1983年起,扎加耶夫斯基便往来于法国和美国之间,在多所大学教授诗歌和创意写作课程。扎加耶夫斯基现居克拉科夫,至今已出版诗集十八种,散文、随笔十一种,被公认为当代波兰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扎加耶夫斯基开始诗歌创作,并迅速成长为波兰非官方文学运动新浪潮派的领军人物。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八年间,扎加耶夫斯基先后出版诗集《公报》《肉铺》《信》,并于一九七五年在日内瓦荣获科希切尔斯基基金会国际文学奖。一九七九年,扎加耶夫斯基赴德国短暂居留并从事写作。一九八五年,出版诗集《去利沃夫》《震惊》。一九八八年,扎加耶夫斯基获纽约绿色回声奖。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七年间,先后出版诗集《画布》《火地岛》《神秘学入门》和散文随笔集《团结,孤独》《两座城市》,并于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分别获得纽约古根海姆奖资助和斯洛文尼亚瓦伦西亚国际文学奖。二〇〇〇年,出版散文集《另一种美》,同年在瑞典韦斯特罗斯获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奖。二〇〇二年,扎加耶夫斯基回到波兰定居,出版诗集《无止境》和散文集《捍卫热情》,同年获得慕尼黑霍斯特边克奖。二〇〇四年,扎加耶夫斯基获得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今日世界文学》颁发的、素有小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二〇一〇年,扎加耶夫斯基在意大利特雷维索获欧洲诗人奖,次年出版诗集《无形之手》和随笔集《轻描淡写》。二〇一四年,扎加耶夫斯基获得中国《诗歌与人》杂志主办的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
二〇一七,扎加耶夫斯基在德国被授予以让埃默里的名字命名的欧洲随笔写作杰出成就奖。以奥地利当代著名作家罗伯特梅纳瑟为首的评审团对这位擅长多语种的波兰人和一个世界主义者评价是:扎加耶夫斯基结合了清醒的政治意识和共情的艺术关怀博学,而不自视其高;全面,而不流于琐碎;反讽,而不愤世嫉俗。他带领读者穿行于历史和当代的欧洲文化,使他们因此而改变、丰富,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悬而不明的处境。而这一艺术特质,几乎贯穿了扎加耶夫斯基全部的创作历程。
一
波兰昔日的首都克拉科夫是欧洲文学名城,更是诗歌的中心因为米沃什,因为扎加耶夫斯基,也因为被誉为诗界莫扎特的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斯卡。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波兰诗人们似乎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上述诗人都以各自不同的风格书写波兰(以及欧洲的)历史与更为深广的人性。对他们而言,幸或不幸,作为一名波兰诗人,二战前的德国占领和战后的苏联重置都是无法言说的痛楚,也是无法擦除的记忆。他们或许没有直接书写现实政治,但绝非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所做的,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绘来反抗意识形态的侵袭。在这一方面,扎加耶夫斯基与他的前辈切斯瓦夫米沃什(以及兹别格涅夫赫贝特)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大学毕业后,在克拉科夫,扎加耶夫斯基所投身的诗歌运动,后来被文学史整体命名为新浪潮。其实,在波兰新浪潮这一名号之下,各地存在若干派别,如华沙的杂交方针诗社、弗罗茨瓦夫的阿果拉诗社和六六诗社、波兹南的考验诗社、科托维茨的上下文诗社,等等。扎加耶夫斯基组织和参与的克拉科夫诗歌派别名为现在派,曾受美国垮掉派诗歌、法国新新小说以及英国愤怒的青年等西方文学思潮影响。除了扎加耶夫斯基,该派的代表诗人还包括后来蜚声国际诗坛的斯坦尼斯拉夫巴朗恰卡和朱利安科恩豪塞尔等人,其代表作则为扎加耶夫斯基和科恩豪塞尔合写的论文《未被呈现的世界》。在内容题材方面,他们指责当代诗歌和小说逃避现实、缺乏探索当代问题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勇气,主张恢复诗歌讲真话的权利,重提诗人独立思想的天职。在诗歌形式方面,扎加耶夫斯基主张诗歌不应讲究韵律,其形式应更接近散文由此,扎加耶夫斯基以一种诗学的反叛姿态登上诗歌历史舞台,开始在波兰战后文人团体中崭露头角。
诚如扎加耶夫斯基本人所说,我不是历史学家,可我希望文学能严肃地、有意识地担当编年史的职能。我不想学现代史学家的样子,他们大多是一些冷漠的家伙,缩在档案文献中皓首穷经,用一种丑陋、木然、官腔十足、诗性全无、没有人情味的语言潮虫般乏味。与上述历史学家相反,他对待历史的态度既非冷若冰霜亦非超然物外,而是以一种同情的眼光审视历史中的人和事,力图通过叙述性的元素将历史感与抒情性结合起来,将真实的细节和鲜活的个体展现出来,并由此规避抒情诗常有的自我迷恋和情感放纵的缺陷。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是扎加耶夫斯基最负盛名的一首诗。据扎加耶夫斯基本人日后在访谈中说,这首诗写于一九九九年或二〇〇〇年春天:
产生这首诗的想法的时候,我正一个人搭火车,很孤单,思绪便开始漫游。突然之间,我就想起和父亲去一起爬山的情景,那年我大概十八岁。我父亲很喜欢爬山,但我没有这种爱好,于是常常被父亲拉去一起爬山。那一次,我们经过一个小村落,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村子里的居民都被驱逐出去了。这一地区五十来个村庄的居民都是乌克兰人。二战期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属于某个乌克兰国家地下反抗组织,曾经和纳粹合作,战后还曾袭击过波兰政府。之后,波兰政府采取措施,把这一地区的居民,无论其是否和那个极端组织有关系,一律驱逐出去。我们路过的这个村子,虽然废弃了,但仍能感到有人曾在这里生活过,果园虽没有人打理,但长得很茂盛,开着很多花,让我感受到一个损毁的世界。
九一一事件发生前,《纽约客》诗歌编辑爱丽丝奎因已经拿到这首诗的手稿。事发当天清晨,她刚好在看诗稿,要从中遴选一首诗。灾难发生几个小时后,《纽约客》编辑部开会,决定发表一首诗来回应这次灾难。六天以后,《纽约客》在封底位置发表该诗。这是《纽约客》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封底发表诗作,这也使得扎加耶夫斯基的名字一夜之间在美国家喻户晓。无数悲伤的美国人捧读这首诗,原本绝望的心情立刻又充满了希望。在英美文学界,该诗也可谓是好评如潮,其中当属苏珊桑塔格的评论最具代表性:这里有痛苦,但平静总能不断地降临。这里有鄙视,但博爱的钟声迟早会敲响。这里也有绝望,但慰藉的到来同样势不可当。可见,在灾难和希望、残缺和赞美之间的琴弦上行走,不仅构成了扎加耶夫斯基内在的诗歌张力,也是他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诗歌仿佛建立在一条窄道上,扎加耶夫斯基在另外一次访谈中说:在这条窄道上,一边是可怕的、非人道的东西,另一边是友好的、鼓舞人心的、崭新的、欣喜若狂的东西。诗歌激励我们,让我们抖擞精神,恢复我们的童真,但与此同时也不允许我们忘记什么是困难和痛苦。扎加耶夫斯基同意记者(以及评论家)普遍的看法:他的诗让人想到神像画,其中既不乏黑暗的阴影,同时也有闪现的光明,或神启的时刻。用他的精神导师米沃什的话说,即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中得以统一。
众所周知,扎加耶夫斯基非常崇拜米沃什。据他本人坦言,在他年轻的时候,要读到米沃什的诗需要大费周折,获得的渠道只能是地下出版物或朋友私相授受,因为那时已经流亡欧美的米沃什是一位危险的政治异见分子他的诗在波兰被禁止出版。在移居巴黎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三年,扎加耶夫斯基终于有机会结识仰慕已久的米沃什,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经常晤面聊天。而他的诗风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我二三十岁的时候,已经写了很多诗,那时候的诗有点愤青,比较政治化,当时新浪潮诗歌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很多朋友也这样写。那时,我们这代诗人认为写诗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与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辩论,我们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制度里,感觉不幸福,还有书报检查等,自由度很少,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来,我们的大辩论起到了好的作用,社会发生了变化,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观点和诗风也发生了变化,我希望诗更属于世界文化,而不是政治。我的诗开始带有更多的哲学思辨,融入了更多现代手法,变得更成熟。
由此,原本富于进攻性的干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抒情诗,逐步演变成对政治和社会斗争保持一定情感距离的、讽刺的、观察世界的和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抒情诗诗歌是文学而不是政治。阿多诺所谓奥斯维辛悲剧之后不应再写诗的观点,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过于片面在面对世界的苦难和残酷时,诗歌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功能。一方面,奥斯维辛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诗歌同时也有愉悦和游戏的成分,没有哪个奥斯维辛可以将它完全清除。因此,作为诗人,不仅应该铭记奥斯维辛的残酷,也不应忘却诗歌的游戏功能和欢乐时刻,并应当与读者分享这一种诗歌的体验。扎加耶夫斯基承认,当下许多诗歌(包括他本人的诗作)并没有致力于寻求人类和世界的真理,而是局限于追寻自由,在世界的海滩上收集一些漂亮的小玩意、鹅卵石的贝壳。然而,在他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诗歌的衰落。诗歌可以描写平凡的事物,但诗歌的情感却不能平凡,它能让读者看到隐藏在远处的战栗和狂喜。这种追求精神崇高而又不忽略生活日常性的存在,被扎加耶夫斯基恰当地描述为苏格拉底理性的狂迷说它定义了自由的不同概念。这也是扎加耶夫斯基对米沃什满心崇拜的根本原因。照他的说法,米沃什改写了安泰的神话:一个人同时接触大地和天空才会恢复力量。换言之,唯有理智与情感的完美结合,才能造就不朽的诗歌。
鉴于这个世界本质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扎加耶夫斯基认为诗人是在用自身的双重性向现实的真实结构致敬白昼与黑夜,欲望与满足,清醒的理智与飞逝的幻觉,事实上所有诗歌都应该具备这种双重性。他在《赫贝特》一书序言中曾说:双重性是评判伟大诗人的重要标准。以赫贝特为例,在他的诗中,既有令人意乱情迷的瑰丽场景,又不乏日常家居的点滴白描,但读者切不可被他诗中出现的那些圆柱和拱门、宁芙和萨提尔等装饰所迷惑他的诗歌蕴藏着二十世纪的苦难,容纳了一个非人时代的残酷,而且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现实感。更重要的是,诗人没有因此丧失他的抒情或幽默,而这才是一个伟大艺术家深沉的秘密。熟悉扎加耶夫斯基风格的读者不难看出,与其说他是评述赫贝特,不如说是夫子自道。另外,像赫贝特一样,扎加耶夫斯基算不上非高产作家,而是习惯于字斟句酌他在《轻描淡写》中不止一次说过,有时候在书桌前坐上半天,也写不了几行字。他在另一首诗中也曾说过:我写得很慢,仿佛我可以活两百年。
二
纵观扎加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以对不合理社会制度与秩序的反抗始,到与世界和上帝的和解终。事实上,这一条主线也体现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波兰诗歌文化传统。历史地看,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哈诺夫斯基和巴洛克时期的萨尔别夫斯基,还是启蒙时期的克拉西茨基和浪漫主义时期的一出娘胎就受着奴隶的煎熬,在襁褓中就被人钉上了锁链一代人的代表密茨凯维奇,波兰诗人在欧洲文学史上皆深具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反抗意识。二十世纪波兰著名文艺理论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在《反对诗歌》中批评诗歌的甜蜜性,称诗歌是过度的文字、过度的隐喻、过度的崇高和过度的提纯。很显然,他反对的是脱离社会现实的所谓纯诗。在这一点上,扎加耶夫斯基与贡布罗维奇的看法高度一致。
不仅于此,除了继承古典的波兰诗学传统,扎加耶夫斯基还从当代两位大师米沃什和赫贝特那里汲取了养分。从赫贝特那里,他学到反讽一种对于世界审慎质疑而富于幽默的态度;从米沃什身上,他继承希望后者倡导一种希望的诗学,一种对于历史和存在的信心,它们来源于担当的勇气,来源于对真实的探索热情。作为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既拥抱了米沃什的诗歌之火,又延续了赫贝特独具特质的反讽精神。这两种特质融汇在他晚期记述个人游历或怀旧的作品(如《轻描淡写》)中,形成鲜明的创作特色,或可称为个人历史化的抒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