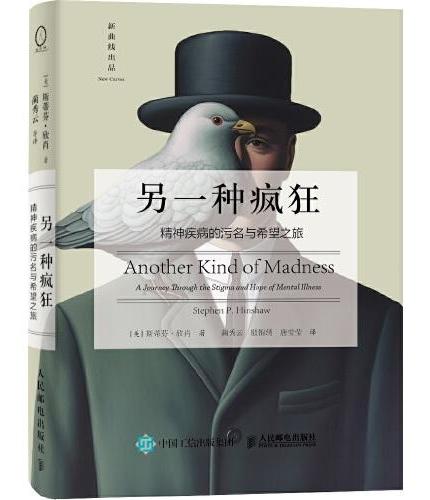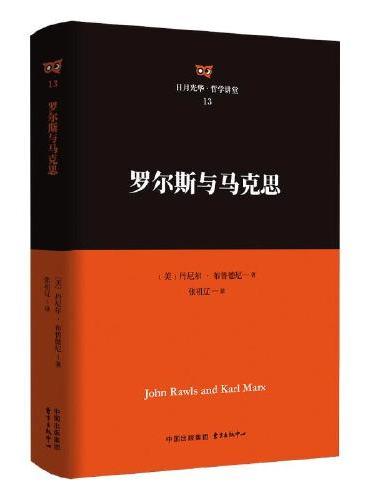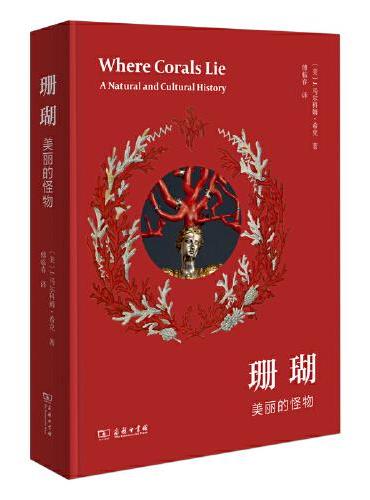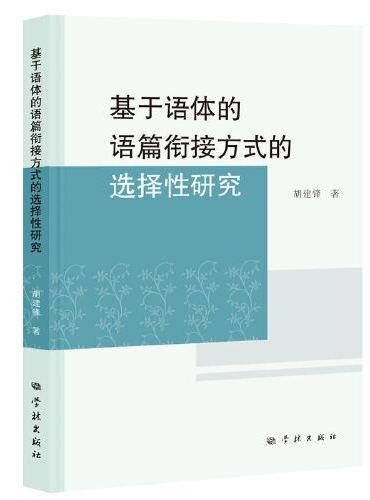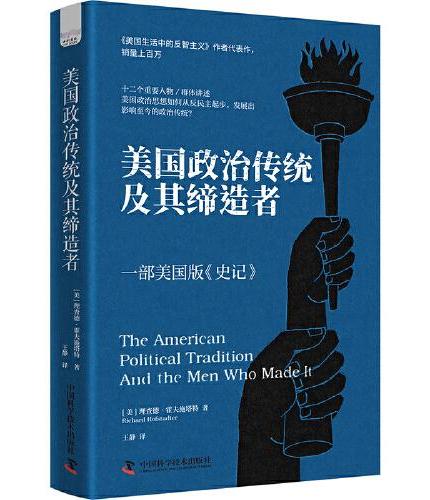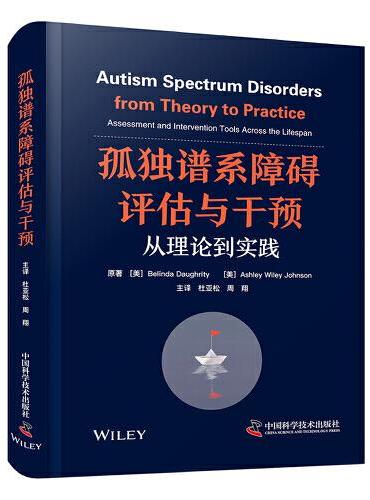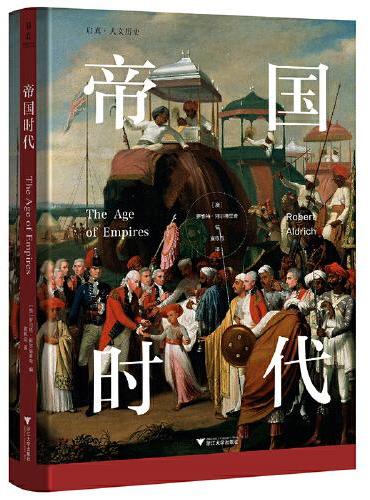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NT$
587.0
《
基于语体的语篇衔接方式的选择性研究
》 售價:NT$
347.0
《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部美国版《史记》
》 售價:NT$
449.0
《
孤独谱系障碍评估与干预:从理论到实践 国际经典医学心理学译著
》 售價:NT$
1061.0
《
大数据导论(第2版)
》 售價:NT$
352.0
《
帝国时代
》 售價:NT$
959.0
編輯推薦:
★《布鲁克林》《大师》作者托宾*作品
內容簡介:
我已经熟悉死亡的气息。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率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几年以后,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开始讲述她的故事。此时,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她的情夫埃癸斯托斯统治着迈锡尼,两人计划在阿伽门农凯旋之际暗杀他。
關於作者: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他1955年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镇。毕业于都柏林大学。自199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戏剧、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1999)、《大师》(2004)、《玛利亚的自白》(2012)都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荣获2006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文学奖。《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名门》(2017)是他最新一部长篇小说。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同年,他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奖,以表彰他对爱尔兰文学做出的贡献。2014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外籍荣誉院士。
目錄
人物 001
內容試閱
跋:我如何重写古希腊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