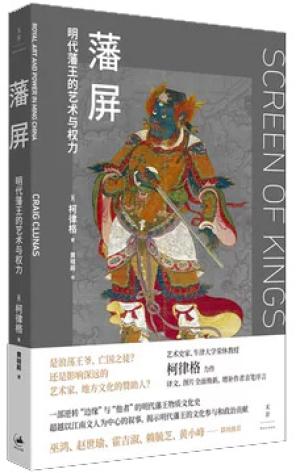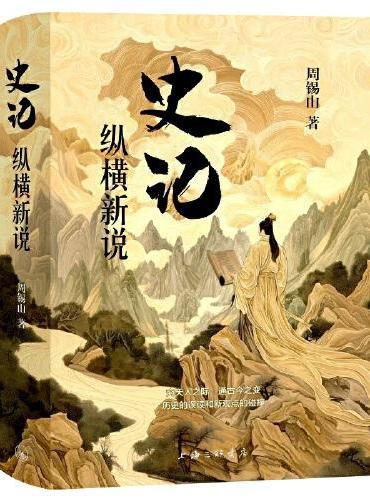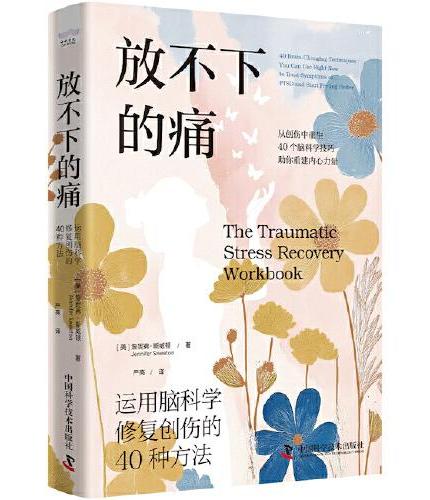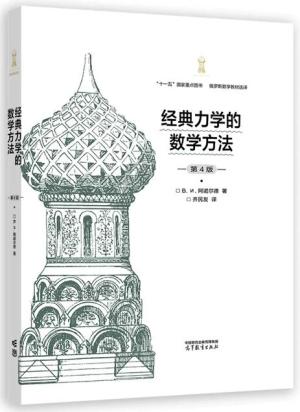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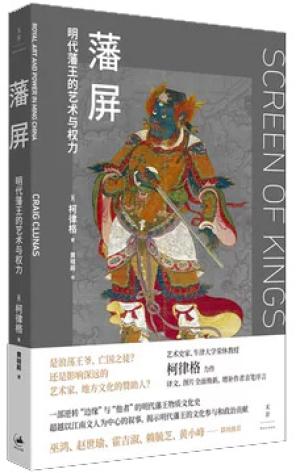
《
藩屏:明代藩王的艺术与权力(柯律格代表作,一部逆转“边缘”与“他者”的明代藩王物质文化史,填补研究空白)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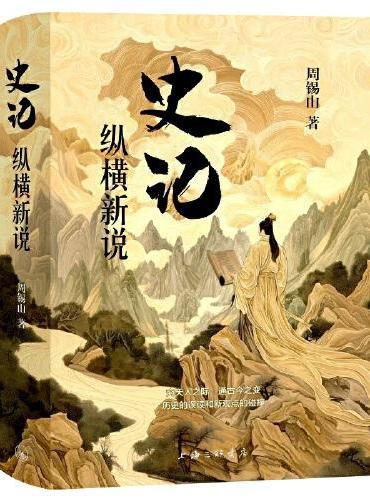
《
《史记》纵横新说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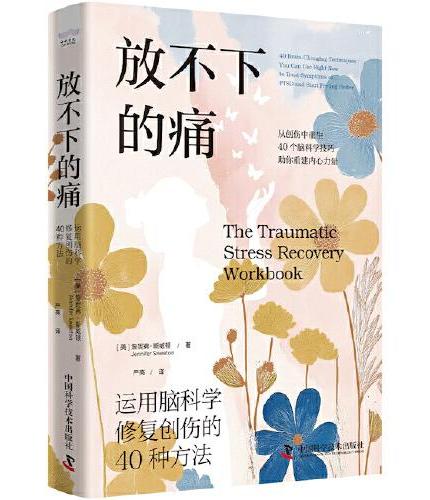
《
放不下的痛:运用脑科学修复创伤的40种方法(神经科学专家带你深入了解创伤背后的脑机制,开启全面康复之旅!)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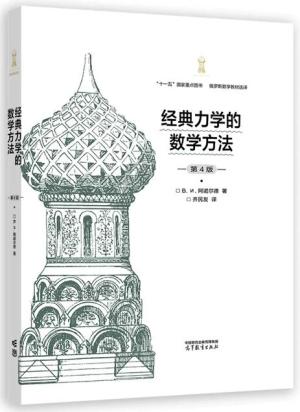
《
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第4版)
》
售價:NT$
403.0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跟随历史的足迹 见证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抗争
》
售價:NT$
305.0

《
功名诀:左宗棠镜像
》
售價:NT$
908.0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NT$
439.0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1.精心选目:收录加缪代表性作品,涵盖小说、散文、笔记等文体,从时间跨度上贯穿加缪的创作历程。
2.完整呈现:法国文学研究专家郭宏安翻译、研究加缪成果完整呈现。
3.可靠底本:根据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版翻译,注释详尽。
4.过硬译本:“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得者翻译,译文准确、优美。
5.全新装帧:精装方脊,使用正版授权图片设计封面;内文使用顺纹纸,柔软轻盈,阅读舒适。
6.赠品丰富:每卷均附赠引文书签和封面同款纪念卡片,套装另赠两款海报。
|
| 內容簡介: |
本套装收录加缪作品:
《反与正》(L’Envers et L’Endroit),1937
《婚礼集》(Noces),1938
《局外人》(L’?tranger),1942
《西绪福斯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1942
《夏天集》(L’?té),1 954
《堕落》(La Chute),1956
《流放与王国》(L’Exil et le Royaume),1956
《加缪笔记》精选集(Carnets),1935—1959
郭宏安作品: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
|
| 關於作者: |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
法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之一。
他有着冷峻而不乏温情的面孔,俊朗而略显清癯的轮廓,博大而偶见僵硬的情怀,清醒而不事伪装的精神,澄澈而时现激愤的文笔,高贵而不畏强权的心灵。
郭宏安(1943—)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历任第二炮兵司令部参谋,新华社对外部翻译,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加缪研究和翻译,至今不辍。
|
| 目錄:
|
局外人 西绪福斯神话
堕落 流放与王国
反与正 婚礼集 夏天集
加缪笔记:1935—1959(精选集)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
阿尔贝·加缪
加缪与小说艺术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美与历史的博弈
《局外人》: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
《西绪福斯神话》:荒诞·反抗·幸福
再读《鼠疫》
《堕落》:法官—忏悔者
《堕落》:一幅当代知识分子的画像
《流放与王国》
我读《不贞的妻子》
《叛教者》的参照
《沉默的人们》与现实主义问题
我读《来客》
《约拿》别解
《生长的石头》:一块西绪福斯的巨石
《反抗的人》:敢于抵抗一时风气的人
《加缪笔记:1935—1959》(精选集)译后记
谁是“个人”?——我读《个人》
《阳光与阴影》:加缪的秘密
一个拒绝进入先贤祠的人——《孤独与团结:阿尔贝·加缪影像集》译后记
我为什么将书名译作《孤独与团结》?
代跋:标准·效果·理想·方法——以加缪的《局外人》为例谈文学翻译
|
| 內容試閱:
|
《加缪笔记:1935—1959(精选集)》译后记
1935年5月,阿尔贝·加缪参与《阿斯杜里起义》的创作,时年二十二岁;1960年1月,加缪在前往巴黎的时候殒命于车祸,时年四十七岁。二十五年间,从初入文坛到猝然弃笔,加缪以近似笔记的形式写下了日记、思考,内容包括文学、哲学、政治、关于人类命运的观点、写作计划、构思、提纲、读书随想、花草树木、风景、游记、交往、偶尔听到的别人的对话、故事以及对本人作品评论的反应等,共写了九本学生用的练习簿,其中有些条目,例如第七本,还打印成册。这九本笔记本中的文字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作为作家的加缪的创作经历、思想演变和精神历程,看似随手而记,实则精心结撰,何况事后还有修改、补充和删减等。伽利玛出版社于1962年、1964年和1989年分别出版了这九本笔记,分为三卷,总名曰《加缪笔记》(Carnets)。九本笔记,分别称为“笔记本Ⅰ”“笔记本Ⅱ”……直至“笔记本Ⅸ”,两千五百余个条目,短则一个词,长则两千字,有一段竟达三千字,可说是洋洋大观。本书选择了近一半的条目,舍弃了引文、提示性的词语以及因为不明就里而无从猜测的文字等,意在精彩也。
九本笔记本,加缪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行所为通过简明扼要、澄澈如水的文字表现了出来,读来似清流样沁人肺腑,似雕刻般印上脑际。他是一个小说家、剧作家和随笔作家,然而他往往以艺术家自称,作家当然是艺术家,可是一位作家坚持称自己是艺术家,就不那么当然了。在笔记中,加缪说:“要写作,在表达上永远应该稍稍不及(与过相比)。反正勿饶舌。”“真正的艺术品是说得少的作品。”一个人写作时应该做到的“是学会自我控制”。这是加缪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也是他对文学写作提出的要求,往更远些说,是对人类文字表达提出的要求。加缪是一位“相信文字”的作家,是一位自觉追求风格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的大手笔,他的风格是一种“高贵的风格”,是一种“恰到好处”“含而不露”的风格。他谈及自己的写作时,经常见诸笔端的是“限制”“堤坝”“秩序”“适度”“栅栏”等表示“不过分”的词汇,总之是“勿饶舌”。这种对于“度”的自觉意识,使加缪为文有一种挺拔瘦硬、冲淡清奇的风采。《加缪笔记》就是一个明证。
“饶舌”,加缪用的是“bavardage”,即为喋喋不休的闲话,译为“饶舌”,可谓恰当。文坛上确有一部分人,下笔如同呼吸,滔滔不绝,一泻千里,但是言不及义,难免产生一堆文字垃圾。加缪以为不可。笔记一类的文体,本来就要求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一击便中,但是加缪写作笔记,不单单是遵循为文的规矩,而且还有意简单,不说废话,言简而意赅。作为一个中国人,译者虽不才,但是与加缪不免心有戚戚焉。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说:“敏于事而慎于言。”这都是每一个中国人应牢记在心的古训。就为文而言,清人刘大櫆的主张就更与加缪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了。他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露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他把为文的“老”“意”“辞”“理”“味”“气”“品”“神”诸般一一说到,后归结为“文章尽境”,可以说是对“简”字的鞭辟入里、全面深刻的理解。可见无论古今中外,作文的道理是一致的,即“勿饶舌”。
如果说笔记体的文字要求当日事当日记,勿饶舌是其固有的品格,《加缪笔记》还不足以印证加缪的主张的话,那么试举小说《局外人》为例,以说明之。“勿饶舌”的主张是加缪在1938年8月(?)提出的,那时他已开始创作《局外人》了。实际上,远在1935年,加缪就有了写作一部关于“自由的人”作品的念头,到了1938年,《局外人》的大量的细节就出现了,1940年5月,书完成了,名之曰《局外人》,1942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至今仍居畅销书之列,虽然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从孕育到呱呱坠地,一件作品经过了七年的酝酿和磨炼,译成中文仅仅五万余字,可谓精练到了极致。《局外人》具有古典主义的澄澈,文笔老到,意图真诚,词语恳切,道理恰当,滋味清淡,气势蕴藉,品格高贵,精神深远而含蓄不露,无一废词缀句,所以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历七十五年而不衰,可以说是“勿饶舌”之典范。“真实的艺术品是说得少的作品。”《局外人》是一件真实的艺术品,它说得少,可它含义隽永,对它的解说连篇累牍,至今似乎还没有穷尽。
1957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落在了加缪的头上,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贫穷的,但是他从不抱怨,不追求也不羡慕有钱人的生活,而是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不费分文的馈赠:阳光和大海,坚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他蔑视的是富人的炫耀,捍卫的是穷人的尊严。他在《笔记本Ⅶ》中写道:“我喜欢的十个词,答案:世界,痛苦,土地,母亲,人,荒原,荣誉,贫穷,夏天,大海。”“贫穷”赫然位列其中。这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概括了加缪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加缪对世人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宁可贫穷而自由,不要富有而为奴。当然人人都愿意富有而自由,这就是有时候使他们既贫穷又为奴的原因。”他不想空洞地颂扬贫穷,只想自由地生活而甘愿贫穷,以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贫穷是一种以慷慨为美德的状态。”慷慨者,不吝啬之谓也。这不禁让人想起了“箪食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的故事。这故事在过去是一桩美谈,不知今日变成了什么。现代人为什么不幸福?司汤达说,是因为我们“虚荣”。虚荣导致贪婪,贪婪引发逐利,逐利形成了灵与肉的分裂。信矣!
加缪从不攀附权贵,正相反,他以此为耻。1953年4月,他的妻子接受了法国总统奥里奥尔的午餐邀请,加缪得知后很生气,并在一次旅行中向母亲讲了这件事。母亲问他吃了什么,他说什么也没吃,因为他们拒绝了邀请。加缪的母亲说:“这很好,儿子,这些人和我们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说得多好!加缪一向不理解巴黎有钱人的生活,他不习惯上流社会甚至知识界的生活,他只在印刷和排字工人中间感到自在,视他们为朋友。他在笔记的第七本中写道:“在阿尔及尔,别墅区内的高墙上开满鲜花。这是另一个世界,我在那里感到被流放。”“另一个世界”,说得多好!这与他拒绝法国总统的午餐邀请出于同一机杼。加缪出身贫寒,但是他认为他的家庭“有一种高贵的气质”,身处有钱人的世界无异于一种流放。以一种平常心看待财富与地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甚至有些以“民主”为标榜的人以见到废帝为荣,口称“皇上”,说不定还沾沾自喜呢。“巴黎是一座丛林,那里的野兽很难看。”所以,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在普罗旺斯的卢尔马兰买了房子。加缪是一位艺术家,坚信“是艺术和艺术家重建了这个世界,但永远是怀着一种抗议的背后意图”,所谓“背后意图”乃是一个“反抗的人”对抗和批判一个“荒诞的世界”,后达到“博爱”和“幸福”,而这种对抗和批判不能直接地说出来,因为“艺术的活动有其廉耻。它不能直接地把事情说出来”。所以加缪才说:“我为什么是一个艺术家而非哲学家?因为我根据词句而非概念来思考。”他从具体的事物出发,也就是说他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出发来进行有血有肉的思考。在他的眼中,艺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艺术)是我们这个无序的种族产生的有序的产物。这是千百个哨兵的呐喊,千百座迷宫的回声,这是人们无法遮盖的灯塔,这是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尊严给出的好的见证”。《加缪笔记》是否一种见证?我想起码加缪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写出了攀登艺术高峰过程中的艰难的行走与攀爬。《加缪笔记》止于加缪刚过四十六岁的时候,所记录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充满了痛苦与欢乐的旅途。令人扼腕的是,一个绚烂之后渐趋平淡的人竟然折戟于盛年,岂非荒诞乎?
……
瑞士阿尔卑斯山间的路旁常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停一下吧,欣赏啊!”立牌子的人深谙旅游者的心理,他希望那些乘车的、骑马的、徒步的人,都暂时停下自己的脚步,喘一口气,好好观赏这雄浑而绮丽的风景:山间的湖泊,倒挂的瀑布,峰顶的积雪,碧绿的草场,绚烂的野花,挺拔的松柏,悠闲的牛羊……我很希望能有这样一块牌子,写上这句话,让你在这一部《加缪笔记》的选本面前,“停一下吧,欣赏啊!”在你一生的旅途上,或是一马平川,或是崎岖山路,的确需要喘一口气啊!当然,我愿意再加上一句:“理解啊!”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后记
代跋:标准· 效果· 理想·方法
——以加缪的《局外人》为例谈文学翻译
(一)
《圣经 · 创世记》说:先民本来言语口音是一样的,他们商量在巴别这个城市里修一座塔通天,告诉后代,以防他们分散居住而沟通不畅。耶和华怒其狂妄,说:“看哪,他们要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于是,上帝变乱他们的言语口音,引起他们的纷争,这塔也就停工不造了。从此,人们以语言的不同而分散居住,其间的沟通交流不得不通过语言的转换,即翻译。据称,中国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的诗歌。可见无论中外,翻译都是一件十分古老的事情。
然而,什么是翻译?翻译理论家、翻译工作者和翻译爱好者给出了多少有些不同的回答。我的回答是一个翻译爱好者的回答:翻译就是用一种文字(语言)传达用另一种文字(语言)写成或说成的作品,后形成文字的作品而不变更所表达和蕴涵的意义与信息。用杨绛先生的话说,翻译就是“把原作换一种文字,照模照样地表达。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也怎么说”。这是一种平实可靠、人人可以接受的定义。什么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就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翻译。翻译有许多种,口译且不论,有科技翻译,有文学翻译,有理论翻译,有实用翻译,有社会科学翻译,有人文科学翻译,有自然科学翻译,等等,唯有文学翻译具有文学性,有的哲学、历史等著作的翻译也具有文学性。那么,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性就是“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例如想象力、虚构、描写、象征、比喻、修辞等等,即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中所理解的严复的“翻译三难说”中的“雅”字,此为文学翻译所独有。“信、达、雅”之中的“雅”字,历来解说甚夥,然而大多斤斤于字面,多皮相之谈,唯钱锺书先生从反面予以阐释,谓“雅非为饰达”,“非润色加藻”,一个“非”字搔着了“雅”字的痒处,较之“文雅”“高雅”“古雅”“汉以前字法句法”等等,更能切中肯綮,打开思路。以文学性解“雅”,可以与时俱进,对一个旧的概念给予新的解释,令其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并非所有新的说法都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译文对原作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此为文学翻译也。故“雅”字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
“译事三难:信、达、雅。”当合而析之,不应分而观之,以此为标准,可以分出译品的好坏善恶,全面而精当。大部分的翻译家对“信、达”取信服的态度,对“雅”字则如履薄冰,做种种或明或显的抗拒状,以文学性解“雅”谅可消除其对“雅”的疑虑。如果扩大一些,对“雅”做广泛的理解,则可以为“神似”,然而神似并非形似的反面,完全可以以形出神,不必“弃形取神”。“神似”的说法,以傅雷的观点为著名,他说:“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效果”,而非标准。标准是衡量事物的准则,而效果则是由行为产生的有效的结果,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再说,“不在形似”不等于不要形似,完全可以既要形似,又要神似,形神兼顾,形留而神出。有一种说法,认为“神似”进一步发展,则进入“化境”。“化境”的说法来自钱锺书先生,他在1979年的《林纾的翻译》(收在《旧文四篇》里)中说:“文学翻译的理想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持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所谓“原有的风味”者,乃是原作的风格之谓也。《林纾的翻译》于1964年首次发表,当时,“理想”一语是写作“标准”的,后来标准改为理想,显然不是信手随意的,必是深思熟虑而后的产物。“理想”是同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有实现可能的想象,故标准是现实的存在,理想是追求的目标,两者不是同一性质的东西。因此,标准、效果和理想不是同一范畴的事物,不可混为一谈。由“信、达、雅”而“神似”,而“化境”,刘靖之先生将其看作一条由浅入深、不断延伸的线,“一脉相承”,我觉得,由标准而效果,而理想,不妨看作一个面,不断扩展,仿佛一圈圈涟漪。这样产生的译作可以称作善译,而其实现的方法,则如杨绛先生所说:“把原文的句子作为单位,一句挨一句翻。”换句话说,就是以句子为单位的直译。于是,标准,效果,理想,方法,由点及面,一种翻译理论就宛然在目了。
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不在内容,而在形式,换句话说,决定一件作品是否文学作品,不是因为它讲述或描写了什么,而是取决于它是怎么讲述、怎么描写的。一件作品的“怎么”形成了这件作品的精神风貌,它是简约的,还是繁缛的,是清丽的,还是浓艳的,是婉约的,还是豪放的,是优美的,还是雄伟的,等等,都是由其选词造句、结构框架、气息节奏、叙述技巧等决定的,一言以蔽之,是由其风格决定的。因此,依据“信、达、雅”的标准,翻译文学作品,只有“信、达”还不够,必须有“雅”,即必须有文学性,也即是说,必须传达出原作的风格,然后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实现所追求的理想。然而,什么是原作的风格,什么是译作的风格,原作的风格和译作的风格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翻译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风格可译不可译的问题。简言之,认为风格可译的,大多是主张直译的人,一句挨一句地翻,就有可能多少传达原作的风格,有人将这些人称为语言学派,颇有不屑的意味;主张风格不可译的,大多是主张意译的人,他们自称文艺学派,由于认为原作的风格不可译,就随便给译作一种他们认为美的风格。主张风格不可译者未必明确地声称风格不可译,也不是都反对“信、达、雅”,不过他们以为“雅”就是高雅、典雅、美的词汇,雅的句子,就是文采,而且认为只有华丽才是文采,总之,认为翻译是“美化之艺术”。一经美化,译作倒是有了风格,但已不是原作的风格了。在持这种观点的翻译家的眼中,什么原作的风格,译作的风格,根本是两种不相干的东西,各自管各自的事情好了。在他们的译作中,不,应该说在他们的“创作”中,出现一些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词汇或表达方式,就毫不奇怪了。读者不免怀疑,难道外国人也有相同或类似的俗语和陈词滥调吗?一味求美,则雕缋满眼,其实只是堆砌辞藻,而真正的美则荡然无存了。不过,就实际的情况来说,真正“美化”的翻译实在是太少了,文艺学派的翻译家们似乎在沙盘推演,纸上谈兵。如果一定要分出派来的话,我宁愿加入直译派。
译作的风格只能以原作为依归,能否传达原作的风格,应该视为文学翻译的境界。是否达到了,则要看译者个人的造化。也许传达原作的风格只能是的理想,可望而难即,然而“望”与“不望”,差距不止毫厘。宋严羽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趋愈远;……”八百年前的古人之言,可供今之译者深思。你可能实现不了这种理想、进入不了这种境界,但是你正走在实现这种理想和进入这种境界的道路上。诚然,传达原作的风格,是很难的一件事,也许百不一见。但是,能不能是一回事,难不难是另一回事,不可将“很难”视作“不能”。译者主观上是否具有传达的意图,其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有,就会自设藩篱,循迹而行,或可在译文中见原作风格于一二;没有,就会自由散漫,失去约束,原作的风格也将不知所终。如此则不仅“雅”失去了准的,恐怕连“信、达”都要打折扣了。传达原作的风格是很困难的,但是有为的译者正是要克服这种困难,成就与原作相配的译作,正如杨绛先生在《艺术与克服困难》中所说:“创作过程中遇到阻碍和约束,正可以通过作者去搜索、去建造一个适合于自己的方式;而在搜索和建造的同时,他也锤炼了所要表达的内容,使合乎他自建的形式。这样他就把自己深刻、真挚的思想感情很完美地表达出来,成为伟大的艺术品。好比一股流水,遇到石头阻拦,又有堤岸的约束,得另觅途径,却又不能逃避阻碍,只好从石缝中迸出,于是就激荡出波澜,冲溅出浪花来。”石头、堤坝、石缝等等,好比实现艺术目的的种种困难,原作者要克服困难,译者也要跟随着原作者克服困难,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有限制的艺术,所谓戴着镣铐的舞蹈。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