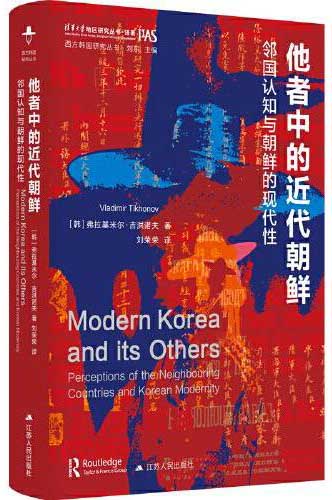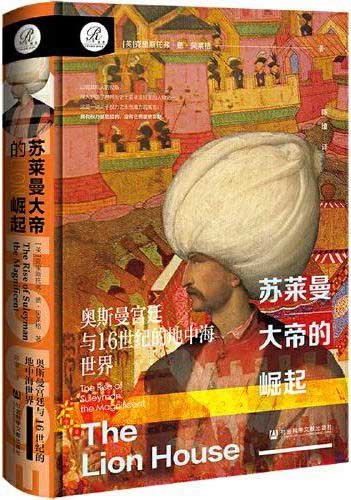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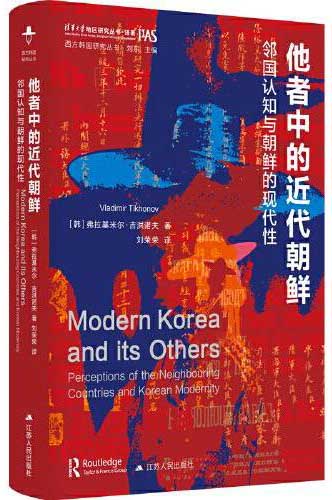
《
他者中的近代朝鲜(西方韩国研究丛书)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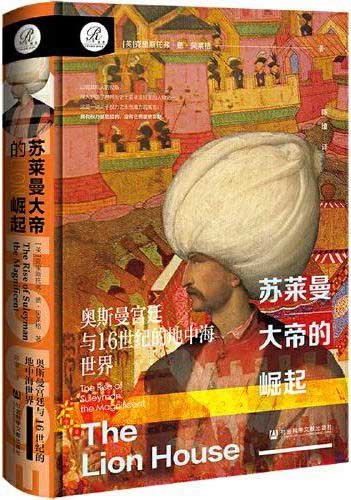
《
索恩丛书·苏莱曼大帝的崛起:奥斯曼宫廷与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
》
售價:NT$
403.0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NT$
454.0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NT$
454.0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NT$
352.0

《
应对百年变局Ⅲ: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新发展格局
》
售價:NT$
398.0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NT$
454.0

《
《诗经》全注全译全本彩图 全书系列50万册焕新升级典藏纪念版
》
售價:NT$
2545.0
|
| 內容簡介: |
内容介绍:
◎在故宫藏品中,品汉字书写之美,感悟“千古风流人物”
◎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故宫艺术的典藏读本
◎收录两岸故宫及海内外博物馆近百幅书法高清详图,全彩印刷,精装典藏
祝勇用诗意的语言、散文的笔法、史学的态度,以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怀素、张旭、蔡襄、蔡京、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十余位古代书法家为线索,选取两岸故宫收藏的书法名作,讲述了这些书法名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再现了这些书法家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
关于“故宫”,祝勇这么说:
六百年的宫殿(到2020年,紫禁城刚好建成六百周年)、七千年的文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就不见了踪影。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认真地注视和倾听。
关于“书法”,祝勇这么说:
书法,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是世界上*美的独语。一个人心底的话,不能被听见,却能被看见,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还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
|
| 關於作者: |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出版《故宫六百年》《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
任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历史的拐点》《苏东坡》、北京电视台大型文化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季)总编剧,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天山脚下》获评“新中国70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藏作品”。
|
| 目錄:
|
序章 汉字书写之美
章 李斯的江山
第二章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第三章 纸上的李白
第四章 血色文稿
第五章 吃鱼的文化学
第六章 蔡襄以及蔡京
第七章 欧阳修的醉与醒
第八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
第九章 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
第十章 他的世界里没有边境
第十一章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第十二章 挑灯看剑辛弃疾
第十三章 西线无战事
第十四章 崖山以后
图版目录
注释
|
| 內容試閱:
|
一
关于故宫收藏的文物,我已经出版过《故宫的古物之美》三卷,其中卷写器物,第二卷和第三卷写绘画,这是第四卷,内容全部关涉故宫收藏的历代法书,但本书的写作历程却很漫长,我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写的篇文章,就是收在本书中的《永和九年的那场醉》,至今已经过去了近十年。十年中,我零零星星地写,陆陆续续地发表(其间也写了其他作品),先是在《十月》杂志上,开了一个名叫《故宫的风花雪月》的专栏,后来又在《当代》开了一个专栏,杂志社给我起名,叫《故宫谈艺录》,自2017 年开始,一直写到现在,今年是第五年,这是《当代》杂志,也是我自己开得久的一个专栏。
这两个专栏里的文章,有关于故宫藏古代绘画的,也有关于法书的,但在《当代》上的专栏文章,关于历代法书的居多。我对法书有着长久的迷恋,这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写字人(广义上的),对文字,尤其是汉字之美有着高度的敏感。瑞典汉学家林西莉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汉字王国》,是一本讲甲骨文的书,我喜欢它的名字:“汉字王国”。古代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由汉字连接起来的王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必定会想到统一汉字,因为当时各国的文字千差万别,只有“书同文”,“国”才算是真正地统一。没有文字的统一,秦朝的江山就不是真正的一统。我在《李斯的江山》里写:“一个书写者,无论在关中,还是在岭南,也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庙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种相互认识的文字在书写和交谈。秦代小篆,成为所有交谈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话’。”“文化是强有力的黏合剂,小篆,则让帝国实现了无缝衔接”。
二
汉字是国族聚合的纽带,还是世界上造型感的文字,而软笔书写,又使汉字呈现出变幻无尽的线条之美。中国人写字,不只是为了传递信息,也是一种美的表达。对中国人来说,文字不只有工具性,还有审美性。于是在“书写”中,产生了“书法”。
“书法”,原本是指“书之法”,即书写的方法——唐代书学家张怀瓘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周汝昌先生将其简化为:用笔、结构、风格。它侧重于写字的过程,而非指结果(书法作品)。“法书”,则是指向书写的结果,即那些由古代名家书写的、可以作为楷模的范本,是对先贤墨迹的敬称。
只有中国人,让“书”上升为“法”。西方人据说也有书法,我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到过印刷术传入之前的书籍,全部是“手抄本”,书写工整漂亮,加以若干装饰,色彩艳丽,像“印刷”的一样,可见“工整”是西方人对于美的理想之一,连他们的园林,也要把蓬勃多姿的草木修剪成标准的几何形状,仿佛想用艺术
来证明他们的科学理性。周汝昌先生讲,“(西方人)‘精美’的书法可以成为图案画”,但是与中国的书法比起来,实在是小儿科。这缘于“西洋笔尖是用硬物制造,没有弹力(俗语或叫‘软硬劲儿’),或有亦不多。中国笔尖是用兽毛制成,特点与要求是弹力强”。
与西方人以工整为美的“书法”比起来,中国法书更感性,也更自由。尽管秦始皇(通过李斯)缔造了帝国的“标准字体”——小篆,但这一“标准”从来不曾限制书体演变的脚步。《泰山刻石》是小篆的极致,却不是中国法书的极致。中国法书没有极致,因为在一个极致之后,紧跟着另一个极致。任何一个极致都是阶段性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使中国书法,从高潮涌向高潮,从胜利走向胜利,自由变化,好戏连台。
工具方面的原因,正是在于中国人使用的是这一支有弹性的笔,这样的笔让文字有了弹性,点画勾连、浓郁枯淡,变化无尽,在李斯的铁画银钩之后,又有了王羲之的秀美飘逸、张旭的飞舞流动、欧阳询的法度庄严、苏轼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的“树梢挂蛇”、宋徽宗“瘦金体”薄刃般的锋芒、徐渭犹如暗夜哭号般的幽咽顿挫……同样一支笔,带来的风格流变,几乎是无限的,就像中国人的自然观,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亦如太极功夫,可以在闪展腾挪、无声无息中,产生雷霆万钧的力度。
我想起金庸在小说《神雕侠侣》里,写到侠客朱子柳练就一身“书法武功”,与蒙古王子霍都决战时,兵器竟只有一支毛笔。决战的关键回合,他亮出的就是《石门颂》的功夫,让观战的黄蓉不觉惊叹:“古人言道:‘瘦硬方通神’,这一路‘褒斜道石刻’当真是千古未有之奇观。”以书法入武功,这发明权想必不在朱
子柳,而应归于中国传统文化造诣极深的金庸。
《石门颂》的书写者王升,就是一个有“书法武功”的人。张祖翼说《石门颂》:“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我胆怯,我力弱,但我不死心,每次读《石门颂》拓本,都让人血脉偾张,被它煽动着,立刻要研墨临帖。但《石门颂》看上去简单,实际上非常难写。我的笔触一落到纸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原
因很简单:我身上的功夫不够,一招一式,都学不到位。《石门颂》像一个圈套,不动声色地诱惑我们,让我们放松警惕,一旦进入它的领地,临帖者立刻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三
对中国人来说,美,是对生活、生命的升华,但它们从来不曾脱离生活,而是与日常生活相连、与内心情感相连。从来没有一种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孤悬于生命欲求之外的美。今天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名器,许多被奉为经典的法书,原本都是在生活的内部产生的,到后来,才被孤悬于殿堂之上。我们看秦碑汉简、晋人残纸,在上面书写的人,许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它们对美的追求却丝毫没有松懈。时光掩去了他们的脸,他们的毛笔,在暗中舞动,在近两千年之后,成为被我们伫望的经典。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大量的秦汉碑帖,在这些碑帖中,我独爱《石门颂》。其他的碑石铭文,我亦喜欢,但它们大多出于公共目的书写的,有点像今天的大众媒体,记录着王朝的功业(如《石门颂》)、事件(如《礼器碑》)、祭祀典礼(如《华山庙碑》)、经文(如《熹平石经》),因而它的书写,必定是权威的、精英的、标准化的,也必定是浑圆的、饱满的、均衡的,像《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字正腔圆,简洁铿锵。唯有《石门颂》是一个异数,因为它在端庄的背后,掺杂着调皮和搞怪,比如“高祖受命”的“命”字,那一竖拉得很长,让一个“命”字差不多占了三个字的高度。“高祖受命”这么严肃的事,他居然写得如此“随意”。很多年后的宋代,苏东坡写《寒食帖》,把“但见乌衔纸”中“纸”(“帋”)字的一竖拉得很长很长,我想他说不定看到过《石门颂》的拓本。或许,是一纸《石门颂》拓片,怂恿了他的任性。
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大量的汉代简牍,这些简牍,就是一些书写在竹简、木简上的信札、日志、报表、账册、契据、经籍。与高大厚重的碑石铭文相比,它们更加亲切。这些汉代简牍(比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大多是由普通人写的,一些身份微末的小吏,用笔墨记录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字,不会出现在显赫的位置上,不会展览在众目睽睽之下,许多就是寻常的家书,它的读者,只是远方的某一个人,甚至有许多家书,根本就无法抵达家人的手里。因此那些文字,更没有拘束,没有表演性,更加随意、潇洒、灿烂,也更合乎“书法”的本意,即:“书法”作为艺术,价值在于表达人的情感、精神(舞蹈、音乐、文学等艺术门类莫不如此),而不是一种真空式的“纯艺术”。
在草木葱茏的古代,竹与木,几乎是容易得到的材料。因而在纸张发明以前,简书也成为流行的书写方式。汉简是写在竹简、木简上的文字。“把竹子剖开,一片一片的竹子用刀刮去上面的青皮,在火上烤一烤,烤出汗汁,用毛笔直接在上面书写。写错了,用刀削去上面薄薄一层,下面的竹简还是可以用。(内蒙古额济纳河沿岸古代居延关塞出土的汉简,就有削去成刨花有墨迹的简牍。)”烤竹子时,里面的水分渗出,好
像竹子在出汗,所以叫“汗青”。文天祥说“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源于这一工序,用竹简(“汗青”)比喻史册。竹子原本是青色,烤干后青色消失,这道工序被称为“杀青”。
面对这些简册(所谓的“册”,其实就是对一条一条的“简”捆绑串连起来的样子的象形描述),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毛笔在上面点画勾写时的流畅与轻快,没有碑书那样肃括宏深、力敌万钧的气势,却有着轻骑一般的灵动洒脱,让我骤然想起唐代卢纶的那句“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当笔墨的流动受到竹木纹理的阻遏,而产生了一种滞涩感,更产生了一种粗朴的美感。
其实简书也包含着一种“武功”——一种“轻功”,它不像飞檐那样沉重,具有一种庄严而凌厉的美,但它举重若轻,以轻敌重。它可以在荒野上疾行,也可以在飞檐上奔走。轻功在身,它是自由的行者,没有什么能够限制它的脚步。
四
那些站立在书法艺术上的人,正是在这一肥沃的书写土壤里产生的,是这一浩大的、无名的书写群体的代表人物。我们看得见的,是这些“名人”;看不见的,是他们背后那个庞大到无边无际的书写群体。“名人”们的书法老师,也是从前那些寂寂无名的书写者,所以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杨守敬在《平碑记》里说,那些秦碑,那些汉简,“行笔真如野鹤闻鸣,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假如说那些“无名者”在汉简牍、晋残纸上写下的字迹代表着一种民间书法,有如“民歌”的嘶吼,不加修饰,率性自然,带着生命中真挚的热情、真实的痛痒,那么本书写到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蔡襄、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人,则代表着知识群体对书法艺术的提炼与升华。唐朝画家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我的理解是,所谓造化,不仅包括山水自然,也包括红尘人间,其实就是我们身处的整个世界,在经过心的熔铸之后,变成他们的艺术。书法是线条艺术,在书法者那里,线条不是线条,是世界,就像石涛在阐释自己的“一画论”时所说:“此一画收尽鸿蒙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
他们许多是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巨人,但他们首先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被记住的。在我看来,不以“专业”书法家自居的他们,写下的每一片纸页,都要比今天的“专业”书法家更值得我们欣赏和铭记。书法是附着在他们的生命中,内置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的。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笔迹的圈圈点点、横横斜斜,牵动着他们生命的回转、情感的起伏。像张旭,肚子痛了,写下《肚痛帖》;像怀素,吃一条鱼,写下《食鱼帖》;像蔡襄,脚气犯了,不能行走,写下《脚气帖》;更不用说苏东坡,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寒食节,把他的全部委屈与愤懑、呐喊与彷徨全部写进了《寒食帖》。李白《上阳台帖》、米芾《盛制帖》、辛弃疾《去国帖》、范成大《中流一壶帖》、文天祥《上宏斋帖》,无不是他们内心世界真切的表达。当然也有颜真卿《祭侄文稿》《裴将军诗帖》这样洪钟大吕式的震撼人心之作,但它们也无不是泣血椎心之作,书写者的直率的性格、喷涌的激情和“向死而生”的气魄,透过笔端贯注到纸页上。他们信笔随心,所以他们的法书浑然天成,不见营谋算计。我在那篇写陆游的《西线无战事》里所说:“书法,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是世界上美的独语。一个人心底的话,不能被听见,却能被看见,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还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
他们之所以成为今人眼中的“千古风流人物”,秘诀在于他们的法书既是从生命中来,不与生命相脱离,又不陷于生活的泥潭不能自拔。他们的法书,介于人神之间,闪烁着人性的光泽,又不失神性的光辉。一如古中国的绘画,永远以四十五度角俯瞰人间(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离世俗很近,触手可及,又离天空很近,仿佛随时可以摆脱地心引力,飞天而去。所谓潇洒,意思是既是红尘中人,又是红尘外人。中国古代艺术家把“四十五度角哲学”贯彻始终,在我看来,这是艺术创造的角度,也是中华艺术优越于西方的原因所在(西方绘画要么像宗教画那样在天国漫游,要么彻底下降到人间,像文艺复兴以后的绘画那样以正常人的身高为视点进行平视)。
我们有时会忽略他们的书法家身份,一是因为他们在其他领域的光芒太过耀眼(如李斯、李白、“唐宋八大家”、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遮蔽了他们在书法领域的光环,其次是因为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还有亲笔书写的墨迹留到今天,更无从感受他们遗留在那些纸页上的生命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历代的收藏者,感谢今天的博物院,让汉字书写的痕迹,没有被时间抹去。有了这些纸页,他们的文化价值才能被准确地复原,他们的精神世界才能完整地重现,我们的汉字世界才更能显示出它的瑰丽妖娆。
五
书法,不仅因其产生得早(甲骨文、石鼓文、金文),更因其与心灵相通,而成为一切艺术的根基。譬如绘画,赵孟说“书画本同源”,实际上就是从书法中寻找绘画的源头,赵孟在绘画创作中,起笔运笔、枯湿浓淡中,还特别强调书法的笔墨质感。音乐、诗歌、戏剧、小说,它们叙事的曲线、鲜明的节奏感,乃至闪烁其中的魔法般的灵感火光,不能说没有书法的精髓渗透在其中。我们住在语言里,语言住在文字里,文字住在法书里。正如我在《血色文稿》里所写:“语言的效用是有限的,越是复杂的情感,语言越是难以表达,但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古人都交给了书法。书法要借助文字,也借助语言,但书法又是超越文字,超越语言的。书法不只是书法,书法也是绘画,是音乐,是建筑——几乎是所有艺术的总和。书法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或许,在古人眼中亦如是),书法是一切艺术中核心的,也是的形式,甚至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它就是生命本身。”
这是一本关于法书的书,但它不是书法史,因为它还关涉着文学史、音乐史、戏剧史、美术史,甚至是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重要的,是生活史、生命史、心灵史。常见的书法史里装不下这些大历史,但书法史本身就应该是大历史,世界上不存在一部与其他历史无关的书法史。这也是本书写到了书法史以外看似无关、鸡零狗碎的事物的原因。
千百年过去了,这些书写者的肉体消失了,声音消失了,所有与记忆有关的事物都被时间席卷而去,但他们的文字(以诗词文章的形式)留下来了,甚至,作为文字的形式的法书(诗词尺牍的手稿)也留传下来,不只是供我们观看,而且供我们倾听、触摸、辨认——倾听他们的心语,触摸他们生命的肌理,辨认他们精神的路径。
人们常说“见字如面”,见到这些字,写字者本人也就鲜活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早已随风而逝,但这些存世的法书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真的消逝。他们在飞扬的笔画里活着,在舒展的线条里活着。逝去的是朝代,而他们,须臾不曾离开。
......
李斯的时代,是小篆的时代。此前,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字体是大篆。广义地说,大篆就是商周时代通行的、区别于小篆的古文字。这种古韵十足的字体,被大量保存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石鼓、龟甲、兽骨上,文字也因刻写材料的不同,分为金文(也称钟鼎文[图1-1])、石鼓文和甲骨文。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件先秦石鼓( 又称“ 陈仓石鼓”[图1-2])上,可以看见中国早的石刻文字[图1-3],被称为“篆书之祖”,一字抵万金,被康有为誉为“中华文物”。这十只先秦石鼓,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每个重约一吨,每个石鼓上镌刻的“石鼓文”,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使用的大篆,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它上承秦公簋(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下接小篆,是中国文字由大篆向小篆衍变,在尚未定型时期的过渡性字体,结体促长伸短,字形方正丰厚,笔触又圆融浑劲,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透露出秦国上升时期强悍雄浑的力量感。
大篆的写法,各国不同,笔画烦琐华丽,巧饰斑斓。秦灭六国,重塑汉字就成为政府号文化工程,丞相李斯亲力亲为,为帝国制作标准字样,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于是,一种名为小篆的字体,就这样出现在书法史的视野中。
这种小篆字体,不仅对文字的笔画进行了精简、抽象,使它更加简朴、实用,薄衣少带、骨骼精练,更重要的是,在美学上,它注意到笔画的圆匀一律、结构的对称均等,字形基本上为长方形,几乎字字合乎二比三的比例,符合视觉中的几何之美。这使文字整体上显得规整端庄,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力量感,透过小篆,秦始皇那种正襟危坐、睥睨天下的威严形象,隐隐浮现。
其实,早在秦始皇之前,大禹就已经把自己的功绩刻写在石头上了——治水完成后,大禹用奇特的古篆文,在天然峭壁上刻下一组文字,从此成为后世金石学家们终生难解的谜题。大禹的行动说明,文字不只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对此,我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也是华夏政治的核心。美术史家巫鸿说:“从一开始,立碑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纪念和标准化的主要方式。”“碑定义了一种合法性的场域(legitimate site),在那里‘共识的历史’(consensual history)被建构,并向公众呈现。”华夏词库里的很多词语,或许因此而生成,比如树碑立传,比如刻骨铭心。
被大禹镌刻的这块石头,被称作《禹王碑》。人们发现它,是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岣嵝峰左侧的苍紫色石壁上,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作《岣嵝碑》。这应该是中国古老的铭刻,文字分九行,共七十七个字,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三年,也只认出三个字。唐朝时,复古运动领袖韩愈曾专赴衡山寻找此碑,却连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失望之余,写下一首诡秘的诗作——《岣嵝山禹王碑》。当然,对于这一神秘物体的来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众说不一,但即使从唐朝算起,这块铭刻也足够久远了。
帝王们把各自的历史凝固在石头上,试图通过石头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强化自身的威权。但我们不得不说,在对文字的运用上,秦始皇比大禹还要聪明,因为对他来说,文字不只是为了抵抗忘却,也是他操控现实政治的工具。秦始皇用标准化生产的方式炮制了长城和兵马俑,他当然对工具的意义了如指掌。他知道文字是文化的基本材料,只有把文字这件工具标准化,他才能真正驾驭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因此,在夏禹那里,文字是死的;而在秦始皇手中,文字是活的,像他的臣民一样,对他唯命是从。
文字也是一个“国”。“中国”的“国”字,里面包含着一个“戈”字,后来变成“玉”,其实后者更能概括中国的性质。“玉”是什么?“玉”是文化。真正的“国”,却不是由武器,而是由文化构建的。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文字。那时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那时的“天下”,不只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或者说,是文化的,因为它从来没有一道明确和固定的边界。国的疆域,其实就是文化的疆域。秦始皇时代,小篆,就是这国家的界碑。
一个书写者,无论在关中,还是在岭南,也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庙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种相互认识的文字书写和交谈。秦代小篆,成为所有交谈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话”。它跨越了山川旷野的间隔,缩短了人和人的距离,直至把所有人黏合在一起。文化是强有力的黏合剂,小篆,则让帝国实现了无缝衔接,以至于今天,大秦帝国早已化作灰烟,但那共同体留了下来,比秦始皇修建的长城还要坚固,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遗产。
——章:李斯的江山
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上班的天,郑欣淼先生的博士徐婉玲说,午门上正办“兰亭特展”,相约一起去看。尽管我知道,王羲之的那份真迹,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得益于两岸故宫的合作,依旧不失为一场文化盛宴。那份真迹消失了,被一千六百多年的岁月隐匿起来,从此成了中国文人心头的一块病。我在展厅里看见的是后人的摹本,它们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陆继善、陈献章、赵孟、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甚至宋高宗赵构、清高宗乾隆……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南宋赵孟坚,曾携带一本兰亭刻帖过河,不想舟翻落水,救起后自题:“性命可轻,《兰亭》至宝。”这份摹本,也从此有了一个生动的名字——“落水《兰亭》”。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书法,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后一千六百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些复制品,是治文人心病的药。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 年)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等朋友及子弟四十二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褉”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
魏晋名士尚酒,史上有名。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王羲之的酒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羲之写照图》,图中的王羲之,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酒杯是小的,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总之,兰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集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更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卷《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卷《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乃至百遍,都达不到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传家宝。
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张纸究竟能走出多远?
一种说法是,《兰亭序》的真本传到王氏家族第七代孙智永的手上,由于智永无子,于是传给弟子辩才,后被唐太宗李世民派遣监察御史萧翼,以计策骗到手;还有一种说法,《兰亭序》的真本,以一种更加离奇的方式流传。唐太宗死后,它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夜里。后世的评论者说:“《兰亭序》真迹如同天边绚丽的晚霞,在人间短暂现身,随即消没于长久的黑夜。虽然士大夫家刻一石让它化身千万,但是山阴真面却也永久成谜。”
——第二章: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颜真卿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书法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中的英雄、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写下《祭侄文稿》的。书法史上有名的书法家其实都是“兼职”,都不“专业”,否则他们就沦为了技术性的抄写员—— 一个被他人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因此,假如有一个“书法史”存在,它也是和“政治史”“思想史”混在一起的。以唐朝而论,无论皇帝,还是公卿大臣,大多书法优秀,他们书写,并不是为了出“作品”,而是为了传达思想、表达情感。“天下三大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东坡《寒食帖》,都是在某一事件的触发下写成的,都有偶发性,在偶然间,触发、调动了书写者庞大的精神和情感系统,像文学里的意识流,记录下他们的心绪流动。
颜真卿不是用笔在写,而是用心,用他的全部生命在写。他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他手里的笔,让积压在心头、时时翻搅的那些难言的情愫,都通过笔得到了表达。
语言的效用是有限的,越是复杂的情感,语言越是难以表达,但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古人都交给了书法。书法要借助文字,也借助语言,但书法又是超越文字,超越语言的,书法不只是书法,书法也是绘画、是音乐、是建筑——几乎是所有艺术的总和。书法的价值是不可比拟的,在我看来(或许,在古人眼中亦如是),书法是一切艺术中核心的,也是的形式,甚至于,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艺术,它就是生命本身。
就此可以理解,弘一法师李叔同,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近代文艺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身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的全能型选手、夏丏尊眼中的“翩翩之佳公子”“多才之艺人”,遁入空门之后,所有的艺术活动都渐渐禁绝,唯有书法不肯舍弃。他的书法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融汇在他的笔墨中,使他的书法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闲雅冲逸。连一向挑剔的鲁迅,在面对他的书法时,都忍不住惊呼:“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他圆寂的时候,应当是不著一字的,在我看来,那才算得上真正的潇洒,真正的“空”,但他还是写了,“悲欣交集”四个字,容纳了他一生的情感。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李叔同的心里,书法在他的心里占据着多么不可撼动的位置,能表达他心底复杂情感的,只有书法,在他眼里,书法是艺术中的艺术。
当然,只有汉字能够成就这样高级的艺术,拉丁字母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艺术,这也是西方人很难读懂中国书法,进而很难读懂中国文化的原因。他们手里的笔不是笔,是他心脏、血管、神经的延伸,是他肉身的一部分,因此,他手里的笔不是死物,而是有触感,甚至有痛感的。只有手里的笔,知道书写者心底的爱与仇。
同理,《祭侄文稿》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书法作品,我说它是“超书法”,是因为书法史空间太小,容不下它;颜真卿也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写下《祭侄文稿》的,《祭侄文稿》只是颜真卿平生功业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当安禄山反于范阳,颜真卿或许就觉得,身为朝廷命臣,不挺身而出就是一件可耻的事。像初唐诗人那样沉浸于风月无边,已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梦想,此时的他,必须去超越生与死之间横亘的关隘。
我恍然看见颜真卿写完《祭侄文稿》,站直了身子,风满襟袖,须发皆动,有如风中的一棵老树。
——第四章:血色文稿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