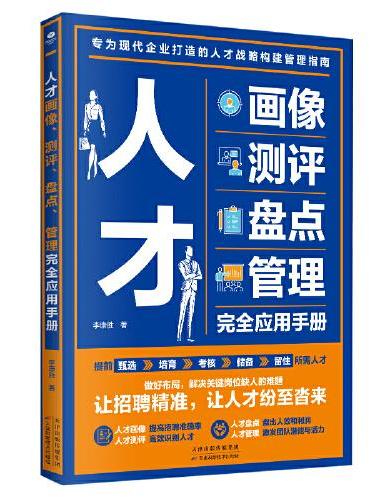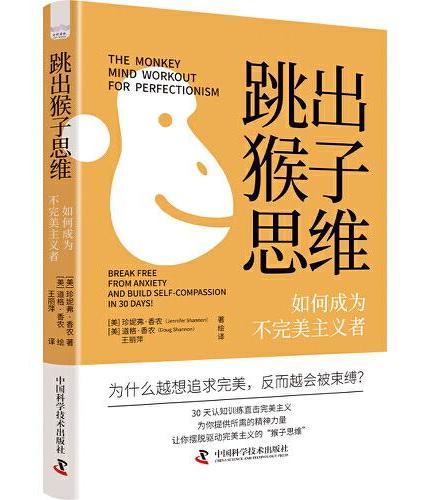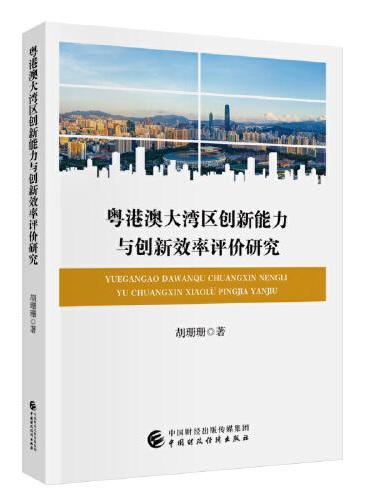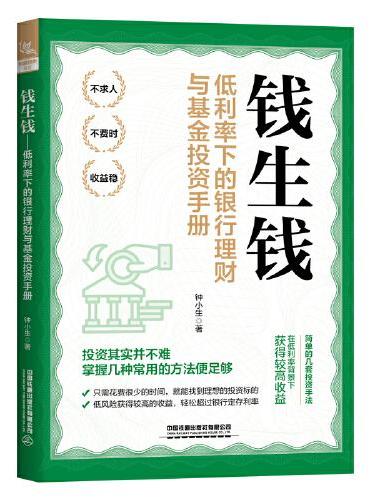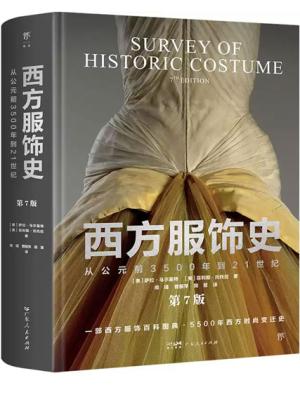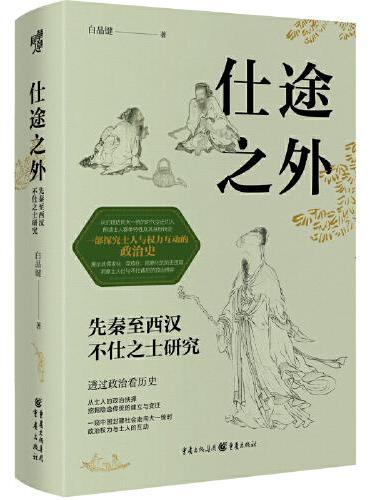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
跳出猴子思维: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30天认知训练打破完美主义的困扰!实现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改变!)
》 售價:NT$
301.0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售價:NT$
398.0
《
钱生钱:低利率下的银行理财与基金投资手册
》 售價:NT$
352.0
《
西方服饰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21世纪(第7版,一部西方服饰百科图典。5500年时尚变迁史,装帧典雅,收藏珍品)
》 售價:NT$
2030.0
《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
》 售價:NT$
305.0
編輯推薦:
民族国家的出现,是构成现代中国史学有别于传统史学重要的差异,此一差异不只将民族国家视为现代史学形成的外在条件,抑且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不论在时间、空间和记载人群活动的事类等范畴,民族国家都成了根本且不证自明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历史如何被重新书写?新的历史知识如何建立?历史学家如何操作不同的社会网络,传播新的历史观念给一般广大群众?因着民族主义、战争动员而逐渐趋于单一化的叙事方式,是不是摧折了历史原本复线多元发展的可能性?
內容簡介:
本书将从知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国家的观念如何制约着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以及标榜着科学、客观的研究方法和制度化的学术机制,又是如何为历史书写的公正品质提供保证,从而使人们相信学院生产的历史知识为真。
關於作者:
刘龙心,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东吴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东亚研究中心(Modern East Asia Research Centre, Leiden Universit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知识史、学术思想史。著有《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2002年)、《王权释放与近代空间生产——20世纪初的调查旅行》、《地志书写与家国想象——民初〈大中华地理志〉的地方与国家认同》等专书、期刊论文多篇。
目錄
简体版序
內容試閱
简体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