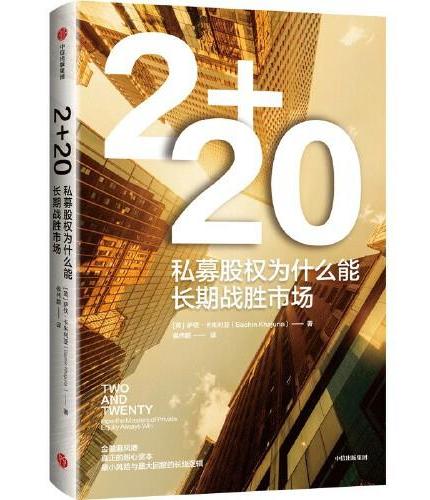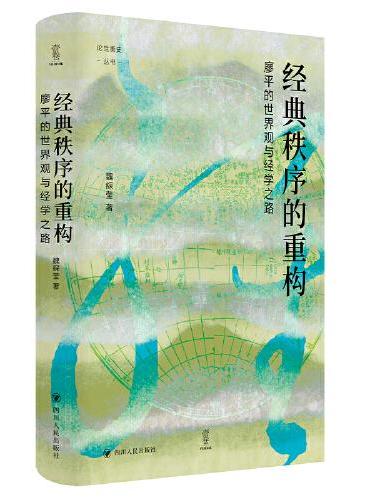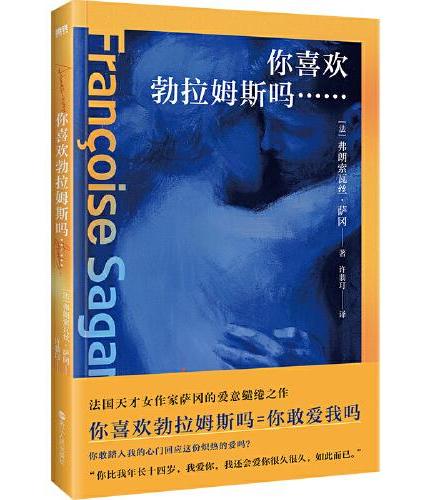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NT$
254.0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NT$
296.0

《
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看英国科普黄金时代的科学家如何担当科普主力,打造科学共识!)
》
售價:NT$
403.0

《
太极拳套路完全图解 陈氏56式 杨氏24式和普及48式 精编口袋版
》
售價:NT$
1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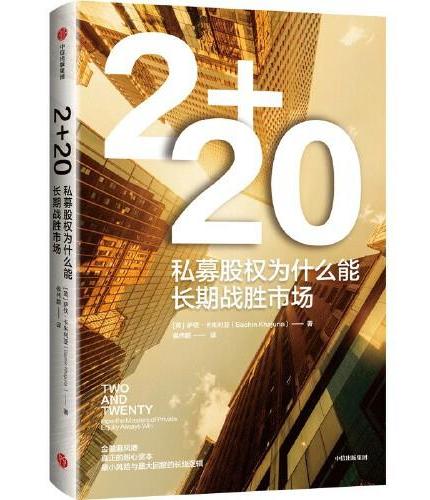
《
2+20:私募股权为什么能长期战胜市场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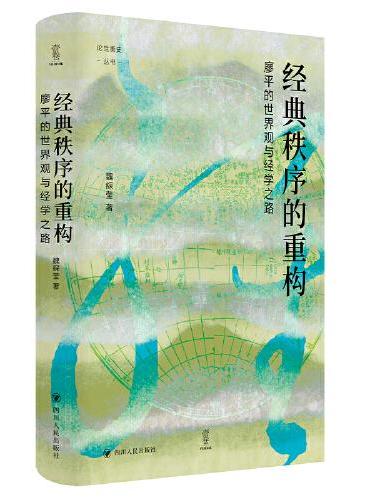
《
经典秩序的重构:廖平的世界观与经学之路(探究廖平经学思想,以新视角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在西学冲击下的转型)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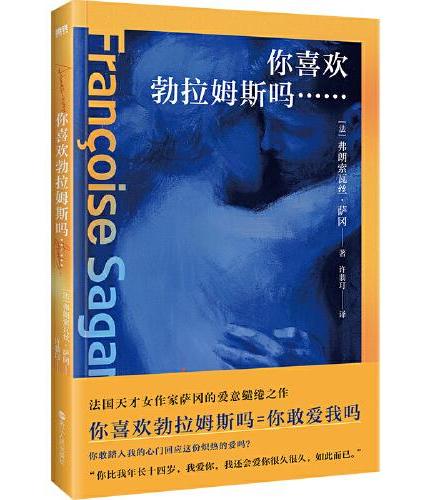
《
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
售價:NT$
245.0

《
背影渐远犹低徊:清北民国大先生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大众政治兴起,古代帝国失效,当代读者更应关注近代帝国
大众政治到来,掠夺型政府消失,以前被“官民关系”遮掩的族群问题必须在大众政治的框架内得到解决。近代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有和异己携手共建政治共同体的经验,古代帝国是机械堆积的结果,依赖的是人民的政治冷漠与顺从。从这个角度讲,古代帝国都几乎不是什么让人惊异、眼睛一亮的创举。我们很难说,古代帝国的治理术对现代政治实践能有什么借鉴作用,真正需要观察的,是那些活动在大众政治年代里的帝国。
各近代欧洲帝国的多元性更强,观察它们如何应对大众政治年代所带来的压力,不仅能使我们看到人类政治想象与政治设计的界限,同时也能为现代一些限于多元社会纷争的国度提供某些历史教训,因为它们有的时候也是在“统治不可统治之地”。
※详述近代帝国的统治压力与应对之道,提纲挈领勾勒帝国的技艺
帝国压力来自内外两个层面 :在内,帝国的扩张、发展与维持会冲击核心区既有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形态,从而破坏本地的政治平衡。在外,近代环境下,核心区对边缘区的统治不能只是简单地以军事优势为基础的统治,而必须有一定的法理基础 ;过去那种上下统治关系,必须以“群群关系”替代,
|
| 內容簡介: |
帝国,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政治构造,航行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风暴中。帝国的掌舵者们,并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有些船搁浅了,有些船则被时代大潮打成了碎片。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现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对我们而言,观察这些水手的举动(即使是他们在礁石上撞得粉碎的时候),仍然是有益的。《帝国的技艺》想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近代帝国是如何统治其多民族属民的?在统治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内在的困难?它们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帝国的技艺》有几个基本假设:,近代帝国并不只是征服—统治的等级关系,也不只是一撮人以某个地方及其人群为本部向外申延政治影响的工具和实体,其统治者、统治阶层通常都能超越狭隘的地区、人群本位,有切实的(当然同时也是自私的)整体考虑。第二,在许多帝国统治者眼中,帝国并不是一次短期投资,而是长期持有的一项事业。因此,凭借武力驾凌一方并不是长久之策。“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这不只是陆贾与刘邦才能理解的中国古代智慧,也是所有近代帝国的治国之道。第三,诸帝国的构建模式本身很复杂,并不一定是一个由帝国中心出发对边缘区、社群进行管制的同心圆。
简而言之,近代帝国并不是古代的遗迹,也不是急就章式的多民族、多地域的拼凑之物,而是有正经政治考量的多元政治实体。《帝国的技艺》将按如下线索展现对上述问题的思索。
引言中,《帝国的技艺》将介绍帝国的定义,解释为什么应该研究近代帝国而不是古代帝国。章,《帝国的技艺》将陈述本书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和假设—在近代,帝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诸帝国又是通过调整哪些政制、政策来应对这些挑战的。第二章至第五章,将英帝国、法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作为历史案例,以之来验证《帝国的技艺》的基本假设。在结语中,主要是将各个帝国的应对之道做一比较,指出异同,也简略讨论了帝国民族方略之间的关系、帝国选择各自方略的依据,以及帝国属民对帝国方略的反应。
|
| 關於作者: |
郑非
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从事比较政治研究,对族群政治、帝国政治与后发展国家政党政治感兴趣。著有《帝国的技艺》《帝国的失败》《帝国的分裂》等多部作品。
|
| 目錄:
|
序言 航行在民族主义的风暴中 / 001
引言 “帝国”的“通词膨胀”与古今之变 / 013
一 帝国是什么? / 013
二 帝国的古今之变 / 027
三 为什么研究近代帝国? / 037
章 帝国压力与帝国之道 / 051
一 帝国压力 / 051
二 帝国的分类 / 075
三 假说:帝国的应对之道 / 089
第二章 英帝国 / 097
一 反帝国主义 / 098
二 美国革命与帝国宪法 / 106
三 帝国改革运动:1837—1869 / 126
四 帝国联邦运动 / 149
五 社会隔离 / 161
第三章 法帝国 / 173
一 法帝国的源流与动力 / 175
二 帝国的治理方针 / 189
三 历史惯性与共和主义意识形态 / 201
四 帝国治理的后果 / 220
五 法帝国的终结:帝国改革计划的失败 / 245
第四章 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 / 253
一 帝国的由来与诸次改革 / 258
二 集权—隔离政治 / 294
三 制度隔离的效果 / 318
第五章 俄罗斯帝国 / 337
一 没有“帝国民族”的帝国 / 337
二 一个非正式的帝国 / 353
三 波兰综合征 / 363
四 俄罗斯化及其后果 / 384
五 俄罗斯化与革命 / 407
结语 帝国比较 / 417
参考文献 / 447
|
| 內容試閱:
|
上海人都知道,市里洋气、适合逛马路的地方是原来的法租界。那里的道路干净清爽,两边满是法式梧桐、花园洋房、咖啡馆与画廊。其实,从晚清到民国,法租界就已经是一个高档社区了。相形之下,英租界(公共租界)给人的印象就比较淡薄,外滩多的是高楼大厦、洋行商站,更像一个纯商业区。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同为租界,为什么英租界看起来就没有法租界那么宜人?
法国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中回答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法两国在租界管制上的理念、做法完全不同。用白吉尔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颠的自由主义制度,法租界则奉行雅各宾派的传统。一边是商人寡头挖空心思维护自身的利益,另一边则是专制官僚自称要为共和理想服务。”
大致来说,公共租界的管理方式是商人自治。对这些商人,英国领事告诫道:“在华英商应该自强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弃了这种态度,过多的依靠国家帮助,他们就不再是企业家……不再是英国人。”公共租界的领导机关是工部局,对市政建设兴趣寥寥。该租界的公共设施由私人投资,以盈利为目的,既不充足,也不普及,有也只供外国侨民使用,尽管在19世纪后期已经有大量的中国人选择在此生活。
法租界的情况就两样了,其奉行的是巴黎到上海的垂直行政管理。白吉尔指出,“如果说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于自由港的地位,那么法租界则像是一块受巴黎政府管辖的殖民飞地”。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领导机关)董事会虽然经由纳税人选举产生,但要听命于法国领事。法租界的年度行政预算是在巴黎规划制订,由外交部直接派发,市政建设的经费也得到了法国国内的支援。相比英国商人,在沪的法国商人要少得多,行政官僚、医生和传教士居于侨区的领导地位,其主要活动并不是求取利润,也不具备同巴黎抗衡的动机与实力。相比工部局,公董局更像一个巴黎派出的政府机关,有“大政府”的气魄。
这当然是由于法国大一统与政府集权传统所致,但公正地说,法国人对其属民,确实也要比英国人来得更“一视同仁”。虽然屈尊纡贵,但是,公董局或多或少都表示出对整体利益(租界的中外居民)的某种关心。“例如,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计划地进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设。反观公共租界所开辟的公园,直到1928年都禁止华人入内。”又比如,在公共租界,自来水由私人运营,向私人开放。在法租界,则是免费面向全体的。这是大革命时代共和理想的遗泽—人人平等、社会进步和理性规划。正是由于这种共和理想的普世性格,法租界在1914年就引入了两名中国士绅进入公董局担任咨询董事,这一举动比起公共租界要早12年。正是由于法租界的公共建设较好,所以当时有大批中国的富商、士绅搬到了法租界,为租界提供了大量的税源,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法租界公共建设的发展。正因如此,法租界才有了现在洋气宜人的外貌。
以上并不是要说,法租界的治理比英租界好,而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法租界的治理模式呈现了整个法兰西帝国的特性。在本章中,我们将部分以英法对比的形式介绍法帝国的治理方略。
一 法帝国的源流与动力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鼎盛时期,法国及其海外领土—有些人称之为“大法兰西”(La plus grande France),拥有1,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亿多居民。巴黎控制着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领地囊括加勒比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岛屿,北非、西非和赤道非洲上的大片土地,以及印度支那半岛和马达加斯加。如果说英帝国领土上的太阳永不落下,那么法帝国也是一样。
这个帝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的末尾,都会遭受一次明显的挫折,并出现大幅度退潮。我们可以大致将法帝国的发展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6世纪初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从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到1870年(第二帝国灭亡);从1875年第三共和国时期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去殖民化浪潮的高峰)。
法兰西殖民帝国是从16世纪早中叶开始的,当时,在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竞争中,法国开始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建立商贸点与殖民地。从一开始,法国人的殖民行为就跟英国人非常不同。日后德意志帝国的首相俾斯麦打趣说:“法国有殖民地,但没有殖民者。”俾斯麦虽然评论的是他那个时期法国人的殖民行为,但追溯历史,这一说法也是非常准确的。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领土的范围,它的富饶,一直以来都位列大陆强权中的头等。陆地一直是展示它力量与荣耀的国家舞台。海上贸易只不过是它存在的附属品。海洋从未激起,也永远不会激起那些航海和商业民族对之会有的那种尊敬和国家情绪。海洋事业从未吸引法国的重视,也没有获得财力或人才方面的帮助。”除了少数商人与冒险家,很少有法国人愿意出海定居。
拿法国北美殖民地新法兰西的重要据点魁北克来说,1763年,法国在“七年战争”中失败,并将之割让给英国人,当时魁北克的法裔人口总共才不过5万到8万(而其他地方多才有2万人),而英国的北美十三殖民地总人口已经达到了200万,实在是众寡悬殊。商人其实也并没有表现得更好一点,为了开拓海外领地而建立的私人公司大都纷纷失败。法属西印度公司在1664年建立,只勉强维持了10年就被政府接管。法属东印度公司同样在1664年建立,维持的时间虽要长得多,但是其开拓的力度不大,只维持了几个贸易点,在1769年同样被政府接管。其他的公司也纷纷破产。
由于缺乏足够的殖民者和足够的商业与社会刺激,法兰西殖民帝国很脆弱。当英国人通过“以海养海”获得海上霸权之后,法国在一系列海外战争(从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到拿破仑战争)中就一直居于下风,并逐渐丧失了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欧洲战争几乎完全使法国把目光从海外收回。强势如拿破仑·波拿巴,考虑到法国在北美的大片领土并无人居住因此难于保卫之后,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将路易斯安那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新生的美国。有一次,他表示并不愿意出售路易斯安那,认为美国将在两三百年后成为欧洲的威胁,但是他并无闲暇为后人操心。他对印度倒是表现出了兴趣,但那多半是为了打击英国,以及向亚历山大看齐。在拿破仑统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拿破仑的目标都是在欧洲建立一个大陆帝国,而不是一个海外帝国。
拿破仑埋头建设自己的大陆帝国无暇他顾(其帝国旋起旋灭,无足道),等到拿破仑战败,法国剩下的一些殖民地也相继丧失。法国留下的地盘只有加勒比海上的几座岛屿、纽芬兰附近的一个渔业基地、印度的几座商站、塞内加尔的四个老殖民城镇(被称为“四公社”),等等。
之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坐守困城”,也没有什么海外作为。直到1830年,法国才几乎从零开始重启海外征服事业。在此之前几年,法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阿尔及尔的藩属诸侯起了外交争端,到了1830年,法王查理十世内外交困,正面对一场可能的革命(七月革命),为此,他的首相建议他发动一场海外战争,来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于是,在该年6月,法军登陆阿尔及尔西部,并迅速击败本地的德伊,占据了阿尔及尔城。虽然这一胜利并没有挽救查理十世的政治生命(同年7月,法国人发动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是法国在阿尔及尔就此盘踞下来,开启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统治。在接下来的40年时间里,法国进行了一场耗资巨大又漫长的征服战争,将法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推进到突尼斯边境和撒哈拉沙漠的内陆地区,然后引入欧洲移民进行垦殖。这种由政治因素推动的征服,日后成了法兰西帝国的一大显著特征。
七月革命之后所建立的七月王朝(1830—1848年)是一个目光内敛的政权。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君王,他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喊出的口号是“通过勤劳与节俭而致富”。他本人在1842年国民议会中发表演讲说:“我坚信,总的来说,法国继续在远离本土的地区开拓新的大型殖民地是不合适的。”他认为,法国需要的是一些关键的贸易点,而不是殖民地。如此作为的原因在于,开拓与维持殖民地的费用高昂,非此时能够实现。
相较于他的资产阶级前任,拿破仑三世要激进得多。他的理想是实现“进步的君主制”。他和他的叔叔虽然都是法国大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但他努力向旧王朝靠拢,做“驯服法国革命的人”。但是帝国的革命色彩使他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皇帝这个头衔又使他与共和派反目。在没有确定社会阶层支持的情况下,皇帝陛下不得不依靠反复的借力打力与政治腾挪。他需要借助公决、普选产生的立法团体来表示自己受到了人民的拥戴,但又不能真的将之化为政治现实。为了应对这个两难局面,第二帝国需要一位张扬的君主,需要议题政治,需要皇帝陛下用宣传、游行、节庆、城市翻新和外交冒险来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以掩盖他帽子下面那只拿着兔子的手。所以在他的时代,法国四面出击,几乎同时进行了很多场冒险,有些惨痛地失败了,比如他试图在墨西哥扶植奥地利的一位王子,有些则获得了成功,比如他在1854年占领了新喀里多尼亚,在1854至1865年间持续推动对塞内加尔的殖民化,在1858至1870年间相继占领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与此同时,他也大大巩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占领与改造。
拿破仑三世的冒险终于以他在德法战争中的惨淡结局收场。法国战败,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给德国,巴黎公社起义,“一半人想要掐死另外一半”(福楼拜语)。令人吃惊的是,在分裂中新生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被证明带来了法兰西帝国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帝国高歌猛进,迅速成长,帝国的面积增加十倍不止。在东南亚,法国在1884至1887年间,陆续占领越南中部、北部,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1893年老挝也被纳入其中)。在北非,法国以阿尔及利亚为基地向东西方向扩张,突尼斯于1881年、摩纳哥于1912年沦为法国保护国;在西非,法国以塞内加尔为据点,逐次将几内亚、达荷美(贝宁旧称)、科特迪瓦、马里、毛里塔尼亚直到尼日尔等地都囊括旗下(于1895年成立所谓法属西非);在中非(赤道非洲),则是喀麦隆(从德国手上获得)、刚果、加蓬、乍得、中非等地(于1910年设立所谓法属赤道非洲);在南非,马达加斯加岛则于1896年落入法国之手。
为什么帝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狂飙突进?可能有好几个答案。简单的答案可能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动荡终于落下了帷幕。在此之前,法国始终有足够多的国内问题要处理,没有精力放在持久的海外事业上。
第二个答案则要归结于普法战争。这场大灾难大大刺激了法国人,甚至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法国人对海外帝国事业的态度。首先,法国人有迫切恢复大国地位、走出屈辱的心理动机。曾经两度担任法国总理的茹费理(Jules Ferry)是殖民事业的坚定支持者,1885年7月28日,他在众议院为其殖民政策辩护,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
(法国政府是否要)沉溺于这些痛苦而无所作为?是否准备当一个看客,任由其他民族控制突尼斯和越南……掌控赤道非洲地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民族是否伟大在于它遵循怎样的发展路径……(如果)没有实际行动,不参与世界事务……我保证这样的态度会使我们的国家很快走向终结……法国不能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她也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欧洲的命运中行使属于她的所有影响力。她必须在世界各地传播这种影响力,带去她的语言、习俗、旗帜、武力和精神。
在演讲后的第五年,茹费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其中,他给出了一个极短而有力的论断:“如果一个人只是待在后院,就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法国的众议院对茹费理报以热烈的掌声。茹费理的这些主张直接来自法国学者保罗·勒鲁瓦—波利欧( Paul Leroy-Beaulieu)于187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该文提出:“殖民就是一个民族的扩张,权力的复制,将一个民族的语言、习俗、思想传播到世界的过程。拥有多殖民地的民族是高等的民族,即便现在不是,有朝一日也会成为高等的民族。”换言之,由殖民入手,恢复国家荣誉。
其次,当时德国无论在人口还是出生率上都要远远超过法国(法国的人口年增长率为0. 3%,是整个欧洲的),法国需要在外部寻找人力资源充实自己。当时的普遍认知是,“为了拯救一个小法国,必须有一个更大的法国” 。“一战”时,帝国动员数百万海外属民为法国而战,就证明了这一动机。
后,由于普法战争耻辱性的失败,法国的军人也有挽回颜面的需要。库马尔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法国军人的这一愿望:“在撒哈拉沙漠和印度支那的丛林中,他们将消灭1870年至1871年的耻辱。此外,他们敏锐地感到这项任务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既有的需要,也有好的机会。他们经常主动采取行动,对巴黎文官政府的指令置若罔闻。”
那么,还有没有经济上的原因呢?
许多法国帝国主义者在为海外扩张提供理由时,确实提出了一些经济上的主张。比如,茹费理自己在1884年面对众议院说:“在经济领域,我这里有统计数据的支持,向你们说明了为殖民扩张政策辩护的各种考虑,从需要的角度来看,欧洲工业化人口,特别是我们富裕和勤劳的法国人民越来越迫切地感受到了对出口渠道的需要。”
问题在于,行动人物的理由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动机,即使动机真实,行动是否符合动机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法国对一些殖民地的占领是很难用经济理由来解释的。北非的毛里塔尼亚,国土的90%都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法国在赤道非洲所进行的征服,也肯定是亏本的。在尼日尔,灼热的沙漠,缺水,气温高达50摄氏度,农业或矿产资源明显缺乏,这些使得尼日尔极度缺乏经济吸引力。征服乍得时,带队的法国军官承认,乍得非常干旱,很难找到饮用水。他后来说:“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为了征服这样一个被遗弃的国家而杀死这么多人,付出这么多痛苦,这真是不值得。”20世纪初,在整个乍得,只有20名欧洲人居住,其中只有一名法国商人。强迫劳动和对人民征收的各种税负所产生的收入只相当于行政费用的一半。
宏观的经济数据也并不能支持茹费理的说法。1882至1886年间,法国与殖民地的贸易只占法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 71%(1909—1913年,上升到10. 2%),而同时期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要占到总贸易额的三成以上。法国对外投资的重心是奥斯曼土耳其、东南欧、俄国和南美洲,而不是自己的殖民地。1900年,法国对外投资的71. 1%是在欧洲(俄罗斯就占了25%),只有5. 3%的投资是花在了法国自己的殖民地身上(1914年,终于上升到8. 8%)。
通过观察是哪些人在推动法国的殖民活动,我们也许能够得到更准确的答案。
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圈子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超党派集团,其由各个派别的人士组成,尽管在其他方面可能会互相敌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主张—海外扩张。茹费里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其他成员有政府的高级官员、巴黎地理学会的探险家、重要军事将领、神职人员、学者和探险家,还包括一些商人和金融家。
他们提出了若干主张。殖民地应该为法国服务。它们必须提供有用的原材料、购买法国商品和吸引法国投资。海外业务将扩充逐渐饱和的国内市场,使法国在经济竞争加剧和保护主义抬头时获得有保障的贸易渠道。它们必须扩大法国的实力和威望,对抗国际竞争对手。此外,殖民地必须有助于解决民族问题。社会改革者希望至少有一些殖民地能够为无地农民、城市失业者甚至孤儿提供家园。那些被判犯有刑事罪或政治罪的人可以被送往殖民地,以消除法国政体中的危险因素。帝国将复兴一个由于自我满足、懒散从而丧失民族意志的法国。传教士认为,当地人的福音化将会对抗日益增长的反教权主义和世俗主义。技术专家和工程师则把这个帝国看作一个巨大的桥梁、运河、港口和铁路工地。社会主义者梦想着建立模范定居点。道德家则说,帝国将为青春活力、男子气概和开拓精神的发挥提供一个平台。对军人而言,帝国将成为陆军和海军的训练基地。
尽管这些人有以上这些五花八门的主张,但不是所有人都真的投入了海外殖民活动。首先,普通民众对帝国似乎并不感兴趣。次世界大战前,居住在法国殖民地的法国人只有70万,其中50万还集中居住在阿尔及利亚。在有些法国殖民地,法国居民的人数甚至要少于其他欧洲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虽然仍然动荡(换总理如翻书),但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仍属平稳、宽容,没有什么少数群体因受迫害需要出走。而且相对来说,法国所占领的那些殖民地也实在很难说是什么风景如画的肥沃之地,对移民的吸引力也小。
的例外是阿尔及利亚,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1848年革命之后,特别是在1852年拿破仑三世政变和第二帝国建立以后,政府将两万名以上的政治犯运到了阿尔及利亚;1871年,法国被德国打败之后,阿尔萨斯和洛林部分地区的难民也被送往北非安置。此外,从西班牙、意大利和马耳他也涌来了很多外裔移民,他们抛弃了自己的贫穷国度,因法国政府的优惠安置政策而来到这个相对邻近的地方。1889年,巴黎将公民身份扩大到外国移民在阿尔及利亚出生的子女,这极大地增加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人口数量。这些因素都是不太可能复制到其他殖民地的。
尽管商人、金融家和工业家对殖民地所能产生的收益非常感兴趣,但是法国政府才是殖民经济背后的发动机,到20世纪早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很少有殖民地可以做到自给自足,法国驻军和官僚机构是法国产品的市场,政府承担和资助的公共工程是许多殖民地活力的经济活动,政府的各种政策决定着投资盈利与否。正如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法国资本家对殖民地的投资并不多。所以,雷蒙·阿隆坚持认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建立并非是法国企业界的功劳,因为它明显动力不足。另外一位法国作家则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想象力不足,他们追寻的是自己内心的反复无常或头脑的精明,对国家目的不屑一顾。
真正具有冲劲和主动性的是两个群体—传教士和军队。法国国内,教权主义与世俗主义的斗争异常激烈,受此刺激,传教士希望能够在国外发展大批信众,反过来复兴法国的天主教信仰。拉维杰里主教(Charles Lavigerie)对法国的北非政策施加了相当的影响,一家意大利报纸中肯地评论: “红衣主教拉维杰里在地中海的影响力超过了一支军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传教士团体都是各殖民地的民间组织。
至于军队,他们与海外征服的关系要更加密切。巴黎政府对海外军队的控制似乎非常弱,而军官们从海外冒险中看到了相当的机会。库马尔尖锐地评论说,在法国的帝国英雄万神殿中,商人们是缺席的,他们的位置由士兵取而代之。
利奥泰元帅(Marshal Hubert Lyautey)就是个中典型,他在北非和印度支那服役,战功卓著。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时候,他写道:“在这里,我就像水中的鱼,因为操纵事物和人类就是力量,是我所热爱的一切。”之后他被派到马达加斯加岛任南部地区的总督,控制着将近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和100万人口,他甚至在给父亲的信中自诩为路易十四。再之后他被调往阿尔及利亚。1903年,他未经巴黎政府的许可就移师摩洛哥。1911年,他成了摩洛哥的实际统治者,直到1925年去任为止。
军队的自行其是并不是从利奥泰元帅开始的,19世纪30年代指挥军队入侵阿尔及利亚的比若将军就说过一句名言:“命令应该烧毁,以免我们忍不住地想看。”他认为,“军队中的不服从现象已经上升为一种艺术”。1862年,海军上将波纳尔强令越南政府将南圻的三个省割让给法国,1867年,拉格朗迪埃完全征服了南圻,而这些都是指挥官罔顾命令、自行其是的结果。之所以军队能频频自行其是,恐怕与法国军界同政治的关系特别紧密是有关系的。英国史学家罗纳德·罗宾逊特别就此指出:“在巴黎混乱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军人)有机会将三色旗带去远方。法军的军官都是一只手抱着格林机关枪,另一只手书写着回忆录。英国的军官早在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时期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 *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际推动法国海外帝国扩张事业的,并不是殖民者所具备的社会与经济动力;真正的推动能量是政治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威望或短期功利的考虑。克里孟梭在1890年辛辣地指出:
既然你们是伟大的殖民者,那么,请殖民吧!你说,有了这些殖民地,资本会流到那里去,殖民者也会去那儿,工业繁荣、贸易达成,也会发现新的市场。好吧,动手吧!但是到目前为止,你只是输出了一大堆花了我们很多钱的官员,他们除了阻碍上面这一切发生就别无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