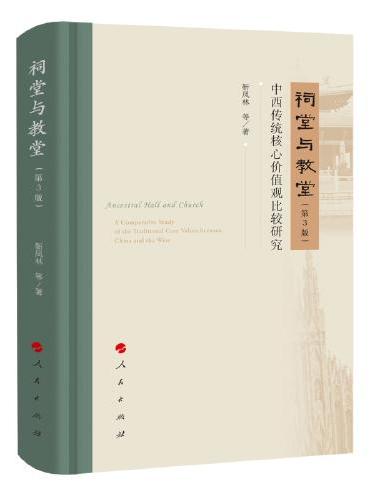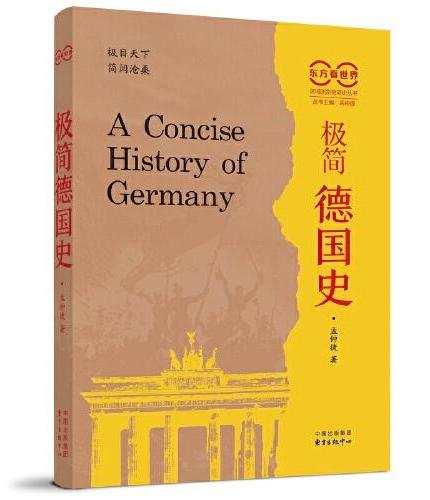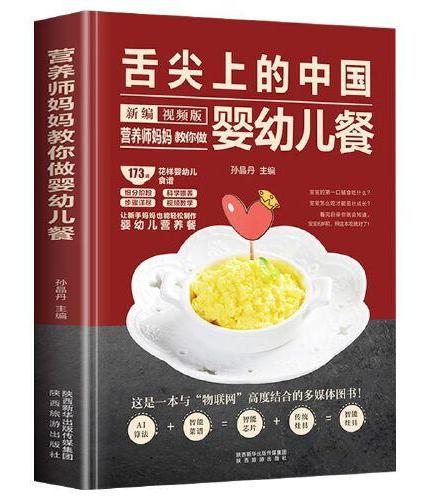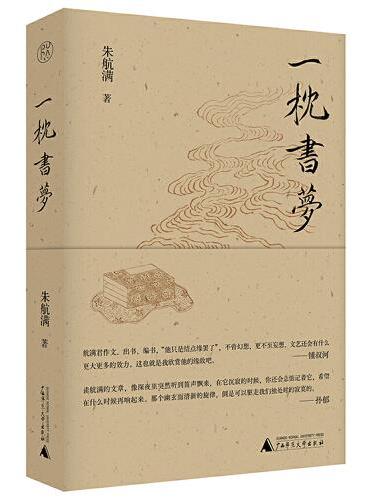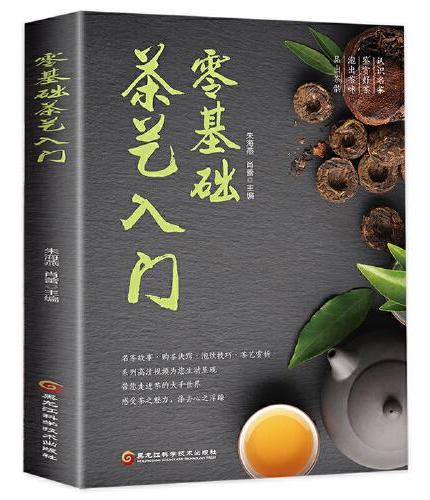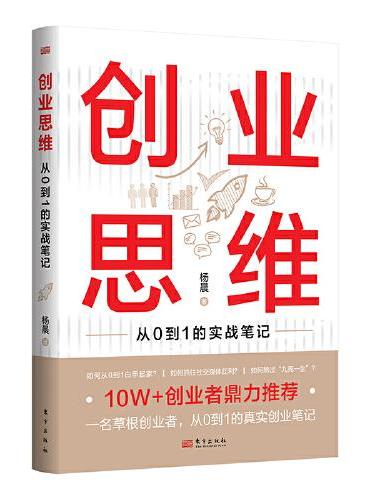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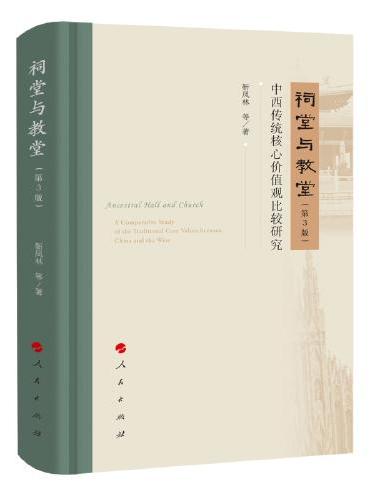
《
祠堂与教堂:中西传统核心价值观比较研究(第3版)
》
售價:NT$
5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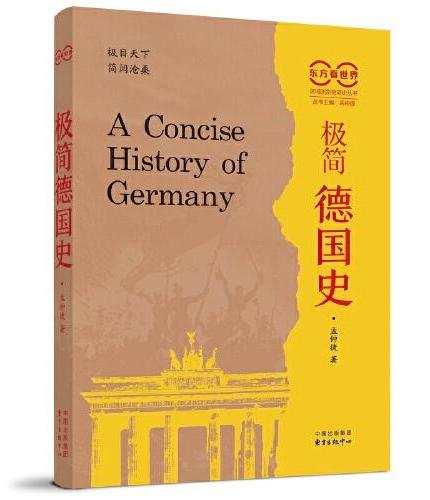
《
极简德国东方看世界·极简德国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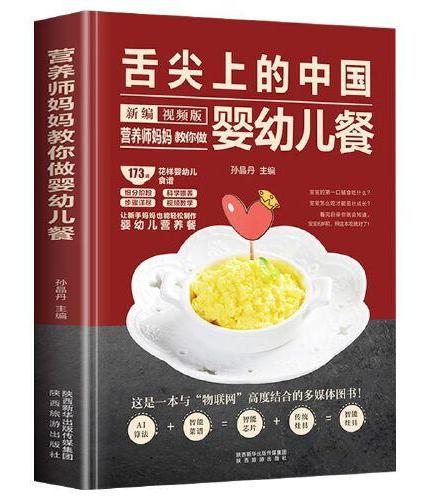
《
舌尖上的中国新编视频版营养师妈妈教你做婴幼儿餐
》
售價:NT$
296.0

《
Scratch创意编程进阶:多学科融合编程100例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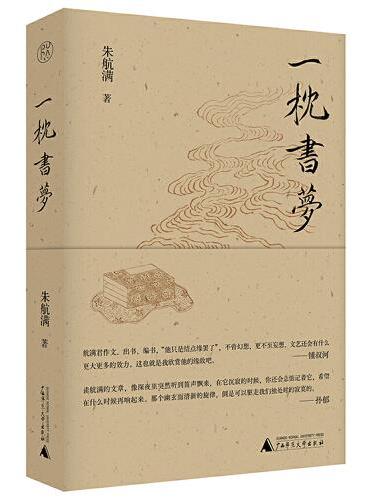
《
纯粹·一枕书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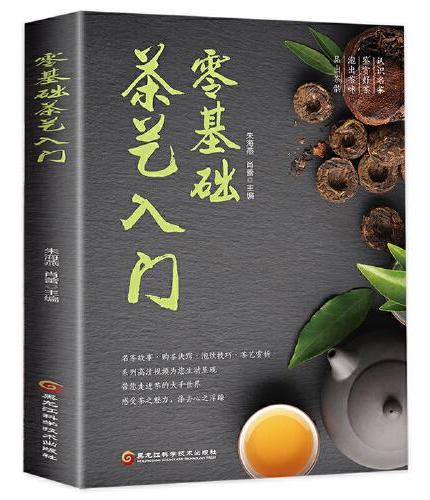
《
新版-零基础茶艺入门
》
售價:NT$
1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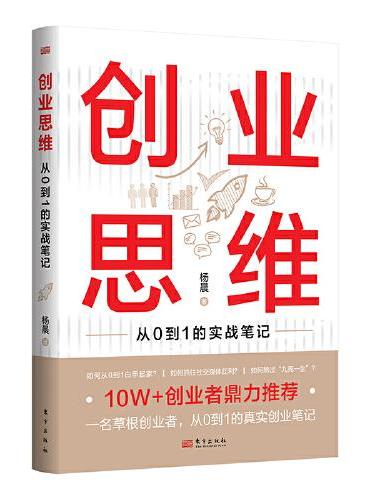
《
创业思维:从0到1的实战笔记
》
售價:NT$
356.0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
| 編輯推薦: |
|
作品试图突破少数民族题材小说的写作模式,糅合了多种元素(少数民族、爱情、悬疑、家庭……),在这个试图讲得好看的故事背后,作品想要去除的是我们对凉山彝族先入为主的预期(异域风情、穷、艰苦……),反映彝族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也会面对的问题,彝族人在进入大城市获取生存资源时会碰到的境况,彝族青年在时代更迭、融入大的民族国家社会时难免会碰上的问题,他们也有很多已经走出来的优秀青年在思考并设法改善这些问题,等等。但是总而言之,彝族社群和大多数中国乡村可能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多不同。
|
| 內容簡介: |
|
故事背景放在当今北京,一个优秀善良的彝族青年阿合,经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已是在北京拥有家庭和工作的知识分子,业余热心协助公安民警处理和少数民族群众有关的民事案件。某一天,和阿合有种种前缘的彝族女子史尼出现,走入他和“我”的生活中,层层隐秘前缘和新故事依次展开……在一个侦探式的故事中,作品跳出少数民族环境,反映彝族人在城市化大潮中,融入更大的民族国家社会时的处境。
|
| 關於作者: |
|
冯良,1963年生,四川凉山人。198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藏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西南边》《西藏物语》《秦娥》、散文集《彝娘汉老子》等。
|
| 目錄:
|
笼中人 / 001
阿合和他的父亲 / 008
和妈妈没有相处之道 / 014
只有我在伪装快乐吗 / 021
优秀的松茸 / 031
一个治安志愿者的阅历 / 037
用虫草和羚羊堆梦 / 046
互为局外人 / 057
鸟声鸣啭 / 067
指桑说槐 / 077
阿合版 / 085
暗物质 / 101
替古人担忧 / 108
“开放日” / 120
飘 逝 / 130
史尼的“药” / 139
史尼版 / 146
月光柔亮 / 156
风,流贯在青冈林里 / 167
盘加的浪漫 / 175
不如自己做主嫁掉 / 183
打工时和阿芝的相处 / 190
跟盘加走 / 201
不 安 / 208
不算突发事件 / 215
警方上门 / 223
小季版 / 237
母兮鞠我 / 252
义 气 / 259
这里那里 / 266
|
| 內容試閱:
|
就是那一天,阿合告诉我说,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治安志愿者,帮民警分担一些甄别、翻译、调解的工作,涉及的不外是迷路、被骗、寻亲、小偷小摸,基本属于民事范畴,刑事方面的偶尔一回半次,也在外围。
可怎么给他爸解释都听不进去,就是觉得当警察荣光,有面子。阿合帮助乡亲有功的事例老挂在嘴上炫耀,确实也有当事者上门或通过亲友向他爸致谢的,还收到过当作谢仪的鸡或鸡蛋。
阿合说,他上大学时,派出所来学校找志愿者在他之前已成惯例,不单他附近的派出所,很远的派出所也有找来的。联网后,需求量有所增长。
找来的派出所,基本上都是请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南方方言的学生当翻译。操这些语言的当事人,让派出所的北方民警大伤脑筋,不知所云,更无从明白求助者的诉求,以及涉嫌违法者的情况、背景了。
阿合大二那个秋天,附近的派出所来了一位貌似干练的农妇,五十出头。
自诉,随在北京一家餐馆里做厨师的儿子等一行去香山赏红叶,红叶没看到几树,也没啥看头,比不上秋天老家山上的梨树叶,那才叫红和透亮呢。游玩的男女青年,反而比红叶惹人眼目。三下两下,还不就跟错了队伍,儿子等一干人不知去了哪里。
扯起嗓子喊,着意打望穿牛仔衣的男孩,有几位的背影实在太像儿子了,扒拉过来一看,全不是。
天黑下来,漫山的人陆续都堆到了公交车站、地铁站。记得来时坐的一辆公交车有个“3”字,捡了辆带“3”字的就挤了上去。从头坐到尾,下车后,天已黑尽。
幸好兜里有儿子给的几个零花钱,囫囵吃了屉小笼包子,一边向卖包子的人打听儿子的餐馆。
怎么打听得到,她说的是彝话,间插的三几个汉语词和彝话也没区别,人家听着直摇头。其中一位女服务员热心,引她到近的派出所求助。
这都是阿合来到派出所后她絮叨的,神情好像盼来了救星,一直抓着阿合的手不放。
通过阿合的翻译,不费吹灰之力,民警就帮老妇人找到了儿子所在的餐馆。那是一家彝式风味餐厅。
回就旗开得胜。
又有一回在火车站派出所,一位老者扎撒开双臂,紧护着自己的大小四五件行李,从其中的一个包里散发出的熏香味,来自阿合家乡的腊肉香肠,那是用高山上的柏树枝焐出的烟熏制的。
用彝话一问,虽然老者也用彝话回答他,但他并非彝人,而是傈僳族。傈僳和自称“诺苏”的彝人居住在同一地域,语言几乎相通,阿合实际也能说傈僳话。
老者一身黑蓝布中山装,要去东北看儿子,打算和儿子一家过那一年的傈僳年。傈僳年一般在公历的十一月左右,和彝年的时间差不多。可在北京转车时,他装着火车票的小布兜子被偷了。里面还有他的身份证和手机。儿子的手机号和家里的电话必得从手机里才能查到,他是记不得的。他能说汉话,川方言,民族音浓郁,对北方语系的铁路职工来说,等同于另一种语言,入耳即晕。
老者的道理简单,他认为自己的布兜子是在火车上被偷的,火车是公家的,应该公家负责,起码负责一半。他自己当然也有责任,没有看管好自己的财物,明明车站、火车上到处都贴着标语,让旅客警惕小偷小摸。合情合理的做法是,手机、钞票的损失由他自己承担,公家帮他解决下半程的火车票。
绕了那么远,没想到这么好通融,马上,铁路这个公家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也感谢阿合的及时出现。
这下,儿子的手机号码也记得了,即刻通了电话,告知晚到一天半的原因。
老者上车时,阿合送他一百元钱以备不时之需,他也接了过去。
等铁路上的地勤与列车员交接完离开后,老者执意把钱还给了阿合。
他探脚碰碰阿合的鞋尖,掀起裤脚,让看他自己脚上的高筒旅游鞋,鞋带系得紧紧的,还是死扣,这是右脚,与左脚不同,那边是活扣。环顾四周,压扁嗓门,悄悄说,大票子都踩在脚下呢,被偷的只是几个零花钱。耸耸肩,再挤挤眼睛,显出自己多狡猾似的,“我又不是傻瓜!”他说。
上述两例以外,阿合还讲过一位在超市偷东西的妇女的故事。
这位妇女不认可摆在她面前的赃物,说,一条秋裤、两包巧克力豆不在其中。
自诉自己某天在锣鼓巷的某家炒货摊上偷抓了把糖炒栗子,还有哪里又顺了两根冰糖葫芦、三根红果冰棍。
开始,警察以为她在拖时间,和他们逗闷子。
确实有此嫌疑,比如冰糖葫芦和红果冰棍,她为啥喜欢呢,因为酸酸甜甜的,和老家的花红果一样。畅想等老家秋天园子里的两株花红果成熟后,也照冰糖葫芦的样子做来卖钱。到时,摆到十字路口,要不学校门口,女娃儿喜欢酸甜的味道了,肯定好卖得很,她说。
糖山药她也吃过,她觉得山药像洋芋,她可以用洋芋来代替,她家山上的地种出来的洋芋“又糯又香”。
打听她犯的事会坐多久的牢,按她的推测,一个月应该够了吧?因为她在超市偷东西才第二次就被捉住了。让赶紧判她坐牢,坐完好回家做冰糖花红果的买卖。
至于少年男女懵懂中出来寻师,为实现自己的歌星舞星梦,被骗的何止八九例。再有困于讨薪的农民工、出走的中学生、逃避包办婚姻的女子、被拐卖的妇女,严重如走私嫌疑人、售卖假虫草的等等,阿合都有过接触。
阿合说,上述人等,不管懂不懂汉话,他们每一位在听到他的彝话时,如果同为彝族,再呆滞的眼睛都会闪亮、活泛,洋溢出的笑意能柔软他们绷紧的身体、脸庞。
他们不回答警察的提问,先问他姓啥,是哪家的儿子。得到他的答复后,会从各自的父系、母系延展出去,只要捋到蛛丝马迹的关系,就会热情的和他攀亲戚、排辈分。可能,他们中的这位、那位他得叫叔叔、爷爷,那位、这位得叫他叔叔、爷爷,也有同辈的,那就兄弟相称。
接下来,无一例外,他们会细数自己碰到的麻烦。
和民事相关的人员,来龙去脉只要理顺了,瞬间解决问题。
涉案嫌疑人,仗着警察听不懂自己的语言,要不装乖服软,让他编几句好话哄警察;要不耍横,逼他骗警察,不然的话,老辈子如我服完刑出去看不收拾你。
那种时候,阿合会觑定对方,诚恳地说,自己没有那个本事,哄或骗不了警察。万一头脑发昏,真的那样做了的话,自己的爪爪也会被铐住的。这要传回老家,那是必然会传回去的,他反问那让他哄或骗警察的人,你怎么向老家我们共同的亲戚、朋友交代?你还有啥脸面再在众乡亲家出入呢?
话说到这份上,有求于他的涉案嫌疑人基本就蔫了。
一旁的警察见状,促阿合趁势而进,但他仍保持与嫌疑人拉家常的态势,言语温温,以保有他们的自尊心,问他们的儿女在哪里,打工还是上学,如果在读书,学费呢?也问出来某位的家里有病人。再往后会问到嫌疑人跑一趟买卖能挣多少钱?是给儿女攒学费,还是给病人凑医疗费,或者就是为了生活的安逸。渐渐的,话题近到调查的核心,嫌案水落石出。比如两位逃逸在外多年的嫌疑人,一位是因为偷猎豹皮还卖了;另一位是点火烧和自己小有纠纷的邻家的羊圈,不想,引燃住房,烧伤了两人。
阿合说,自己当志愿者七八年下来遇到的也不乏恶劣的家伙,其中的一个少年时就跑出来混,到处坑蒙拐骗,不是老婆警觉,恐怕也得被他卖了换酒喝。装可怜,谎话连篇,称自己用假麝香骗钱是为了给两个学龄儿女交学费,竟然不知道九年义务教育,如今上学不但不交学费,连午餐都是免费的。
说到所以能成功助警,阿合称,很大程度上,自己靠的是乡情民俗,可以说是礼俗助警。
他说,自己曾给一位警官解释他们的礼俗。
绕来绕去,那位警官都不能理解,下结论说,阿合在警事中接触到的那些人,民事的刑事的都包括,全是他的亲戚,再怎么着,也肯定是远亲旧戚,深以为凉山弹丸之地,一个大村庄的规模,要不怎么阿合随便一牵连,就能拉扯出这个爷爷那个叔叔、哥哥的。
警官拿自己打比方,说他吧,遇到同姓者,除非有特别的想法,一般不拉扯关系,要拉扯也只是说,咱们是家门啊,或者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
说到各家的家谱,阿合相熟的警官中有个别恍然明白道,你们这是和孔姓有一比啊!那也没听说,分散在全中国全世界的老孔家因为辈分见面互称爷爷、叔叔或者兄弟的,还是你们凉山人少地方小
阿合说,他真想把说这话的警官请来凉山,让他领略领略凉山的千山万水!
我是领略过的,当然知晓凉山何其大哉!可我也有疑问,某回问阿合:
“你敢打保票,你接触过的当事人没有骗过你吗?”我不大相信解放至今七十年了,阿合的乡亲里五十岁上下的竟然很多人不会汉话。
阿合不敢打保票,他说,的确有嫌疑人骗过他,不止一次,假装不懂汉话,用彝话和他东拉西扯。他呢,被人家牵着鼻子天远地远都走迷路了,还毫无察觉。旁边的警官踢他的脚腕子、拽他的衣摆都不管用,逼得警官亲自上阵,假意通报案情进展,或同案另一位嫌疑人的供词,才激出嫌疑对象否定唯恐不及的汉话。
阿合说,不要说五十岁上下的,即便四十岁左右的人群里,在凉山上,不会汉语的也不少。他建议我上百度查去,看二百万彝族人口的凉山上各个年龄段汉语盲的比例。越往下,比如二十岁以下,汉语汉文普及度大而广泛,尤其乡村幼儿园都在开办汉彝双语班的情况下,自然,汉语汉文的程度也越高。
阿合说,他在上小学前几乎不会汉话,偶尔他爸参加完公社进而全县的民兵篮球赛回来,会有那么几天延续赛会上的用语,嘀咕几句汉话,也教他,至今他还记得的一句是:“要个糖包子”。显见是饭堂专用语。
他母亲的汉话是他教的,他说,他母亲学习汉话的动力来自他爸,因为怕他爸的魂,被随季节买卖花椒、菌子、苦荞茶、脐橙、清茶时遇到的女人勾走,彝女人汉女人都算。
阿合说,他妈妈讲的汉话是四川话,他是先四川话再普通话,他的小学中学阶段还没有推行普通话,老师讲课全用四川话,他之后的年轻人起步就都是普通话了。
普通话也可以说是打工话,他说,在他之后的很多男女孩子如果没上学或者辍学了,十五六岁起便散向全国各地,主要是在沿海和深圳当打工一族,他们的语言便直接从彝话过渡到了普通话,多多少少在彝腔之外还带着打工所在地的腔调,比如粤语味、浙江味、江苏味、河南味、山西味,不一而足,反倒本省的官话——四川话听不大懂了。
难怪,他表妹史尼操一口港味普通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