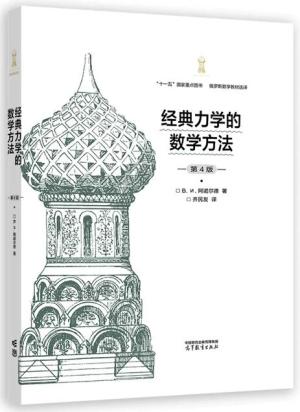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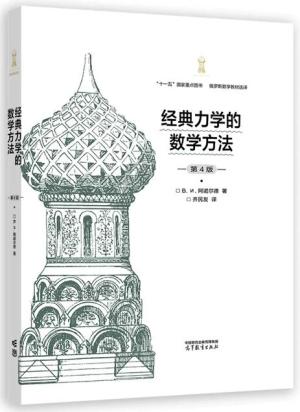
《
经典力学的数学方法(第4版)
》
售價:NT$
403.0

《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跟随历史的足迹 见证一个民族的觉醒与抗争
》
售價:NT$
305.0

《
功名诀:左宗棠镜像
》
售價:NT$
908.0

《
布克哈特书信选
》
售價:NT$
439.0

《
DK园艺的科学(100+个与园艺有关的真相,让你读懂你的植物,打造理想花园。)
》
售價:NT$
500.0

《
牛津呼吸护理指南(原书第2版) 国际经典护理学译著
》
售價:NT$
959.0

《
窥夜:全二册
》
售價:NT$
407.0

《
有底气(冯唐半生成事精华,写给所有人的底气心法,一个人内核越强,越有底气!)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 《傻瓜吉姆佩尔》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成名作,已成为世界文坛的经典。
★ 辛格被誉为20世纪“会讲故事的短篇小说大师”。
★ 辛格为“中国图书界的诺贝尔奖效应”肇始者,深刻影响中国当代文坛的作家。
★ 一部影响和感动了中国几代作家的作品,余华曾说“《傻瓜吉姆佩尔》是一部震撼灵魂的杰作”。
★ 一个既软弱又强大的傻瓜,一个比白纸还要洁白的灵魂,一个世界文学史中的标志性形象。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那充满激情的叙事艺术,植根于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生动描述了具有普世性的人类境况。——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
| 內容簡介: |
|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巴·辛格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傻瓜吉姆佩尔》是他晓谕世界的名篇。辛格化用传说、寓言、宗教题材,以鬼怪形象喻指欲望与诱惑,书写普通人的困境与救赎。忠厚的傻瓜用宽容和忍耐报以欺辱刁难他的人;撒旦化身绅士降临穷困村镇,并将一次狂欢化为末日浩劫;精明的守财奴折磨死一任又一任妻子之后差点栽在女骗子手里;虔诚的拉比痛失爱女后,彻悟“人生在世当欢欢喜喜”……
|
| 關於作者: |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
美国籍波兰裔犹太作家。1904年出生于波兰莱昂辛小镇里的一个犹太拉比世家。1925年发表篇短篇小说《在晚年》。1935年在哥哥约书亚的帮助下移居美国纽约,从事记者与专栏作家的工作。1953年,辛格的小说《傻瓜吉姆佩尔》由索尔?贝娄译成英文发表于《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引起批评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1970年凭借儿童文学《快活的一天:一个在华沙长大的孩子的故事》、1974年凭借短篇小说集《羽冠》两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辛格在20世纪被称为“短篇小说大师”“当代会讲故事的小说大师”,终生用意第绪语写作,作品通过英译本而广为人知。辛格擅写魔鬼、精灵、恶魔、巫师的故事,总是能以极小的篇幅、简洁的形式表现深刻的主题,文风集讽刺、诙谐、智慧于一体,创造性地呈现了业已消失的犹太人世界。 郭国良,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理事,浙江省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译有《终结的感觉》《无可慰藉》《赎罪》《水之乡》等作品。
|
| 目錄:
|
|
序言鸣谢傻瓜吉姆佩尔来自克拉科夫的绅士杀妻狂—一则民间故事纪念烛之光镜子小鞋匠欢乐未出生者日记老人火隐身人
|
| 內容試閱:
|
傻瓜吉姆佩尔
1
我是傻瓜吉姆佩尔,但我觉得自己不傻,可人们都这样叫我。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我总共有七个“名字”:弱智、蠢驴、木头、呆子、闷葫芦、笨蛋和傻瓜。后一个名字至今都甩不掉。我傻在哪儿?我容易上当。他们说:“吉姆佩尔,你知不知道拉比的老婆生孩子了?”于是我翘了课。唉,原来是个谎言。可我怎么知道是谎言呢?她当然没有大肚子,不过我也未曾瞧过她的肚子。可那真有那么傻吗?这帮人嬉皮笑脸,又跺脚又跳舞,还唱起晚安的祈祷文。当一个女人分娩,他们没给我葡萄干,而在我手里塞满了羊粪。我并不是个瘦弱的人,如果我给人一巴掌,就能把他扇到克拉科夫去,但我本性不好斗。我心想:算了。于是他们便继续捉弄我。
我从学校回家时听见一条狗在叫唤。我不怕狗,但我从来不想去招惹它们。它们中万一有条疯狗把你咬伤,那么世界上无论哪个鞑靼人都救不了你。于是,我就抄小路走。接着我环顾四周,看见整个集市的人都在狂笑。原来根本没有狗,而是小偷沃尔夫—莱布。我怎么会知道是他呢?他叫起来像只嚎叫的母狗。
当那些爱搞恶作剧、捉弄人的人发觉我容易上当之后,他们个个都想在我身上碰碰运气。“吉姆佩尔,沙皇快到弗兰波尔了;吉姆佩尔,月亮掉到托尔平了;吉姆佩尔,小霍德尔?弗比斯在澡堂的后面发现了宝藏。”而我像个泥人似的相信了所有人。,世上一切皆有可能,就如《先人的智慧》中说的那样,但我这会儿想不起原话了;第二,我不得不去相信,当全镇的人都和我这么说的时候!如果我有胆说:“哼,你们在骗我!”那就麻烦了,人们会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我们都是骗子吗?”我能怎么办呢?我相信他们,并希望这样至少能给他们一些好处。
我是个孤儿。抚养我长大的祖父眼看着快要入土了。所以他们就将我交给一个做面包的师傅,我在那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每个来烤一炉烙饼的女人或姑娘至少会戏弄我一次。“吉姆佩尔,天上有个集市;吉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就生下一头小牛;吉姆佩尔,一头牛从屋顶飞过还下了些铜蛋。”一个犹太学校的学生来买面包卷,他说:“你,吉姆佩尔,你在这儿用面包师的铲子刮锅炉时,救世主降临了。死人都复生了。”“你什么意思?”我问,“我可没听见谁在吹羊角!”他说:“你聋了?”这时人们都叫起来:“我们都听到啦,我们都听到啦!”然后来了蜡烛工里兹,她用嘶哑的喉咙喊道:“吉姆佩尔,你的父亲和母亲从坟里站起来了,他们正在找你。”
说真的,我心里很清楚这些事从没发生过,可人们照样谈论着,我穿上羊毛背心走了出去。也许真有什么事发生了。去看看又有什么损失?行吧,大家又哈哈大笑!于是我心里发誓再也不去相信什么了。可这样也行不通。他们这样捉弄我,我连大小粗细都搞不清楚了。
我去找拉比给我出主意。他说:“圣书上写,‘一世愚者好过片刻恶人’。你不是傻瓜。他们才是傻瓜。因为一个让邻居蒙羞的人将失去他的天堂。”然而拉比的女儿又让我上了当。就在我离开拉比的圣坛时,她说:“你吻过这儿的墙吗?”我说:“没有,怎么了?”她回答说:“这可是个规矩。你每次走的时候都得这样做。”行吧,这看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害处。接着她突然大笑。这是个高明的把戏,她完完全全骗到了我,好吧。
我想搬到另一个镇去,可是人们又忙着帮我张罗对象,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几乎要把我上衣的下摆撕下来了。他们对我说呀说的,直到我耳朵上都沾了口水。她不是个贞洁的姑娘,可他们告诉我她是个纯洁的处女。她有点跛脚,他们说是故意装的,因为害羞。她有个私生子,可他们告诉我这孩子是她的小弟弟。我嚷道:“你们在浪费时间。我不会娶那婊子!”但他们愤懑地说:“你怎么这样说话?难道你不害臊?你这样败坏她的名声,我们可以把你带到拉比那去评理,处罚。”我才看出来我不可能很容易地摆脱他们,我心想:他们是存心想让我变成他们的笑柄。不过结婚后丈夫就是一家之主,如果她也认同,对我也就还好。再说,你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别期望太高。
我去了她的泥房子,盖在一个沙丘上,那帮人又是叫、又是唱的,跟在我身后。他们的举止活像一群耍熊的。我们来到井边时,他们一起都停下了。他们都怕和艾尔卡打交道。她的嘴巴一张开就像装上了铰链似的,而且言辞锋利、语言泼辣。我走进屋子。一条条绳子从这面墙拉到那面墙,衣服挂在上面沥干。艾尔卡赤着脚站在水桶边,正洗着衣服。她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旧毛绒长袍。她把她的头发编成辫子横别在头上。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头发的臭味太熏人了。
显然她知道我是谁。她朝我看了一眼,说:“瞧是谁来了!他来了,这无趣又愚蠢的个性软弱的人。自己找个地方坐。”
我告诉了她一切,我没否认任何事。“跟我说实话,”我说,“你真的是个处女吗?那个顽皮鬼耶契尔真的是你弟弟吗?别骗我,看在我是个孤儿的分上。”
“我也是个孤儿。”她回答,“谁要是想捉弄你,就让他的鼻子长歪。可谁都甭想占我便宜。我要一份五十盾的嫁妆,让他们另外再为我凑一笔钱。否则,让他们来亲我的那个玩意儿。”她倒是
直来直去。我说:“出嫁妆的应该是新娘,而不是新郎。”然后她说:“别和我讨价还价,要么成,要么不成—你哪来的回哪去。”
我想:这个生面团烤不出任何面包来。不过我们镇也并不是块穷地方。他们答应了所有条件,接着举行了婚礼。那时恰逢痢疾流行。婚礼在公墓的大门口举行,边上就是小小的洗尸房。人们都喝得酩酊大醉。当起草婚书时,我听见那位虔诚、尚的拉比问:“新娘是个寡妇还是个离了婚的女人?”会堂执事的老婆替她回答:“既是寡妇,又离过婚。”真是个尴尬扫兴的时刻。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从婚篷下逃走吗?
人们又唱又跳。一个老太太在我对面跳舞,抱着一个奶油白面包。婚礼主持人唱了一首《仁慈的上帝》纪念新娘的双亲。男学生们扔着刺果,像在过阿布月初九斋戒日。人们在致贺词后送来了很多礼物:一块擀面板、一个揉面槽、一只水桶、几把扫帚、几个勺子,还有些家用小东西。接着我瞄了一眼,看见两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抬着一个婴儿床。“我们要这个干什么?”我问。他们这样说:“你别多想了。这玩意好用极了,有你用的。”我意识到我又一次被耍了。换个角度想,我又损失了什么呢?我思忖:且看结果如何吧。全镇的人不可能都一起疯了。
(选摘完)
傻瓜吉姆佩尔
1
我是傻瓜吉姆佩尔,但我觉得自己不傻,可人们都这样叫我。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个绰号。我总共有七个“名字”:弱智、蠢驴、木头、呆子、闷葫芦、笨蛋和傻瓜。后一个名字至今都甩不掉。我傻在哪儿?我容易上当。他们说:“吉姆佩尔,你知不知道拉比的老婆生孩子了?”于是我翘了课。唉,原来是个谎言。可我怎么知道是谎言呢?她当然没有大肚子,不过我也未曾瞧过她的肚子。可那真有那么傻吗?这帮人嬉皮笑脸,又跺脚又跳舞,还唱起晚安的祈祷文。当一个女人分娩,他们没给我葡萄干,而在我手里塞满了羊粪。我并不是个瘦弱的人,如果我给人一巴掌,就能把他扇到克拉科夫去,但我本性不好斗。我心想:算了。于是他们便继续捉弄我。
我从学校回家时听见一条狗在叫唤。我不怕狗,但我从来不想去招惹它们。它们中万一有条疯狗把你咬伤,那么世界上无论哪个鞑靼人都救不了你。于是,我就抄小路走。接着我环顾四周,看见整个集市的人都在狂笑。原来根本没有狗,而是小偷沃尔夫—莱布。我怎么会知道是他呢?他叫起来像只嚎叫的母狗。
当那些爱搞恶作剧、捉弄人的人发觉我容易上当之后,他们个个都想在我身上碰碰运气。“吉姆佩尔,沙皇快到弗兰波尔了;吉姆佩尔,月亮掉到托尔平了;吉姆佩尔,小霍德尔?弗比斯在澡堂的后面发现了宝藏。”而我像个泥人似的相信了所有人。,世上一切皆有可能,就如《先人的智慧》中说的那样,但我这会儿想不起原话了;第二,我不得不去相信,当全镇的人都和我这么说的时候!如果我有胆说:“哼,你们在骗我!”那就麻烦了,人们会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我们都是骗子吗?”我能怎么办呢?我相信他们,并希望这样至少能给他们一些好处。
我是个孤儿。抚养我长大的祖父眼看着快要入土了。所以他们就将我交给一个做面包的师傅,我在那里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每个来烤一炉烙饼的女人或姑娘至少会戏弄我一次。“吉姆佩尔,天上有个集市;吉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就生下一头小牛;吉姆佩尔,一头牛从屋顶飞过还下了些铜蛋。”一个犹太学校的学生来买面包卷,他说:“你,吉姆佩尔,你在这儿用面包师的铲子刮锅炉时,救世主降临了。死人都复生了。”“你什么意思?”我问,“我可没听见谁在吹羊角!”他说:“你聋了?”这时人们都叫起来:“我们都听到啦,我们都听到啦!”然后来了蜡烛工里兹,她用嘶哑的喉咙喊道:“吉姆佩尔,你的父亲和母亲从坟里站起来了,他们正在找你。”
说真的,我心里很清楚这些事从没发生过,可人们照样谈论着,我穿上羊毛背心走了出去。也许真有什么事发生了。去看看又有什么损失?行吧,大家又哈哈大笑!于是我心里发誓再也不去相信什么了。可这样也行不通。他们这样捉弄我,我连大小粗细都搞不清楚了。
我去找拉比给我出主意。他说:“圣书上写,‘一世愚者好过片刻恶人’。你不是傻瓜。他们才是傻瓜。因为一个让邻居蒙羞的人将失去他的天堂。”然而拉比的女儿又让我上了当。就在我离开拉比的圣坛时,她说:“你吻过这儿的墙吗?”我说:“没有,怎么了?”她回答说:“这可是个规矩。你每次走的时候都得这样做。”行吧,这看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害处。接着她突然大笑。这是个高明的把戏,她完完全全骗到了我,好吧。
我想搬到另一个镇去,可是人们又忙着帮我张罗对象,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几乎要把我上衣的下摆撕下来了。他们对我说呀说的,直到我耳朵上都沾了口水。她不是个贞洁的姑娘,可他们告诉我她是个纯洁的处女。她有点跛脚,他们说是故意装的,因为害羞。她有个私生子,可他们告诉我这孩子是她的小弟弟。我嚷道:“你们在浪费时间。我不会娶那婊子!”但他们愤懑地说:“你怎么这样说话?难道你不害臊?你这样败坏她的名声,我们可以把你带到拉比那去评理,处罚。”我才看出来我不可能很容易地摆脱他们,我心想:他们是存心想让我变成他们的笑柄。不过结婚后丈夫就是一家之主,如果她也认同,对我也就还好。再说,你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度过一生,别期望太高。
我去了她的泥房子,盖在一个沙丘上,那帮人又是叫、又是唱的,跟在我身后。他们的举止活像一群耍熊的。我们来到井边时,他们一起都停下了。他们都怕和艾尔卡打交道。她的嘴巴一张开就像装上了铰链似的,而且言辞锋利、语言泼辣。我走进屋子。一条条绳子从这面墙拉到那面墙,衣服挂在上面沥干。艾尔卡赤着脚站在水桶边,正洗着衣服。她穿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旧毛绒长袍。她把她的头发编成辫子横别在头上。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头发的臭味太熏人了。
显然她知道我是谁。她朝我看了一眼,说:“瞧是谁来了!他来了,这无趣又愚蠢的个性软弱的人。自己找个地方坐。”
我告诉了她一切,我没否认任何事。“跟我说实话,”我说,“你真的是个处女吗?那个顽皮鬼耶契尔真的是你弟弟吗?别骗我,看在我是个孤儿的分上。”
“我也是个孤儿。”她回答,“谁要是想捉弄你,就让他的鼻子长歪。可谁都甭想占我便宜。我要一份五十盾的嫁妆,让他们另外再为我凑一笔钱。否则,让他们来亲我的那个玩意儿。”她倒是
直来直去。我说:“出嫁妆的应该是新娘,而不是新郎。”然后她说:“别和我讨价还价,要么成,要么不成—你哪来的回哪去。”
我想:这个生面团烤不出任何面包来。不过我们镇也并不是块穷地方。他们答应了所有条件,接着举行了婚礼。那时恰逢痢疾流行。婚礼在公墓的大门口举行,边上就是小小的洗尸房。人们都喝得酩酊大醉。当起草婚书时,我听见那位虔诚、尚的拉比问:“新娘是个寡妇还是个离了婚的女人?”会堂执事的老婆替她回答:“既是寡妇,又离过婚。”真是个尴尬扫兴的时刻。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从婚篷下逃走吗?
人们又唱又跳。一个老太太在我对面跳舞,抱着一个奶油白面包。婚礼主持人唱了一首《仁慈的上帝》纪念新娘的双亲。男学生们扔着刺果,像在过阿布月初九斋戒日。人们在致贺词后送来了很多礼物:一块擀面板、一个揉面槽、一只水桶、几把扫帚、几个勺子,还有些家用小东西。接着我瞄了一眼,看见两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抬着一个婴儿床。“我们要这个干什么?”我问。他们这样说:“你别多想了。这玩意好用极了,有你用的。”我意识到我又一次被耍了。换个角度想,我又损失了什么呢?我思忖:且看结果如何吧。全镇的人不可能都一起疯了。
(选摘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