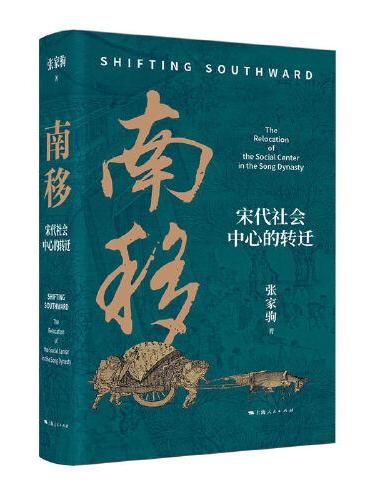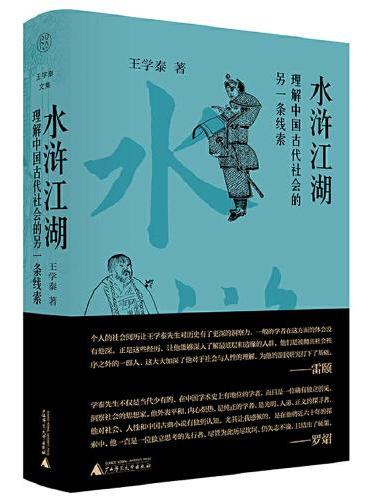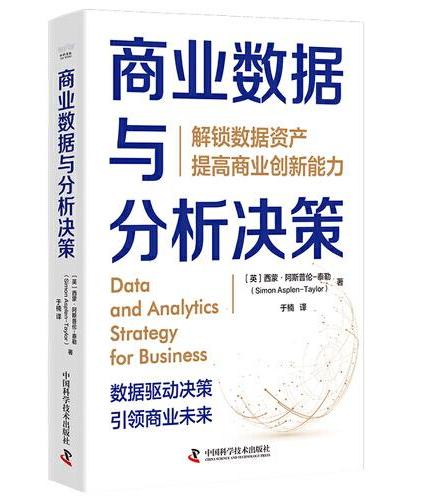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NT$
653.0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NT$
500.0

《
慢性胃炎的中医研究 胃
》
售價:NT$
30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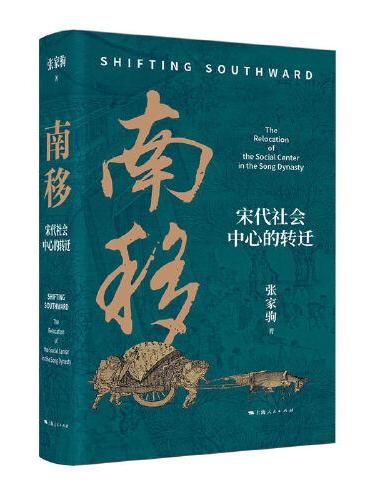
《
南移:宋代社会中心的转迁
》
售價:NT$
7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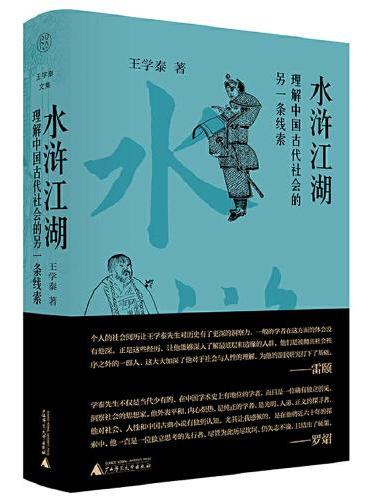
《
纯粹·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另一条线索
》
售價:NT$
469.0

《
肌骨复健实践指南:运动损伤与慢性疼痛
》
售價:NT$
1367.0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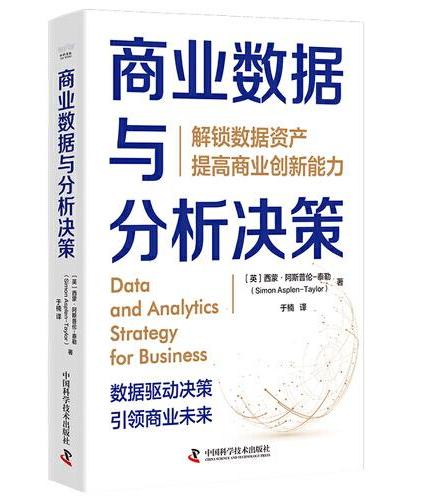
《
商业数据与分析决策:解锁数据资产,提高商业创新能力
》
售價:NT$
367.0
|
| 編輯推薦: |
|
作者立足于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新时代乡村,回望童年与故乡,作者大部分的诗歌主要表现城市化进程中工业文明对乡村农耕文明的冲击以及个体身在其中情感微妙的变化,对逝去的时光和当下乡村的现状与处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以作者的亲身体验和真情实感,有血有肉地表现了内心的感触,让人在乡村诗歌中深切感受乡村变化。作者以一名归乡者的乡愁,描摹乡村生活记忆,传达了新时代的乡野所迸发的盎然诗意,并由此引起读者共鸣。
|
| 內容簡介: |
|
本诗集收录作者近年来创作的一百余首现代诗歌。一个没有诗意的乡村是苍白的,是没有灵魂的,振兴乡村应从文化开始。管清志一直坚持“乡村诗歌”写作。他有乡村生活经历,也有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与延伸,他的文化心态和生活阅历已经超出了地域界限,他笔下的诗歌不再是传统的“乡土”,而是现代意识中的乡镇风情。他获取了乡村自然留下的密码和气息,又带着能辨别是非的眼睛张望现实,在熟悉的环境下,敏锐地发现了人与物、人与人、物与物等互通的情感与特质,彰显了创作者与时代、与世界对话的广阔诗界。
|
| 關於作者: |
|
管清志,七零后,山东诸城人。乡村泥瓦匠之子,生长于鲁东障日山北麓,密水河畔。山东作协会员。创作以诗歌为主,偶写小说,作品见于《诗探索》《星星》《北京文学》《山东文学》《北方文学》《诗潮》《诗林》《青岛文学》《时代文学》等文学刊物,入选多种年度选本。曾获第四届《诗探索》中国春泥诗歌奖,参加首届《山东文学》齐鲁诗会。出版诗合集《宋词里的秋雨》《潍河七子诗选》等。
|
| 內容試閱:
|
在村口,我依然是个孩子
我的家乡是一个典型的鲁东小山村,村子隐藏在泰沂山脉连绵起伏的丘陵褶皱中。村子西边,匍匐着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河水静静流淌,经年不断。后来,我在史料上查到了小河的名字,原来它就是密州大地上那条古老的河流——密水,它的源头就在村西障日山的南麓。障日山,因为宋代密州太守苏轼的登临而名声大噪,太守曾有诗云:“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密水河岸两边,繁茂的树林一望无际。河水蜿蜒北去,在下游大约十几公里的地方注入潍河,那里,是广阔的昌潍平原。河水滋润着村子和星罗棋布的农田,我祖祖辈辈的亲人们,已经在这里耕种了六百多年。
我二十岁之前的时光,都盛放在这个名字叫作西树山的村庄里。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石头房子、每一条弯曲的胡同、每一棵开着不同花朵的树;田野中,我知道每一块土地的主人,每一株野草、野菜的名字;我和小伙伴登上过村子四周所有的山头,我们的脚印,踏遍了村子的沟沟坎坎。
在这里,我见证过一棵树苗的成长、一头牛犊的新生、一粒麦子的成熟、一座桥的诞生;见证过一条小路变成了笔直的大道,通往更远的远方。我凝视过一朵海棠花的开放,看见一只蜜蜂正扇动翅膀,慢慢靠近花心。一场雨后,地下的“知了猴”用坚硬的前爪,刨开湿润的泥土,打开了久违的光明之窗。我在一棵柳树的树干上见到了它,它正用尽全身力气钻出蝉蜕,一点点舒展开它薄薄的翅膀,它软嫩的皮肤在空气中,渐渐变成了黑色,而那个空空的蝉蜕,依旧在风中紧紧抱住树干。
在村口,我见到一个离乡很久的人冒着大雾而来。他站在山坡上,向着村子一遍一遍大声呼喊:“西树山,我回来啦!”他泪流满面,一身沧桑。我也数次跟随送葬的人群,慢吞吞,把死去的亲人安放到田野中向阳的坡地里。
在村后的场院里,我亲眼看见的一场大火,把人们过冬的秸草焚烧殆尽。火焰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把天空映得通红一片。纵火的那个人,是个戴着眼镜的“朝巴”(注:方言,意思为傻子),他看着惊慌失措赶来的人们,竟然手舞足蹈起来。
以上这一切,大概都是我诗歌写作的缘起吧!高中时候,十六岁的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作“候鸟”,我在一首诗中写道:“当一个少年有了叫作‘候鸟’的名字,他的双手在挥动的时候,便有了飞翔的欲望。”
当然,家乡也承载着我青春的压抑和时代的苦闷。我的梦想在这里遭受过冷眼与耻笑。我像那只蝉一样,努力挣脱着束缚自己的命运,离开家乡的时候,我甚至头也不回。
多年来,我与家乡渐行渐远,二十多年漫长的日子里,我失去了我的奶奶、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也满头银发一身病疼。而我那些背负农具、手握种子的乡亲都一个个不知所踪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逼仄的生活本身带给我的困顿与迷茫,我对自己的写作也充满着各种怀疑。不经意间,氤氲弥漫的乡愁开始笼罩着我,家乡的河流、丘陵、山峰一次次出现在恍惚之间。面对着失去,我手足无措,我在诗中写道:“我至今无法/把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称为往事/依然无法/把一个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叫作故乡”。
有一天,我打开家乡深锁已久的木门,看见荒芜的杂草高过了屋顶,而父亲当年栽下的月季和大花马齿苋,在漫长的岁月中,依然开着鲜艳的花朵。我抚摸着经过时光漂洗的井台、石臼和耙犁等一些锈蚀的农具时突然发现,我字里行间所有的描述、追忆、隐喻和赞美无不指向家乡的时间与空间。赫尔德说:“乡愁是一种最高贵的痛苦。”其实我的写作,不过是家乡把自己的模样呈现给了我,而我在寂寞的时候把自己的情感经验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恰巧又被怀着同样心境的你看到了而已。我理解了那个在大雾中哭喊的乡亲,当年目睹的那场大火,再一次在我体内燃烧起来。
站在村口,那个种瓜的老人已经认不出我了。当年,南岭下密水河边他种下的瓜果,香气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记忆里。老人佝偻着身子问我的父亲是谁,而我,心里依旧有着当年偷瓜的歉意,怯生生,像个孩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