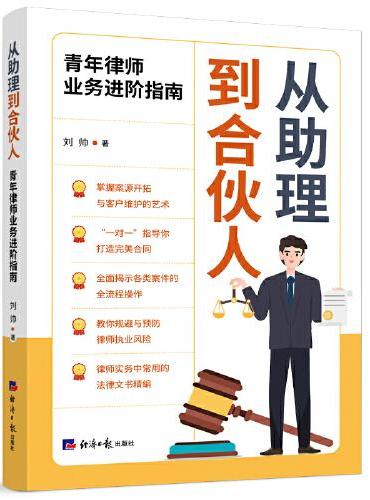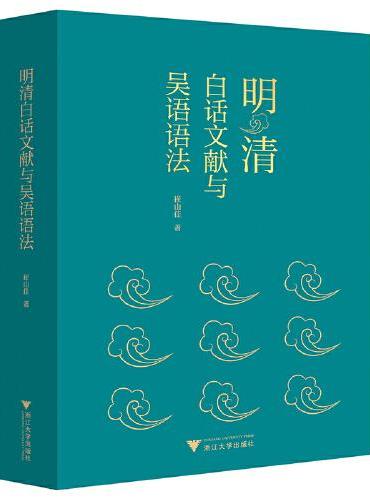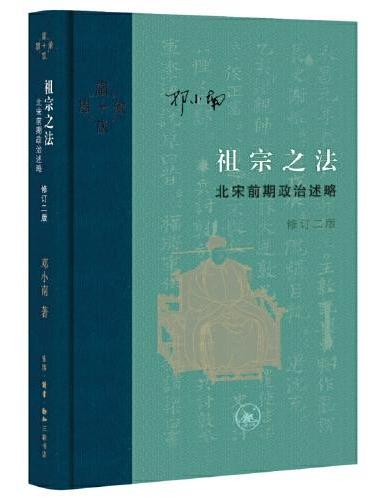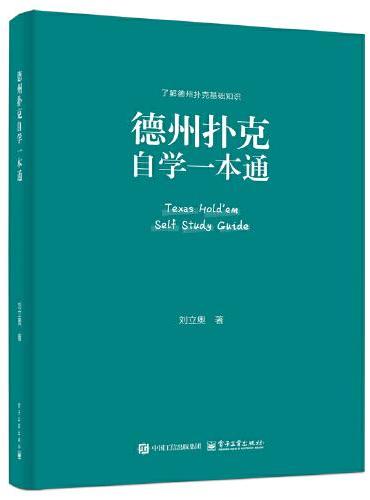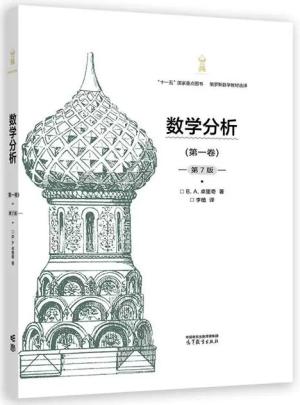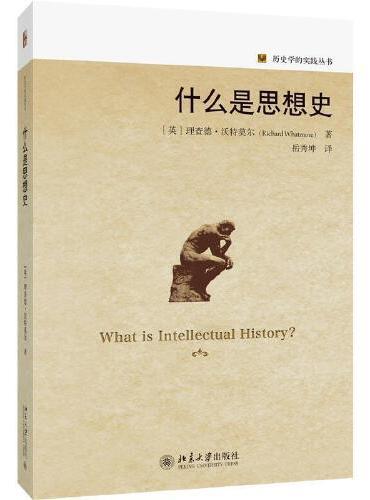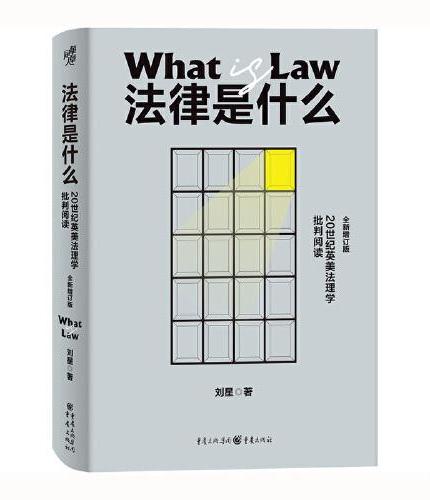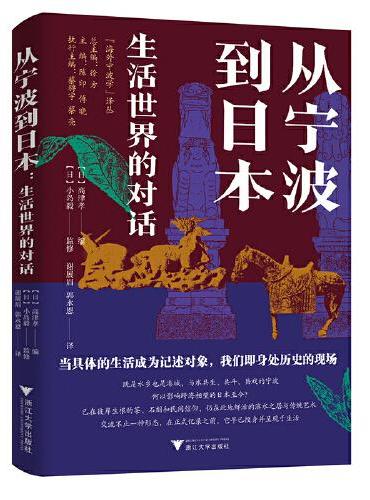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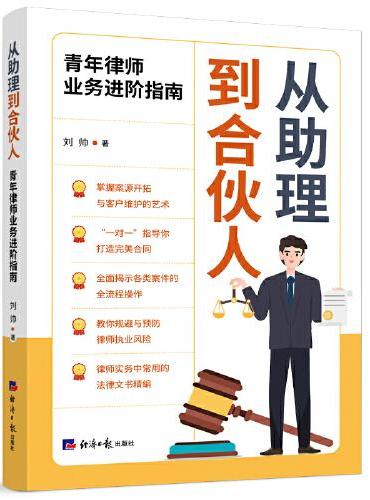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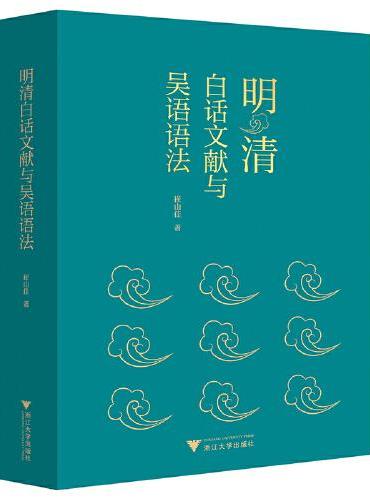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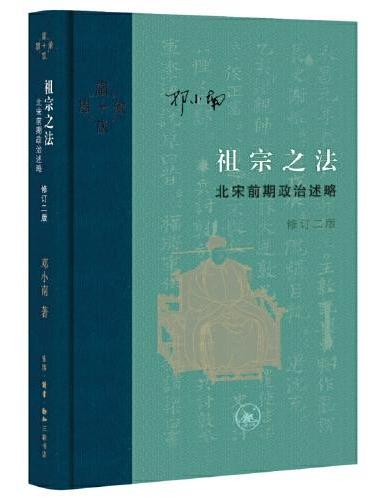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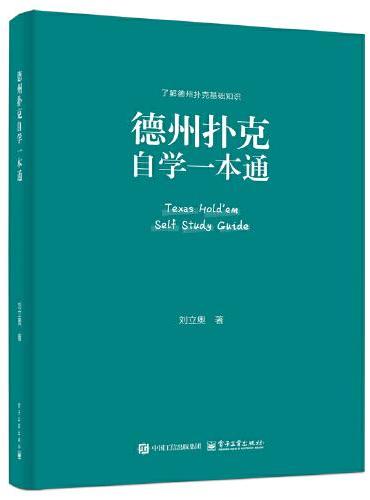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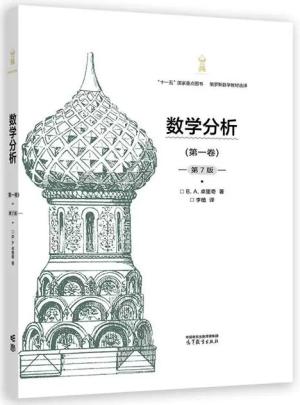
《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7版)(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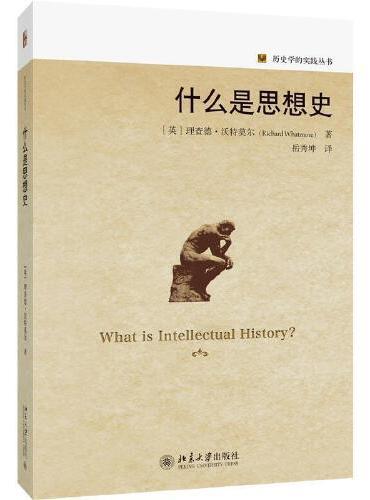
《
什么是思想史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NT$
2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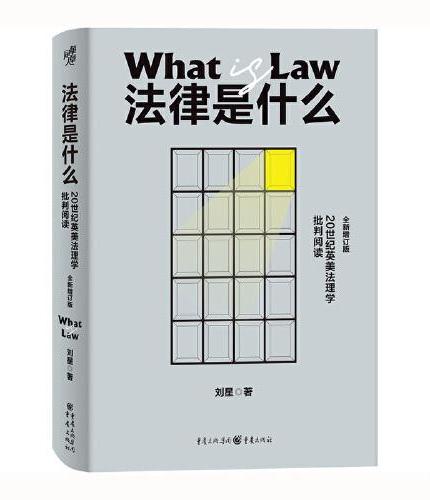
《
法律是什么:20世纪英美法理学批判阅读(全新增订版)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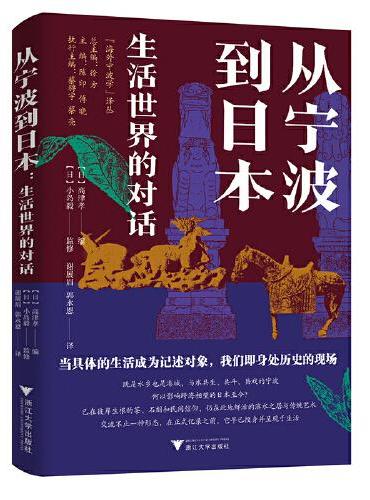
《
从宁波到日本:生活世界的对话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著名历史学家黄一农教授重磅力作!科技史角度,探究明清战争胜负密码!
★以红夷大炮的作战使用,解密明清军事实力的扭转,清朝为何能击败明朝定鼎中原!
★站在“大航海时代”的环球视野,欧洲沉船、西方传教士、外籍雇佣兵、南洋华工……这一个个落点,逐渐汇成明清易代的历史图景!
★作者以天文学家身份纵入历史学界成为名家,研究视角新颖,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足够“硬核”!
|
| 內容簡介: |
本书作者实地勘查了散在世界各地的数百门明清红夷大炮,并结合庞杂的史料记述,尝试勾勒出这些西式火器的“文化传记”,重现其在中国两百多年间的演变过程和多样性。
红夷大炮的操作与铸造技术,是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课。书中首先探索十七世纪初自闽粤沿海欧洲沉船上打捞的大炮,如何在天主教徒的努力下进入辽东战场,并在萨尔浒之役(1619)重创努尔哈赤。皇太极又如何起用降顺的汉人铸炮、操炮,并以汉人炮兵与满蒙步骑兵协同作战的卓越战术,迅速在中原攻城略地。此事不仅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军事革命,更使清朝建立起亚洲*强大的“火药帝国”。
明清两朝所先后发展出的铁心铜体红夷大炮,不仅比铜炮更轻更省,且大幅强化了炮管的抗膛压能力,其品质曾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然而,即使是此独特的复合金属制法,在清朝定鼎之后的长期平和状态中也遭到遗忘,十九世纪时遂无力面对列强新一代火器的挑战……
|
| 關於作者: |
|
黄一农,198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而后于马萨诸塞州立大学从事天文学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座教授,曾兼人文社会学院院长,“中研院”院士,是以研究科技史闻名的历史学家。曾任荷兰莱顿大学首届“胡适汉学访问讲座”教授、香港大学及香港理工大学荣誉教授、北京清华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北京中国科学院名誉研究员、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名誉高级研究员等。其研究领域涵盖科技史、中西文明交流史、明清史、术数史、军事史、红学等。代表作有《两头蛇:明末清初的代天主教徒》《制天命而用:星占、术数与中国古代社会》《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红楼梦外:曹雪芹〈画册〉与〈废艺斋集稿〉新证》等。
|
| 目錄:
|
上编 引进·仿制
第一章 明末萨尔浒之役的溃败与西洋大炮的引进 / 003
第二章 欧洲沉船与明末传华的西洋大炮 / 035
第三章 明清之际红夷大炮在东南沿海的流布及其影响 / 092
中编 时局·军事
第四章 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新考 / 145
第五章 明末至澳门募葡兵的姜云龙小考 / 178
第六章 刘兴治兄弟与明季东江海上防线的崩溃 / 195
第七章 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 / 225
第八章 崇祯朝“吴桥兵变”重要文献析探 / 270
第九章 吴桥兵变: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 / 290
第十章 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 / 336
下编 技术·文化
第十一章 比例规在火炮学上的应用 / 385
第十二章 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以火炮测准技术之演变为例 / 392
第十三章 明清独特复合金属炮的兴衰 / 431
第十四章 清朝火药帝国的盛衰:从江阴之役至鸦片战争 / 488
大事年表 / 522
传教士、外籍人士姓名对照表 / 530
参考文献 / 533
重要人物人名索引 / 568
|
| 內容試閱:
|
自 序
人生有些道路往往是事前完全无法预料的。我年轻的时候痴心想得诺贝尔奖,要当世界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要解决连爱因斯坦都没能解决的统一场论(unified field theory),所以跟随留学潮于1979年到了世界十大名校之一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些现实状况让我很快体会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年后我就决定转换跑道至从小着迷的天文学。当时我的研究还算不错,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等一流期刊上都曾发表过论文,并于全美的微波射电天文台(millimeter-wave radio observatory)担任博士后研究员。1987年我在通过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创院院长李亦园院士的面试后,毅然送掉了所有物理和天文的书籍离开美国,改行进入母校刚成立的历史研究所。报到后,所里才告知我不是长聘教师,得经两年试用之后再决定是否可留任。如果事前知道,我应该不敢受聘,而会以两岸代射电天文学家的身份留在科学界打拼,那将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学术生涯。
回台的个学期,我不被允许开课,因为有老师认为我没有文科学位,所以无资格教此专业。当时内心的确很难过,但换成另一种思维,工资照领,我每天都徜徉在新竹和台北的几间大图书馆中,努力建立自己的知识地图,那个学期或许是我一生中既痛苦却又成长快的时刻。
我很幸运,转行一开始就碰到所谓的 “逆增上缘”,让我必须拿出的努力并激发出所有潜力来面对生存挑战。1991年我成为台湾学界位以科学史的研究成果升等为正教授之人,2006年我更侥幸获得“中研院”文科院士的桂冠,但这段努力存活并蹈厉奋发的过程,也令我因此错过两个女儿成长过程不少的重要时光。而每每一激动就想转行的我,在这段期间其实还遭逢一些生命分岔,我曾入列校内天文研究所以及资讯系统与应用研究所创办时的教授名单,也曾带领一群年轻人设立了当时华文世界的网络虚拟博物馆——清蔚园,甚至成立过网络公司。有段时间,更差点离开学术圈,转去担任一座科学类博物馆的馆长,亦尝受邀去参选一所艺术类大学的校长,还起念想编写一个明清之际史诗型电影的剧本,拍部有机会能感人肺腑的电影……
如果人生能重走一遍,我喜欢的应该还是做一名历史学家,因为在这领域我真正体会到安身立命的感觉,我对自己的研究题材也始终怀抱热情,虽然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投资回报率极低的行业。
我进入文史学界后,学术生涯中所遭遇比较大的问题,是因成长过程全靠自己摸索,欠缺师长的明灯指引,故在科学家思考模式的强烈影响之下,一直以发表论文为主要研究目标,未能积极撰写专书。此一心态直到2005年出版《两头蛇:明末清初的代天主教徒》后才有了重大改变,然因新切入的红学领域仍颇需全力投入,故始终无法抽出精力对早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此书的成形要归功于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小友邹近先生,没有他的主动积极,不可能从这一堆单篇论文中编整出目前的面貌。此外,没有诤友中国人民大学张瑞龙老师的热情校稿与意见提供,我也会缺少付梓的勇气。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自己已长时间不曾关注此领域,编纂此书时真有点近乡情怯的感觉,因这将是我在军事史范畴的本书,也应该会是的一本,尤其知道我已不再有多余心力可将这些一二十年前钻研过的议题,在大数据的新环境下以理想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然而在爬梳近年学界相关研究的过程中,既高兴见到一代新锐(如郑诚、尹晓东、刘鸿亮、张建、周维强、常修铭诸博士)的新作,因可借以补充先前论述的不足,也庆幸自己早先的研究尚无须做较大程度的修订。
此书原本构思的名字是 “三头兽:引发明清军事革命的红夷大炮”,以呼应笔者先前出版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代天主教徒》(2005)及《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2014)的书名,但后还是选择了较简短直接的 “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在此,“红夷大炮”主要指的是欧洲所发展出的前装滑膛加农炮。而 “三头兽”则谓1553年在意大利阿雷佐(Arezzo)城挖掘出的著名铜雕基迈拉(Chimaera),其主体是一只会喷火的三头怪兽,兽身的前半部有狮以及山羊的头,兽尾则是一条蛇,正用嘴逗弄山羊的右角。该铜雕现藏佛罗伦萨的考古博物馆(Archeological Museum in Firenze),风格属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托斯卡纳艺术(Etruscan Art),为意大利本土、希腊和东方元素的混合体。在基迈拉出土的前一年,很巧合地,利玛窦诞生于约180千米以东的马切拉塔(Macerata)城,他或许是入华耶稣会士甚至意大利人在中国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更是中外交流史上的时代巨人。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选择天文历算和红夷大炮作为吸引明朝统治阶层重视的媒介,但后两者却都沦为清朝所用。
由于钦天监每年所编制的历日中订有朔闰与节候的时间,而此一关乎日用民生的纪日标准,是治理一个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的,故中国历代对颁历一事均甚为看重,并将其升华成拥有统治权的具体表征,此事所含蕴之“奉正朔”或“颁正朔”的政治意义,在朝代更替之际尤其明显。至于原先被明军视为足以对抗八旗精锐步骑的红夷大炮,后却因缘际会倒转成为清军摧毁中国传统城池结构之利器,让清朝得以在很短时间入主中原。本书即尝试梳理在萨非(Safavid)、莫卧儿(Mughal;或译作蒙兀儿)以及日本之后,清朝如何于十七世纪转变成亚洲强大“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又为何在十九世纪时无力面对列强的侵略。
十六世纪是欧洲文明所开创“大航海时代” 的起点,他们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像海啸般一波波地强烈冲击包括亚洲在内紧邻大洋的各个国家,不仅在四处点状地建置商港和堡垒,更开始进行面状的殖民扩张。葡萄牙首先于1510年在印度西岸的卧亚(Goa;今译果阿)建立根据地,并将势力范围陆续延伸至印度次大陆的滨海地区、东南亚盛产香料的岛屿以及中国沿海的澳门。西班牙则于1571年入据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与其在美洲的殖民地相互呼应。1580年起,葡萄牙王位由拥有优先继承权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兼领,此一信奉天主教的西、葡联合王国,虽然内部矛盾不断,但至少表面上形成了海上强权,教廷的传教士在其保护与支持之下,也积极至亚洲各地宣教。
但随着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征英的惨败,西、葡两国在亚洲所拥有的优势,开始遭到欧洲新教国家的挑战。1581年宣布脱离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在1600年派船航抵日本,两年之后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而1600年创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爪哇岛上的万丹(Bantam)建立据点,往来欧洲、东南亚和日本进行贸易。荷、英两国透过东印度公司的设置,整合国家与民间的军事以及经济力量,将其触角强而有力地伸入亚洲,它们不仅相互掠夺,也不断与西、葡发生激烈冲突。从印度洋、南中国海、中国东南沿海以迄日本南端的九州岛海域,欧洲强权的战舰与商船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海战,整个亚洲几乎只剩下一些内陆地区还未明显感受到西潮的冲击。
大明帝国末期主要的威胁,乃来自陆上精于骑射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内部的民变,在连亘二三十年的军事冲突中,对火器的倚重益发明显,不仅外来的火绳铳(又名鸟铳,十六世纪中叶即已传入)逐渐加入个人用火器的行列,且自天启元年起,曾数度将西方铸造的红夷大炮解京运用,这些炮大多打捞自广东沿海的欧洲沉船,威力远超过中国军队长期所使用的佛郎机铳、将军炮、灭虏炮或虎蹲炮等。火炮的操作与铸造技术,因此成为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课,并在战场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当欧洲文明于十六世纪开始张开大帆迈向海洋时,他们所掌握的优越航海技术和所具备的旺盛探险精神,令邻近大洋的其他文明均不再可能闭关自守,而那些商船和战舰上的先进大炮,更是他们扩张海权的利器,并成为几乎每一个东方国家的梦魇。郑和以后的大明帝国对于海洋的关注度一向不高,甚至还曾采取海禁政策,但在大航海时代中,却也无法阻拦已经冲击到中国沿岸的西潮。而东西方接触后所衍生的庞大经济利益,不仅令欧洲这些海权国家积极开创或争夺这一广大市场,更吸引了闽粤人士开始发展私人海上贸易。
本书即从十七世纪全世界规模的会战之一萨尔浒之役(1619)出发,探索金国如何以其训练精良的弓箭手,搭配雷霆万钧的铁骑,大败过度迷信传统火器的明军。而战败的明军又如何在南洋地区闽籍工匠的协助下,积极仿铸欧洲前膛装填式的“吕宋大铜炮”,惟因品质远逊,结果未能在稍后的沈辽之役(1621)力挽狂澜。而澳门地方也因自身的防卫吃紧,且其铸炮工业尚在起步阶段,又不愿将其赖以生存的高阶武器提供外人,以致无法满足明廷的迫切需求。在此状况之下,广东沿岸的欧洲沉船遂因缘际会地成为西炮的供应来源。天启年间,先后共有来自三艘沉船的四十二门大炮因此被打捞并解运至北京。这几艘远渡大洋却沉没在东方大陆边缘的欧洲帆船,均是在相互劫掠或运送货物的过程中遭逢意外(暴风雨或触礁等),亦即,在这中西次大规模接触的时代里,沉船还不是双方军事冲突的结果。这些捞得的先进火器,虽然只是当时欧洲扩张在世界各地所衍生出的一小段插曲,却直接或间接催化了中国军队所用武器的重大变革,不仅因此改变了中国战场上的攻守形态,甚至进而在明清鼎革的大动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接着,徐光启、孙元化等官员更努力引进西方炮学,还招募澳门的葡萄牙铳师至山东训练部队,进行了一场由天主教相关人士主导的军事事务革命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不幸的是,这支全中国战力强、装备好且受澳门来的葡萄牙军事顾问团直接训练的炮队,却在崇祯四年的吴桥兵变中,随同孔有德、耿仲明(原均为登莱巡抚孙元化的属下,皇太极特封二人为王)降金,致使后金军事实力大幅提升,成为其后来攻城略地、入主中原的关键之一。
皇太极因先前在宁远、锦州等役的失利,深刻认识到红夷大炮的长项,遂积极起用降顺的汉人铸炮、操炮,甚至创建了八旗汉军,并开创出以汉人炮兵与满蒙步骑兵协同作战的卓越战术。满洲政权经由这场军事革命因此得以统治中国两百多年。书中尝试将皇太极应有的令名搬上世界军事史的舞台,以与恰处于同一时代而被誉为“近代战争之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东西辉映。
后笔者将以十七世纪在中国所发展出的独特复合金属炮为例,探索明人如何在与清军长年交战的过程中,融入南方较发达的铸铁工艺以及北方已有逾百年传统的铁心铜体佛郎机子铳制法,造出品质绝佳的铁心铜体“定辽大将军”炮。稍后,清朝也利用投降汉人工匠成功量产出结构类似的“神威大将军”炮。这些复合金属炮比铜炮更轻更省,且可强化炮管的抗膛压能力,其品质在世界应居领先地位。然而,此一先进制法却在清朝定鼎之后长期的平和状态中遭到遗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被迫大量造炮以备战的清廷,虽重新采用复合金属技法铸炮,却已无能面对西方列强所采用卡龙炮(carronade)以及后装线膛炮(breech-loading rifled cannon)等新一代火器的挑战,天朝终于在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败的耻辱中崩溃。
这本火炮史的专书大致总结了笔者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虽对红夷大炮的传华史事、仿铸与演进、瞄准与操作等课题,均有不少开创性的劳绩,也触及这种新型武器在一些重要战役中所曾发挥的影响,但因过程中常处于独学而无友的状态,且到底受限于个人的能力与学养,以致研究的涵盖面与深入度均尚欠完备,但对未来治明清军事史的学者而言,或仍可提供一相互切磋或攻错的基石。
惭愧!由于我转换跑道太过频繁(内子笑我一定偷学过川剧变脸),且早期又缺乏较好的学术生涯规划,以致十年前因亟于探索文科在大数据时代所可能面临的新机遇,遂转进遭逢重大发展瓶颈的红学领域,选择成为火炮史研究的逃兵(小友张建每次相逢都调侃我该早日迷途知返)。期盼有兴趣的学界新锐们,能在大数据的新研究环境之下,并肩挑起开辟此课题新沃野的重责。
2020年10月定稿于新竹南庄二寄轩
十六世纪是欧洲文明所开创“大航海时代”的起点,他们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一波波地强烈冲击包括亚洲在内紧邻大洋的各个国家。荷、英两国透过东印度公司的设置,整合国家与民间的军事以及经济力量,将其触角强有力地伸入亚洲,它们不仅相互掠夺,也在从孟加拉湾、南海、东海以迄日本海的区域,不断地与西、葡发生激烈冲突,整个亚洲几乎只剩下一些内陆地区还未曾感受到西潮的冲击。
大明帝国末期主要的威协,乃来自陆上精于骑射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内部的民变。在绵延二三十年的军事冲突中,对火器的倚重益发明显,不仅外来的火绳铳(又名鸟铳,十六世纪中叶即已传入)逐渐加入个人用火器的行列,且自天启元年起,曾数度将西方铸造的重型前装滑膛火炮(所谓的“红夷大炮”)解京运用。这些炮大多打捞自广东沿海的欧洲沉船(详见后文),威力远超过中国军队长期所使用的佛郎机铳、将军炮、灭虏炮或虎蹲炮等。火炮的操作与铸造技术,因此成为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课,并在战场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然而,中外早期文献对西洋大炮传华的相关史事,不仅记载不一,更屡屡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形。在有些十七世纪的欧洲文献中,由于其作者未能掌握一手材料,以致叙事常未能信而有征。即使是出自在华传教士的著述,也往往因认识不足甚或为宣传的目的,而有曲解或误解事实的情形。晚近学界虽已针对此一课题进行过一些深入的研究,但仍存在许多尚待厘清的问题,且在相关的史学专著中,不仅对西洋火炮传华的过程和影响未给予适当的比重,甚至常出现错误的陈述,尤其,迄今未见学者对这些船炮取得的历程有较翔实的着墨。
本章因此尝试重新梳理中文文献(含新发现之打捞阳江沉船的记载),并整合西方原始材料(如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平户商馆日记和书信、时人的航海日志和游记、沉船资料、船炮的配置纪录等),再对照中国现存欧洲古炮的实物,希望能较全面地了解此一西方火炮东传的事件(可与章相参照)。
一、万历末年仿制的西洋大炮
现今许多学者常误以为红夷炮是因荷兰人首先传入而命名的,且是明军在交战中所缴获的战利品,此说主要衍生自《明史》的记载,其中《兵志》有云:
万历中,通判华光大奏其父所制神异火器,命下兵部。其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天启中,锡以大将军号,遣官祀之。
原任山东兖州府通判的华光大是在万历二十四年上奏的,先前因东虏入寇河北广平,光大之父华富负责督放自制的“神异火器”,得获大捷。由于前引文中以“复得”一词来形容西洋巨炮,不知华富所制的火器是否亦为红夷炮之属。又,该文虽称红夷炮乃得自来华的“大西洋船”,其实并未明确指出该炮是缴获的。
由于明人在十六世纪末叶应已具备制造红夷炮的技术水平,故若华富所铸的“神异火器”确属该种炮的形制,亦不令人意外。查在嘉靖二年的西草湾(位于今广东新会)之役中,汪曾缴获葡萄牙人的佛郎机铳二十多门,大者重千余斤,未几,冶铸业发达的广东东莞地区就已能仿制。另据嘉靖末年的统计,辽东各城总共配置了各式佛郎机铳一千四百四十三门,其中至少有五百四十九门为铜铳。而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中,亦曾提及的佛郎机铳长达九尺(明代一尺约合32厘米)。知在华富铸炮之前,明人应已充分掌握制造大型佛郎机铳的能力。而因佛郎机铳的炮管后段必须有一凹槽以与子铳密合,亦即其制造应较红夷炮复杂,故若中国工匠能获得红夷炮的形制规格,仿制或不应太难。
但前引《明史》中对红夷炮的描述,出现许多夸大或讹误之处。因以1599年的英国海军为例,其所配置的型火炮为大鸩铳(cannon),口径约20厘米,长约325厘米,重6000—7000磅(明代一斤约合597克,相当于1.32磅),射程为1.2千米;较次级的半鸩铳(demi-cannon),口径16.5—17厘米,长约300厘米,重4000—6000磅,射程约1千米;再次级的大蛇铳(culverin),口径约14.5厘米,长约390厘米,重4000—4500磅,射程约1.45千米。故当时来华的船炮绝不可能长达二丈余(逾6.4米),且亦不可能拥有“震数十里”(明代一里约合576米)的威力,顶多只可形容为“长一丈余……震数里”。
《明史·和兰传》中对来华的荷兰船炮,也有类似的夸大叙述,其言曰:
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其所恃惟巨舟、大炮,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巨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世所称红夷炮,即其制也。
查万历二十九年确有两艘荷兰船首航抵澳门,要求与中国通商,但为澳人所逐。三十一年,刚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又遣两舰攻澳,亦遭击退。翌年七月,三艘荷兰船在韦麻郎的率领下占领澎湖。十月,始被浯屿把总沈有容把酒劝离。韦麻郎临行时曾以“铜铳、铳弹及国产物”赠送沈有容,沈氏只取无直接杀伤力的铳弹留念,韦麻郎因而“感泣谢别”。知在中荷接触之初,明军应不曾取得或缴获红夷炮,而中荷间的激烈交战可能要到天启二至四年荷人再度占领澎湖时才发生。
根据明人的记载,荷兰船较明军战船大“十倍”,船身还加附铁板,上列铜铸大铳三十余门,所用之铁弹且有号称重数十斤者,因而予人“器械精利,非诸夷比”的印象。然而,当时荷兰的铸炮业其实并不特别发达,许多大炮均是购自英国,惟荷兰东印度公司船上所配置的火力确实要较一般商船为强。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明军在萨尔浒之役几乎全军覆没。六月,信奉天主教的徐光启上疏指陈辽东的局势危急,主张应立刻访求“闽、广、浙、直等处精巧工匠”,以铸造大炮。同年九月,他亦疏奏应从广东“募送能造西洋大小神铳巧匠十数名”,并“买解西洋大小诸色铳炮各十数具”,且称“福建监生伍继彩自言同乡有能造海洋极大铳炮者”,请求应“作速遣行,从厚给资,趋令星夜前来,听候委用”。由于当时闽粤地区的冶铸技术冠于全国,而大炮的运送又旷时费事,故徐光启建议应访求南方巧匠至京仿制西洋大炮。
天启元年四月,因沈阳和辽阳均于月前被攻陷,刑部尚书黄克缵乃疏请“演神器并收遗兵”,中称自己先前在奉命协理京营戎政时,曾召募工匠在京铸造“吕宋大铜炮”,其言曰:
臣任协理戎政时,曾募能铸吕宋大铜炮匠人来京,铸完大炮二十八位。遣援辽守备黄调焕同壮士陈有功、顾应泰等三十人,解去辽阳七位。其一位重三千余斤,为李秉诚请去奉集,一发击毙建夷七百余人、将官二人,此道臣高出之所目击。其余重二千余斤及一千斤者,分守辽阳、山东,闻再发击毙建夷二千余人,此袁经略(农按:指袁应泰)之所面赏。今三炮一埋地中、其二击破,惟有四号者三位,为建夷所得,然彼亦不能用也。所遣三十人,初以为尽于辽矣,今尚存二十六人,见在宁前,真壮士也。戎政府中尚有大炮十七位、大佛郎机十二位,……此则神器所当即演者也。
知当时共铸成铜炮二十八门,者分别重三千余斤、二千余斤以及一千斤,余为千斤以下之炮。
黄克缵为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奉旨以南京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十二月,升任工部尚书;四十八年七月,转刑部尚书;泰昌元年十月,以刑部尚书暂署兵部并协理戎政,同月丙寅,旋由崔景荣接掌兵部。由于黄氏在泰昌朝担任协理戎政的时间极短,因知这批型式不一的铜炮应可能铸成于万历四十七年下半年,此事或呼应先前徐光启的建议。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因辽镇请发各式火炮,兵仗局于是回奏称“神器已经试验,俱各堪用”,奉旨差官将炮星夜运解前去,这里所谓的“神器”或指的就是包含一门重达三千斤之“吕宋大铜炮”在内的新铸火炮。当时负责解送数门铜炮出关的黄调焕,乃黄克缵的侄孙,但在辽东经略熊廷弼亲自试放时,其中一门重千斤者却当场炸裂无存。
户科给事中官应震亦尝于万历四十八年的疏奏中提及此一铸铜炮之事,曰:
若火炮,则中朝虽有,而制造失传,击杀不多,唯是西洋夷人善造、善放,皆精妙有法。计一大炮铜重万斤者,可杀人无筭。在岁癸卯,西洋人仅四百计耳,以用火炮,致我闽漳泉贩夫、贾子被歼于吕宋者四万。今西洋人潜住粤澳,实繁有徒,闽人尚多传得其法。戎政尚书黄克缵业捐多金,购闽人之善造者十数辈至京,同泰宁侯(农按:指总督京营戎政的陈良弼)造炮于京营,已造成大炮一位,铜重三千斤。
他指出西洋人所造的铜炮,大者重可万斤,在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岁的吕宋惨案中,即有约四万(亦有作两三万)名居住在马尼拉的闽人,被为数仅四百的西班牙人以强力火炮杀害。官氏并称有不少闽人曾自西班牙人习得铸铜炮之法。
相较于中国其他地区,闽南与菲律宾的往来既多且早。早在万历二年追剿海贼林凤的事件中,双方官府即有所接触。其时,西人初占菲岛,物资供应颇赖每年来航的中国商船,而所载去的货物当中,除生活用品外,还包括火药和铁弹等军备物件,以及制造铜炮和弹药的原料。万历年间,马尼拉的华人(主要来自闽南)也一直维持在数千至三四万之谱,此一频繁的交往应提供“吕宋大铜炮”铸法传华的绝佳环境。
福建道监察御史彭鲲化在万历四十七年的《通州兵哗幸定》一疏中,尝称:“戎臣(农按:应指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欲制吕宋炮,一可当万,闽中行之既效矣,此当速造以为中国长技。”彭氏在天启三年五月的奏疏中,亦有“吕宋火炮,闽中放之既效”句,指出在之前福建已有人成功仿铸并使用过“吕宋大铜炮”。又,徐光启在天启元年曾指出广州有工匠曾在澳门打造大炮,二年九月,驻防厦门的总兵官徐一鸣因有荷船五艘入侵,亦曾“向洋商铁匠暂借铳器”,与夷船对打,知先前闽粤沿海确已有工匠掌握部分相关技术。
虽然有学者认为该“吕宋大铜炮”乃后膛装填的佛郎机炮,但由于黄克缵在前疏中将其与大佛郎机并称,显见两者不同。且万历四十七年黄氏曾要求南京兵仗局将所藏七八尺长的铜铸佛郎机二十门解京,而他在该疏中并不曾使用“吕宋大铜炮”之名,故疑“吕宋大铜炮”或指的是前装滑膛的西洋大炮。尤其,天启元年李之藻所上的《奏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有云:
香山嶴夷商所传红夷大铳者,臣向已经营有绪,……则夫西铳流传,正济今日之亟用。……臣闻往岁经营亦曾仿造此铳,然而规制则是,质料则非,炼铸、点放,未尝尽得其术。
内所称先前仿制之铳,或即黄克缵铸造的“吕宋大铜炮”,其“规制”与红夷大铳相同,但材料品质则远逊。
天启元年二月,兵部命守备黄调焕率新募之官兵两千余名援辽,三月,后金陷沈阳,辽东经略袁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力守辽阳,惟诸将均溃败,监军道高出等自城中遁逃,应泰亦自杀。黄克缵在前疏中所称这批“吕宋大铜炮”中者(重三千余斤),大概是元年二、三月间运至奉集的。黄氏引述败军之将高出和袁应泰的话,称这些炮曾分别毙敌七百余人或二千余人,此明显过于浮夸,否则辽沈之役亦不至于一败涂地。这批炮或因品质不佳,或因操作不得当,以致出现“随装随放,炮热药燃”“连发炮热,装药即喷”等情形,袁应泰亦称“内府解发铜炮虽多,放辄炸裂”,尤其,的三门当中就有两门膛炸。
综前所论,明末之人乃因欧洲国家的海权扩张而得见西洋大炮(本章中的炮或铳,除与佛郎机连用之外,均指前装滑膛型),闽人应早在万历初年即已经由与吕宋的交流而有所接触,此种炮同时也随着往来频繁的葡萄牙船而屡见于广东和澳门海域。惟因西、葡两国自万历以后即未与中国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故明人应是首从荷兰人亲历此种炮的威力,遂将欧洲各国所制造的前装滑膛炮铳称作“红夷炮”,而非因荷兰炮质量超绝或传华早之故。虽然,万历末年福建工匠曾加以仿铸,但不论是炼铁或点放,均“未尝尽得其术”,以致未能在辽东战场上发挥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