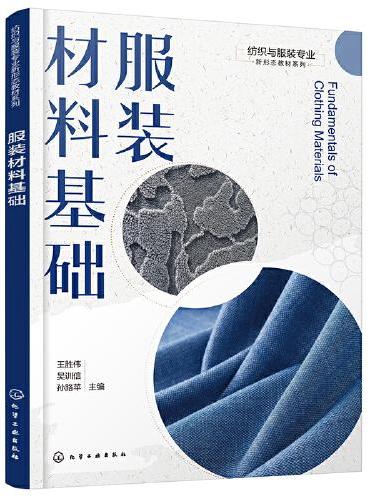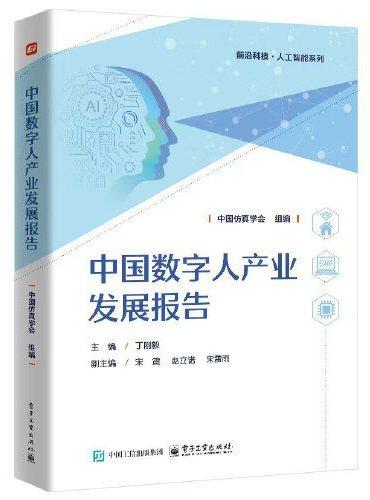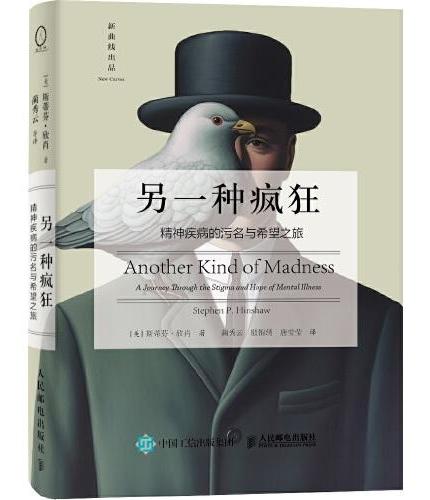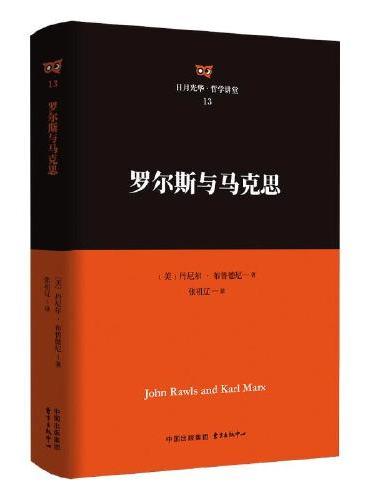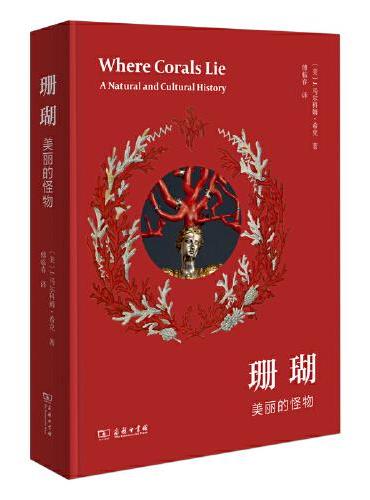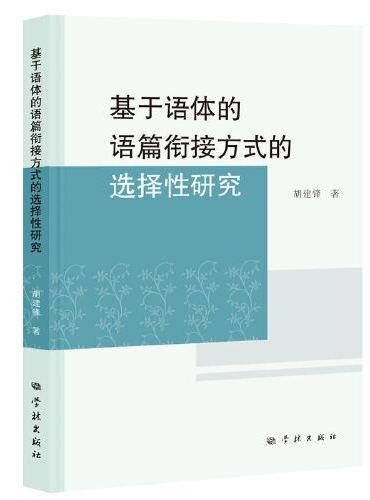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家庭财富管理指南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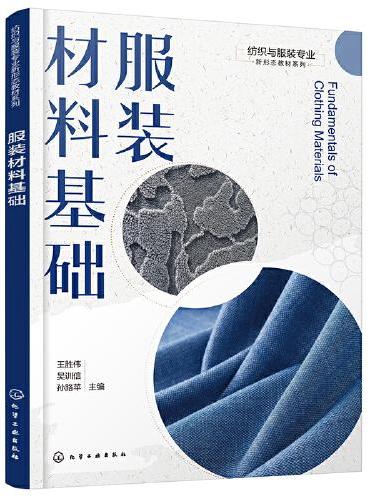
《
服装材料基础
》
售價:NT$
296.0

《
国家名片C919(跟踪十余年,采访百余人,全景式呈现中国大飞机C919,让读者领略到中国航空科技的最新成就)
》
售價:NT$
6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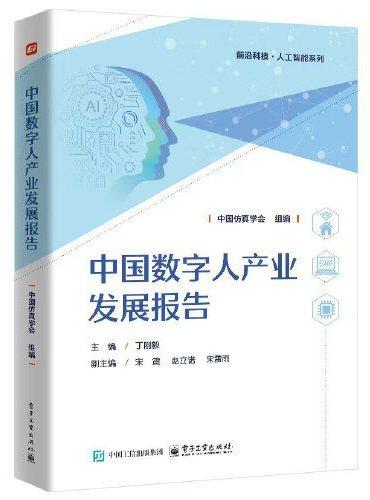
《
中国数字人产业发展报告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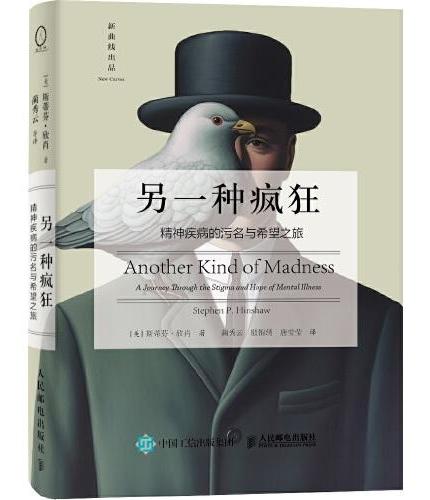
《
另一种疯狂:精神疾病的污名与希望之旅(APS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斯蒂芬·欣肖教授倾其一生撰写;2018年美国图书节最佳图书奖)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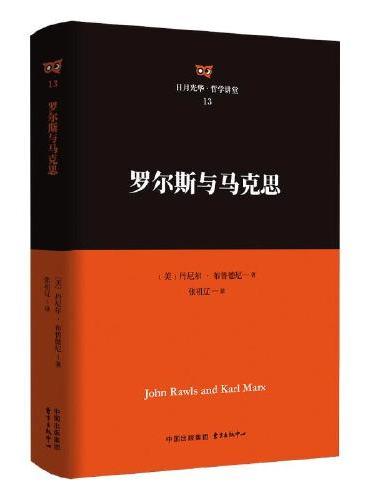
《
罗尔斯与马克思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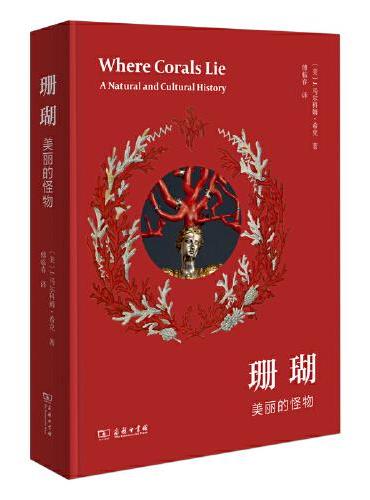
《
珊瑚:美丽的怪物
》
售價:NT$
58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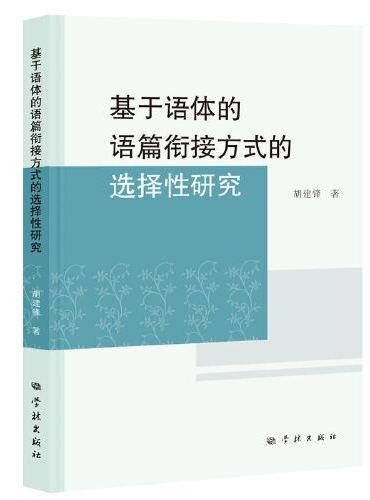
《
基于语体的语篇衔接方式的选择性研究
》
售價:NT$
347.0
|
|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得主之一、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后天小说奖得主之一、七〇后实力派小说家赵志明全新小说集。收入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双子星”奖获奖作品《歧路亡羊》。每篇小说自带独特的叙述角度,写法亦各有春秋,配上赵志明式自成一家的日常情感体验描写,引人共鸣。同一时空下,同样平凡的他们却过着被我们无意隐去的生活:一生黑暗的盲人、见弃于人的流浪儿、不得志的年轻人……鲜活丰满的人物,被命运无情抛弃的人生,为摆脱局外人困境所作的努力——是时候让他们被看见了。图书采用折叠式大腰封,内印精美插画,暗合“看不见的生活”主题,潜入人世和心灵的迷离之境。
“赵志明在他本人、他的小说,以及他所处的世界中,构建了某种隐秘而独特的联系。”
——徐则臣(小说家)
编辑推荐
写作近二十年,小说家赵志明在探索中成长,一直表现不俗。继《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万物停止生长时》《无影人》《中国怪谈》等小说集之后,赵志明携全新力作再次闪亮登场,为读者献上他对平凡人物的持续关注,对日常生活(家庭、婚姻、生死等)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洞见,对人类共同情感/心理自成一派的细腻描
|
| 內容簡介: |
十一个故事,《看不见的生活》《歧路亡羊》《洞中男孩》《深夜狗叫》……这些脱胎于平淡日常的小说,无论是故土记忆还是都市生活,赵志明都以真诚悲悯又不失先锋幽默的独特笔触呈现出来,撕开了平凡生命下一段段暗流翻涌的无奈人生。但即使身处困境,这些平凡人仍努力寻找生命的出口,重获新生。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人类共有的情感让本书对生存际遇的描写免于流俗的追问与思考,具有难得的温度、高度与冲击力。
《看不见的生活》:一个盲人貌似波澜不惊却又暗流翻涌的生活;
《洞中男孩》:童年捉迷藏的恐怖记忆与成年现实生活交叠互回,是困于生活之洞还是走出生命之洞;
《歧路亡羊》:诸事不顺的年轻人为逃离现实,劫持了一对老年夫妇,胁迫了分手的爱人,歧路通向何方……
|
| 關於作者: |
|
赵志明,江苏常州人,写作史近二十年,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得主之一、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后天小说奖得主之一、七〇后实力派小说家。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文联签约专业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青蛙满足灵魂的想象》《万物停止生长时》《无影人》《中国怪谈》等。
|
| 目錄:
|
看不见的生活 …… 1
如果你是我 …… 25
歧路亡羊 …… 41
路口 …… 89
一封电报 …… 131
逃跑家 …… 153
深夜狗叫 …… 173
洞中男孩 …… 199
我们的朋友小正 …… 219
象舞之年 …… 243
参与商 …… 279
|
| 內容試閱:
|
(本文为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双子星”奖获奖作品)歧路亡羊(节选)
在陶菊英那里,空间简化,呈现一种“里外里”的关系。她只需说出两个词,“出去”意指去到家的外面,“家啊”就是回到家的里面。家也简化为东南西北任意一堵高竖而起的墙,或者一面窗,很可能只是作为触目可及的参照物,以不断被忽略的方式逐渐解体,缓慢消融。只有丈夫老鲁,她还可以凭借习惯依赖他,依循气味辨认出他。当她从身体里摇出一颗声音骰子,发出“出去”或“家啊”的坚定回响,老鲁便照做,陪着陶菊英出去,或者带她回来。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家,漂浮在二三十米的空中。名下还有一辆车,趴在车位里像生锈的甲虫,跑在路上像懒驴拉的辎重。在家中时,陶菊英喜欢坐在窗前,长久地看着外面。窗外通常一只鸟也没有,但不乏云和飞机。云无心以出岫,往往张挂在上下两道眼皮之间,造成一动不动的错觉。陶菊英盯住云,轻易不眨眼,怕把云咔嚓几下挤不见了。飞机出现的频率很高,半个小时左右一架,展开一双翅膀,或昂首攀高,或俯身下降。一旦飞机跳进窗格子里面,陶菊英的视线便随之移动,她的左右肩也呈现出阶梯的曲折,好像在用力帮助机翼维持平衡。
饱经风霜的六十八岁老人,倒像六七岁不谙世事的小女童,要“出去”的时候极其依心火。她有两张轮椅,笨重而宽松的只在家里使用,若外出便暂时移交托付给轻简可折叠的,进出电梯很方便,之后也能收纳进车后备厢。由于在外面的时间长短不定,老鲁会哄着陶菊英先上厕所,之后给她换好纸尿裤。车后座也嵌着“儿童座椅”,卡带会将陶菊英的身体牢牢固定住。虽然坐进去稍微费劲一些,但出于安全考虑很有必要。好在老鲁已经熟悉上手,不会让陶菊英撞着头,也不会别了腿,或者磕碰到腰和肩。
起初,老鲁希望陶菊英坐在副驾位,这样眼里便能时时照顾到她,右手也可以及时触抚。但空间实在太过拥挤,夫妻俩都坐在前面,竟然让车子显露出头重脚轻的疲态,经过缓震带时,老鲁更是担心车子会在马路上翻跟头。陶菊英独自坐在后面,老鲁也不放心,总要用一只眼留意着,因此车速过于缓慢,像是老夫老妻牵着手在马路上一前一后地走,举步维艰。另一个原因,陶菊英也喜欢隔着车窗瞧外面的热闹,太快了不容易看清楚。老鲁巴不得陶菊英看见什么就说出来,医院、学校、派出所、邮局、饭店、商场、电影院,哪怕不知所云。但更多时候陶菊英只是望痴了眼,缄默不语,任道旁景物徐徐划过,双眼如两口枯井,溅不起一点语言的声响。对于陶菊英,世界且新且旧,老鲁往往因此悲欣交集。
有一次,陶菊英竟然想起了潮白河。他们此前周末常去潮白河岸边的林子里度假。于是乎,潮白河在老鲁心中泛滥,河身肥大,水质洁净,云的投影宛若白鹅浮动。老鲁为此不惜把车开往北京周边郊区的各个地方,以期唤醒陶菊英的任何相关记忆。虽然路程遥远,有时陶菊英还不免遗屎遗尿在身上,但很值得。
北京太大,一个人活着太小,经历有限,记忆更是不断缩减。像陶菊英,有朝一日怕是连老鲁都记不起来。像老鲁,如果陶菊英忘了他,即使他时刻寸步不离地守护在陶菊英身边,自身记忆清晰得如同南墙,不停地供他撞身取暖,哪怕撞得鼻青眼肿,他便也成了陶菊英眼里一堵会走动的陌生的墙。陶菊英时不时会问道于墙:“你是谁?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或者:“我是谁?为什么你会在这里?”答案老鲁都知道,但于他是答案,在陶菊英那里就不是,可能连问题都算不上,因为她转瞬即忘,再难想起。好像所有将两个人箍在一起的关系词语,都松动脱落了,不产生作用,也毫无意义,甚至唤醒不了任何回忆。作用、意义和回忆倒是在老鲁这副躯体里越塞越满,陶菊英脑子里却空空如也,像她的一世人生。老鲁和陶菊英的关系,再也不是手伸手便能互相揽着的,更像一个孩子放一只线人风筝,陶菊英是那个孩子;或者是一只湿漉漉的线人风筝在放一个干净得出奇的孩子,老鲁是那只线人风筝;中间那根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断了。
这个身形臃肿总是显得好奇并且不时流露疲态的孩子,会突然想起“家”,于是说“家啊”,老鲁便开车返回。家在老鲁那里,自然是清晰的、固定的、明确的,哪个街道,什么小区,几幢几层几号,须臾不敢忘,连同陶菊英的那一份记忆也刻进脑子里。他负责手牵着手带她回去。陶菊英已经不能独自坐电梯,甚至忘了走路这回事。这些可怕的变故在老鲁眼前霎然生成,但也可能经过了缓慢积累,由量变到质变,只是他看不见细微的变化而已。陶菊英肯定通过孩子似的行为提醒过他,诸如拽着他的手或衣襟不放,不肯向前移动脚步,眼前认不出一张人脸,脑子里想不出一个简单的汉字。这是她的惊惧,源于嗅到了某种灾难散发出的可怕气味,在危险发生之前已经将她团团死命缠绕住。他却没有理会到,于是在他面前她就只保持了孩子的简单特性,连多余的表情都不给他。她像透明茧中的一颗蛹,无须意识丰满也能活下去,身体却不断干瘪迟钝。
谁能在另一个空间里加以阻止呢?老鲁因此经常琢磨时间。时间仿佛茧的厚度,是从蛹中不断抽离出来的丝,也等同于蛹体僵硬的过程。时间就是陶菊英坐在一个地方,不管是房间里还是车子里,看到的所有空与不空,以及所有动与不动。时间对老鲁来说就是不断延展的路面,为了开好车,他必须保持专注,而她不需要。她已经疏于感受,越来越无动于衷。当他担心陶菊英并通过后视镜察看时,时间总是瞅准时机汹涌地流过,她毫无抵抗地被裹挟而去,而他就像置身于洪水中毫发无损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打湿的人。这令他沮丧,气急败坏。
他一再尝试着要她“听我说”,虽然明知道在陶菊英那里“我”早就支离破碎,“你”也已经不复存在。固定“你和我”的卯榫已经断裂,之间的距离恣意汪洋,犹如银河,盈盈一握间,脉脉不得语。确实如此,夫妻之间再无对话,经常是各说各话。自说自话也是好的,不然房子和车子都会显得很空。人是房子的胆。只要不住人,房子会很快衰败。语言是人的胆。一旦语言不声不响地离开,人就会显得太孤零零,太无助,像一个被隔绝在广漠空间里的毫不起眼的个体,连遗弃也变得轻描淡写,如同光经过障碍物时留下的倏忽而去的影子。
如果陶菊英不再说话,不愿吐露一个字,无论是坐在家里的窗前,还是车里的专座上—他不敢设想这样的情景。到了那时,陶菊英鸿飞不计东西,彻底将他遗弃在此。他只能一个人守着所有的记忆艰苦度日,而他和她共有的记忆,折合成两个人共同度过的时间,也许连他一生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以五分之一对抗五分之四,他毫无胜算,因而更觉每过一天每延长一秒,都是煎熬,都没有意义。
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希望不是在家中,而是在车上。为这一天,他等了不知多少天。陶菊英说“出去”,他便抱起她上厕所,为她换上纸尿裤,让她在可折叠的轮椅上坐好。拿起行李包,锁上门,推着陶菊英下电梯,打开车门,让陶菊英在车里坐好,收起折叠椅,放进后备厢,然后发动车子,坦然上路。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出去”,出去便不回来。因为在路上,当陶菊英再次感到困倦时,她会忘了说“家啊”。她忘了家,他便也没有了家,无法也不愿一个人回去。这是人间最大的恨事,有情未必白首,同去常不同归。即使在路上,即使开着车,只有他们始终在一起,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所有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他们所有的驾轻就熟,俱是为了不再返回。
对于老鲁来说,他已经想明白,也为不断争取到的延缓执行而暗自庆幸。他爱着坍缩在时光里的老妻。虽然这份爱除了守护别无良方。而她忘了她对他的爱。忘了而已,不代表不爱。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果她忘记一切,他便和这一切一起沉没。这是他对她的爱。他想不到其他的表达。他也找不到更多的表达。
《路口》(节选)
现在,是时候和汤警官坐下来聊聊了,对此他们都有些迫不及待。
他们约在天桥上会合,放眼望去,推土机和铲车已经开始进场作业,噪音在他们耳旁轰响,巨大的机械臂在半空中挥舞。按照这样的进度,不出一个星期,他们面前就会是一片废墟,残垣断瓦里面,还有什么遗迹可寻,还有什么秘密能被继续掩藏?再过一两个月,他们脚下所站的天桥也会消失不见,据说取代这座年代久远天桥的会是一座彩虹桥。什么是彩虹桥?是像彩虹一样的桥,还是能通过汽车的那种巨大的立交桥?
汤警官已经知道了陈卫国的死讯,但陈卫国显然不是他们的聊天重点,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即使他偶尔出现在话题范围内,也会像横生的枝节,被他们及时剪掉。汤警官主要跟陈学勤说了两个案件。对这两个案件他浸淫多年,魂牵梦萦,可以说如数家珍。一个就是应城人都一清二楚的应城村镇储蓄所恶性杀人案,由于一直没有找到重大嫌疑人夏青川,始终无法结案,时不时就会被公安局领导或好事群众拎出来。还有一个是枪支失窃案,案发地点依然是应城村镇储蓄所。考虑到枪支失窃会引起社会恐慌,这个案子就没有对外扩散,只是在内部做了处理,一个是把储蓄所所长降职调任,一个是加强储蓄所的安保力量,增派了人手。夏青川就是那个时候调到储蓄所,担任保安处副处长的。
杀人案陈学勤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么多年来,每次陪晓慧站在天桥上,那个画面都会不由自主地映现在陈学勤的脑中。夏青川掏出手枪,把两个保安杀了,然后远走高飞。没人知道夏青川为什么要杀两个保安,这也是汤警官苦苦想要弄明白的作案动机。如果夏青川就是凶手,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两个保安死了,储蓄所里那笔巨款却分毫未动,那就不是为财。不是为财又是为了什么?夏青川和这两个保安平时并没有过节,不要说这两个保安,他跟储蓄所里的所有同事都没有红过脸,但偏偏就是这么一个人,却动机不明地杀了两个人,然后失踪了。这不合理,也不应该。但夏青川又必然是第一嫌疑人,案发时只有他在现场,和两个保安一起值夜班。两个保安死了,夏青川失踪了,第一嫌疑人只能落在他的头上。只有排除了他的嫌疑,才能围绕储蓄所做第二轮排查,看看有没有新的嫌疑人,比如说,陈学勤的父亲陈卫国。
汤警官试探着说出陈卫国名字的时候,陈学勤没有吃惊。事实上,陈学勤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父亲,如果夏青川不是杀人凶手,那杀人凶手就有可能是其他所有人,自然也有可能是陈卫国,可是陈学勤想不透自己父亲的作案动机。如果是夏青川和陈卫国联手作案的呢?这个也解释不通。另外,如果夏青川不是杀人凶手,凶手另有其人,那么夏青川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他会遭遇什么不测?具体下落会在哪里?像现在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所有的揣测就只能是揣测,夏青川重大嫌疑人的身份就永远无法洗脱。
汤警官告诉陈学勤,杀人案的关键在枪。凶手的枪从哪里来?通过子弹的对比,当时就已经确定凶手使用的杀人凶器和储蓄所保险柜里的枪支子弹完全一致。只不过,枪支失窃案偏偏发生在杀人案的三年前。三年前,作为杀人案重大嫌疑人的夏青川,他的生活轨迹和应城村镇储蓄所毫无交集,更不用说他竟然清楚保险柜里有枪,还能悄悄地潜进来把枪盗走,然后再瞅准机会想方设法调到应城村镇储蓄所,等了快三年时间,处心积虑,只为在一个夜晚把两个保安杀了,最后逃之夭夭。换句话说,如果夏青川不是窃枪的人,他就不可能是应城村镇储蓄所杀人案的真凶。谁偷了枪,谁就杀了人。这样的证据链才是闭环,才能最后指认出真正的凶手。可是,夏青川找不着,枪也找不着,案件最大的缺口就在这里,缺口填不上,真相很难浮出水面。只要能找到夏青川,就能够马上证明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如果不是,就可以重新立案展开侦查,相信很快能够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应城村镇储蓄所的保险柜里有手枪,这陈学勤是知道的。小时候,陈学勤甚至围着那个黑色的保险箱转过无数的圈圈,希望能透视进去,看看手枪到底长什么样,或者闻到手枪的气味,那种铁锈味,那种火药味。不过,手枪被偷的事情,陈学勤却毫不知情。当时陈学勤围着转的,说不定就是一个空的保险箱。手枪早已经不翼而飞。储蓄所里的人也许会在背后笑话陈学勤,不过他们可能也是不知情者。手枪被窃,这是天大的事情,没有手枪震慑敌胆,坏人就会闻讯而来,打储蓄所的主意。陈学勤仿佛看到坏人们趁着夜色包围了储蓄所,双方展开激战,最后夏青川掏出手枪,砰砰两枪,把企图闯进储蓄所的两个歹徒当场击毙,余下的歹徒抱头鼠窜。剧情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夏青川不是杀人犯和在逃犯,他是战斗英雄,他也没有枪杀自己的两个同事,他一直在和战友们并肩御敌。
杀人案发生后,汤警官调阅了应城村镇储蓄所近年来的所有人事档案和记录。正是他第一时间大胆提出了枪支失窃案和杀人案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可惜的是,由于当年处理枪支失窃案的指导原则是防止消息扩散,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只是在内部悄悄做了问询,没有展开彻底排查,匆匆了事,错过了最佳破案时机。窃枪者肯定了解储蓄所的值班和防范情况,才有机可乘,轻易得手,很有可能是银行系统的人,甚至就是应城村镇储蓄所内部的员工,当年的员工都应该做重点调查。
既然有人窃枪,就会有动机,总不能说动机是为了在三年后开枪杀人。如果这样假设,夏青川基本可以排除出嫌疑人队列。可是,刑侦永远不能停留在假设上,除非能确定夏青川不是凶手,否则失踪的他注定永远是第一嫌疑人。案情太棘手了,既不能定案,也不能帮嫌疑人洗脱罪名,就只能悬置着,成为悬案。
枪支失窃后,当年的储蓄所领导受到降职处分,被调到另外一个储蓄所做主任。陈卫国当时就是保安处处长,按理说也难逃失职之责,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至少在陈学勤的印象里,他既没有跟家里面说过枪支失窃这样的大案(出于保密原则),也没有透露过他受到什么处分(碍于面子问题)。一个应城村镇储蓄所的保安处处长,升职基本无望,降职的话要么成为普通保安,要么彻底失去这份工作,两者陈卫国都没有遇上,他一直好好地做着他的保安处处长,枪支失窃前是处长,杀人案后也是处长,储蓄所在长金街时是处长,搬迁后依然是处长,好像做这个处长做习惯了,也做麻木了。
汤警官认为陈卫国言行太谨慎了,不像是退伍军人,倒像是读过公安学校的毕业生,那么笃定,那么有条不紊。陈学勤小时候不也是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是便衣警察嘛。因为陈卫国的表现,汤警官不是没有怀疑过他。可是,陈卫国按部就班,尽忠职守,自始至终没有流露出任何破绽。
枪支失窃之前,在一次部门例会上,陈卫国就专门提出了处理枪支的建议。陈卫国提出,储蓄所里存放枪支其实存有一定的隐患,理由如下:第一,枪支存在失窃风险,流落到社会上那就是大问题;第二,储蓄所现有安保人员,对付小贼已经绰绰有余,枪支其实就是一个摆设,用上的可能性不大;第三,虽然有枪可以壮胆,但除了陈卫国自己,四个保安没有一个拿过枪的,不会使用,真的遇到紧急情况也是白瞎。有鉴于此,陈卫国建议把枪支交到上面去。可惜,储蓄所领导没有接纳,他坚持认为有枪在所里,心里更踏实。也许他是管钱的,不是管枪的,下意识里还是觉得,钱被抢了是他的责任,枪要是不见了和他关系不大。就这么一个小疏忽,没想到接连引出了后面两桩大纰漏,不仅失枪,还正是从这把丢失的枪里射出的子弹,杀死了两个人。陈卫国不是事后诸葛亮,但是他预估到了风险,并在例会上郑重提出建议。这是有记录在案的。因此,枪支失窃之后,陈卫国第一个洗脱嫌疑。储蓄所的领导受到处分,大家也一致觉得是活该,谁让他不听陈卫国的建议呢,一意孤行,刚愎自用,难免要受现世报。
杀人案之前,陈卫国也在安保会议上着重强调安防措施必须要做到位,一不能留死点盲点,二不能存侥幸心理。当时储蓄所里已经布控了摄像头,全所内外联网,时刻在线监控。但就是在案发之前,监控出现了故障,交由夏青川负责修理。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疏忽,导致案发现场竟然没有留下一点画面。由于当天晚上有大宗钱款在储蓄所过夜,夏青川负责带领两个保安值班,下班前,陈卫国还特意当众随口问夏青川,任务重大,不容有失,需不需要多一个人留下来一起值班。夏青川一口回绝,觉得陈卫国有点儿小题大做。陈卫国还是不放心,跟他们说,他就在浴室过夜,有事情也能立刻赶过来。种种迹象表明,夏青川不仅支开了陈卫国,还有意拖延修复监控设备,已经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如果夏青川不是凶手,还有谁会是凶手呢?如果夏青川不是凶手,凶手另有其人,那这个人心思之缜密,也许真的到了百密无疏的地步,步步为营,精打细算,才能够巧妙设局,置身事外,逃出生天。话说回来,他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窃枪在前,杀人在后,这两个案件的动机是一脉相承,还是各自有因呢?
汤警官苦于找不到实证,二十多年来始终无法勘破这个谜题。他断定夏青川和陈卫国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两个人,可是夏青川生死未卜,已经失踪不见,而陈卫国也已躺在病床多年,刚刚撒手人寰,又怎么能够撬开这两个不存在的人的嘴巴呢?连那当年的血案现场,也早已另作别用,此刻更是一片废墟,难道还能指望那里会有什么新发现吗?
一个多年失踪者,一个重度昏迷者,一个念念不忘束手无策的退休老警察,一对饱受困扰发誓要找出真相的儿女,一块彻底推倒重建的“Y”形废墟,两个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重大案件,四个受牵连的不幸家庭,一个早已经置身事外的单位,命运的车轮究竟会怎样无情碾压所有人?
施害人也许比受害人更受良心的谴责和折磨。在汤警官看来,这个世界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人,犯罪的人和无辜的人,说极端点,就是杀过人的人和没有杀过人的人,再细分下来,就是用枪杀过人的人和被枪杀的人。杀过人的人,是人又不是人,从法律层面上说,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从人性层面上说,又希望他迷途知返,洗心革面,改过自新。否则,犯罪和杀戮就只是简单的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重复。罪行的唯一意义就在于,让罪人忏悔,以儆效尤,并最终获得谅解,作为人类正在试图走出无边愚昧和黑暗的证明。
每个城市都会有“Y”字形路,像两条温柔的手臂,轻抚着这一区域的人们安然入睡;也像两条勒得越来越紧的臂膀,让人透不过气来;更像一把弹弓,弹丸已经射出,下落不明。正如随便从一个地方挖下去,就会挖到坟墓、尸骸、煤炭、岩石,陈学勤坚信每个人立足之处,其下都是森森白骨,不然怎么解释,地球存在几十亿年来,其上生活过的所有生命体都去哪里了呢?但陈学勤从来没有想过,在应城村镇储蓄所那个狭小不透气的地下室的土层里,竟然也挖出了一具尸骸,以及一把手枪。手枪被一块布包着,布早已经腐烂,手枪跌落在尸骸的腹腔部位,枪管朝上,好像正在瞄准射击。
这正是失踪了二十多年的夏青川,他通过这个方式重回人们的视线,被人们到处讨论,一举洗脱已经背负了二十多年的嫌疑。很显然,他不可能在枪杀了两个同事之后,再把自己埋进地下室深深的土层里,连同那把手枪。傻子都能明白,凶手另有其人,他杀了三个人,把其中一个人埋到地底下,为的是嫁祸给这个人并造成这个人逃亡的假象。
凶手会是陈卫国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