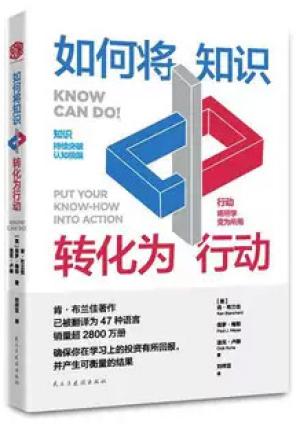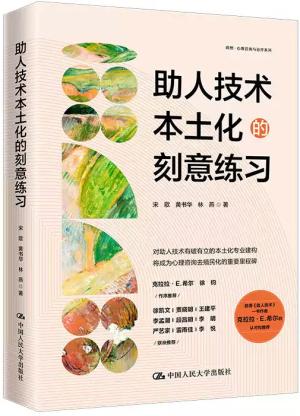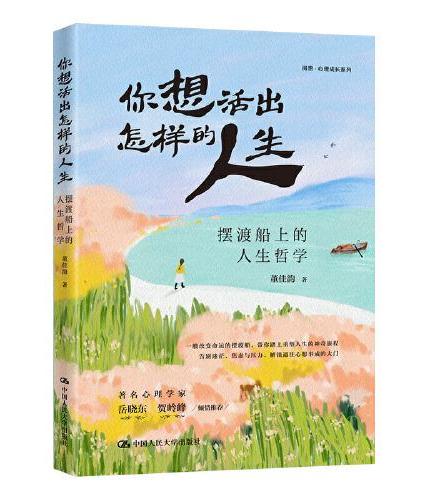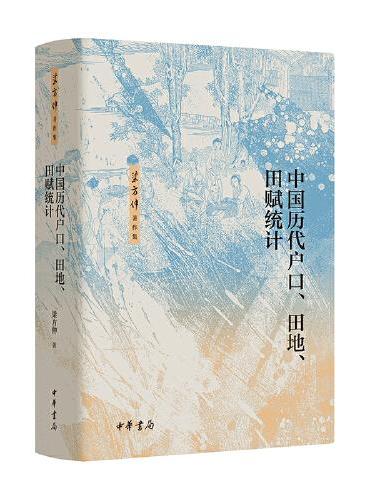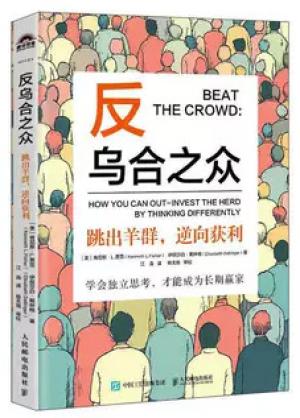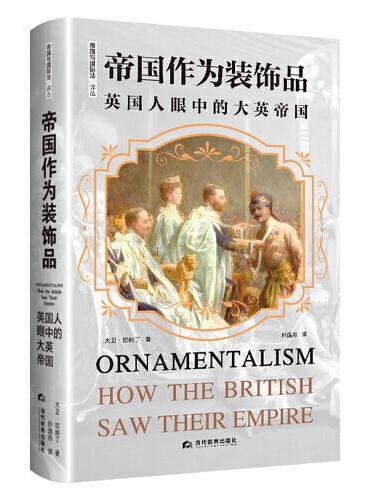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NT$
95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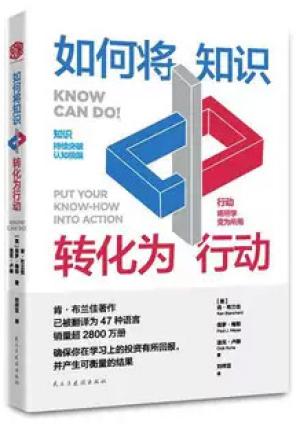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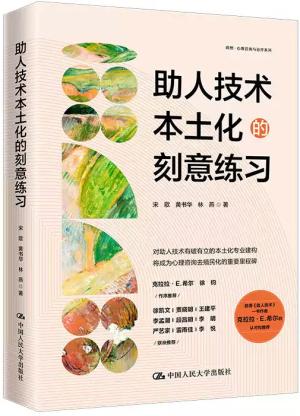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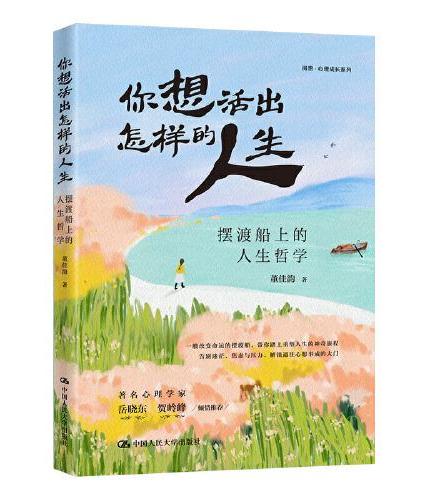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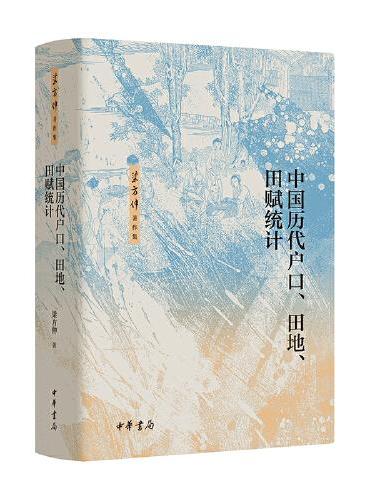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68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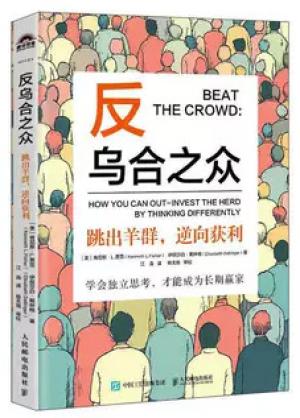
《
反乌合之众——跳出羊群,逆向获利
》
售價:NT$
3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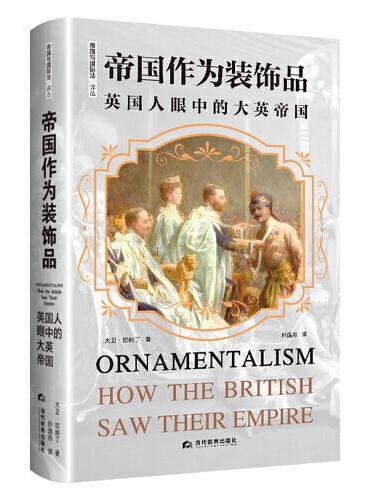
《
帝国作为装饰品:英国人眼中的大英帝国(帝国与国际法译丛)
》
售價:NT$
403.0
|
| 編輯推薦: |
评论家一致盛赞,同时又普遍认为,本书太过黑暗,无法流行!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约瑟夫·海勒,不要从这本书开始!
先读读《第二十二条军规》或《完美如金》,然后深吸一口气,再准备好一头栽进《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
1. 库尔特·冯内古特称其为“世界上蕞不开心的书之一”。
辛辣吐槽,道出生活的真相;
戳心金句,令人捧腹又不免唏嘘;
坦诚剖白,描摹中年男人生活中的苦闷与懊恼。
十足的荒诞不经,辛辣的黑色幽默,无情的精神分析——阅读本书将带给你兴奋十足的自虐式快感。
2. 平日的地狱,刻画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细微恐怖。
鲍勃不开心,工作把他掏空,让他筋疲力尽,使他与世隔绝。在无可逃避的办公室政治之下,是蔓延终日的忧郁,还有来自同事和上级的恶意与琐碎羞辱。如果鲍勃的办公室里存在某种文化现象,那一定是恐惧:恐惧其他同事,恐惧被解雇,同时又恐惧再也无法脱身。
鲍勃不开心,家庭生活仿佛一座囹圄,更令他窒息的是,一切好像都几近完美,无可怨诉——位于郊区的独栋大屋、安定无忧的生活、优雅动人的妻子、三个成长中的孩子,一切都备受艳羡。可是,鲍勃就是不开心。
|
| 內容簡介: |
鲍勃?斯洛克姆的生活是美国梦的典范。他是一家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一个中产之家中的丈夫与三个孩子的父亲,过着富足的生活,还有源源不断的情人。他的生活安定而有序,他循规蹈矩,社会也要求他感到幸福——或者至少假装自己很幸福。
但是,这种伪装变得越来越艰难。斯洛克姆的内心充满了不愉快,这种不愉快逐渐恶化为凄凉和恐惧,直到有一天,出事了。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约瑟夫?海勒(1923—1999),美国小说家,黑色幽默文学蕞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以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闻名于世。
1923年,海勒出生于纽约一个贫困的俄罗斯犹太人家庭,他从小颇具语言天赋,爱好写作。从亚伯拉罕?林肯高中毕业后的一年中,做过铁匠学徒、信童与文员。
这位声称“通过深入彻底的自我审视,我发现自己不适合军队”的作家于1942年参军,加入美国空军前往意大利前线,驾驶B-25轰炸机完成了60次飞行作战任务。
战后,海勒先后在南加州大学和纽约大学研习语言,后又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
1961年,《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起初市场反应平平,后随着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兴起获得民众的强烈共鸣,迅速成为畅销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从未获得过任何奖项,却成为世界上蕞畅销的小说之一。除此之外,海勒的黑色幽默代表作还有《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1974)、《完美如金》(1979)、《天知道》(1984)、《最后时光》(1994)等。
1977年,海勒当选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他晚年饱受病痛折磨,于1999年因心脏病发作在家中去世。
【译者简介】
靖振忠,资深译者。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硕士。现居加拿大。译有《零K》《索拉里斯星》《一个中年男子的苦闷》《完美如金》等。
|
| 目錄:
|
一 我心里发毛
二 我上班的地方
三 我妻子不开心
四 我女儿不开心
五 我儿子遇到了一些困难
六 事实并非如此
七 这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八 我儿子不跟我讲话了
九 没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
|
| 內容試閱:
|
一 我心里发毛
每当我看到关着的门,我心里就发毛。就连在我上班的地方也是如此。尽管如今我在公司里干得很不错,可有的时候,只要我看到一扇关着的门,我就会感到害怕,觉得门背后正发生着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给我带来不利影响。每当我前一天晚上整夜都在撒谎、酗酒或是玩女人,或者仅仅是因为神经紧张而彻夜难眠,因而在第二天感到疲倦沮丧时,我便几乎可以闻到灾难在无形中蔓延,透过门上的磨砂玻璃向我涌来。我可能会手心冒汗,嗓音也变得怪怪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定是因为在我身上曾经出过什么事。
也许是那天我因为发烧嗓子疼意外提早回家,结果碰见我父母正在床上做爱,于是给我留下了对门的恐惧心理,害怕开门,对关着的门心存疑虑。或者也许是我在童年晚期发现自己家境贫穷,于是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或者也许是我父亲去世的那天,他的死给我心里留下了内疚和羞愧—因为当时我以为自己是整个世界上唯一没有爸爸的小男孩。或者也许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我将永远都不会长得肩膀宽宽,二头肌发达,永远都不够出色、不够高大、不够强壮、不够勇敢,因此无法成为一名全美明星橄榄球运动员或职业拳击冠军。我很早就认识到,不管我这辈子尝试着做什么,我身边总会有人能够比我做得更好,这令我感到悲伤沮丧。或者也许是那天我伸手打开了另一扇门,结果看见我姐姐赤身裸体,站在浴室的白瓷砖地板上擦干身子。尽管她明知自己没锁门,我是在无意中撞见了她,她还是冲我大喊大叫。我当时被吓坏了。
我还记得另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很有趣,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随意走进了我们家住的红砖公寓楼后面装煤用的旧木棚,结果发现我哥哥和比利?福斯特的妹妹一起躺在地板上。比利的妹妹瘦瘦的,年纪不过和我一般大,在学校里还和我同班。我在垃圾桶旁边捡到了一辆破烂的婴儿车,想到木棚里用锤子把它的轮子和轮轴敲下来,好用在一辆我打算用装甜瓜的板条箱和一块长木板做成的小车上。我刚走进这个黑洞洞的地方,便听到一阵微弱而狂乱的骚动,并感觉好像踩到了什么活的东西身上。我吓了一跳,鼻子里闻到了一股尘土的味道。接着,我看到原来是我哥哥,和一个人一起躺在棚子一角乌黑的阴影里。我松了一口气,露出了微笑。我又觉得安全了。我说:
“你好,埃迪。是你吗,埃迪?你在干什么,埃迪?”
他却大声喊道:
“给我滚出去,你这个狗娘养的!”然后把一块煤使劲冲我扔了过来。
我躲开了,轻声呻吟了一声,泪水涌上我的双眼,然后我便仓皇逃命。我跑到棚子外面热气腾腾、明亮刺眼的阳光里,无助地在家门前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心里很纳闷,不知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事,把我哥哥惹得这么生气,以至于他把我骂得那么难听,还拿那么大的一块煤砸我。我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应该逃走,还是应该待在这儿等着。我心里非常内疚,因此不愿逃走,同时我又非常害怕,几乎不敢留下来接受我应得的惩罚—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我无法下定决心,于是只好颤抖着在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来回晃悠,直到那间旧棚子的大木门终于咯吱一声朝着我打开,他们二人从那个大张着的黑口子中慢慢走了出来。我哥哥走在她身后,一副得意扬扬的表情。他看见我时冲我笑了笑,这让我心里感觉好受了一些。看到他的笑容之后,我才注意到走在他前面的女孩是比利?福斯特又高又瘦的小妹妹。她在学校里字写得不错,但是在拼写、地理和算术考试中从来都上不了七十分,尽管她总是在想方设法作弊。看到他们俩在一起我很惊讶,我压根就没想到我哥哥会认识她。她低头走着,假装没看见我。他们慢慢向我走近。这一切花了很长时间。她在生气,一言不发。我也没有作声。我哥哥在她身后冲着我眨眼示意,并夸张地提了提裤腰。他走路的姿势大摇大摆,一副我从来没见过的样子,我马上就知道自己对此有反感。看到他和平时判若两人,我觉得很不自在。但我对他的眨眼示意感激不已,我觉得既高兴又兴奋,浑身开始扭动,并冲着他咯咯直笑,几乎无法控制。我一下子如释重负,有些忘乎所以,嘴里开始讲个不停。我说道:
“嘿,埃迪。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埃迪?出什么事了吗?”
他笑着答道:“噢,是的,的确出了点事。是不是出了点事啊,杰拉尔丁?”他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开玩笑地用胳膊肘轻轻捅了一下她的胳膊。
杰拉尔丁从他身边走开,脸上闪过一丝恼怒的微笑。她头也没抬,就把我们俩甩在了身后。等她走了之后,我哥哥说:
“别告诉妈妈。”
他知道,只要他叫我别告诉妈妈,我就不会告诉她。
事后,我开始想象并沉湎于那天在煤棚地板上可能的确44发生了的许多湿乎乎、硬扎扎、热烈而又亲密的事情(每当我回首往事,我仍会幻想并沉湎于这一幕,而如今我越来越经常回首往事)。一想到我哥哥和比利?福斯特干瘦的小妹妹发生了性关系,我就感到惊讶不已,几乎令我大声惊叹。她甚至比我还要小几个月,长着大板牙,而且一点也不漂亮。
关于他们俩在那间棚子地板上所做的事情,我当时还有很多细节想要了解,但我胆子太小,一直都不敢问,尽管我哥哥在世时一直都对我很好,而且平时一向性情温和,乐于助人。
如今,有好多事情我都不想44去了解。比如说,在我十几岁的女儿参加的聚会上,他们玩的是什么样的游戏,抽的是什么样的烟,吸的或吞的是什么颜色的药片或胶囊,这些事情我真的宁愿不知道(尽管我和我妻子觉得有义务打探)。每当警车蜂拥出现,我不想知道是为了什么,尽管我很高兴他们能赶到,并希望他们来得及时,能够完成他们被叫来完成的任务。如果有救护车开来,我也宁愿不知道他们来抢救的是谁。当有孩子因溺水或窒息而死,或是被汽车或火车撞死的时候,我也不想知道这些孩子是谁,因为我总是害怕发现他们原来是我的孩子。
我对医院怀有类似的反感,而且对生了病的熟人也有着同样的顾虑和厌恶。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我绝不会去医院探望病人,因为在那里总会有这种风险,我可能会打开某间私人病房或半私人病房的门,看到某些我事先毫无精神准备的可怕景象。(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第一次在病房里看到一根橡皮管从仍沾着血的鼻孔伸入人体内时所感受到的那种震惊。那根管子是棕黄色,半透明。)现在,当朋友、亲戚和生意上的熟人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我从不打电话到医院或病房去了解他们的病情,因为总有这种危险,那就是我可能会发现他们已经死了。我会尽量避免与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谈话,除非我首先跟某个已经44和他们谈过话的人进行了核实,而且此人能够向我保证情况没有恶化。这有时会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包括我和我妻子之间的关系,因为她总是见人就问他们怎么样,而且还总是带着礼物跑到医院去探望住院的人),但我不在乎。我只是不想和那些家里有丈夫、父亲、妻子、母亲或孩子可能正在垂死的人谈话,即使我对那个垂死的人本人有着很深的情感。我从来都不想发现哪个我认识的人去世了。
不过有一次(哈哈),一个我认识的人真的死了,于是我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假装不知道,当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他的病情。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听到医院通知我某个熟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想知道他们会怎么说,这个技术性问题占据了我的全部注意力,甚至让我感到有些兴奋。他们是会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去世了,病逝了,亡故了,还是甚至会说他断气了?(就像杂志订阅或旧借书卡期满失效一样?)医院接电话的女人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她说:
“______先生已不在病人名单之上。”
打这个电话需要不小的勇气,实际上,它把我所有的444勇气都用完了。挂断电话时,我就像一片树叶一样浑身抖个不停。毫无疑问,我的心在咚咚直跳,为我的侥幸脱险而充满快乐,兴奋不已。因为从我张口发出的第一个音节,从我伸手拨打的第一个号码开始,我就一直想象着医院接电话的那个女人对我的意图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想象她能通过电话线将我一眼看透,看穿我的心思—并且会揭穿我的把戏。但她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按规定作答,让我安然逃脱。(这难道是事先录好的通知吗?)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们那种委婉的处理方式:
“______先生已不在病人名单之上。”
______先生已经死了。他已不在活人之列。______先生已不在病人名单之上,而三天后我不得不去参加他的葬礼。
我讨厌葬礼—我对葬礼深恶痛绝,因为葬礼总是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而且我尽量避免参加任何葬礼(尤其是我自己的葬礼,哈哈)。在我必须参加的葬礼上,我尽量不跟任何人说话,而只是把双手合在一起,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我会偶尔咕哝一两句没人听得清的话语,而且总是目光低垂,就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人们的做法。我信不过我自己,不敢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有人去世时应该说些什么话才算得体,所以我总是担心自己一张口就会说错话。在任何我无法控制或预测其结果的紧张情况下,我真的再也信不过我自己了。甚至就连换保险丝或换电灯泡这种事我都不喜欢。
不知在什么地方,在我身上的确曾经出过什么事,使我丧失了信心和勇气,让我对发现和变化感到害怕,并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未知事物产生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恐惧心理。我不喜欢任何意外的事情。如果有人在我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稍稍重新布置了一下屋里的家具(即使是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就会觉得像是脸上挨了一拳,或是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我不喜欢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不管是哪种意外,都会令我恼火,使我不快。就连那些为了给我带来快乐而安排的惊喜也总是以一种悲伤和自怜的回味而告终,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计划反对我,利用我来让他人开心,就像是有人向我隐瞒了一个秘密,成功地策划了一个阴谋,而我却被排除在外。(我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我讨厌冲突(不管是跟什么人,我自己的家庭成员除外)。有许多日常生活中的小冲突,如今我只有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屈辱才能应付过去。比如和修理工意见不合,此人不是试图偷工减料,就是想多骗我一点钱;或者是向电话公司业务部的人投诉,这些人面无表情,善于逃避责任。(我宁愿自己受骗。)或者是那次我们家公寓里进了老鼠,那还是在我当上公司里的一名小主管,并开始挣够钱搬进城外康涅狄格州我自己的房子之前(我不喜欢这栋房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些老鼠。我一直都没看见过它们。只有清洁女工看见过,或者是她说自己看见过。有一次我妻子以为她看见了,还有一次我妻子的母亲几乎肯定自己看见了。过了一阵,那些老鼠就销声匿迹。它们不见了,再也没有出来过。我甚至没法肯定它们真的曾经存在过。我们不再谈论它们,它们似乎不见了,就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它们是些小老鼠(据所有可靠的描述所言),一定是从暖气金属网罩上的小方孔里钻进来的。我对老鼠并不太在意,只要我不必看到或听到它们就行,不过我经常会发现自己在侧耳倾听,看看有没有它们的动静,并且偶尔觉得的确听到了它们的声音。但是它们令我妻子毛骨悚然,使她整天惊恐不安。她想让我想办法对付它们。
因此每天晚上我都得到处安放老鼠夹。每天早晨,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藏在我背后,惊恐地观望着,而我则不得不打开每一个壁橱和橱柜,向每一张沙发、每张床和每把墙角扶手椅后面窥视,看看有什么新鲜而可憎的意外之物在那儿等着我,帮助我开始这新的一天。甚至就连没有意外也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意外。我的家人全都站在我身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我,面容严肃,充满焦虑,这让我感到很不安,因为我的两个孩子本来就很容易紧张,没有安全感,他们已经够害怕的了。我的另一个儿子脑子有缺陷,什么事也不懂。而且即使是在当时,我也不能完全肯定自己对这群家人足够喜欢,以至于希望他们在一个如此紧张而私密的情况下紧紧地簇拥在我的周围。
每当我打开一扇扇柜门,检查我设下的老鼠夹,或是向家具、炉子或冰箱后面张望时,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我担心自己会把老鼠捉住,发现它们已经死在了老鼠夹里,从而不得不把它们处理掉。我又害怕自己捉不到老鼠,从而不得不重复这种令人厌恶的程序,每天晚上设置老鼠夹,每天早晨检查老鼠夹,日复一日,天知道要这样持续多久。然而最让我担心的是,我会打开厨房里的一扇柜门,发现一只活老鼠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它犹豫片刻,只够让我能看到它,接着它便会蹦出来,一下子从我身边蹿过去。我冒着汗的手里总是攥着一本厚厚的杂志,卷起来当作武器,而那只老鼠蹿过时正好就在那本杂志下面。哦,上帝啊,如果哪天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如果哪天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知道我必须强迫自己用尽全力去打它。我知道我必须强迫自己竭尽全力朝它打下去,试图以一记重击将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打死,而且我知道我一定会失败,结果只是把它打了个残废。然后,当它躺在我面前,它的腿已被彻底打断,但它还在挣扎时,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但我知道我将不得不举起那本沉重的杂志,再打它一下,然后再一下,也许接下来还得再打一下,直到把它完全打死。
在我每天早上打开的每一扇门后面,都有可能发现一只活老鼠,这一点让我感到十分恶心,使我浑身战栗。这并不是因为我害怕那只老鼠本身(我还没那么傻),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真的发现了一只老鼠,我将不得不想办法去对付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