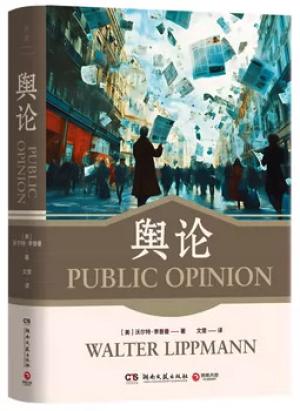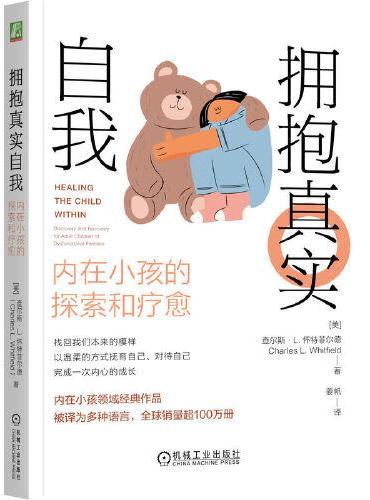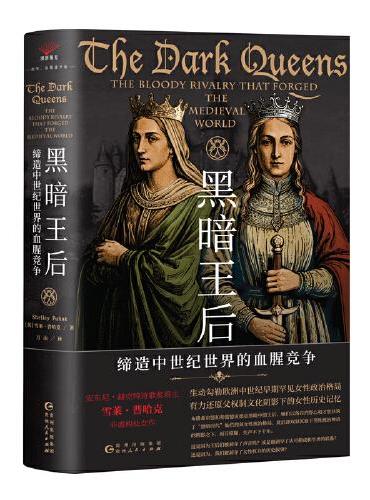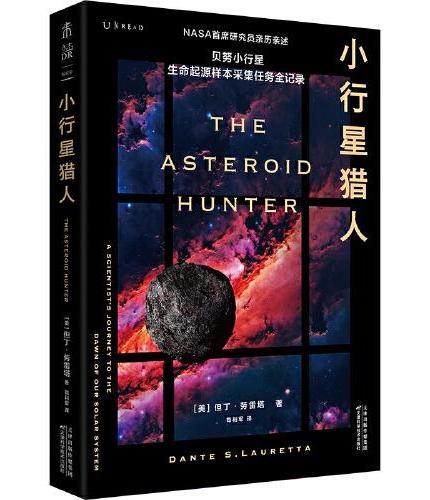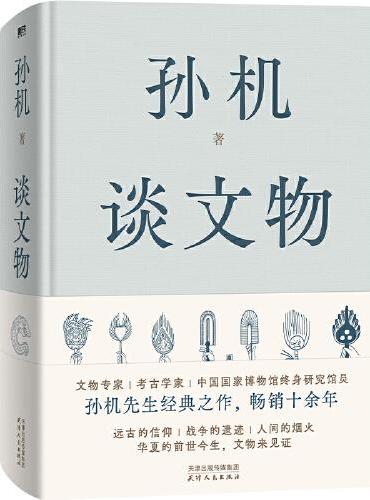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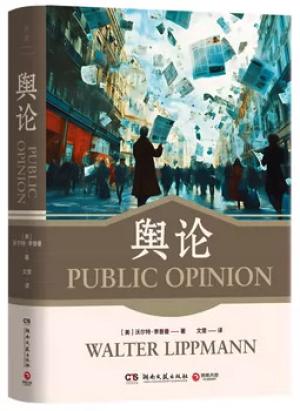
《
舆论(普利策奖得主、“现代新闻学之父”沃尔特·李普曼传播学经典)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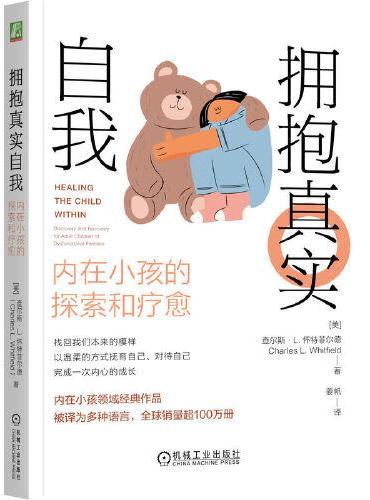
《
拥抱真实自我:内在小孩的探索和疗愈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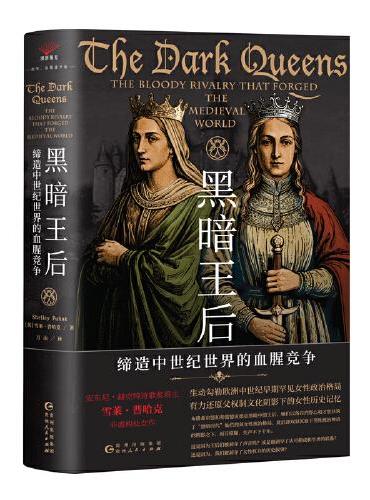
《
黑暗王后:缔造中世纪世界的血腥竞争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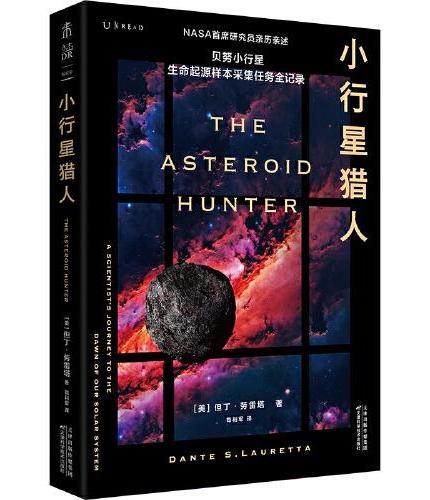
《
小行星猎人:贝努小行星生命起源样本采集任务全记录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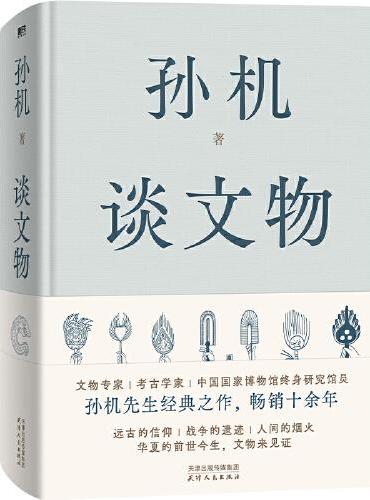
《
孙机谈文物
》
售價:NT$
551.0

《
诡舍(夜来风雨声悬疑幻想震撼之作)
》
售價:NT$
254.0

《
讲给青少年的人工智能
》
售價:NT$
245.0

《
海外中国研究·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经典收藏版)--重构宋代文人的精神内核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每一朵花开,都充满喜悦与期待。 ——横行胭脂
有爱有光就有方向。 ——陈仓
文学是一场相识。 ——陈年喜
作者将想象融入真实生活,用诗意文字展示深沉现实。 ——导演王丽娜
《树伴》用一种非常珍贵的记录方式,给读者空间,在文字的也界里连接自己的情感。——导演郭柯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连李第三本小说集,收集了作者自2018年至2021年的十一个中短篇故事。少数故事有着悲喜剧的讽刺和乖张——在《车祸》中,男人在一场本不致命的车祸现场,亲自密谋了自己的死亡;在《面具》里戴着面具的人有很多,揭开面具的那一刻,时间回到了被遗忘的最深处。大部分故事则以魔幻现实的手法呈现,逃离、对自我的凝望、诡异的追踪,是全书的基调——在《夜更得以声》和《101次飞扬》中,那些敏感又迟钝的角色既存在,又不存在;《树伴》中,奶奶的心口上生出了一棵树;《春日夜行列车》搭载了一段没有发生过的相遇。
故事有时在城市,有时在小镇,有时在遥远的山村。有时它只是囿于当下,某条逼仄的马路上,一个不透光的家庭,甚至有时根本没有故事发生……但这些司空见惯中生出的是诡异,离奇和爱:
精神疗养院中的一次探望;
绝望的单身女人和一个陌生三岁男孩相处的一天;
一个孤寡老人刚刚从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昏迷中清醒过来;
……
然而,在这些虚构的世界里,即便最细微的事物,也拥有巨大的倒影。
|
| 關於作者: |
|
连李 著有长篇小说《陆树的五夜》《莲升的门》,戏剧作品《24点》《长椅》。
|
| 目錄:
|
目录
边月白 /01
等 等 /20
春日夜行列车 /44
夜更得以声 /69
树 伴 /98
车 祸 /118
101次飞扬 /138
花园派对 /148
鹿回头 /205
江上风清 /243
面 具 /286
|
| 內容試閱:
|
序
有关《形单影双》
一个孤独的个体能为我们呈现无数可能的影像和其所提供的时光,我们参与孤独,有时候也旁观孤独。
但这仅仅是开始。
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在我们赋予他人以及从后者那里所汲取的人生里,孤独似乎是永远的主题也正是如此,爱和陪伴才如此重要,它们使孤独充满能量。
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
我们总是被美好的事物击中,无论是《101次飞扬》的梦境,还是《花园派对》的归隐式人生,抑或是《树伴》所提供的某种恒在,《春日夜行列车》的隐喻当美好成为一种时间策略,孤独便被巧妙地取代了。我们轻易洞察到的意志,在“时间”的最后都变成了谎言。
但这仅仅是真正的开始。
《形单影双》不旨在刻画孤独本身,甚至故事中的人也不在刻画范围之内。它只是试图利用故事所塑造的时空,围绕自我开展一场不屈不挠的跟踪,就像人物的影子对他们所展开的追踪,而追踪的目的当然不是迫使孤独发声或者改变,而是使光立于永恒的舞台之上。
所以《形单影双》是有关孤独的创造,像保罗·奥斯特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所述:“故事以终为始。每个事实都被下一个事实抵消,每种想法都会引起一种相等而对立的想法。”
每个影子都是为了取代上一个影子。因此我们会活着,以及稍纵即逝地复活。故事以终为始。
天边月白
游泳课上,姑娘们嘻嘻哈哈散落在教练谢园身边,而后者的心神在池边那个独自消沉的身影上。这周的第三次了,他想。她怎么了呢?
姜月的心事在妹妹姜玲身上。今天是姜玲18岁的生日,早上出门前,她们还没争论出最终决议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如果姜玲听话地去做了手术,现在正是结束的时间。她游向对面那个散发着光亮的身体她当然清楚,这仅仅是开始。
一年后,姜月和谢园的婚礼热闹纷呈,同学和老师们把酒言欢。秋日午时的阳光乏善可陈,任意塑造无聊的景象,姜月尽可能地跟随着它,试图体验一年前它倾泻在谢园身上的那些瞬间。
又是一年。商铺“天边月白”在镇上开张了,姐妹花老板声名远扬。
谢园变得越来越忙,不归家成了家常便饭。姜月便也在天边月白过夜,阁楼的窗子常常向夜空敞开。
数月未见,他们在家门口相遇大概是初冬的第一天,谢园带进来的阳光湮灭了整间屋子,浅灰色的橡木地板,两只光秃秃的、从狭长倾斜的天花板上荡下来的灯泡,窗帘上的大帆船图案,米色墙壁,阁楼的气味,上桌吃饭的默契,做爱之后的空气,盘底垫着的银杏叶……都消失不见了。
“一起吃饺子吗?”他们异口同声,相视而笑。
大雪日复一日倾轧着单薄的小城,小城里的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冬眠。天边月白进入淡季,一近落日便关门打烊。这天晚上,就在姜月将卷帘门拉下的一瞬间,一只带着酸味的手帕盖住了她的脸,一只有力的大手将她拖进一辆面包车里,疾驰而去。
迷迷糊糊醒来的姜月被反手捆绑在汽车后座上。而车子正晃晃悠悠地在一条小路上行驶着。窗外一片漆黑,偶尔有狗吠声散落四处。她惶恐地打量着开车的司机:衣领白净,看上去应该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
从后视镜里看到姜月醒了,司机将车缓缓地开到路边停下,点燃一根烟,坦白地说:“你被绑了,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也就是个打工的。你打电话叫你姐准备50万,放到白马咖啡厅马路对面58路公交车站的绿色垃圾桶里。限时后天下午四点前。”
姜月立刻明白了。他们绑错人了,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妹妹姜玲。
姜月思考了一会儿,她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必要隐瞒事实。
于是她直截了当地说:“你绑错了,我是姜月。”看男人不信,她补充:“我妹嘴上有颗痣,我没有。不信你问问你老板。”
男人刚刚发动的车子又熄了火。他开始对姜月进行搜身,果然搜到了姜月的身份证。
沉默片刻之后,男人说没关系,那就由你妹妹来出这个钱。反正老板要的是钱。绑哪个不一样。
姜月辩驳道:“那可不一样,我有钱,我妹妹没钱。虽然我俩一起开店,但她根本不管账,只问我要钱花,每天也不来店里。你现在让她筹钱,她的银行卡里估计连一万块也没有。”
车子在一片沉默中路过雪山,路过灯光寥寥的村庄,开往更远的远方。
姜月异常寒冷,她在惊吓和车子的颠簸中发起了烧,窗外的月亮变得模糊不清,湮灭在盛满灯光的水缸里。
车子最终在一排乌黑的矮房子前停下了。男人拽着姜月下车,向其中一间房子走去。
屋里充斥着中草药和汽油的味道。把姜月扔到床上后,男人熟门熟路地点火烧饭。不到十分钟,男人就把两碗热腾腾的面端到了床边的塑料桌上。解绑了姜月,自顾自地吃起面来。
姜月没有心情吃饭,她打量着面前的屋子:墙角堆着三个油桶,上面盖着几块已经被油污浸透的蓝布,蓝布上面你挤我我挤你地堆满了生活用品:玻璃杯、烧水壶、牙具、碗筷,等等。触目惊心的污浊感令姜月一阵恶心。但她更担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从目前来看活命应该没问题,但被强暴应该避免不了了。
男人面无表情地说:“如果你不吃,接下来的九个小时你都没的吃。吃完你只能睡两个小时,我们还要赶路。”
姜月问男人要去哪里。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的任务本来是绑架姜玲,问姜月要钱,然后杀掉姜玲,独自一个人去沙漠。但现在他错绑了姜月,既惊动了姜玲又拿不到钱,也不能放姜月回去。他现在考虑要不要杀掉姜月。
姜月大惊,告诉他,她的卡就带在身上。随时可以取钱,何必要杀她?
男人摇头:“不行。我会暴露。而且,我也不信任你。”
吃完饭,男人从车上取下来一套新棉被:“这个是给我媳妇买的,你先用吧,是新的。”说完男人开门出去,将房门反锁。
在巨大的疲惫感中,姜月很快睡熟了。
梦中她正睡在树上的一个鸟巢里,温暖而舒适。她细嗅着香甜的空气,耳边是随着清风随处摆荡的虫鸣鸟叫声。她睁开眼,打量着盖在自己脸上的云朵,却发现竟是黑色的……她惊恐地望下去,发现自己身下的树正在飞速向上攀缘生长,将她托上更高的天际,与那些黑云连接在一起……
她猛地睁开眼,汗已湿透衣背。男人正在盯着她看,将一杯水和一颗药丸递到她手里:“这是退烧药。”
姜月接过,犹豫了几秒,还是吃了下去。
男人将姜月盖的被子铺在后座上,将反手绑着的姜月带上去后,继续上路。窗外的画面颠簸地在她的眼前闪现,一道道绿色或者棕色的线条掠过。远处,这个山的形状替换成另一座山的形状。这一座与下一座也没有什么不同。
她周而复始地睡去,又醒来。大概是药起了作用,姜月的神志逐渐清醒。她盯着男人的后脑勺。
男人警觉地问:“你想什么呢?”
姜月说:“我手机没电了。姜玲肯定联系过我了,如果明天再找不到我,她肯定会报警。”
男人说:“他们找不到我。你现在先拿这个电话给姜玲打一个电话,告诉她你和朋友去旅行了。”
姜月点头:“好。那我还提钱的事儿吗?”
男人从后视镜里瞥了姜月一眼:“不用了,我也联系不上李峰了。他把我拉黑了。”
姜月大惊:“李峰?你的意思是?”
男人点头:“嗯,是李峰让我绑架的。我猜是姜玲去找他了,他以为我没有绑架姜玲……或者,他猜到我绑错了。他大概知道姜玲只能从你这里搞钱。”
姜月问:“你是说,是我妹妹的对象让你绑架她,管我要钱?”
男人:“嗯。”
姜月说:“这个畜生。”
男人笑了:“他确实是个畜生。”
姜月:“那你还杀我吗?”
男人想了想:“我没想好。”
姜月:“我给你钱还不行吗?放了我吧。”
男人:“现在不是钱的事儿了,或者说,不仅仅是钱的事儿了。”
车子继续向前行驶。窗外的景色已经替换成永无止境的沙漠,驻扎在国道两侧混混沌沌打转的风车,基本都是三个一组,每过一公里就能看得见。上空则是浩浩荡荡、久久不散的扬尘。阴雨时则云雾蔓延,视线很少清澈过。
偶尔有车辆擦身而过时,有司机积极地向车里探望。男人很警觉地从后视镜里看姜月的反应。看到她一直面无表情,男人才逐渐放松了戒备,开始和姜月攀谈。
“我们一会儿就到阿拉山口,我们会在那儿住一晚上。”
“那是什么地方?”
“新疆的一个边境。挺冷,也挺美。”
“那儿有什么?”
“有骆驼,有雪,还有我的一个朋友。”
姜月本来想问的是“我就一直这么跟着你去新疆?然后呢?”但是她更怕自己的提醒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
大约是在第五天夜里,他们到了一个旅馆。招待的女孩子说着姜月听不懂的语言。男人向她解释:“他们是哈萨克族。”
然而,旅馆没有多余的房间。他们站在路边,想着可以去哪儿过夜。
姜月建议他们在车上凑合一夜。但男人不同意:“我太累了,我要洗澡,要睡个好觉。”
姜月建议:“不如去当地人家借宿。”
男人犹豫地看着她:“会很脏。而且……那样我们估计得睡一个房间。”
姜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叫男人帮她拿好,她则对着“镜子”重新梳理自己的马尾。内衣的花边自然地从衣服里跑了出来。姜月捕捉到了男人躲避的目光。
男人问:“你干什么?”
姜月已经站在了马路上,把自己的围巾卸下来用力挥舞:“当然是给我们找住的地方了。”
一辆车又一辆车,远光缓慢而挑衅地打量着路边的两人,然后疾驰而过。姜月坚持不住了,她靠在了路灯后面的一个石柱子上。男人犹豫了一下,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了姜月身上。
姜月说:“谢谢。”
一辆面包车停在他们脚边,从车窗里探出一个50岁的胖女人的脑袋,仔细打量了男人和姜月,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男人说:“关你屁事。”
姜月忙说:“他是我男朋友,你别介意,我们刚吵架了。”
女人看了姜月身后的旅馆一眼,说:“上车吧,去我家住,我家就我一个喘气儿的,空房间倒是多。这种小馆子是不会有热水的。”
男人开着车子跟着胖女人的车,姜月听着车辆闯过植物和夜雾的声音。周围已经黑透了。远处总是有一处路灯,但是灯光漫不过来。
男人说:“你刚才说我是你男朋友,那女的就会让我们住一个屋。”
姜月说:“就算她不让,你也不会让我一个人住。”
男人笑了:“你很可笑。”说罢从后视镜看了姜月一眼,补充道:“很蠢。不过很识时务。”
胖女人的车子在一个上坡路上戛然而止。男人和姜月跳下车,一头撞进浓雾里。
男人压低声音介绍:“这里一到晚上就起雾。”
姜月说:“现在就是你让我逃我也不逃,外面太可怕了。”
男人面无表情的脸出现在后视镜里:“我对你没有兴趣,你不必逃。”
紧接着他补充:“到了乌鲁木齐,如果我找到我想见的人,那你也不用死了,我死。”
男人果真一夜都安静地在冰凉的地上打鼾,但是姜月却睡不着了。她的大脑像风车一样旋转,混浊的空气一股股地滚进来。她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并不是害怕或者恐惧,而是兴奋。她盯着地上的男人,知道自己的眼睛里弥漫着危险的蓝色。
她头脑里溢出的画面不停地变换着各种颜色:她和男人一起在乌鲁木齐的牧场里追逐打闹,傍晚时分他们各骑一匹白色的马下山。她的头发上有说不出的芳香,那香味沿着山路弥漫出梦一样的白色,和月亮一样的金色。
她的世界很安静,有谢园和姜玲的那个世界一片沉默。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想法:她真的可以和这个男人一起走,哪怕一起死,也是可以的。
因为姜月再次发烧,他们推迟了行程,男人打算在第三天的凌晨再出发。胖女人很兴奋,她准备了酒和菜。姜月察觉出胖女人对男人颇有兴趣,她莫名不悦,强撑身体要一起喝酒。
胖女人很高兴:“我们这里的人都说,一杯酒能治百病。喝好了你的病明天就好了。”
男人酒醉后对姜月吐出实情:他的妻子李明明失踪了,他记得李明明说过,有一个她放不下的人在乌鲁木齐。他对姜月说最好他不会在乌鲁木齐找到李明明,否则,他会和她一起死。
姜月问起男人的姓名。
男人回答她:“田园。”
有了醉意的姜月不禁笑了:“谢园,田园。怎么你们都是园,都喜欢把人关起来吗?……你说谢园找过我吗?”
男人:“谁?你男人?”
姜月说:“一个星期了,你说他找过我吗?”
田园把手机扔给姜月:“你给他打电话吧。”
姜月没有拿手机,转身躺下了。
他们上路了。一路上仍旧是漫长的戈壁滩和永远也无法抵达的山头, 但姜月的心头越来越宽敞和明亮。田园告诉姜月:差不多夕阳落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到达乌鲁木齐了。
姜月看着仍旧在眼底起伏无边的沙丘,默默地点头。她心里想的话没有说出口:她希望永远和他一起在路上。
姜月指了指远处的太阳:“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追过太阳。”
夕阳只剩下一条红边的时候,他们的车驶进了乌鲁木齐服务站。
车停在路边,姜月去解手,田园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洗手间,就发动车辆向前开。
姜月在厕所里排着长队,不断有人插队,她没有指责,只是等着。
田园的车向前行驶了不过一公里,他就忽然掉了头。返回原地。车子刚刚熄火,姜月就走了出来,抱歉地说:“排长队。”
从服务站出发后半个小时左右,田园缓缓地减慢了车速。姜月才发现路边停着一辆车。路边隐约有三个人,两男一女,两个男的正在互相推搡,女人抱着胳膊站在一边,见到有车辆靠近,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抿着嘴上前来招手。
田园一边叮嘱姜月无论怎么样都别下车,一边从扶手箱里摸了一会儿,摸出来一个小锤子,拿在手里掂了掂分量。
姜月很警觉:“你要干什么?你认识这些人?”
田园:“不认识。”
姜月:“那我们走吧。”
田园回头盯着姜月看了几秒,笑着说:“就凭你说的这个‘我们’,我明天就放你走。”
姜月说:“我不走。”
田园没再搭理姜月,他摇下车窗问拦路的女人:“咋了?”
女人带着哭腔,惶恐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两个男人:“大哥,让我上车吧。”
田园下车,帮女人拉开车门:“上车吧。”然后向两个男人走去。
两个男人停止了厮打,周围掀起的尘土缓缓落下,他们并排站在一起看着田园。
其中一个穿条纹衬衫的男人从地上摸起一块石头:“我们这解决家庭纠纷呢,和你没关系。赶紧走啊!”
田园笑了:“在这?用你手里的石头?”
另一个谢顶男想了想说:“兄弟,事情挺复杂的,一时半会儿我给你解释不清楚。”
田园对条纹衬衫说:“他解释不了,你解释解释。要不然你们今天走不了。”
条纹衬衫说:“我老婆被他睡了。就上你车那女的。”
田园说:“你是要杀了他俩?”
条纹衬衫说:“关你什么事。”
田园叹了口气:“要是你想杀她,我可以帮你。”他边说边回头看一眼车,车里的女人正对他投来求助的目光。
两个男人互相对视了一下,条纹衬衫说:“你赶紧滚,不然我马上砸死你。”
田园从裤兜里掏出锤子,朝着条纹衬衫的肩膀用力砸了一下。他痛苦地倒在地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