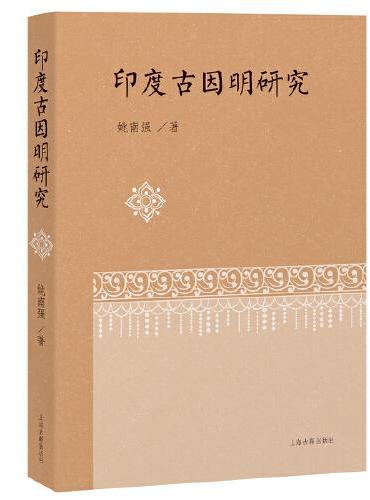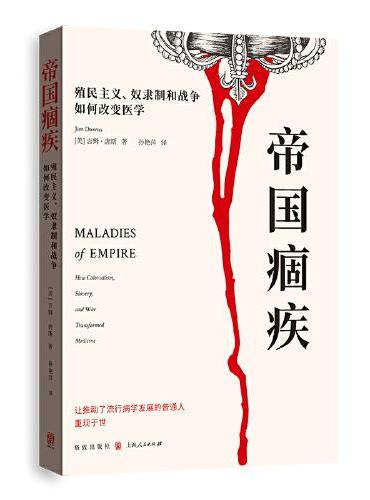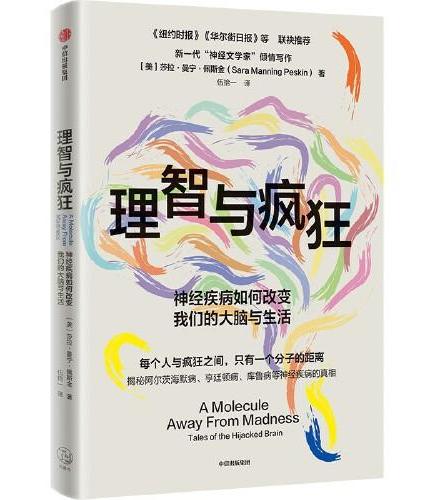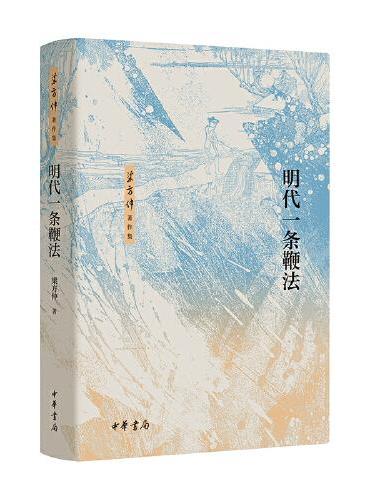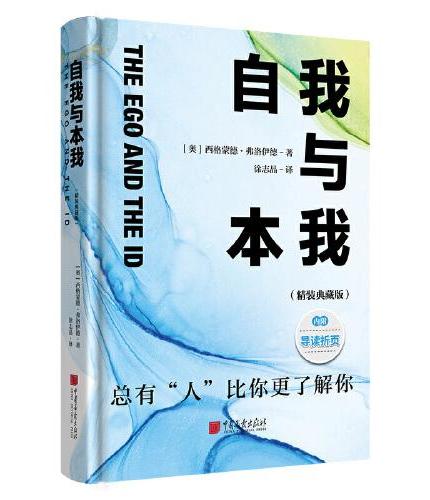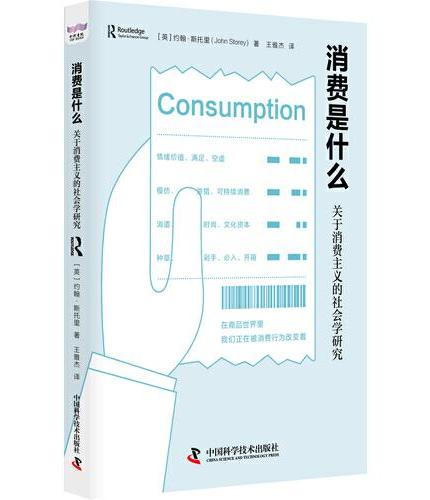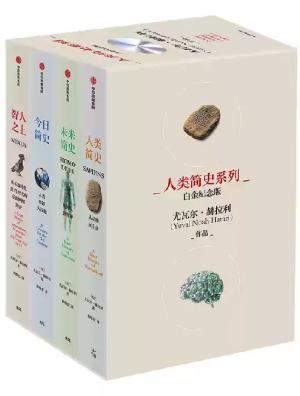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精选集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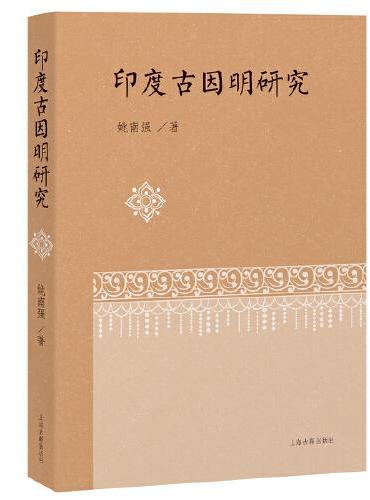
《
印度古因明研究
》
售價:NT$
6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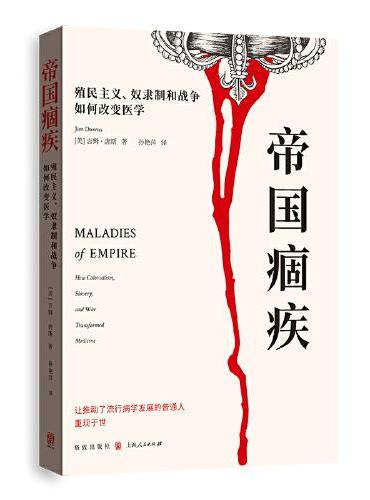
《
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
》
售價:NT$
3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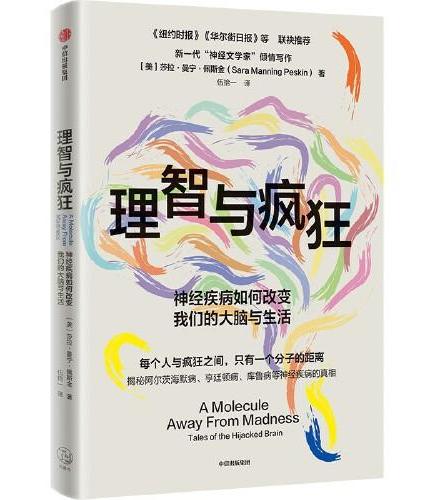
《
理智与疯狂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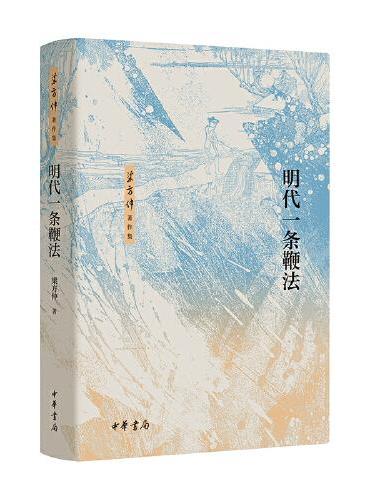
《
明代一条鞭法(精)--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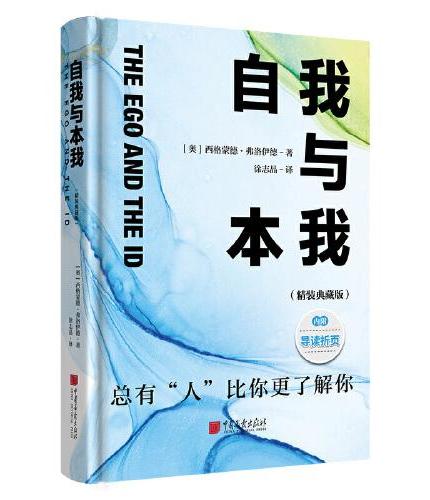
《
自我与本我:弗洛伊德经典心理学著作(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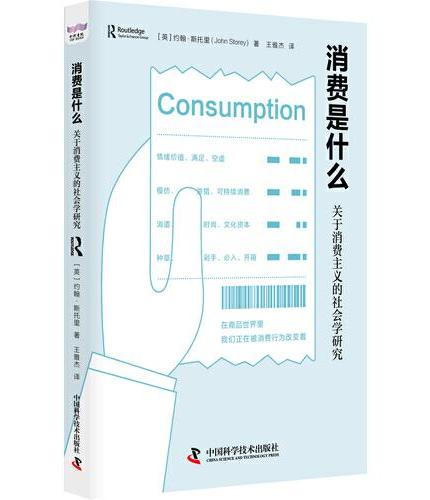
《
消费是什么 : 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一本书告诉你为什么买买买之后也有巨大空虚感)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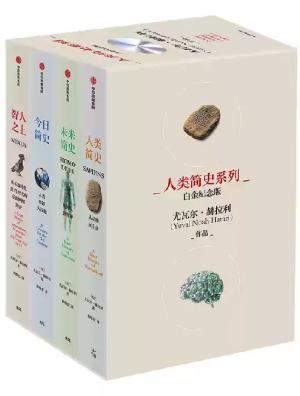
《
人类简史系列(白金纪念版)(套装共4册)
》
售價:NT$
1612.0
|
| 編輯推薦: |
☆ 班宇、淡豹、贾行家联袂推荐,一个谋杀案、一次复仇和一段被篡改的历史;
☆ 首 部获得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的非洲作家作品,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得主阿瓜卢萨引爆世界文坛的大师杰作;
☆ 阿瓜卢萨是当代安哥拉乃至整个葡语世界的代表作家,也是近年来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作品译为30多种语言出版,全球文学爱好者必 读;
☆ 疯狂奇幻的想象力,博尔赫斯的灵魂转投蜥蜴肉身,穿行于梦和现实,具有神秘而明亮的热带气息;
☆ 轻盈叙事的典范,媲美《遗忘通论》的精湛结构和故事技巧。
|
| 內容簡介: |
“我”是一只蜥蜴,在屋子里四处游荡,像神一般睥睨着屋里屋外的一切,偶尔我也会回想起前世那些身为人类的旧时光。
屋子的主人是一个白化病患者,名叫费利什·文图拉,他是一个“贩卖过去的人”。安哥拉独立后涌现出许多新贵,他们唯一的遗憾是缺少体面的出身,文图拉的工作便是为他们造出一个风雅和高贵的族谱,满足他们对身份的虚荣渴望。
一天,一名葡萄牙摄影师找上门来,文图拉将其命名为若泽·布赫曼,并为他制作了虚构的家谱。诡异的事接连发生,现实与梦境越来越难以分辨,而摄影师的真实身份中,隐隐浮现出安哥拉几十年动荡的历史。
|
| 關於作者: |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1960年出生于安哥拉,曾在葡萄牙学习农学和林学,作家、记者,著作颇丰,其作品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
近年来,阿瓜卢萨在英语世界声名鹊起,成为当代安哥拉乃至整个葡语世界的代表作家。2007年凭借《贩卖过去的人》获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是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非洲作家。《遗忘通论》入围2016年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并获得2017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
|
| 目錄:
|
小夜神
房屋
外国人
一艘满载声音的船
第一个梦
阿尔巴
若泽·布赫曼的诞生
第二个梦
光辉
一只蜥蜴的哲学
幻觉
我没有在第一次死亡中死去
第三个梦
风铃
第四个梦
我,欧拉利奥
童年的雨
在生活与书本之间
小世界
蝎子
部长
艰难岁月的果实
第五个梦
真实的角色
反高潮
无关紧要的人生
埃德蒙多·巴拉塔·多斯雷斯
爱情,一场犯罪
叶子花的呐喊
戴面具的人
第六个梦
费利什·文图拉开始写日记了
记忆、历史与重建中的国家——代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记忆、历史与重建中的国家——代译后记
“费利什·文图拉,保证给您的孩子一个更好的过去。”本书的主人公,那位“贩卖过去的人”,在名片上如此宣传自己的工作。初次读到这句话时,想必许多人会下意识将其直接解读为伪造文件、售卖假身份。而在故事开端,古怪的外国人在某天夜晚上门造访,拿着一沓大额钞票向费利什·文图拉表明来意,这样的业务内容被文图拉本人矢口否认——他贩卖过去、编织梦境、修补记忆,而在文图拉眼中,这与单纯的造假证是截然不同的。
费利什·文图拉的主要客户群体来自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这与小说中故事所发生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75 年,安哥拉摆脱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然而此时,国内局势仍旧动荡不安,很快又开始了更为旷日持久的内战。阿瓜卢萨的作品正是这一时期安哥拉社会的真实写照,尽管国家已经独立,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与创伤仍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成为安哥拉人民挥之不去的阴影。此时,“企业主、各部部长、农场主、钻石走私商和军官”,这一全新的资产阶级找上费利什·文图拉,他们无一例外拥有光明的未来,却想要从记忆商人处得到“一个美好的过去”,这既是在国家独立后粉饰自身、争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需要,也是一种重塑过去的诉求,深深反映出安哥拉人对摆脱战争伤痛的渴望,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身份塑造的焦虑与不安。
《贩卖过去的人》中,无论是老埃斯佩兰萨在武装袭击中死里逃生,从此坚信自己对死亡免疫,还是小时候偷摘枇杷的男孩在长大后入伍成为工兵,参与清除地雷时嘴巴里仿佛又品尝出枇杷的味道,许多细节处都能令读者感受到战争对国家和亲历者造成的影响,或是如老埃斯佩兰萨一般变得更为坚强有力,或是像枇杷男孩那样将自己的经历变成一个充满讽刺的玩笑,而只有战争的伤痛确实埋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就像数以千万的地雷埋在了安哥拉的土地里。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安哥拉的土地里埋了多少颗地雷。一千万到两千万。地雷有可能比安哥拉人还多。(第13 页)
除了战争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安哥拉人民记忆与身份构建问题的另一个表现是文化的融合。阿瓜卢萨作为巴西与葡萄牙移民的后代,本人便是一位带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作家,童年时跟随父亲游走多地的生活与之后在里斯本求学的经历更是丰富了这一点。安哥拉的社会也充满了类似的复杂性,漫长的殖民历史破坏了非洲的本土文化习俗,而同时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与人口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葡萄牙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如何在这种复杂且混乱的融合中定位自己的身份,找到民族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成为战后安哥拉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包括《贩卖过去的人》在内阿瓜卢萨许多作品的永恒主题。
费利什·文图拉,一个因患有白化病而被误认为白人的黑人,在客人面前坚定宣称自己“是纯正的黑人”:
“白人,我?!”白化病人一下子噎住了。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手帕,拭干额头,“不,不是!我是黑人!我是纯正的黑人。就是当地人。你没看出我是黑人吗?”(第24 页)
这一显然特意而为的主人公身份,无疑是阿瓜卢萨所设计的一个小小讽刺。在他看来,从来没有所谓“纯正的黑人”“纯正的白人”或“纯正的安哥拉人”,因为安哥拉的历史已经与葡萄牙的殖民关联颇深,在多方面都经历着一种交汇混合的过程,这也恰恰成为安哥拉人民寻求身份认同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正如阿瓜卢萨自己曾在接受巴西《论坛》杂志的采访时说道:
我不喜欢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几乎总会导向法西斯主义。在作为安哥拉公民之前,我是世界公民,我有权利书写整个世界,有权利阅读那些伟大的作家并吸收他们带给我的影响。有一个种族主义的陷阱,预设了非洲作家只能书写有关自己家后院的内容,否则就是异类。但与此同时,欧洲作家却可以书写非洲,甚至十分合适——展现出对于他人文化的开放。这种现象可以总结为:对白人而言,是整个世界;对黑人而言,是自己家后院。
在这个意义上,阿瓜卢萨似乎为这一身份建构的问题给出了他的解答。在《贩卖过去的人》中,名为“欧拉利奥”的蜥蜴作为一个拟人化的叙述者,其断尾脱身的习性似乎象征着文图拉那些渴望摆脱过去、开启全新人生的客户,然而欧拉利奥在梦境中获得化身,以人类的形态目睹参与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并在和费利什·文图拉同居一室的过程中,见证了那位外国人成为“若泽·布赫曼”,又在最后被揭露出真名与真实过去的全过程。这恰恰说明,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无法抛弃、无法割离的,这是在定义身份、寻求认同的过程中必须正视的一点。正如故事的开头,费利什·文图拉听过的那首歌《给一条河流的摇篮曲》歌词所说:“过去就是一条入睡的河”,“记忆是一道变化莫测的谎言”,即便选择掩饰,或是选择遗忘,伤痛和苦难也从未消失,“过去”只是“入睡了”,而一旦唤醒,便将成为记忆最不可忽视的存在。
因此,不难理解有评论家将《贩卖过去的人》解读为一部历史学元文学,从对人们记忆的探讨,拓展到对国家历史的思考。小说的结尾,蜥蜴欧拉利奥死去了,而费利什·文图拉却接过它的职能,开始写日记,尝试记录下自己所经历与见证的过去,将无形的记忆转化为有形的文字。正如安哥拉的国家与人民,在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与动荡的岁月过后,站在痛苦与创伤的废墟之上,崭新的社会、文化与身份正在形成。今天,对于许多中国读者而言,非洲的历史与文化仍显得相对陌生,《贩卖过去的人》一书作为阿瓜卢萨的代表作,语言精练,情节精彩,无疑可以成为一个认识和了解非洲的良好窗口。而在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深的当代,随着我们与各国间交流增多,阿瓜卢萨在书中所传达的思想与主题也表现出了更多的现实意义,带给我们值得思考的内容。
朱豫歌
2023 年2 月于里斯本
小夜神
我在这栋房子里出生,又在这里长大,从未离开过它。黄昏时分,我将身体倚在窗玻璃上,凝望天空。我喜欢看着高高的火焰,看着疾行的云朵,还有它们之上的天使,成群的天使,发丝上抖落火花,宽阔的双翼在火焰中扇动。景象总是大同小异,但每一个午后,我都会来这里,愉快又激动,仿佛第一次见到这些。上周,费利什·文图拉来早了些,我吃了一惊,一边还在笑着,因为当时在屋外,一片混乱的蓝天之上,一朵巨大的云彩正转着圈,好像一条狗在试图扑灭烧着了尾巴的火。“唉,我不敢相信!你笑了?!”
生物的怪诞刺激到了我。我感到恐惧,却还一动不动。那位白化病人摘下墨镜,收进外套的里兜,然后满脸忧愁地慢慢脱下外套,小心地挂到椅背上。他挑出一张黑胶唱片,放上一架老旧留声机的唱盘。《给一条河流的摇篮曲》,来自有“知了”之称的巴西女歌手多拉,我猜她在1970 年代享有一定的声誉。让我如此推测的是唱片封面的图案,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女人,她黑皮肤,很漂亮,背上绑着几只宽大的蝴蝶翅膀。“知了多拉,《给一条河流的摇篮曲》,时下流行”。她的嗓音在空中燃烧。最近几周,这已经成了黄昏的背景配乐。我将歌词牢记于心。
什么也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终结
过去就是
一条入睡的河
而记忆是一道
变化莫测的谎言
河水入睡了
白昼也在我的膝头
入睡了
伤痛入睡了
还有苦难
也入睡了
什么也没有过去,什么也没有终结
过去就是
一条睡着的河
宛如死去,气若游丝
唤醒它,它将跳跃
在一片呼声中
在灯光下,费利什等待着钢琴奏出的最后几个音符也消散而去。接着,他转动一张沙发,让它对着窗户,动作几乎没有声响。最后他总算坐下,伸开双腿,叹了口气:
“不敢相信!‘小东西大人’刚才笑了?!绝对是新奇事……”
我感觉他有点疲惫。他凑近我的脸,我能看清他充满血丝的眼眸。他呼出的气息将我的身躯包裹。是一种尖酸的温暖。
“糟透了,你的皮肤。咱们肯定是一家人。”
我一直等着这个。若是我说得出话来,肯定很没礼貌。我的发声器官却只许我发笑。但我还是试图冲着他的脸发出一阵激烈的大笑,某种能吓唬到他的声音,好让他从我这里走开。可是最后我只能发出漱口般微弱的声音。一直到上周,白化病人总是对我视而不见。但从那个时候起,就是从他听见我笑的时候开始,他就来得更早了。他会走进厨房,再出来时拿着一杯木瓜汁。他坐到沙发上,与我共享这场落日之宴。我们会交谈,或者说得更明白些,他讲话,我倾听。有时候我会笑,而这就让他满足了。我疑心一条友情之线已经将我们连在了一起。周六晚上,白化病人会领过来一个姑娘。都是又高又瘦、身体柔软的年轻女孩,双腿如鹭鸟般纤细。其中几个进来的时候还有点害怕,只坐在椅子边上,避免与费利什面对面,难以掩饰内心对他的排斥。她们喝点饮料,一口一口地喝,接着便默默地脱下衣服,躺下来伸展身体,手臂在胸前交叉,等待着他。
另一些女孩就更加大胆,她们贸然在屋子里乱逛,对着银器上的光泽与家具的品质指指点点。但她们很快又回到客厅里来,房间和走廊上成堆的书籍让她们吃惊不已,尤其还有戴高帽与单片眼镜的绅士肃穆的目光、罗安达和本格拉的贝桑加纳女人们玩味的目光、穿节日礼服的葡萄牙海军军官惊奇的目光、一位19 世纪的刚果王子疯狂的目光,还有一名著名的北美黑人作家挑衅的目光,所有这些人都在金色的边框中摆着永恒的姿势。她们又在书架上找起什么唱片。“你这儿没有库杜罗吗,先生?”既然白化病人那里没有库杜罗,自然也没有基宗巴,既没有奇迹乐队,也没有保罗·弗洛雷斯,这些时下的大热门。最后她们还是挑了一张封面最华丽的唱片,通常会是古巴的调子。她们跳起舞,在木地板上织出细小的舞步,同时一个接一个地解开衬衫的纽扣。完美无瑕的肌肤黝黑湿润、熠熠闪光,和白化病人干燥又粗糙的粉红色皮肤对比强烈。我什么都看见了。在这间房子里,我就像一个小小的夜晚之神。而在白天,我沉睡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