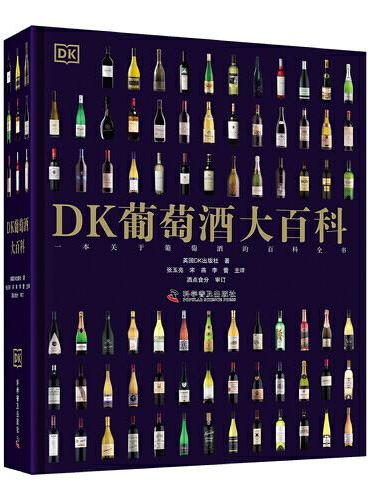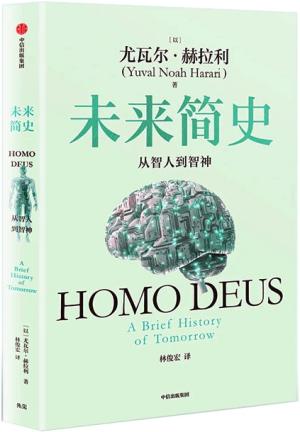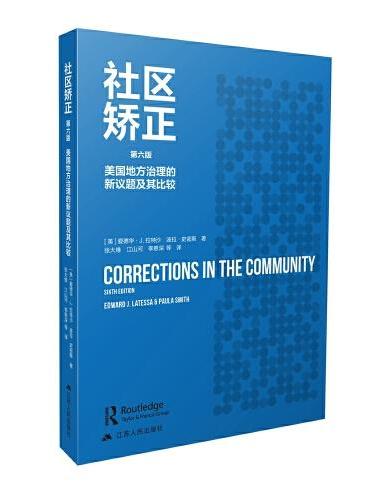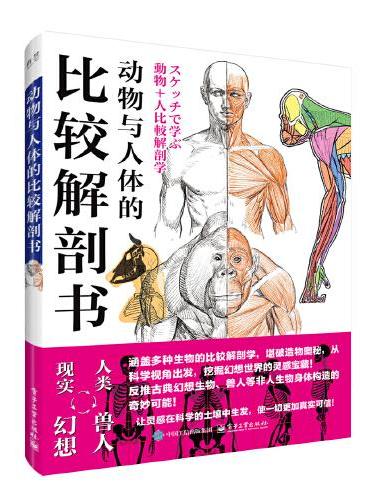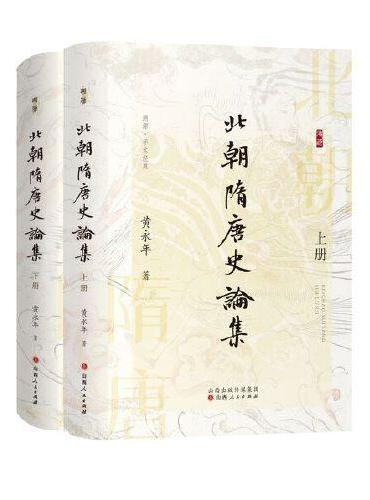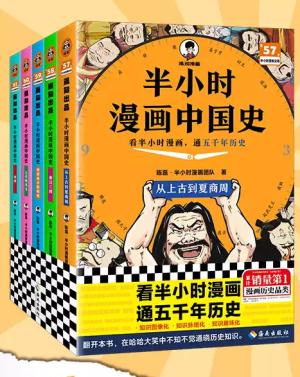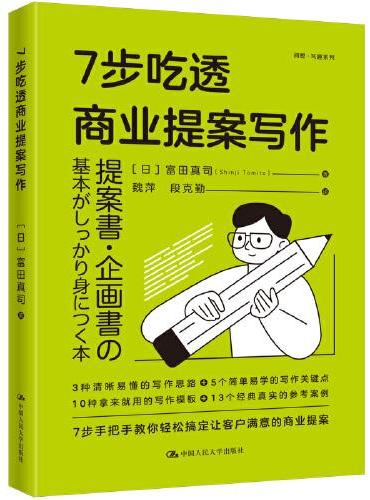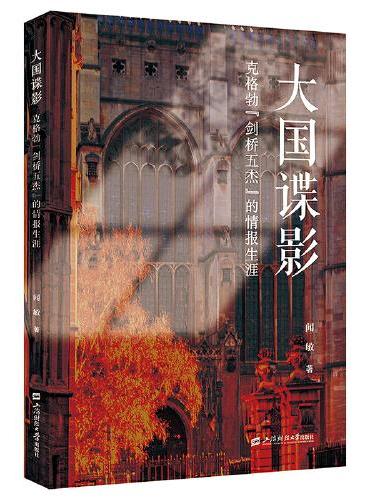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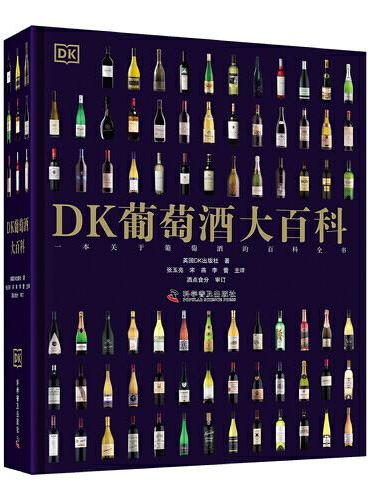
《
DK葡萄酒大百科:一本关于葡萄酒的百科全书
》
售價:NT$
25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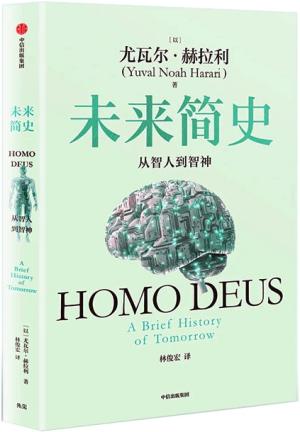
《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2025白金纪念版)
》
售價:NT$
40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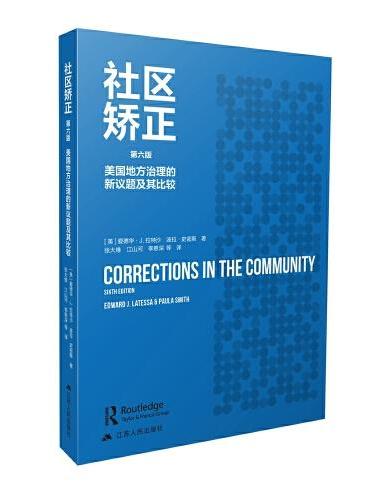
《
社区矫正(第六版):美国地方治理的新议题及其比较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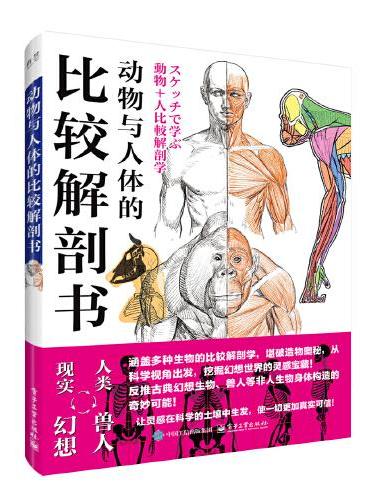
《
动物与人体的比较解剖书
》
售價:NT$
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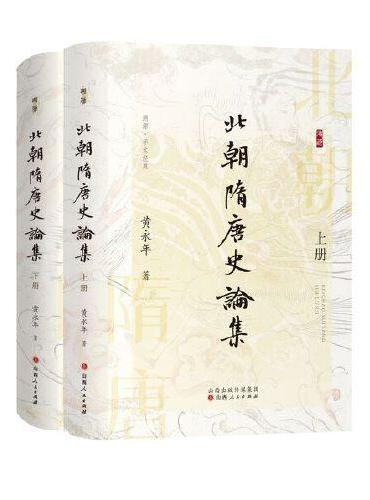
《
北朝隋唐史论集
》
售價:NT$
12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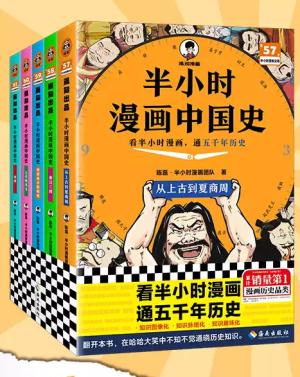
《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全5册)
》
售價:NT$
12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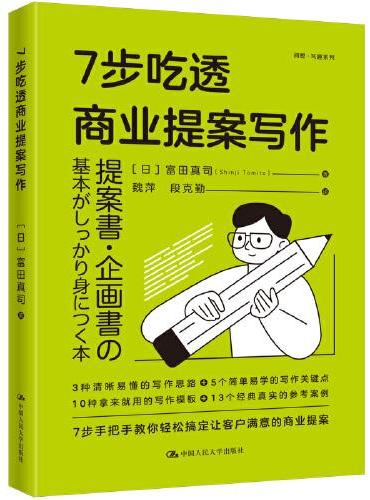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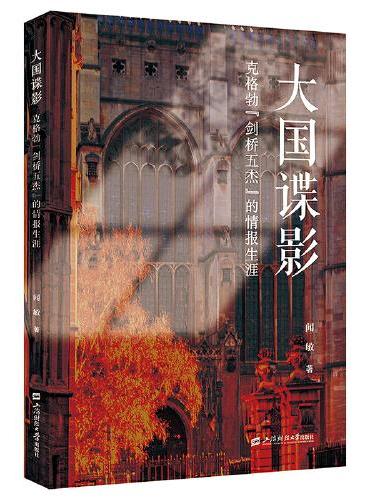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让你轻松理解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
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畅快淋漓的科学爽文,敌对国家之间科学家的隔空合作,竟促成一段科学国际主义的佳话
这不仅是一部科学史,也是一部关于科学的人文史,还是一部关于爱因斯坦和爱丁顿的传记
《自然》和《科学》杂志专业推荐
|
| 內容簡介: |
人人都知道相对论,却鲜有人知道相对论的提出和验证,穿越了战争和民族主义的隔阂,结合了两位敌对国科学家的努力,构成了国际科学共识的一块基石。
本书是一部扣人心弦、饱含人文关怀的科学史作品,既展示了相对论征服世界的历史,也呈现了充满隔阂和敌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身处敌对国的爱因斯坦和爱丁顿如何付出了卓绝的努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才使得相对论成为现代物理学的奠基理论。马修·斯坦利的这部作品,是一部关于科学理性和求知精神如何战胜偏见和民族主义的史诗,也是对当代科学精神和国际合作的赞歌。
|
| 關於作者: |
|
马修·斯坦利,纽约大学科学史教授,拥有历史学、天文学、物理学和宗教学学位,定期为《今日物理学》、《物理世界》和《洛杉矶书评》撰稿,开设有物理学科普播客“What the If?”。
|
| 目錄:
|
序 曲 “恶魔在咆哮,‘吼!……”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科学世界
第二章 跨越国界的科学
第三章 战争爆发
第四章 越发孤立
第五章 国际科学的瓦解
第六章 一次关键的胜利
第七章 跨越战壕
第八章 宇宙的边界
第九章 抵制相对论
第十章 革命天使
第十一章 验证相对论
第十二章 相对论闹剧
尾声 爱因斯坦与爱丁顿对后世的影响
致谢
注释
索引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科学世界
爱因斯坦家族都是乐于尝鲜的。雅各布和赫尔曼兄弟二人经营着一家小公司,主营业务是当时最前沿的革新技术:电气化。他们让德国南部的大街小巷都亮起了电灯,成了这个国家在19世纪末最超乎想象的进步之一。1871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随后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因此,此时的德意志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统一前的25个公国和王国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级帝国,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迅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以及引领整个欧洲大陆发展的学术和文化机构。这样的德国似乎已经是“现代性”的最佳范例了。马克· 吐温曾在1878年访问德国,他写道:“这真是一座天堂,人们的衣着是那么整洁,面容是那么友善,洋溢着那么安静的满足感,这里是那么繁荣,有真正的自由和一流的政府。而且我很高兴,因为我不需要对这一切负责,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享受这一切。”
在马克· 吐温到访德国一年后,赫尔曼的妻子波琳生下了两人的第一个孩子阿尔伯特。当时他们一家住在多瑙河畔一个规模不算太大的城市乌尔姆(这里的城市格言是“乌尔姆人都是数学家”)。没过多久,爱因斯坦一家就从乌尔姆举家搬到了位于德国南部的大都市慕尼黑。幼年时的阿尔伯特很晚才开口说话。他习惯于先把要说的话反复讲给自己听,确定正确无误后才开口讲出来。他发脾气的样子也很出名,整张脸会变得蜡黄,鼻尖变得雪白。据阿尔伯特的妹妹回忆,有一次哥哥生气了,就用花园里的锄头砸了她的头。
爱因斯坦一家是犹太人,但已几乎完全世俗化了。德意志帝国对犹太人几乎已经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限制,但很多反犹太人的传统仍然存在。与大多数同化主义家庭相同,爱因斯坦一家也深深融入了德国的世俗文化。赫尔曼会在晚上给孩子们大声朗读席勒和海涅。波琳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钢琴师,她希望阿尔伯特能成为自己的音乐伙伴,因此在他六岁时便开始教他拉小提琴。此时,小男孩阿尔伯特非常讨厌这种机械而又重复的训练,因此只是很不情愿地学习音乐,这也仿佛是对未来的一种预兆。直到多年以后,阿尔伯特发现了自己对莫扎特奏鸣曲的热情,才开始全心全意地学习小提琴。他在多年以后曾回忆道:“我完全相信,相比于责任感,爱是更好的老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然而,对他来说很不幸的是,那时的德国教育更强调责任而非爱。阿尔伯特就读于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刚好是一所天主教学校。学校纪律严明,崇尚军国主义。阿尔伯特不喜欢总是有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于是几乎与所有老师都对着干。他曾经用椅子砸自己的家庭教师,还总喜欢用“你”而不是“您”来称呼老师,让人非常恼火。根据爱因斯坦的家族故事记录,有一位老师曾严厉训斥阿尔伯特说:“就算你只是出现在这里,也已经是整个班级对我的不尊敬了。”但这些言语对阿尔伯特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阿尔伯特几乎没有朋友,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很独立了(四岁时就可以独自走在慕尼黑最繁华的街道上)。他最喜欢的游戏是用纸牌搭房子。与那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所描述的不同,阿尔伯特的成绩其实并不差。学校总是强调对经典语言的学习,这并不合阿尔伯特的胃口。因此,阿尔伯特所接受的持续性教育大多来自家庭。老年阿尔伯特曾经忆起那个点燃了自己对科学之热爱的瞬间。那是在他四五岁的时候,他那喜欢小物件的父亲把一个罗盘当作礼物送给了他。罗盘里的指针总是指向北,这个简单的现象深深吸引了年幼的阿尔伯特。在现象的背后,那些看不见的力始终保持不变,也绝不会出现差错,阿尔伯特为此而着迷。这些是什么?是不是还有更多这样的事物?可以去理解它们吗?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
1919年的日食持续了很长时间。这并不是说日食本身,因为那只有短短几分钟,而是说这场日食的影响,它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每一代人都用爱因斯坦和日食的故事来解释科学是什么,如何发挥作用,又意味着什么。这个故事究竟给人们上了怎样的一课,这一点在过去不断发生变化,未来还将继续变化。然而,1919年的日食已经变成了展示科学本质的一个典范,不管这个本质是好还是坏。
如果你找到一位当代科学家,问他什么样的观点才算是“科学的”观点,你很有可能只会得到一个茫然的眼神(关于这个问题,科学家并不需要进行多么深入的思考)。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一个答复,那么它很有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是可证伪的,那么它就是个科学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通常是通过实验来实现),那么这就是科学的观点。这样一来,科学就不是要证明好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是要证明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消除了所有不适当的观点后,科学家们就可以越来越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了。
这种态度有一个很古怪的名字:证伪主义。在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群中,这种态度确实非常普遍。这种思想态度是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的智慧结晶。波普尔生于奥地利,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像对爱因斯坦一样,人们对波普尔的印象似乎也是他生来就是个老人:下颌宽大,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到脑后,耳朵庞大如象耳。然而,要理解波普尔与1919年日食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了解一下那位年轻英俊、时髦潇洒的波普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于1902年的波普尔还太年轻,不能上战场,却足以看清战争的不公。这让他在年仅十五岁时便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到了波普尔十七岁时,随着1919年的日食让爱因斯坦现象在全世界遍地开花,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学术英雄。在1919年到1920年的那个冬天,年轻的波普尔聆听了这位天才在维也纳的演讲,结果发现自己变得“迷惑茫然”了。
让波普尔感到震惊和迷惑的并不是时间的膨胀和弯曲的时空。事实上,相较于相对论的科学本身,波普尔更感兴趣的是爱因斯坦是如何谈论科学的。让波普尔最为震撼的是爱因斯坦的“知识谦虚”,也就是说这位物理学家明确指出了相对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被推翻。如果没有引力红移,那就没有相对论;如果没有光线偏折,那就没有相对论。这种大胆(这是我的预言,你们可以去验证它们)与试探(我的理论只是暂时如此,你随时可以去证明它是错误的)让波普尔印象尤为深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