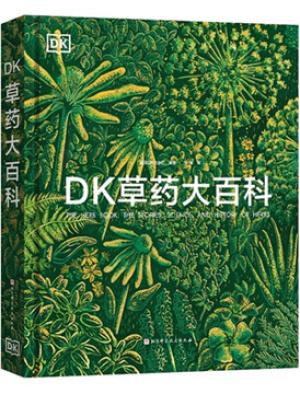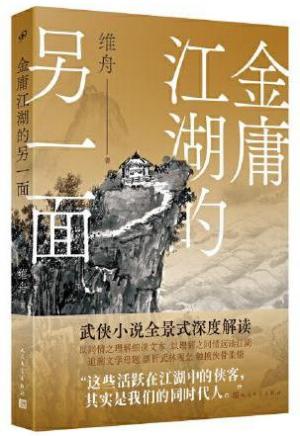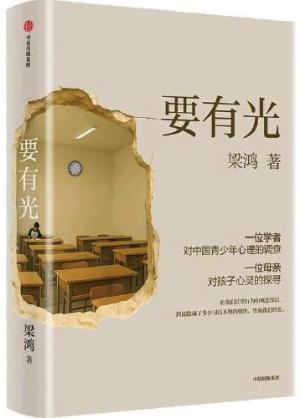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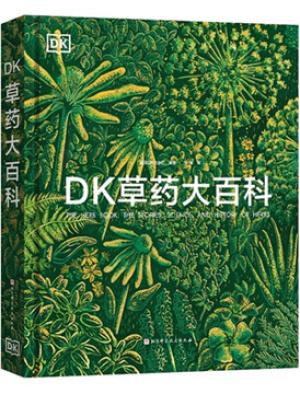
《
DK草药大百科
》
售價:NT$
1367.0

《
以远见超越未见:当今时代的教育、文化与未来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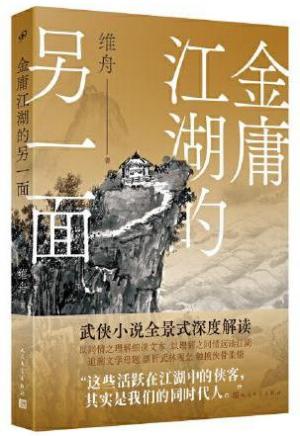
《
金庸江湖的另一面
》
售價:NT$
301.0

《
乘风而上(美依礼芽中文自传)
》
售價:NT$
398.0

《
索恩丛书·帝国计划:英国世界体系的兴衰(1830~1970)
》
售價:NT$
8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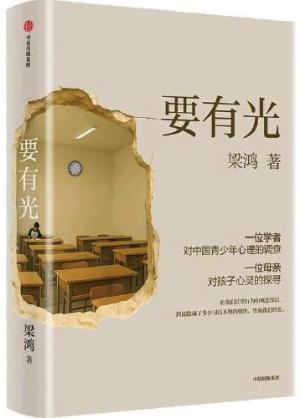
《
要有光
》
售價:NT$
352.0

《
广雅·法史万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撷英(通过礼与法、情与法的关系,展现法律史背后的文化史。)
》
售價:NT$
403.0

《
梁启超:维新1873—1898
》
售價:NT$
449.0
|
| 編輯推薦: |
|
《大儒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导读》,晚清中兴名臣的军事密码,一部改变中国近代史的战略决策实录!
|
| 內容簡介: |
|
本书由同济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刘强注译导读。深度解析中国古代儒家与兵家的内在关系,重点聚焦近代大儒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精彩阐释“中国十大兵书”之《曾胡治兵语录》的治军方略与领导智慧。每章设导读、原文注释、白话译文三大板块:导读勾连古今,揭示兵法要旨:注释考校严谨,破解古文深意:译文精准流畅,实现零门槛阅读。卷首长序及书后多篇附录,梳理明晰,资料详实,对于军事爱好者,尤具参考价值。
|
| 關於作者: |
|
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兼任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写作学会副会长、台湾东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等。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先秦诸子经典,儒学与古典诗学、文言笔记小说等。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世说学引论》《竹林七贤》《魏晋风流》《论语新识》《四书通讲》《世说新语通识》等著作二十余种,主编《中华少儿诗教亲子读本》(11 卷)、《世说新语鉴赏辞典》等多种。作品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湖南省优秀社科普及读物奖、儒家网十大好书奖、伯鸿书香奖·阅读推广奖。
|
| 目錄:
|
自序 “法自儒家有” /001
初版序 世上再无曾国藩/038
凡例/057
前言 /060
梁启超序/074
蔡锷序 /078
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 蒋中正 /081
第一章 将材 /001
第二章 用人/014
第三章 尚志/024
第四章 诚实 /035
第五章 勇毅 /054
第六章 严明/071
第七章 公明/082
第八章 仁爱/095
第九章 勤劳/106
第十章 和辑/118
第十一章 兵机/126
第十二章 战守/ 148
第十三章 治心 / 162
附 录
曾国藩治兵语录辑补/194
一、书信之属/194
二、日记之属 /209
三、杂著之属 /219
四、奏疏之属/223
五、诗文之属/226
保守平安歌 / 226
爱民歌 /229
解散歌 /231
水师得胜歌/232
陆军得胜歌/234
晓谕新募乡勇 /237
劝诫营官四条 /238
治军条规四种/239
后记/ 243
|
| 內容試閱:
|
前言
《曾胡治兵语录》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一部著名的语录体兵书,“中国十大兵书”之一。该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晚清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和治军方法,民国初年,被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
《曾胡治兵语录》由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所辑录,成书于1911年,最初只是作为教材使用,并未传之社会。蔡锷逝世后一年,即1917年,始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版本,今所知民国时期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7年中国书店《古代兵经》本等。
关于编写者及编写缘起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后改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将领、军事家。
蔡锷自幼聪慧好学,14岁中秀才,15岁考入清末颇有影响的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提倡变法维新的谭嗣同、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任教,谭嗣同任学堂总监,梁启超任学堂总教习。年轻的蔡锷深受谭、梁二公思想的影响,并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慷慨就义,梁启超流亡日本。朝政的腐败使血气方刚的蔡锷深受刺激,他曾计划行刺慈禧太后,因故未果。
1900年,蔡锷赴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回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其间著有《军事计划》一书,对加强国防建设和治军用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1911年初,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月下旬,英国军队入侵我国云南边境片马地区。蔡锷感到,军人为国尽职的时候到了。他见到新军风气败坏,军纪涣散,十分焦急,很想为改变风气、鼓舞士气做出应有的贡献。恰在此时,第十九镇镇统钟麟同找到蔡锷,要他编写一个针对军人的“精神讲话”。于是,蔡锷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以阐述自己关于治军的见解,希望借此唤醒军心,把新军训练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书中的曾、胡,系指清末政治家、军事家、湘军统帅曾国藩和胡林翼。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革命党人密商响应,10月30日在昆明组织武装起义。次日,起义军占领全城,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嗣后,因忧心于西方列强觊觎我国西南地区,蔡锷主持编写了《五省边防计划》,提出了拱卫边疆,加强防务,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具体方案。
1913年,蔡锷被袁世凯调北京任参政院参政等职,授将军府昭威将军。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遂由北京潜回云南,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他抱病亲帅第一军入川,依靠人民支援和士气优势,运用近战和迂回包围战术,同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鏖战川南,克宜宾、江安、纳溪等地,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1916年6月,护国战争胜利结束,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1月8日,病逝于日本,年仅35岁。
严格说来,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曾国藩和胡林翼,但是,蔡锷将这些丛杂的语录钩沉出来,并按照十三个门类加以编排,再加上序言和按语,便如线之贯珠,使全书纲举目张,夺胎换骨,有了一个新的系统和生命。故蔡锷又可以算是此书的缔造者,也是曾、胡二公军事思想的整理者和弘扬者。
关于曾国藩与胡林翼
曾国藩、胡林翼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湘军的核心人物。二人都是“儒将”,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注意借鉴传统文化和军事理论,善于总结和思考,从而提炼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在近代军事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今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人。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有“中兴第一名臣”之誉。湘军创始人,近代洋务运动发起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之第一人。
曾国藩家世儒学,幼年就读于家塾“利见斋”。24岁考取举人,1838年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及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十年之内,连升十级,可谓官运亨通。然其为人,则有鲁钝之名,谦卑戒慎,勤恪笃敬,在京师做官期间,究心于诗文和理学,著述享誉士林,有“一代儒宗”之称。
1853年,太平军以势不可挡之势进攻湖南,清廷上下惊恐万分。连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也被皇帝指派于家乡“帮办团练”,以阻击太平军的攻势。从此,曾氏弃文就武,从办团练开始,募陆军,创水师,逐步建立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世称“湘军”。随后亲率湘军出省作战,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战略要地武昌田家镇,控制了长江上游。1855年,其水师在湖口遭太平军重创,被迫退守南昌。次年,趁太平军天京内乱之际,重新聚集力量,再次夺回武汉、九江等地。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分兵三路攻取浙江、支援上海、围困天京。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清廷封曾国藩为一等侯,加太子太保衔。次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因战败去职。后曾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曾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872年病逝于南京。著作被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1836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1850年,署贵州镇远知府,次年补黎平知府。1854年补贵东道员,率黔勇到湖北,与曾国藩一同阻击太平军。同年,迁四川按察使,调任湖北,从此与曾国藩同任湘军统帅。次年,配合曾国藩进攻江西九江、湖口,升任湖北布政使,回救武昌。1856年,任湖北巡抚,以湖北财力全力支持曾国藩,并多次派部增援庐州(今合肥)、安庆。1861年9月,因所遣之部攻陷安庆,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太平军攻克黄州(今黄冈),迫近武昌,胡氏惊忧成疾,呕血而亡。抚鄂期间,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其所著《读史兵略》46卷,奏议、书牍10卷等,辑有《胡文忠公遗集》,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
蔡锷对曾、胡治军思想的敬重与推崇
曾、胡二公乃一代人杰,虽然其所捍卫与护持的乃是日趋衰败的清王朝,用以治理湘军的思想武器也是在西方文明冲击下面临危机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呈现出鲜明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特色,并且在具体实践中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撇开政治上的考量不论,二公的行迹与人格、军事才能与事功成就,无疑是应该受到公允评价和理性肯认的。
曾国藩逝世10年后才出生的蔡锷,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也予以相当程度的认同。他从内心深处对曾、胡这两位同乡先贤的事功尤其是治军方略表现出钦敬之情,对他们的军事才干十分推崇,并对二公的军事思想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认为他们的兵学言论大都切中近代军事时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指导意义。因此,尽管曾、胡是为清王朝服务的人物,但身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蔡锷,仍然把他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榜样来看待,尤其是对曾、胡在治军方面的思想主张,从总体上予以了认同和表彰。其要点如下:
(一)对曾、胡“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来选拔和培养将领的思想,蔡锷认为是“扼要探本之论”。
曾、胡在治理湘军时,继承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把“练将”摆在十分重要地位的经验,反复强调:“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哉”;“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伟之才。……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以上见《曾国藩全集·书信》)。对此,蔡锷认为其主旨源于中国传统的论将五德,即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与西方军事家所说的“天所持赋之智与勇”基本相似,且有了新的发展。“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这一治军思想,是曾、胡等人从实践中得来。蔡锷充分肯定了曾、胡等人以“忠义血性”作为治军思想的历史地位,并把它吸取继承过来,用以唤起革命军人为推翻清王朝、建设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自觉性。这种态度,反映了蔡锷的实学精神非常明显:尽管蔡锷所处的时代比曾、胡的时代已前进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蔡锷根据清末民初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尤其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实情,从总体上对曾、胡的治军思想予以认同,是符合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的。
(二)对曾、胡提出的将材由“陶冶而成”,不必拘定一格,应使其各显其长,各去其短的主张,蔡锷表示完全赞同。
曾、胡将将材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如果能做到“智略深远”又“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之将。然而,有才能的人并非无缺点,将材是经过陶冶、磨练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多见的。所以,曾、胡主张用人尤其是使用将材不须规定一格,不必求全责备,重要的是发挥各人的专长,在实践中锻炼其才干。对此,蔡锷作了具体阐发:“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而“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但并非专指一二人,譬如官长居目兵之上位,中级官居下级官之上位等,人人都有责任从自己做起,关键的问题应当是“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这样的话,“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蔡锷强调,只有像曾、胡所倡导“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互提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既倒于”,才能收到潜移默化,“日趋于善”的效果。
(三)对于曾、胡所主张的以“诚实”二字引导士兵养成高尚的志向,不为金钱、地位所诱惑,做到“忠愤耿耿”的治军思想,蔡锷推崇为“至理名言”。
曾、胡二公反复指出:对于部属重要的不在于怂恿他们如何去猎取地位金钱之大小多寡,“不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对于这一观点,蔡锷作出评论。他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在时局日坏、兵祸频仍之际,如果下定了“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的志向,就“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的精神,去达到最终目的。反之,如果做将官的人都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做士兵的人都“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那么国家民族的兴旺和前途,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曾、胡认为,要使将领和兵勇相互信任支持,不去追逐金钱地位,凡事必须始终坚持一个“诚”字和一个“实”字,以此去反复启发引导人人心中内在的良知。蔡锷明确认定这是决定一支部队能否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他深知,军营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全靠万众“不容有丝毫芥蒂”。要能做到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就必须像曾、胡所主张的那样,用“诚实”二字来“贯串”、来“维系”感情;否则就会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
(四)对曾、胡有关公正廉明、知人晓事的治军思想,蔡锷充分肯定其“持论至为正当”。
曾、胡用人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是由于他有一套完整的人才理论,切合实际的处理方法,这就是做到“公正廉明”然后才能“知人晓事”,治军更是如此。蔡锷则认为,用人能否相当,取决于对人的了解是否明了;办事是否有才能,取决于看问题是否透彻。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曾、胡所说的,辨别一个好的将领是君子还是小人,最重要的要看他“能否利人济物”。如果所用的人不能称职,所办的事得不到好结果,即使出发点是好的,终究也难成好官、好将领。自古以来,一切公正廉明的圣贤之士,在用人方面一般都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蔡锷列举曾国藩荐举左宗棠而不计私嫌,弹劾李元度而不念旧情的实例来加以论证,高度赞扬曾氏“不以恩怨而废举劾”,真正是“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曾、胡以知人善用闻名于近代,清咸丰、同治年间所谓的“中兴名臣”,大都与他们的荐举提拔有关,他们在从政、治军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蔡锷及其统率的军队仍然处于内忧外患同时并至的非常时期,所以他对于曾、胡知人善用的治军思想,很自然地产生了予以继承的迫切愿望。
(五)对于曾、胡提出的“恩威并用”的治军思想,蔡锷表示全面认同。
曾、胡二公治军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尽力将孔、孟之“仁”和“礼”的思想融合于士兵的言行之中,把封建的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联成一体,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友谊关系来掩饰、调剂、弥补将帅之间和士兵之间的摩擦与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长官、服从官长、维护官长,甚至为之死力卖命,在所不惜。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曾、胡反复强调要坚持“仁爱”和“严肃”即“恩威并用”这四个字。什么是“仁爱”呢?据曾、胡解释,军人既然以军营为第二家庭,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官长对士兵,也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这是因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爱互助,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所以到了战时就会互相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什么是“严肃”呢?曾、胡认为,军事不同于儿戏,行军作战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从而,他又主张对士兵要用“严肃”二字即进行军队纪律性的训练:对待兵勇不可过于宽纵,平时之规矩,应当严格执行,“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他反复强调,在抓正规化军事训练的同时,应严格禁止此营议彼营之短,彼营议此营之过。在行军驻扎之时,不准扰害百姓。为了严肃军规军纪,针对兵勇中大多数人不识字的特点,曾、胡用浅显的语句,将兵勇的起居生活,营房驻扎,出阵攻守等方面的规章与告诫之言,编制成种种歌词,如《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要求兵勇口诵心记,于无形之中印入脑海,在日常言行中约束自己,以期收到预期的效果。
蔡锷充分肯定曾国藩所说的“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语,以为“最为慈仁贴切”。如果谁能真正以曾国藩这一名言时常存于心中并落实到行动上,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去熟读古今兵书所言的带兵之道了。蔡锷具体作了解释,如果做官长的、做上级的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事事处处都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那么他就能做到:当他感到士兵愚顽无知时,则会想方设法开导他们;看到士兵饥寒苦痛时,则会百般爱护关心他们;发觉士兵放荡无羁、浮华不实时,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指责,细心诱导,等等。这一切,无论是宽容还是严厉,是爱护还是憎恨,是奖赏还是惩罚,都是出于“至诚无伪”,都会起到感化、启迪士兵情感,使之人人学好,个个成材的积极效果。反过来,“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
蔡锷亦推崇曾国藩的“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之说“亲切有味”,并且做了详尽的阐发。他认为,原因在于官长与兵勇之间的相处是师友般的平等关系;官长对于兵勇的约束督责、百般爱护的情谊,就如父兄对子弟一般的至亲纯净;士兵对于官长如果能做到“恪恭将事”,也就如子弟对于师长父兄那样出自内心的真诚,这样,官长与兵勇在平时彼此和睦相处,战时同患难共生死,去为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蔡锷还特别强调,应该将曾、胡所说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的观点,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加以体会实践。他具体解释其理由说,用兵本来就是为了安民。国家有难,天下不太平,才不得不用兵。如果用兵不是以爱民为本,而是去扰害百姓,那么就是“悖用兵之本旨”。这样,不仅在筹集粮饷、征发夫役、探访敌情等方面得不到积极的支助,且将“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应该说,这些观点都是其来有自且颇具现实意义的。
关于《曾胡治兵语录》
中国兵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有人统计,现今存世与存目的兵书约3300余部,23500余卷,如果再加上以散失不见著录者,中国兵书当在4000部,30000卷左右。目前最著名的兵书有十部,它们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诸葛亮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曾胡治兵语录》。
在编评《曾胡治兵语录》过程中,蔡锷对曾、胡的军事战略战术做了中肯的评价,同时指出了这些观点形成的时代背景。蔡锷十分推崇曾、胡二公,却又并不囿于二公的理论,而是根据国情现实提出了诱敌深入,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近代特色的军事思想。蔡锷在每章之末,都附有一段简略的按语,或对本章大意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尤其是在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按语中,蔡锷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在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曾、胡的某些言论做了修正,很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十二章,系统地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前十章围绕置将、整军、训练等,论述治军中的种种问题;后二章则专门论述战略战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将材》一章,主要论述高级将领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曾、胡兴兵之日,正是晚清政治最腐败的多事之秋。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早已渗入军队,当时的官军八旗、绿营,将帅贪鄙,士兵离心,军纪松弛。在士气高涨的太平军面前,官军不堪一击,屡战屡败。针对这种局面,曾、胡认为,用兵须先治兵,治兵须先治将。他们一再强调,“天下强兵在将”,就是这个意思。从《将材》看,曾、胡治将,又首重选将。他们要求将领除了具备基本的军事才能外,还必须“才堪治民”,可谓文武并重、德才兼求。而在众多要求中,又最重道德品质,即必须“有良心,有血性”。
曾、胡对中下级军官的选拔也同样重视。胡林翼说:“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
从《用人》一章看,曾、胡对中下级军官虽重选拔,但更重培养。他们一再强调,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而要善于用其所长,并在实践中对之进行培养和熏陶。
《尚志》《诚实》《勇毅》三章,都是讲军人的修养和素质。曾、胡认为,做人要有远大志向,做军人也要立志高远、淡泊名利。胡林翼说:“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本着这样的认识,曾、胡指出,治理军队应该先治人心。他们认为,军人做到诚实质朴,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影响到战争胜负的关键性问题。在论述勇毅时,曾、胡虽然也很注重不怕死的精神,但并不赞赏匹夫之勇,而是提倡一种具有浩然之气的“大勇”。
《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等五章,都是讲练兵、带兵的方略和原则。曾、胡认为,赏罚严明、军纪整肃是克敌制胜的保证,必须使军队做到“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又说,将帅身居高位,掌握军中生杀大权,做事应出以公心;应以仁爱之心带兵,使士兵有以军营为第二家庭的感觉。曾、胡指出,行军打仗,经常会遇到一些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军人只有时刻勤于训练,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当几支部队联合行动时,必须号令统一,团结协作。胡林翼说,“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
《兵机》《战守》二章,所论多与用兵谋略和作战攻守相关,集中反映了曾、胡的战略战术思想。曾、胡论兵,主张谨慎稳重,一再强调,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决不轻言出战。他们特别强调运用士气,讲究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在攻守作战方面,则极重主客之说,力求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论防守时,强调控制重点,选择枢纽之地厚集重兵把守。曾、胡还指出,兵机是时常变化的,作战时必须“奇”“正”相辅,灵活应对。胡林翼说:“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从《兵机》《战守》二章可以看出,曾、胡善于将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灵活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并能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因而,《曾胡治兵语录》中曾、胡二公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