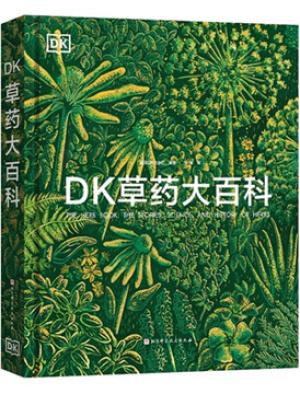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意大利读画记
》
售價:NT$
347.0

《
动物社会的生存哲学 : 探索冲突、背叛、合作和繁荣的奥秘
》
售價:NT$
454.0

《
百越: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文化与社会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
售價:NT$
755.0

《
雾越邸暴雪谜案:全2册(綾辻行人作品)
》
售價:NT$
658.0

《
朱子的穷理工夫论 | 香江哲学丛书
》
售價:NT$
485.0

《
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一部政治思想史力作,反思传统时代的王朝周期)
》
售價:NT$
403.0

《
甲骨文丛书·英国人在印度:三百年社会史
》
售價:NT$
8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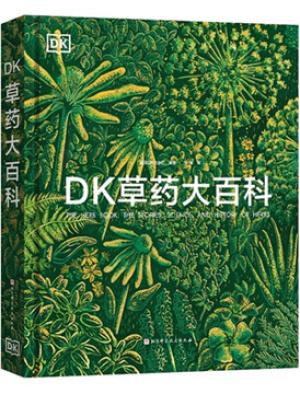
《
DK草药大百科
》
售價:NT$
1367.0
|
| 編輯推薦: |
书名《美丽新人类》致敬赫胥黎的反乌托邦经典作品《美丽新世界》,提醒读者警惕辅助生殖技术背后被淡化的伦理问题。
《美丽新人类》的作者萨拉?丁格尔本人就是通过供体受孕出生的亲历者,又是专业的写作者,其曲折的个人经历和专业的调查能力使得本书既有说服力又引人入胜。
本书开篇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历史做了生动有趣的回顾。据称,人类对作用于同类(而非家畜)的人工授精的尝试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澳洲是最早尝试现代化的供体受孕技术的国家之一,其辅助生殖产业技术成熟且历史悠久,更凸显出该产业长期缺乏合理监管之荒唐。而澳洲存在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普遍性。
书中提到的一名通过供体受孕出生者的经历让人印象深刻:乔伊成年后才发现自己身世的真相,而且其生物学父亲是为自己的父母治疗生育问题的医生。这名医生在从业生涯中经常秘密地使用自己的精子,至少创造了75个后代。乔伊痛呼:
“我不是爱的产物,我是谎言和商业化的产物。”
在创造“新人类”的过程中,辅助生殖机构以“帮助家庭”的名义将生命商品化,漠视人类想要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的最基本的权利。医生、委托父母、大企业等当事方都是生殖技术的受益者,唯一受害
|
| 內容簡介: |
萨拉?丁格尔在27岁时突然得知自己是通过捐赠精子出生的,自己与父亲并没有血缘关系。萨拉想要知道自己的来历,身为调查记者的她运用专业技能,开始寻找生父。
这场“寻父之旅”长达十年,她查阅医院记录、追踪每一条线索,一路上的发现令她震惊:妇女因接受携带病毒的精子而死亡;医生使用自己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委托父母毫不知情;医院的记录经常被销毁,全球数十万通过供体受孕出生的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谁;同一捐赠人的精子被大量使用,潜在的同父兄弟姐妹的数量远超想象,意外乱伦绝非危言耸听……
辅助生殖行业方兴未艾、风靡全球,却始终缺乏有效的监管。生殖医疗的道德伦理困境,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
| 關於作者: |
萨拉?丁格尔丨Sarah Dingle
1983年出生于悉尼,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调查记者和主持人,参与制作广播与电视的时事新闻和纪录片等。
丁格尔两次获有“澳洲普利策奖”之称的沃克利奖。她关于妇女儿童遭受暴力的报道获沃克利基金会“我们的观察”奖。她还曾获联合国媒体和平奖、无声媒体奖和澳大利亚教育专家协会媒体奖。她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010年的安德鲁?奥勒学者。
|
| 內容試閱:
|
【前言/序言】:
序言
那天是复活节。一个周六的晚上,我给她带了花,我们坐在距离牛津街几米远的一家越南餐馆里。
27岁的我模糊地意识到时间不再是无限的。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不想很快要孩子。但我也不想在埋头工作时错失其他的选择。我母亲并不总是我寻求建议的第一个对象,但她的人生经验比我多。她生育了我。
“妈妈,我知道你生我时挺高龄的,”我小心翼翼地说,“那你怀我时有什么困难吗?”
她的眼神闪烁。我母亲60多岁了。她是马来西亚华人,留着短短的花白头发。
“为什么问这个,莎拉?”
“因为,”我解释说,并意识到这是我们之间一个不同寻常的私人问题,“因为我不确定我现在是否想要孩子,还是根本不想要,我想知道这事儿能拖到什么时候。如果有个最后期限的话,我有必要知道。”(我说话的方式真不愧是个记者。)
她在座位上动了动。“也许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好时候。”她耸耸肩,“不过,你爸爸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什么?
“你在开玩笑,对吗?”我说。
“没有。我们……我们一直怀不上,最后发现是你爸爸的问题。所以我们借助了捐精者。”
什么?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妈妈——是玩笑吧?”
“不,不是。”
片刻沉寂之后——
“但唯一的区别,”她迅速开口,一口气说完她要说的话,“对你来说,唯一的不同只有你的病史。只需要弄清你的病史就行了。因为你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他爱你如己出。你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父亲了。他是你最棒的父亲。”
我母亲现在显得很焦虑。她说:“这没有改变什么,不是吗,莎拉?”
我感觉房间里的气压下降了。灯光和墙壁都变得很黄,周遭的声音也消失了。我的大脑回响着她刚刚告诉我的事情,拒绝作出反应。
就在这一停顿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当你是一名记者时,你很难完全置身其中:某个外在的自我总是站在远处,观察着,记录着。因此,尽管处于震惊之中,我还是自动捕捉到了谈话中力量的流动。
这是她放下防备的时刻。她其实并不是在问我。她是在寻求安慰。而且她需要马上听到。
我想尖叫,想扯掉桌布,想砸东西,想去洗手间大哭一场。
“不,”我说,“没什么区别。”
这就是我得知自己是通过供体受孕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感受:你对整件事情的感受得排在最后。
【在线试读】:第六章(节选)
重要的不仅是要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还有一种基本需求是了解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所有的兄弟姐妹。这可能是一项比看起来更艰巨的任务。
如今,澳大利亚已尝试限制供体受孕所诞生兄弟姐妹的数量。但这些法律限制只存在于全国8个州和领地中那4个有生育行业法律的州。
而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很多。
据估计,1982年澳大利亚约有1万名15岁以下的儿童是通过供体人工授精出生的。(这还没算上1982年15岁以上的此类人群的人数。)2010年的参议院调查报告称:“据估计,澳大利亚有超过6万人是由供体受孕者所生。”8
这是10多年前的数据。现在也许有8万。也许有10万。也许更多。而就人口而言,澳大利亚还只是个小国。
我接触过数百名澳大利亚各地通过供体受孕出生的人以及数百名海外的此类人士。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自信地说,他们知道自己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谁。他们中有些人有几十个兄弟姐妹。有的有上百个。想想看。想想这其中的恐怖与艰辛。如果你不知道谁是你的兄弟姐妹,你怎么知道你是否曾和他们中的一个甚至多个接过吻?你是否曾和他们中的一个甚至多个上过床?你是否和他们有过孩子?
但是,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兄弟姐妹,以至于乱伦成为实实在在的风险呢?很简单。因为没有人知道,从一个诊所到另一个诊所,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谁是谁的父亲,谁是谁的母亲。
尽管从捐赠者的后代到参议院议员都在呼吁,但澳大利亚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精子、卵子和胚胎捐赠者登记系统。人们本以为,这至少会成为《临床实践和研究中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国家伦理准则》的一个政策问题。根据这份全国性的准则,无论如何,诊所应该从现在起收集所有这些数据。那为什么不要求他们将所有信息发送给一个中央机构呢?
不幸的是,面对这项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建议时,国家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发布的《伦理准则》却效仿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声称:“建立国家登记处超出了本《伦理准则》的职权范围。”
如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捐赠者中央登记系统,就注定会酿成一场社会灾难。捐赠者可以在全国各地不同的诊所多次捐献。此外,诊所还会跨州运送精子。无法统计一个人总共捐了多少次。他们的活动将永远不会被记录在案。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让我们以维多利亚州为例进行研究。维多利亚州的限制条件如下:一名捐赠者的材料只能用来令不超过10名女性生育子女。不是生出10个孩子。而是令10名女性怀孕,她们每人可以生不止一个孩子。假设委托父母——委托女性及其伴侣——希望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同父同母的,那么他们就会一直使用同一位捐赠者。很好,这本身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假设这10位委托女性每人都生2到3个孩子,突然之间,就会出现30个兄弟姐妹。他们互相全都认识吗?不会。因为即使身份信息被记录并保存在中央登记机构,而且这些孩子中有人知道登记机构存在并正式向登记机构表示愿意相互认识,但有这样一个情况:任何委托父母都可能向自己的孩子撒谎,隐瞒他们是通过供体受孕而出生的事实。因此,那些被欺骗的孩子从一开始就不会联系登记机构。
在维多利亚州,这条“不超过10名女性”的规定中还包括捐赠者的现任或前任伴侣,她们也可能与捐赠者生孩子,所以也算在“10名女性”之内。好吧。但如果捐赠者在捐献后与其伴侣分手了呢?然后这位捐赠者又有了一段或两段,或更多段生儿育女的亲密关系呢?突然之间,你面临的可能是12个家庭的兄弟姐妹,而捐赠者自己抚养的孩子会认识其他兄弟姐妹的可能性甚至更难保证。如果捐赠者是跨州捐献呢?如果没有全国性的捐赠者登记机构,会有人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达到了10名女性的上限吗?
我们被告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而,当涉及真相和儿童权利时,每个人都在推卸责任。联邦政府将其推给各州和领地。而各州和领地则推给生育行业。生育专家把责任推给委托父母。而委托父母会做什么,没有人会知道。金钱易手。我们,甚至是大批量的我们,被秘密地制造、出生、成长。国家承认对被收养者有一定程度的照顾和责任,但对像我这样的人却没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