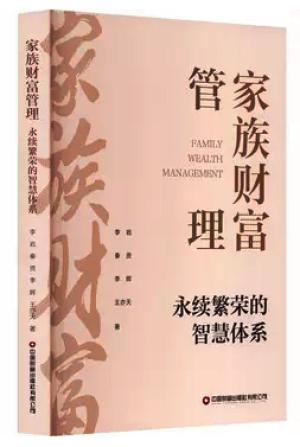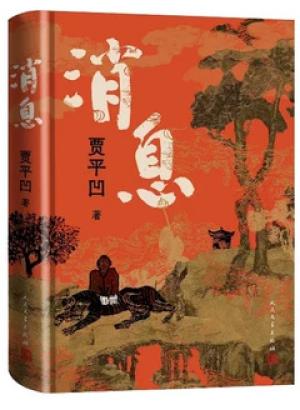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物联网漏洞挖掘与利用:方法、技巧和案例
》
售價:HK$
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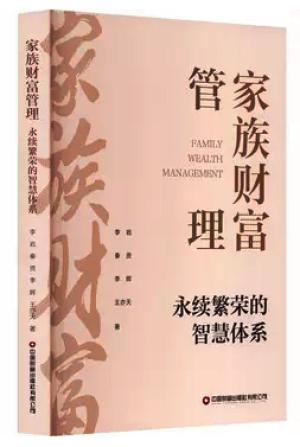
《
家族财富管理:永续繁荣的智慧体
》
售價:HK$
347

《
让我留在你身边升级新版
》
售價:HK$
286

《
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755

《
我在东汉学伤寒 全两册 仲景医案解读《伤寒论》
》
售價:HK$
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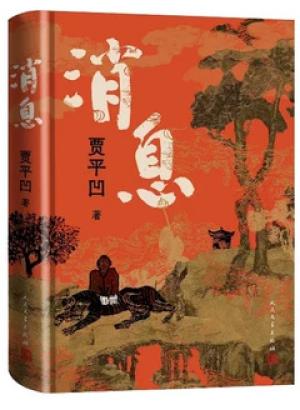
《
消息(贾平凹新书,长篇笔记体小说)
》
售價:HK$
352

《
长安四千年:都城史视角下的王朝兴衰史
》
售價:HK$
857

《
渔樵问对
》
售價:HK$
301
|
| 編輯推薦: |
诗中有画,画中有史,史中有魂
19幅原创国画×9首长诗×5首抒情史诗,构筑一部流淌在黄河岸边的精神史诗
以诗写史,以画传神,在文字与笔墨间探寻文明的根脉
在诗行里触摸历史,在画卷中看见山河
以黄河“几”字湾为背景,书写汉民族与多文明的碰撞与共生
轩辕黄帝、赫连勃勃、李元昊、成吉思汗、李自成……
在“高墙”内外,书写民族融合的壮阔与深邃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诗人远村的长诗集,由九首长诗和五首抒情史诗组成。作品以黄河“几”字湾为地理背景,以高墙为精神象征,展开一场关于民族记忆、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的宏大诗篇;既是对汉民族精神脉络的探寻,也是诗人以个人视角回应集体历史的深情书写。
全书以“高墙”为核心意象,通过富有张力的语言,交织对照自然演变与人类文明,展现历史进程中的冲突与新生。五首抒情史诗分别以轩辕黄帝、赫连勃勃、李元昊、成吉思汗、李自成为主线,对他们在高墙南北叱咤奔腾的历史进行诗意的还原与理性的复述。诗人以“物性与心性交融”的创作理念,在历史纵深与个人体验之间架起桥梁,最终勾勒出一幅多民族相融共生的伟大的史诗画卷。
|
| 關於作者: |
|
远村,陕西延川人,诗人,书画家,资深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1993年被评为全国十佳诗人,2022年被评为年度十佳华语诗人。曾获陕西省首届青年文艺创作奖(1993),第二届柳青文学奖(2010),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奖金驼奖(2020),第七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2022)第七届中国当代诗歌奖创作奖(2024)等多项奖励。出版《浮土与苍生》《画地为天》《向北的高墙》等8部诗集,《错误的房子》等2部散文集,《远村的诗书画》《诗书画》等5部诗书画集。
|
| 目錄:
|
自序/1
浮生不居/1
颂歌无约/7
灵出北地/11
蹈火之巫/15
雷公不惧/19
风后如炬/23
幽走的山鬼/27
河神醒来/31
天地大合/34
轩辕黄帝/37
赫连勃勃/43
李元昊/48
成吉思汗/55
李自成/62
附:评论二则/68
|
| 內容試閱:
|
让有限的语言说出无限的可能性
远 村/
一直以来,我主张诗歌写作诗人一定要在场。无论面对什么题材,什么境遇,什么形制,只要诗人有足够多的时间慢下来,厘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将它们之间存在的客观的逻辑关系,转化为形而上的语言关系,从而有效地说出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本我的那一部分,就可以了。我是要说,诗人从来都不负责全部,只需要说出自己认为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足够了。
就以我不久前完成的长诗《向北的高墙》为例吧。首先,它是一首大诗,大得足以让诗人和阅读者一起心惊肉跳而喘不过气来,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发展史、再造史相互交织而成的一张诗性之网,被我张开。
其次,它才是一首长诗。长诗写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有的选项都指向一个鲜活的对应物,而这个物,它是具有物的客观性和可感性的,诗人只有把物性与心性融会贯通了,才可以抵达更高语境的诗性。这就自然而然引出了一个事关诗歌写作的话题,即如何贯通,如何抵达。
我的长诗《向北的高墙》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迫切付诸行动的一次写作尝试与自我考量。全诗由九首长诗和五首小长诗组成,九首长诗围绕着高墙这个物象,敞开了多民族在黄河流过北方大地形成的“几”字形大 湾里相融共生的伟大的史诗画卷。五首小长诗,分别以轩辕黄帝、赫连勃勃、李元昊、成吉思汗、李自成为主线,对他们在高墙南北叱咤奔腾的历史,进行诗意的还原与理性的复述,以期抵达一直以来,我们难以进入的庞大的华夏民族的心灵史、再造史、成长史的核心版图,进而廓清所谓的学者的主观臆测、地域性误判与想当然的史学假定,让读者最终明白一个朴素而简单的道理,即我们今天所指的宽泛意义上的汉民族究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我能想象,这个一再被大儒们有意省略或淡化的话题一旦经由一个诗人说出,将是一个多么惊人而愉快的事件。这是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诗人必须深潜其中,与他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遗传或裂变的基因发生直接关系,并按照诗歌的逻辑,说出其中极小的那一部分,即使是某一事件某一人物在某一时刻的某一次沉寂与活跃,都要当作诗歌的生成元素,进行必要的挖掘、整理,与进一步重组,最终以有限的语言说出文明无限的可能性。在整个过程中,诗人既是目击者、游历者、替代者,也是发现者和言说者。
当然,想写这部长诗的念头由来已久,只是不到火候,我不便轻易下笔而一拖再拖。直至疫情卷土重来,我被迫居家,才开始写这部长诗。准备工作用了一年多时间,写作用了一年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三年的居家生活,恐怕长诗《向北的高墙》的写作还要推后一些,至少不会这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
现在,就让我说一说这首长诗吧,说说它在我长达四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现实意义,与我以往的诗歌相比,有多大的变化,它们的差异性何在?首先,写作的动因不同。在此之前,我比较在乎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内在感受,写作的侧重点放在诗歌的表现方式和对语 言结构的精心打磨上,仅仅满足于让自我在语言的抚慰下变得放松、坦然、自洽。后来,我就不那么热衷于个人的小抒情了,开始把眼光放在群体或 社会大众普遍存在的隐忍、焦虑、无助等方面,为了能更好地说出这些既是自己的同时也是大家的非必要生活,我选择由内向外转变。其次,写作的方式和方法不同。以前,公务繁忙,我一门心思要写出空灵的简短的句子,而有意回避一个诗人应该持有的对社会的关怀,大概是受了那个年代写作风气的影响吧,写了一些看上去似是而非的东西。当我不得不正面与现实生活交锋时,就觉得过去的写法有些力不从心或出力不讨好。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任意挥霍。我可以静下心来细心研读外国的当代诗歌,也可以认真梳理中国的古典诗歌,我发现二者有一个惊人相似之处,就是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对抒情与叙事,从来都不厚此薄彼,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们在一首诗里和睦共存。就是这个意外发现,促使我的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我对事与史的诗性再现与陈述,能够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态下完成。再次,写作的主题和主体不同。在以往的写作中,我关注的主题,大都是一些生活日常与个人思想的小觉醒、小意思,现在不同了,我极为注重对宏阔的具有浩然气派的人和事进行诗意的史诗性书写,《向北的高墙》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完成的一部作品,它是我几十年诗歌写作的重要收获。与此同时,写作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在诗歌写作中,诗人的在场性是十分重要的,在许多场合,我都会反复强调,诗歌是人与诗合二为一的语言艺术,作为诗歌写作者,在动笔之前务必要提醒自己,一切从我出发。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年轻的时候,自己在诗歌中的位置格外显眼,所写的内容都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总担心读者不能领会自己的言外之意,非要多说上几句,反倒因为把诗歌的空间塞得过满,让读者读过之后,觉得太堵。现在,我已进入中年,自然会淡化个人在诗歌写作中的角色意识,对琐碎的日常,也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并主动去拥抱每一个需要仰望才能看清楚的历史真相。整个过程,体现了我对一个未知世界无尽的向往和敬意。
如果,我再继续深究下去,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差异性被我发掘出来,那样我就会滔滔不绝而成为一个话痨,让人厌烦。截至目前,我没有在这些诗学问题上浪费过太多时间,作为一个诗人,在写作的过程中,能够进行一些适度的自我反省是非常必要的,但一味羁绊于写作之表的是非曲直,肯定是本末倒置了。我对那些年纪轻轻就爆得大名却低调地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大诗人,敬若神明,无论多么匆忙,我都会投以真诚的一瞥,他们对世界的发现与言说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他们一直在无垠的星空闪烁,是否能看见一个后来者在茫茫人海中不辞辛苦地行走,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耗时三年写成的长诗《向北的高墙》,和他们的诗歌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一些词和句子不够完美。也可能我这么快就完成这个巨大的工程,有一些草率,甚或由于自己修行不足,会笔力不逮,而伤了我与诗歌之间的和气。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本来就各有所安,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件物不是抱残守缺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愿我的努力,能让我的诗歌说出被时间一再遮蔽的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