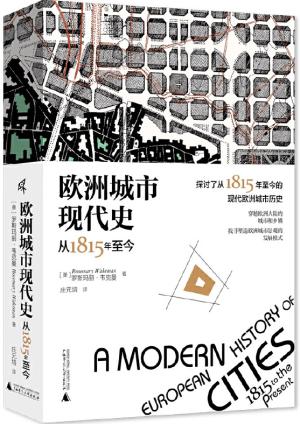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猫和花草的刺绣
》
售價:HK$
250

《
《史记·货殖列传新诠》 一篇学问世故、治身治国的文章;一个经济、教育大学者的经世解读;奇伟文章在乱世
》
售價:HK$
194

《
博物馆里的中国 故宫
》
售價:HK$
398

《
海洋治理与中国的行动(2024)
》
售價:HK$
500

《
阿萨姆茶园:一部环境文化史
》
售價:HK$
500

《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资料编译·第一辑
》
售價:HK$
500

《
绝对历史主义何以可能?--黑格尔主义进路下的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思想研究
》
售價:HK$
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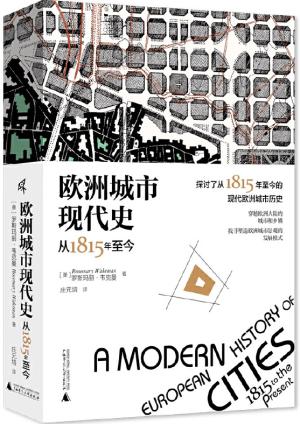
《
新民说·欧洲城市现代史:从 1815 年至今
》
售價:HK$
449
|
| 編輯推薦: |
|
本书通过对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探寻知识分子对土地、农民的文化感情及其精神联系,揭示了作家与乡村、农民之间的文化关系及其文学表达方式。论述因为融入了作者自我体验和感情而特具足以称为“风格标记”的抒情性,是此书的一个亮点。
|
| 內容簡介: |
在中国这个泱泱农业大国中,广大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乡土、大地有着深广的感情。《地之子》通过对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探寻知识分子对土地、农民的文化感情及其精神联系,揭示了作家与乡村、农民之间的文化关系及其文学表达方式。论述因为融入了作者自我体验和感情而特具足以称为“风格标记”的抒情性,是此书的一个亮点。全书视野开阔,将丰富的历史文本纳入考察范围,论析达致“入乎中出乎外”,既有切身的体贴与同情,又注意拉开距离的观照与衡度,体现了论者浸润现当代文学多年的非凡功力。
《地之子》是较早的一本研究乡土文学的名作,2007年在我社初版,广受学界认可和读者欢迎。本次收入“赵园文集”再版。
|
| 關於作者: |
赵园
----------------------------
赵园,1945年生,河南尉氏人。196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师从王瑶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由现当代文学转治明清思想史,著有《艰难的选择》《论小说十家》《北京:城与人》《地之子》《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 《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想象与叙述》《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以及散文集《独语》《红之羽》等。
|
| 目錄:
|
自序
第一章 大地·乡土·荒原
第一节 大地
第二节 乡土
第三节 荒原
第二章 农民与农民文化
第一节 农民
第二节 土地意识与性文化
第三节 在群集中,死亡之际
第三章 “大地”的颜色
第一节 模式及其变易
第二节 色彩斑驳——读作品札记
第三节 方言趣味及其他
第四节 南北东西
第四章 知青作者与知青文学
第一节 知青一代·知青文学
第二节 怀念与回归——“知青文学”主题之一
第三节 知青历史反思——“知青文学”主题之二
第四节 评价难题——“知青文学”主题之三
第五节 知青作者
附录 知青作者的作品及其电影诠释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
| 內容試閱:
|
自序
我是生自土中,
来自田间的,
这大地,我的母亲,
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
——李广田:《地之子》
一
“地之子”,20世纪30年代李广田以之作为诗题;前于他,20年代,台静农已以此题名他的小说集。“地之子”应属“五四”新文学作者创造的表达式。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其有承继自“土地”的精神血脉,“大地之歌”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性吟唱。亦如古代诗人托言田父野老,新诗人在让他们的农民人物倾诉大地之爱时,往往忘记了那份爱原是他们本人的。赫尔曼·黑塞在他著名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称艺术家、诗人为“母性的人”,此种人以大地为故乡,酣眠于母亲的怀抱,是由于他们富于爱和感受能力。“协和广场对出租汽车司机说来不是审美对象,田野对农夫也不是审美对象”,这却又不只受制于爱和感受能力,更因为赖土地为生的农夫不可能对田野持“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因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近代知识分子由于摆脱了与“田野”的基本生存联系,脱出了农夫式的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才便于自命为地之子。朱晓平在他的小说里说,知识分子向天,农民向地。或许只有“向天”者才拥有一块与农民的土地不同的“大地”,赖有超越基本生存关系的对大地的凝视,也才会有知识分子的乡村感知和乡村文化思考。
我在这里不免将“地”的不同语义、语用混淆了。李广田与台静农这两位作者,其所谓“地之子”的“地”,应有一点细微的区别。台静农将其小说集题献韦素园,“地之子”显系概括韦素园沉毅坚实的人格风貌。朱自清在他的长诗《毁灭》的篇末写着:“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里的“土泥”,不消说也非指农民所耕耘之地。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代作者关注农民的命运,对发生于乡村的痛苦怀有深切的悲悯之情,但他们更自居为那个空前广阔的时代之子(“时代儿”)。乡村痛苦,在他们的感觉中,是与所在皆有的人生痛苦连成一片的。
已有的文学史著作一般不将李广田归为“主流作家”,但上述诗作中李广田的血缘宣告,却系于风尚。由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土地革命”,极大地动员了文学。即使未必出诸自觉,未必全系履行组织、社团的决议,自20年代末起,大批诗人与小说家,的确将目光集注在了乡村、农民。乡村的破产、贫困化、革命化,成为覆盖性极大的文学“主题”。在这一过程中,“地之子”的“地”,那较空泛的“大地”(意指“实际”、现实生活等等),代之以乡村的农民的“土地”。不止一位诗人以“母—子”作为其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的象喻形式。艾青《献给乡村的诗》中说,那“生长我的小小的乡村”,“它存在于我的心里,像母亲存在儿子心里”;臧克家《写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说,他的熟悉农民,“象一个孩子清楚母亲身上的哪根汗毛长”。“母—子”,这一关系的重大性,是不待论证的。上述象喻有极严重的性质:那是传统社会里至为庄严的出身、血缘宣告。
“出自……”“来自……”在传统的意义范畴,甚至意味着“隶属”:“子”是属于“母”的,“母”对于“子”享有某种权利。此时人们回头看郭沫若写于1919年的《地球,我的母亲!》,或许会有隔世之感。这种以“地球”为母体,自居于其“人类”的“子”,只能出自那眼界阔大激情喷涌的年代,只能出自“五四”高潮期的时代热情和那一代人曾经有过的世界眼光、广阔浩渺的生存感受。它甚至只能属于郭沫若本人创作中的《女神》时期,年轻诗人隔海遥望祖国之时。此后的历史运动,唤起的只能是极具体的土地感知。生当20世纪,郭沫若也注定了只能是中国之子,时代的儿子。
“母—子”这一种诗式表达,不断受到意识形态加工。其中“母”的语义进一步扩展为“人民”。这种关系式进入知识者的自我意识,其根基之深固,是人所共知的。近些年,较为年轻的一代作者中,张承志提供了最完整(也最诗意)的关于“母—子”的关系描述:草原母亲与“草原义子”(《黑山羊谣》),蒙古族额吉(以及哈萨克族切夏、回族妈妈)与她们的儿子。“我伏在草地上,风摇着牧草拂过我的身躯。我睡着了。”“而当我伏在草原母亲的胸脯上时,我只是呼呼大睡。我后来梦见自己变成了一个三岁的小孩子。”(《GRAFFITI——胡涂乱抹》)张承志痴迷于下述自我想象:露出于地平线的,属于那大地那草原、与那大地草原息息相通的“赤裸的黑污的小孩”。“那小孩摇晃着张开小手奔跑过来,不管不顾地叫喊着。辽阔的草原灼烫又富有弹性,有一支歌,有一种神秘和消息,从那小孩赤裸的双脚传了上来。”(同上)这里不是狭义的土地(乡村、农民)之子,是“人民之子”。
二三十年代同情、悲悯乡民,以其创作“参与”土地革命,以至直接从事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子孙,距乡村都不遥远。后来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更制造了亲近土地、农民的机会。上述关系形式及其诗意表达,是中国经济现实(如“城市化”进展缓慢)与政治历史的双重产物。即使这样,仍然应当如实地说,“地之子”从来都不是所有现代史上知识者的自我意识,因而也不宜于被无条件地作为“五四”新文学与当代文学写乡村、乡民之作的“背景”。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知识者与乡村与农民的关系形式都是极其多样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用以和鲁迅所代表的知识者对比,就举出过所谓“薄海民”,扬抑之间透露了知识者为近现代历史运动所“改造”的信息。至于关系所经历的当代调整,则正是本书将要谈到的。
…………(二—六略,详见书中)
本书拟由乡村文学,探究知识者与乡村、农民间的联系,及这种联系经由审美活动在作品中的呈现,作为我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方面。乡村那片土地是我时时怀念的。
我本人也在我所描述的“知识者”中。
方言趣味
“方言文学”不属于当代创造。“五四”新文学前,已有吴语小说如《海上花列传》,有京白小说如《小额》。名著中,《红楼梦》《儿女英雄传》运用当时北京方言的成就,一向为人称道。“小说”既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汉书·艺文志》),从来是方言口语、民间语、官话、文人腔调等等的仓库,有时期性、地域性及社会各层话语的丰富存储。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现代史上由文人发动的文学运动,其最初所设的对立面(文学思潮、运动通常要以此种设置为自我界定),就有市场极大的市民通俗文学。这种对立强化了初期新文学的精英品性,使之不能不在话语层面,严于与市民通俗文学的区分(以免模糊了运动的性质)。其实运动的发动者如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深知古典白话小说的好处,也未必真的以为当时的通俗小说一无可取(鲁迅供鲁老太太读张恨水的小说,可为佐证)。由此看来,20世纪20年代新小说界的文人腔、知识分子腔,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此外,现代白话文尚无规范,初期作者多受学院式教育,一时无从占有更为丰富的语言材料,也是不难知道的事实。
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众化运动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背景,是一次改造新文学使之适应政治需求的运动。运动中对于初期新文学语言方面的批评虽嫌尖刻,却是切中时弊的。“大众语”的说法,以“知识者”与“大众”的二项对立为自明的前提:大众语更指底层话语。此次运动确也导致了新文学向底层人生的进一步靠近。“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注意,鲁迅这里说的是“活人”,而未指明是某一社会阶层的人),成为作者们自觉的追求。方言以其民间性、口语性以及表情达意的生动性,自然被作为重要的语言材料。大众语运动明白可见的成绩是,30年代到40年代写乡村的小说,较之20年代更有口语的自然,以至当代文学在这一具体方面,也要拜新文学之赐。
1917年文学革命以后,小说的口语化,方言的入(新)文学,是与“新小说”作为艺术形式的成熟同步的。仅由话语层面,也令人看出作者们经验的扩展,他们使叙描具体化的能力。话语作为所写“生活”的质地,其日渐丰富的过程,是新文学疏浚、拓宽其河道的过程,也是新文学的文学语言的美感以至文化涵蕴日趋丰厚的过程。
下面的语言现象颇耐人寻味。现代城市较之乡村更有活跃的语言创造力,实际生活中经常发生着的,是城市语(挟城市优势)向乡村实施文化渗透的过程。我想,即使在城乡壁垒高筑的现代史上,上述过程也应已发生着(“五四”新文学即写了进城农民以及阿Q式的对城市话语的新奇感)。反映在“五四”新文学中的,却更是乡民的口语、方言对知识者(城市人)的吸引。仅此一点上,倒像是乡村文化向城市的渗透或曰“倒流”。写城市的作品,相当长时期内其成就集中于写老旧城市(如老北京),作者于此表达的,更是对古老文化的钟爱,不足以反映城市语言创造的活跃事实。这种情况直到近十几年才有所改变。但除“京味小说”外,“方言趣味”仍然只是乡民语言趣味,城市(除北京外)像是在方言区域之外。这除了因城市五方杂处、知识分子集中外,也因乡村文学口语化、方言化的积久的优势。这种情况或许不会持续得太久。小说对于乡民语言、方言的迷恋,目下已成城乡文化对流中的偶然事件。但你仍然不妨承认,文学中的乡村魅力是可供玩味的象征:乡村即使在经济劣势中仍保有某种文化优势,乡村对于知识者的吸引在一定范围还是不争的事实。方言趣味中或许有保守的文化心态,但文学从来就以此种不趋时,坚持了自己的文化品性、自己的价值立场与审美好尚。即使在将来的某一天,富于方言趣味的当代小说(包括京味小说)被视为语言化石的仓库,它们的价值也将在于以化石的形态保存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语言文化面貌。
这里将话题扯远了,我们仍回到文学史的线索上来。
在“五四”新文学作者那里,方言是作为大众语、民间语、口语被采用的。在当时,写乡村而特重地域特性,特具人文地理意识、趣味,将方言作为地域文化材料的作者,实不多见。你看根据地小说(如《高干大》《种谷记》等),甚至看赵树理的作品,都会有此感。吴组缃写《鸭嘴涝》(后改名《洪水》),本来企图将篇中对话“纯写方言口语”,后来承认“这次的试验碰了钉子。简单的说罢:第一,方言口语中的词儿往往有其严格的窄狭的地方性……第二,就是多数方言口语中的词儿,根本写不出来。……因这些困难,原想把对话写的活泼逼肖些的,结果却弄得似是而非,半死不活,还是不像个话”。有其志而无其力,应属那时文学实践中普遍的困窘。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沙汀写四川,对于人物话语的川味就有良好的感觉与传达能力。这一时期的老舍,其创作中北京方言的运用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当时亦有写京白小说的提倡,只是除老舍外并无相应的实绩罢了。
方言之为“趣味”,在现当代文学中,是积累而成的。
周立波写湖南,就较沈从文之作更有方言趣味。这不关水准,或许除作者气禀外,也缘风气。
“五四”新文学因系建立在“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虽亦强调“不避俗字俗语”(胡适),却必得极端注重现代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即使老舍,其志也在“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因而写北京市民语言力避生僻费解,务求于口语的自然中,兼有北京以外读者易读易晓的明白畅达(倒是当代京味小说以至京味的影视作品不守此种规则)。下文将引述的汪曾祺评赵树理的那句话,说的正是新文学作者共同遵循的原则。马烽等被归为“山药蛋派”的作者,亦奉此为圭臬,用语绝不一味求土。“普遍化”的原则以外,还有提炼的原则。“原味儿”要靠烧制才能出来。上述原则仍为当代一些乡村小说作者所遵行。由柳青、王汶石到路遥等写陕西乡村的作者,笔调毋宁说是相当“文”的,文字极雅驯,写人物话语使用方言尚且节制,叙描用的更是所谓“知识分子调子”。新文学史家承认有“山药蛋”“荷花淀”派,写陕甘宁边区的那批作品却不名一“派”,应与地域色彩尚不鲜明有关——也包括了方言魅力尚未在文学中形成。有关作者对“运动”的兴趣绝对压倒了领略风情的热心。“风情”是赖有悠然闲适的态度,才成其为文学的对象的。
当代,尤其近十几年,较之“五四”新文学,大大发展了“方言趣味”这一种文字趣味。这与“文化热”不无关系,也因“文革”后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鼓励了审美追求。“文字趣味”被公然作为目标,从来是在意义追求相对放松的时期。即使当代(近十几年)的京味小说,比之老舍作品,也更表现出对语言本身的陶醉。
汪曾祺称许赵树理的语言工夫,以为赵树理所写是山西味很醇的普通话,而眼下的不少乡土文学作品,怎么写怎么看,都觉得是城里人在说乡下话;我则以为,有时作品的味道,正在“城里人在说乡下话”。“乡下人”从来更靠“城里人”发现,乡村与城市原是互为界定的。外来者与土著,自有不同的文化兴趣,各有其熟悉与陌生,作者正不妨利用其外来者或土著的便利。方言在土生土长者,会如空气一样,因呼吸其间反不大被留意,通常赖有外来者凭借陌生感将其拔出习常状态,赋予其审美品格。知青作者写乡村,较之土生土长的作者,有时有更浓厚的方言兴趣,也因作者系外来者、城里人,更有对乡气、土气的敏感,对方言的鉴赏以至研究态度。你比较了韩少功的《归去来》与古华的作品,史铁生的《插队的故事》、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与贾平凹、路遥的小说,不难同意我的说法。当代京味小说作者(包括汪曾祺)中,有不止一位外省人。周立波固是湘籍,却是“城里人”。他对湘中土语的敏感,亦未必不是由“城里人”的趣味所致。
这也证明了方言的美感功能并非出诸“天然”,而是被赋予的。文学中的方言是选择的结果。被以为“天然”“本色”的,恰是一种经努力而达的美感境界。方言魅力赖有外来者的发现,是外来者的文化发现的一部分。即使运用中因其“外来”而并不十分地道,也会由于较为自觉的审美意图而更有“创造”性质。与此相关的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方言(亦可谓“大众语”、民间语)在这样的运用中不再为了掩盖作者的知识者身份,倒强调了知识者的主体意向。为汪曾祺所不满的“城里人在说乡下话”,表现在有意的强化、浓化、特征化;方言不只被作为构造作者个人的文学话语的材料,而且被作为文化剖露的材料。方言、乡语在这种运用中,有可能离本来的乡民语言更远,更具知识分子趣味(及城里人趣味)。
当代文学中对方言的鉴赏态度,以方言为地域文化现象的研究态度,构成特殊的文学语言现象,使方言作为语言材料的运用,有前所未有的复杂动机。发展“地域性”的得失,一向众说纷纭,对于方言运用的这一方面的批评已不新鲜。我想,至少在一个时期,对于方言的上述鉴赏与研究态度,有助于文字训练、审美训练。这也因为自新文学兴起至今,流行腔、共用语更是创作界的痼疾。这里所说的“方言趣味”,以及下面将要谈到的“文言趣味”“通俗文学趣味”,得失不论,在我看来,都属于脱出“大路”文调的努力。对文字本身的兴趣,从来都有益于推进创作。
新时期文学中,其方言趣味值得谈论的,是京味小说与写晋、陕乡村的作品。晋、陕文学由根据地时期起经了不少老作家经营,到当代作家笔下,其方言趣味似更引人注目。郑义笔下太行山民的话语,比之赵树理小说人物的,的确更有浓重的乡气,那山地风情在人物以及叙事话语中,也更见凄婉缠绵。“呀呀,美气!真个是‘拉面面、油点点、葱花花、姜片片’!杨万牛呼呼噜噜吃了两大碗,提上鞋,拎起羊鞭便往外走。”(《远村》)那些个叠字,使所写“生活”绵软,平添了几多柔情。
晋、陕文学少北方式的鲁直、粗鄙,或也既因地方风情,也因作者们的方言提炼。黄土地文化的魅力,相当程度来自文学家提取的方言魅力。此种经了提炼的方言作为“质料”,确较别处的方言更富于质感,更有可触摸的泥土之感,对于呈现那黄土地,像是有某种奇妙的“直接性”似的。史铁生生长在北京,写胡同生活并不追求京味的纯粹,却对陕北方言情有独钟。《插队的故事》写乡民,描摹口吻,神情毕见,因方言更见出黄土地的纯良质朴,在这一个城里人那里感印之深。大西北方言魅力在文学中,主要来自那带天真气的纯朴——这种语言感觉,不消说为城里人、知识者所特具。方言对“纯朴”的模仿最令人酸楚,《麦客》(邵振
国)即以此动人。大西北方言的纯朴之美,甚至吸引了张承志,他在写宁夏回族农民的《黄泥小屋》里,为逼近生活的原色,不惜牺牲了他引为骄傲的华丽的长句。
或许可以说,就乡村小说看,写北方乡村者,更富方言趣味。同一时期歌坛“西北风”独盛,“探索片”屡以大西北黄土地为背景,或也多少凭借了文学营造的大西北形象。西北之外,河北作者的方言运用亦成绩可观。汪曾祺说曹乃谦的语言“带有莜麦味,因为他用的是雁北人的叙述方式”。至于刘绍棠,王蒙说:“刘绍棠的成就首推他写的京郊农民的语言。”我研究京味小说,是将刘绍棠的作品有意排开的,因京城内市民与近京乡民的话语,在我看来并非一味。以刘绍棠写大运河的作品论,较之京味诸作,文字少一点机趣雅趣,明亮或又过之——刘绍棠作品的语言,的确使人感到亮度,给人以视觉触觉上的亮滑之感。乡民——又是燕赵之地的乡民——比之市民,口语自然少一点曲折,多一点亢爽之气,声音意象与“气质”均有不同,溜滑脆爽处或又近之。这明亮而带着脆响儿的乡语,自不会有掩映之美,不便写幽渺曲折的情致,其涂染出的,是北方那干燥清爽的乡村世界。刘绍棠得力于“生活”的熟,似无所用其深思,即有浓烈的乡俗趣味。民间文化、俗文化趣味浓到了十分,那文字亦是一种“文化”。无论文野、无论审美品位的高低,都值得研究。
我却由这里察觉了外来者与土生土长者方言材料运用中的另一种不同。刘绍棠(贾平凹亦然)不对乡民口语之“土”加意强调,他们更熟于运用乡间“成语”、俗谚等,用到极熟时令人忘其为“方言”。这是别一种方言趣味。对乡间“成语”(经了提炼而成“共用”的乡民俗语)的熟稔自非久居乡村者不能及。有关作者叙述语风的紧凑,也因诸种语言材料的并用而无间隙(人物语言与叙事语言有时亦无间隙)。叙事风格的不同,其实也与语言材料的掌握与运用有关。
至于张承志在《美文的沙漠》一文中谈到的“母语”,不是指方言,而是指民族语,属于更深奥的语言学课题。这课题即使在张承志,也仍然是未解的。他在《金牧场》中一再写到对蒙古族额吉、哈萨克族老妪,尤其对西海固回族阿訇宗教祈祷的语音感受,在《凝固火焰》(以及《金牧场》)中,写异族伙伴间的交流,极力寻索话语微妙的文化意味——这也可以用来注释新时期一代作者共有的语言文化兴趣。至于用所谓“母语”表达,我由张承志那里,还未看出此种前景。
无论母语还是方言,都并不能保障文学语言上的成功。母语、方言在未经制作、未经“审美赋予”时只能是大众语、(某一地域某一民族的)共用语。张承志早期的《北望长城外》与较后的《黄泥小屋》使用方言,反失了这位作者语言的固有魅力(不过以此种代价证明了一种能力而已),可以作为因特殊的语言材料反成“大路”的例子。张作的魅力,仍在那文人气十足的时见滞重的书面语中,在那些情感含量极重的长句里。这长句、书面语,才更能呈现张承志的个人情境。进一步说,张作的魅力应在那种呈现“难言”的话语努力中。读他的作品,你时时可感作者在极力使难言者可言,使微妙、飘忽朦胧暧昧、形态不定似不可把握的极其个人、内在的意绪呈现于话语。这“难言”与“言说”(且务求痛快淋漓)之间的张力,影响到他的作品的整个文字面貌。
写到这里,有必要申明,方言趣味只是当代乡村小说文字趣味之一种。我已说过,这趣味在多数作者那儿,正是知识者趣味而非乡民趣味、农民文化趣味。这一时期的文学,比之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新文学,比之“十七年”的创作,有更纯粹更浓厚的知识分子趣味,其表现就包括了使用知识者特有的话语形式写乡村,如何士光、贾平凹、张炜(张炜且钟爱所写乡村人物的知识者气质)。这是新时期知识者意识苏醒的文学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