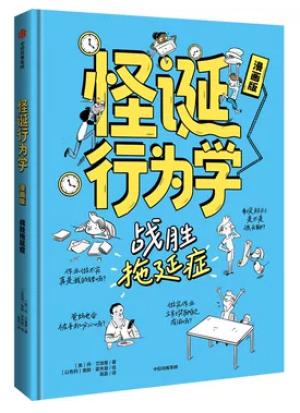新書推薦:

《
HR数智化转型:人机协同与共生
》
售價:NT$
367

《
范怨武讲透中医基础理论(全2册,中医临床医生范怨武历经四年精心创作)
》
售價:NT$
5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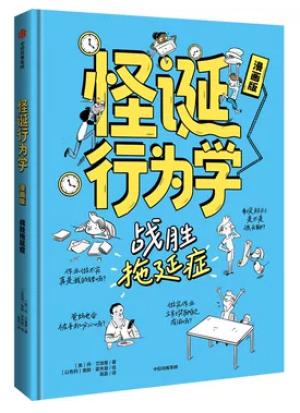
《
怪诞行为学·漫画版——战胜拖延症
》
售價:NT$
194

《
四海资身笔一枝:唐寅的书画人生【全球33家顶级机构珍藏,全景展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艺术世界】
》
售價:NT$
857

《
50岁后的家庭生活:中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家务劳动与孩童照料
》
售價:NT$
653

《
壹卷Yebook——《正义论》导读( 理解《正义论》关于哲学、科学、社会、历史和人类未来的批判性思考
》
售價:NT$
418

《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平装版 全八册)
》
售價:NT$
1520

《
万物皆有时:中世纪的时间与生活
》
售價:NT$
449
|
| 編輯推薦: |
在 19 世纪的法国,一场洞察现代社会的思想探索正展开 ——
这里思想者辈出,用深邃的思考剖析时代命题,而托克维尔正是其中最具预见性的洞察者。
他以对民主的深刻研究闻名,与同时代思想者共同叩问社会走向,既是预见民主潮流的思想先知,也是擅长实地考察的观察家;是跨越国界的思想传播者,更是关注人类命运的思考者。
他以《论美国的民主》为镜,映照民主制度的优劣,在观察中探寻规律,在思考中警示风险。其对民主、平等、自由的思考穿越时空,不仅为后世理解民主提供了范本,更不断引发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深思。
翻开书页,你将看见这位 “民主先知” 如何用思想启迪世界 —— 他的光芒,至今仍在文明长河中闪耀。
|
| 內容簡介: |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其对美国政治的出色洞察力,对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分析而广受赞誉,但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他仍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作为一位写下了一部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分析美国政治的著作的政治学家,一位19世纪法国最富鉴别力的历史学家,一位现代社会学家的先驱,一位曾当选众议员并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务实的政治人物,托克维尔让每个人都可以有所借鉴。然而,要想把所有这些方面都融为一体却并非易事。
这部书信选集提供了一幅更为全面的托克维尔的画像,精选自内容权威、广泛的书信集的法、英译本。
|
| 關於作者: |
著者: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 出身贵族世家,历经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捕,获释后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因而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
译者:黄艳红,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近代史和中世纪史。2011年11月到2012年8月,受“布罗代尔奖学金”资助,在法国人文之家从事博士后研究。著有《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译有《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记忆之场》《历史性的体制》《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等著作十余部。
|
| 目錄:
|
1第一部分青年时代和
北美之旅(1823—1832)1. 致欧仁·斯托菲尔
2. 致路易·德·凯戈莱
3. 致路易·德·凯戈莱
4. 致路易·德·凯戈莱
5. 古斯塔夫·德·博蒙致托克维尔
6. 致欧内斯特·德·夏布罗尔
7. 致欧仁·斯托菲尔
8. 致路易·德·凯戈莱
9. 致欧内斯特·德·夏布罗尔
10. 致夏尔·斯托菲尔
11. 致兄弟伊波利特
12. 致母亲第二部分政治思考,《民主在美国》
和当选众议员(1832—1839)13.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14. 致欧仁·斯托菲尔
15.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16. 致玛丽·莫特莱
17. 致路易·德·凯戈莱
18. 致路易·德·凯戈莱
19. 致路易·德·凯戈莱
20. 致拿骚·威廉·西尼奥尔
21. 致欧仁·斯托菲尔
22. 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23. 致路易·德·凯戈莱
24.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25. 致克劳德弗朗索瓦·德·科塞尔
26. 致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
27. 致欧仁·斯托菲尔
28. 致亨利·里夫
29. 致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
30.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31.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32.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33. 致保罗·克拉默冈
34.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第三部分七月王朝时期的
政治生涯(1839—1847)35. 致保罗·克拉默冈
36. 致亨利·里夫
37.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38. 致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
39. 致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40. 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41. 致让雅克·安培
42. 致皮埃尔保罗·卢瓦耶科拉尔
43. 致保罗·克拉默冈
44.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45.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46.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47.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48. 古斯塔夫·德·博蒙致托克维尔
49.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50.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51. 致保罗·克拉默冈
52. 致拿骚·威廉·西尼奥尔
53. 致路易·德·凯戈莱第四部分从二月革命到路易·
波拿巴当选(1848)54. 致保罗·克拉默冈
55. 致拿骚·威廉·西尼奥尔
56.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57. 致拉德诺爵士
58. 致保罗·克拉默冈
59. 致欧仁·斯托菲尔
60.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61. 致保罗·克拉默冈第五部分路易·拿破仑和第二帝国
的诞生(1849—1851)62.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63.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64.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65. 致阿图尔·德·戈比诺
66.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67. 致哈丽亚特·格罗特
68. 致路易·德·凯戈莱
69.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70. 致《伦敦时报》编辑第六部分从第二帝国初期到《旧制度》
的发表(1852—1856)71. 致亨利·里夫
72.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73.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74. 致弗朗西斯科·德·科塞尔
75. 致皮埃尔·弗里斯隆
76. 致阿图尔·德·戈比诺
77. 致阿道夫·德·希尔古尔
78. 致阿图尔·德·戈比诺
79.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80.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81. 致西奥多·西奇威克
82.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83.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84. 致克劳德弗朗索瓦·德·科塞尔
85.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86.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87. 致索菲亚·斯维金娜
88.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89.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第七部分最后的岁月(1856—1859)90. 致索菲亚·斯维金娜
91. 致欧仁妮·德·格朗塞
92. 致阿图尔·德·戈比诺
93. 致索菲亚·斯维金娜
94. 致于贝尔·德·托克维尔
95.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96. 致弗朗西斯科·德·科塞尔
97. 致路易·德·凯戈莱
98. 致哈瑟顿爵士
99. 致亨利·里夫
100.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101. 致皮埃尔·弗里斯隆
102. 致路易·德·凯戈莱
103. 致阿图尔·德·戈比诺
104. 致古斯塔夫·德·博蒙
105. 致索菲亚·斯维金娜
附录一托克维尔的通信者简介
附录二托克维尔年表
附录三本选集书信来源
|
| 內容試閱:
|
编译前言:托克维尔的焦虑
托克维尔(1805—1859)生活于一个没有根基和充满动荡的世界中。自从16岁阅读启蒙作品遭遇了信仰的颠覆之后,终生寻求确定性而不得,一直被怀疑所困扰,而怀疑被他视为人生最大的不幸之一。在他所处的时代,法国在革命和专制中挣扎,他为自己民族的自由而奋斗,却最终发现这个民族“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1853年9月23日致皮埃尔·弗里斯隆,第75封信)。托克维尔喜欢用大海来比喻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身处一个咆哮的、但没有海岸的海洋;至少,这个海岸是如此遥远、如此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第59封信,参第7封信)。在这样一个“天空不再给予希望,大地不再给予尊严”(贡斯当语)的世界,自我对每个人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托克维尔在26岁时就对此有深深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我了解最少的存在莫过于我自己了。我对于我自己不断地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1831年10月18日致欧仁·斯托菲尔的信)这并非一个缺乏自信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怀疑,而是延续了一生的挑战。去世前两年,在1857年2月26日给斯维金娜夫人的信中,他写道:“每当我仔细打量自己时,我找不到一丝的欢乐……我们有理由说,人从来不能自知:人们经常弄不明白那些支配自己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说法是正确的。”(第105封信)在一个承认自我的权利和价值的时代,自我成了最大的问题;而对于一个辩护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何面对这个成为问题的自我可能是最大的挑战了。
如果天空远离大地,上帝从世界中退隐,那么个体将承担自我的命运,这是启蒙运动的应许和民主社会的期待。而等级制社会的瓦解使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断淡化,个体也获得独立的可能,于是“他们习惯于自视独立,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全部命运在他们自己的手中”。然而,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发现美国人“身处幸福之中而焦虑不安”,焦虑(inquiétude)在他看来是美国人显著的性格特征之一。平等虽然使个体在形式上获得不断改善自己状况的可能,但平等将个体置于与所有人的竞争之中,结果个体不得不忍受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和现实的挫败之间的反差,陷入焦虑和嫉妒之中。民主充分暴露了个体的软弱,自我的独立非但不是自由,而往往成为奴役。贡斯当笔下的那个现代自我的典型阿道尔夫在摆脱了成为捆绑的情人之后获得了独立,但同时却发现:“以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多的眼泪重新获得的自由,对他竟毫无用处。”民主的个体在砸碎了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枷锁之后,发现他们获得的自由竟可能是新的枷锁。自由这个现代社会的最高神祇与罗马人的雅努斯一样,还有另外一副面孔。这个现代雅努斯成为《民主在美国》所勾勒的现代人的肖像。然而托克维尔对美国人或者民主心灵的深刻揭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洞察力。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圣伯夫对托克维尔的评价:他在读书之前就已经开始思考。这一评价并非夸张之辞,然而托克维尔如何去思考?他的思考资源在哪里呢?他的书信给了我们答案:他的观察和思考资源就是他自己,他自己身上的雅努斯使他能更深刻地理解现代人的雅努斯。
现代性曙光初现时,蒙田开启了自我的探究。蒙田很敏锐地认识到现代是个体的时代,那么只要对自己进行剖析,就可以理解人类了。因此,他声称他的散文是以自己为材料的,他的自我书写并非是为了像奥古斯丁那样在忏悔中发现自我并否定自我,而是把自我当成研究对象,让自己和别人更了解他本人,也让别人通过他的自我去了解他们自己的自我。托克维尔的书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蒙田式的散文,在和他人的书信往来中呈现自我,也让他所处的时代在他的自我当中展露出来。托克维尔热爱写信,所以已经出版的17卷托克维尔全集中书信占了一半以上。事实上这种对书信以及日记的热爱是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知识界和文学界的某种风尚,也表明这一时期人们拷问自我的迫切。
托克维尔终身被焦虑所困扰。他的焦虑在他看来是无法治愈的“漫长的疾病”,因为焦虑成为他的个人气质的一部分,是他的自我的构成因素。在托克维尔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他常常试图向亲人和好友描述这种在他看来无法言传的焦虑。它对他来说是“无端的折磨,徒劳的躁动,巨大的痛苦”(第39封信),既给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托克维尔非常理性地观察和描述自己这种非理性的不幸,这让他更为绝望,因为他的理性对于他的焦虑无能为力:“我有非常冷静的头脑和爱推理的甚至善于计算的心智;但是,在这旁边却存在着强烈的激情,这些激情将我裹挟而去却不能说服我,驯服我的意志却听任我的理性自由自在。一句话,我很清晰地看到善,但每天却做那些恶的事情。”这让人想起《新约·罗马书》第7章保罗的内心交战:“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罗马书》7:15)托克维尔虽然并非基督徒,但他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仍然不断地回到基督教的视野当中。焦虑对人的控制像罪对人的捆绑一样是人的理性所无能为力的。在托克维尔看来,理性充其量只是一个囚笼,即便可以阻止他采取行动,却不能让他不在铁窗后咬牙切齿(第42封信)。这里我们已经依稀看到了以后为韦伯所阐发的铁笼主题。
这个充满焦虑的托克维尔似乎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那是一个饱含激情而又充满理性的思考者,在他的作品中理性和激情构成了优美的和谐。然而,思想当中理性与激情的和谐,同生活当中这两者的冲突并不构成矛盾,而是生命的不同层面。并且,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思想也可能成为焦虑的原因。这首先是因为思想本身的艰难,但托克维尔并不隐瞒自己从事思考和写作背后的那些并不那么伟大的动机。在给斯维金娜夫人的信中,托克维尔不惮于从“最难看”的一点来坦白他的焦虑的原因:“您相信这种精神上的不安主要难道不是源于终生激励我的对于成就、影响和声望的激情吗?这一激情有时能促成伟大的事物,但它本身显然并不伟大。这是作家们通常有的一点坏毛病。对此我也像别人一样无法逃避。”(第105封信)1840年《民主在美国》第2卷的出版并没有像第1卷那样取得成功,托克维尔对评论界的沉默感到沮丧,在给卢瓦耶—科拉尔的信中(第38封信)中表达了对自己的作品的价值的怀疑。这并非仅仅像评论者认为的那样说明托克维尔缺乏自信,而是托克维尔对于自己不能取得期待的成功而感到失望。托克维尔并没有否定伟大事业背后的个体对不朽和荣耀的追求,他甚至希望民主时代的软弱个体能有这样一种雄心和骄傲,但是他知道这种个体的骄傲作为一种自我的私欲,本身不是那么崇高的,不是他所推崇的那种忘我的美德。不过,托克维尔并非要对个体的骄傲进行道德审判,而是要指出这种骄傲会因为其挫败成为个体的重负,特别是在一个承认个体的骄傲和尊严的民主时代。
然而,托克维尔的焦虑更多的并非这样一种追求成功而不得所带来的苦恼。他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一个有理智的人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他自己决不是这样一个理智的人,因为他要在一个平庸的时代追求伟大,在民主的时代梦想贵族时代的德性。寻求伟大的托克维尔的焦虑不同于追求福利而不得的民主个体的焦虑。《民主在美国》通篇是对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比较,时时浮现出对贵族制的伟大的怀念,虽然他强调民主制远比贵族制公正。他一直被一种追求伟大的激情所支配:“神已赐给我对于伟大行为和伟大美德的天然爱好,然而当这种伟大事物总是在我眼前飘荡而我却一直无法把握时,我很失望;我的灵魂希望生活于一种理想的创造当中,而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时代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令人悲哀。”(第105封信)生不逢时而不能像先辈一样在伟大的事业中呈现生命的意义,这是托克维尔的焦虑所在。托克维尔所追求的伟大是一种自由的政治行动,它并非为了谋求利益——他的书信中常常表现出对利益的鄙视,更是彰显一种如其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所表现出来的自我牺牲的公共精神和刚毅的美德(1838年4月22日致博蒙,第32封信)。因此,托克维尔总是把自由和伟大关联起来,自由的意义在于通向伟大。然而,民主时代的人们热爱自由不过是因为自由可以使他们追逐自己的利益,而如果专制能够更好地保证利益,他们宁愿放弃自由。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人特别是资产者滥用自由竞逐私利;而第二帝国时期,法国人为了他们的私利而放弃了自由。因此,托克维尔悲痛地看到他和他的时代格格不入。平庸的日常生活令他厌倦和焦虑,“回到日常的习惯,生活的单一让我非常厌倦;我感到被一种不可言状的、内心的焦虑所抓住”(1831年10月18日致欧仁·斯托菲尔)。只有“重大的事物和崇高的情感”才能让他平静。托克维尔以政治人为自己的理想,致力于在政治上成就大业,因为只有政治行动带来的激情才能平息他的焦虑。然而,他不幸生活在一个政治为名利所充斥的时代,他自己的信念和气质与之背道而驰。事实上从政不久,托克维尔就悲哀地发现自己在当时法国的议会政治乃至政治世界中找不到位置(第42封信),政治行动中的无力感常常使他陷于一种深深的忧郁和焦虑。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一直受到他的选民的支持,选民的忠诚是他在政治的荒漠中的一小块绿洲。他长时间担任家乡地区拉芒什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他一直珍惜这个职位,因为在其中他能够为他的家乡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不过,这些都只是绿洲罢了,仅仅是失意中的安慰,他不得不在骄阳尘土中继续探险(1842年10月6日给斯托菲尔的信)。然而,这些探险只是一次次地告诉他,他没有力量在一个不追求伟大的时代实现伟大,他只能无奈地面对达不到目标的失落,“我跌落得太低,因为我期待的太高”(1837年5月26日致博蒙信)。
然而,即使托克维尔获得了他期待的成功,在他渴望的伟大事业中大展身手,他的焦虑就一定平息了吗?他自己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他的焦虑有更深的根源:“我的生活阅历足以让自己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美好的事物,它带来的享受能完全吸引我,让我满足。我达到了在开始我的职业时我没有预期的高度。这并没有给予我幸福。我的想象力很容易达到人类崇高的顶点,当它把我带到那里时,那光彩炫目的体验并不能阻止我感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就是即便达到了顶点,我仍然像今天一样感到强烈的痛苦……驱动灵魂的是不同的东西,但灵魂还是同一个——这颗焦虑而不知餍足的灵魂,它蔑视世上一切好的事物(tous les biens),但它又永远渴求被激励起来去抓住这些好的事物,以便逃避那痛苦的麻木,而一旦灵魂依赖于自己,它就会体验到这种麻木感。真是悲伤的故事。它差不多是所有人的故事,但有些人比其他人经历得多,而我自己则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要多。对于这种没有止境的欲望,你会对我说只有一样事物对它们来说是合适的并且能带来某种放松:这就是另一个世界的无限视野。但我却没有这一资源。这并非是因为——感谢上帝——我是物质主义者或反基督教者。但是,我相信的普遍真理以一种非常抽象的形式、穿越如此厚重的云雾呈现在我的心灵中,以至于我的灵魂不能把它们当成某种立场。无疑这是巨大的不幸,但在我看来,至少从人的角度来说,它不可能被医治;因为我多次想尝试去对付它,但都无功而返。”(1840年11月2日致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第39封信)自从托克维尔16岁失去信仰之后,他的焦虑就成了存在意义上的问题,因为他的灵魂失去了根基和方向,生命当中缺乏一种根本的确定性。这颗灵魂在世界中上下求索却无法找到安息之处,人世的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能在根本上满足它。托克维尔对人类存在的种种问题感到忧心,试图去探求人生的奥秘但却总是陷入不确定当中(第105封信)。托克维尔一直试图重建信仰、寻回生命可以立足的确定性根基,对人类生存的问题寻求确定的答案,然而他一直没有成功。他在1837年12月26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在一切事情上我想追求一种理想,但它总是不断后退。我渴望一种绝对、一种完整,但它们并不存在。”他对信仰有一些抽象的普遍性观念,如上帝的存在及其绝对正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及对善恶的赏罚等,但除此之外,他无法形成或接受其他的信念。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他不得不承受怀疑的折磨,一直把怀疑视为世界上最让人不能承受的恶之一,年轻时将其置于疾病和死亡之后(第10封信),而到了中年则认为它比死亡更糟糕,比疾病更恶劣(1850年8月致科塞尔的信)。面对怀疑,人自身的无能为力彰显无遗:在晚年(1858年)给他的哲学家朋友布希泰的信中对人的状况的描述和帕斯卡如出一辙:“(人)被赋予足够的光以向他展示他的状况的悲惨,却没有足够的光来改变它。”
托克维尔认为他的焦虑是“所有人的故事”,是现代人的处境。不过,托克维尔并没有因此陷入绝望。1831年还只有26岁时,虽然还不知道未来的道路,他在给夏尔·斯托菲尔的信中表明,他对生存的境况已经进行了艰难而透彻的思考,承认焦虑和怀疑是人的境遇也是自己存在的一部分,但仍然因此而勇敢地面对人生并探求人生的意义。他认为对完美的幸福和绝对的真理的追求是幼稚的,是一种虚弱的、不够男子气的情感。如果对缺乏完美和绝对的人生感到失望,那是“对作为人而灰心失望,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本质中最不可改变的法则之一”。“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也不是很坏,而是某种由好坏两方面所混合的中等事物……生活既非享乐也非受苦;它是我们承担的一项严肃事务,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好地完成它。”(第10封信)以这样一种坚韧的斯多亚态度去面对人生,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勇敢地面对痛苦和平庸,成为托克维尔一贯的人生态度。他后来成为作家、思想家、政治人物、历史学家,经历了成功,更遭遇了失败,但他的思想、追求和人生态度始终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一贯和坚定。大革命之后法国政界频频改朝换代,社会动荡不定,改变立场、转换阵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以至于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不动摇(linflexibilité)、坚定(constance)成为受人钦佩的德性。我们在托克维尔身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德性,虽然他一直在议会政治中处于边缘,无法进行真正的政治行动,但他始终秉持自己的道德操守。他接受了一度被他视为精神导师的科拉尔的教导,一个人不能指望在政治中发现高贵,而是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使政治高贵,正如科拉尔所言:“今天议会代表的生活是一种粗俗的生活……别指望在那里找到光荣,应当把光荣带给它。”1855年冬天,这时托克维尔早已接受了他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败而退出政界,他在雪后的贡比涅森林中散步,回首差不多25年前他和博蒙在田纳西的森林中散步的情形,对岁月的流逝充满感伤,然而他对自己过去的选择和奋斗并不后悔。在给博蒙的信中写道:“当我回顾这些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重新开始这四分之一世纪,我想做的事与我已经做的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于是我又感到宽慰。也许我会努力改正细节上的错误,防止一些明显的蠢行,但整体而言,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甚至我的行为,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对于人的总体看法很少变化。关于年轻时的幻想和成年时的幻灭,人们谈论得很多。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人类的缺陷和弱点从一开始就映入我的眼中,至于当时我所发现的人的优良品质,我不能说此后我没有遇到近似的东西;这段短暂的回顾使我心绪更好,而当我想起那个与我一起在孟菲斯捕猎鹦鹉的朋友(指博蒙——译者注),直到今天他依然是我的知己,而时间只是使我们之间当时存在的信任和友谊更加紧密,这更让我焕发生气。这想法让我觉得比考虑所有其他事情都更让人快乐。”(第82封信)如果把这封信与上述那封25年前给斯托菲尔的信加以比较,我们发现,托克维尔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焦虑和怀疑的人,也是一个在道德上坚定、忠诚于自己的原则的人。
正如这封给博蒙的信中所体现的,这种忠诚特别体现在友谊当中。与蒙田用旁征博引来为自我做注脚不同,托克维尔直抒胸臆,让自我的沉重、内在的冲突在对朋友的倾诉中完全暴露出来。书信中的自我并非散文、日记和回忆录中的独白式的自我,而是和他人分担的自我、在友谊中敞开的自我。通过书信来表达自我,托克维尔事实上是在借助友谊来面对孤独的自我。与他的人生态度的坚定一样,托克维尔对友谊的执着是不同寻常的,他同儿时的伙伴如凯戈莱和中学时的同学如欧仁·斯托菲尔一直终身保持亲密的关系,即便后来在人生道路和政治立场上他们往往分道扬镳。这些儿时的朋友在他心目中有某种特殊的地位,除了他妻子玛丽以及他的兄弟以外,似乎只有他们被他以“你”相称,而即便是后来和他一道出生入死的博蒙,他也始终以“您”相称。当然,这种称呼上的差异,并不就简单地对应为友谊深浅之别。他和博蒙的友谊堪称典范,尤其是因为他们曾一度龃龉不和但最终捐弃前嫌重归于好(第47—49封信)。经历过艰险的共同游历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的考验的友谊是伟大的,因此托克维尔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只能向这位朋友发出求告:“请您来这里。”在死亡面前,走向生命尽头、孤立无援的托克维尔毫不犹豫地向朋友敞开自己的无助,正如以前他毫无遮掩地袒露自己的软弱、怀疑和焦虑。还在23岁时,他就告诉凯戈莱只有友谊在这个世界上是可靠和持久的——当然后来在结婚后他还加上了夫妻之情。在政治的艰苦斗争当中,托克维尔发现他所珍视的价值和理想并不为他的时代所理解和接受,在政治的喧嚣当中他却感到一种比荒野中的孤单还要难以忍受的精神的孤独,“孤独总让我害怕,要想快乐,甚至要想得到安宁,我总需要——这并不总是明智的——身边有一些帮助,总希望能依靠我的一些同伴的同情。那人独居不好《圣经·创世记》2:18。:这句深刻的话尤其适用于我”(1856年1月7日致索菲亚·斯维金娜,第87封信)。托克维尔理解的友谊首先是一种信任和尊敬的情感,能够体贴和关心彼此的软弱,也能够像对方敞开自己的软弱。对于少年和年轻时的朋友,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后来认识的一些长者,托克维尔也强调自己对他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他们对他的善意和理解以及他对他们尊敬和信任基础上的。其次,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这种友谊还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在于理解和接纳对方的“善”或品性,并以自己的善和品性来加以回应,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回报的友爱则包含着选择,而选择出于一种品质”。真正的友谊要求相互的回应和责任。奥古斯丁指出,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对方的爱而没有回报,这表明事实上他没有真正拥有所得到的爱。友谊也一样,如果接受友谊而没有回应也意味着没有拥有友谊。托克维尔在信中或者以坦诚倾诉或者以激励劝勉来回报朋友的友谊,正如他在给斯维金娜的信中写到的那样:“您的信中对我有一种亲切感,我希望能配得上这种亲切,因为一个像您这样的人的友谊是要求做出回应的。它不仅要求人们心怀感激,而且要人们有所行动来表明配得上这一友谊。”(第87封信)托克维尔希望“自己在大社会以外形成一个理想的小城邦,那里居住着我热爱和尊敬的人,我希望在那里生活”(第29封信)。通过他的书信我们可以领略一下他“理想的小城邦”,那里的少数居民围绕着一些严肃的关乎人生、信仰和政治的重要问题在进行讨论;托克维尔常常与他的朋友们探讨他的作品,与他们分享他写作的动机、意图、构思、困惑和主题等等,倾听他们批评和意见。在托克维尔那里,思想构成友谊的源泉,而友谊也成为思想的伙伴。
托克维尔以道德和友谊来面对焦虑,但并没有克服焦虑。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无论在他的肖像还是在他的文字中都能感受到一种忧郁。他没有逃避自己的命运,面对内心的紧张而坚守对德性和伟大的追求,并不惜承担由这一追求带来的更大的紧张。《民主在美国》的写作也是托克维尔理解和面对其焦虑的一种方式。他通过处理民主时代的人的焦虑来思考自己的焦虑。我们已经提到,他从自己对成功的渴望而感到的焦虑当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现代人关注自我利益和成功而带来的焦虑。现代人沉溺于自我的焦虑而遗忘了对伟大和德性的追求,因此民主时代的平庸和堕落会让追求德性和伟大的人感到焦虑;而现代社会中上帝的不在场让现代人陷于对生命意义的焦虑之中。民主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沉溺于第一种焦虑之中甚至不会再产生后两种焦虑。因此,托克维尔首先致力于说明第一种焦虑可能导致的平庸、堕落和罪恶等种种危险,而试图借助于通过政治自由和宗教来培育道德和友谊。如果在一个民族实现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良好的民情成为政治的基础,公民的友谊成为城邦的纽带,那么这第一种焦虑是可以克服,或至少是可以被缓解的。至于对伟大和对生命意义的焦虑,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取决于人们自己如何在政治、友谊和宗教中去面对了。一个没有能够拥有确定信仰的人竭力强调宗教对于现代心灵的意义,并非一个有隐微教导的人提倡一种显白的教导,而是常常对帕斯卡感佩不已的托克维尔对人生的某种深切理解。不过托克维尔远没有对人产生厌倦,他一直拒绝戈比诺宿命论的种族主义,而是相信“如果想要从别人和自己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蔑视人”(第32封信)。根本上,托克维尔是一个有宗教情怀而敢于直面人生之不幸的人文主义者。本书的内容和结构参考托克维尔书信选集的英文本(Alexis de Tocqueville, Selected letter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ed. Roger Boesche, trans. James Toup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翻译时则依据托克维尔的法文书信选集(Alexis de Tocqueville, Lettres Choisies·Souvenirs, ed. Franoise Mélonio, Laurence Guellec, Gallimard 2003)——由于该选集有一千多页,无法全部译出。最后由编者根据法文和英文本校对。本书收录的最后一封信(托克维尔1857年2月26日致索菲亚·斯维金娜)是英文本所没有收录的,但对于理解托克维尔非常重要,因此从上述法文本译出。书信译文中的注释,为中文译校者添加的标为译注或校注,未有任何说明或标为法文版注的为法文版注释。本书的附录均出自英译本。译文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