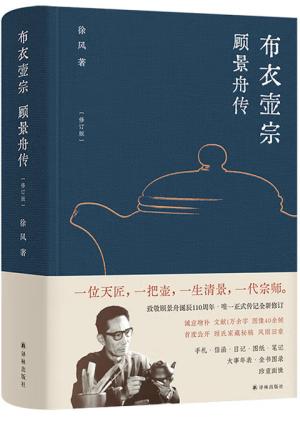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财富的秘密:一部瑞士经济发展史
》
售價:NT$
245

《
猎头游戏(尤·奈斯博邪恶又疯狂的独立作 当昆汀遇上科恩兄弟 改编电影创造挪威票房奇迹)
》
售價:NT$
254

《
全彩速学低压电气电路
》
售價:NT$
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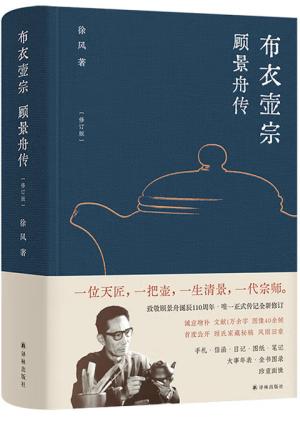
《
布衣壶宗:顾景舟传 一位天匠,一把壶,一生清景,一代宗师。致敬顾景舟诞辰110周年 顾景舟WEI一正
》
售價:NT$
551

《
非虚构写作课: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
》
售價:NT$
250

《
治城与治国:组织研究视角下的中国城市治理
》
售價:NT$
551

《
张爱玲 我的后半生 纪念张爱玲逝世30周年
》
售價:NT$
352

《
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
》
售價:NT$
454
|
| 編輯推薦: |
|
从篇幅上看《伊凡·伊里奇之死》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并不起眼,然而在思想方面却有着和他的三大长篇不相上下的重要地位。伊凡·伊里奇是一个典型人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普世的人物,他的身份如此不上不下,以至于他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经历又是如此普通甚至庸俗,以至于我常常会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他由生至死的过程如此突如其来又如此漫长,仿佛印证着那句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个先到来;他对生命意义的诘问和对死亡的恐惧如此真实,几乎写出了所有人对人生产生怀疑时那种焦虑、痛不欲生的真实境况。这并非是我第一次读这本书,然而随着生命的流逝,我愈发在其中发现了惊人的力量,人生中顿悟的契机可遇不可求,而这部作品足以让人的灵魂发生震颤。
|
| 內容簡介: |
|
《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短篇小说,通过对伊凡·伊里奇死亡的全过程细致白描,发出对人生死意义的终极诘问。伊凡·伊里奇的一生“极为简单、寻常,又极为恐怖”,他一生都过着一种无比自洽的生活,直至因一次微小的意外身染重疾,最终发展为不治之症。随着生命走向终点,他如遭雷击般意识到自己过往的生活“不对头”,他苦苦思索,生命的意义何在、死又到底为何物,最终在临死前一刻顿悟。尽管这篇小说的篇幅不大,却蕴含着巨大的精神能量,堪称人类文学中直面死亡的巅峰之作。人对必死的命运的清醒认识,既是焦虑的源头,也是重构生命意义的契机,《伊凡·伊里奇之死》或许便是理解“向死而生”,挣脱日常生活沉沦状态的一把钥匙。
|
| 關於作者: |
|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他的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将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巅峰,代表了当时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与文学创作结伴同行的是影响托尔斯泰一生的几次思想转折,在这些精神世界的转折之后,“托尔斯泰主义”也成为了完整的思想体系。随着托尔斯泰社会威望和国际声誉的不断扩大,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他的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托尔斯泰思想上的广博与深刻,并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忠实信徒。
|
| 內容試閱:
|
【前言/序言】:
由死及生的追问
——《伊凡·伊里奇之死》导读
人对必死的命运的清醒认识,既是焦虑的源头,也是重构生命意义的契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提出了“向死而生”的概念,通过直面死亡的不可回避性,挣脱日常生活的沉沦状态,实现对自身本真性的觉醒。不过,话虽这么说,对于大多数身体健康、没有遭受重大挫折,且尚未步入老年的人来说,死亡终究是一件遥远且讨厌的事,最好把它抛在脑后,而不是提前去面对它、打量它、思索它。在一些相对传奇化、戏剧化的事例里,这样的事例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某人因为遭遇意外险些丢掉性命,在死里逃生之后大彻大悟,彻底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和态度。姑且不论这类传闻有多少夸张渲染的成分,只说这种改变的契机——意外——毕竟不可多得,何况我们也并不想遇到。那么,或许可以试试读这本书,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纳博科夫曾把托尔斯泰比喻为“太阳”,称他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伊凡·伊里奇之死》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事实上,托尔斯泰三十岁时还写过另一篇以死亡为主题的小说《三死》,当时他还年轻,大概受佛家思想影响,对死怀有一种相对淡然的超脱态度。而写《伊凡·伊里奇之死》时他已经年近六十,目睹或听闻了许多同龄人的离世,自然也意识到自己离死不远。于是在这部作品里,他没有采用烘托或留白之类的小说技巧,而是以一种看似笨拙的白描手段,正面刻画了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的死亡全过程,并借由他的眼光回顾了他的整个生平,促使读者与他一同对死亡和生命意义发起追问。
伊凡·伊里奇的父亲是一个才干平庸的三等文官,伊凡·伊里奇则是三兄弟中最优秀的一个,从法律学校毕业后成为公务员,一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最后当上了法官。他的妻子是贵族出身,不过并不富有,在怀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渐渐变得脾气暴躁、控制欲强、爱吃醋。于是他选择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以回避家庭的不和睦。所幸两个孩子都受到不错的教育,女儿有一个体面的追求者,儿子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尽管不是没有遇过挫折,但总的来说,他的人生是得意的、顺利的,工作能力出色,受到人们尊敬,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也算是家境殷实。
然而托尔斯泰却写道:伊凡·伊里奇过往的历史极为简单、寻常,又极为恐怖。可是,既然简单、寻常,说明他过的生活和旁人过的差不多,这样的生平又怎能称之为恐怖呢?于是我们跟随着托尔斯泰的叙述,一点点地穿透伊凡·伊里奇的人生轨迹和轮廓,深入到他生活的内核中。小说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开篇第一小节即宣告了伊凡·伊里奇的死讯。他生前的同僚们对此表现出的自私和冷漠可能让读者鄙夷,因为他们更关心职位的补缺和晚上的牌局,而不是悼念死者。可是我们不妨想深一层,假如这个部门里每个人都如此,那曾和他们相处融洽的伊凡·伊里奇又怎会是一个异类?换言之,假如死的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伊凡·伊里奇的表现未必会和他们有很大区别。
不过,讽刺只是托尔斯泰擅长的表现手段之一,却不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基调。尤其对于晚年的托尔斯泰来说,讽刺和批判只适合针对具体的现象,针对是与非、对与错的揭露和鞭挞,却无法承载他整体的生命感受和困惑,以及他的终极追问和解脱。他要写的绝不仅是一部讽刺小品,而是尝试为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寻求出路。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这样的雄心简直不可想象。为此他创造了伊凡·伊里奇这个角色——恰恰因为死降临在他身上,他才得以逐渐觉醒——人总是在面对死的时候,才开始反思应该如何活。
从青春年少时起,伊凡·伊里奇就以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为榜样,像苍蝇趋光一样仰慕、结交和仿效他们。在法律学校就读的时候,他也像别的年轻人一样放纵自己,为此良心感到过不安。可是他看到那些光鲜的偶像也这么做,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于是就安心了,不再为此难过和自责。进入工作之后,他在处理公务时认真、正直、克制、稳重,同时私生活中也不乏寻欢作乐的内容,这些都符合他对上等人生活的想象。至于结婚,这是他想成为的那类人必须做的事,刚好他又爱上一位女士,于是一切顺理成章。婚后的生活和他想的不一样,妻子有自己的意愿和喜恶,不是凡事顺着他、由得他。但别的夫妻也有这些摩擦,情况大抵也差不多。
挫折发生在婚后的第十七年,他一直觊觎的职位被一个不如自己的人得到,为此他大为光火,得罪了上司,此后的升迁机会更轮不到他了。他决定反击,到首都去托关系。结果非常幸运,他的一个老友刚刚接任要职,动用手中的权力帮了他一把。这成为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扬眉吐气,报仇雪恨,夫妻俩因为对光明的未来有着共同的构想而重归于好。为了履新,他们搬到另一个城市,伊凡·伊里奇先行负责找房子、装修、购置家具。他并不富有,家装品味也不高明,尽管他和渴望显得比实际富有的人几乎难分彼此,可他还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灾难在此时埋下了种子。房子装修期间,因为对新生活热情高涨,伊凡·伊里奇有次在给壁布工示范如何贴壁布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当时似乎并无大碍,只是腰部青了一块。可是不久之后,这个伤发作起来,越来越严重,小说也由此进入正题。接下来的部分,是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作品中,对死亡最著名、最有力,也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正面描写。
文学作品中的死亡其实不鲜见,别的不说,光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公爵就死于战场上的炮火,而《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安娜最后死于火车轮下。可是,主人公死于战场,作品关注的焦点难免偏向反思战争,假如死于谋杀或自杀,我们又更关心其中的道德意义。而伊凡·伊里奇的死却是一个极其平常,也极其偶然的小意外,它不是为了引导读者探讨别的什么,而只是让读者直面死和生本身。
随着病情的发展——医生甚至说不清是什么病——伊凡·伊里奇对自己的过往生平、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也越来越深刻。他察觉到自己看似按部就班的人生可能误入歧途了。在病榻上,他问自己想要什么,答案是想要活着。可是活着是为了什么,他回答不出来。渐渐他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活法不对头,简直没有真正地活过。可是到底哪里不对头,他说不出来。对头的活法是怎样的,他也不知道。这才是恐怖之处:直到快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生白活了。在度过童年之后,他的每一个追求,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对待每一个人,相信的所有观念,全部不是发自真心,就像鬼迷心窍一样。奇怪的是,他从没意识到应该追寻自己的真心,也不清楚怎样去追寻。
这是俄罗斯文学中典型的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同样的母题也反复出现在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中。我们中国人相信“好死不如歹活”,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不需要别的意义使它成立。可是当活着成为一种苦难和惩罚时,有一个答案至少让人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曾经,基督教提供了这个答案,俄罗斯人也习惯了这一点,没有这个答案他们就活不踏实。可是启蒙运动严重地削弱了宗教的权威性,到了十九世纪,即使在相对落后的俄罗斯,精英阶层也很难再把教条视为真理了。至少伊凡·伊里奇无法说一句,这就是主的安排,然后坦然地接受死亡。这并不是说,在基督教强盛的时候,俄罗斯人都不怕死。他们也会哭诉,谴责上帝不公、缺少仁慈,可是他们不会因此质疑生活的全部目标和意义。
伍尔夫对俄罗斯文学的评价很高,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尤其高,称他为“所有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她认为相对于欧洲文学,俄罗斯文学是异质的,西欧读者很难理解俄罗斯文学。西欧虽然同属基督教世界,但从文艺复兴开始,他们已经反思宗教文化,因此不像十九世纪的俄罗斯那样陷于信仰真空的精神困境。西欧毕竟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从殖民扩张中掠夺了财富和资本、从工业革命中产生了技术和资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中诞生了人权和民主思想……繁荣兴盛的世俗文化有力地填补了宗教式微后形成的价值空洞。而可怜、落后的俄罗斯却仍然停留在封建农奴制,仍旧面对着无穷无尽的苦难、不幸、恐惧和悲伤,并且曾经让他们安心的教义也渐渐失去效力。不过或许确实是国家不幸诗家幸,俄罗斯亘古不变的苦难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一批伟大作家。
俄罗斯有句民谚:蚜虫吃青草,锈吃铁,虚伪吃灵魂。俄罗斯作家大多对虚伪特别敏感,托尔斯泰也不例外,认为是虚伪普遍地毒害了人们的生活。许许多多的人每天做的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是符合自己身份和形象的事,说出来的不是自己真实的想法,而是符合自己身份和形象的话。久而久之,真实的自己就像疏于照看的花木一样凋谢了、枯萎了。人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不是成为真正的自己。不过,和悲观、理性乃至近乎虚无的契诃夫不同,托尔斯泰始终相信救赎。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弥赛亚往往由妓女担任。因为妓女是最卑贱、最无力的受难者,是不出卖身体和尊严就活不下去的人,因此她们的赎罪最彻底,也最纯洁。而托尔斯泰的弥赛亚却是那些朴实、善良、逆来顺受的农奴。作为一名贵族,他不仅在小说中,甚至在生活里,也提倡向农奴学习。他自己就经常和农奴一同劳作。在这些几乎一无所有的人身上,他看到了最理想的人性,也看到了全人类的精神出路。不过我们要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妓女和托尔斯泰的农奴都经过抽象加工,不是具体的人。
在伊凡·伊里奇人生的最后时刻,只有两个人仍然真正地在乎他、关心他,为他感到难过。其中一个是他的小儿子,他还保留着人性中的纯真,没有被成人的世界污染,并且爱着自己的父亲。另一个是帮厨格拉西姆,他是个单纯、知足、任劳任怨的乡下人,对人怀着真正的善意,不像伊凡·伊里奇以及他的妻女、同事和医生那样自私、虚假和做作。
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伊凡·伊里奇终于心疼起妻子来,他蓦然意识到自己为身边的人制造了太多的痛苦。这个时候,曾经苦思不得的解脱遽然降临:不该把自己看得比所有人重要,心疼他们,应当做得让他们不心痛。让他们以及自身摆脱这些痛苦。当醒悟到这点后,对死亡的恐惧消失了:什么恐惧都没了,因为死也没了。取代死的是光。伊凡·伊里奇在临终前获得了救赎。
胡安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