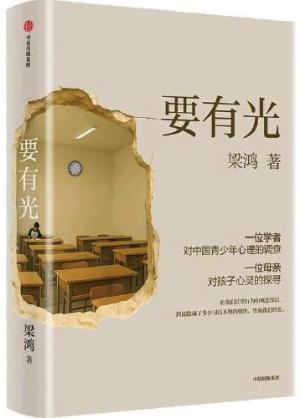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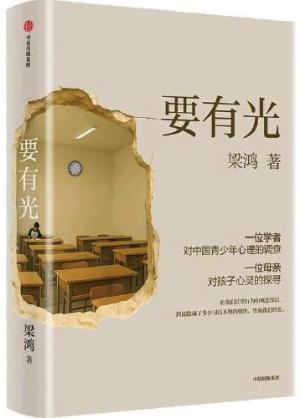
《
要有光
》
售價:HK$
352

《
岁月的泡沫(波伏瓦、加缪的密友,法国文坛鬼才书写爱情霍乱!科塔萨尔、鲍德温盛赞!20世纪百大经典to
》
售價:HK$
214

《
索恩丛书·帝国计划:英国世界体系的兴衰(1830~1970)
》
售價:HK$
862

《
改变的勇气:数十个真实人生蜕变故事,教你改变命运的密码。
》
售價:HK$
301

《
明清时期的灾害治理机制
》
售價:HK$
306

《
甲骨文丛书·理查国王:尼克松和水门事件
》
售價:HK$
505

《
绣罗衣裳照暮春——古代服饰与时尚
》
售價:HK$
434

《
HR如何招聘人才:招聘思维与技能
》
售價:HK$
286
|
| 編輯推薦: |
|
本书稿精选了有代表性的老师、学生,将他们在西南联大学生、生活、抗战的故事集结成册。1944级学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始于叙永,却又不局限于叙永,他们在昆明、印缅、祖国的领空、重庆渣滓洞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刚毅卓绝”“不问西东”的精神。
|
| 內容簡介: |
|
1940年,抗战烽烟正炽,山河破碎之际,数百位西南联大师生再度踏上迁徙之路,将知识的火种带至西南边城叙永,虽不足一年光阴,却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绽放出璀璨的光辉。本书通过珍贵的史料和亲历者口述,重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办学岁月,见证了中国学人在民族危亡时的文化坚守。
|
| 關於作者: |
|
王 立,女,1953年12月生,祖籍湖北黄冈,中共党员、民革党员,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江汉大学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所长,退休经年,居北京。因家中多位长辈抗战期间求学于湖北联中、西南联大等大中学校,退休后即致力于中国抗战教育研究,出版专著《黉府弦歌烽火中:抗战烽火中的湖北联中(1938-1946)》(九州出版社,2018年2月),发表《王康与闻一多》《燕京、魁阁、清华:那些社会学先贤的心灵驿站》《民主之火永不熄灭》《让艺术成长在人民里》《向达与胡庆钧的师生之谊》等有关西南联大研究论文多篇。
|
| 目錄:
|
叙忆往昔 永铭怀想(代序) 向清三 / 1
黉府弦歌叙永城(前言) 王立 / 1
弦歌春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大事记 / 34
樊际昌关于叙永分校校舍致梅贻琦、蒋梦麟函 / 37
忆叙永 苏良赫 / 40
叙永杂谈 辰? 伯(吴晗) / 44
在叙永的西南联大 欧阳青 / 51
在叙永一年 赵景伦 / 53
码 头 彦元甲(韩明谟)/ 55
岁月回响
“到橘子林去” 李? 岫 / 60
童年记忆中的叙永之行 袁? 刚 / 68
父亲袁复礼的西南联大情结 袁? 方 / 77
终生难忘的西南联大 孙捷先 / 90
追念五位在西南联大工作或学习过的长辈
——从联大叙永分校说起 朱庆之 / 104
永宁河记忆——朱自清先生叙永逸事 朱小涛 / 112
巴山蜀水行路难——记梅贻琦、郑天挺1941年的川渝之行 郑? 光 / 120
志业长昭 乐育垂绩——追忆我的祖父樊际昌 樊文渊 / 138
薪火相传
我的伯父——著名社会学家王康先生 王? 立 / 150
我的母亲彭兰先生 张晓岚 / 175
我国单模光纤之父黄宏嘉院士 王? 立? 吴? 嘉? / 183
揖别朝天门 南下叙永城
——忆父亲黄宏嘉的联大求学路 黄? 柯 / 194
迈入高等学府 张咸恭 / 210
走向远山——回忆父亲张咸恭 张? 磊? 王? 薇 / 221
刚毅坚卓 矢志不渝
——追忆“叙永哥”蒋大宗的家国情怀 蒋本珊 / 226
联大叙永分校生活琐记 吴铭绩 / 245
平凡的一生体现出刚毅坚卓的精神
——悼念父亲吴铭绩 吴慧文? 吴慧立 / 253
杂 忆——叙永求学,印缅从军 卢少忱 / 257
抗战老兵卢少忱先生 王? 立? 吴? 嘉 / 267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生参加空军纪实 马? 豫 / 277
从西南联大走出的抗战飞行员
——我的叔叔马豫 马庆芳 / 279
投笔从戎 血染长空
——我的二叔李嘉禾 李? 安 / 288
红岩烈士刘国鋕 刘以治 / 300
后记 联大弦歌永不辍 / 322
参考文献 / 331
|
| 內容試閱:
|
叙忆往昔 永铭怀想(代序)
向清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我父母曾经求学和工作的地方。他们都是清华12级的学生(父亲向仁生,母亲曹宗巽),1936年入学。1937年暑期发生了七七事变,再开学时学校就南迁到了湖南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后,三校联校再度远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4月,正式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抗日 战争胜利之后,三校才陆续迁返北京和天津的原校址。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提起西南联大,马上就会想到云南昆明。直到不久前,我受邀加入了王立女士主持的一个微信群,才注意到与联大相关的一个更加边远的地方——四川省的叙永县。这里距昆明约600公里,是联大曾经计划再次迁移的目的地。1940年至1941年,联大建立了叙永分校,并在那里集中对当年入学的新生授课。
我母亲作为年轻教师,曾跟随恩师李继侗先生,经艰苦长途跋涉,赴叙永任
教。据多年前我母亲缅怀李先生的文章叙述,“当时由昆明到叙永的交通工具只有随时可能抛锚的长途汽车。记得在贵州毕节我们等了一个星期之久才上了车”。叙永的办学条件,比昆明还要艰苦一些,但师生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却是那般充实而有意义!
在联大叙永分校的教师名录中,我还看到了郑华炽先生。郑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他曾负责叙永分校的收尾工作。1982年我大学毕业之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拜见过他老人家。
西南联大,除了位于昆明的本部,还有包括叙永在内的分部,如同璀璨的群星,高悬在祖国的西南方向。这一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令人惊叹,永铭怀想。 据此,写下几句感言。
2025年2月23日于加拿大温哥华
杂 忆——叙永求学,印缅从军
我和许多叙永1941级同学一样,对叙永求学和1944年被征调入伍都有着深切的怀念或感受,值此出版50周年纪念刊之际,也来写一点杂忆。
北平——昆明——叙永
1940年1月,北平已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两年多了,我正好读完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因不甘在敌人统治下当亡国奴,我和同学黄天佑(叙永商学系)决心离开北平,奔向昆明。我们在天津大沽口乘往上海的轮船,上船前,日本兵逐一盘问、检查,先问去上海干什么,我们说是投奔亲友当伙计,他看我们剃光了头,穿着长衫、布鞋,不像是学生,就没找麻烦,但是箱子翻了个底朝天才放行。我们乘上打地铺睡的五等舱顺利到达上海,在亲戚家住了几天,又转船去香港。轮船一抵香港,不能靠岸,许多小舢板纷纷划近轮船,有人飞速爬上大船,抢运旅客行李到对岸,有的老年旅客一不小心,行李被提走就找不着人了。我们各自一手提箱子,扛上铺盖卷,走下大船,免被抢走。在香港又投靠亲友,住了一个月,等候船期和办理去海防的手续。
乘轮船到海防,刚上岸,只见许多中国人拥挤着排成长队等候海关检查。长长的行李台上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神气十足的法国人,态度蛮横而傲慢,他把每个人的箱子翻遍,只要看见几块香皂或几支牙膏,就只给你留下一块或一支,其余的全扔进行李台里面扣留。最令人气愤的是,他只要看见后面有年轻漂亮的妇女,就用食指向上一挑,示意要她前来先检查,并蓄意问三问四,磨蹭时间,着实可恶。
在海防住了两三天,即乘火车往昆明,车轨窄而陈旧,火车头上标有1905年造的标记,铁路弯曲且多山洞,洞内煤烟呛鼻。车身中间堆放行李货物,两旁是长排座位。乘客大多是不断咀嚼着槟榔的越南人,其中有些是小贩,带上车的成捆甘蔗和硬块红糖不时发出发酵的酸味。
1940年3月到昆明后,找到联大先修班的中学同学许鸿义和吴坚(叙永航空系,回昆明考入空军,赴美训练驾驶战斗机,回国对日作战,一次迫降解放区被救起,送回国统区,一次起飞迎战,机械失灵,坠毁牺牲),经他们指点,我们到教育BU沦陷区各地来昆就学指导处登记,进了高中毕业补习班。因经济来源断绝,又无亲友接济,仅靠每月领到的10余元生活费在联大新校舍入伙,勉强维持。后来居住也成问题,经同学马启伟的协助,黄天佑和我曾在文林街的文林堂里面仅容两张床的小屋住宿。我们经常为举办唱片音乐会和星期做礼拜做些打扫卫生环境、整理座位的工作,并兼管期刊的借阅。平时很清静,倒是读书准备考大学的好地方。报考大学前,自感基础差,希望不大,但很幸运,发榜时竟按第一志愿录取到西南联大文学院。
从昆明到叙永分校又是一个难题,经历了一番曲折。当时西南联大已发给黄天佑、吴坚和我三张搭乘西南运输处卡车的免费票,可是路途要六七天,每人食宿需100元,而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才100元,已经是12月了,学校快开学了,非走不可。第一天我们搭上了西南运输处的一辆货车,刚到沾益,司机看我们是穷学生,没油水,硬说车已超重,就把我们连人带行李甩下车开跑了。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从上午等到下午3时,一个年轻的司机开了一辆载满钢板的敞篷卡车,路过这里停下来,我们向他说明是从敌占区北平出来要去叙永上学,中途被甩了下来。他慷慨地让我们上车,坐在钢板上。我们三人担心半路又被甩掉,决心拿出手头上的一半钱(50元)给他,自己宁可忍饥挨饿,只要能到校就行,可是这位好心肠的司机知道我们是流亡的穷学生后,不但拒收我们的钱,反而每到一地都拉着我们同押送钢板车上的商人一齐吃饭,饭后坚决阻拦我们掏钱,而让那位商人付账。我们本无心白吃,他却有意解决我们的困难。
从昆明去叙永路经沾益、宣威、威宁、赫章、毕节、赤水河等地,沿途多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常是云雾遮天,公路曲折、狭窄又颠簸。有的司机为节省汽油私卖,在汽车下高坡时熄火放空档溜车,经常发生坠入深渊的车祸。我们中途遇过两天雨,在无篷的卡车里,淋得浑身湿透,无处躲避。然而,由于这位司机的热心帮助和安全驾驶,我们终于顺利到达叙永。三个人总共花了90元,还余10元,简直难以置信。这位司机热心帮助,不是为了别的,而完全出自他对逃离日寇统治、背井离乡的学子的无限同情。
在叙永,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同学们的艰苦学习生活永远难以忘怀。吴晗老师在文庙第一次同历史系全班同学见面时曾说:“学历史做大官的不多,不就是胡适和蒋廷黻么!要想做大官,就别读历史系,现在转系还不晚。”接着说:“学历史要像老和尚撞钟,持之以恒。”寓意多么深刻又激励人心啊!吴晗老师讲中国通史讲到汉代外戚专权时感慨地说,“现在是什么政治,一言以蔽之,‘小舅子政治’”,引得哄堂大笑。李广田老师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讲起文学的“典型性、代表性”来,深刻又通俗。滕茂桐老师讲到马歇尔的“Marginal Utility”语调缓慢又深沉。龚祥瑞老师讲政治学提到Laski时,音调铿锵有力。还有其他老师……虽然5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风貌犹历历在目,印象深刻难以磨灭。
一提到叙永,不由得想起同学们勤奋学习和艰苦的生活情景,那时,破旧拥挤的春秋祠和其他宿舍一样,床挨床、上下铺,晚上三五个同学聚在一盏小油灯下,自觉地抓紧学习,唯恐每月发的灯油费不够用到月底。对断绝经济来源的同学们,尤其是从敌占区来的同学,想泡一次茶馆,既解渴又能借灯光看书,却非易事。早上若能偶尔买一小碗“鸡丝”豆腐脑或是晚上喝上一碗炒米糖开水,就是小小享受。若是几个人在饭馆买回一小碗干菜垫底、上面只有几片肉的“回锅肉”,就算大大改善了。难以想象的是每天早上洗脸、刷牙要走到200米远的永宁河畔,如逢下雨,上游黄泥水冲下,只好抹把脸算了,牙就免刷了。因从北平出来一年多,鞋穿破了没办法,我和几个同学只好买草鞋穿,好像是两毛钱一双,麻编的鞋贵约两倍,买不起。开始穿不习惯,逐渐才适应,但就怕下雨,脚板湿冷,草鞋还不易干,一双鞋最多穿上二十几天就破烂了。1989年我有幸再去叙永,但很难看到卖草鞋的了。
叙永虽学习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同学们却朝气蓬勃,充满乐观精神和青春活力,课余之时,拉胡琴、唱京剧、吹口琴、唱歌、打球、打桥牌、爬红岩、下河游泳、游橘林,确实是苦中有乐,其乐也无穷。
半个世纪前700多名师生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冲破艰难险阻不远千里来到叙永,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呢?我想,这是由于大家都怀有“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必胜的共同信念吧。
印缅从军
1944年3月初,随同全校1944级同学征调入伍充当译员,心想距毕业只有一个学期了,放弃学业未免惋惜,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投笔从戎,也责无旁贷。经过译员训练班半个月的军事生活——每天穿军服、打裹腿、上操和紧张的英语学习后,3月中旬公布了一批人员的分配名单,我是按自己填写的志愿分配到印缅战区。在简单的体格检查后,我们这一批共16人同乘C-47运输机自昆明启程。同机的同学记得有地质系王忠诗、欧大澄、陈鑫,经济系魏书玉、蔡永祺、郭凤章、郑梦奇、陈羽纶和政治系邹宏藩等。飞越驼峰高空时,俯视下面是一片厚白的云层,大家只穿着单军服、短裤、打着裹腿,机内冰冷难熬。不巧气流变化激剧,飞机上下颠簸异常,除我一人外,几乎全部呕吐了,躺卧在两旁座位上。飞机在印度汀江机场降落,正好是炎热的晴天,一下飞机好像进入了热锅。当天晚上住在茅竹搭起的棚屋,一个挨一个排着睡。次晨,除个别人外,全都上了一辆卡车,但不知到哪里去。卡车走了两三个小时,开到了印度列多第48后送医院(48 Evacuation Hospital),才知道是在这里工作。
1.第48后送医院
医院是在荒野上建起的,病房和宿舍很简陋,全都用粗茅竹当支柱,四周用竹篾当围墙,地面是泥土地。睡的是行军床,每人发蚊帐一顶。吃的是罐头和有时带有霉味的粗糙大米,难能吃到青菜。有一种经常吃的猪肉肠罐头(Pork Sausage),肉肠里面多少带有怪味香料,难以下咽,大家起名叫它“大便罐头”。好容易等到轮休,便搭便车到20里外市镇上一家华侨饭馆,花钱吃一顿新鲜蔬菜或肉食,改换一下口味。
医院由美国人管理,医官和护士等也全由美国人担任,当时从前方孟关、孟拱一带用飞机运回很多需急救的中国重伤员,有的连夜动手术、输液、抢救,忙个不停。我们每天还配合美国医官(上尉或少校不等)巡查病房和治疗做翻译工作。总的来说,医院的医疗设备较好,药品充足,医术较高。起初对同日寇作战负伤的中国士兵也还尊重,但是,由于种族歧视传统观念的存在,就必然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有所反映。例如,最初倒尿壶、便盆由美国护士兵护理,不久则改成雇用当地印度人料理。有的医官对负伤疼痛难忍要求止痛片的伤员,不闻不问,置之不理。有一次,一个伤员手术后双腿裹上了石膏,日久,从里面爬出蛆来,疼痒难挨,要求美国医官用药水或其他办法杀死里面的蛆虫,医官非但不管,反而说没有关系,蛆在里面吃烂肉,有好处,气的伤兵直骂街又无可奈何。诸如此类歧视中国人的不负责态度,时而发生,曾一度激起全医院翻译官的愤懑,集体向美籍华裔的上校副院长(姓关)据实反映,他表示理解和同情,但也无能为力。
在医院工作了三个多月,因不愿忍受这份闲气,王忠诗、陈鑫和我先后请求调离医院到前方的中国作战部队工作,经过军委外事局驻印办事处的批准,我们如愿以偿,调离了医院。
2.参加密支那战役
1944年5月17日,中美联军越过野人山,奇袭缅甸密支那,抢占了机场,日寇退入市区坚守顽抗,当时我方急需增援兵力,也需要译员紧密配合。王忠诗、陈鑫和我分别在五月底和六月初自印度列多乘运输机飞抵密支那。他们俩配属在30师88团,我配属在30师90团二营。
密支那是缅北最大的城市和铁路终点,又是打通中缅印公路必争之地,南下可进攻八莫、南坎、腊戍并切断日寇向我滇西增援,因此,日寇死守密支那,战斗异常激烈,相持了80天,方解决战斗,共消灭日寇3000余人,俘虏官兵60多人,我方伤亡官兵6000余人,其中阵亡2000余人。
当时中国部队是主力,每个步兵团配有美国校尉级联络官5人(两人在团部,每营各1人),翻译官也按5人配备,翻译官主要的任务是在团长、营长同美国联络官共同研究作战情况和请求美方补充弹药、给养或飞机支援等方面做翻译和联络工作。
时值六七月雨季,大雨连绵,双方炮火不断,必须成天躲在积水的掩蔽部里,皮肤泡得发白。最困难的时刻,喝的水是用随身携带的消毒药片泡过的雨水或河水。吃的是密封纸盒包装的干粮,分早、中、晚(B、D、S)三种,大同小异,不外是几片饼干、一小罐罐头、几支香烟、一块巧克力或果脯干,经常干噎,不免倒胃。当地疟疾盛行,有一种恶性疟疾,24小时可致命,每人每天必须吃黄色的阿的平药片,预防疟疾,常吃皮肤会变成黄色。潮湿的地面,蚂蟥遍地,吸住皮肉不撒嘴,如果揪断,仍吸住不放,只能用烟头烧烫尾部或涂以防蚊油方能摆脱。
丛林战(Tungle Warfore)好像是在丛林里捉迷藏,难攻易守。在茂密的丛林中,日寇经常埋伏着狙击手(Sniper),从上下左右放冷枪阻挡我部队前进。有一次,我身后一名士兵挨了一枪,但看不见敌人在哪里。总之,每前进一步都有危险,要付出代价。有时不得不用机枪扫清枝叶和丛草向前进。
战斗的相持阶段,日寇虽被包围,仍抗拒坚守,白天不敢暴露目标,每到夜晚尤其是雨夜,组成三个或几个人的小组出击,企图突围。有一次,半夜里大雨倾盆,我们营部共六个人(营长、副官、勤务兵、电话员、联络官和我)在掩蔽部里忽然听见20多米外日寇“哈依、哈依”的招呼声,我们趁其不备,先下手为强,五支冲锋枪和一支卡宾枪同时猛扫,击溃敌人的偷袭,但次日清晨才发现数十米处我们的一名哨兵靠在树干上被日寇攮死。还有一次雨夜里,我们营部听见后面响起阵阵日本三八枪的“咔嘣”声,这时接到后面团部电话说,一股日寇流窜到团部和营部之间,因团部和营部相距不远,命令营部不要向后开枪,以免混乱,我们营部几个人只好持枪通宵警戒,直到团部将敌人击溃。
密支那战斗艰苦而激烈,我所在的第二营张营长担任一线主攻,曾因斗志消沉,行动不果断,当场撤职,换上沉默寡言、指挥若定的刘营长。在久攻不下两军相持阶段,已经61岁灰白发的史迪威将军曾亲历前线视察战况,他身着一般士兵的绿色军服、戴军便帽,瘦小的身材背着卡宾枪,不断在壕沟跳上跳下了解情况,说话稳重却平易近人,没有总司令的派头。
战斗后期,我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日寇更加困兽犹斗,陈尸遍野。一次我军淌过一条半身深的小河,水上漂着许多具敌军尸体,身上爬满白蛆,整条河水散发着死尸腐烂的臭味,我们过河后,身上沾上的这种臭味,久而不散,令人作呕。
8月3日,逼近市区发动总攻击那天,气候晴朗,从营部用肉眼可望见数百米外日寇占据的火车站附近的仓库。约在上午8时,一声令下,3个连奔向目标,我和联络官跟了上去,因敌人大多已伤亡,个别人渡江逃跑,战斗顺利结束。据说有一个日寇少尉军官在掩蔽部里不肯出来,最后要往里面扔手榴弹,他才举手投降。我曾见到一个负伤的日军俘虏,面黄肌瘦蹲在地上两手合捧着说“密西、密西”要吃的。那份“大日本皇军”的威风,不也烟消云散了吗!我还看见被抓获的一群军妓从远处缓缓走过,她们纯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后方,日本俘虏被关在用刺丝围起来的场地和茅屋,口粮不缺,有时还在空场上打球锻炼身体。这与日寇惨无人道杀害中国人民和俘虏的罪行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
在印缅战场上,中国军队有消灭日寇、打回中国去的决心,斗志旺盛,勇敢顽强。有人问过日本俘虏,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如何,他傲慢回答:“印度的,一个抵十个;美国的,一个抵三个;中国的,一个抵一个”,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也不无反映一定的客观事实。
3.随战车进军八莫
1944年8月初,占领密支那后,9月我因故回到印度列多,当时中美混合战车指挥组(下辖两个战车营)需要翻译官,军委外事局驻印办事处负责人(黎秘书)把48医院欧大澄同学和我转调到战车营的炮一连和炮二连,同学罗济欧也已在指挥组工作。驻地是在印度东北端铁路终点——萨地亚。在那里参加训练坦克、汽车驾驶、炮兵(75mm榴弹炮、37mm战防炮)射击等翻译工作。许多驾驶技术、机件、射击要领等专门名词术语与步兵大不相同,很感陌生,只好从干中学、学中干,几乎每天驾驶坦克,既颠簸又吃力,因天气炎热,训练完已是浑身臭汗,沾满泥土,这时跳入布拉马普特拉大江(雅鲁藏布江下游)洗个澡、游个泳,感到莫大乐趣。
约在11月初,战车营从萨地亚乘汽车和驾驶坦克出发,美国联络官和翻译官同驾驶一辆带有通信设备的指挥车(Command Car),途经印度列多,越过野人山,进入缅甸的新背洋、马科因、夏都塞、卡马因、孟拱、密支那,开赴八莫会战。行军沿途穿过无数原始森林、峻岭、深谷、急流险滩。每到一处驻扎,大部用汽油烧掉丛草开辟宿营地。白天,树上蟒蛇和地面野象足迹到处可见,入夜,森林深处虎啸、狼嚎、猴啼等叫声不绝于耳,枕枪而眠,习以为常,八莫在密支那以南240里,位于伊洛瓦底江边,是缅北第二个大城市,它对打通中、缅、印公路有重大战略意义。战车营约在11月下旬抵达八莫市区外围整军待命。当时日寇西面背倚伊洛瓦底宽大江面,东、南、北三面已被我新一军包围,围困在市区内约3000余人,仍坚持顽抗,战斗激烈。据统计自10月中旬自密支那向八莫进军到12月中旬占领八莫的两个月,共击毙日寇2400余人,生俘20余人,我方伤亡1000余人。
12月15日,发动全面总攻击的头天晚上,坦克部队已做好作战准备,可是次日清晨,我所在的战车营炮兵连还没有上阵,八莫已被新一军所属步兵师占领。据说日寇生沉千余伤员于伊洛瓦底江,残余部队大部已被击毙,极少数溃逃出去。当天,我随部队进入八莫市区,房屋几乎全被飞机、大炮摧毁,仅存一片残垣瓦砾,血染的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击毙的日寇尸体,有的头部和胸部被炸得稀巴烂,血肉横飞,显然是引爆手榴弹自杀死的。八莫占领后战车营继续向南推进,1945年1月15日,第30师和第38师攻占南坎后,中缅印公路打通,宣告通车,日寇向南腊戍溃退。战车指挥组所属战车营不再随步兵南下,3月间东向回师缅中交界的木姐,建立战车训练班,就地训练坦克部队,直到同年日本投降,我在10月10日回到昆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