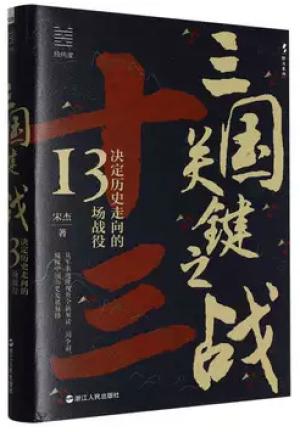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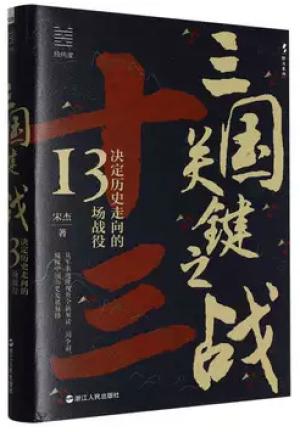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三国关键之战:决定历史走向的13场战役
》
售價:HK$
347

《
动物结构与造型图谱 骨骼×肌肉×立体造型×生活百态
》
售價:HK$
458

《
救命有术
》
售價:HK$
347

《
中国历代图书总目·哲学卷(全20册)
》
售價:HK$
10200

《
RNA时代(诺奖得主解密RNA分子如何创造生命的新奇迹)
》
售價:HK$
403

《
无论在哪儿都是生活(中国好书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奖特别奖得主肖复兴新作)
》
售價:HK$
245

《
隋唐与东亚
》
售價:HK$
296

《
理解集(1930-1954)(阿伦特作品集)
》
售價:HK$
551
|
| 編輯推薦: |
经典理论与现实的强适配性。作为百年前的群体心理学奠基之作,书中提炼的群体盲从、情绪传染、领袖操控等规律,并非过时的抽象概念。从街头运动的动员逻辑到网络舆论的发酵路径,从消费主义下的非理性抢购到职场中的派系站队,这些现象都能在书中找到精准对应的解析,让读者透过历史理论看清当下社会的运行肌理。?自我认知的深度照见。它跳出单纯的社会分析,成为个体审视自身的工具。书中揭示人在群体中易丢失独立判断、被口号裹挟的心理机制,能帮读者发现自身在集体环境中的认知盲区 —— 比如为何会不自觉跟随大众选择,为何会被煽动性言论影响,从而实现对自我行为逻辑的深层认知。?实用的清醒生存指南。区别于纯粹的学术著作,它提供可落地的认知策略。不倡导脱离群体,而是教会读者在喧嚣中守住思考锚点:如何识别情绪操控,如何在集体压力下保持独立判断,如何利用群体心理规律规避陷阱。这种 “入世式清醒” 的指导,让读者能在复杂社会场景中掌握主动权,最终实现对自身命运的掌控。?
。
|
| 內容簡介: |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经典著作,1895 年问世后成为群体心理学的奠基之作,被译成近 20 种语言全球传播。?
书中突破 “人群是个体叠加” 的认知,提出群体会形成全新心理主体,受 “集体潜意识” 支配。勒庞以冷峻笔触剖析群体盲从、情绪传染、领袖操控等规律,揭示个体融入群体后理性弱化、判断力丧失的心理机制。?
它不仅是社会现象的解码器,更是个体认知的照妖镜 —— 从街头运动到网络狂欢,从消费盲从到职场站队,现实中诸多群体行为都能在此找到对应解析。书中不教逃避群体,而是提供 “入世式清醒” 指南,助读者在喧嚣中守住独立判断,掌控自身命运,堪称理解现代社会的**书目。?
|
| 關於作者: |
古斯塔夫?勒庞于 1841 年 5 月 7 日出生在法国诺晋特 - 勒 - 卢特鲁 ,是群体心理学的开山鼻祖,有着 “群体社会的马基雅维里” 之誉 。1866 年,他在巴黎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后游历欧、亚、非多地,这段经历为他创作人类学和考古学著作积累了丰富素材 。
普法战争期间,勒庞担任军医,战后他对军队纪律、指挥以及人在压力下的行为展开反思,相关文章成为法国圣西尔军校教材 。19 世纪 90 年代,勒庞将研究重点转向心理学和社会学,提出人群聚合会形成受 “集体潜意识” 影响的全新心理主体 。同一时期,他还展现出科研工具创新能力,发明了便携式头部测量仪 。勒庞一生著作等身,如《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战争心理学》等,极大推动了心理学和人类学发展 。1895 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最为知名,堪称群体心理学奠基之作,已被译成近 20 种语言 。
|
| 目錄:
|
导言:群体时代的到来?/?001
第一卷 群体心理?/?013
1.群体的一般特征?/?015
2.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029
3.群体的观念、推理与想象力?/?057
4.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071
第二卷 群体的观点与信念?/?081
1.群体观点与信念中的间接因素?/?083
2.群体观点的直接因素?/?109
3.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127
4.群体信念和观念的变化范围?/?157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其特点?/?173
1.群体的分类?/?175
2.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181
3.刑事案件的陪审团?/?189
4.作为选民的群体?/?201
5.议会?/?215
译后记?/?241
|
| 內容試閱:
|
该书的目的是对社会各种群体的特征做一个说明。遗传赋予种族中的个体以某些相同特征,这些特征合起来构成了这个种族的气质。只是当其中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群体时,仅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外,这个群体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很多时候与种族特征并不相符。
在各民族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都起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著。群体无意识行为代替个体有意识行为,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
对于群体行为所引起的困难问题,我用纯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考察研究。也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是方法上的考量,不受各种观点、理论以及教条的影响。我们深信,这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有效方法,当探讨的问题受到关注却众说纷纭时尤其如此。努力弄清某种现象的科学家,对于自己的研究是否可能伤害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在意的。不属于当代任何学派的杰出思想家阿尔维耶先生在他最近的一部著作中说,他经常发现自己的结论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冲突。我希望这部新作也能如此。一旦属于某个学派,人们就很难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意见以及存在偏见。
在这里我需要向读者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出一些让大家乍看起来很难接受的结论。比如,为什么我在指出包括拥有一些杰出人士在内的团体的群体精神极度低劣后,还是断言,这种群体精神尽管低劣,但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
原因就是,历史事实毫无例外地证实,社会组织就像所有有机生命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其在短时间内发生深刻变革的能力。大自然有时当然会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不过从来也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表明,一个民族如果过于热衷重大变革,无论这种变革在理论上多么正确、多么出色,都是存在致命危险的。当这种变革只有即刻使民族气质发生变化时,才是有用的。可惜只有时间才拥有这样的能力。人们会受到各种思想、情感以及习惯的控制——人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无一不是人的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人的需要。作为社会产物的制度和法律,是无法改变这种性格的。
社会现象和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是紧密相关的。很多时候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些现象似乎有绝对的价值,而实际上它们的价值仅仅是相对的。
因此,对待一种社会现象,应该分清先后,从不同方面加以考量。如此就会发现,很多时候纯粹理性的道理与实践理性的道理相悖。这样的划分适用于包括科学对象在内的几乎全部对象。按照公理,一个立方体或者一个圆,是由相关公式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但一旦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些原本规则的几何形状就会变得不同。通过透视,立方体会变成锥体或者方形,圆形会变成椭圆形或者直线形,而一般来说,分析这些多变虚幻的物理图形,总是比分析它们真正的形状显得更重要,原因是它们,也只有它们,才是我们看到并能用拍照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很多时候不真实比起真实蕴含更多的真理。如果按照事物真实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很可能恰恰是在歪曲这个事物,使之变得难以辨别。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全世界的人只会复制照搬,但无法接触这些事物,人们是很难对事物外形形成正确认识的。同时,关于事物形状的知识若仅仅由某些专家掌握,那么这些事物对人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应该记住,所有现象除了理论价值还有实际价值,而只有后者才与文明的发展有关系,因此是更重要的。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再考虑一开始从逻辑上迫使别人接受结论时,就会采取谨慎态度。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导致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现象如此复杂,无法加以全方位掌握或预见它们相互影响造成的后果。同时,在看得见的事实背后,往往隐藏着无数看不见的事实。可见的社会现象有可能是某种庞大的无意识机制产生的,这种机制通常超出了人的分析能力的范畴。我们可以把感觉到的现象比喻为波浪,而波浪不过是大海深处看不见的湍流的反映。群体的大多数行为,在精神层面表现为一种独特的低劣品性,但在另外的行为中,社会似乎由某种强大的神秘力量控制,古人称之为命运、自然规律或天意,而我们将其称为“幽灵的回声”。虽然我们无法了解它,却不能低估它的威力。一个民族的内心深处,仿佛有某种恒久的力量在支配着它。我们以语言为例,还有什么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性、更神奇的东西吗?但正是令人赞叹高度组织化的语言,不恰好是来自群体无意识,而不可能来自别的地方吗?那些最博学、最具威望的语言学家,所能做的也不过是找出支配语言的规律,而不可能创造这种规律。谁也不能断言那些伟大人物的思想完全是他们头脑的产物。是的,这些思想的确是由这些了不起的头脑创造的,但难道不正是群体的禀赋为之提供了无数沙砾,才形成这种思想生长的土壤吗?
群体总是无意识的,但或许它巨大力量的来源,恰恰就隐藏在这种无意识中。在大自然中,受本能支配的生物做出某些动作,其精巧复杂程度让人叹为观止。理性不过是较为晚近的人类才拥有的属性,并且并没有强大到能揭示无意识的规律的程度,要做到这点,尚需时日。比较起来,无意识对我们行为的影响,要远超过理性。无意识作为一种至今不为人知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假如你打算待在一个狭小安全的范围内,利用科学技术获取知识,不进入猜测与假想的领域,那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注意观察各种现象,并且所有的思考只针对它这些现象。当然由这种思考得出的任何结论都不可能是成熟无误的,因为在我们接触的现象背后,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现象,或者隐约能够看到的现象。
1.群体的一般特征
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的构成/大量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心理的特征/群体中个体固有的思想情感发生的变化以及个性的消失/群体总是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的消失和脊髓活动的得势/智力的下降和情感的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情感,既可以比群体中个人的情感更好,也可以比群体中个人的情感更糟/群体既易于英勇无畏,也易于犯罪。
一般意义上,“群体”指的是个体聚集到一起,不管民族、职业或性别属性如何,也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聚集到一起。但从心理学角度看,“群体”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以及重要性。某些既定条件下,并且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一群人会表现出某种新特点,这种新特点完全不同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的特点。人聚集成群后,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就会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自主性、个性消失,只剩下一种集体心理。这种集体心理无疑是暂时的,却表现出一些鲜明特点。这些聚集成群的个体进入一种状态,因为没有更好的说法,姑且称之为一个组织化的群体,或换个也许更为可取的说法——一个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受群体精神统一规律的支配。
当然,一些人只是偶然组织在一起。这个事实并不足以使这些人获得组织化群体的特点。一千个偶然聚集到公共场所的个体,如果没有任何明确、统一的目标,从心理学角度说,这也不是一个群体。要想具备群体的特征,得有某些前提条件,我们必须对群体的性质加以确定。
自主性的消失,并且感情和思想和其他人一起转向共同的方向,是即将成为组织化群体的人们的主要特征,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一些个体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很多时候,在某种激烈的情绪下,比如遇到国家重大事件时,无数原本互不相关的个体也会表现出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因素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起来,立刻形成群体特有的属性。很多时候,五六个人就能构成一个心理学的群体,而几千人偶然聚在一起却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另外,虽然很难看到整个民族聚集起来,但在某些因素影响下,民族也会形成拥有共同方向的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就会获得一些鲜明的暂时性普遍特征。除了这些普遍特征外,心理群体还会有一些附带特征,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个体不同而不同,并且其精神结构也会不同。因此,对心理群体进行分类并不难。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异质性群体(即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即具有大体相同的要素,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等)相同的特征。除了共同特征外,一些各自具有的特点也使这两类群体有所区别。
在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群体前,必须先考察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将采用自然科学家通常采用的方法,先描述一个族系全体成员的共同特点,再着手研究该族系所包含的属、种区别开来的具体特性。
群体心理不易做精确描述,因为它的组织不仅在种族和构成方式上存在不同,还因为所受刺激因素的性质与强度不同而有所区别。不过,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一个人性格一生保持不变的情形,只在小说里才可能发生。只有单一性的环境,才能造成单一性的性格。我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所有精神结构都包含各种不同性格存在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这足以用来解释为何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原本都是文雅谦和的公民。在正常环境下,他们是平和的公证人,是善良的官员。并且一旦动乱结束,他们就恢复了原本的样子,成为安静守法的公民。拿破仑正是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顺服的臣民。
这里不可能对群体组织程度的强弱做全面研究,我们只关注达到完全组织化程度的群体。这样我们能看到群体变化的过程以及可能性,而不是其一成不变的样子。只有在高度组织化阶段,一个种族一般来说不变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某些新特点。这时,群体的全部情感和思想的变化,就会朝一个明确的方向发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群体精神统一律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挥作用。
在群体的心理特征中,有的特征可能与完全孤立的个体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有一些则完全为群体所特有,只能在群体中见到。我们首先研究的是群体的特征,并力图揭示其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的最惊人特点是: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体不管是谁,也无论其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有多大差异,当成为一个群体后,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集体心理。他们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于他们作为个体时的情感、思想和行为。正是因为群体的形成,才使得千差万别的个体有了原本不可能有的信念、情感和行动。心理群体是由异质成分形成的暂时现象,当不同的个体结合在一起时,就像细胞在整合后构成一种新生命体一样,表现出一些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相径庭。
与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相反,在形成群体的人群中,并不存在这些人群特征的总和及平均值。实际表现出来的,是在新特点下形成的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比如酸碱反应后形成新物质一样,新的组合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不同于形成此群体的个体特性。
构成群体的个体不同于独立的个人,想证明这一点并不难,然而找出其中的原因却不容易。
想要尽可能地找出其中的原因,首先要牢记现代心理学已经确认的一个真理,即无意识现象在有机体生活中和智力活动中发挥着压倒性的作用。和无意识因素相比,精神生活中有意识因素只起很小作用。即使是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充其量也只能找出一点支配人们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我们的有意识行为,主要是遗传影响下形成的无意识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在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祖辈遗传下来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形成了一个种族的先天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中,可以说明的原因后面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这些没有说明的原因背后,还有其他许多连我们自己也完全不知道的神秘原因。我们大部分的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一些隐蔽动机产生的结果。
无意识构成种族先天禀性,尤其在这个方面,种族的成员之间有明确的相似性,而个体成员间有所不同,主要是他们性格中存在的那些有意识的方面(例如教育)的结果,但更多的是独特的遗传条件导致的。人在智力上差异虽大,但他们却有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这些属于情感领域的事件上,最杰出的人物不见得比凡夫俗子更高明。智力方面,伟大的数学家和鞋匠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但从性格角度看,他们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毫无差别。
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一个种族中绝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等程度上具备这些特征。我们认为,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群体的共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体的才智被削弱,从而使其个性也被削弱。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占了上风。
群体通常只有普通的品质,这解释了群体为何无法完成需要高智力的工作。涉及普遍利益的决定,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作出的,但各个行业专家的决定事实上并不比一群蠢人更加高明。实际上,他们通常只能用普通个人具有的平庸才智处理手头的工作。群体累加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可能比伏尔泰聪明,倒不妨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体只是把他们共有的寻常品质累加了起来,就只会带来平庸,而不会如我们所认为的创造出新的特点。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正是我们将要研究的。
能否产生那些为一个群体所独有、孤立的个体并不具备的特点,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很多的。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优势考虑,群体中的个体也会感觉到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个体敢于发泄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个体必须克制这些欲望。个体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群体中个体的约束力量也就彻底消失。
其次,传染性对群体特点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还决定了群体的倾向。传染性的存在虽然很容易确定,但要解释清楚很难。这种传染性有点像催眠,接下来我们就对此做简单的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情感和行为都具有传染性,其严重程度足以让群体中的每个人随时都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人的天性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群体中的一员,个体很少会具备这样的倾向。
决定群体特点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独立个体的特点相比,群体中的个体所表现的特点截然相反。我指的是对暗示的接受程度,这也是传染性带来的必然结果。
理解这种现象,必须记住心理学上的一些最新发现。这些发现告诉我们,通过不同方式,个体可以被带入丧失自主意识的状态,对暗示者表现出绝对的服从,做出一些与其性格和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细致的观察似乎已证实,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不久就会发现或者因为群体催眠的作用,或者由于一些我们无从知道的原因,进入一种特殊状态,类似被催眠师操纵下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变成了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无意识的奴隶。有意识的自主人格消失,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情感和思想都受催眠师的驱使。
心理群体中的个体也处于这种状态。个体对自己行为失去控制力。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意识被屏蔽起来,对自己一部分能力的控制力消失,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能力却可能被强化。在某种暗示下,个体会因难以抗拒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群体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难以抗拒,这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有同样作用,这种相互影响会形成群体巨大的力量。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能抵制暗示的个体寥寥无几,不足以造成影响。这种巨大的群体力量只能因不同的暗示而改弦易辙。例如,有时一句顺耳的话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阻止群体最血腥的暴行。现在我们知道了,个体思想和情感受暗示和相互传染影响转向一个共同方向,自主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占据主导,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构成群体的个体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群体中的个体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由此可见,仅仅是成为有机群体的成员,就能使个体在文明阶梯上倒退好几步。独立的个体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却变成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野蛮人,甚至一个动物。群体中的个体显得身不由己,残暴狂热,表现出只有原始人才有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为相似的是,群体中的个体甘心让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而在独立存在时,根本不会受这些言辞和形象的影响。群体中的个体会情不自禁地做出违背其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习惯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体,不过是众多沙砾中的一粒,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
正是这种原因,会导致陪审团作出陪审员作为个体时不会赞成的判决;议会会颁布每个议员作为个体时都不可能同意的法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的委员,每个人作为个体时都是温文尔雅的开明公民,但当成为群体一员时,却不假思索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不顾自己的利益,放弃原本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相残杀。群体中的个体不但在行动上和本人有本质差别,在完全丧失独立性之前,其思想和情感就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让怀疑论者变成信徒,让老实人变成罪犯,让懦夫变成英雄。在1789年8月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投票放弃了自己的特权,如果让他们各自独立思考作出决定,就没有一个人会同意。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的智力总是低于独立的个体,但从情绪以及激起的行动角度看,在不同环境下,群体的表现可以比个体表现得更好或更差。群体所受暗示的性质起着决定作用。这就是那个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完全没有理解的要点。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群体,也常常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体,会不顾一切地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保证;会在荣誉的驱使下赴汤蹈火;会像十字军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还基督墓地,或像1793年那样捍卫祖国。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是以冷酷无情的方式行动,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记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