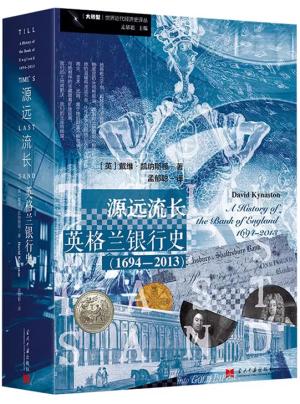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印章的故事
》
售價:HK$
230

《
数字化口腔
》
售價:HK$
2030

《
中国史前玉器
》
售價:HK$
449

《
最后的使团:1795年荷兰访华使团及被遗忘的中西相遇史
》
售價:HK$
4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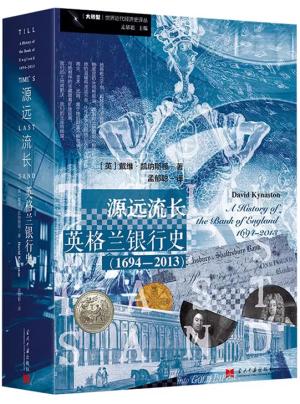
《
源远流长:英格兰银行史(1694-2013)
》
售價:HK$
857

《
第一性原理穿透思维定势
》
售價:HK$
398

《
俄国史译丛——先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知识界
》
售價:HK$
539

《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报告(2025)
》
售價:HK$
924
|
| 內容簡介: |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得主魏思孝全新力作
游走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坦诚讲述
那些念念不忘的亲人、朋友、曾经的我,还有没能说出口的告别,都成了书里未干的墨
用文字剖开那些被时光腌渍的瞬间
这里的故事,如藏在衣柜深处的旧毛衣,每次摸都扎手,却舍不得扔掉……
父亲的一生,勤劳俭省,沉默寡言。父亲病逝后,“我”写下他的“生平”。业余编剧罗运生忍受着孤独,笔耕不辍,文学的荣光却始终没有落在他的肩上。艺术青年丘河初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只有在画画时,他才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行为乖张骇俗的诗人劲辉,追求的梦想逐一破碎,最终陷入无物之阵。心气高傲的农村青年吴安柱,为出人头地,走上一条危险的路途……妻子死后,张因兵的哀伤尚未淡去,却在手机上意外发现妻子的秘密……
《叙旧》是作家魏思孝最新小说集。十篇小说,十场萦绕于心的记忆——亲友的面庞、自我的跋涉、生活的况味,都在这里一一诚实摊开。在这些小说中,魏思孝通过一个个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及其命运轨迹,写出了我们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的某种人生阶段:怀抱理想却频频受挫,耗尽力气却收获寥寥,所爱的人已在回忆中,故交友人日渐疏远,突然的风暴将生活击溃……小说语言精炼质朴,平实中见跌宕,冷峻中有温情。作者极擅对人的体察与同情,通过对日常经验的细致书写,展现个体的切身处境与内心世界,写出了生活的不易与不甘,与命运的如影随形。
|
| 關於作者: |
|
魏思孝,1986年生于山东淄博。出版有《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土广寸木》等多部作品,曾获第三届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等荣誉。《王能好》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土广寸木》获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入选南方周末2024年度十大好书等重磅榜单。
|
| 目錄:
|
1生平
2亲家
3丧偶
4内情
5闲话
6诗人
7业余
8聚会
9事迹
10叙旧
11后记
|
| 內容試閱:
|
生平
1,
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活到新世纪刚迈进第二个十年。五十多年里,我不清楚他是否有觉得生活轻松的时刻,我认为这样的情况不多,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是一家老小的生计。至于他自己有什么喜好或者消遣,我并不太清楚,春节时喜欢多买些鞭炮、烟花和二踢脚可能算是一个。面对母亲的指责,父亲总说,这是驱穷气。晚上他一个人披着袄,在天井里放完鞭炮,进屋时总一脸兴奋,似乎来年家景会更好些。从我五六岁记事起,他就是年近四十岁的中年人,关于他过去的岁月我知道的不多,也很少听人提及,仅有可供联想的是他第一代身份证上模糊不清的照片,因黑白和附着的网格图案,面目辨别不清,只是大概的五官。确实如母亲所说,浓眉大眼。母亲在数次相亲不成后,这次终于点头同意这门亲事。那时父亲二十七,母亲比她大两岁。周围的人劝母亲,说这人家负担重,嫁过去受累。父亲是家里最小的,爷爷奶奶岁数大了,还有一个弱智的哥哥。母亲嫁过来时,白面都没得吃,还要她隔三差五回娘家驮面接济。母亲同意这门亲事,除了父亲的长相,还有他嘴拙,不说大话,肯吃苦。她说,人老实,肯吃苦,日子就能过。尽管母亲在随后的岁月里,经常抱怨跟着父亲没过几天好日子,只剩吃苦受累。在农村,就是如此。这对年轻的夫妇,应该从各自的勤劳本分中映照出生活的希望,才如此相濡以沫,拌嘴争吵并没有让他俩懈怠或是背离。
父亲死后,我们收拾旧物,找出一沓他年轻时赶马车运货时的记工本。小开本,手掌大小。笔记本已经散页,只留下从一九九一年一月份到一九九二年十月份的。我翻到三十年前的今天:1991年10月18号:储运厂到(应为“倒”)重轨12.5米,共90支,1天。人员:元、方、于、王、达(父亲名字最后一个字),共5人。注:立金没干。当时,父亲和现在的我同龄,三十五岁,天气大概也如现在一样,气温中午在十七八度,早上和晚上只有四五度,需要穿上外套。地里已经种上了小麦,他当时父母还健在,都是过八十的年纪,只能做点零碎的家务活,要在未来的两年内相继生病离世。他的儿子五岁,还没上小学。他的女儿十岁,念五年级。他的妻子三十七岁,四处打零工。我脑海中浮现出年少时,在村口看到父亲坐在马车上身子蜷缩手持马鞭回家的画面。他下工没有准点,有次家里刚买了当时流行的玻璃茶几,天很晚了父亲还没回来,我一直担心他是否在路上出了意外,永远也看不到茶几了。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四号那天,记工本单独一页:总库至乙烯技校、召口建筑队,拉螺纹钢15#,1.05T,人员:达。注:毕义贤他们拉木头。红色笔,在旁边写:这一天。11.00元。(后一页是八月七号,中间有十余天空缺,没有找到活干。)这页左上角出现了我的名字,字迹和父亲的不同,笔画分离,大小不一,一看就是来自幼童。这天恰好是我的阳历生日。父亲进入这行,先是跟着毕义贤的车队干活。车队的头负责联系活,从车队的每个人里面抽成。老毕这边活不多,后来又跟着孟凡武干。老孟健谈,会来事。七八年的马夫生涯,装卸全靠人力,谈不上轻松。他正值壮年,有力气。一身黝黑壮硕的肌肉。
有劳当时在村里还有些威望的祖父,父亲年轻时在生产队里当过一段时间记账员,这大概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不需要卖苦力的日子。公社结束,分田到户,家里人口多,抓阄分到的七八块土地分散在村子周围。拔草、打药等零碎活略过不提,单说每年春秋两季农忙,机械化没有普及,六月份顶着烈日,拿着镰把麦子割好,打成捆,装到地排车上,运到麦场,驴或人力一次次拉石辊压麦秸,选出麦秆,等麦粒晒干的间隙,扛着锄头种玉米。每道工序,都让人晒脱一层皮。九月底,玉米熟透,掰下装车拉回家,扒皮系成垛,用绳子拉上屋顶,等冬天风干后再运下来手工脱粒。犁地、打地、扶脊、播种,每个流程都是一种难言的痛苦,如身披几十斤的枷锁,蚯蚓般在土地上挪动。我和姐都还小,跟在后面,只觉得日头难熬。父母总说,知道苦,就好好学习,以后别当农民。后来机械化普及,犁地、平地、播种都不太需要人力参与。我上小学时,有了脱麦粒的机器,人工把麦秸往仓里续。后来,脱粒机在地里收割,麦秸打碎在田里,不需要人工割麦子。我上大学时,有了掰玉米的机器,玉米秸秆打碎还田。这都是后话。播种后浇灌是个问题。村里没有机井,为了浇灌,家里四处借钱买了柴油机和水泵,从村边齐鲁石化修建的污水沟里没日没夜抽水灌溉。一两年,柴油机收回了成本。如此好多年,直到村里打了机井,每家地头都按上水阀。这是父亲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超前投资,还是在母亲的多番催促下。
父亲死后,又过了许多年,母亲可以从容回忆过去的家庭生活——主要集中在我的少年,他们的壮年。日子过得苦,负担又重,一次吵架后,父亲趁着夜色出了门。过了一会,母亲预感不好,出去寻他。父亲在屋后墙根蜷缩着,怀里揣着东西。母亲上去撕开,夺过敌敌畏摔了。母亲把父亲拽回家,训斥中夹杂着宽慰,鸡毛蒜皮的事用得上寻死觅活了,你死了我和孩子怎么办,你再弄这出我把你头给拧下来。死亡的主题,在母亲的讲述下只剩下她的诙谐和父亲的懦弱,至于这个男人为何想死,是否前不久自杀的堂哥触动了他,这都不得而知。我不清楚父亲后来是否有过轻生的念头,生活中少有顺心时刻的他还会屡次想到死亡。
公路越修越宽,越来越平整,到处悬挂着禁止畜类车的标识,马路也成为一个古旧的词汇。父亲把骡子和马车卖掉,思前想后没有买拖拉机。此后多年,母亲都责怪他。原因也无外乎,家里终于还清外债。或许也确实难以再借到钱了,亲戚们也都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一堆事。父亲放下马鞭,自己成了一匹骡马,开始漫长且艰辛的在附近化工厂、塑编厂打工的生涯,机器化没普及,主要是人力,黑夜颠倒,上十二歇十二,从疾病找上门到他去世,十多年里,一年到头,在工厂和土地来回腾挪自己的身姿。与赶马车时不同,我不知道父亲在工厂里怎么样,总归轻松不了。他古板、严肃、不耍滑头,同样也看不惯其他人偷懒,做事一板一眼,与工友的关系谈不上融洽,也有几个投脾气的。上完夜班,为了让自己快速入睡,他有了喝劣质白酒的习惯。更多时候,下了夜班,白天还要忙家里的农活,只能短暂睡一会。家里弥漫着一股化学原料的味道,他越来越沉默寡言。我很少看父亲再笑过,身形总是疲惫。
自我上高中,在家越来越少,沉浸在青春期的哀伤中,不考虑学业,为稚嫩的情感奔忙,家和亲情被闲置在角落,是无需费心经营的。那些年,父亲在我记忆中是模糊的。总结也成为一件艰难的事。父亲仅有摆脱劳作的日子,大概是几次住院,一等到指标稳定,身体恢复些气力就着急出院,为了省钱,为了把花掉的钱尽快再赚来。他成了家里的一个无底洞,只身跳进去,用自己的身躯填补这个缺口。父亲当然不知道西西弗斯,他大概也体会到自己身上发生的荒诞和无力感,愁容下的不忿,对自己失望,重复祖辈们的老路,认命且把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我带来的总是失望,他没有在活着的时候,从我这里得到慰藉,更多的是担忧。
父亲一米七的个头,最胖也没超过一百五十斤。四十七岁那年,他再次住院,医生警告他这次不养好后果很严重。父亲戒烟(后来又抽了),养了几只羊,穿着棉裤棉袄,每天去放羊,打扮比同龄人老了一辈。吃不起医生说的补充蛋白的鱼和肉,母亲买了成筐的胡萝卜。赚不来钱,父亲心存亏欠,在家里有些抬不起头,脾气都缓和了许多。来年春天,身体指标稳定后,父亲又去厂子干活。到后来查出癌症,七八年间,他再没住过院,也避讳去医院体检。我不记得父亲曾吹嘘过自己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过去的人生似乎并无可炫耀的地方,肯定不是所过的生活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他压根也不是对生活充满野心的人。人群中,他并不现眼,却无形中给人踏实和信任,大家都称呼他老魏,也并不是年龄的缘故。他是许多逆来顺受的农民中普通的一个,也是构成社会的基石,勤恳又愚昧,依赖过往贫瘠的人生经验,对新鲜的事物总是抱有警惕和本能的距离,容易被蛊惑,又绝不迈出危险的一步,肩膀上承担着生活,步伐谨慎又足迹明显。他唯一傍身的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力气,这些都失去后,个人就没有了价值。
父亲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吃穿用度上都是如此。有次过年,他吃过一次野猪肉,回来和我说,觉得我没跟着他去吃,是个损失。我不清楚他是否还吃过其余的美食,无非就是从酒宴上吃平日家常菜中不多见的食物。少年时的饥饿让父亲对粮食尊重,也从来没表露过想要吃什么。对口腹之欲,他有着一种内敛的尊严。他十来岁时去挖沟渠,搬石头,能吃上一根油条,带油性的东西,就觉得很满足。过去艰苦的日子,我也没办法深入体会,一如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身为人父,督促女儿多吃虾,她摇头不想吃时,我反观自己少时吃的都是虾皮,吃到一整条虾时早就过了发育的年纪。毛呢大衣是我印象中父亲穿过的最体面的衣服,只在过年时穿一下,又明显感觉出他有些不适应,姿态拘谨,像穿着盔甲。后来再拿出来,衣服崭新,但款式已经过时。干体力活时搭配粗布衣服,工厂的工作服也常年沾染着灰尘。父亲很少穿衬衣,衣服都是偏黑色,耐脏为主。父亲有过的交通工具——自行车、马车、摩托车、电动车。他会简单修理柴油机,闲置后用帆布包裹,十多年后还能用,因为价钱太低又舍不得卖掉。摩托车的后备箱里常年备着工具和火花塞,小问题他都是自己解决。经他手的物件,都维护得当。这是精通各类农活外,他为数不多的特长。他爱惜物品多过爱惜自己。
父亲成长的年代,物资短缺,生存艰难,民风的淳朴和友善只在没有利益纠葛时。蛮横不讲理,偷奸耍滑,不占便宜就是吃亏更是流行的生存准则。这与家族的性格相违背,老实除了换来好名声,别无他用,魏家的男人都不好争抢,强悍的妻子就至关重要。父亲性格中的腼腆和不时闪现的细腻,有些话总是开不了口,争夺意味着在意,这有碍他的自尊,又生怕别人瞧不起,吃亏也就成为常态。母亲以其泼辣直爽的性格捍卫着家庭,不占别人便宜,也绝不吃亏。父亲经常怀念生产队的日子,一帮人出工不出力,所有都是公社的,都没钱,也谈不上攀比,关系融洽,有说有笑。包产到户后就不一样了,各自为家,自私自利,父亲失落是看不惯的太多,又无力改变,也无法融入。拖欠工资,少记账,这些事情都由母亲出头解决。在村里,父亲能说上话的人不多。他不喜欢话多的,也不喜欢做事邋遢的。他不够聪明,有时急躁,但手脚足够麻利。父亲在村里有几个要好的玩伴,单身时也凑一起打牌喝酒。成家后为了生活,平时来往不多,逢年过节保持走动。村里集中盖砖瓦房屋的那些年,在家里或给邻居帮工,管饭喝酒,父亲喝酒后成了另外一个人,话多,总是笑,他酒量不大,劝酒下定力不够,总是喝多,口齿不清说些酒话。母亲什么脏话都骂出口,为这事两个人经常吵架动手。母亲情急之下,拿过菜刀要剁下他的头。这都是他们三十多岁的事。
父亲赶马车那些年,和车队里的七八个人来往密集。车队散了,有时在路上碰到,还异常亲切,各自家里婚丧嫁娶都会通知。有几个人死得早,生病,出车祸。孟凡武死时,父亲尤为难受。我记事起,总见到他。盖屋时老孟还来送过肉和菜。父亲四十多时,在南山上的一家私人化工厂当车间主任,比普通工人一个月多领一百块钱,也负责给新来的员工培训。小耿二十出头,小邱三十多岁,他们三个人在一组,负责一条流水线。小耿和小邱家里没地,父亲农忙时,多亏他俩补上。父亲那阵子心情好,下工后总会说起他俩。先前在别的化工厂当班长,管人,不听,受气不少。小耿和小邱来家里吃过饭,那天父亲喝多了,在院子里吐完,躺在地上睡着了。母亲回来,拿着铁锨把他拍醒了。母亲气了好久,不是疼喝酒,他那时肝已经不好,住过一次院。后来,母亲就不让人来家里喝酒,也不允许父亲出去喝。父亲死时来了许多人——亲戚、朋友——没通知外面的。有些老相识,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人多。一是,父亲算不上老,亲戚朋友大多也健在。二是,平时村里的丧事,父亲作为家族的代表,鞍前马后,积攒下的名声。父亲的丧事,算得上风光,不缺人气。上礼金的答谢名单,写满一张张白纸,在村口的墙上贴了一长溜,比村里另外一个人的答谢名单,长了足有一倍多。
2,
肉体消亡,伴随精神上的复活。父亲总在不经事间出现,我们刻意回避,但他留下的印记在肉眼所及的任何角落。遗像在柜子里一放十年,每次打开找东西,隐约的黑白色调在心里搅动起风暴。我们假装没看到,快速关上。缅怀在暗地里进行,没人提议把遗像悬挂在墙上。抽屉里还有父亲留下的手机,黑色的老式诺基亚,和其余杂物一样布满尘土,躺在不显眼的边角处。父亲的衣物随着下葬当天、“五七坟”、“百天坟”陆续焚烧,母亲偶尔还能翻出一些,无一例外都是她帮着挑选的,来历都记得清楚,或是崭新没穿过几次,留着重要场合再穿,或是处于节俭的本能,不舍得扔掉,。抽屉里有他的记工本,上面别着圆珠笔,内页上的字迹如旧,诸如“拌料”“检修”“零工”,简单明了的记录那些年每天都是如何度过的。父亲生前爱听的邓丽君和民歌合集的碟片,还在电视柜下面的抽屉里,和不用的影碟机放在一起,都已经过时。父亲生前听碟片的机会也不多,过年打扫卫生会放。化工厂车间噪音重,他听力受损,音乐声音放得很大。有些我们没有勇气再去看,比如婚礼录像的光盘,里面有他唯一的影像。过去那么多年,不知道光盘还能不能出画。双亲致辞环节,母亲接过司仪的话筒,看着天井里围观的乡亲,平时快言快语的她,嘴唇打颤,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父亲戴着毛线帽子,上身穿着黑色棉服,抢过话筒,开口先感谢共产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吃上饭。这句话引来众人一阵哄笑,父亲抿嘴,又感谢老少爷们大冷天来帮忙。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少有的面对这么多人公开讲话,不知心里预习了多久。父亲用过的农具,农忙时我们继续用。他赶马车那些年收攒下来的木板和铁器,扔也不是,留着也没什么用,还堆在杂物间。
父亲留下的东西逐渐被清理。
父亲骑了十二年的摩托车,在他死后不久卖给收废品的。他最后那年,代步工具是我结婚时买的电动车。摩托车破旧不堪,保险杠松了,后备箱坏了,机身掉漆,排气筒被铁丝固定着。里程表早就坏了,定格在十五万公里。父亲骑着它找过走失的哥哥,没有找到。父亲骑着它送过我上学,也驮着粮食送去姐姐读书的中专食堂换粮票。后来姐姐嫁人,父亲又骑着它去城里给姐姐送馒头。父亲骑着摩托车去医院看病,也载着母亲赶集。十来年中,这辆摩托车载着我们家人四处远行。父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最多到临市,也是坐长途车。他没有坐过火车,更别说是飞机。两百公里以内,他总是骑摩托车。
父亲一砖一瓦建造的房子还在,自他死后,房子总是出现各种问题,厦檐漏水,雨棚坏了,屋里的电灯泡灭了,抽水泵坏了,天井的水泥地面裂纹。每次遇到这些状况,我都想到父亲,他对这些拿手。母亲看着我大致抹平的地面,装上的雨棚,总是不满意。如果他还在就好了。我怎么是这种命。那些年,母亲总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
埋在村西边的墓田,有上百个坟包,村里死去的人都在这里,其中一个是父亲。一年后,物流园占地,墓田迁到几百米外。后半夜,全村赶在天亮前迁坟。父亲的骨灰盒已经腐烂,骨灰露出,里面有大块的骨片。我手捧骨灰,想起从火葬场回家,捧着骨灰盒的那个烫手的午后,感慨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的温度。我用手指抚摸着他的骨片,心想这是我对父亲最为密切的触摸。几年后,又一次政府占地,再次迁坟。如今的墓地,在西山上新修建的通往城区的公路的下面。每个墓碑旁都栽种着松柏,比先前的整洁。大理石碑面扣住墓穴,呈一个斜面。村民还保持着压坟头纸的习惯,用石块将黄纸压在大理石的一侧。墓穴分为两个坑,其中一个是留给母亲的。碑面没有刻字,母亲说等她死后一起刻,省事。我在城区西北买的房子,如今每次回村都走这条路,歪头能看到墓地里茂盛的柏树。一年中,除了春节、清明、中元节、忌日、寒衣节定时去上坟,其余时间我没去过。有时,我心里一些话没处诉说时,也想在父亲的坟前说一下。尤其是他刚走那会,大到世界上的新闻,小到家族和家里的事,都想对他说。但每次在坟地里,听到自己的声音,都有些羞怯,只好在心里面默念。
我时常梦到父亲,梦里他不说话,只是笑。梦到最多的是,父亲身体好了,我高兴坏了,叮嘱他不要出去干活,就在家里待着,没事遛弯晒太阳,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他身体没事,一切都不是问题。梦醒后,更多的是遗憾,没来及告诉他真实的病情,让他走得不明不白。他对我会有怨恨,以为不给他看病,也会怀疑一生操劳为整个家付出,到头来换回什么。父亲会认为自己的一生失败,起初我也如此以为,慢慢的,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日渐高大和伟岸,我缺乏他对生活的热忱,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到繁重枯燥的劳动中,克制自己的私欲,节衣缩食,一切从简,只为多省下点钱用在家庭生活中。他的妻儿老小以及后代,是他个体的延续。
一些字眼——丈夫、老伴、那口子——成为母亲心中跨不过去的伤口。她厌恶别人提父亲的名字,不管是关切还是增加谈资,她一律说,提他干什么,谁家里还不死人了。慢慢的,好事者开始给母亲介绍老伴。她态度坚决,不找,又不是孩子还小,养不活。自行车车胎坏了,母亲推去村口老宋的修车铺,回来便对我说,有你爸的时候,他给我补胎,车胎没气了,也是他给我打气,这些事根本不用我操心。干活回到家,只有她一个人,母亲也想,你爸要在家,早就把饭做好了,我吃现成的,现在倒好,冷锅冷灶的。更多的时候,母亲的心事没处说,遇到事没人商量,尽管父亲活着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个拿主意的人。她总絮叨两句话,1,我怎么是这种命。2,谁知道我心里的滋味。几年后,母亲有了孙女,这多少缓解了她的心情。这些年,母亲生过一次病,住院半月,按时吃药。她习惯一个人住在村里。晚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是母亲主要的消遣。她闲不住,不是出去干活,就是伺候庄稼,家里家外,有条有理,都没撇下。母亲遇到事和我说,听她说完,她自己决定。
十年后,母亲终于坦然怀念过去,说父亲当年怎么样。语气有遗憾,表情更多是温情。母亲照旧要强,在外面吃不了亏。从去年开始,母亲跟着村里的人,在城区维护绿化带,拔草,浇树。早上去,下午回来。四里八乡的老头老太,她总捡着轻快的活,回来和我说这天又怎么偷懒的,很是自傲。十年里,母亲体重控制在一百三十斤左右,血压正常,血糖有点高。脸上的白斑病,又长出新的正常皮肤,还不如都是白色,样子不算好看,这是她的一块心病。母亲不愿意住在城区,一是没人说话,二是不喜欢别人审视她的目光。在村里,熟人社会,没人过多在意她的面容。六十岁后,母亲每个月领两百块钱的养老金。她时而感叹,父亲没赶上好日子,如今不用节衣缩食过日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水果和肉不断。她偶尔对儿子露出一丝的骄傲,买房也没欠下什么债。母亲身型有些佝偻,干了农活总是腰酸背痛,恢复需要好几天。她的生活哲学是争取活久点,有病要及时看,这是她从父亲身上吸取的教训。我想,母亲想到父亲的频率,只会比我更高。她住在和父亲一起亲手建造的砖瓦房里,墙面上有了裂纹,小毛病不断,并不碍事,房子没人住才老化得快。有人住,人气就在。有年夏天,连续下了半个月的大雨,后墙结满青苔。天好后,母亲用刮刀,一块块刮掉,看不出痕迹。
这些年,村里各家各户在口粮田里种上果树,等着占地拿补偿款。如今家里的五亩地,只有两亩还种着粮食,比以前省心多了。麦子打回家,在胡同里晾晒两天收起来。玉米装袋用绳子拉到屋顶上,等冬天晒干后再推下来脱粒。其余三亩地种上了树,在树的空隙,母亲栽种时令蔬菜,以及地瓜、花生、南瓜等。吃不了,送给邻居,或是在村口的集市上卖。十年过去,每隔一两年,政府下发拆迁的文件,又一直没有动静。传闻越来越多,规划的搬迁地点也从市区到了镇的西边。
父亲死的那年春天,村里刚选举完,干了三届村主任的刘猛下台。王本道竞选成功,在全村选了四个小*长,父亲是其中之一。有次打电话,父亲喝了酒,心情不错,感觉自己受到重视。三年后,刘猛又竞选失利,王本道要不回占地款,各项补贴也都不知道怎么花掉的。我们村成了四里八乡的笑柄,在区县的考核评比中垫底。以刘、王为首,村里分成对立的两拨人马。大街小巷的墙上粉刷了王本道贪污的标语。王本道磕绊着干完第二任期,刘猛当上村主任。王本道借助前些年发展的本族党员,成了村书记。国家出台政策,有犯罪前科的不能在村里任职,刘猛又下去了。没多久,上面也撤掉了王本道的村书记。如今,村书记是镇上的一个科员,早年从村里考出去,上面委派他回来。大家对他不熟,也不服众。这十年,母亲一直是村民代表,去村里开会,回来就开骂,没有一个能办实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