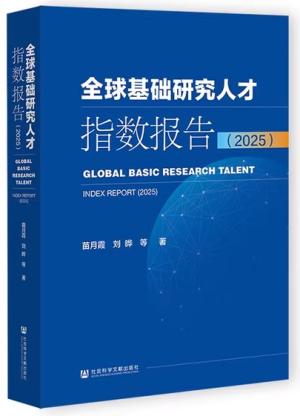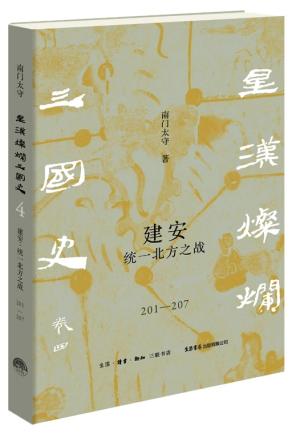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全球基础研究人才指数报告(2025)
》 售價:HK$
1520
《
投资的心法:从传统文化视角看清投资中的规律
》 售價:HK$
352
《
如何使孩子爱上阅读:家长和教师能做些什么(基于科学原理,培养孩子阅读水平与内在动机)
》 售價:HK$
255
《
博物馆学辞典 博物馆学核心工具书,权威专家联合编纂,理论与实践的指南!
》 售價:HK$
1255
《
战时的博弈:教宗庇护十二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秘史(理想国译丛075)
》 售價:HK$
755
《
明亡清兴 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
》 售價:HK$
347
《
北大版康德三大批判
》 售價:HK$
1428
《
建安 统一北方之战(201—207)
》 售價:HK$
250
編輯推薦:
★ 文学、物理学、哲学的跨学科深度对话
內容簡介:
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奇才,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共振。
關於作者:
威廉·埃金顿
目錄
引言 它去哪儿了?
內容試閱
引言 它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