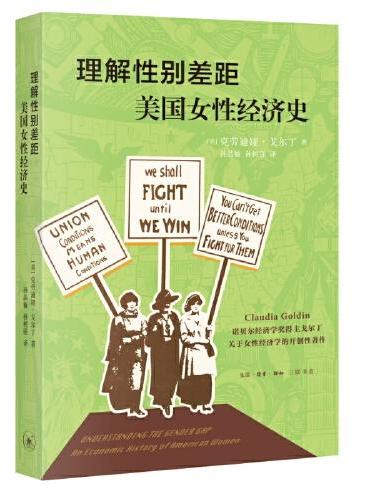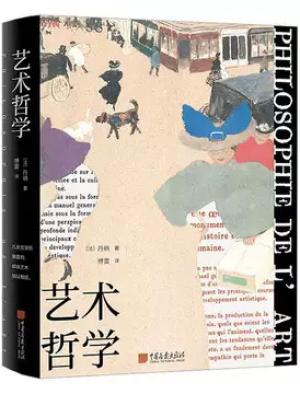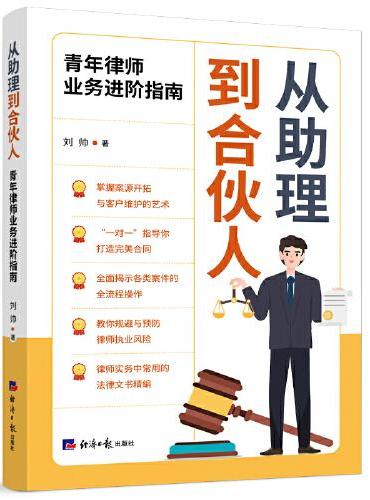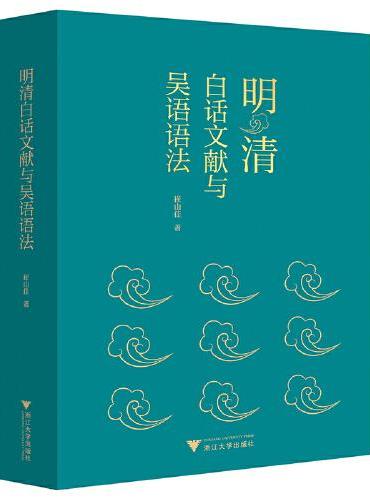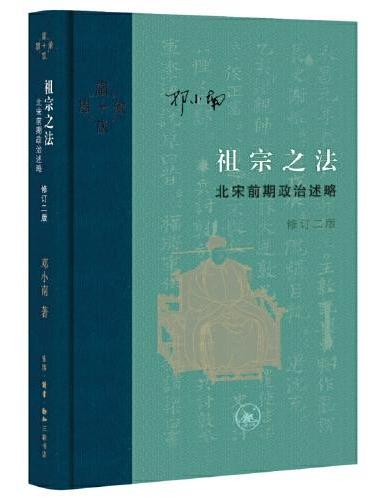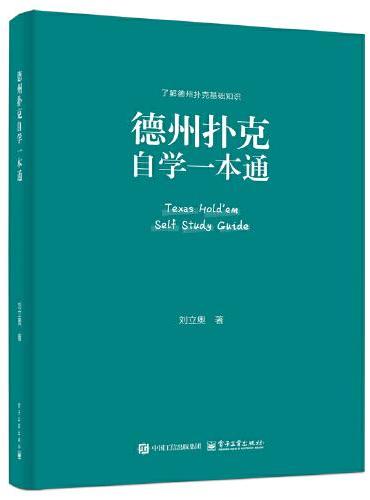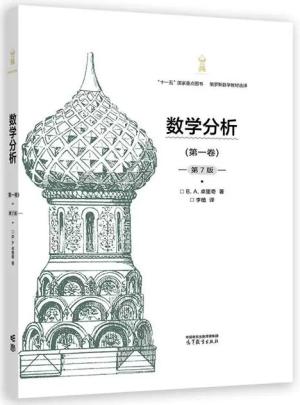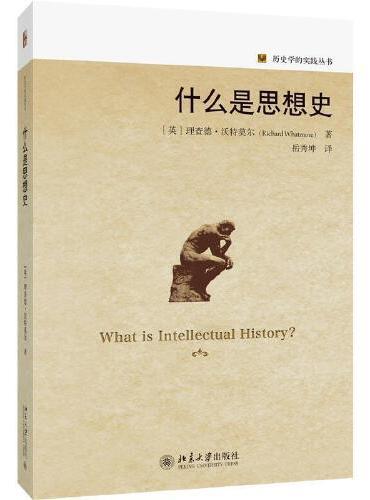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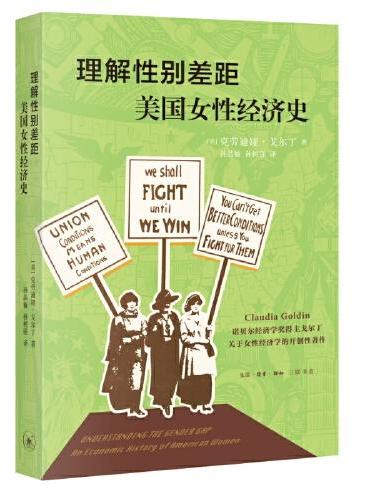
《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
售價:NT$
4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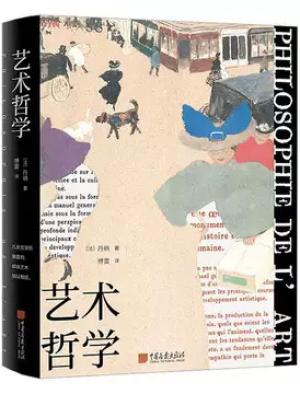
《
艺术哲学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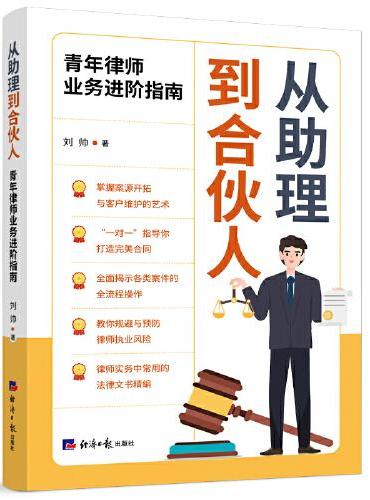
《
从助理到合伙人-青年律师业务进阶指南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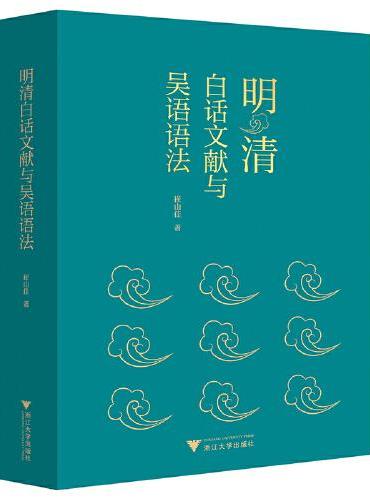
《
明清白话文献与吴语语法
》
售價:NT$
10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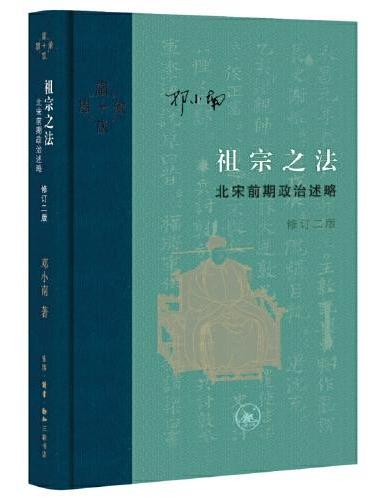
《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二版)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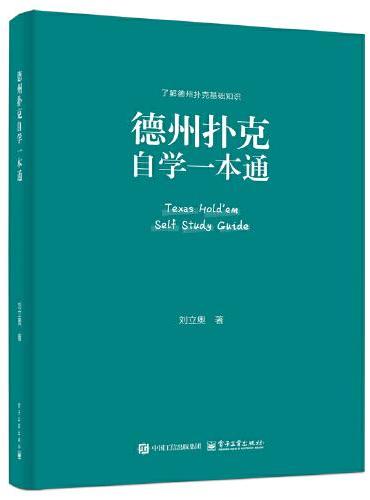
《
德州扑克自学一本通
》
售價:NT$
25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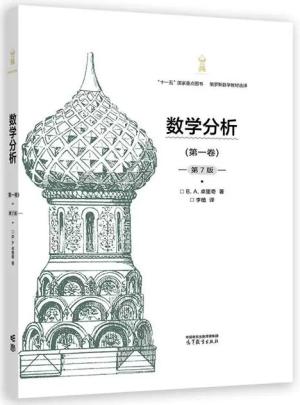
《
数学分析(第一卷)(第7版)(精装典藏版)
》
售價:NT$
4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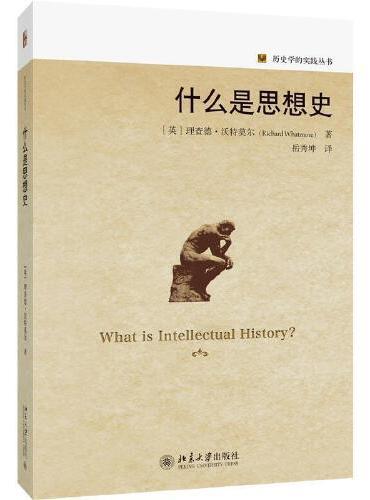
《
什么是思想史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
售價:NT$
286.0
|
| 編輯推薦: |
“小说之王”科马克·麦卡锡最经典之作
全球畅销1000万册
美国国家图书奖与国家书评奖获奖作品
西部 牛仔 田园
勇敢的人类亲近与回归大自然的瑰壮画卷
热血少年马踏天下的追梦传奇
|
| 內容簡介: |
《天下骏马》讲述少年牛仔约翰·格雷迪不满于家族牧场的衰败,与好伙伴罗林斯一起离开故乡得克萨斯,骑着心爱的马儿,南下遥远的墨西哥追寻心中梦想。途中他们遇到了骑着漂亮的大棕红马的少年布莱文斯,三人结伴南行。可是,谁也不曾想到,大棕红马却成为小伙子们的梦魇……
因为这匹骏马惹祸上身,布莱文斯只得独自离去,格雷迪和罗林斯到达理想的处所圣母牧场,成为整天与马儿为伴的牧人。其间,格雷迪爱上了场主的女儿。在异国的土地上,这朵爱情之花能否抗击暴戾难御的命运巨轮?
正是由于大棕红马引来的麻烦,格雷迪和罗林斯被人从牧场逮捕。造化弄人,他们与命案在身的布莱文斯意外重逢。但是,在押送过程中,人生中最可怕的厄运却盯上了他们……
|
| 關於作者: |
科马克·麦卡锡(C·rmac
McCarthy),美国小说家、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1933年7月出生于美国罗德岛。代表作有《血色子午线》、《边境三部曲》、《老无所依》、《路》等。《血色子午线》开启麦卡锡创作的转折点,在《纽约时报》评选的“过去25年美国最佳小说”中名列第三。《边境三部曲》引起图书界轰动,荣膺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奖。《老无所依》改编为同名电影,力夺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项重量级奖项。《路》荣获2007年普利策最佳小说奖,据其改编的电影《末日危途》引起极大轰动。这些均奠定了麦卡锡的大师地位,令其由此获誉“当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海明威与福克纳唯一的继承者”。
|
| 內容試閱:
|
约翰·格雷迪拿着布袋径直朝那匹大头驹走去。这马驹转过身小跑起来,约翰·格雷迪陪着它沿栅栏走着,拾起拖在地上的绳子,把马拉转过来。马驹站住,身子在微微颤抖着。约翰·格雷迪走到它身边,又开始和它谈起话来,然后用粗布口袋去擦拭和抚慰它。罗林斯则取来了马鞍、鞍褥和笼头。
这日,他俩用了一整天工夫驯骑这支由十六匹小马驹组成的加鞍备用马群。约翰·格雷迪先骑第一遍,罗林斯骑第二遍,直到夜里十点方才停手。星期二他们又驯了一天马。在星期三清晨,太阳还未露面,约翰·格雷迪便将第一匹马套上了鞍,向栏门骑去。
“打开门。”他说。
“我来挑一匹马上鞍,好跟着你。”
“没那么多时间。”
“要是那匹大头崽子把你的屁股摔成两半,你就有时间了。”
“那我最好待在鞍子上。”
“我得找匹好马上鞍。”
“那好吧。”
约翰·格雷迪牵着罗林斯挑好的马骑出栏门,等罗林斯关好门过来上马,两人便并肩上路了。两匹野性尚未脱尽的小马驹不安地踱步侧行。
“这简直成了瞎子领着瞎子走,对吧?”
罗林斯点着头:“这就好像老丁骨瓦茨,他给我老爹干活的时候,大家都对他那个粗重的喘气声抱怨不休。他跟他们说,这样喘气总比压根儿喘不了气要强。”
约翰·格雷迪咧嘴一笑,用靴子踢了一下马腹,让它跑起来。他俩便上了路。
下午三点左右,约翰·格雷迪把这十六匹马驹又都驯骑了一遍。罗林斯在栏里忙着的时候,约翰·格雷迪便把罗林斯选中的那匹小格鲁洛骑出去遛了遛。牧场北边两英里处有一个浅水湖,湖畔的小路边长满了蒲草、柳树和野梅。就在这块景致优美的地方,那姑娘骑在黑马上从他身旁越过。
他听到身后有马蹄声,本来要转头回身看看的,但听到马儿变了步法。他一直等到那匹阿拉伯骏马和自己的马并行时才去看那女孩。她的马踏着步子,长脖子仰成优美的拱形,一只眼睛瞟着旁边的大头马驹,目光里透出的不是警惕,而是马类之间的些微反感。她骑到约翰·格雷迪身旁五英尺远的地方,转过那张轮廓优美的面庞,从正面看着他。她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女孩点了点头,或者不如说她只是把头稍稍低了一下,以便看清楚他骑的是什么马。约翰·格雷迪只见她头上的阔边黑帽微微倾斜了一下,长长的黑色秀发随之轻轻飘起。然后她便从他身边骑了过去,她的马又变了步法。她的娇躯笔挺,纤细的腰肢衬着那宽宽的双肩,打马小跑着上了路,在马上显得风姿绰约。这匹大头马驹在路中心停下来,两条前腿叉开而立。它的主人坐在鞍上,痴痴地望着女孩远去的背影。他本想和她说话的,但那双眼睛在短如心跳的一瞬便永远地改变了一切。她消失在湖边的柳丛中,一群小鸟被惊了起来,带着微细的叫声从他头顶飞过。
这天晚上,安东尼奥和总管来到畜栏视察这批小马驹时,约翰·格雷迪正在训练格鲁洛小马驮着罗林斯倒步走。他们很有兴趣地看着,总管还边看边剔着牙。安东尼奥试骑了两匹备好鞍子的马,让它们在畜栏中来回地跑,还令它们骤然停步。他下了马,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和总管一起去检查畜栏另一端的马匹了。罗林斯和约翰·格雷迪互相望了一眼,便把两匹马卸了鞍,把马群赶进了栏,提着鞍子和其他马具回了大房子,擦洗过后准备吃晚饭。牧人们已经在长桌旁坐定,他俩取了自己的盘子,在炉旁倒了咖啡,走到桌旁,跨过一条腿坐下。桌子中央有一陶盘玉米饼,上面还盖着毛巾。约翰·格雷迪伸手一指,想让他们递过饼子来,众人登时从桌子两边伸出了手,端起盘子传到他俩面前。这场景就像在举行什么仪式。
三天以后,他们进了山区,工头派了一个男佣为他们做饭并照料马匹,还派出三名比他俩大不了几岁的年轻牧人同行。这男佣是位单腿残废的老人,名叫刘易斯,曾先后在托雷昂、圣佩德罗和萨卡特卡斯打过仗;几个年轻的牧人都是当地的孩子,其中两个都出生在牧场,只有一个到过蒙特雷城这么远的地方。
他们每人领着三匹马,外带专驮食物和炊事篷的马,排成一队进了山。他们在山地的松林、浆果鹃丛和干河床等野马躲藏地捕获了一群野马,把它们赶上了高高的平顶山,圈在一道深谷里。这里有早在十年前就设置好的栅栏和栏门。野马在里面兜着圈子,乱转乱挤,尖声嘶鸣,并在陡峭的岩坡上不断攀爬,然后转过来互相缠斗,又咬又踢。约翰·格雷迪提着绳子在喧闹的马堆里行走着,满身是汗和尘土,仿佛是在做有关马儿的噩梦。当夜,他们在一处高地上宿营。山风骤起,篝火被刮得像锯齿一样在黑暗中闪动。刘易斯老人坐在火旁向几个年轻人讲述了这个地方和住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其中提到了一些故去的人物的经历。老人终生爱马,他和父亲以及两个兄弟都曾在骑兵里作过战。父兄虽都战死疆场,但是他们无不极其蔑视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及其罪恶行径--比鄙视其他任何恶人恶行更甚。老人说,和韦尔塔相比,犹大倒成了另一个基督了。这时,一个牧人移开了目光,而另一个则开始祷告,祈神赐福。老人又说,战争毁了这个国家,但只有用战争才能制伏战争,正像术士用蛇肉医疗蛇伤的道理一样。他谈到了自己在墨西哥的沙漠上打的诸多战役,那年他胯下好几匹马先后死去。老人认为马的灵魂反映出人的灵魂,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准确。他说马也是喜欢战争的。小伙子们说他们对此略有耳闻,但他说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体会到。老人的父亲说过,没有骑马打过仗的人是不会真正懂得马的。他说,虽然他希望事情不像父亲说得那样绝对,但事实却正是如此。
最后老人说,他曾经看见过马的灵魂。那可是十分可怕的东西。他说,这灵魂只有在马死的特定时刻才能看到。因为马类共有一个灵魂,而它们各自的生命乃是由全体马使之成形,最终难免一死。他说,如果一个人能认识马类的灵魂,那么他就能理解所有的马了。
他们都坐在地上抽着烟,望着余火最深处通红的木炭噼啪作响,四处迸溅。
“那么人是不是也这样呢?”约翰·格雷迪问道。
老人努了努嘴,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后来他说,人与人之间没有马类之间那样共通的灵魂,那种认为人类可以相互理解的想法可能只是个错觉。罗林斯用蹩脚的西班牙语问老人,马儿是否也有天国,老人摇着头说,马儿不需要天国。最后,约翰·格雷迪问老人,如果所有的马都从世上消失了,马类的灵魂是不是也会消亡呢,因为这灵魂已经没有了容身之地。但老人只回答说,要谈论世上没有马的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上帝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每次捕捉到一批野马,他们便押送着涉过溪流,穿越山谷,行经肥美的草地,最后把它们圈进栏里。他们连续三周都干着这个活,到了4月底,他们已经将八十匹野马投入栏中,其中大部分都已经被驯服,有的都被选定上鞍备骑了。此时驱赶野马的工作仍在持续,每天都有一群群的野马从荒野被送到牧场的草地上来。可是不少牧人每次只能牵两三匹马上路,因此大批的新马都还被关在山上的畜栏里。在5月的第二个早晨,主人专用的红色“赛斯那”飞机由南方开来,在牧场上空盘旋一圈后,开始斜身转弯,降低高度,最后滑翔着驶离众人视线,掠过一丛树林,降落下来。
一小时后,约翰·格雷迪手里拿着帽子,站在牧场的厨房里。屋里,一个女人正在水池旁洗涤碗盘,一个男人正坐在桌旁看报纸。这女人见到约翰·格雷迪,立即把手在围裙上擦干,走到另一间屋子里。不一会儿,她回来了,说:“请等一会儿。”
约翰·格雷迪点点头。“谢谢。”他回答道。
此时那个男人站了起来,他折起报纸,穿过厨房,拿回来了木制挂肉架、剔骨刀、油石,并全部摊在一张大纸上。与此同时,牧场主埃克托尔先生来到了门口,他站在那里,直视着约翰·格雷迪。
他是个瘦削的人,但肩膀宽阔。他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像个北方人。他走进厨房,作了自我介绍。约翰·格雷迪立即把帽子从右手移到左手,和埃克托尔先生握了手。
“玛丽亚,”牧场主说,“请来点咖啡。”
他伸出手掌朝着门廊示意,约翰·格雷迪便穿过厨房,走进大厅。厅里清凉、安静,可以嗅到蜡和花的气味。落地大钟立在过道左侧,铜制的钟摆在玻璃罩后来回摆动。他转过身来回头看时,牧场主对他一笑,并把手朝餐厅一指,“这边请。”他说。
他们在一张英国胡桃木的长桌旁坐下,餐厅的四面墙上都覆盖着蓝色的织花布,悬挂着人物和骏马的画像。餐厅的一头是胡桃木餐具柜,上面摆放着暖锅和细颈玻璃饮料瓶。外面的窗台边有四只猫卧在那里晒太阳。埃克托尔先生伸手到身后的餐具柜上拿了瓷烟灰缸放在他们面前,又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小锡盒英国香烟,打开口递到约翰·格雷迪面前。约翰·格雷迪抽出一支。“谢谢。”他说。
牧场主把香烟盒搁在桌子的中间,从衣袋里掏出银制打火机,先给小伙子点着了烟,然后自己也点上。
“谢谢。”
埃克托尔先生慢慢地往桌下吐出一道细细的烟气,笑了笑。
“喂,”他说,“我们可以说英语。”
“悉听尊便。”约翰·格雷迪说。
“阿曼多对我说你了解马。”
“我养过一些马。”
牧场主若有所思地抽着烟,似乎等着小伙子多说几句。这时,方才坐在厨房里看报的那个男人托着大银盘进来了。盘中盛着一套喝咖啡的用具--咖啡杯、奶精杯、糖罐,还有一碟点心。他把盘子放在桌上,在一边站了片刻,主人谢过他后,他便退了出去。
埃克托尔先生亲自将杯子摆好,倒上咖啡,然后朝盘中点点头,说:“请自便。”
“谢谢,我不加糖。”
“你们俩是从得克萨斯来的?”
“是的,先生。”
牧场主点点头,呷了一口咖啡。他双腿交叉地斜对着桌子而坐,脚上套着一双巧克力色的小牛犊皮靴。他转脸看了看约翰·格雷迪,笑着问:“你们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呢?”
约翰·格雷迪看看牧场主,又低头看着晒太阳的猫咪投在桌上的一排剪纸般的略微倾斜的影子,然后又抬起头看着牧场主。
“我只是想出来见见世面,我们就这样来了。”
“我能知道你多大了吗?”
“十六。”
牧场主扬了扬眉毛。“十六。”他重复道。
“是的,先生。”
牧场主又笑了。“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就告诉别人我十八了。”
约翰·格雷迪呷了一口咖啡。
“你的朋友也是十六?”
“他十七。”
“但你是个头儿。”
“我们没有头儿,我们就是哥们。”
“那当然。”
埃克托尔先生把盛点心的碟子朝前推了推。“请吧,”他说,“随便吃点。”
“谢谢您。我刚刚吃过早饭。”
牧场主欠身把烟灰磕进瓷烟灰缸里,又坐回去。
“你看雌马的情况怎么样?”他问。
“这一批里有几匹好雌马。”
“是的。你知道有匹名叫三条纹的雄马吗?”
“那是匹良种马。”
“你知道这匹马?”
“我知道这马参加过巴西大奖赛,我认为它产自肯塔基州,但它的主人却是亚利桑那州道格拉斯市一个名叫维尔的人。”
“对,这马生在肯塔基州帕里斯的蒙特雷牧场。它和我买的那匹雄种马还是同母异父兄弟呢!”
“是,先生。它现在在哪里?”
“它出门了。”
“上哪儿去了?”
“从墨西哥出门了。”牧场主笑道,“它一直都在忙着配种。”
“您是想养赛马吗?”
“不,我想养夸脱马。”
“就在这牧场上用?”
“是的。”
“您想让这匹雄马和刚逮回的雌马交配?”
“是的,你的意见如何?”
“我没什么意见。我认识一些配种的人,其中几个很有经验,但是我注意到,他们都很少发表什么意见。反正我知道有不少好的牧牛马是由良种雄马生出来的。”
“是的,你觉得雌马有多重要呢?”
“我看和雄马一样重要。”
“大多数养马人对雄马更有信心。”
“是的,先生。”
牧场主笑了:“我正好和你的观点一致。”
约翰·格雷迪朝前倾身,把烟灰弹掉。“您不一定非要和我一致。”
“当然不,你也一样。”
“是,先生。”
“再给我讲讲平顶山上那些野马的情况。”
“山上也许还有些好的雌马,但是不多了。剩下的我看都是矮小的劣种马了,有的只能凑合做牧牛马,就是到处都能看到的那种马。西班牙矮种马,就是我们过去常叫的--奇瓦瓦马,都是老非洲种。这些马都个头小,体重轻,它们也没有像拦牛马那样粗壮的臀部和后腿。但可以用它们去套牛……”
他说着说着停住了,看着自己膝上的帽子,用指头去划帽边的折缝,然后抬起头来说:“我说的您都知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