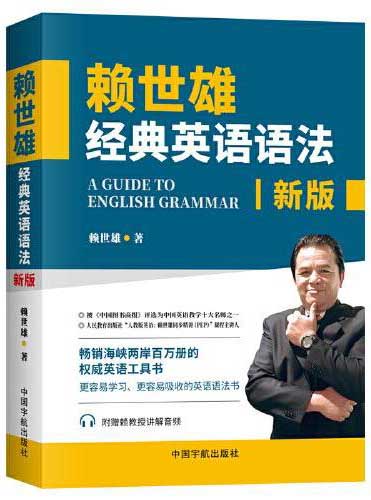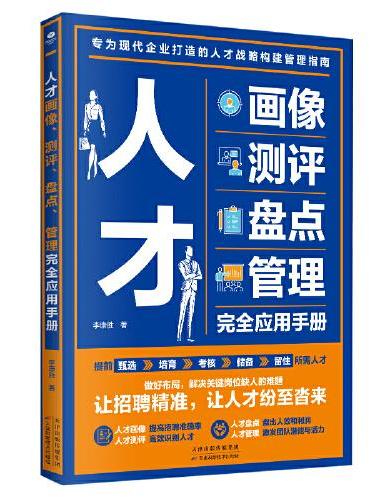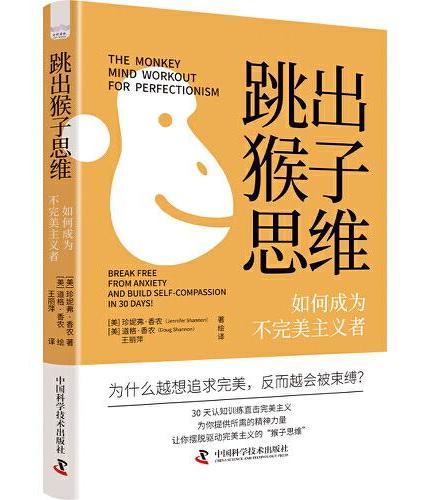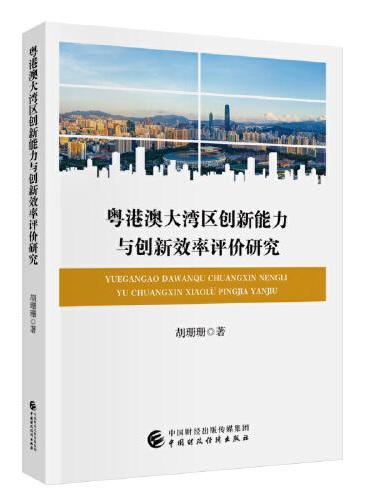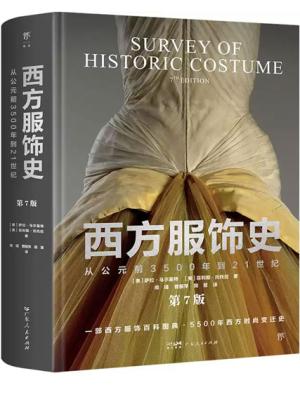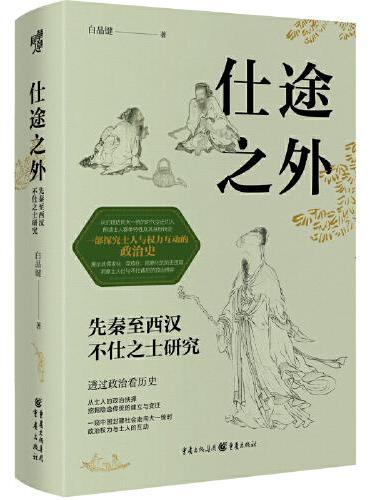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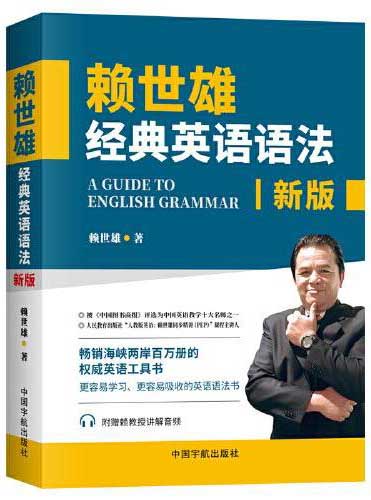
《
赖世雄经典英语语法:2025全新修订版(赖老师经典外语教材,老版《赖氏经典英语语法》超32000条读者好评!)
》
售價:NT$
305.0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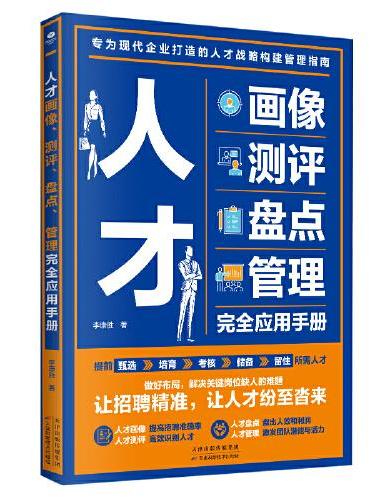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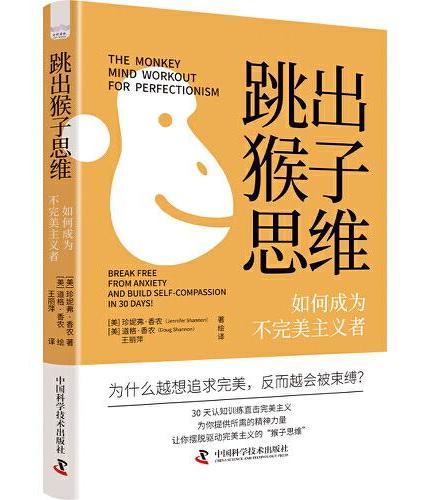
《
跳出猴子思维: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30天认知训练打破完美主义的困扰!实现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改变!)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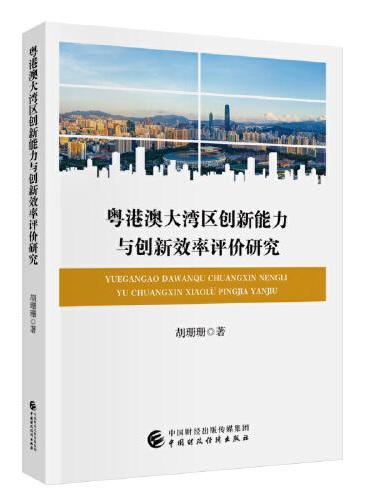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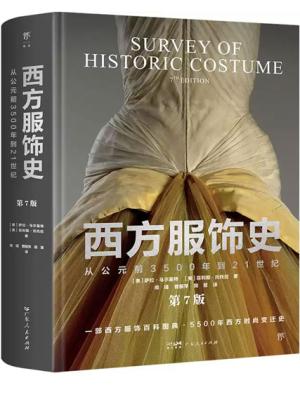
《
西方服饰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21世纪(第7版,一部西方服饰百科图典。5500年时尚变迁史,装帧典雅,收藏珍品)
》
售價:NT$
20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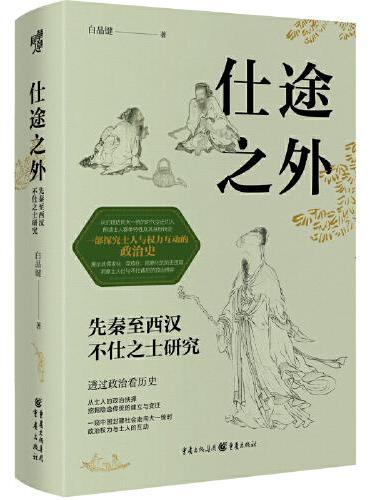
《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
》
售價:NT$
305.0
|
| 編輯推薦: |
再也没有人可以让你觉得好
你怀念的
自始至终都是 爱
这是一本直白赤裸的爱情宣言,放下世俗的顾虑,不再被舆论打败;勇敢追逐属于自己的爱情,却比任何时候更觉坦然。原来爱情不必假于外物。
畅销7年,王臣再度诚意修订:致我们终将被理解的爱。
|
| 內容簡介: |
《浮光》
是爱,让人万劫不复。也是爱,让人得到救赎。
这是一本直白赤裸的爱情宣言,爱上一个人,而那个人刚好是同性而已。
放下世俗的顾虑,不再被舆论打败;勇敢追逐属于自己的爱情,却比任何时候更觉坦然。原来爱情不必假于外物。
爱与性别无关,感觉对了就爱上,发现不解和歧视都徒有虚名。
原来这样快乐过,那我什么都原谅。
|
| 關於作者: |
王臣
王臣,被誉为“最具汉语文字美感”的作家。
曾先后被《亚洲周刊》等多家媒体报道。其作品一经出版均陆续登上各大畅销榜。
已出版长篇小说《世界上你最疼爱的那个人还在吗》、《柢年》,散文集《一个人流浪,不必去远方》、《你若不来,我怎敢老去》等。
|
| 目錄:
|
第二版序 七年之后你们还在吗
第一版序 独自心目悦和
第一场. 始 上阙种妖记 下阙冷花记
第二场. 渡 上阙流岚记 下阙沉鸟记
第三场. 劫 上阙蓝玉记 下阙投土记
第四场. 终 上阙焚光记 下阙清水记
|
| 內容試閱:
|
1
十二月二十七日。
零时,小雨。
世界是疯狂,人间是绝望。
路家,碎玻璃,血迹,以及撕烂的衣物布匹,路安琪瘫坐在走廊的镜头,衣服被自己撕扯得烂掉。右脚伸进了路海的卧室。她对动作和声音失去了一切敏感。我抽出她夹在手里的信,所有的字迹都被浸湿,寻不见蛛丝马迹。我终于知道她没有救回苏言,路海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心脏上插着一把水果刀。
空气里只剩下血液和眼泪的气味。上帝是一个蠢货。我哭泣的样子很不堪,肌肉扭曲,纠结在一起。像是一种昭示,昭示一切纷杂繁复而不堪的烟尘俗事。摊开掌心,手里一摊血迹。一块微不足道的碎玻璃,划出一道绝望出口,流淌出浓稠的血。
几个小时后之后我被带走,我回头望过去,路家的豪宅仿佛一座巨大的坟墓,住在里面只有死路一条。黑猫踩过我的脚,我的声音断裂。医生带走了安琪,警察带走了我,二十四小时之后,他们重新放了我。走出警局的那一刹那,我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这是灵魂最深处的感知,准确无误,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疑惑。我不具备思考生死福祸的能力,但是我终究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命何其脆弱。
我已经彻彻底底地失去了语言表述的能力,面对这个苍白荒谬的世界,唯一能做的是沉默和低头。周身的一切再与我无关,这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呆坐在路边,迎面的车来人往倏忽而混乱,一切都是木讷呆滞的。连氧气都变得浑浊,我呼吸困难。突然起风,扫起一地尘埃,沙子窜进了我的眼睛,闭上眼的一刹那,我看见迎面飞来的破碎报纸上一张极光的照片。
生活是一场盛大的决裂。
像极光一般,恢宏壮烈。
2
开始一个梦。
又是一个梦。
接着一个梦。
继续着另一个梦。
一直不停,整个人像虚脱了,像患了绝症。眼神呆滞,神色单调,身体以及灵魂都渐渐空掉,我总会看见那些支离破碎,头破血流,我开始害怕,害怕任何关于死亡的信息,旋律以及文字,表情以及手势。不能听音乐,不能写字,不能说话,不能出门,不能见光,不能闭眼。吃饼干,喝矿泉水。我终于让自己病倒,不想再起来。
脑浆崩裂的头颅、掉落的眼球、支离破碎的尸体、白衣、血迹、笑声、发、手指甲以及阳具、腐烂的猫狗、发臭的老鼠。坚硬的骷髅、滴血的横梁以及裂开的棺木,睁眼幻象,合眼梦魇,那些恐怖的意象决绝惨烈极端并且变态,像是经历着一场一场的轮回,满眼尽是生命最惨烈处的苦难与悲伤。
梦魇是一座迷城,一层一层,一圈一圈,走了进去,再也不能出来。没有了方向,纯粹地孤独,嚣张地惶恐。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得不到片刻的消停。让我身体觉得不适,梦醒之后会长久地呕吐,后来我开始害怕睡眠,开始长久地步行。走很长的夜路,直到天亮方才休止。
那些梦,一个一个,一幕一幕,一场一场。我决绝地与之疏离,我把身体和午夜给了它,却得不到回报,只带来内心的惶恐与不安。黑暗不可以再持续,绝不可以。
没有梦到过具体的人。比如森、苏言,以及路海。或者许诺、1223、娃娃以及叶小。只是无数个绚烂的人形影像带着惨烈的面容与身体的形状同我周旋。伸手不见,却可以摸到大片的绝望。那些景致长成一株一株的食人树,把我渐渐吞噬,将尸骨无存。我是个脆弱的人,终于开始疲惫憔悴,挣脱的欲望胜过一切。
想逃离。
永远地逃离。
出门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讨论流星雨。于是我也期望着可以目睹那些短暂生命的容貌,是辉煌还是落寞。一颗,两颗,三颗,许多颗,一闪而过,你就知道了生命的脆弱。我突然想起曾经写给一本杂志的一篇零碎的字。一个一个黑色的宋体字就像一句一句的诅咒,诅咒了世界,终得到恶报。
3
经常想到死亡的方式。时间的空白里有一些黑一些灰一些血色。亡魂、尸体、葬礼以及弥撒。极端,直接,颓废。充斥着胀破的力量和实感。会让你想到神灵与信徒、祭祀、坟墓、疾病、痛苦、发臭的水、凋谢的花、撕裂的布匹、赤裸的犯罪、废墟、老鼠、妖孽、救赎、十字架、刑具、白骨、屠杀、战争、历史、魔法、灵力、原罪、诅咒,还有爱情。
关于地铁、火车以及春暖花开。
地铁站里。很暖的温度。好看的光线。干净的地面与华丽的广告牌。拥挤的人群。老人、孩子、恋人。还有寂寞的人。以及病人。嗜爱成瘾的病人。你与我,都是左手半支烟荒废掉寂寞的人,都是沿着铁轨逆光行走的人。卧,只是一个姿势的勇气。心无所恋,你会这么说。春暖花开,面朝大海。
关于刃、浴室里的水以及绽放。
九把诡异的刀,漂亮,耀眼,锋利,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故事里面有血迹。大片大片殷红的血。像桃花、牡丹、红莲,妖冶绽放。有触摸皮肤的习惯。很暖很软很安稳,我们都爱。想起一个女人。《告别薇安》里那个叫作“乔”的女子。割破手腕,躺进浴缸。水管里会不会有血在滴落?一声一声,直入心脾,肮脏,刃,划破了伤痛的堕落。然后,一声叹息。
关于天台以及飞。
站得高一点,再高一点。漠视脚下的险恶与苦难。他的前世是飞鸟,无脚。街角还有人在拥抱。楼下的孩子哭声那么纯澈。男人女人眼神里的歇斯底里仍在蔓延。蔓延出一片苍白。与你无关。没有翅膀,一样地飞翔。他这么想。《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的唱腔那么辽远,把几万公里之外的爱辐射。穿越透彻。蝴蝶沧海,终难成爱。他依旧是个美丽的男子。
都死绝,终。
我给它取名:《死亡花》。
4
我开始执意地相信,人死之前,那21克的灵魂会出窍,变成一朵死亡花,然后身体伸出手把它抓住,双手合十把它夹在手心,揉碎,再吞噬。最后身体死去。这是一个完整的死亡过程,像是一道工艺,讲究时间火候与姿态,一切都要恰到好处。死亡是一件程序不可错乱的事,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上帝设置得紧凑而严密。
所有人都遵循并且对此无望。
天空闪过一道电,刹那大雨倾盆,我呆坐在那片枯死的草地上,任凭大雨冲刷。草地上的泥土瞬间变得泥泞不堪,黏附在衣服上,终于,我的身体在泥浆中被透彻地浸染,泥浆里混杂着一些清新的气味,往身体里钻,接上最轻灵的地气,人也变得通明冷清。很久很久以后,雨水渐止,悲伤开到荼蘼,然后止住,自己开始渐渐可以站立,然后走路。
去医院探望了安琪。
医生说她患上严重的癔症。女子太透彻。透彻的结局是,病掉。癔症的表现很多,有各种各样的躯体功能障碍,意识范围缩小、精神爆发朦胧仪式状态、交替人格、童样痴呆或者选择性遗忘等精神症状。医生说,这个女子很幸运,她只是患上了选择性遗忘症。选择性遗忘,她的内心会有趋向光的选择倾向,这是种福气。
我在玻璃房外望着她。她呆坐在窗子前,一言不发,仰着头望天,像是在寻找着什么。我的心里有些难过,渐渐汹涌。她看上去是那么安静,那么淡定,那么温婉和祥和。我为她祷告,祈祷她一直忘下去,再不要想起,人若是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把美好筑造然后延续下去也未尝不好,即便被她丢掉的记忆连带着我,即便她再也不认得我。
她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都是天然,都是美好。柔软透明的小溪、光净的鹅卵石、浣纱女子、桥头茕茕孑立的男子。清蓝的海,古旧的渔船,纯朴的妇人靠在憨实男人的肩头。苍茫的山,大片的常绿阔叶树,山里有歌者,以及水边干净的舞蹈动作。青草、花树、孩童、微笑、阳光、清风,轻盈的姿态与安静的面容。
而之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都不会再有。时光在流逝,天空有青鸟。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再为安琪做什么。我只能祝愿她好,但愿,一切可以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安静下来,一直下去。
但愿。
5
腊月二十二。
一阵敲锣打鼓声把我惊醒,拉开窗帘,村里的一户人家举行婚嫁仪式。门支开一条缝,蹿进一团毛茸茸。那只波斯猫,它重新回到身边。它望着我,望着望着,我再一次难过。走出门,日光刺目,缓缓睁开眼,门前的腊梅绽出许多红。
今年,我要回家过年。
下阙,清水记。
36静花
1
D城。旧貌换新颜。
我可以想象得出我不在的那些日子里,它定当像一个巨大的工地。不休不止地更换着看上去更有名堂的房子与马路。即使不适合人居住,但终究也是某种时代意义上的进步。看着也不觉得有太多不妥。内里依旧淳朴。
我没有通知父亲和母亲,期望着我的出现会是个惊喜,家里一直住老房子,好几十年的历史。原来一个丝织单位的员工宿舍区,现在看来更像是一个四合院,不过倒也朴素恬淡,生活终究还是平实一点,人才觉得坦荡。
进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在缝制被褥。我就站在门口一动没动,看了母亲好久。她看上去那么瘦小那么纤弱,只是不会有人知道她曾经历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纠结与伤痛。母亲老了,真的老了。也许,有一天当我年岁长到与父母相仿的时候,这些将成为旧事的过往可以看得淡些,那些悲伤也不再那么让人撕心裂肺。
突然我感觉身后有人盯着我。
回头望去,父亲夹着一份刚买的报纸站在院子里。他是英俊的,纵使年岁苍老,也掩饰不了他年少时俊朗的轮廓。恍然觉得自己明白了时间的意义。时光里,无非是人在一场一场的悲喜里苍老了轮廓,散尽了风华,时光消耗得总是太多,太深刻。三木。父亲轻唤我的那一刻,母亲陡然转过身体。一刹那,泪流满面,我终于深刻地明白了自己的罪孽深重。
我在风华正茂里让苍老的人更加苍老。
母亲说,她正在为我缝制这床被褥。她说天冷了她的儿子需要一些温暖。说着说着,我们一起再次淌下了眼泪。我放下简单的行李,从背包里放出了小森。父亲和母亲看见小家伙都异常地欢喜,它似乎也深爱着这里。猫一直是最有灵气和通人性的动物,所以我把这只陪伴我很长的时间的小家伙带回了家,留给父亲和母亲。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父亲买回一个生日蛋糕。
我问是谁过生日。
父亲说:我们全家。
2
这个年对我来说刻骨铭心。
从小,跟父亲母亲一直不亲密,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是我童年的全部记忆,所以想来有些疏离也是情理之中。只是毕竟年岁渐长,太过执着,终究不是一件幸事。终究,我还是深爱着他们。年夜饭吃得温暖而欣慰,一家三口人,从未有过此时的融洽祥和。看上去,像是上帝一次不经意的恩惠,我仍旧充满感激。
大年初一的时候,问候杂志的编辑。她是个清新文静的女子。我说,如今,我的生活空掉了,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过气的演员,剧本没有完戏却快结束了。她邀请我去实习,我说再等等吧,我无法怀揣一颗没有痊愈的心与思考的能力去做一本杂志,那样我觉得有些不妥。
晚上接到电话。
安琪的号码。
一刹那,整个人像是被神秘的点穴术点住了身子,甚至连思维也都不能运转。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我们学校医学院的学生,去年毕业分配在安琪现在所在的医院工作。他问我记不记得他。我说,怎么,难道我们见过?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那个曾经我在路上撞见的被安琪甩过一个耳光的英俊男子,很久远的事了。
他说,他一直关注着这个曾经冷若冰霜的女子。爱一个人,有时候会盲目执着到匪夷所思。他爱她,一如既往。即使被她甩过若干次耳光,他仍旧爱着她,不能自拔。
他申请了辞职,准备去丽江或者某个偏远宁静的地方开一家诊所挣取一些生活的费用,尽管他的家世显赫。我问他安琪怎么回应。他告诉我,安琪现在忘记了所有该忘掉的事。真的变了。当他向安琪再次袒露心意的时候,安琪竟然红了脸,像是一朵初绽的含羞草。这是不可以不去动容的一件美好无比的情事。
我说,男子,谢谢。
人是要时刻铭记恩惠并懂得感恩的。
3
那天,陪同父亲和母亲逛了街。他们看上去是幸福的,而他们始终不能知道我内心深处的难当痛楚。那些破裂的事像毒药一样渗进了我的骨髓,每一次行动,都会激活一切的曾经,时刻警醒着自己不得已地温习着悲伤,无论你情愿与否。这是一种规则,谁也无法成为特例,尤其是我。
父亲谈起今日他出租车的生意,他说,他遇到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富商。他们无意中聊起到子女,然后那男人说他一对儿女都在N城读大学,一个在N大,一个在H大,过年都没有回家,心里满是牵挂。母亲问,那男人叫什么。我知道,这些对话多么家常,没有做任何接受信息的准备,只是彼此循着一些线索拉近心上的距离,但是我听见父亲说:
那男人叫苏堇生。
我终于没有忍住,蹲下,把脸深深埋下。一颗一颗的眼泪滴在裤脚上,仿佛那些眼泪要拼命地流到地面渗进土里,去帮我寻觅那些潮湿却终究完全的曾经。父亲走过来不说话。搭着我的肩膀说,流泪之后男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是渴望他们来询问我缘由的,只是他们都太过明朗,什么也不会多过问,只是单纯地希望我可以变得好,更好。
这样的场面我无力自持。只是,我的内心终有信仰。我预知得到,安稳静默才是内心最终的真相。就像我一直相信着莲花开放时可以绽放出声响。我仰起头看天,对着星辰祈祷。我只是希望自己可以明朗些,放开些,静默些。
4
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又匆匆赶回N城。因为房租到期,房东要收回屋子,说自己将回到这间陈旧的小屋,因为他的妻子怀孕了,他需要这间僻静的屋子给妻子休养。是个善良体贴的男子,觉得珍贵,于是,我辗转回N城。
回到小屋的时候天上开始下起微弱的雪。推开门,刹那就觉得屋子里的东西跟自己有了莫可名状的疏远,除了那件衬衫。晚上我穿上那件衬衫躺在床上,点上了一支烟,失眠,然后开始回忆这近四年里困扰我至形影不离的梦境,反复纠结没有终了的景致。
回忆,就像是一场阅读,无可悔改。
一幕。
那棵树,一寸高,墨蓝的颜色嵌入瞳孔最深处,像针扎,望得久了眼目会剧烈地疼痛。那树长在一个巨大并且空荡的房间里,推门走进去你不注意便会踩死了它。它就长在门与地面之间的空隙里。我不知道怎么走进这样一个场子,经常来到这里,便真以为这是块熟悉的地。我没有那样细致的心思去发现这样微小的作品。我只是推开门就下意识地蹲下来看见了它并一直盯着它,像是受到了某些未明力量的指使。
我伸出手去摸它,然后它一刹那从中间裂开,碎裂成两半。一半飞出了窗外,一半钻进了我的身体。身体没有发生变化,我却撕心裂肺地疼痛。我觉得它就要在我的体内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撑破我的身体,从我的皮肤头发指甲里迸出。我觉得自己快要变成一只怪物,我终于害怕得哭出声了,可是,没有人回应,一直哭,哭到醒。
看过去,我还是个孩子。
二幕。
一枚蝴蝶标本,褐色的蝶,美丽却诡异。死去了依旧栩栩如生,仿佛不经意间她就会扇动翅膀跃然纸上。我盯着它。天开始下雨,下雨的时候就像天空和大地在做爱。雨水灌进我的嘴巴以及鼻腔里,呼吸困难。总是望见前面有沼泽,一具一具身体往下陷。想停下却已经不能自控,仿佛投奔一场看得见的自杀。终于,当我再不能动弹身体而下陷的时候,那只硕大的褐色蝴蝶瞬间消失,仿佛只是一场幻觉。
它像个胎记。
而我已经没有退路,唯有等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