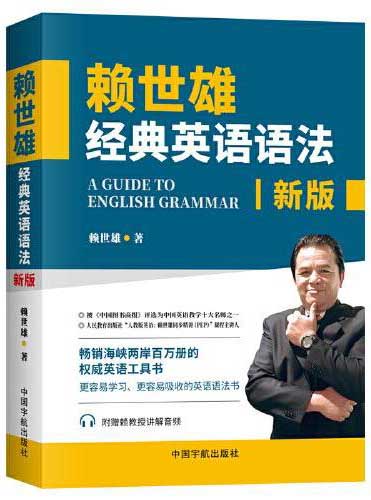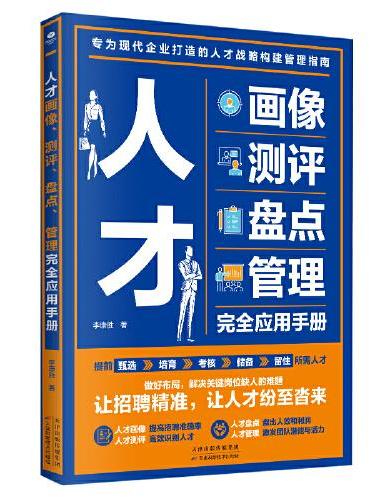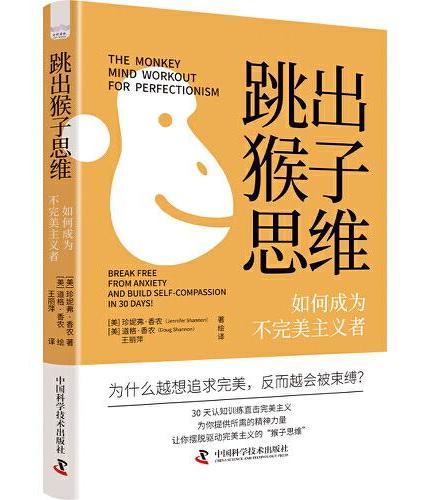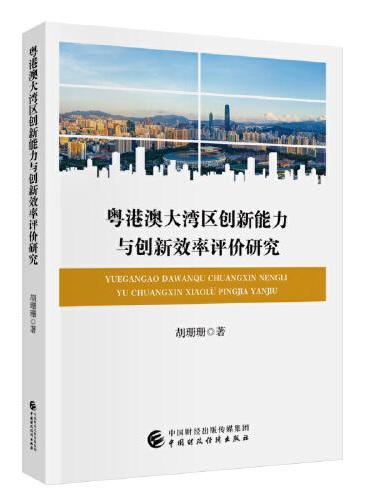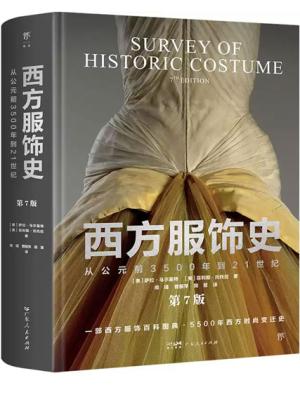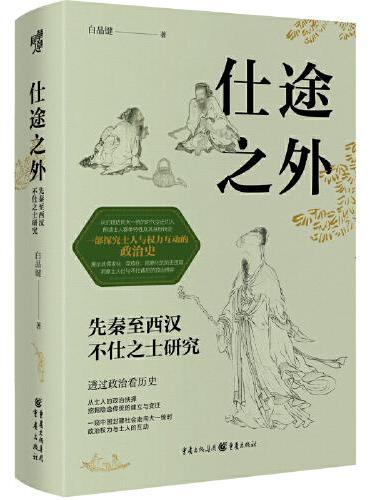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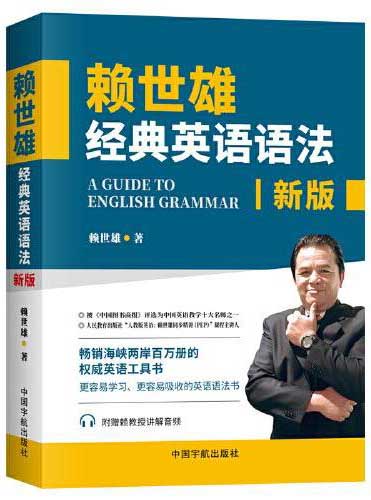
《
赖世雄经典英语语法:2025全新修订版(赖老师经典外语教材,老版《赖氏经典英语语法》超32000条读者好评!)
》
售價:NT$
305.0

《
影神图 精装版
》
售價:NT$
653.0

《
不止于判断:判断与决策学的发展史、方法学及判断理论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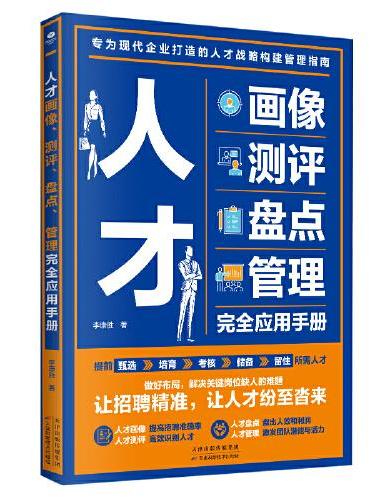
《
人才画像、测评、盘点、管理完全应用手册
》
售價:NT$
2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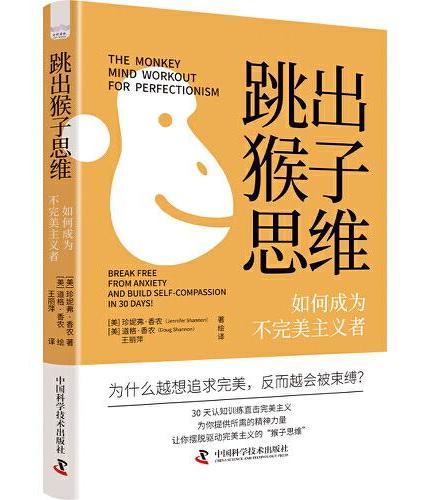
《
跳出猴子思维:如何成为不完美主义者(30天认知训练打破完美主义的困扰!实现从思维到行为的全面改变!)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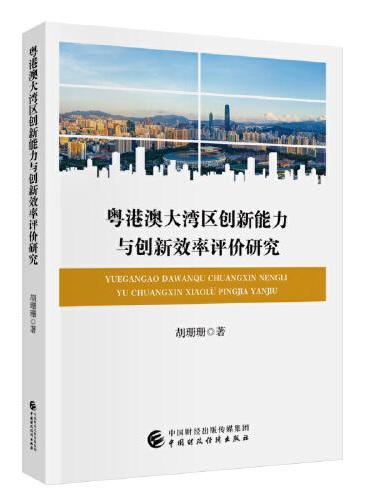
《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与创新效率评价研究
》
售價:NT$
3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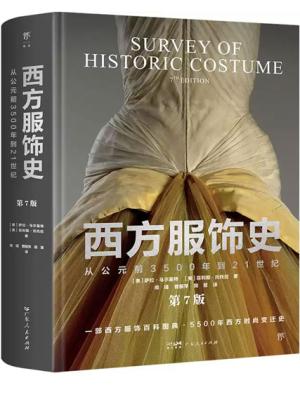
《
西方服饰史:从公元前3500年到21世纪(第7版,一部西方服饰百科图典。5500年时尚变迁史,装帧典雅,收藏珍品)
》
售價:NT$
20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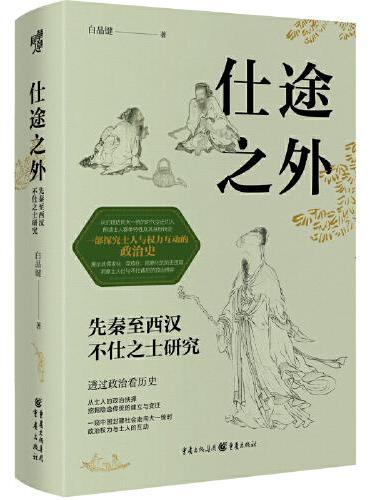
《
仕途之外:先秦至西汉不仕之士研究
》
售價:NT$
305.0
|
| 內容簡介: |
只有当我们看到陶渊明是多么深刻地植根于文学和文化传统,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他对传统的革新。手抄本文化的世界变动不居,而这种流动本质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尚未得到正确的理解或重视。我们将会发现,陶渊明的诗歌文本,即使在诗人逝世之后,仍被后人不断地生产和创造。传统意义上那个“真正的陶渊明”,只是陶渊明众多可能的形象之一。
——田晓菲
“校书如拂尘,旋拂旋生”,“尘几”是对校勘与编辑的完美比喻,也象征着我们对嘈杂无序的手抄本世界的云游。本书为田晓菲的学术成名作,旨在探讨读者如何积极主动地参与对“陶渊明”的生产和创造,从而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形象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通过检视文本传播的机制与历史,作者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文本的流动性,以及手抄本时代的文本如何因为后代的需要而被重新建构和变形。
|
| 關於作者: |
|
田晓菲,1971年生于哈尔滨,在天津长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哈佛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文学和文化、书籍史及比较文学。著有《秋水堂论金瓶梅》(2003)、《“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2004)、《赭城》(2006)、《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2007)、《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2011)、《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2021)等。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合编《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 年—公元900 年)》并执笔其中部分章节。2012 年度获哈佛大学卡波特奖。
|
| 目錄:
|
引 言
杜诗与韦氏妓: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求真”的误区
生尘的几案
章 得失之间
见山与望山
有人夜半持山去
得与失
乱 曰
第二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正名:五柳先生与六朝隐逸话语
重构五柳先生:传记四种
第三章 失去的田园:归陶
不受欢迎的植物
“颇为老农”
饮食与文字
第四章 饮食、死亡与叙事
得 仙
何有于名?
阅读到天黑
文化想象的版图和燃烧的文字
第五章 成 器
中空的羞耻
荣 木
清算与盘点
紫葵的悲哀
无 成
第六章 实/ 石证
栗 里
场所与空间
“吐痕尚新”
石头记:一个关于文学的寓言
结 语
附录一 文本的历程
附录二 清醒的阐释:《述酒》
附录三 陶诗选评
引用书目
中文版后记
|
| 內容試閱:
|
杜诗与韦氏妓: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因为传播媒介——纸张——的脆弱易毁,中国的早期手抄本大多已经绝迹了。唐与五代保留在敦煌的抄本,因为干燥的沙漠气候和偏远的地理位置而得以幸存,是十分特殊的例子(此外,还有少数存于日本、韩国的唐写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同时代的文字记载里,一瞥手抄本发生变化的过程,从而认识到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本质。在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作者本人发现他的作品被抄写流传之后变得几乎无法辨认,另一个例子则讲
述一个女子如何补订她负责抄写的文本。
先让我们看看个例子。唐代诗僧贯休为他的一组《山居诗》写下这样的序言:
愚咸通(860—874)四五年中,于钟陵作山居诗二十四章。放笔,稿被人将去。厥后或有散书于屋壁,或吟咏于人口,一首两首,时或闻之,皆多字句舛错。洎乾符辛丑岁,避寇于山寺,偶全获其本:风调野俗,格力低浊,岂可闻于大雅君子?一日抽毫改之。或留之、除之、修之、补之。却成二十四首。亦斐然也。
贯休的序言使我们看到,这些诗篇好像诗人的后代,刚一出生就被带走,直到长成之后才回到父母身边,而父母几乎认不出来这就是他们的儿女。诗人对自己的作品完全失控:当他看到和听到自己的诗句时,他发现它们充满了“舛错”;只有依靠偶然的机会,原作者才得以“全获其本”。
贯休遇到的情况在手抄本文化中是常见的现象。据《北史》记载,公元六世纪中叶,阳俊之曾经“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这位阳俊之是北朝著名文人阳休之(509—582)的弟弟;阳休之不是别人,正是陶渊明文集早的编辑者之一。在这则故事里,我们再次看到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失去控制。只不过阳俊之因为被书贩子当成了“古之贤人”而感到万分高兴,所以,他很可能终没有修改写本中的谬误。
即使我们退一步说,抄手总是可以准确无误地抄写文本(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还是不能保证流传到后世的文本的权威性。在南北朝时期,文本流传的速度可以非常快。陶渊明同时代的诗人谢灵运(385—433)享有盛名,“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陶渊明死后一百余年,梁朝诗人刘孝绰(481—539)的诗文为当世取则,据《梁书》记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者后来对自己的诗文加以修订,则自然成为异文产生的又一契机。在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西塞罗曾把《论道德目的》的初稿借给朋友阅读,当得知文稿被朋友抄写了一份之后,西塞罗十分担心“抄本会广为流传,取代后的定本”。可知在手抄本文化中,这是一种常常发生的情形,举世皆然。
我们从贯休的序言里得知,文本在离开作者之后会经历意想不到的变化,那么随后而来的问题就是: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九世纪作家高彦休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出身世家、进士及第的韦公子,“尝纳妓于洛”。她年仅十六,“颜色明华,尤善音律”,但让韦公子心动的地方,是她的“慧心巧思”:“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能够随笔铅正杜诗抄本中的“舛缺”,的确需要慧心巧思,不过,令现代读者惊异的,恐怕不仅仅是少女的聪明,还是她随笔铅正杜诗文本的自信,更是韦公子和故事的叙述者对此所持的态度:他们似乎都觉得修补和改正一部舛缺的文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一部如是订正过的杜诗抄本也显然并不减少它的价值。这第二个例子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一个中世纪的读者,在对待他或她阅读的文本时,和一个现代读者是多么不同。
对现代读者来说,理解这种差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习惯了印刷书籍的稳定不变,习惯于权威性版本、版权以及“知识产权”的概念。在现代社会,我们仍然可以被我们阅读的书籍所改变,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改变我们阅读的书籍。在抄本时代,一个抄写者作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可以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哪怕这作品属于杜甫,中国伟大的诗人之一。而且,这个抄写者可以是任何性别、年龄和社会背景的人:职业抄手、显赫的文人、世家子弟、读书识字然而学问不算渊博的一般平民,或者,多才多艺的妓女。抄写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他或她抄写一部文本,可以是为了谋生,为了对诗歌的爱好,或者为了爱情。这些人以其抄写、编辑、改动、修饰、补缺等种种活动,参与了手抄本的创造。他们的参与极为主动、活跃,因此我们不能再把这种参与描述为读者对某一固定文本的被动接受,而必须视之为读者对一个从根本上来说变动不居的文本积极主动的创造。在这样一种模式里,“作者”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在其作品里,“作者”已经不再占据稳定、权威的中心地位,不再是一个全能的、控制和掌握了一切的存在。
在一篇题为《宋代中国书籍文化和文本传播》的长文中,美国学者车淑珊(Susan Cherniack)探讨了宋朝文本随着印刷文化的崛起而产生的流动性。她认为,印刷文本中的错误对读者产生的影响较手抄本更为广泛,因为“任何一个抄本中的错误都会限制在相对比较小的读者圈子里”。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同一版的印刷书籍全都一模一样,印刷可以限制异文数量的产生;与此相比,每一份抄本都是独一无二的,都可能产生新的异文,这样一来,比起印刷文本,手抄本就会大大增加异文的总数。
我们从韦氏妓的故事里得知,异文并不都是抄写者无心的错误,而完全可能是有意的改动,是对文本自觉地进行编辑整理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北宋编辑们在准备印刷一部书籍时所做的事情。他们面对的,往往不只是一份抄本,而是同一文集的许多份不同的抄本。他们必须从众多异文中进行选择。有时,他们还得处理纸本和金石文献的不同。欧阳修校正的《韩愈文集》被公认为善本,但是,当他后来把集中韩文和碑刻进行比较时,还是发现了很多差异。欧阳修不由感叹道:“乃知文字之传,久而转失其真者多矣。”
北宋的学者、编者、校勘者,继承了唐代手抄本文化巨大、分散、混乱的遗产。也许,正因为印刷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人们有史以来次对手抄本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强烈的关怀。这告诉我们,物质文化和技术的发展会反过来影响人们感受认知世界的方式。叶梦得(1077—1148)的《避暑录话》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中书酷爱杜诗,“每令书史取其诗稿示客,有不解意以录本至者,必嗔目怒叱曰:‘何不将我真本来!’”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不知道“真本”到底如何不同于“录本”:虽然号称“真本”,它不太可能是杜甫的手稿,那么,它是不是一份从唐代流传下来的手抄本,而“录本”只是这位中书自己抄录或倩人抄录的副本呢?无论如何,这一故事反映出人们对所谓“真本”的强烈意识和追求,而这样的态度在宋朝以前则是很少见的。校勘,这一历来十分重要的活动,现在变得格外充满紧迫感。在的情况下,校对精良的善本书甚至可以影响房地产的价钱。朱弁(?—1144)在《曲洧旧闻》里记载过这样一则逸事:宋敏求(1019—1079)家的藏书往往校过四五遍以上,爱好读书的士大夫为了借书方便,纷纷迁居到宋家所在的春明坊,春明坊地带的房价由此大增。
前面说过,当陶渊明还在世时,他的诗歌已经在其朋友圈子里流传。陶集中有很多诗篇,或为赠答,或为同赋。陶渊明在《饮酒》诗序中说,他写的诗,曾经“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在手抄本时代,文本的保存完全建立在抄写的基础上,因此,抄写的意义,实在远远超出了“以为欢笑”的范围:文本只有被人抄写才能流传,流传越广泛,得以存留到后世的机会也就越大。
北宋初年, 存在着大量陶集抄本。据宋庠(996—1066)“私记”:“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同。”宋庠又说:“余前后所得本仅数十家,卒不知何者为是。”一个“仅”字,向我们显示了陶集抄本行世之众多;“卒不知何者为是”,则表明这些抄本各各不同。蔡居厚(一名启,字宽夫,1109 年左右在世)也说:“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
选择“正确”的异文,是一项使北宋学者非常头痛的任务。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处理手抄本文化留下的庞大而令人困惑的遗产。柳开(947—1000)是一位大刀阔斧型的编辑,他在校订韩愈文集时,改动了五千七百多字。陶渊明的作品,就像所有的宋前文学作品一样,是经过了北宋文学价值观念的中介而流传下来的。理解宋人的“编辑方针”,对于我们理解陶诗至关重要,因为陶诗具有欺骗性的“单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北宋编校者的施为。
对于后代编校者来说,宋人的编辑措施常常显得过于主观。据苏轼说,杜诗“白鸥没浩荡” 的“没”字被宋敏求改为“波”字,因为宋敏求认为白鸥不会“没”于波浪。又据十二世纪初期的《道山清话》记载,杜诗“天阙象纬逼”被王安石(1021—1086)直改为“天阅象纬
逼”,而黄庭坚(1045—1105)“对众极言其是”。蔡居厚曾经比较王洙(字原叔,997—1057)和王安石对杜诗的不同编辑策略:“今世所传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辞有两出者,多并存于注,不敢彻去。至王荆公为《百家诗选》,始参考择其善者定归一辞。”在举例说明之后,蔡居厚告诉我们:“若此之类,不可概举。其采择之当,亦固可见矣。”
我们要知道,这些大胆的编辑,诸如柳开、宋敏求、王安石,对手抄本进行的改动,并非孤立的例子,而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和韦氏妓并无本质区别。至于他们的“铅正”究竟基于什么样的编辑方针,这样的编辑方针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