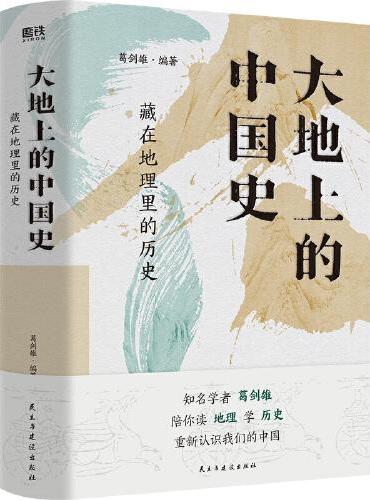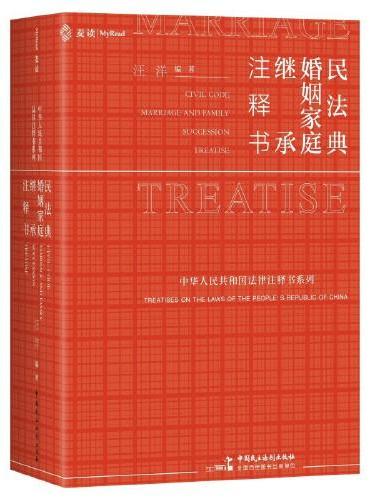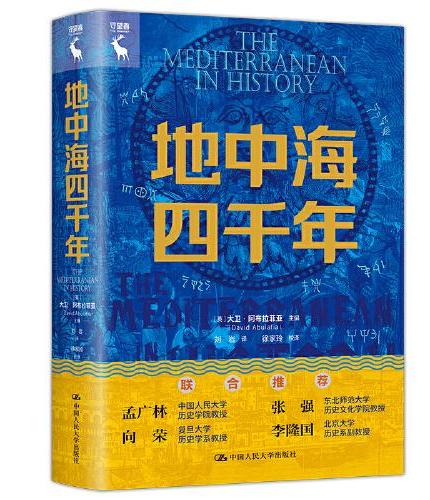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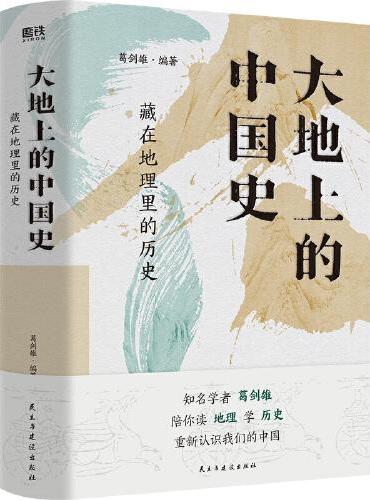
《
大地上的中国史:藏在地理里的历史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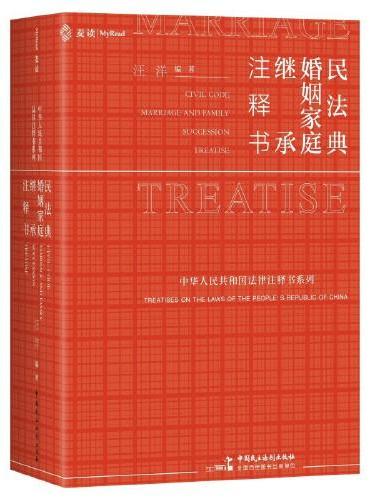
《
《民法典·婚姻家庭继承注释书》(家事法专用小红书,一书尽揽现行有效办案依据:条文释义+相关立法+行政法规+地方立法+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地方法院规范+权威案例,麦读法律54)
》
售價:NT$
6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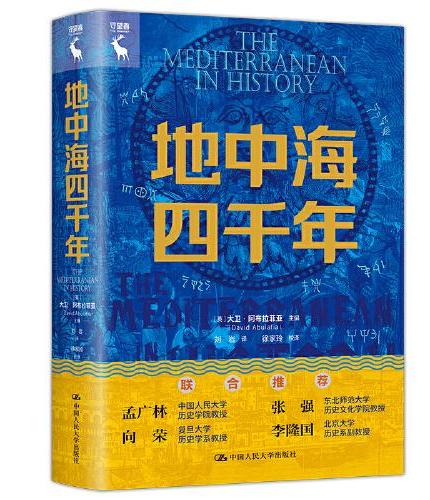
《
地中海四千年
》
售價:NT$
857.0

《
君子至交:丁聪、萧乾、茅盾等与荒芜通信札记
》
售價:NT$
316.0

《
日和·缝纫机与金鱼
》
售價:NT$
194.0

《
金手铐(讲述海外留学群体面临的困境与挣扎、收获与失去)
》
售價:NT$
347.0

《
五谷杂粮养全家 正版书籍养生配方大全饮食健康营养食品药膳食谱养生食疗杂粮搭配减糖饮食书百病食疗家庭中医养生药膳入门书籍
》
售價:NT$
254.0

《
七种模式成就卓越班组:升级版
》
售價:NT$
296.0
|
| 編輯推薦: |
1.这是一部关于爱、失落的纯真以及奋斗的小说。它是对马耳他女性生命的赞颂,展现了她们的坚韧和紧密的家庭纽带。
2.第一本引进中国的马耳他小说,涵盖其不同历史阶段:被殖民、战争和移民热潮。
3.一本女性家族史,是女人在不同时代的艰难求生塑造了我们的历史。
4.girl‘s power的充分彰显,girls help girls的绝佳典范。
|
| 內容簡介: |
这是一个关于外婆的外婆的故事——一部女性家族史。一个马耳他家族五代女性逐一登场,时间横跨一个世纪,地点则涉及马耳他、纽约、悉尼和墨尔本多地。她们在乱世中谋生,凭一己之力养育孩子,被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捉弄,与无情的世界抗争,与自身的欲望缠斗,甜品店既是她们奋斗的地方,也庇护着所有人。
古迪塔、利西娅、弗朗西丝、克莱尔、达芙妮,她们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度遭遇着截然不同的磨难,但女性特有的品质让她们忍受、适应、生存和相互关怀。最终,最小的女孩重返马耳他,把曾经中断的故事继续讲下去,那里有马耳他特有的连帽斗篷“法尔代塔”、公用烤炉“沙瓦”、吊床摇篮“本涅娜”、黑色妖怪“巴巴妖”……
|
| 關於作者: |
卢·德罗菲尼科,1941年出生于马耳他,现居住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获得了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多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担任过各种职位。
她的小说和短篇小说探讨了马耳他人的移民问题,特别是妇女移民、移民创伤、长期流亡以及对移居国家日益增长的热爱。她的小说在澳大利亚和马耳他均荣获多种奖项。
除了写作,卢对有机种植很有热情,她很爱自己的花园,在那里种植了各种花卉、水果和蔬菜。卢有四个子女和七个孙辈。
|
| 目錄:
|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135
第三部 215
致谢 244
译后记 245
|
| 內容試閱:
|
译后记
最初被这本书吸引,因为这是一本关于外婆的外婆的故事 —— 一部女性家族史。女性在乱世中谋生,凭一己之力养育孩子,被命运一而再、再而三的捉弄,与无情的世界抗争,与自身的欲望缠斗,这不正是我一直想写的故事吗?
一个家族五代女性逐一登场,场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地中海孤岛马耳他,切换到二十一世纪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一个家族的百年写出了两个世界的感觉。
母系的寻根比父系的寻根要难,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族谱中对女性的记录都少之又少。女性出嫁以后,地址变了,姓氏变了,朋友圈也变了,经过一些年月,要寻找她生命的足迹就变得十分困难。一生仿佛被砍成了两截,难怪乎,女人结婚也被称为二次投胎。
结婚生子的女性,隐在男性身后,主要角色就是妻子母亲,一辈子像陀螺一样,忙碌不休,却始终原地旋转,似乎也就失去了著书立传的必要。小说中的前三代女性,因为各种不幸失去了配偶,却也正是在这种男性缺席的情况下,女性反倒显现出了她们身为独立个体的价值。
限制女性发展的力量何其之多,父权、夫权、宗教、世俗,甚至子女。但和其他禁锢不同的是,孩子在母亲身上激发的能量远大于消耗的能量。就拿我自己来说,生孩子以前,想象中的自己有着无限的可能,生孩子以后才发现,自己能做到的,远比想象中的更多。
本书作者卢?德罗菲尼科是一名女性,也是一位移民。对于移民而言,母国的文化历史是他们的根,寻根几乎是一种本能。她的小说建立在广泛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在书中详细描绘了自己的故乡——有“地中海心脏”之称的马耳他,百年前寻常人家的住宅、饮食、服饰、民俗。连帽斗篷“法尔代塔”、公用烤炉“沙瓦”、 吊床摇篮“本涅娜”、黑色妖怪“巴巴妖”,正是这些细节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
书中引用了一些马耳他语词汇,这是一种起源于阿拉伯语,又杂糅了意大利语、法语和英语的语言,现今大约只有几十万人仍在使用这种语言。为了翻译这些马耳他语,我旁逸斜出地读了一些有趣的资料。
比如书中提到的连帽斗篷“法尔代塔”,又名“贡内拉”,是马耳他独有的服装,在马耳他流行了好几百年,现在已几近绝迹。它由棉布或者丝绸制成,长度一般过膝,帽檐由藤条或鲸骨撑起,行走时用手捏住衣襟,面部在帽檐的遮挡下时隐时现。旅行家、插画家威廉?亨利?巴特利特曾在1851年这样描写过它:能令丑女也变得迷人……如修女般庄重,却又俏皮妖娆……深邃的黑眼睛更显灵动。这不禁让我产生了“犹抱琵芭半遮面”的联想。
还有书中提到的马耳他经典小说《银十字架》,出版于1939年,我甚至刷到了几十年前据此拍摄的电视剧,一个富家小姐和穷小子的爱情悲剧。看着片头地中海的滔滔海水,不知怎的,脑海里却响起了《上海滩》的主题曲。
译完这本书再去地中海,看到路边咖啡店里神侃着的老人们,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却感觉已经认识他们很久了。
2022年4月
于瑞士
父亲的葬礼弥撒结束,古迪塔·瓦萨洛坠着颗沉重的心回家。她在前门站定,理了理门环上被风吹乱了的黑色蝴蝶结,从口袋里掏出把大钥匙,打开门,走进面包房。关上门,脱下黑色的法尔代塔连帽斗篷,把它的褶皱收拢,将衬有硬纸板的帽檐贴在胸前,她走过两个木桶、柜台和烤炉,眼中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到。打开通往后屋的门。在狭窄的走廊中她呼吸着清冷的空气,把法尔代塔斗篷挂在门后的钉子上,然后上楼走进自己的卧室。出于习惯,她关上了卧室的门。她的手拂过黑色的丧服,感受到自己紧实的胸部、小腹和大腿。她踢掉黑色的鞋,脱下黑色的连裤袜,除去黑色的衣裙。屋里的两面镜子都蒙上了床单,但她知道自己看上去一定糟透了。黑色吸走了她脸上所有的血色,而且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也将如此。她仰面躺在床上,衬裙遮着腿,双手十指交叉掩着腹部,她思绪万千,想弄明白过去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的父亲死在了意大利面和兔子肉之间。她就是这样告诉医生的,不用多做解释,医生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知道,就在她返身把兔子肉铺在炸土豆上的那一刻,她的父亲走了。他走得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当她托着两个盘子转回身,看到她的父亲脸朝下趴在桌子上时,她还在琢磨,他这是在搞什么鬼,他向来并不爱胡闹的。现在就这样躺着,她的目光扫过天花板——两根支撑着房顶石板的橡木梁,一块大雨过后就会出现的霉斑,一根黑色的蜘蛛丝,像吊床一样从一个角落悬到另一个角落,她本想打扫那里的。 现在古迪塔不得不想一想未来了。三十二岁依然未婚的她,可以想见的未来就是孤身一人在这面包房中辛苦劳作。当然她也可以结婚。但是,嫁给谁呢?她把村子这头每一条大街小巷在自己的脑子里捋了一遍。三个带着孩子的鳏夫,一个又聋又哑的掘墓人,一个年过半百的裁缝。当然她也可以请媒人。她还真认识几个,只是如果她让媒人进家门,她父亲一定会大怒。 “他已经死了。”她想,叹了口气。
虽然葬礼弥撒的时间很短,但还是耗尽了她的气力。神父没有讲关于死亡和救赎的长篇大论,这让寥寥几个参加葬礼的女人们松了一口气。 匆匆地画了十字,点头以示同情后,女人们就走了。古迪塔知道,自己的面包房一关门,她们就必须走去村子另一头买面包。现在父亲静静地躺在教堂下面的墓穴中,再也没法高声责骂,再也不会诅天咒地。现在这片屋檐下终于得以安宁,这个想法让她一阵内疚。她唯恐父亲的魂魄能够读取她的思想,而且还会用某种方式来惩罚她,于是她努力抹去记忆中父亲僵硬而愤怒的面容,并且努力搜寻他微笑的样子,但是一无所获。 “他不懂快乐,”她想,“同时还扼杀了我的那一份。”
她的朋友姬蒂说有种从天而降的欢乐,她何时体味过?姬蒂形容,快乐悄悄潜入身体,当它充盈全身时,她恨不得放声高歌,又或者站在屋顶飞向蓝色的苍穹。那样纯粹的快乐,古迪塔从未体验过,儿时不曾有过,成年后也未曾经历。为什么一切都是那样沉重不堪?为什么生活仿佛掏空了自己,她才三十二岁却感觉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还有什么可以指望吗?姬蒂描述的那种感觉,那种怀着期待心儿扬起小腹缩起的感受,她还会不会有?她还能快乐吗?父亲去世以来,她的眼角第一次落下一滴真正的眼泪,这滴泪并非为那些期待她悲伤的人们而流。更多的泪水涌了出来,她这才意识到,她不是在为父亲哭泣,而是为自己,为了那些在父亲钢铁意志的禁锢下逝去的年华。尽管害怕坟墓中的父亲仍能控制自己,但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呼声。 “他走了,你的生活可以自己做主了。” 是的,这屋子、这面包房都可以按照她的意愿来处置。她可以把一切都卖了,然后像早些年她父亲的亲戚们那样远走他乡,她可以去澳大利亚找她种甘蔗的叔叔,或者去纽约找她姑妈。不过她知道她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毕竟她的生活已经被细细密密地织入了这纠结的乡村生活。搬去其他地方,将切断她的生命线,这条将她和这房子拴在了一起的线,也是她生计和活力的来源。她知道她无法独自经营面包房,要搬沉重的面粉袋,要照看炉火,还要接待顾客,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和父亲一起工作仿佛照着剧本演戏。除非出了意外,比如烟囱堵了,面包房里满是令人窒息的烟雾,或者面粉有了霉味,又或者更糟,顾客拿着发霉的面包找了回来。正常情况下都是行云流水一般。父亲站在搅拌桶的一边,她站在另一边。他提起一袋重重的面粉,熟练地把部分面粉倒入搅拌桶,一勺也不会泼洒出来,他掏出一个坑,她把准备好的一壶温水注入其中。两人都预知对方接下来的动作。经过多年的练习,配合臻于完美。这一刻她看见他的脸,那不是时不时被愤怒扭曲了的脸,而是一张全神贯注的脸,他的眼睛盯着白色面团和他的双手——这双手就男人而言是小了些——轻轻拍打面团,仿佛那是个活物一般。现在终于,她为他感到悲伤,真心地为他哀悼。虽然与他相处不易,但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且把一切都教给了她,现在即便没有他,她也能经营这个面包房,并且以此为生。精疲力尽的她睡着了,脑海中最后的念头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愿意在她的面包房中干重活儿的人。
|
|